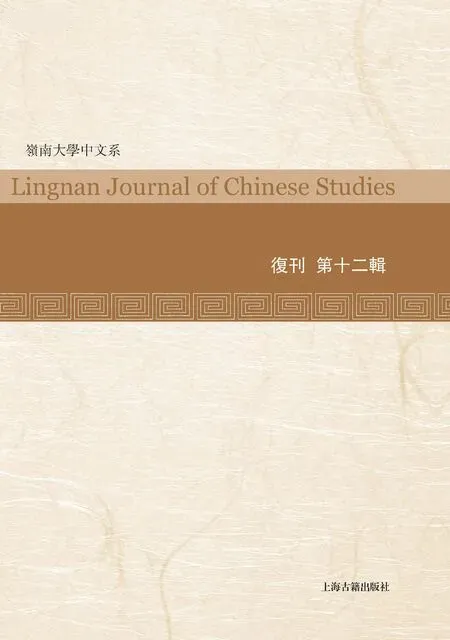杜亞泉的啟蒙理性與生態意識
——兼及生態時代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魯樞元
生態危機歸根結底是人類的文化危機。
在西方,是由啟蒙理念主導的現代文化走上極端之後的隱患發作;在東方以及大多發展國家則體現為這一現代文化與本土傳統文化的衝突與博弈。
縱觀近百年的世界歷史,源自歐洲的啟蒙理念在推動全球現代化的同時,也將環境災難與生態危機播及全世界。人類原本期待的福音,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變成噩夢。看似無關輕重的文化選擇與文化衝突,卻在不經意間決定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與後果。
中國,地球上這一龐大的生命共同體,在邁進現代化、全球化的大門時,原本是有過重大爭議與討論的。這些圍繞文化選向的論爭最終決定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去向,如今看來,所得所失已不難分辨。歷史不可能重新開始,人們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卻有益於對未來社會的想象與籌畫。
杜亞泉,是20世紀初中國最早展開的東西方文化論爭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本文試圖以他作為個案,對東西方文化的衝突與交流、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暴露出的某些偏頗與失誤略加闡述。
一、中國傳統社會啟蒙者杜亞泉
杜亞泉,生於1873年,卒於1933年,浙江紹興人,與梁啟超同庚,與蔡元培、秋瑾、魯迅同鄉。他16歲得中秀才,修習於杭州崇文書院,舊學根底深厚。甲午戰爭後,受時代大潮衝擊,以開啟民智、濟世強國為己任,奮發自學西方科學文化知識,並游歷東洋,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生理學、心理學、醫學以及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語言學諸領域均有所涉獵。他一生從事教育、編輯、出版事業,當年商務印書館編寫、出版的百餘種自然科學教科書,皆出自他之手。另有哲學專著《人生哲學》。由他引爆的20世紀初中國首場關於中西文化大論戰,即發生在他擔任《東方雜誌》主編期間。
1933年歲末,杜亞泉在上海寓所於貧病交集中去世,享年僅60歲。杜亞泉去世之後,胡愈之在悼詞中稱“先生實不失為中國啟蒙時期的一個典型學者”,他“没有替遺屬留下物質的遺產,卻已替社會留下無數精神的遺產”①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0、11頁。。他的商務印書館的後繼者在回憶文章中説,與他同代的知識份子都曾從杜亞泉編著的教科書中取得大量“啟蒙知識”。
在中國近現代,杜亞泉是一位繼容閎、嚴復之後,胡適、梁漱溟、張君勱之前的啟蒙思想家。他的啟蒙思想集中表現在“引進科學、開發民智、變革人心、改良社會”,尤其在“引進科學”、“變革人心”方面成績卓著。直到去世當年,他雖然疾病纏身,仍變賣家產,籌資編印《小學自然科詞書》,全書包羅了天文學、氣象學、物理學、化學、礦物學、地理學、生物學、衛生學、工程學,以及農業、森林、製造、建築、食品、攝影等二十多個門類的基礎知識,被胡愈之譽為“中國科學界的先驅”。就向國民普及科學知識、科學觀念的實績而言,在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中,應無出其右者。“就近代中國的知識更新和觀念進化而言,其影響尤為深遠,它不僅一般地滿足了世紀之初興學浪潮對自然科學教科書的迫切需要,而且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的知識結構,並進而推動新舊知識的更替和思想觀念的進化,對近代科學觀念的形成和科學精神的確立具有重大的啟蒙意義。”①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第196頁。
遺憾的是,杜亞泉,這樣一位富有實績的啟蒙思想家,在此後波瀾起伏的中國社會變革中竟然很快被忽略、被遺忘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史著作中看不到他的身影,即使論述中國近現代中西文化之爭的書中也很少提到他。
杜亞泉被埋没多年後再次“出土”,已是他去世60年之後、當代中國改革開放方興未艾之際,對此做出重大奉獻的是宣導“新啟蒙”的思想家王元化及史學家許紀霖。此後,在中國學術界曾引發一場不大不小的“杜亞泉熱”,1993年在杜亞泉的家鄉紹興上虞舉辦了紀念杜亞泉誕辰120周年全國學術研討會,接著相繼出版了《杜亞泉文選》、《杜亞泉文存》、《杜亞泉著作兩種》、杜亞泉評論集《一溪集》、《杜亞泉重要思想概覽》,同時發表了不少研究文章,並出版了浙江大學高力克教授研究杜亞泉思想的力作《調適的智慧》。
一個甲子過後,杜亞泉重現於中國思想界的視野,大多學者認可了王元化對他的定位:“他在胡適之前,首開以科學方法治學的風氣”,“他不僅是啟蒙者,也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他在東西文化之間“主張温和和漸進改革的理論”②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5頁。,寄望於“從傳統資源中發掘新舊調和觀點”以變革中國社會③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13頁。。
但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社會的進程基本上為激進革命派掌控,對於西方現代文化,力倡全盤接受;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從根本上取締。以政治革命取代社會改良成為時代大趨勢,已容不得任何“折中”、“調和”、“改良”、“漸進”思想的存在。因此,在“五四”運動前夕爆發的那場東西方文化論戰中,杜亞泉竟被革命陣營的主將陳獨秀斥為維護封建名教綱常的保守主義者、謀叛共和的反動分子①陳獨秀:《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頁。。十年過後,中國革命形勢趨於更加激烈,原先位於“左翼領袖”的陳獨秀已被視為“右傾”,本已經屬於“右翼”的杜亞泉自然就更加邊緣化。加上他慣常的那身長袍馬褂、秋帽布履的服飾,“時代落伍者”的頭銜儼然已被坐實。此後,在風急浪高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就再也見不到他的身影。
時過60年,中國學界重提杜亞泉並非簡單地為這位啟蒙學者恢復名譽,而是具有顯著現實意義的。王元化在通讀了杜亞泉當年留下的文字後竟發出如此感慨:我們現在思考的很多問題,他在八十年前就注意到了。
“五四”以來的近百年裏,事實一再證明,激進主義的革命思潮即使初心良苦,一旦失去多元因素的制約與抗衡,就注定陷入劇烈的錯謬之境。近百年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庸俗淺薄的社會進化論,包治百病的科學主義,獨尊一説的教條主義,粗暴武斷的鬥爭哲學通過形形色色政治運動的方式,不知給現代化進程中的中華民族帶來幾多挫折和災難。60年後在重新評價杜亞泉的不幸遭遇時,有學者以“萬山不許一溪奔”相喻,失去溪水滋潤的山川,只能淪為一片精神的荒漠。
歷史學家許紀霖認為“五四實際是一個多元的、各種現代性思潮相互衝突的啟蒙運動”②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495頁。,以杜亞泉和《東方雜誌》為代表的是“另一種啟蒙,一種温和的、中庸的啟蒙”,“激進的啟蒙與温和的啟蒙、轉化的模式與調適的模式,其複雜的關係和歷史功過究竟如何,可以進一步討論,但絶對不是一個進步與落後的機械思維可以概括。二者之間,並非啟蒙與反啟蒙的對立,而是啟蒙陣營中的分歧”③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497頁。。這使我想到同是法國啟蒙思想家的伏爾泰與盧梭,熱衷於政治鬥爭的陳獨秀神似伏爾泰,乃至羅伯斯庇爾;而杜亞泉則與謙和、清醒的盧梭擁有更多相似之處,他們都對如日中天的科學主義、專制主義保持沉著的批判態度。歷史最終證明,看似柔弱的盧梭比叱吒風雲的伏爾泰、羅伯斯庇爾更具生命力。據傳,歌德曾經做出過這樣的判斷:“伏爾泰標誌著舊世界的結束,盧梭代表了新世界的誕生。”④[法]亨利·古耶:《盧梭與伏爾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我們是否也可以套用一下歌德的句式:陳獨秀為埋葬舊世界燃起一把烈火,而杜亞泉則為尚未到來的新時代添加一抹晨曦。
這裏説的“新時代”,是指啟蒙運動、工業革命開創的“現代社會”之後的這個時代。人們往往把這個時代籠統地稱作“後現代”,我認定這應該是一個“生態時代”。單向度的,激進式的啟蒙理念正是釀成當今全球生態危機的源頭,而杜亞泉力倡的多元的、中庸的、調和的、統整的,接續的、漸進的啟蒙理念中,或許就已經包含了生態社會的因數。陳獨秀等人單向度的啟蒙者屬於他們自己身處的那個時代,是那個時代的弄潮兒;而杜亞泉以及與他類似的一些思想者,如比他晚生20年的梁漱溟,都有可能已經超越了他們身處的那個時代,成為他們身後那個時代的預言者。我希望沿著這一方向探討下去,以發現杜亞泉啟蒙理性中的生態意識與生態精神。
二、啟蒙思想家杜亞泉的生態意識
美國漢學家艾愷(Guy Salvatore Alitto)將啟蒙理性扼要地概括為六個字“擅理性,役自然”①[美]艾愷:《世界範圍内的反現代化思潮》,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頁。,“啟蒙理性”的集中體現即現代科學技術。啟蒙理性將人置於自然之外、之上,憑藉不斷發展的科學技術開發自然,役使自然,為自己源源不絶地獲取福利,長期以來已經對自然造成嚴重傷害,同時也破壞了人類自己生存的環境,污染了人類自己的心靈與精神世界,在地球上釀成日益嚴重的生態災難。
若是從以上視角看,啟蒙理性與生態精神似乎是完全對立的,甚至是敵對的。以塞亞·伯林(Isaian Berlin)在論及啟蒙時代那些傑出的、位居主流的思想家時指出:伏爾泰把哲學變成了解剖工具,狄德羅把社會生活視為“巨大的製作工廠”②[英]塞亞·伯林:《啟蒙的時代》,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9頁。,洛克把“心理”當作“被動的貯存器”③[英]塞亞·伯林:《啟蒙的時代》,第42頁。,18世紀的這些哲學家們試圖讓世界的一切事物都遵循牛頓的物理學定律,認定憑藉自然科學人們就能夠解決時代面臨的一切問題。
伯林在他的書中一再指出:“導致了18世紀思想中最光輝燦爛的洞見,同時也導致了敗壞這種洞見的重大謬誤,即以科學證明哲學。”①[英]塞亞·伯林:《啟蒙的時代》,第14頁。在伯林看來,18世紀這些思想家的“科學崇拜心理”儘管一時發揮了顯而易見的效用,歸根結底卻是“虚妄不實”的,並且隱埋下重大失誤。伯林在他的這本書中依次評點了洛克、伏爾泰、貝克萊、休漠、孔狄亞、哈曼諸多啟蒙思想家,卻没有提到大名鼎鼎的盧梭,或許,他也是把盧梭作為一個啟蒙思想界的“異類”對待的,盧梭的思想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另樹旗幟,在某種意義上預言了時代將釀成的那些謬誤。
中國的啟蒙者杜亞泉是否也是如此?
杜亞泉雖然博學多聞,熟悉當時的自然、人文諸多學科的理論知識,但從其現存的著作中未見他明確地講到生態學。他在其《人生哲學》一書中論及生物的發生與進化時曾提到的生物學家恩斯特·赫克爾(E·H·Haeckel,1834—1919),今譯海克爾,乃最初為“生態學”命名的生物學家②《杜亞泉著作兩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頁。。那時,即使在西方,生態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也僅剛剛出現。在《杜亞泉文存》中,杜亞泉曾兩處説到“生態”,一處為:“農作苦於某種害蟲,則為之演講某種蟲之生態及驅除之方。”③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335頁。另一處為:“一切生物,其機官之發達,生態之變遷,奚為本能之所發展,而非出於知能作用者。”④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176頁。這裏講到的“生態”,乃指生物體的“生存狀態”,與生態學研究的對象相關,但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生態學概念。儘管如此,從現代生態學的視野看來,我們仍然不難發現,較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主流啟蒙思想家,杜亞泉的著作中展現的生態觀念、生態意識、生態精神仍然是十分豐富與顯突的。
現代生態學是一門研究生物體與其生存環境之間交互關係、及生物體彼此間交互關係的學科。最初僅僅被局限於動物、植物界,直到20世紀中期,當生態災難已經釀成普遍危機時,生態學纔開始轉向人類社會及人類精神領域,被學術界稱作“生態學的人文轉向”。生態學的核心觀念是世界的整體性,人與自然萬物是一個有機整體,世界萬物之間存在著普遍聯繫與多元共生作用,並在不斷生發演替的過程中維護著生態系統的持續平衡。
對照上述生態學觀念,杜亞泉的生態意識、生態精神内涵表現在下邊諸多方面。
(一)杜亞泉認定人與其它生物同類共祖,相依相生,處於同一生存循環之中,更宜相親相愛。
吾嘗思物競之理矣,動物非食植物不生,人類非食動植物不生,則吾人之殘害動植物也亦太忍,而獨至人與人則雖日日肆其有形無形之競爭,而講群學者則必以愛其同類為鵠的。夫人與人之宜相親相愛,固亦天理所當然。但何以人與人宜相親相愛,而於動物植物,則待之若不必親愛而可殘暴也?以為人與人為同類共祖也,宜愛之親之也。則人為脊椎動物之一類,而他之脊椎動物即吾類也;人又為動物中之一類,則動物皆吾同類也;人為生物中之一類,則凡生物皆吾同類也。以為同類者亦不妨殘暴,則人與人亦不過同類也耳。親愛之宜也,則親愛亦無極;殘暴而可也,則殘暴亦無極。①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5頁。
杜亞泉的這段話發表在他主編的《普通學報》1901年第2期上,這時恩斯特·海克爾還健在,而生態學尚未成型。杜亞泉的這段話其實就已經道出生態學的核心觀念,世界上所有生物,包括人類在内都是一個有機整體,都存在於一個綿延不絶的系統之中。及至晚年,杜亞泉似乎對於生態學的原理有了更多的瞭解,在《人生哲學》一書中,不但花費許多筆墨闡述生物體與環境的關係,甚至還曾論及生物鏈中的碳循環:“没有植物的積貯,動物就没得消耗;但没有動物的消耗,空氣中碳氣缺乏,植物也就不能營同化作用。可見動植物是相依為命的。”②《杜亞泉著作兩種》,第21頁。同時,他對人類與自然萬物在同一個大的系統中循環演進也做出了更為確切的表述:“人類的生命,決不孤立於其它生命之外;一切生物,皆互相結合,同循此偉大的衝動而進行。動物立於植物之上,人類又立於一切動植之上,為共同進行的一大軍隊。”③《杜亞泉著作兩種》,第134頁。杜亞泉的這些論述看似常識,實則皆為生態學學科中的基本原則。
(二)杜亞泉特别強調宇宙間萬事萬物通過“調適”、“協同”達成的“統整性”,即多元的對立統一。
杜亞泉並不否認世界萬物之間存在著分化、對立與競爭,但他更看重的是分化、對立與競爭的各方通過“調適”達成“統整”,“宇宙進化之理法,為分化與統整”,“統整無止境,即進化之無止境也,此宇宙進化之大意也”①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50、51頁。。他否認“叢林法則”僅只一味的對立與競爭,而協力與合作纔是自然界的根本法則:“人類之趨向於協力,若男女之要求,若陰陽之相翕,終非人力所能抵抗。”②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21頁。只有將“生存競爭”與“生存協力”統一起來,纔能使事物進入平衡、和諧狀態。只有將“統整”作為最終目的,世界萬物,包括人類在内,纔能結成一個共存共榮的生命共同體。
而達成統整的途徑則是“中和”,扣其兩端,適當妥協,相互寬容,存異求同,行“中庸之道”。具體到某一社會問題,比如“進步黨”與“保守黨”,他認為各有利弊,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只有整合一體纔能正常行進③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141頁。。又如“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本處極端矛盾之地”,也並非不能“交互提攜”、“協同以進行”,“天下事理,絶非一種主義所能包涵盡淨”④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30頁。。
杜亞泉去世後,蔡元培在總結其一生行狀時指出:
先生既以科學的方法研求哲理,故週評審慎,力避偏宕,對於各種學説,往往執兩端而取其中,如唯物與唯心,個人與社會,歐化與國粹,國粹中之漢學與宋學,動機論與功利論,樂天觀與厭世觀,種種相對的主張,無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長而調和之;於倫理主義取普泛的完成主義,於人生觀取改善觀,皆其折衷的綜合的哲學見解也。先生之行己與處世,亦可以此推知之。⑤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第8頁。
蔡元培不僅是杜亞泉的同鄉、同事,更堪稱推心置腹的“知己”。
同是“異類啟蒙者”,與杜亞泉推崇“統整”相似,法國的盧梭看重的是“整全”(depature from wholeness)。盧梭的“整全”面對的是人類社會在“文明”與“自然”之間的悖逆與對立,“在一個被人類文明敗壞的墮落社會中如何可能保存天性,過上一種符合自然的生活”①[英]凱利:《盧梭的榜樣人生》,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頁。。杜亞泉與盧梭在求取人生與社會的和諧、完善上思路是一致的。
(三)杜亞泉對於“科學至上”、“科學萬能”、“科學救國”的審視與警惕。
在現代社會經濟體制下,“科學技術的進步”往往又催生出許多生態災難,因此“科學技術”本身常常受到質疑,類似的故事就曾發生在美國記者瑞秋·卡遜(Rachel Carson)的生態批評名著《寂靜的春天》裏。
清末民初,中國最早的一批傑出的啟蒙思想家幾乎衆口一詞地讚頌著“科學至上”、“科學萬能”、“科學救國”,而杜亞泉卻已清醒地注意到科學問題的複雜性、局限性。從現存資料看,杜亞泉對“科學主義”的審視並不像當代生態批評家那樣將矛頭指向由科學技術高速發展釀成的資源枯竭、大氣升温、環境污染等自然界的病變。因為在當時的中國,這些生態災難尚未呈現。杜亞泉對科學主義的警惕,仍然是從他的“統整”、“調適”觀念出發的。在他的心目中,人類世界是由物理、生理、倫理、心理諸多層面構成的有機整體,相互聯繫而又相互區别,不能相互取代,因而就不能指望單靠“科學”包治百病、解決人類面臨的所有問題。杜亞泉鄭重指出:
希望明白科學的,不要做“科學萬能”的迷想。世界事物,在現世科學的範圍以内者,不過一部分。科學家的責任,在把科學的範圍擴大起來。若説“世界事事物物都不能出了科學的範圍”,這句話,就是不明白科學的人所講。②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第147頁。
對此,學者高立克評述到:“杜亞泉的科學觀中貫穿著一種承認科學和人類知識能力之有限性的‘理智的謙虚’,而與五四流行之科學主義思潮的僭妄相映成趣。”③高力克:《調適的智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頁。不只“理智的謙虚”,更為難得的還有思維的深刻與縝密。杜亞泉在其《人生哲學》一書中敏鋭地指出:
科學雖征服自然,使自然為人類所有,而人類的精神轉因此喪失。本來希望人制馭自然,實際上為自然制馭人類。①《杜亞泉著作兩種》,第11頁。
數十年過後,當科學真的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征服自然”後,系統論創始人貝塔朗菲(L.V.Bertalanffy)悲慘地指出:“我們已經征服了世界,但是卻在征途中的某個地方喪失了靈魂!”②[奥]貝塔朗菲、[美]拉維奥萊特:《人的系統觀》,第19頁。這似乎也應驗了早先盧梭的判斷:“在一個領域裏的進步,必不可免地伴隨著在另一個領域裏的倒退。”③[法]亨利·古耶:《盧梭與伏爾泰》,第8頁。啟蒙運動以來三百年的歷史,中國現代化的百年歷史都已經説明: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物質生活日漸豐富,社會的道德倫理水準並未隨之提升,甚至不升反降,而生態環境比起三百年前不知惡化了多少倍!
(四)杜亞泉認為物質主義、功利主義、消費主義、拜金主義暴殄天物、敗壞社會風氣、荼毒人的心靈。
民國初建,老中華帝國積弱已久,急需振興實業、發展經濟。杜亞泉對此並無異議,自己也曾指導親朋建工廠,開商店。但作為一位持有機整體性思維的學者,一位注重調適漸進的啟蒙思想家,他從一開始就注意到單一向度的憑藉刺激消費發展經濟,將破壞物質與精神之間的平衡,給社會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傷。民國初建不久,中國社會剛剛開始對外開放,奢靡之風即開始流播蔓延,杜亞泉對此充滿憂慮:
暴殄之天物,浪擲之金錢,何可限量。地產之所出,既以供無謂之取求,人力之所造,又復偏重於淫巧之物品,而純正之產業,寶貴之人工,轉不克完其正當之效用,以增益國富。且一度領略奢華之後,決不能復安於淡泊,苟其失之,亦必榨取豪奪,行險僥倖,以求復得焉。④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315頁。
杜亞泉已經隱約感到,國内興起的此類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拜金主義源自西方現代社會的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是有缺陷的,並不完全適合中國的國情:
今日社會中之歡迎物質文明,仿效歐美奢侈之生活者,實破壞其社會之特質,而自速其滅亡……縱慾之國民,常失其奮鬥之能力。覽六朝之興替,觀羅馬之衰亡,俱足為社會之殷鑒。今日歐美社會中文明病之流行,識者亦抱無限之隱憂,蓋為此也。吾東亞人民,欲於歐風美雨之中,免社會之飄摇,亦惟有保持其克己之特質,以養成其奮鬥之精神而已。①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288頁。
在杜亞泉看來,鑒於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可勉強效尤西洋,不應為西洋物質文明所眩惑,“論進化之大原,謂為由於慾望之向上,無寧謂為由於勤儉所積貯之較為中理也”②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313頁。。他主張維持傳統的勤儉樸素之風,讓科學技術、經濟生產為下層社會廣大民衆日常生活服務,而不可用鼓勵奢侈性、冗餘性消費促進經濟發展,推動社會進步。
一百年前的杜亞泉不可能具備清晰、明確的生態學理論知識,他的憂慮也僅只停留在“奢侈消費”引發的社會問題上,他自己提出的經濟學理論也是樸素的,即消費不是無止境的,消費不應成為少數人謀取金錢與財富的手段,而應當服務於人民大衆實際的生活日用。一百年過後,杜亞泉擔心並拒斥的歐美消費觀念不但没有受到遏止,反而成為一種“全球化的意識形態”風行世界,在杜亞泉自己的國度,如今“消費”的指數已經領先世界,據貝恩諮詢機構最近發佈的“全球奢侈品市場年度報告”披露,2018年中國已經佔據全球個人奢侈品消費市場的33%,遠超歐洲與美國,更是日本的三倍。而且消費者還在迅速年輕化③見2019年5月23日《南方週末》相關報導。。
當代生態批評家布浪(Lester R.Brown)警告世人:“我們正在掏空地球的自然資源來刺激消費。我們有半數的人生活在地下水位下降、水井乾涸的國家。有三分之一的農田土壤流失超過新土壤形成,土地的肥力在逐步喪失。全世界不斷增長的牛羊大軍,正在將廣袤的草原變成沙漠。我們砍伐森林來擴大農業耕地、生產木材和紙張,使森林每年萎縮530萬公頃。五分之四的海洋漁場因滿負荷或過度捕撈面臨崩潰。”①[美]萊斯特·R·布朗:《崩潰邊緣的世界》,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頁。
長此以往,不但導致地球生態系統的崩潰,還將導致人種的退化衰敗。回望當年杜亞泉的憂慮,就不難看出他那“簡陋”的經濟學主張中藴含的生態智慧。
(五)杜亞泉認為“物質救國”的結果不但傷及山水森林,還將招致“精神破產”,並因此宣導精神救世。
在日益深入的世界生態運動中,人們在驚呼自然環境遭受嚴重破壞的同時,發現人們的精神狀態也在隨之惡化。雅斯貝斯(karl Jaspers)將其視為“技術進步”中的“精神萎縮”②[德]卡爾·雅斯貝斯著:《時代的精神狀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頁。,貝塔朗菲將其看作人類精神世界中符號系統的迷狂和紊亂③參見[奥]馮·貝塔朗菲:《人的系統觀》,第25—28頁。;比利時生態學教授P·迪維諾(P.Durigneaud)明確的將其稱作“精神污染”④P.迪維諾:《生態學概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頁。。在上述諸位西方思想家之前,中國近代啟蒙者杜亞泉就已經對這一問題做出不少論述。他指出:奢侈型消費無端損耗了珍貴的自然資源,結果反而招致國民精神破產,“湖海森林,無不經吾人之搜索,一條之河,一丘之山,無或免吾人之穿鑿。吾人之一軀,其所需何如是之夥耶!實則吾人非為應其需要而營衣食住,乃為滿足其功名心與虚榮心而營其衣食住。”⑤《杜亞泉著作兩種》,第242頁。“人類在世,決不僅僅解決衣食住等物質生活,畢其生活能事,如道德、科學、藝術等,均為吾人精神生活的要求。此等精神生活,當不受物質生活的拘束,獨立進行,自由表現。”⑥《杜亞泉著作兩種》,第13頁。“精神文明之優勢,不能以富強貴賤為衡。”針對中國社會鼎革之後呈現的種種“精神破產之情況”,如權利競爭,唯利是圖,貪享奢侈,縱情食色,昨為民党今作官僚,早擁共和夕擁帝制,改節變倫不以為羞,投機鑽營自以為智,他厲聲驚呼:“吾國之鶴(指精神追求,引者注),已斃於物質的彈丸之下矣!”⑦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366頁。“中華民國將變為動物之藪澤。”①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54頁。杜亞泉對於“科學”、“實業”的瞭解並不比當時的主流啟蒙思想家少,但他仍然不相信僅僅依靠“科學”與“實業”就可以救中國,反而提出“精神救國論”。“蓋近數十年中,吾國民所得宣導之物質救國論,將釀成物質亡國之事實,反其道而蔽之,則精神救國論之本旨也。”
杜亞泉在宣導“精神救世”、“精神救國”時,把古羅馬時期的斯葛多學派的思想家塞湼卡(Seneca)奉為楷模,將其《幸福論》作為中國“救時之良藥”。而《幸福論》的主旨,即:“使形體服從於精神,肉身服從於靈魂,為得全幸福之道。”②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238頁。當時,生態學的奠基人海克爾的著作已經由馬君武、劉文典翻譯出版,其中《宇宙之謎》一書中寫道:19世紀的自然科學不僅在理論上取得驚人的進步,而且在技術、工業、交通等世紀應用過程中也取得了極為豐碩的成果,然而“在精神生活和社會關係這樣重要的領域裏,與過去世紀相比,我們卻取得很少或者乾脆没有取得什麽進步,甚至令人遺憾地出現某些嚴重的倒退。這種明顯的矛盾,不僅使人產生一種内部支離破碎、虚妄荒謬的令人厭惡的感覺,而且還會在政治與社會領域裏引起重大災難的危險”③[法]恩斯特·海克爾:《宇宙之謎》,第4頁。。
杜亞泉應該是看過海克爾的書的,並把這一觀點視為西方人對物質主義的反思告誡給中國社會的主流啟蒙思想家們,可惜並未得到認可。而海克爾在19世紀最後一年做出的這一論斷很快就被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所證實。如果考慮到20世紀世界以及中國社會政治中發生的一系列慘劇,回頭再看杜亞泉大聲疾呼的“精神救世”、“精神救國”的主張,就不得不承認他作為一位思想者的嚴肅性與前瞻性。二戰後,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明確指出:“要根治現代社會的弊病,只能依靠來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④[英]湯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紀》,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66頁。湯因比將“精神革命”視為人類為地球生態解困的唯一途徑,這與杜亞泉當年呼籲的“精神救國”、“精神救時”也是一致的。
杜亞泉“精神救國”的宣導,莫説在當時,即使在“發展是硬道理”的當代中國,也難免被視為書生之議。然而,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即使達到世界前列,如果思想貧瘠,信仰全無,道德滑坡,民生涣散,也還是難以成為世界強國的。
以上五點,是我對中國啟蒙運動的先驅杜亞泉學術思想中生態精神的發掘。其實,杜亞泉當年所關注的而如今已經成為嚴重生態問題的,還不止於這些。如他對忽視農村文化建設、過度城市化的擔憂:
田野生活者,富國之源泉,物質文明之生產地也。近今歐美各國,每以人民群集都會,引為文明過盛之隱憂。吾國文明,尚在幼稚,而都市生活之趨勢,已露端倪,亦宜杜漸防微,力為禁遏,夫然後受物質之利而不承其弊也。①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274頁。
況近今農民,咸慕都會之繁華,工業之安逸,有日趨都會之傾向。苟不急為補救,使住居田舍者稍得慰藉之途,則優良者將輕棄其鄉里,别營城市之生涯,劣下者或愈即於畸邪,流為賭博之征途,馴至田野荒蕪,風俗墮壞。②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333頁。
為此,他宣導在鄉村開發民智,普及新知,建立機構,改良民生,“隨時勢之需要,寓教於樂,使農民略有相當之知識,以應外界之潮流”③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335頁。。
又如,他認為中國的官場制度弊端嚴重,政治生態日益敗壞,如不痛加改良將禍國殃民。
人民重視官吏,其危害之及於國家甚大。直接之影響,使國家之政治不安,間接之影響,使社會之實業不振,其關係可得而言焉。蓋人民既視官吏為最優之職業,則必努力以造成官吏之人才,教育乃首承其弊……而一般人民,且以登第學生之多寡,定學校之價值。試驗之成績如何,為學校之死活問題,於此而欲施正當之教育,殆無可望。風氣所趨,年年歲歲,制出多數之官吏候補者,供過於求,無待言矣。此等多餘之官吏,其學問志願,除政治生涯外,不適於他種之職業,即或為學校教師,或為新聞記者,亦無非鼓吹政治主義,挑撥政治感情,使政治風潮,波及學校,政治新聞彌漫於城市而已。①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267頁。
杜亞泉的這段話已經深刻地涉及中國在教育體制、價值導向、官場生態方面存在的頑疾,他提出的改良措施是“裁減冗員”、“簡放政務”、“劃除官威”、“釐訂官俸”,讓官員“謹身修己亦貢獻國家”,讓民衆“平等視官”以做好自己的營生。杜亞泉的這些建議,對於今日中國政治生態、教育生態仍具有現實意義。
究竟出於什麽原因,使清末民初的杜亞泉在中國社會剛剛跨進現代化的門檻,就讓他意識到現代性存在的嚴重問題,並由此發表許多如今看來甚具“生態批評精神”的言論,從而使他成為中國獨樹一幟的啟蒙者。
我想到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他對西方哲學與現代科學有著多方面的認知與把握。
杜亞泉不是某一學科的專家,他的知識空間具有廣泛的跨學科性,幾乎跨越他那個時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方方面面。並且,他對西方近現代思想家如達爾文、斯賓塞、伏爾泰、盧梭、貝克萊、休謨、孔德、康得、孟德斯鳩、海克爾、黑格爾、馮特、詹姆斯、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叔本華等人的思想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吸納。他還曾一度游學日本。這不但使他擁有了科學與哲學的開闊視野,也使他具備了反思性的思維方式。在現代諸多學科門類中,杜亞泉對海克爾的生物學、叔本華的生命哲學、威廉·詹姆斯的機能主義心理學,塞涅卡的倫理學情有獨鍾,在我看來,這些學科與當代生態學及生態批評、環保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對杜亞泉生態意識的形成起到明顯的作用。
二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滋養。
杜亞泉從童蒙時代即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青年時代中秀才,於經史子集、訓詁音韻之學均有悉心研究。形成於漫長農業社會的中國傳統文化,其核心實為人與自然合一的生態文化。杜亞泉對此是認同的,他説過中國傳統文化“一切皆注重於自然”,“以自然為善,一切皆以天意,遵天命,循天理,”“我國人之文明為順自然的”②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339頁。。這個傳統文化中藴含的“生生為易”、“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物與民胞”、“抱樸懷素”、“知白守黑”、“無為而無不為”等等生態精神注定對杜亞泉產生過潛移默化的作用。西方現代科學中的生態理念與古代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底藴相結合,是杜亞泉生態意識產生的重要成因。當然,對於西方現代文化,他不一味順從;對於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他也並不一味地膜拜,而是有所揚棄。比如中國傳統道德中的“克己”,從好的一面説,養成了民族重内輕外,重精神輕物質的優良品性,但一味“克己”又使國民才智内縮、畏葸苟且、求逸避險、卑曲萎靡,理想的人格則為“保持克己之特質,養成奮鬥之精神”①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288頁。。杜亞泉熱衷西方科學卻不忘科學之懷疑精神,珍愛民族傳統文化,始終秉持“扣其兩端而取其中”的中庸之道,這也是當代生態運動應當發揚的識見。
三是杜亞泉擁有報刊記者的時事眼光。
這使他能夠及時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性做出整體性反思。在西方,“科學主義”神話的破產,“物質主義”的批判,社會進步論的幻滅,以及“現代性的反思”,多半是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後發生的。這一時期的傑出思想家,如西美爾、舍勒、懷特海、韋伯、别爾嘉耶夫,斯賓格勒、德日進、馬爾庫塞,他們對人類社會文化的反思,都是以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為背景的,舍勒於一戰爆發之際發表的《戰爭的天才》,指出物質戰勝了人,變成“機械殘殺”的工具,人類自身成了時代面臨的最大麻煩。斯賓格勒寫於一戰期間的名著《西方的没落》認為,在“金錢”與“機器”統治下,人的精神創造力消失了,所謂進步帶來了越來越多的資源耗費和環境惡化,西方文化作為一個整體正在衰敗。這些思想家們的反思,有意無意間都涉及了人與自然,人性與工業文明的衝突,因而具備了生態批評的傾向。杜亞泉作為一位資深的報刊記者、編輯,身歷一戰的醖釀、爆發、結束全過程,他在此期間發表了大量言論。如“自歐戰發生以來,西洋諸國,日以其科學的發明之利器,戮殺其同類,悲慘劇烈之狀態,不但為吾國的歷史之所無,亦且為世界從來所未有”②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338頁。。杜亞泉的關於東西方文明優劣之比較研究,關於人類文明之趨向之判斷,應是在總結一戰教訓基礎上展開的,這也就使得他的思想觀念中充滿了敏鋭而又不自覺的生態批評精神。
四是内斂、沉著、冷靜、審慎、善疑、多思的個性。
對於文學創作來説,有一句名言“風格即人”,即人的個性。那麽學者的個性與學者的治學有無關係呢?恐怕不能説没有關係,對於盧梭與杜亞泉這樣自學成才的學者來説,關係更大,幾乎是決定性的。杜亞泉去世後,親友對其性情、為人有許多評價。蔡元培描述他:“君身頎面瘦,腦力特鋭。所攻之學,無堅不破,所發之論,無奥不宣。有時獨行,舉步甚緩,或諦視一景,佇立移時,望而知其無時無處無思索也。”①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第3頁。“先生雖專攻數理,頭腦較冷,而討尋哲理針砭社會之熱誠,激不可遏。”②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第6頁。胡愈之在追悼文章中寫道:“先生生平自奉之儉,治學之勤,待人之和藹,處事的果敢,無不足為青年人效法。”③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第12頁。他的兒子回憶説:父親是一位既嚴肅又慈祥的老人,不苟言笑,衣著古板,刻苦自學,勤奮寫作,自奉甚儉,立志不當官,不經商④參考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第41—43頁。。對照上述評説,結合他自己的大量著作,我們不難看出杜亞泉是一位勤學多思、敏鋭善疑、冷峻内斂、自奉儉約、甘守清貧、淡於名利卻又能仗義執言的人。這樣的人並不適合商業社會的競爭,反而屢受其害;這樣的人也不可能投身革命運動的戰場,而只會提出一些建言與清議,説到底他還只是變革時代一位堅持獨立思考、堅持自由發聲的書生,或曰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人已經溢出啟蒙時代主流意識之外,反而與生態時代的精神氣息更為接近。陳獨秀、李大釗、吴稚暉以及丁文江、胡適,這些中國社會傑出的啟蒙思想家,依其豐富的知識,堅定的信念,努力奮取的鬥志,在當時何以不能意識到人類已經面臨的生態問題?只能説是現代化的強光,遮蔽了他們的視線,内在的局限使他們一股道疾馳在想象中的社會進步的“金光大道”上,相對於他們,杜亞泉就顯得更柔弱也更複雜些,更矛盾也更豐富些。柔弱,複雜,豐富,不也正是地球生物圈的屬性嗎?
回望歷史,杜亞泉是清末民初中國社會轉型時期一位嚴肅認真、品節高尚、見地卓越的文化人、思考者。他或許尚未成為像盧梭乃至在中國稍遲於他的梁漱溟那樣的大思想家,他有他自身的弱勢與局限性。自學成才,使他免受學院派的約束,也使他的某些術語、概念的運用流於隨意性,對此他自己也曾做出反省:介紹諸説,多輾轉迻譯,不免謬誤;摘要舉示,不免得粗遺精,時以記者之見地,妄為取捨①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第48頁。。他的有機、統整、調適、接續的思維方式使他在分析問題時透遞出許多寶貴的現代生態批評的思想光芒,但他身處的時代,自然生態在中國尚未成為重要問題;就西方社會而言生態學的人文轉向尚未啟動,因此,杜亞泉在論及生態問題時,常常還是站在人類中心的立場上,未能達到更深的層次。杜亞泉不組黨,不結盟,不像陳獨秀那樣有強大的組織力量支撐;他雖然熱衷於建學校辦教育,無奈總是艱難多舛以失敗告終,這又使得他不像胡適那樣門徒、弟子遍佈四海。所以,在他去世後,他的學説以及他的存在很快就消失在中國社會大變革的洪流中,這不僅是他個人的不幸,更是中國思想界的不幸。
三、20世紀初中國的文化選向及人類新文明建設
20世紀初,中國進入現代社會之際就文化選擇而言,一度曾存在三個向度:守舊主義、漸進主義、激進主義。固守傳統、泥古不化的守舊主義很快就潰不成軍敗下陣來。此後,持續不斷的主要是漸進主義與激進主義的論戰。首場大規模的論戰即爆發在《東方雜誌》與《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之間的“東西文化之爭”。據相關專家統計,這場爭辯從1915年起延續十餘年,先後參與者數百人,發表文章近千篇,對以後中國近現代的文化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②陳崧主編:《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頁。。論戰的主將,激進主義一方是陳獨秀,漸進一方是杜亞泉。所謂“激進”、“漸進”,當時的主要分歧在於對待西方外來文化與本土民族文化的態度。
陳獨秀持全盤西化的立場,對歐洲啟蒙運動以來卓有成效的“科學主義”、“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文化理念推崇備至,竭力主張以西方現代文化取代中國的傳統文化,以“革命”的方式建立一個“新中國”。杜亞泉則採取兼收並蓄、調和折中、統整接續的立場,主張既吸收西方現代文化的特長又要避開其已經顯露的弊端,同時吸納接續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選擇中西文明融合的道路,以漸進“改良”的方式推動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
這場論戰的稍後階段,梁漱溟曾提出文化選擇的三個路向,一是“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的印度文化,一是“意欲向前要求的西方文化”,一是“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的中國文化”,他的文化立場顯然是站在杜亞泉一邊的,有甚於杜的是,他斷定“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①《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頁。。年輕氣盛的梁漱溟的這些論斷不免有些粗疏武斷,但胡適在批評他時,連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也否定了,認為世界上的文化不過大同小異,不存在性質的差别,只存在落後、先進的程度。當然,胡適認可的代表人類同一屬性的文化是西方文化,居於先進地位的也是西方文化。這場轟動一時的文化論戰以杜亞泉、梁漱溟的失敗告終。梁漱溟在不久後辭離北京大學到山東菏澤教中學去了;杜亞泉竟因此被免去《東方雜誌》主編的職務。而陳獨秀與胡適隨後都成為引領時代的風雲人物。中國社會在歷史轉折的緊要關頭,選擇了由歐洲啟蒙理性主導的以“科學主義”、“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為内涵、以“革命”為手段的激進主義文化路向。
從1915年展開的這場文化論戰,到如今已經過去一百多年。一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經歷過俄國十月革命、五四運動、兩次世界大戰、國共兩黨的合作與決裂、新中國成立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直到最近40年的經濟建設高潮。其中的成敗功過當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夠説清楚的。可以大體做出判斷的是:中國社會的變革是巨大的,成就顯著,問題突出。“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就與問題就文化層面上來説,當然不能全部歸結於啟蒙時期的激進主義,但與在現代化進程的起跑線上選擇了激進主義路線密切相關。國内文化學者陳來就曾指出:“可以説,整個20世紀中國文化運動是受激進主義所主導的。”②陳來:《傳統與現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頁。農業問題專家温鐵軍將其一部總結中國農村現代化的著作命名為《告别百年激進》,他認為中國農村現代化的教訓就是激進主義主導了整個過程。而這一過程,正是以1915年的東西方文化論戰為起點的。
激進主義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面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趕超心態”。中國與西方在文化上的差異既然僅僅是時段與發達程度上的,那就是説我們可以在同一條道上通過自身努力趕上甚至超越過去。陳獨秀早在1917年就主張:“西洋種種的文明制度,都非中國所及。但就經濟能力而言,我們中國人萬萬趕不上。倘不急起直追,真是無法可以救亡。”①陳獨秀:《獨秀文存》,第107頁。孫中山也把其建國大計寄託在對於西方的趕超上,他相信人力完全可以超越自然進化,只要發揮出火一般的革命意志和創造精神,中國就能夠“壓縮”許多進化“階段”,神速地達到“進化”的高級階段,後來居上,超過歐美,並成為世界進化新潮流的領導者②見鄭大華、鄒小站主編:《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頁。。孫中山去世早,尚未來得及實施他的趕超學説,而他的後繼者毛澤東卻把這一學説發展到了極致。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毛澤東提出了要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上七年超過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後來又將時間縮短為三到十年。激進的夢想落實為揠苗助長,結果只能是慘重的災難。我是當年全民“大煉鋼鐵”的親歷者,為了實現這一趕超目標,家裏灶房的鐵鍋、牆上的鐵釘都拿去煉鋼,周邊的大樹全都砍去做了燃料。勞民傷財,煉出的不過是一堆廢鐵。“大躍進”後隨之而來的是“大饑荒”,千萬人死於非命,震驚了整個世界。
激進主義的另一個突出表現是把“鬥爭”絶對化。杜亞泉以“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形容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差異。他列舉的“動的文明”的首要屬性即“競爭自烈”、“對抗紛爭”、“戰爭為常態,和平其變態”、“以競爭勝利為生存必要之條件,故視勝利為最重,而道德次之”。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則重在“勤儉克己,安心守分”、“清心寡欲”、“與世無爭”。陳獨秀完全否定這一劃分,李大釗倒是認可杜亞泉的説法,只是他對中國的“靜的生活”持否定態度,認為只有“棄其從來之一切靜的生活,取彼西洋之一切動的生活;去其從來之一切靜的文明,迎彼西洋之一切動的文明”,方能夠救中國。他號召青年一代行動起來,迎合世界潮流,將中國由靜的國家改變為動的國家③《李大釗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頁。。此後,競爭、對抗心態迅速在中國社會蔓延開來,更加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説的活學活用,遂生成一種愈演愈烈的“鬥爭哲學”,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外鬥加内鬥,“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一度成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頭等大事,政治鬥爭運動每隔七八年就要來一次,“灑向人間都是怨”,嚴重地破壞了國家與民族的安定團結。
激進的功利主義干擾了科學文化教育界的健康發展。在這場論爭中,《東方雜誌》陣營中錢智修的《功利主義與學術》一文也成為激進派猛烈攻擊的靶子。錢文認為中國受西方文化影響最大的是“功利主義”。由邊沁(Jeremy Bentham)、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創始的功利主義是一個内容極為繁富的學派,中國文化界在引進這一“功利主義”學説時已經功利主義地將其大大簡化了,大抵只剩下“實用”、“急用”、“對大多數人有用才有價值”的條文。錢文列舉了此類功利主義在中國學術界引發的種種弊病,如:僅把應用價值作為學術研究的目的是有害於學術的;學術受制於應用將妨礙學術之獨立;“文化重心,自在高深之學,所謂普及教育,不過演繹此高深學問之一部分,為中下等人説法耳”;“功利主義之最大多數説,其弊在絶聖棄智。使學術界無領袖人才”;“唯以國家之力助少數學人脱離社會之約束,俾得從容治學”,學術才有精進之望①陳崧主編:《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第50、52頁。。對於錢文,陳獨秀卻大不以為然,他認為“人世間去功利主義無善行”,針鋒相對地提出中國應該“徹頭徹尾頌揚功利主義”的口號②陳崧主編:《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第75頁。。百年過後,從今日的實際狀況看,中國大衆的普及教育以及科學技術的普及應用都取得了顯著成績,但高等教育的品質及基礎理論研究的水準始終落在世界後面;無論自然科學還是人文學科,堪稱“學界領袖”的學術大師越來越稀缺;不少重大核心科學技術多停留在借用仿效階段,缺乏自主創新能力。追根溯源,不能説與現代中國在科技文化教育界長期持守的急功近利的激進思維模式無關。
激進主義的現代化運動嚴重地破壞了地球生態。發生在20世紀初的這場文化論戰,關於人類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判斷,激進派顯然也壓倒了杜亞泉的温和派。文化史學者王中江對中國激進主義革命派的宇宙觀曾做出以下描述:“革命派對宇宙自然與人類社會的二重處理方式,最終也落腳在人類社會對於宇宙自然的優越、人類社會與自然的不同上”,“他們的‘意圖’是要通過人類與自然的二元化,把人類從被動的自然秩序之下解放出來,使之成為‘創造’進化的積極‘主體’”。在陳獨秀那裏,“人類主體”被表述為:“以人勝天,以學理構成原則,自造禍福,自導其知行”。陳獨秀的這一觀念並非他自己的發明,而是啟蒙理性的核心,即人類憑藉自己獨有的“學理”高居自然之上,戰天鬥地,為自己謀取福利。這一簡單不過的邏輯,既是啟蒙理性的核心,也是生態災難的源頭。中國社會在現代化伊始選擇了這一發展邏輯,也就為此後的生態災難打開了潘朵拉盒子,乃至付出慘重的代價。至於當前的生態災難嚴重到什麽程度,報紙網路天天都有大量報導,本文不必再一一列舉那些統計數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切身體驗。總之,連吃飯、飲水、呼吸、生殖、繁育這些人類生存的最基本的保障都已經成了大問題。“先污染,後治理”實際上成為中國當代經濟建設領域的潛意識。若是仔細考慮到經濟高速發展的生態成本,改革開放的紅利就不得不大大打個折扣。
以上四點只是擇要説明激進主義給中國現代化進程造成的傷害。雖然説以啟蒙理性為核心的西方現代性理念自身就存在許多問題,但中國的問題更大程度上是長期將這一啟蒙理念付諸單一地、片面地、過激地實踐,而且從來缺少認真地反思。
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人類做出的第一次重大反思是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犧牲掉數以千萬計的人類生命之後。這次反思以西方學者為主,對西方現代社會賴以存在的思想基礎進行了全面的、徹底的反思與批判,其中就包括曾經被杜亞泉“漸進主義者”懷疑、質問過,被陳獨秀“激進主義”褒獎、頌揚過的“科學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以及“機械唯物論”、“直線進步論”等等。為了矯正西方社會的偏頗、挽救現代社會的敗落,西方的一些著名學者也曾把目光轉向世界的東方。我甚至猜想,德國思想家馬克斯·舍勒(Wax Scheler)在當時似乎就已經察覺到中國思想界的論爭,以及論爭中不同學者關於東西方文化的不同立場:
特别是中國和日本等國中的某些階層今天正竭盡全力去掌握歐洲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去掌握相應的工廠化生產方式和經商方式,因而資本主義機制普遍化看來是近在咫尺了;然而,儘管如此,近些年來這些民族的更為高貴的代表們已知道,這種錯誤的所謂“歐化”只能觸及心靈和生命的皮毛,對於種族相應的、出自民族自身歷史的精神性基本態度(在宗教、倫理、藝術中一切屬於生命意義的東西)卻依舊毫未觸及。……這些國家中的佼佼者還知道:西歐作為信使把資本主義“精神”作為自己最後的光束帶給這些國家,而這一精神之根,就是説,在西歐的中心本身,這一“精神”正在慢慢衰亡。這些國家中都有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維約夫、托爾斯泰:他們帶著諷刺的微笑瞧著本土市民群衆的歐化狂潮勁兒,因為他們知道,正當自己的國家的群衆將為勝利、為自己的國家與歐洲一樣實現了文明而歡呼時,朝他們迎面走來的“舊的”歐洲此時卻正在垮下去,正將讓位給一個新的、更高貴的歐洲。①[德]馬克斯·舍勒:《資本主義的未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81頁。
舍勒的這段話顯然是在批評一味追隨西方“全盤歐化”的“某些階層”,因為他們看不到西方在其現代化道路上已經惹下要命的麻煩,紮根於啟蒙理性的西方文化已經到了矯枉糾偏的時刻;舍勒同時又在點贊東方民族本土思想家中那些“更為高貴的佼佼者”,認為他們著手設計的將是一個新時代的新的文明。至於這個“新時代”的命名,舍勒進而説到:
如果我站在這個新時代的大門口題獻一個名稱,而這個名稱又將包含著這個時代的總體趨勢的話,那麽,只有一個名稱在我看來似乎是適應的,這就是“協調的時代”(Ausgleich)。②[德]馬克斯·舍勒:《資本主義的未來》,第215頁。
舍勒認為這種“協調”將在自然界、物理界、精神界的各個層面展開,其中包括種族間緊張關係的協調、東西方不同文化群落之間的協調、原始文明與高級文明之間的協調、科學技術知識與人文精神之間的協調等。
對照舍勒的評析,對照杜亞泉執守的“統整”、“調適”理念,在20世紀初中國思想界發生的這場事關中國前途的論戰中,誰是“歐化狂潮”的激進者,誰是深謀遠慮的“佼佼者”,不就一目了然嗎?
地球人類第二次面臨的生死選擇,該是自20世紀中期逐日逼近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較之上一次的反思,這一次的反思體現出更為廣闊也更為深刻的世界性的視野。
愈演愈烈的生態危機逼迫人們不得不做出重大選擇:人類將進入一個與以往不同的新的歷史時期,一個新的文明階段。相對於由啟蒙運動開創的工業文明及現代社會,這一“新文明”就是“生態文明”,這一“新的歷史時期”就是生態時代。
最初做出這一判斷的是奥地利學者、系統論的創始人路德維希·馮·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他在20世紀50年代就宣告:由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開創的西方文明已經完成自己的使命,它的偉大創造週期已告結束。新的文明,將是一種生存的智慧,一種生態學意義上的文明。生物學的世界觀正在取代物理學的世界觀。“19世紀的世界觀是物理學的世界觀……同時它也為非物理學領域——生命有機體、精神和人類社會提供了概念模型。但在今天,所有的學科都牽涉到‘整體’、‘組織’或‘格式塔’這些概念表徵的問題,而這些概念在生物學領域中都有它們的根基。”“從這個意義上説,生物學對現代世界觀的形成做出了根本性的貢獻。”①[奥]貝塔朗菲著:《生命問題—現代生物學思想評價》,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頁。另一位傑出的思想家E·拉兹洛(Ervin Laszlo)則指出:這是人類史上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之後的“第三次真正的革命”,即將來臨的時代是一個“人類生態學的時代”②[美]拉兹洛著:《布達佩斯俱樂部全球問題最新報告》,第106頁。。
對照上述當代西方思想家的言論,我們再去仔細研究20世紀初發生在中國的那場“東西方文化大論戰”,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杜亞泉的融匯中西、統整古今、調適漸進、人與自然共生的主張更具前瞻性,更吻合生態文明、生態時代的精神。哲學的功用是緩慢的,思想並不總能“立竿見影”,而是往往要潛伏很長時間纔會顯現其意義與價值。
自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以來,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起伏跌宕、波譎雲詭,許多時候就像中國京劇《三岔口》中的表演,充滿隔膜、偏執、誤讀、臆測。而且存在著嚴重的不對等。比如,伊莉莎白·迪瓦恩(Elizabeth Devine)等人編纂的《20世紀思想家詞典》是我案頭常備的工具書,其中收録的思想家共計414人,但東方僅4人,其中印度3人,或許還是沾了英殖民地的光;日本1人;中國則完全缺席③見[英]伊莉莎白·迪瓦恩等人編:《20世紀思想家辭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編纂者如果不是出於傲慢,那就是出於知識的嚴重欠缺。面對生態時代的到來,這種情形可能將要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生態危機的全球性、後現代時期信息傳播的高效性,已經為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充分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在即將到來的生態時代,無論西方或是東方,世界上各個國家的思想家與知識分子精英之間的基本見解正在日益趨向一致。時過百年再來回顧中國上個世紀初展開的那場事關中國命運的文化論戰,經驗與教訓都已經大抵清楚。反思這場論爭,不但有益於當下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同時也會有益於世界新時代文明的創建。其中,異類思想家杜亞泉啟蒙理念中藴含的生態意識就更值得我們珍視、發揚、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