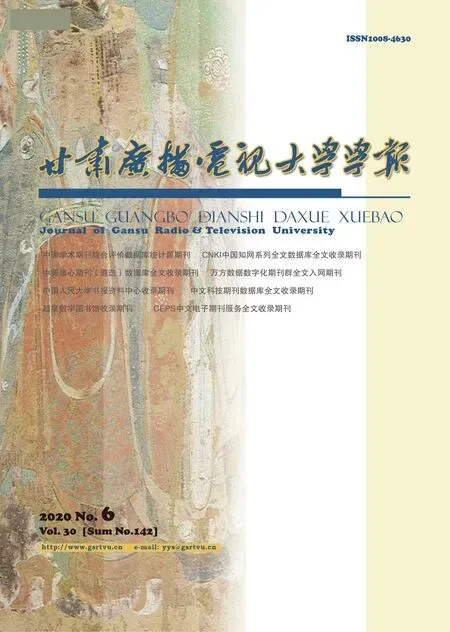秋毫之末直至天人合一
——论《农历》中的饮食书写
刘晋汝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在谈到《农历》的创作时,郭文斌指出:“‘农历’是另一个大自然,在这个大自然里,有天然的岁月、天然的哲学、天然的美学、天然的文学、天然的教育、天然的传承、天然的祝福。”[1]3《农历》的确是一部立足于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从细小处起笔,终笔于“天意”与民族传统精神的大书,具有厚重的思想内涵、丰富的文化深意和别具一格的乡土色彩。作者以乔家的两位儿童五月和六月为主人公,讲述了乔家下庄的乔大先生一家在农历各个节气中的日常生活。作为小说中乡土精神和传统魂魄的承继者,五月和六月的成长始终伴随着诗书礼仪的教化和儒释道文化的浸染,他们在西北的乡土高原上,在祥和的四季轮回中,真切地感受着天地万物的存在与给予。还在父母亲的指引下参悟着人生的智慧与哲理,在传统节日的温馨氛围和神秘的民俗文化中逐渐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获得了对自然万物的仁爱与敬畏之心。
作者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为讲述对象,并以乔家这一德高望重的家庭作为载体。通过儿童纯真的生命视角,按照四季轮回的自然序列,将原本物质资源匮乏的乡村社会,打造成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家园。《农历》饱含具有天然意味的现实指导和教育意义,成为一本“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读的书,也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读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1]4。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于饮食的书写贯穿始终。民以食为天,食物不仅是支撑人类生活的必要物质,而且蕴藏着十分宏大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自古以来,食物在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中就占据着重要位置。《农历》立足西北农村的风俗与饮食习惯,以此来挖掘融汇在日常生活中的民间传统文化,表现质朴乡民的人情美和无限智慧。因此,《农历》一切关于食物的描写,除体现日常生活状况外,更具有承载文化和精神的重要作用,使之从秋毫之末入手,最终抵达天人合一的宏阔境界。
一、饮食中的守望
《农历》对于饮食的书写,蕴藏着作者对过去的追忆,包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内涵。
首先,体现为作品中大量与食物相关的神话与传说故事。《元宵》一节在写到捏灯盏的习俗时,母亲用神话传说为六月解答为何只能用荞面捏灯盏。荞原是观音菩萨的女弟子,聪明美丽却是个瞎子,一个阴天的晚上,她从观音菩萨那里上完课回去时,观音菩萨让她打着灯笼,说尽管她自己看不见,但别人看到亮光就不会撞到她了。回去的路上荞还是被一个和尚撞倒,原来她手中的灯笼早灭了,但在那一刻荞的眼前出现了光亮。她悟到“任何外面的光明都是不长久的,靠不住的,一个人得有自己的光明”[1]4。为报答师父的苦心,她投身为荞麦,做了众生的明心灯。《龙节》提到二月二炒豆豆这一习俗的来历,相传武则天在男尊女卑的时代做了皇帝,玉皇大帝大怒,下令三年内不得向人间降一滴雨,龙王不忍,偷降大雨。玉帝将龙王打下天宫,压在山下,立碑说除非金豆开花,否则龙王永世不得重回天宫。人们为救龙王,遍寻开花的金豆,未果。有一年二月二,一人在晒豌豆种子时想到把豆子炒开花便是开了花的金豆,于是家家户户这样做,使龙王重回天庭,继续为人间布雨。以后每年的二月二,人们都用炒豆豆来感念龙王的恩德。《冬至》关于扁食的来源也有典故,扁食原是一种药,上古时候一位姓孙的医仙不忍冬天人们被冻掉耳朵,就用百草制出一种药让人们服用,此后人们的耳朵再未被冻掉过。于是每年冬至,人们都包与耳朵形状相像的扁食来纪念这位医仙。这些由饮食书写引发的神话传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先民的生存智慧和古老的医学文化,更蕴含着深厚的儒释道哲学。比如心中的光明胜过一切外界的光源,只要一个人的内心是光亮的,眼前的黑暗便不算什么。这些饮食书写还承载着关于仁爱、感恩、好生之德等传统精神。这些无一不是通过日常的饮食书写,实现对传统和历史的守望。
其次,体现在地域民俗和祭祀仪式中。《端午》中“娘说,还没供呢,端午吃的东西可是要供的”,“爹和娘已经在院子里摆好了供桌。等他们洗完脸,娘已经把甜醅子和花馍馍端到桌子上了,还有干果、净水”[1]92。甜醅子和花馍馍作为具有西北地区地域特色的食物,关于其吃法和做法,作者都有介绍:“甜醅子是莜麦发酵的。”“花馍馍当然不同于平常的馍馍了,是娘用干面打成的,里面放了蜂蜜和清油,爹用面杖压了一百次,娘用手团了一百次,又在盆里饧了一夜,才放到锅里慢火烙的。”[1]94花馍馍需要“先从中间的绿线上掰开,再从掰开的那半牙中间的红线上掰开,再从掰开的那小半牙上的黄线上掰开……可是娘说这是有讲究的,上山时必须吃一点供品”[1]94。端午这天的午饭也十分独特,“娘把大年留的馒头十五留的元宵二十三留的饺子早上新擀的长面新烙的饼子放在大盘子里,说元宵是龙眼睛,面条是龙胡子,饺子是龙耳朵,饼子是龙皮,馒头是龙蛋,让大家每样吃一点,说是沾龙气”[1]55。这种由食物形状而生发的特殊隐喻,不仅具有民俗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且与先辈用以具体观抽象的方式来理解世界的传统思维相吻合,成为具有民族色彩的集体无意识的象征。《寒节》同样描写了一种具有地域色彩和民俗特点的小吃——麻麸馍。一年只有十月一这一天才能吃到,做法是将麻籽炒熟后碾成麻麸,和萝卜丝一起包入面皮中,烙成馅饼。《重阳》则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当地滚锅盔的有趣风俗,圆圆的锅盔从山顶滚下,象征着吉祥如意、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和十全十美等美满的意味,食物成为寄托节日祝福和人们对生活美好心愿的最佳载体。
《中元》祭祀鬼神的仪式,“爹拿起筷子,夹起一筷头碎菜,往后台扔去……五月说,这叫放馅口,是让那些游魂野鬼吃的”[1]146。《冬至》中的祭祀仪式更是独特,“接下来爹从盘子里端了素边水碗,放在供桌下面。去年六月已经问过爹,知道这叫陪水,是给那些受不起头的众生饮用的。然后爹把五月刚端来的一小碟扁食放在供桌下面的陪水旁边,不用问,六月知道这还是给那些受不起头的众生吃的”[1]212。还有《大年》的献灶爷和泼散,都是通过饮食书写体现民俗特点和传统习俗。
此外,饮食中的守望还体现在隐匿于食物中的儒释道哲学智慧里。儒家天下归仁的核心思想在乔家面对食物的态度中多有体现。梨子成熟了,六月在父亲的劝说下将梨子分给了邻居,于是“厨房面板上少了六十只梨,却多了数不清的番瓜、茭瓜、苹果、花红、玉米,等等”,“真是有意思,自家的梨到了别人家,别人家的东西到了自己家。原来‘自己’和‘别人’是可以变换的”[1]167。邻里之间无私地分享食物,将好的留给别人,不计较得失,这种通过日常琐事展现出的温暖人情,正是儒家文化天下大同思想融入人们灵魂后,产生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家园。而佛家文化除渗透在大篇幅引用的《目连出关》戏文中之外,还通过饮食书写映射出来。比如五月劝阻六月不要掏喜鹊窝的时候讲道,一个馋痨用枪打死小鸽子吃了肉,第二天发现母鸽子死在门前,剖开看到母鸽子的肠子断成了截,从此这个人再也不吃肉。《七巧》写:“爹说神仙之所以不喜欢吃肉的人就是因为吃肉的人比不吃肉的人更臭。”[1]103表现出佛教不吃肉的禁忌。乔先生一家节日时为牛羊等家禽改善伙食的行为,则显示出佛教对万物的善念和慈悲心,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安详境界。《冬至》献水的习俗则蕴含着道家文化,借五月之口背诵“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1]220就是最直接的表现。
二、饮食中的童真
《农历》以儿童为主人公,并通过儿童视角展开故事的叙述,因此儿童的天真纯洁贯穿始终。食物与儿童的关联最为紧密,在他们极其单纯的日常生活中,食物的吸引力显然比其他事物来得更为强烈。因此,在与美食的互动中,儿童独有的可爱天性尽显无疑。
首先,书中具有大量以食物为喻体或者将食物拟人化的表述。《元宵》:“只见那个大胖娃娃已经变成了几排小面仔,队伍一样整装待发。”[1]1《中秋》:“小外甥的脸露出来,就像一个刚出锅的白面馒头。”[1]169《重阳》:“六月发现,是黑暗加强了五月给他的温暖,水果糖一样的温暖。”[1]180《大年》:“年像一个大面包一样,把人都香晕了。”[1]278这种用具体事物感知抽象的认知方法十分符合儿童的思维方式。作者选用儿童较感兴趣的食物作为他们感知世界与表达自我的媒介,将儿童柔嫩的肌肤比作刚出锅的白馒头,把心灵上的温暖感受具象化为水果糖一般的甜蜜。最为传神的是,作者把“年”比作大面包,通过儿童对面包的热爱,形象地传达出他们对过年的真挚渴望和强烈期盼。关于饮食的隐喻书写,不仅生动展现了儿童纯洁的内心世界,而且为全书增添了童真的生气。
其次,作者描绘了儿童对食物发自内心的热爱,以及由此产生的童趣和对食物的敬畏。谢有顺在评价郭文斌时说:“这是一个有根的作家,他的作品,从大地中来,有故土的气息,同时又对生命饱含正直的理解。他以自己那通达而智慧的心,打量世界,所发现的,往往是别人所难以发现的自得和优美。在苦难叙事成为了主流的时代,对苦难有一种超然的理解,更能显出作家的宽广和坚韧——这正是郭文斌写作的个性。”[2]面对物质匮乏的苦难时代,作者选择用超然的安详笔法描绘世界,从儿童的生命视角出发,用书写饮食展现超越了苦难的童真与安宁。《中秋》五月与六月吃梨,“不多时,五月手里的梨就没了,只留一个梨把儿在双唇间,就像一只松鼠,身子已经钻进洞里,尾巴还在外面。但那尾巴是长眼睛的,看着六月,一眨一眨。六月就学着五月的样子,也留了一个尾巴,看着五月,一眨一眨。谁想就在这时,五月抓着尾巴,出来的却是整个松鼠。六月傻眼了。”[1]163孩子们舍不得吃光宝贵的梨故而略施小计,不仅没有显出物资缺乏的辛酸,反而展现出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童真与狡黠。和一年成熟一次的梨同样珍贵的,还有舅舅从“南里”带来的水果糖,“我们要闭住气,闭上眼睛,隔着糖纸拿着糖的一端,把糖的另一端轻轻地轻轻地点在舌尖上,让那一点慢慢放大,放大,再放大,大到不能再大,然后再点一次,这样就会让糖永远活着”[1]180。儿童单纯的心愿和热烈的渴望跃然纸上。物质的匮乏让看似平常甚至简单的食物显得极具魅力,因此格外被珍惜。六月认为“如果因为说话或者想事情错过这香这味,就太可惜了,就是罪了”,于是他“努力专注在每一次咀嚼时牙的感受上、舌头的感受上,严防死守,不让一丝丝味道轻易滑脱”[1]206,全身心地沉浸在食物中。为了过年时的糖果、核桃、大枣,自进入腊月起,六月就迫切地算着过年的日子,甚至想模仿沉香救母,把年从时间的大山中尽快解救出来。儿童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和纯真可爱的本质,通过对食物的渴求弥漫在字里行间。正是儿童的天真使之超越了物质的苦难,造就出一种独有的祥和味道,慰藉精神的同时还增添了心灵的平和与知足。
再次,儿童由食物引发的智慧与思考同样是童真的体现。六月为专注于食物而产生的对于“想”的控制和思考,是儿童对于自身精神世界自控自悟的有意识行为。还有由冬至献水引发关于善恶的思考,“原来这人的肚子就是一个大杀场啊,看来,这人只要吃饭,就是作恶。人要真正行善,除非不吃饭”[1]221。由水引发的属于儿童的独特思考,毫无违和感,同时通过这种最简单天真的思维,传达出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对于性爱,儿童是懵懂无知的,却也用自己的方式进行阐释,“吃”成为他们理解这一行为的主要途径。六月将“痴情”理解为“吃情”,以至于发出五月是否会被将来的女婿切开吃掉这一疑问。傻气中透着精明,童真中夹杂着幽默,使故事氛围变得愈发鲜活灵动,充满生气。
三、饮食中的祝福
作家在《文学的祝福性》中提到:“文学除了教科书上讲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批判等功能外,应该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祝福功能。”“祝福的功能必定来自于祝福性。”[3]在作者看来,祝福性即将心灵的安详与温暖,透过文字传达到每一个阅读者的心间,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作家在《农历》中通过描写乔大先生一家的日常饮食,将生活的方式化为祝福的方式,传达其淡泊温暖的舒缓态度,如同一股涓涓细流滋润着每一位读者。
首先,通过饮食表现出亲情的温馨和人情的温暖。中秋节时乔家人围在一起赏月吃瓜,“五月六月抢着给爹、娘和大姐递瓜,神情沉稳,其实口水已经把舌头淹过了,爹和娘只吃了两牙就不吃了。大姐不停地把瓜牙吃出一个尖儿,喂进幸福嘴里,让五月和六月看着很着急,但大姐却是一脸的耐心和欢心”[1]173。过年分糖果时母亲把自己的一份留给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母亲也一起吃,母亲“把嘴里的水果糖咬成两半,一半给五月,一半给六月。五月和六月不接受。娘说,娘吃糖牙疼呢,再说,我已经噙了半天了,都已经甜到心上去了。可是五月和六月还是不要”[1]258。将一家人的日常琐事徐徐述之,平淡文字中流露出的是亲人之间浓厚的感情。父母的无私奉献,想把一切的美好留给孩子享用,孩子们也在这充满爱的氛围下懂得感恩与回报。通过平平无奇的一日三餐,展开了一幅幅厚重的亲情画卷,带给读者心灵上的温暖洗涤。
其次,小说中的饮食书写还具有现实的指导教育意义。比如五月和六月在吃西瓜时讨论,倘若西瓜有嘴,它该吃些什么?“六月定睛瞅了一会儿五月,说,苦。五月不解地问,啥?苦?六月说,娘不是说,吃得苦中苦,方得甜中甜嘛。”[1]172通过儿童之口,说出由食物引发的人生哲理,更具有说服力,容易引发读者的共情。中秋节乔大先生将分供品的重任交给六月,尽管对梨子有着强烈的喜爱,但两个孩子毫不犹豫地将多出的三个分给父母和姐姐。孝顺长辈,懂谦让和分享的良好品质通过五月和六月纯净的孩童形象传达出来,极富教育意义。
饮食中还包含着对于生死的思索。《干节》叙述了吃干吊的习俗,六月对于干吊,又产生了新的思考,“如果干梢是树的尸体,那么干吊是萝卜的尸体吗?”“树死了还能烧,萝卜死了还能吃,人死了呢?”当父亲说出人死了是被黄土吃了后,“他一下明白了山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它是黄土的肚子,只因为吃的人太多,才那么鼓。他接着看见,山的血盆大口像黑白无常一样到处转着,寻找着快要死了的人”,“六月第一次感到人的无常,也第一次感到活着的危险”[1]27。吃西瓜时也有类似的想法,西瓜的死换来的是舌尖的甜,究竟死本身是甜的,还是死后才能拥有甜成为孩子们解不开的难题,但生存与死亡的问题俨然在他们天真的脑海中生发。对于还未经历过生死离别的儿童来说,死亡与生存是最模糊遥远的话题。儿童容易将一切事物拟人化,将其他生物也看作与人一样有思想、可以自我感知的生命,由此引发对生与死的严肃思考。他们对于生和死的认知,仅停留在一个萝卜或是一片麦田的层面上,父亲负责村里人的死亡后事,“他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一片人的麦浪,爹的收割机轰隆隆地从村里开过”。而母亲为村里人接生,六月便“觉得娘像拔萝卜似的,挨个儿从村子拔过去,留下一村的萝卜坑”[1]80。儿童的具象性思维将生死这一沉重严肃的话题变得轻松,人的生命也融归于自然,成为麦苗、萝卜般的简单存在。得来不易的复杂人生在这种氛围的映衬下,获得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豁达和释怀,达到心灵深处的平静和淡然。
“我们的失守,正是因为把自己交给了自我的风。”[1]84作者扎根乡村与传统,立足于秋毫之末,将其通达天地万物的超然领悟,诉诸笔端。其中既有童话般的洁净纯真,又有民俗风情的烟火气味和潜藏着的儒释道哲学,述之以安详的文学语言,带给读者的是一次心灵的沉淀和精神家园的回归,最终达至天人合一的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