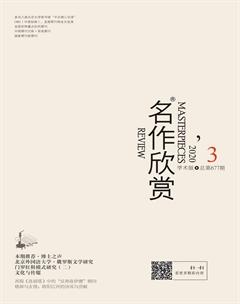“心雨”未停
摘 要:文学创作本就是艺术的再现,它关注表现力、感染力、洞察力以及对读者的启发。施蛰存《梅雨之夕》叙述“我雨中邂逅少女”后的短暂心路历程,但其叙事模式超越了简单的心理还原和分析,背后美学的余味悠长,可谓营造了极富艺术特色的“心雨”。若以审美的眼光重读这部小说,还原人物心境,追问性别认知,观照社会现实,读后更能收获感性的哲思,也可一窥施蛰存进步的创作观、男女观以及深刻的都市思考。
关键词:心理艺术 语境 男女关系 都市心理危机
当前,在对现代新感觉派的心理分析小说研究中,通常关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自我、本我、超我三者的关系,而对小说中的语境、审美要素、心理外因、社会心理层次内涵的关注较少。本文以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梅雨之夕》中的“心雨”为研究对象,由心理环境切入,进一步分析小说中的现代男女关系及其中暗含的女性话语,最后上升到社会心理层次,探讨现代都市病态心理危机,由浅入深,从三个维度分析故事意欲展现的那场不曾停下的“心雨”。
一、雨中“心雨”:心理环境的情景交融
雨——伞——人,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勾勒了才子佳人同撑一把伞的现代版古典“雨中漫步图”,这一叙事场景经过作者有意识的审美选择与艺术加工,由景及情,情景交融。该小说不同于他其他作品的动荡和激烈,如《将军底头》《鸠摩罗什》,而是在清新雅致中引入人物细腻的情感。
初夏时节,江淮流域经常出现一段持续时间较长的阴沉多雨天气,又适逢江南梅子黄熟之时,故亦称“梅雨”季节。作为江南的标志气候现象,梅雨时节空气潮湿阴闷,令人生出孤独凄凉之感。而梅雨持续时间又很长,雨势如烟雾一般空蒙且绵长,很容易与缠绵的情思联系在一起。宋代词人程垓的《忆秦娥·愁无语》借用梅雨意象,写就爱情的绵长愁思:“黄梅雨。新愁一寸,旧愁千缕。”
《梅雨之夕》的故事发生在梅雨季工作日的下午,文中的“我”身处烟雨空蒙的场景,行进间不仅有一种对雨中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感慨,还有一种一切人事物都如真似幻的朦胧,雨的细腻和绵长更给了“我”对美好事物的审美意义上的别样憧憬。这一雨中意境的渲染为心理活动提供了想象、发挥的空间,建构了心理环境(mental environment),借此表现“雨中浪漫”便是水到渠成。
如果将“雨中”看作大的心理环境,那“共伞”就是小的心理环境。伞本有“遮蔽和呵护”的意味,面对雨中佳人“孤寂地只身呆立着望这永远地,永远地垂下来的梅雨”,“我”顿生以伞作为盾牌为伊人“挡着扑面袭来的雨的箭”的冲动,这源于“我”潜意识里男性对女性本能的保护欲。伞一直是浪漫的象征,“共伞”更是爱情的见证。余光中在《伞盟》中表达对“共伞”的憧憬,即“愿你与我做共伞的人,伴我涉过湿冷的雨地”。伞作为雨中的隐蔽,也是“我”与女子仅有的共有空间。不同于戴望舒在《雨巷》中“逢着”一个撑着油纸伞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我”与陌生女子在雨中同撑一把伞,算得上是亲密接触了,对方还是一位完全符合“我”对美的认知的伊人,心理波动则更加激烈。“我”的心理活动正是一次次在伞下偷看女子,并暗自猜测、想象。因为有伞柄的阻隔,“我”恨它阻挡视线,以至于无法“完全观察”,只留依稀中女子的侧脸。但这种物理的阻隔增添了思绪上朦胧的美感,更是让“我”产生了她是多年不见的“初恋”的遐想。在此意义上,伞还赋予了女子诗意的美。
以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语境”(context)a概念进行分析,文中的“雨”是小语境,即文本的“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作者负责展示故事画面,但把“言外语境”留给了读者。此“言外语境”包含阅读主体的主观因素,如身份、处境、知识、心情等,更像是动态的,是大脑的主观产物。故事里的雨映照的是“我”的“心雨”,而不同的读者读《梅雨之夕》,也将建构心中独特的自在语境,于假设、补足、延展中生成自己主观的“心雨”。这也符合“陌生化”和“奇异化”中延长审美时间的观念。
施蛰存点到即止,但虚幻的“心雨”极具感染力,给予读者更大的思考空间,这种创作模式偏向“读者导向型”写作,考虑了“受众”的观感体悟与审美接受。从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人进行推理和思考的自主过程,所以创作应更侧重读者自行思考赏析作品的审美过程。对叙事场景进行“实”的勾勒很重要,可如果作者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倾向,那么小说则会破坏读者的阅读体验。“心雨”一直下,方显意犹未尽、回味无穷。
二、“心雨”的变奏:男性本位的淡化与女性话语的显露
《梅雨之夕》以男性为第一人称叙述,围绕一个让“我”心乱的女子展开。“心雨”于宁静之下暗藏性别认知的“变奏”,宛若一出极具表现力的伦理剧,在“我”对自己、女子、妻子的心理认知波动中,辐射着现代男女的关系,探讨男性对于自己角色的界定以及对于女性的认知。
根据男性本位意识,女性即男性征服或消费的客体。送伞之前,“我”对于女子有“残忍的好奇心”,想看她“在雨中如何自处”。那时,“怜悯和旁观的心理在我身中各占一半”,即便上前借伞也別有目的:“但至少是要求制服她的心在我身里急突地催促着。”如弗洛伊德所说,“被压抑的潜意识和意识的两种心理因素的冲突支配了我们的一生”。“我”潜意识里将女子看作“美的事物”,亲近她是在潜意识的推动下产生的意识。可以说,“我”对于美的事物有潜在的欲望和支配的心理,这放在男性对于女性的认知上,符合男性本位的价值观。
这之后,“我”的一系列心理波动皆受内向投射(introjection)的影响。荣格提出的内向投射指“将主体内容摄入客体之中”,这一心理过程从“我”见到女子将其误认为是初恋情人开始,直到雨停后女子独自离去终了。在此期间,“我”的欲望在自制力的约束之下,始终无法获得满足。“我”展开遐想,并将她与记忆中的初恋少女比对,在屡次的猜测和否定中重新审视眼前的女子,可仍不能肯定是她,也不能确定不是。但因心中有不甘的执念,“我”试图用一切美好的词语来形容这位女子:她时而“娇媚”,时而“端庄”。“我”最初的男性本位意识由于内向投射,在倾注了大量主观好感后,也由“物化女性”变成“美化女性”,戏剧性地渐渐淡化了。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受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影响,但后者侧重“个体”的心理剖析,认为一切心理活动产生于“本我”,即欲望是原动力,故较少关注心理情感发生的社会背景,淡化所谓的“外因”。施蛰存在借用这一手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良,他的心理分析小说在叙事建构上有社会心理学的内涵,是关照人生、映射社会、反思现实的一门艺术。
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写于1933年,故事发生在上海这个当时最繁华的大都市。作者关注的是都市的普通工作者,他思考的是个人情感在都市的喧嚣中“压抑还是释放”的问题,暗含了作者对“个人情感与都市文明碰撞”这一社会话题的关注。这些都是小说男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外因”。
在《梅雨之夕》的结尾,雨停了,但背后的社会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解决,那象征都市被压迫者的心理危机的“心雨”一直未停。就如高尔基所言,“文学是人学”,文学探讨的终极命题应是人活着、存在过的生命意义。物质生活千篇一律,若人的存在只是一串标签与数字,不妨叩问内心,于不可视的内心生活中寻觅“生命本真”,觅得一丝心安。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可谓心理艺术,他着眼于美感与灵性,为生活在现代都市中且不自觉被枯燥工作压抑着的民众发声,在追求效率与物质的理性时代,呼唤人们用心去感受、思考身边美的事物,以此证明人的真实而无可替代的“存在”,其创作背后有着超越文本的深意与跨时代的启迪。
a 小说阅读好比作者与读者进行潜在对话:作者是倾诉者,读者是倾听者。此处借用语言学中的“语境”概念分析这一交互过程。参阅陈晨:《现代修辞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b 施蛰存:《十年创作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 施蛰存.十年创作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 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张炯.文学透视学——文学理论体系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 林树鸣.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 荣格.心理类型[M].吴康译.上海:上海三聯书店,2009.
[7] 陈晨.现代修辞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 朱光潜. 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作 者: 朱泽礽,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