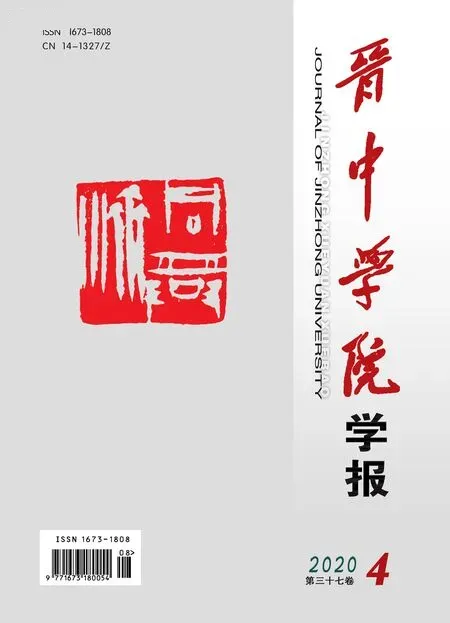近代中国西学传播中的外部因素
张晓艳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山西阳泉 045000)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中国因失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由此进入了苦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许多不甘屈服的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矢志救亡图存,开始注目世界、探求新知,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是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西学东渐”。
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时局的需要,中国出现了“开眼看世界”的先觉者,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二是清政府洋务派从1860至1890年代发起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武器和建立新式的海陆军;设立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培养西学人才。晚清时期选派留学生赴美、日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洋务运动”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以“师夷长技”为手段,以“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是清政府内部的一场救亡运动。三是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为主的“戊戌变法”。他们试图从政治体制上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挽救笈笈可危的满清王朝。虽然“戊戌变法”最终归于失败,但如废除科举、发展工商业、设立新式学堂等“新政”仍然保留了下来。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及洋务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学习西方的主力军。而外国传教士作为西学传播的外部力量,其历史作用同样,不可否认。这些外国传教士介绍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知识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其代表人物有麦都思、傅兰雅、丁韪良、裨治文和李提摩太等。
一、来华传教士的西学传播活动
(一)传教活动
1840年以后,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基督教正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交锋,这些来华传教士肩负着传教的使命,广泛地在各地建立教堂,著名的有上海的天安堂等。英国基督教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开埠后来华,主要从事宣教、出版事业。他翻译《圣经》,设立印刷所,编撰字典,创办报刊,为“福音”传播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传教过程中,出现了教民与当地政府、民众的冲突,各地教案频发。西学东渐引起的文化冲突,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重要篇章。
(二)翻译西书
传教士在翻译《圣经》的同时,还参与翻译了许多自然科学的书籍,对中国的翻译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麦都思联合中国学者王韬、李善兰、管嗣复等和外国学者、传教士伟列压力、艾约瑟等翻译了大量著作,介绍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知识,对西学东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李善兰和伟列压力合作翻译了《续几何原本》《代数学》《谭天》,李善兰和艾约瑟合作翻译了《重学浅说》等。傅兰雅作为英国传教士,长达28年受雇于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与中方学者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合作翻译了大量西书,如他与徐寿合作翻译了《化学鉴原》《代数术》《微积溯源》等。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最大的翻译科学著作的机构,该局译书大致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能了解的最高水平。丁韪良于1863年和美国传教士惠顿翻译了《万国公法》,这本书对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非常深刻,让国人首次结识了“权利、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的思想,开启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丁韪良还组织同文馆的中国学者联芳、庆常等翻译国际法方面的著作《星轺指掌》,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叙述外交制度的专著。他所翻译中国的经典作品《中国的传说与诗歌》,在双向翻译方面贡献巨大。
(三)发展教育和医疗事业
传教士们开办教会学校始于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1818年(鸦片战争之前),他在马六甲开办第一所中文学校——英华书院,其目的是传播西学并藉以传教。他用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办学,采用交互式教学方式教学别具一格广受赞誉。该书院实行中英文双语教学,开设图书馆、西欧文库以促进西方科学知识的在华传播和推广,曾培养了翻译家梁发、袁德辉(林则徐的幕僚)等名人。1834年8月1日马礼逊得急病去世,为了纪念马礼逊,1839年澳门开设了马礼逊学堂,所开设的课程中英文兼备。英文课程有天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化学及音乐等,由外籍教师授课;中文课程有传统儒学经典《四书》《易经》《书经》等,由华人任教。学校突破了中国官学、私学的“四书五经”的限制,课程内容丰富,知识较为新颖,对学生开阔眼界,很有意义,近代人士容闳、黄胜、黄宽等均出自该校。裨治文在1838年创办博济医院,培养了容闳、黄觉、黄胜等中国学生;他同宣教士伯驾医生在广州成立中国医药传道会,开设医院行医,藉此推广福音,这个医院的雒魏林和麦佳迪等医疗宣教士名盛一时。1850年,在上海成立裨文女塾(Bridgeman memorial school),后更名为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裨文女子学校,是上海第九女子中学的前身。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1844年麦都思在上海建立仁济医院。这是上海第一家对华人开放的外国西医医院,是外国教会在中国设立医院的开创之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晚清时期中国的医疗事业。该医院一直延续至今,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迄今已有176年的历史。傅兰雅于1863年在北京同文馆任英文教习,1865年任上海英华学堂校长,后者是一所传教士主持的学堂。1876年,他创办格致书院,后发展成一所西学图书馆,书院创办了科学杂志月刊《格致汇编》,以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给中国引进科学为宗旨。他还任过上海益智书会总编辑,从事科学普及工作,为中国传播西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丁韪良于1865年任北京同文馆教习,1869年至1894年期间为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至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还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筹建大学堂,后创立北京崇实中学(今北京二十一中)并任校长。这些活动客观上对中国新式教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02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兴办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堂之一。他在中国积极推广西方医疗科学,翻译中国古典作品《西游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杰出人才。
(四)创办报刊、学会
麦都思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发起人和奠基人。1853年,他在香港创办《遐迩贯珍》,1856年在上海创办《六合纵谈》,这些中文报刊横跨数个年代,大量介绍西方人文、地理知识及翻译西方著作,如艾约瑟撰写的《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和马传》等在这些报刊上分期刊出。裨治文创办并主编《澳门月报》,刊载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及新旧约全书。1834年,他在广州成立中华益智会,出版推广中文书刊,成为后来新思想的启蒙刊物。裨治文在1833年至1853年期间,创办英文月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意图“唤起全世界基督徒对中国人灵魂觉醒之注意”,主要内容是介绍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地理知识,也记述宣教士们在新加坡、马六甲、槟城、巴达维亚等地的宣教活动,力陈妇女缠足以及吸食鸦片之危害(反鸦片浪潮),力主废除妇女缠足制度,是宣教事业最有成就者。此刊不仅激发西方的教会和基督徒对中国的宣教热忱,更成为当时西方人探索与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还用中英文著述,其中文作品有《关于中国的书信》,宗教书籍有《复活要旨》《联邦志略》和《美理哥合省志略》等;英文作品有《广州方言撮要》《中国丛报》;译著有中文经典《三字经》《千字文》《孝经》;此外他还编辑了《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一书。后人认为裨治文是富有远见的传教士,不仅具有奉献精神和热忱,更明晓语言对宣教工作的重要性,他在传播基督教福音的过程中,以真理和科学启迪了中国社会。李提摩太主要从事传教、翻译、教育、报刊的活动,在上海主理广学会,创办《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创办《中西教会报》,指导中外基督教的发展。这两份报纸是中国报业史上的先驱,并成为日后中文报刊之蓝本,影响深远。他创办广学会,与维新派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的关系密切,做过维新派人士的私人顾问,是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不可低估。
(五)参与清政府教育、政治活动
傅兰雅和丁韪良参与了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在官办机构中从事翻译、教育等工作且卓有成效。傅兰雅是外国人翻译中国科技文献最多的人,他供职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大致代表了当时中国西学翻译的最高水平,为“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科技进步提供了理论支撑。鉴于他的特殊贡献,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和勋章。丁韪良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筹建大学堂,创立北京崇实中学并任校长,担任过北京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他还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翻译法学著作《万国公法》,受到恭亲王的赏识,1885年获三品官衔,1898年又获二品官衔。他组织同文馆的中国学者联芳、庆常等翻译国际法方面的著作《星轺指掌》,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叙述外交制度的专著。裨治文于1839年任林则徐的译员,1844年任美国公使的译员,在《中国丛报》上为中国的销烟行为仗义执言。
二、对于近代西学传播过程中外来力量的评价
近代输入西学有三个主体:一是来华传教士、外国人及相关机构(广学会、教会学校);二是清政府的官办机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三是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及民办机构(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2]。这三者的立场、出发点及其活动都有区别。清政府为挽救时局,实行“洋务运动”,主动提出“中体西用”的主张以吸收西方文化与技术,但是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改良运动,有很强的功利主义的色彩,他们注重技术、自然科学,轻视人文科学。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西学的传播,他们一方面与外国传教士合作翻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类的著作。另一方面又自发地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办报刊、学会,对西学在中国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外国传教士的活动有其独立性,在翻译、教育、卫生领域发挥了独特作用,更多是与清政府和民间组织相互交织,成为二者的有力补充。中外传教士的活动,对封建中国的影响深远,尤其是其翻译、教育、医疗卫生及报刊出版业的活动,带动了国内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事西学传播的活动,并促进了广大民众对西方先进的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认知,成为“西学东渐”过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清政府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及西方传教士在不同领域的活动,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面貌,他们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