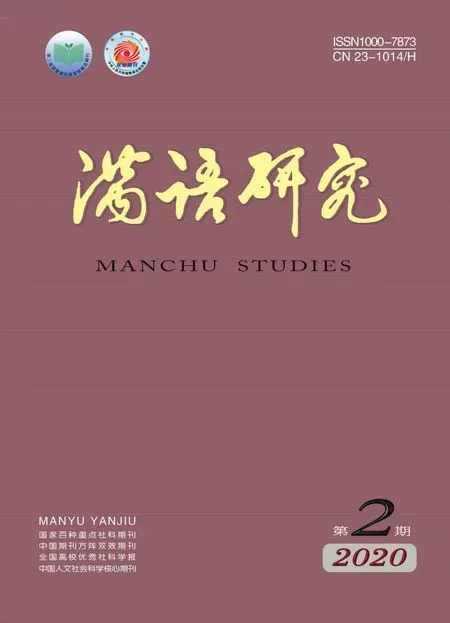人与神的对话
——黑龙江省黑河市大桦树林子臧姓野祭事例
阿拉腾 张 丹
(黑龙江大学 满学研究院,哈尔滨 150080)
作为一种仪式,从结果上看,要求其要有明确的目的;有象征和信息的存在(意识、范式、隐喻等的临时具现化);演示潜在的主张(对意识不到的社会心理事项、社会文化体系中存在的矛盾进行展示或将其加以隐蔽);影响社会关系;文化与混沌(对抗文化的不确定性的主张)。[1]3-24以上这些功能在满族仪式中是如何实现的、满族的仪式为何最终会收敛至程式化的仪式,都是需要阐明的问题。1943年初秋,臧姓家族举行隆重的萨满“巴音波罗力比干衣富陈”(bayan bolori bigan i wecen,富秋野祭),即萨满秋天野祭盛典。这次仪式于1958年由富希陆口述、富育光记录(1)原稿虽标记为富希陆“口述”,但根据该纪实文中所载“(口述人)协助笔录满洲语,兼作齐爷的代书之事”,以及“不顾其琐碎,均收录文稿之中”等内容判断,口述人当初已经就祭祀活动的状况形成大致的文本。形成“大桦树林子臧姓郊祀祭纪实”。此后,其部分内容被收入富育光、赵志忠合编的《满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2]92-95。通过对此次野祭的解读,似乎可以得到以上问题的答案。
一
大桦树林子距黑龙江十余里,原为一片密林,清代屯田后陆续开垦为农田。该屯有住户200多,以满族人居多,有臧、关、吴、张等满族大姓。其中臧氏(sakda hala 萨克达哈拉)家族是附近望族,其男主人臧秋罄曾为村长。全村臧姓虽多,但多数为臧家雇工。臧秋罄主要从事政务,家务则由其弟及弟媳主持。
臧家藏有家谱,显著特点是女性入谱,谱书成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据谱序记载,其族为江东六十四屯补丁屯之老户,起初以渔猎兼农耕为业,后以农业为主。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攻打罗刹时收编入籍,在满洲正红旗牛录率领下,于雅克萨战争后屯田补丁屯。“庚子俄难”时被逼过江,屯居大桦树林子,年长日久人丁兴旺而成望族。该谱总穆昆,皆出自大桦树林子,而独显其俗者,从前六代可稽查其“总穆昆”——即总穆昆达,亦即哈拉达——皆由家主之妻管理。曾祖太母以下均入族谱,分村穆昆则散居各县。臧秋罄家上下20余口人,最高长辈臧关氏65岁,屯人尊称臧老奶奶,据称原为附近名门之秀,能写一笔清秀的满文,其丈夫即臧秋罄兄弟之父,因打鱼而殒命。丈夫去世后,家政即由臧关氏主持。臧关氏重视教育,曾出资办学,在屯中口碑极好。
从以上记载中可总结出如下特征。其一,臧氏家族大穆昆达通常由女性担当,是否有实权虽不明,但大穆昆达的功能在于整个氏族的聚拢上,因而至少握有一种象征性的权力。其二,家庭内部,由丈夫掌握实权,但丈夫去世后,妻子可以主权。其三,此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
因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引发家族内部变迁,导致知识的增加,进而使本地事物的边界及其关系变得模糊,进而引起混乱。女性掌握大穆昆象征性权力,以及家庭内部当丈夫亡故后,妻子可掌握实权的传统,给臧老奶奶复兴本族祭礼、去除混乱提供了条件。据族人追忆,臧姓家祭曾有两次中断。第一次因庚子年逃难。其家族在大桦树林子安家四年之后,方才举行秋天萨满祭祀。除家祭外,尚有山河祭。第二次是在“伪满洲国”建立之时。因社会动荡不安,于1935年秋才得举办家祭,然无山河祭。祭祀的荒废,具体因于对聚拢财富的过分关注而忽视其再分配上。臧氏男主人在世时,曾一心振兴家业,率领族人披星戴月耕种土地,饲养牲畜,醉心于与邻屯的富户比肩,却经常拖欠雇工工钱,雇工的病灾也很少过问。从而引发妻子臧老太太的怨言:“畏根玛发(eigen mafa夫君),你该张罗办办家祭的大事了。自从老额真走了以后,你光顾西地营的那些地和牲口了,家祭荒废,族人心散,再忙于田亩,舍本求末,忘了以礼为先的祖训,就像先不修缮好家室,不唤起众心,能御更大的风塞么?”然而,丈夫仍不在意。于是,臧氏家族有二十来年未曾正式举办祭礼。臧老奶奶“主政”以后,臧氏家族凡遇大事均由臧家老奶奶吩咐做主,逐项办妥。首先,她将住在他屯的丈夫的同族弟弟“七爷”接回来。七爷曾因祭祀荒废之事与臧家主人吵过多次,一怒之下携妻搬到外屯。其次,又将“七爷”的兄长臧博实库及其弟朱阿玛哈接回供养,该二人均为本家族主祭大萨满。兄弟二人分别在7岁和5岁时染上天花,痊愈后又得癫痫,请过许多走屯郎中诊治而无济于事。阖族便凑钱请棲林(鄂伦春)萨满看病,被认为祖上萨满要抓萨满,兄弟二人只有成巫才得痊愈。经同族长老合议后,遂将二人同时选为萨满。一次选中两人,虽较特殊,但众人不敢违拗,害怕神祖慎怒,便举办祭祀,使二人承继臧氏萨满之职。然而,祭祀之后,兄弟二人因家境贫寒,臧家主人又不愿接济,便在外屯打工,长久不归,臧氏家族祭礼仍无法及时进行。本次祭祀,在臧老奶奶的亲自主持之下,由兄弟二人执鼓,七爷当司祭。七爷四屯通信,邀请本族本姓远住本县、外县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得到回应达200余户,近300人,规模盛大。总之,由于社会环境的动荡,导致家族凝聚力降低,需要举办一次大型的仪式消除这种危机。
二
臧氏野祭可大致分为阐述祭祀缘由的报祭、祭坛的准备、在野外连续举办数日的祭祀与欢庆等。其中异于满族寻常家祭之处者为“对答”部分的存在。
1.报祭
大祭日黎明时,由穆昆达率阖族跪在院中香斗前——由太阳未出之前即行活动,以及跪在院中香斗之前的情节判断,该组行为当与北斗星有关。锅头抬黑毛祭猪一口到升斗前,口及四蹄用绳绑好,跪在猪两侧。黑毛祭猪,为常有的习俗;将猪捆绑过来,无疑有强行的意思,说明祭猪仅为供献给星神之用,而非以此与祖先沟通。同时,将猪口绑上,应当意在防止牲猪嚎叫,将自身的痛苦传达到神灵之处。
两位萨满穿全套神服,后面各有男女栽力两名。栽力上身白汗衫,下身神裙,没有神服,各人均执抓鼓;萨满、栽力六人外,左有四大栽力,手执洪乌(honggon神铃),右有四小栽力,手执恰拉器(carki札板)。在左右八栽力后面,更有六小栽力,三女三男,每人手平举哈力玛刀(halmari神刀)。此外,大抬鼓两面,由两位壮年手执大鼓槌;大门口外,站立三名马上男儿,手执长鞭。臧氏族众则站在抬鼓和哈力玛刀仪帐之后。以上服饰,以不同的装束突出两位萨满的存在。同时,以这种阵仗在星神之前展示一族的阵势,表现一族的诚意。
首先申明本次祭祀的目的。由两萨满同时敲响抓鼓开启仪式:大门外驱邪祈福,皮鞭连续甩响,众栽力手打响器。当萨满的抓鼓敲到大约“乌云朱(满语意为九十)”次的时候,众栽力止鼓,萨满兄弟击鼓报祭,“选订吉日,阖族举行盛大隆重的野祭,祈谢山川大地寰宇神灵,富裕的沃土,养育子孙儿女,天天喜乐满堂,年年衣食丰盈,无病无灾,人寿其昌,特恭献祭牲,请神祇恩降享祚”,并且承诺:“所有神事我们精力办,心里祈福的话语向众神表述,不怕苦累,敬祈天神众神多多护爱子孙,多护佑,做不周到多多担待”。萨满阐明祭祀的缘由后,进入牲猪的处理流程。“香斗前宰杀献牲猪,接血,装入血酒盅,两位萨满站起来,将牲血浇洒,敬天,敬地,分别浇洒到主家所有墙角……象征神祇已巡视了儿孙的住室,一切由平安的福血荡涤污秽,吉祥如意”。鲜血既可用来清除污秽,又可增加力量。其后,与满族还愿祭同样,在院中点燃篝火,将猪头和猪蹄褪毛后供在香斗前,猪全身各处割下一部分,扎在草把中,立院中神竿,祭告天神。此所谓“天神”,恐为萨满的各种“天”,同时这种天已经成为退位神,仅从整体上干预宇宙的事物,人们在举办祭祀活动时顺便予以关照。全猪带毛烤肉,族人边烤边祈祷众神来享,烤黑焦半熟后,锅头放大木槽中用清水刮洗干净,在院中煮熟——以上做法,显然都是在极力模仿野外环境下的情景。
牲猪的处理当经过一整天的时间,院中放大木槽数个,族众以草棍、木棍为筷,围在木槽盆四周,沾盐水割烤皮肉与糜子米合吃。饭后,所余猪肉饭菜不得拿进房中,在星光中送入田园旷野,扬撒供乌鸦、小兽、小鸟、小虫食用,猪骨则要埋在院中四角及烟筒下边,“可祈吉祥除秽”。其深层意义应是使牲猪返回神灵所在之处,生死肉骨后再度来到人间,这是存在于北方民族中的循环理念。《尼山萨满》中便展示了各种生物在阴间转世的情景。[3]398
2.祭坛的设置
天明时,阖族齐到屯外二三里远的空地上,设立祭坛祭柱与祭棚。其实,此前已有族众在该处展开准备活动。祭址由萨满卜选,杀公鸡一只“开祭场”,鸡血洒地,鸡骨埋坛下。祭坛地上以彩绳、彩布装饰,四周围以小树,四边设立四门,正面向南,后门面北。正门立兽头柱6根,9尺高,柱上刻有虎、鹿、熊、鹰、蟒、豹等。从正面入祭场,中央为甬道,正北向南处设祭坛,树旗杆、图喇杆,彩旗上各绘有蟒、虎、熊、豹、猫头鹰、鹿等,神坛上摆臧氏家族祖传瞒爷祖像,用木、石、革、茅、陶质料刻镂编绘而成,有30余尊。祭坛两侧设有宿营帐篷,宰牲用棚及灶房,为献牲而备的牛羊圈,活鸡、鸭、飞龙、野鸡笼子,小鳇鱼圭尾及其他大小活鱼的鱼槽。此外,祭场外有马椿、马圈、大车存放之地。以上祭坛的设置可视为阿伊努人及尼夫赫人祭坛的复杂版。后两者的祭坛,亦设置在村庄生活区域里用木桩隔离出来的空地上。阿依努人祭熊的神座,称为“奴夏桑卡塔”(nusyasankata),四周立高约三尺的桩子,以细竹系在一起,并以白杨削成的“木幣”连接后,周围再围以文席,里边陈列有长短刀、弓箭、玉器及耳环等。[4]2-3尼夫赫人则将杀熊的地点用削制的木桩围起,顶上悬挂卷曲的刨花,显示其为圣地。[5]800-801因而看来,在该区域里,祭坛的格式都是相通的。
3.野祭的过程
野祭以启鼓仪式展开,该仪式与此前的报祭仪式相近。次晨,初请阖族最高神灵“德乌特里大神”,供献各种牺牲动物和花鸟鱼虫形状的食物,以及各种山珍。接着,选树叶茂密的古树,锯断,打掉枝叶,竖立在神案前,砍凿德乌特里神像。再用树干刻出虎、熊、豹、鹿、鹰、蛇、鱼等形象。神坛前点燃篝火,在野祭的日子里,族众都住在用松枝苇草搭建的棚中,围绕篝火日夜参祭。
4.仪式中的对话
一般满族祭礼以家祭为主,有满文神谕,言简意赅,背诵即可。而臧氏祭祀,多数祭程并无世传神谕,一切依萨满请送诸神祇之情绪而定,无法未卜先知,随时随事随情自如答对。这便要求满语纯熟晓彻,否则,各栽力不解其意,助阵时便“手足无措,不能侍神”。而栽力之所以不止一位,恐因神谕需要多人互相印证才能准确领会其意。据当事人说,由于世代变迁,谙熟满语且口若悬河者日渐稀少;本次祭祀前,两萨满亦惴惴不安,没有多少把握。然而,臧老奶奶执意诚祭不苟,理由是“臧家诸神祇数年未尽寿道之心,务应均按祖制行之”。足见对于仪式中答对的重视。
为准确解读神谕,臧氏野祭藏有祖传的《臧氏察玛比特曷(bithe)》,即“臧氏萨满本子”。凡萨满、栽力必先学习该本,谙熟其礼义,方可在神前效劳。从前许多氏族都有类似的本子,只因后来仅余家祭,因忽视而渐消失。本子中均为满语日常动作词语,约有词条5 000之多,汇集满语口语词语并参照《五体清文鉴》中的词类编成。词条以类排序,从天文、地理及至花鸟鱼虫等,丰富而详细,方便祭祀时的对话之用。
野祭上需要答对的问题是随机性的。就跳野神时哪部分问题居多的提问,臧拔什库回答,“这事儿不好说,主要看请神降临都做什么,期望神帮助解决什么事。所以,神前答对,实际上就是针对人间要急办的难题,请祖先神灵和负责此项专门技艺的神祇,告之应该具体怎么操作,怎么去顺利如愿地实现”。就此判断,答对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主题可分为祈问年景及生产状况,卜问前程及休咎状况,诊治各种杂症等类别。在此基础上,还需同承担某项专务的神祇做进一步的答对,“确认是何神,该神有何喜好、秉性、脾气;为办好这宗降神程式,主家需做何准备;请送神祇中有何禁忌和规训”等。这些内容都需要使用满语在萨满与栽力之间对答,只有话语想得细致周全,答对虔诚可悯,才会引起神祇的同情、认真。故此,在野神祭礼中,答对尤为重要。
世代臧姓萨满都会告诫大小萨满承继人“满语答对务须严谨用力,不能马虎、应付,要用准确词句,鹰不能说是鸡,南向不能说成北向,是冷是热,是急是缓,是来一位或者来几位,带什么家俱、兵刃、医药、器皿,一定要答对千真万确。”按照臧拔什库的看法,“有些家主只重视祭程、祭祀形式的壮观隆重,似乎神祇们就高兴。其实关键是萨满的迎神素质,还有栽力们的答对艺能,才是最为紧要的。这就要求答对的用语,一定要极为诱惑神祇,迷醉神祇,使神祇听后义无反顾,乐而效力。”为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就要求栽力自如使用满语日常口语。“神祇们都习惯用老满洲话唠嗑,都是方言方音。这在神降时,萨满所说的话就会清楚地觉察到,一听就有百多年前老人到你面前来了。”按照这种说法,准确的答对自然是为求得神灵的欢喜,以便得到神灵的帮助。再深入一层,可看出他们是以满语对宇宙万物加以切分,只有这样,才能与先前的切分结果对接上,觉察到其中的差异,或予以修正,或予以创新。同时,答对时,一要洪亮,否则神灵听不清楚,族众也难以辨听;二是不能慌慌张张,须逐字说清楚;三要条理清晰,事情须一件件讲明白。从而显示出与神灵准确沟通、将沟通结果与族众分享的重要性。
三
臧氏的野祭注重语言的准确性,即罗素所主张的“原子主义”。这种主张认为,实在是由简单而有明确边界的事实所构成,语言则是由简单而有明确边界的表述所构成。通过仪式,臧氏家族将与神灵之间模糊的关系确定下来,使其边界变得清晰。神的意志通过萨满被模糊地提起,再由栽力们予以精确化的表述。这一过程是即兴的,是其关键所在。历史的过程会随着知识的增长而改变,“假如有增长着的人类知识这样一种东西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见我们明天将知道什么”[6]3。因而臧氏家族需要不时地加以重新抉择。仪式并非为了单纯的重复,也非对于既定路径的确认,而是在遇到混乱或在进路不确定时的一种自由选择。当臧氏家族进入迷茫状态时,需要以仪式中对话的方式予以明确,以便对社会规律及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义和确认。
臧氏之表现为各种食物链顶端动物的这种神灵,实为自然事物及其运行规律,而自然事物又包括各种物建及其相互关系。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动及家族内部关系的变迁,事物的轮廓会持续发生变化,因而就需要与神灵进行对话,对其轮廓不时地予以重新确认。另一方面,人与宇宙的整体性关系,亦因知识的增长而需要层次化,对其予以切分,亦需对其边框予以重新确认。而对话之所以是即兴的,是因为感觉是“此时”的,是对旧有框架的一种否定——旧有的框架是由萨满嘴里的古老方言所提示的。而该“此时”正是最近一段时期困扰族群的各种疑问,这些疑问使一族陷入某种存在主义的困境。
由于满族的宇宙观是整体性的,外部事物可从整体上被全部纳入自己的范式之内,因而对他们而言,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时,他们又通过宗教建有明确的愿景,所以,或积极或消极地顺应由神灵指定的路径前行即可。而要神灵指明路径,只需通过精确的仪式过程即可完成。因而必须要有仪式;在仪式上随机解决具体的问题,并灵活制定路径;决定了野祭的对话是随机的。“必须要有仪式”的问题(亦即一种最低的需求)由程式化的家祭即可完成,而随机的问题解决则须由野祭来完成,这是野祭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在野祭中,萨满的感觉通过语言被组织起来,进而被传达给在场的所有族人。萨满的感觉含糊而神秘,是隐喻的和整体的;栽力的整理则现实而明确,是转喻的和具体的。通过语言,形成一个“神灵—萨满—栽力—族人”的连接过程。不论是家祭,还是野祭,都是通过程式和行为去表达的,因而其隐喻、象征的色彩浓厚,需要以直接对话的方式将整体分层,以众人熟悉的语言去确认事物的轮廓。
野祭较家祭更加古老,可将其视为家祭的原型。清代满族在执政以后,野祭渐趋衰微,被程式化的家祭所替代。程式化的仪式,只要正确行使仪式,便可轻松达到与神灵沟通的目的。而随机的应答方式,则需要特殊的技能,因而其操作困难,逐渐萎缩。背后的原因,首先在于母语的丢失;其次为社会环境的变迁,这种变迁导致氏族危机的救助方式发生改变;再次则为乾隆朝《钦定满洲祭天祭神典礼》的示范效应。这些原因最终使满族的祭祀收敛至注重程式化的仪式上。
——以吉林省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