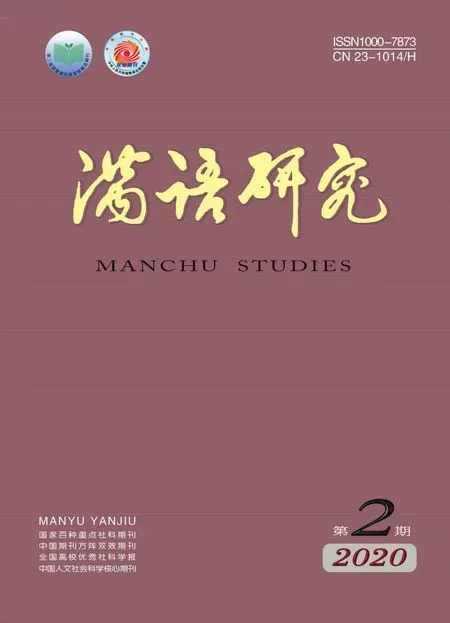清代盛京满文碑刻探析
吴智嘉
(辽宁省民族宗教联络与舆情中心 古籍部,沈阳 110033)
明天启五年(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并营建皇城,盛京地区迎来重大历史转折,由元明时期辽东边镇的卫城一跃成为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清军入关后,对于盛京的建设并未停止。顺治时期,盛京地区设盛京五部,康熙时期扩建外城,乾隆时期设盛京将军,盛京一时地位殊重。有清一代,颁布了数量庞大的诰封、祭文,使之敕建立碑于墓前以彰其开创之功,尤以崇德、顺治、康熙、乾隆等朝为数众多。据《盛京通志》所载,收入“古迹”之碑刻除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等汉将墓以外,清代皇室宗族墓亦有37处之多,足见盛京碑陵规格之隆重。此外,清代重视盛京地区经济与文化,历年兴修土木营建寺宇,亦留有大量纪念性碑刻。因清代提倡“清语清书”,其碑文多为满文或满汉合璧撰写。盛京满文碑刻记录清代重大事件,反映清军入关前后数百年的历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一、盛京地区满文碑的赋存情况及类型
盛京是后金奠定基业的龙兴之地,因此,满文碑刻多为皇帝诰命及追赠敕建碑,正如《雪屐寻碑录》凡例中所言,“以帝诰、御制文、谕祭为最多”[1]11。《盛京通志》将今沈阳等地古墓收入“古迹”一章,而其墓志铭、碑铭等文则以御制文、谕祭、诰赠等形式录入“天章”一节,两者彼此呼应,互相印证,反映出盛京地区的满文碑刻有着其他地区碑刻所不具备的规格和历史价值。
清代盛京地区的满文碑刻按照碑文的内容可分为帝王家世、功勋名臣、寺院碑文、纪念碑文等。
1.帝王家世
盛京所存满文碑多为皇室宗族敕建碑,其中包括为兴京永陵敕建的4通“四祖”碑、盛京福陵、昭陵两通“圣德碑”,顺康两朝敕建的清太祖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穆尔哈齐以及和硕颖亲王萨哈廉墓碑等。此外,盛京地区还存有温庄长公主、端庄固伦公主的两座清代皇室女性的敕建碑。
永陵“肇、兴、景、显”4祖碑均为顺治年间修立。其中,肇祖原皇帝、兴祖直皇帝墓碑修立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墓碑修立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虽为不同年代修立,但4祖碑规格相同,皆通高6.12米,宽1.5米,厚48厘米,碑身双龙盘结,碑额篆书“大清”(daicing gurun)二字,碑身为大理石材质,镌刻满、蒙、汉三体文字,碑座龟趺,碑身阳面刻有碑文,碑阴无字。此4碑现立于新宾永陵碑亭中。盛京福陵圣德碑、昭陵神功圣德碑修立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均龙首龟趺,碑座为花岗岩材质,碑身为大理石材质。两碑均左侧阴刻满文,右侧阴刻汉文。相传碑文均为清圣祖玄烨亲撰,《盛京通志》卷三、《奉天通志》卷二五九均有著录。舒尔哈齐敕建碑及穆尔哈齐敕建碑均在辽阳,今立于辽阳东京陵,碑质为汉白玉,螭首龟趺,碑阳阴刻满汉合璧碑文,满文在左,汉文在右。
义县温庄长公主圹志、辽阳端庄固伦公主敕建碑是盛京地区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清代皇室女性碑志。义县温庄长公主为清太宗皇太极之女,《清太宗实录》记载该女与蒙古联姻下嫁蒙古部落。义县温庄长公主圹志刻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1949年出土于今辽宁省义县城北庙儿沟公主陵,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院。圹志为青石材质,志盖阴刻满汉合璧文字,右侧汉文篆书“温庄长公主圹志”7字共2行,满文为楷体,内容与汉文相同。辽阳端庄固伦公主敕建碑刻立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螭首龟趺,汉白玉材质,碑身盘龙纹饰,碑额阴刻篆书“敕建”二字。碑阳左侧满文7行,右侧刻汉文7行。端庄固伦公主名东果格格,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女,聘于清初五大臣之一栋鄂部主何和礼为妻。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其曾孙齐锡奏请谥号,准赐其为“端庄”,并敕建此碑。此碑现存于辽阳市博物馆。
2.功勋名臣
清入关定都北京之后,顺治帝下谕于盛京各处修葺坟茔刻立碑文,以纪念为帝业立下功绩的大臣。“内三院奏言……今臣等议,臣子荣亲,以王言为重。凡蒙恩封赠官员,似应子孙自备石碑,各将所得诰命刊刻,以垂永久。从之。”[2]97:3自顺治八年(1651年)伊始,陆续在盛京修立众多功勋名臣功绩碑,其中包括清初五大臣之何和礼、额亦都,开国元勋把都里、索尼、何芍图,满文创制者达海,满蒙关系史重要人物恩格德里,民族英雄彭春、僧格林沁等。
顺治朝开追封前朝功臣的先河,在盛京修筑了大量的开业功臣的茔园和碑铭。康熙朝延续了这一传统,本朝功臣去世后,亦于盛京修葺墓园立碑纪念。康熙十年(1671年)敕建奉天将军达都、辅国公大尓差、军事将领彭春等人石碑。康熙十六年(1677年)后,陆续敕建贾弩、噶布喇、哲尔本、渣努、荆山等大臣石碑,均为满汉合璧碑文。雍正朝敕建功臣满汉合璧碑经查仅存一通,为拖尔哈阵亡谕祭碑,现藏瓦房店博物馆。此后,盛京地区的满文诰赠碑大量减少,除碑首等处刻有满文“圣旨”等文字外,碑身为满文或满汉合璧者寥寥无几,这也表明满文盛极而衰的历史过程。
3.寺院碑文
盛京地区的佛教碑刻,始于崇德、顺治时期,在康熙、雍正两朝亦有一定的修建。出于政治于需要,清太宗时期,盛京已与西藏建立联系。为了绥服蒙古,亦为正本清源发展宗教,皇太极设僧录司,颁布诸多佛教禁令,于盛京地区以官方名义修建了广佑寺、实胜寺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喇嘛教寺院,并于崇德八年(1643年)在盛京择四处起工修建护国法轮寺等“四塔”(1)盛京四塔,是指清太宗皇帝皇太极敕建的盛京城外东、南、西、北4座塔寺。东为慧灯郎照,名曰永光寺;南为普安众遮,名曰广慈寺;西为虔祝圣寿,名为延寿寺;北为流通正法,名曰法轮寺。参见“敕建护国法轮寺碑”碑文。。顺治帝继位后,于盛京“四塔”原址继续营建寺庙。顺治二年(1645年),4座喇嘛寺院完工,并刻立四体碑文。
盛京地区早期的寺院碑刻,具有文种多样、年代久远的特点。建于崇德三年(1638年)的莲花净土实胜寺碑,原有碑亭两座,树碑两通,一通刻满、汉两种文字,一通刻蒙、西域两种文字,统称四体文字碑。刻立于顺治二年(1645年)的敕建护国法轮寺碑等“四塔四寺碑”,在四寺中均建碑亭两座,立碑两通,其内容大体相同,记载建立“四塔四寺”的方位、缘由、名称、起竣年代及主要参与施工的人员等。
清代盛京地区的寺院碑刻除沈阳外,又以北宁地区(今辽宁省北镇市)数量众多、特点独特。北宁北镇庙系医巫闾山山神庙,是五大镇山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山神庙,在元、明、清三代历经多次维修和扩建。康熙及乾隆两帝东巡过程中均多次在此处赋诗纪念,因此,清代御制诗文碑及寺庙碑文成为北镇庙碑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其中,以4通北宁北镇庙满汉两体文碑史料价值最为珍贵。该碑始刻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雍正、乾隆两帝亦有修建。其材质为青灰沉积砂岩,螭首龟趺,碑身四周刻游龙戏珠带,碑阳阴刻满汉对书碑文,右起汉字楷书,左起满文楷书,现立于北镇庙御香殿东侧,为北镇庙元明清三代碑林56通石碑中仅存的4通满文碑。
4.纪念碑文
清定鼎北京后,盛京由“留都”尊升“陪都”,因而逐渐形成独特的制度文化、建筑文化、旗民文化和御制典藏文化。盛京太庙、盛京坛子、关外三陵、盛京故宫等宏伟建筑的修缮,以及修建文朔阁等文化政策的侧重,孕育出盛京文化。在这一文化形成过程中,固守满族旧俗,重视“清语骑射”的观念贯穿始终,从而在盛京形成铭刻满文碑以彰祖先创业功绩的规制。
因年代久远、朝代更迭,许多碑石散失无存,现崇德年间所立满文碑仅余数座。崇德二年(1637年)盛京修建钟楼并立碑纪念。该碑砂岩材质,碑首双龙戏珠,碑身两侧刻有番草花纹,碑身阴刻满、蒙、汉三种文字,原立于沈阳城钟楼内,1929年钟楼拆除后,曾收藏于奉天国立故宫博物馆,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崇德六年(1641年)立永安桥碑,碑首红色片麻岩,碑身浮雕蛟龙4条,碑额篆刻“敕建”两字,绿泥板岩材质,阴刻满、汉、蒙三种文字。此碑为今沈阳唯一保存完好且刻有满文的建桥碑。
康熙朝时期,在盛京修建的满文碑有辽阳建园迁墓志碑,为今辽宁地区为数不多的仅以满文书写的纪念性碑刻。康熙五年(1666年),彭春、齐锡、劳满色等为其殁于盛京的先人何和礼、何芍图奏请迁葬于辽阳,康熙七年(1668年)奏准在辽阳安葬并修建墓园。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墓园告竣立碑,碑文详细记载了建立墓园的经过。此碑原立于辽阳市灯塔县公安堡村东阿氏墓园,墓园早年毁平,碑石于1966年被推倒,1978年移存辽阳市博物馆。
乾隆帝遵循东巡祭祖的祖制,4次赴盛京祭陵,留下许多御制诗文及文物资料。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彰显祖先创业之功,制萨尔浒之战书事碑,乾隆帝亲撰碑文,记述萨尔浒之战事及历史意义。碑阴雕刻满文93行,碑阳雕刻汉文94行,正文后刻署款:“乾隆四十一年岁在丙申仲春月,御笔”。碑左侧面另刻有嘉庆帝御笔七律诗一首,为楷书8行计127字,后署款“嘉庆乙丑仲秋中浣,萨尔浒咏事,御笔”,署款下刻有篆书“嘉庆御笔”印两方。该碑为记录萨尔浒之战实物资料。1993年,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定为国家级一级文物,现藏于沈阳故宫东路大政殿东侧。嘉庆十年(1805年)十月,嘉庆帝仿高宗纯皇帝立萨尔浒战书事碑之制,命盛京将军福俊,于杏山东(今辽宁省锦县杏山乡和屯东)立“太宗文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碑”。碑身正面阴刻汉文,背面阴刻满文,记述松山之战清军大破明军的战绩。碑文如今已模糊不清,但两侧嘉庆帝题《望杏山松山即事诗》及道光帝题《望杏山松山述事诗》仍清晰可见。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帝为庋藏《四库全书》,仿杭州天一阁形式,在北京皇宫、圆明园、盛京故宫、承德离宫修建四座大型书库,分别命名为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敬殿阁。乾隆帝分别为此4个典藏经典的书阁作记,并于同年于阁前竖碑勒石予以纪念。盛京文溯阁碑为汉白玉材质,其首、身、座两侧边缘均刻以云饰,碑阳阴刻满汉文对书的乾隆帝所作“御制文溯阁记”,碑阴阴刻满汉文对书乾隆所作“宋孝宗论”。此碑现藏于沈阳故宫文朔阁东侧碑亭之中。“御制文溯阁记”阐述了文溯阁命名的立意及意义;“宋孝宗论”以宋孝宗之孝为戒,警示其子孙牢记“天子之孝,以不失祖业为重”,并指明其东巡、南巡之志“不在游山玩水之小节”,是为“溯涧求本义而予不忘”。(2)清御制文溯阁记,清高宗弘历撰并书,民国拓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盛京地区的满文碑刻经历了清代初期的兴盛之后,伴随着满文的势微日渐衰落,数量有所减少。现存凌海嘉庆、道光皇帝题诗碑盛京地区遗存年代最晚的含有满文的清代碑刻。凌海嘉庆、道光皇帝题词碑刻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和道光九年(1829年),青石材质,碑阳阴刻楷书汉文,碑阴阴刻满文。因风雨剥蚀,碑文难以识读。该碑系嘉庆、道光两帝东巡盛京,途经凌海观纪胜碑有感而作。
除上述数类碑刻外,今辽宁地区也留存了一些有关锡伯族历史的满文石碑,保存完整的有太平寺碑、锡伯纪功碑、三音那功铭汗马碑、达子营锡伯族伊拉里氏墓碑等。其中有满文书写且影响较大的为太平寺碑。盛京太平寺,俗称锡伯家庙,位于实胜寺西邻,创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乾隆年间曾增建和改建。寺内原有石碑两通,今仅存其一。太平寺碑立于嘉庆八年(1803年),阴阳两面均镌满文,记载了锡伯入清之后的变化和沈阳太平寺创立的经过。太平寺因年久失修旧迹无存,此碑却流传下来。该碑为浅黑色石料制成,碑身竖向长方形,下部为须弥座式底座,雕有莲瓣纹,中间刻有花卉纹饰。碑额两面均刻有阴文大字满文四字,满文为tumen jalan enteheme ulabuha,汉译为“万世永传”。碑阳刻小字满文5行24字,汉译为“嘉庆八年七月十六日恭立,袭爵领催珠林泰、庙祝华申保、领催纳丹林、明保”,碑阴刻小字满文12行220字,残16字。此碑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
二、史载散失的盛京地方满文碑
史籍有载、但实物遗失的盛京地区满文碑数量较大,其中史料价值较为珍贵的有慈恩寺碑、敦达里陪葬墓碑、扬古利碑、索尼纪世德碑、议政大臣索尼碑、明珠墓碑、盘山得胜碑、文惠贝勒墓碑、和硕公主坟碑、锦县纪胜碑等。
慈恩寺碑原立于沈阳市沈河区大南街慈恩寺院内,现已无存。其碑为顺治二年(1645年)刻立,汉文碑文为《奉天通志》收录,主要记载了建寺命名原委、选址、重修、捐资等情况,是研究盛京地区佛教传播发展的重要资料。因石碑损毁,满文碑文史籍查无,无法再现。
扬古里墓碑位于沈阳市于洪区陵东乡山岗子村,原有墓碑两通,今已无存。该碑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刻立,记载了扬古里辅佐努尔哈赤、皇太极开创伟业的军功及封赏。扬古里,史籍亦载扬古利,舒穆禄氏,世居珲春,其父郎柱,为库尔喀部首领,后金时期率部众归附,太祖以扬古利为额驸,属满洲正黄旗,为清代开国功臣,死后尊享昭陵左配之制,康熙追封谥号为开国佐运功臣武勋王。
史载盛京地区索尼家族的碑刻有四通,分别为索尼曾祖诰封碑、索尼祖父母诰赠碑、索尼父母诰赠碑、索尼记世德碑。现仅存索尼曾祖诰赠碑,其余三碑已佚。索尼曾祖诰封碑于1983年在沈阳市妇婴医院出土,今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为顺治十六年(1659年)年所立。史载索尼辅佐四朝有功,“诰封三代”。(3)《沈阳市文物志》,碑刻,第219页。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世祖覃赠索尼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三代,其中索尼父母诰命碑文已为《奉天通志》所收录,而索尼祖父母诰命碑及曾祖父母诰命碑史载碑文无存。索尼纪世德碑刻立于康熙六年(1667年),为索尼祖宗所立,碑文盛赞索尼祖先功绩及索尼的辅佐之功,亦反映出索尼家族在清朝享四朝荣宠的特殊地位。此碑今已无存,满文碑文亦无从可考。
史载盛京地区亦存有得胜碑两处,一处为盘山败祖大寿得胜碑,一处为锦县伐明纪胜碑。史载盘山败祖大寿得胜碑在盘山县东北26公里处,相传为清初败祖大寿于此,遂勒碑以纪,“今碑颓祀,字亦摩挲不辩矣”(4)《东三省古迹遗闻》,第99页。。锦县伐明纪胜碑在锦县南杏山屯东旁,民国时期该村村民掘土出石碑一块,“高八尺余,上有满汉文字,其汉文越纪战功永垂千古。据考古学家言,此乃清太宗战胜明师之纪念碑也,后闻日人以五十金购去云”(5)《东三省古迹遗闻续编》,第122页。。此二碑应系皇太极大凌河之战及松山之战得胜所立。这两次战役为后金与明战争史上的著名战役,皇太极借此得以巩固汗位,扭转屡攻宁远不胜而失的锐气,基本扫平了明朝设置在关外的军事力量。后乾隆帝评价此役:“我太宗大破明师十三万,擒洪承畴,式廓皇图,永定帝业”,嘉庆帝也说:“太祖一战而王基开,太宗一战而帝业定”(6)《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本。。其中“太宗一战”指的即是松山之战。
除此之外,亦有一些原碑满汉合璧,现汉文可考,满文无存的情况。如,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于东陵区英达山村的额赤都墓碑,原为满汉对书,发现时已断为三块,且满文部分遗失,所存均为汉文。
三、盛京满文碑刻的历史价值
1.年代久远,承前启后
盛京地区的满文碑刻,始于后金,以战事碑、寺院碑、界碑为主。现存盛京满文碑最久远者可追溯至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所刻立之辽阳大金大宝法师宝记碑,满汉两体,汉文为杨于渭撰文,满文为老满文,成文年代比新满文的创制尚早两年,为国内现存为数不多的老满文碑刻,故弥足珍贵。老满文碑刻的存在,丰富了国内馆藏老满文资料,是早期满文书写形式和历史的有利补充。此外,盛京所存顺治二年(1645年)以前的满文碑刻,为盛京地区独有,可补中国清代碑刻历史之不足。
满族兴起于中国东北,其文化源属女真,本无勒碑为记的传统。清随明制,延续中国的碑刻文化,其突出特点就是以满文为特征的两体文或多体文碑刻书写体例的创制。满文体例碑文的诞生和发展,逐渐形成了满文碑刻体例的规制。清自顺治十年(1633年)始,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逐步议定皇族王、贝勒、公、镇国公及普通公侯官员的碑式形制,碑文也有成例,不得擅自撰写镌刻。自此后,北京盛京两地碑文规制基本相同。盛京满文碑刻文化肇基于清代碑刻规制创建的初期,既有学习明制的初创期特点,又因循清定鼎中原后的规制,是整个清代满文碑刻的见证者,其价值不容忽视。
2.特点鲜明,独树一帜
盛京地区存有多通清入关前的碑刻,研究价值较高。如,天聪四年(1630年)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崇德三年(1638年)盛京莲花净土实胜寺碑、崇德六年(1641年)盛京“重修无垢净光舍利佛塔碑”、崇德六年(1641年)盛京“永安桥碑”等,这些碑刻都保留了清代初期满文石碑的特点和形貌,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清自顺治十年(1653年)始,逐步议定碑式礼仪规制。为犒赏军功卓著的功臣将领,仿照明制,准许阵亡、病故的功臣造亭立碑,此后又逐渐开追封先臣的风气。顺治十一年(1654年),议定恩裳王公诸臣造坟立碑则例,“定给诸王、世子、贝勒、贝子、公、侯、伯、及内外大臣、造坟立碑建亭银两则例。和硕亲王、八千两。世子、六千五百两。多罗郡王、五千两。多罗贝勒、三千两。固山贝子、一千七百两。镇国公、辅国公、俱九百五十两。镇国将军、四百两。公、侯、伯、俱四百五十两。精奇尼哈番内大臣固山额真、大学士、尚书、镇守外省昂邦章京、俱四百两,”[2]90:50“内三院奏言……今臣等议,臣子荣亲,以王言为重。凡蒙恩封赠官员,似应子孙自备石碑,各将所得诰命刊刻,以垂永久,从之。”[2]97:3顺治十二年(1655年)后迎来刻立石碑的高峰。顺治十三年(1656年),议定封赠官碑则例,“内三院奏言、封赠等官墓碑。考之会典、止有碑式大小。其碑上应用何文、未有成例。查故明封赠之官。墓碑称诰赠某官某人之墓。亦有子孙自将封赠诰命之文、刊刻碑文者。亦有不刊刻者。今臣等议、臣子荣亲。以王言为重。凡蒙恩封赠官员、似应子孙自备石碑。各将所得诰命刊刻、以垂永久。从之。”自此之后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于北京盛京多处刻立石碑,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盛京地区的“永陵四碑”“福陵碑”“昭陵碑”均为此时刻立。难能可贵的是,盛京地区还保留了几通顺治初期的满文碑。如顺治二年(1645年)刻立的敕建护国法轮寺碑、顺治八年(1651年)刻立的恩格德里墓碑等。这些含有满文的墓碑刻立于清代墓碑规制形成之前,许多碑文在行文、格式、体例、规格等方面,依旧保存着清入关前碑刻的特点。
(1)多文种布局较早出现,文字格式颇具意味。盛京地区在清代早期即已出现多文种合璧的满文碑刻,顺治朝的多文种碑文数量亦高于其他地区。顺治朝于北京刻立满文碑刻66通,其中64通为满汉合璧碑,一通为满蒙汉三体合璧碑(7)祁今馨:北京顺治朝满文传记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盛京地区最早出现的四体文碑为刻于崇德三年(1638年)的莲花净土实胜寺碑。顺治二年(1645年)刻立“四塔四碑”,分刻满、汉、蒙、西域四种文字,为盛京地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
满文碑刻以左边满文、右边汉文为常例。北京地区满文碑刻之顺治十年(1653年)刻立一等阿思哈尼哈方绰偹碑文、顺治十四年(1657年)塔尔布诰封碑、顺治十六年(1659年)皇清诰赠光禄大夫三等伯固山额真叶臣之碑、康熙三年(1738年)朝艮三代诰封碑等,一反常例,均为汉文在左,满文在右。同期刻立的盛京满文诸碑则无此种情况。
(2)史料价值珍贵,可补官方史料之不足。清代盛京地区的满文碑刻既是文物实物,又是史料依据,作为待发掘的珍贵历史文物,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对于深入研究满族家族史、清前期历史文化、满族语言文字和东北地域风俗历史均大有裨益。如,康熙朝尼满家族四世诰封碑,以满汉两种文字记录了尼满家族自其曾祖父至尼满共四世为清朝开国建树功勋屡受褒封的历史。尼满之曾祖父、祖父、父亲之名未见史载,对该碑文的解读填补了清史之不足,具有较高的价值。[3]
3.取材当地,材质各异
清代盛京地区的满文碑多由汉白玉、火山岩、青石质、花岗岩、大理石、红岩石、红砂石、辉绿岩、碑砂岩、绿泥板岩、沉积沙岩等构成。材料均取自当地,因碑主人的身份地位不同,又因材质的珍稀程度,其碑身、碑头、碑座均有差别。
清代早期的满文碑以碑首汉白玉、碑身大理石、碑座花岗岩为尊。新宾永陵四祖碑,碑首均为汉白玉,为东北地区少有的石材,其碑身为大理石,亦属高等级的石材。顺治朝康熙朝诰封之皇亲贵胄、王公大臣诰封碑多以汉白玉为尊,额亦都、何和礼、巴都里及达都、穆尔哈齐、萨哈廉等人,均配享汉白玉碑质的规制。此后,汉白玉、大理石等石材日渐减少,能以花岗岩制作碑首,大理石制作碑身已属不易。盛京福陵圣德碑、昭陵神功圣德碑均系此时满文碑石材的代表。乾隆朝以后,碑刻多以积砂岩、青石岩、辉绿岩为主。
4.满文书写,意义重大
与北京地区遍立满文碑系昭示政权色彩和文化“首崇满族”的措施相比,盛京地区的满文碑刻是对满洲文化的延续和发扬。碑文中使用满文不仅仅是记录历史信息的工具,更具有保持满洲民族精神、彰显旗人身份地位的作用。盛京满文碑刻虽多数为满汉合璧,但满文书写仍有其独特的价值。
(1)满文碑文有拾遗补缺,易于解读的作用。盛京满文碑刻因年代久远,许多碑文漫漶不清,满文碑可互为补充。更有满文留存,汉文遗失的情况,满文碑文就成为解读原文的唯一线索。如康熙朝尼满家族四世诰封碑,由于汉文满文部分均因漫漶磨蚀殊难辨识,但汉满文两部分对译互补,仍能恢复其原文。再如,太平寺碑记,原有汉文满文碑各一通,今仅存满文,其中记载的锡伯原住地、顺治康熙年间锡伯族迁徙历史等重要信息只能以满文来复原。同时因汉文碑文无存,也留下了sibe aiman daci hailer dergi julergi jalin tolo sere birai šurdeme tehe bihe。
(2)满文书写保留了难得的历史信息。满文碑文于细微处,保留了汉文等其他文字中所未记录的历史信息。如,敕建护国法轮寺碑记中,汉文记载“四寺”起工时间是崇德八年(1643年)“仲春”二月,满文载为niyengniyeri dubei biya,即季春三月;再如,该碑满文部分载ashan i bithei da hede nikan bithe ubaliyambuha,意为“学士黑德译汉文”,汉文碑文中无此记录,弥补了汉文碑文的不足。[4]再者,满文书写保留了关于满族语言文化的历史和信息。如,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事书碑中,左翼作dashūwan,右翼作jebele。dashūwan满文本义为“弓靫”,jebele满文本义为“撒袋”。满族出征或出猎,dashūwan“弓靫”系在其身左侧,jebele“弓箭袋”系在其身右侧,此为满族旧俗,此后则以dashūwan、jebele分别指代军队之左翼与右翼。再如其碑文中,汉文“相距百步”,满文作emu kalfin i dubede,kalfin意为“一挑箭”,即满弓一箭射出之距离。因此,使用的文字不同,折射出文化不同,所反映的信息也不相同。
清代盛京满文碑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盛京地区满文碑刻尚无科学的整理,绝大多数满文碑刻无拓片可寻,研究上仍有很多空白。清代修撰的大型丛书,如,《盛京通志》《盛京通鉴》《碑传集》《八旗文经》,清末民初的诸多人文考察,如,《满洲碑记考》《东三省古迹遗闻》《奉天古迹考》,以及新中国以来编纂的《辽宁省志·文物志》《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碑志精粹》等,均未收录满文碑文。北京地区借助民国和建国初期积攒的满文碑文拓片等资料,形成了《北京馆藏满文碑刻拓片总目》《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北京图书馆历代中国石刻拓片汇编》等大型图书,比较完整的保存了北京地区的满文碑刻信息。而辽宁错失宝贵的抢救整理的时机,现今许多满文石碑迁徙辗转缺乏保护,大量满文碑文信息丢失,这无疑是巨大的遗憾和损失。当今古籍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未来盛京满文碑刻信息数字化保护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