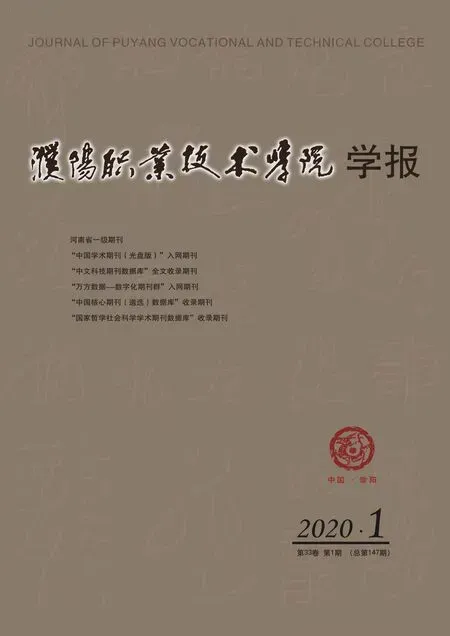宋元画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
侯玉娟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自20 世纪80 年代起, 伴随着沈从文文集的出版、传记资料的丰富、文学地位的正名,在学术界中逐步掀起了一股“沈从文热”。就近30 多年来的研究情况看, 对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思想内涵(新宗教观、泛神论、巫楚文化等)和叙述文体(散文化、诗化等)两大方面。可能是因整体研究起步较晚,所以其作品尚有较广阔的阐释空间。
通过阅读沈从文的自传及其小说文本发现,沈从文与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宋元画有着不解之缘。他自幼对绘画有着极高的天赋与悟性, 青年时代就曾想过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跟随刘海粟学习绘画。艺术是在人的视听感觉之下得以显现,与人的审美体验直接相关, 而文学正是在审美即感性显现方式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得以发展, 所以传达精神理念的文学需从艺术中汲取营养以获得人们情感上的共鸣。 而沈从文正是从宋元画中找到了小说的感性显现方式, 在小说创作中常以宋元绘画的取景方式来描写现实人文景观。
一、国画造诣的潜化
沈从文曾明确表示自己“常常向往做个画家”,据金介甫与沈从文谈话,小说《赤魔》所写的想做画家的事就是沈从文自传性表述。
追溯作家的学习经历, 幼年在私塾读书, 学习《幼学琼林》《孟子》《论语》《诗经》等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三姨父聂仁德更是常向其讲述“宋元哲学”,诠释“大乘”和“因明”,长时间的熏陶使宋元的精神文化逐渐溶入到沈从文的血液中。
从军时在湖南将领“湘西王”陈渠珍身边做书记, 沈从文的主要工作是帮陈渠珍整理他收藏的文物书籍。对年轻的沈从文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学习传统文化(以宋元明清书画艺术为主)的机会。 沈从文曾自述说:“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这里约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全都由我去安排。旧画与古董登记时, 我又得知这一幅画的人名时代同他当时的地位……由于习染,我成天翻来覆去,这些大部分也就慢慢看懂了。 ”[1](108)这样的机会使得沈从文直接、具体地感受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魅力。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尤其是宋元以后的绘画传统的熟习、了解,也使沈从文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形成一种规范。
在中国传统的文艺观念中,诗文、书法、绘画三者的内在精神是相互融通的, 沈从文的绘画爱好也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 韩立群谈及沈从文的创作时提到沈从文在表现湘西的自然风景时常以宋元画来比拟。 沈从文也常在其散文中有情不自禁的流露:
尤以天时晴明的黄昏前后, 光景异常动人。完全是宋元水墨画,笔调超脱而大胆。[2](149)
除上述间接的蛛丝马迹的表现外, 沈从文也直言中国传统绘画(尤其宋代绘画)带给他的启发。 如在《短篇小说》中,他说他在“宋元绘画设计”与“短篇小说创作间”找到了一种共同的慧心、匠心,即认为逼真的写实不是艺术品的最高成就。 对何处施彩,何处着墨,何处留白,“设计”二字才是艺术品的重要处。
二、水墨:浅淡简洁中的孤寂
受宋元超然淡泊文化精神的影响, 在行为方式上,沈从文给人一种平和、寂寞的印象。 他曾说过:“我在孤独中寻求生活和思想, 也在寂寞中得到教育。 ”[3](340)汪曾祺在也说:“可以说是寂寞造就了沈从文。 ”[4](278)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其总体之“色”色相素净、色感清冷,整体画面不是错金漏彩、绚丽灿烂,而是清水芙蓉、落尽繁华,具有“水墨淡彩”与“无色之色”共融的素色旨趣。
通过整理小说的颜色词发现, 沈从文惯用色相简洁、单一的颜色,如白、黑、红、绿、青、蓝等,少有杂色,即少有颜色复合词。受宋元画中“水晕墨章”效果的影响很大,多用墨色晕染平淡幽静。 所以,作品中的画境色彩多是以水墨为基础,再施以淡彩,整体色相少有铺张的浓艳绚烂,少有突兀的感官冲击,呈现一种“素色”旨趣。 如沈从文《湘西》中对沅江上游风光的描写:薄云是银红、紫灰的,小渔船的袅袅白烟如一块白席,再添上绿头水凫,“随意割切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5](379),让人不由得想起南宋夏圭的《溪山清远图》,在天水施以淡墨,以水化墨,以墨破水,有一种“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意境。
墨与水自然是不可分割的。 沈从文笔下有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内视性色彩——“无色之色”,即水色。作家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即已坦言“水”对其创作的深远影响。沈从文笔下的水色时而豆绿,时而泥黄,时而清白,然在更多时候,“水”则弥漫于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淡淡的清新、润泽之境。 沈从文善于写水,写河上的事物,写雨中的景观,比如说他作品中常有水上木筏的描写,更有乡野间的“落雨”乐趣。水的清新、绵延、细腻在这“无色之色”中惟妙惟肖地展示出来。沈从文小说的色彩艺术不是一种强烈、突兀的直观感,却在于一种浅淡、素雅的渗透性。
沈从文小说中的色彩以水墨为主, 往往透出一种孤寂。 但其在最关键处着力,不尚泼墨重彩,而是简单淡雅、粗笔勾勒,通过水墨描绘出一个又一个或美丽、或苍凉的故事。
三、人物:重神忘形的美学风格
中国传统人物画往往不在乎外在形象有多相似, 更在意气韵和神形, 中国画论上又称人物画为“传神”。 宋元绘画中也多注意人物的内在精神和气韵的丰满。像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图》,画面上几乎没有对人物的细节做过多的关注, 而是潇洒地以水墨泼洒而成,甚至其脸部的各个器官:眉、眼、鼻、嘴拥成一团。仔细观察才可看出嘴角微微有一丝笑容,虽然步履蹒跚、 醉意朦胧, 但那双眼睛仿佛看破一切,绝妙地表现出仙人的精神状态看似糊涂,但却熟谙世事。
沈从文受宋元绘画传神的妙理, 对于人物外在的具体形象不作过多的描述, 而重在表现一种自然人性的美。
在《龙朱》中对龙朱这位美男子的介绍是光明鲜艳:“在这人脸上有种孤高鄙夷的表情, 嘴角的笑纹也变成了一条对生存感到厌烦的线……黄色日头照到他一身,使他身上作春天温暖。 天是蓝天,在蓝天作底的景致中, 常常有雁鹅排成八字或一字写在那虚空。 龙朱望到这些也不笑。 ”[6](78)在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作者塑造的是人物的精神气质和风韵,并非是具体的形象。所以,虽然读者无从知道龙朱这个美男子的样貌,但他高贵、谦逊且有着淡淡忧伤的精神特点却已经被表现得栩栩如生。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 对于人物的描写有时不在意清晰线条与轮廓,却注重写意,追求神似。 《边城》中翠翠被美丽的自然风景环绕, 在自然中长大的她眼睛清澈明亮。青山绿水更是映衬得翠翠楚楚动人、纯真美丽。 再看沈从文笔下翠翠的画像:天真善良,潇洒自在,但“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7](75)。 沈从文并没有详细地描写翠翠的面貌,但对她动作形态的描写,将翠翠的羞怯、警惕、娴静表现出来,比文学中刻画人物的模式更胜一筹。
这样诗意的、内涵丰满的艺术效果,假如脱离了沈从文对宋元绘画的以“传神”为核心的人物塑造原则的运用,几乎是很难实现的。
四、意境:无言的阐释
沈从文深受庄子和屈原思想的影响, 这从他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来,在《沉默》中曾以庄子自诩,小说中也多有主人公读《庄子》的场景。 沈从文的孤寂哀怨与屈原的怨愤缠绵有着强烈的共鸣。 而宋元文人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既无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却又不能超然地置身事外, 宋元画的特殊意境正是在这旷达和哀怨混合的复杂情感中形成。 如宗白华所说:“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 ”[8](23)这就使沈从文在宋元画中找到了契合点。
《山静居画论》中有记载欧阳修的说法:“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之,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之趣,简远之心难形。”文人常借目之所及的自然人事,如菊、竹、高山、渔隐,来表达心灵感受,但其中蕴含着文人画家内心或豪放或抑郁的情绪,这些情绪也多因国因家而起,而观画者也未必能悟到。像苏轼的《枯木怪石图》,画面内容虽很简单,但却是其用心画出来的,其一生饱经忧患,曾因“乌台诗案”在潮州入狱,后又被贬。 图中的怪石可看成政治压力,枯木则是其本人的象征,虽受到打击却依然能顽强成长,即使过程中有点畸形。
同样,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也是这样,在淡淡的笔触中蕴含着深沉的忧愁, 有着别人不能读懂的东西和不能体会的感情。 他自己说过:“应当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眼泪, 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来表现的。 ”[2](91)沈从文的小说风格多是淡泊、超然,但其背后确实隐含着强烈的时代焦虑和对底层人民的同情。
《菜园》中的母子在作者笔下颇有几分“种豆南山下”的淡泊情致,但是就在这消闲的氛围中,却隐伏了革命的热力、紧张以及对社会的热情,儿子儿媳最终还是为自己的信仰死去。对于一家人的死,作者只是寥寥几笔, 自然而然地交代出来。 没有任何主观评论, 场面也极其平静。
沈从文用平淡委婉的笔调书写出隐痛和感伤, 比激烈的言辞更深入人心。 如倪云林笔下的画,以清淡、平缓的笔法画出自己的悲愤抑郁, 更能让人体会到他所压抑的痛苦。
又如《丈夫》中,乡下丈夫进城探视在码头卖身的妻子, 目睹了妻子的卖身生活。 年轻的妇人为了乡下的家庭在城里卖身,作者却用“极其平常”来形容。 在这里作者不断使用 “简单”“平常”等词语,看似说明现象的正常性, 但他越是强调平常, 越凸显出这件事情的荒诞性。小说最后丈夫在回家前,妻子照例拿钱给丈夫,此时的丈夫却一改往日的温顺,将钱票洒在地上开始哭泣。 这个动作把丈夫内心的屈辱、痛苦全都写了出来,也表现出作者内心的悲哀。
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特别强调:“你们赞叹我小说的清新,却忽略背后的热情;你们赞叹我文字的朴实,却忽略其中隐忍的悲痛。 ”他用理智过滤掉内心的苦痛, 用表面的平静代替内心汹涌的激流。看似毫不经意的缓缓叙述,却能让人为之动容。
沈从文长期接触中国传统画, 他一生又有着庄子旷达的理想,再加上他和屈原同样不济的命运,使得宋元画能在他的创作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沈从文常以淡淡的水墨来描神画物, 在寂静幽淡的笔调中弥漫着一股无边的寂寞和哀伤。 他的作品多清逸超旷,格调清雅,读来就像是欣赏一幅绝美的宋元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