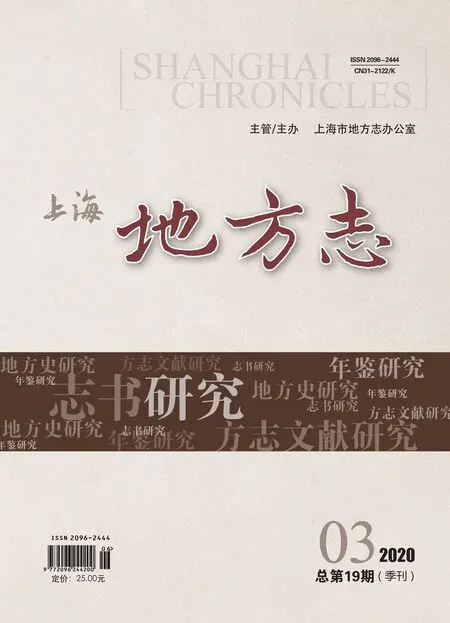论修志本质观念嬗变和笔法演变
韩章训
古今修志实践反复证明,无论是一个时代修志者还是一个集体修志者,其修志观念是至关重要的,是决定修志成败的。就一个修志集体而言,其修志观念与其修志成败关系,恰如清人史致康所云:“心之所之谓之志,记事之言亦谓之志。无是心者弗论矣。有是心而无同是心者,亦无以遂其心而成其志。府之有志,所以记事也。记之于心久而或忘,记之于笔远而弗失,若有志乎此,而又皆有志乎此,合众长以为长,洵所谓有志事竟成者也。”①史致康:《重修嘉定府志序》,同治《嘉定府志》卷一。这里所言“心”即指存在于修志者脑中的思想观念。修志本质观念是方志编纂学中的核心概念,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它总是指导和制约着整个修志事业。修志笔法是修志本质观念的衍生物,其中基本笔法是方志写作学中的核心要素,它也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也总是指导和制约着整个方志写作过程。从史学角度看,无论是修志本质观念嬗变问题还是修志笔法演变问题,都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都是一个实践问题。在此前方志学界,从未有人对修志本质观念嬗变和修志笔法演变两问题进行过纵向系统研究,这实际上也是此前方志编纂学研究的一个缺憾。为促进和深化方志编纂学研究,本文分别对修志本质观念嬗变和修志笔法演变两问题作如下阐述。
一、修志本质观念嬗变
所谓“本质”属哲学概念,它所反映的是隐藏在事物现象之后的那种根本特征。所谓修志本质观念就是从哲学高度来回答修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以现代哲学观点去审视,在古往今来的修志活动中,始终都存在着修志主体与客体的矛盾。也正因为人们对修志中的主客体关系往往持有不同见解,这样形成了不同的修志本质观念。纵观修志本质观念的演化历程,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阶段:
(一)以客体说为主流阶段
此阶段涵盖汉唐至宋元。在此阶段,一般学者都认为,修志过程就是修志者如实记载客观地情的过程。彼时人们修志本质问题的认识有两种典型表述。一是源于班固的“实录”说。班固评司马迁《史记》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②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此后修志界许多人就把“实录”视为修志的一个基本规则。如唐辩机称赞《大唐西域记》曰:“或直书其事,或曲畅其文。优而柔之,推而述之。务从实录,进诚皇极。”①辩机:《大唐西域记赞》,《大唐西域记》卷末。宋陈秀实引太守直阁王公语曰:“天下郡国皆有志,而庐陵独阙,意者其有待乎?子盍有以成吾意,凡四封之内,一事一物,有可以备实录者,咸采摭以告。”②陈秀实:淳熙《西昌志序》,乾隆《泰和县志》卷首《附录》。二是“直文”说。东晋常璩化用班固“实录”思想,率先提出修志“直文”说。他说:“凡此人士,或见《汉书》,或载《耆旧》,或见郡纪,或在《三国书》,并取秀异,表之斯篇。其洪伐弘显者并附载者齐之,其但见名字而不详其行,故或以有传无珍善,阙之,以副直文为实录矣。”③常璩:《华阳国志·益梁宁三州三国两晋以来士女目录》文末。由此可见,在常璩看来,“直文”就是“实录”的另一种表述。自此之后,有的直接沿袭常璩的“直文”说。如唐徐坚曰:“方志直文”。④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一。有的把“直文”演绎为“直书”。如宋丘岳总结《琴川志》编纂经验曰:“直书所闻以授之,使后之人观之,亦足以感发而兴起矣。”⑤丘岳:宝祐《琴川志叙》,至正《重修琴川志》卷首《旧序》。元戴良亦有类似表述。他总结《重修琴川志》编纂经验曰:“直书所闻以授之,使后之人观之亦足以感发而兴起矣。”⑥戴良:《重修琴川志叙》,至正《重修琴川志》卷首。有的把“直文”演绎为“直笔”。如元杨敬德曰:“必传信而后可据,若掩前人之直笔,而妄以己意损贯其间,将何以传信也。”⑦杨敬德:《元统赤城志序》,谢铎编《赤城后集》卷二十九。从现代哲学观点去审视,无论是“实录”说还是“直文、直书、直笔”说,皆片面强调了地情客体在修志中的决定作用,而轻视了编纂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此是不足为训的。其实早在宋元时代,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修志过程并不是全由客体因素决定的。如南宋陈尧道就把修志视为从“胸中志”到“纸上志”的演化过程。他说:“窃惟有纸上志,有胸中志。奇峰峭拔,宜产铺棻,生齿稀而之繁,版赋丰而之缩,纸上志也。用则入徂徕圣德之颂,不用则入文德党籍之碑。仕则致身鼎鼐而一亩不增,不仕则高卧林泉而累召不就,胸中志也。”⑧陈尧道:《仙溪志序》,宝祐《仙溪志》卷首。这里所言“胸中志”即属主体因素——编纂主体对地情客体的一种认识。但因彼时有此认识者极少,故就不能成为彼时修志界的一种主流思潮。
(二)以主体说为主流阶段
此阶段涵盖整个明代。与宋元相较,明代修志本质观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即从往昔以客体说为主流变为以主体说为主流。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由于受王阳明心学思想影响。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就是“知行合一”。以“知行合一”观点去审视修志活动,也必然是“知”与“行”相统一过程。二是由于受强大理学思潮的影响。诞生于宋代的程朱理学(又称道学)虽早在元朝后期就已取得学术主潮的地位,但真正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取得一家独尊地位,还是在明代。也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明代学界就很强调理学对修志的指导作用。如舒芬曰:“作志者,非有见于道而备作史之才,未见志之善也。”⑨舒芬:《顺昌县志序》,正德《顺昌县志》卷首。在明代,许多学者都认为,修志过程就是编纂者表达自己思想的过程。其中典型表述就是“志者”“心之所之”。如徐一鸣曰:“夫志何志也?以志志也。志何以志?君子之志在斯民,欲致其志于民,故志之也,致其志可矣。又何以志?事往则迹湮,势穷则力竭。君子欲致其志于无穷,故志之示久远也。”⑩徐一鸣:《长沙郡志序》,嘉靖《长沙府志》卷首。后汪廷藻还说得更加明确。他说:“夫志也者,志也,识也。志也者,将以明其志也。”⑪汪廷藻:嘉靖《巨野县志序》,道光《巨野县志》卷首《旧志序》。由此可见,在汪氏看来,所谓修志就是其作者“明其志”的过程。彼时曾汝檀、刘廷元、郝綗诸人还有更为精辟见解。曾汝檀认为,修志根本动因就是源于“志者之心”。他说:“志与志通,生于心者也。以识往迹而垂将来,非由心不可也。”“成者之心则志者之心,夫非自外来也。”①曾汝檀:《漳平县志后序》,嘉靖《漳平县志》卷末。刘廷元认为,志有“胸中”志和“简中”志两种。他说:“良于吏者,胸中有全志。夫志何分胸中见上哉?大抵天下事,行之则为实政,置之则为貌言。志不志在力行何如耳。”②刘廷元:万历《南海县志序》,崇祯《南海县志》卷首《旧序》。郝綗还有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修志过程就是表达志书作者和读者思想的过程。他说:“夫志也者,志也。是以作者之志与读者之志精神玄合,相与有成。”③郝綗:《永年县志序》,崇祯《永年县志》卷首。这里所言“读者之志”是指志书作者脑海的潜在读者。刘、郝二说同现代文论相一致,颇具学术见地。在明代,也有一些人在继承传统思想,鼓吹修志必须做到“实录”“直书”“直笔”等。如有人说:“志史类也,藩、省、郡、县类各有之,以记时事。其所贵者,存真焉而已尔。夫真则一方实录,足备采择,以征文献,固信史也。否则浮诞失实,词藻虽工,无所于征,奚以志为。”④贾咏:《临颍县志序》,嘉靖《临颍县志》卷首。但因彼时持此认识者较少,故未能成为彼时修志界的一种主流思潮。
(三)客体说与主体说并行阶段
此时期涵盖整个清代。彼时方志界仍同时流行客体说和主体说,且两者力量相当。持客体说者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对客体论进行深入阐述。例如,顺治《河南通志》卷首《凡例》规定曰:“寇躏多年,屠戮甚惨。凡被难者,尽云忠义可乎?今概从实录,罔有所饰。”后章学诚亦曰:“讥贬原不可为志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直宽隐彰之意,固不可专事浮文,以虚誉为事也。”⑤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章学诚遗书》卷十五《方志略例》二。与此同时,持主体说者也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对主体论进行深入阐述。如李馨说:“谓之志者有二义。志,识也。方识是事而已。分野、形胜欲其悉也,建置、沿革欲其详也,山川、土田欲其核也,人民、户口欲其周也,人心、风俗欲其通也。抑又志者,正其心之所之也。悉形胜则志捍御,详沿革则志张弛,该土田则志垦辟,周户口则志生聚,传人物则志栽培,核赋役则志度支,通风俗则志表正,是故有识记之精而后行心志之正。”⑥李馨:康熙《重修天门县志序》,乾隆《天门县志》卷首原序。李氏此说把修志“二义”统一起来,对后人进一步探究修志本质有启迪意义。嘉庆间,李兆洛亦有类似见解。他阐释修志曰:“夫志者,心之所志也。志民生之休戚也,志天下之命脉也。志前世之盛衰以为法鉴也,志异日之因革以为呼吁也。”⑦李兆洛:《怀远县志序(代康绍镛)》,嘉庆《怀远县志》卷首。其实在晚清学界,就已经萌发主客体相统一的新修志本质观念。如道光间邓存詠说:“盖志者记也,记其事以传之后世也。朱紫阳云‘心之所之谓之志’。是志之纪事,又在人之心知其事而不忘其事,有所法鉴,有所措理也。”⑧邓存詠:《龙安府志序》,道光《龙安府志》卷首。嘉庆间,蒋予藩也说:“夫志何为者也?《说文》曰:志,意也。语曰:志,记也。盖凡言志者,皆精神所流露,事物所见端也。”⑨蒋予藩:嘉庆《营山县志序》,同治《营山县志》卷首原序。由此可见,邓氏、蒋氏皆把修志视为主客体相统一过程。但由于彼时对修志如此认识者不多,故不可能成为彼时修志界的一种主流思潮。
(四)以主客体统一说为主流阶段
此阶段涵盖民国和当代。如果说在清代,主客体相统一的修志本质观念还仅是一种非主流思潮,那么时至民国,在强大西学(含马克思主义)思想潮流影响下,随着修志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主客体相统一的修志本质观念则迅速成为彼时修志界的一种主流思潮。有的认为,所谓修志就是修志者把自己思想演化为书面文字的过程。如有人说:“尝闻志之所至,金石为开,盖志者记也,发之心而记之简者也。”⑩薛凤鸣:《献县志序》,民国《献县志》卷首。有的认为,修志就是客观地情再现和主观思想表现相统一的过程。如有人说:“心之所之谓之志。志者,记也。记其不可以或忘也……从前之实际则不能以意为去取,而务求合乎时尚。方志固非史,而有史之具体。在有或忘之,其不几于向壁虚造者。何限《修文县志》。志修文县之事之人,志修文县之已往,而更有冀于将来。一事一人之或虚,其对已往未必皆无所佐证,而于将来之取信,不又似乎渺渺。故《修文县志》之所以志,正亦纂者之为志也。”①《修文县志凡例》,民国《修文县志》卷首。徐步瀛的认识更为精到。他认为修志是一种从客体地情到主体认识,再到客体文本的二重转化过程。他化用古代“胸有成竹”“庖丁解牛”两成语所蕴含的哲理,认为文本之“志”必然是其作者心中之“志”外化的结果。他论文本之“志”与其作者心中之“志”关系曰:“画竹必胸有成竹,解牛必目无全牛,修志必心存壮志,而后竹也、牛也、志也,乃可画之、解之、修之,以奏成功。”②徐步瀛:《华亭县志序》,民国《华亭县志》卷首。徐氏如此阐释修志观念,与现代文章学原理相吻合,很有学术见地。
时至当代,方志学界对于修志本质问题的研究在继续深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杨静琦就说:“地方志编纂工作的主要矛盾是处理好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要想编出一部符合要求的社会主义新方志,还要解决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问题。”③杨静琦:《地方志与哲学(一)》,杨静琦等主编《地方志与现代科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对于修志本质问题,韩章训在《方志编纂学基础基础教程》也曾作这样表述:“方志编纂既不完全是地情客体的再现过程,也不完全是编纂主体的表现过程,而是客体再现与主体表现的相统一过程。”④韩章训:《方志编纂学基础教程》,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二、修志笔法演变
这里所谓“笔法”不是指修志行文中的那些具体方法(如多说并存、详略互见等),而是指修志行文的基本笔法。修志行文笔法是回答志书“怎么修”的问题。修志本质观念同修志笔法关系十分密切。前者是后者的思想根源,后者是前者衍生物。或者说修志本质观念总是指导或制约着修志者对修志笔法的选择或创造。纵观修志笔法演变历程,可归纳为如下四阶段:
(一)以述而不作说为主流阶段
此阶段涵盖东晋至宋元。先秦孔子总结自己作《春秋》经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⑤孔子:《论语·述而》。后东晋常璩率先把孔子“述而不作”说移用到修志领域,并主张修志必须以“述而不作”为基本笔法。他说:“善志者述而不作,序事者实而不华。”⑥常璩:《华阳国志》之《序志》《后贤志》小序。时至唐代,有的学者则祖述常璩“述而不作”说。如许嵩总结自己编纂《建康实录》经验曰:“嵩述而不作,窃思好古今,质正传,旁采遗文。”⑦许嵩:《建康实录序》,《建康实录》卷首。有的则把“述而不作”演绎为“直文”。如徐坚在《初学记》卷二十一中说:“方志直文。”有的则把“述而不作”演绎为“直书”。李冲昭总结《南岳小录》编纂经验曰:“历代得道飞升之流、灵异之端,撮而直书,总成一卷,目为《南岳小录》。”⑧李冲昭:《南岳小录序》,《南岳小录》卷首。时至宋元,学界多把“述而不作”奉为修志的一项基本信条。如南宋褚中认为,修志同作史一样,必须奉行“述而不作”笔法。他说:“圣人之于史,亦惟述而不作,况邑志乎?”⑨褚中:《琴川志叙》,《重修琴川志》卷首《旧序》。元杨敬德认为,修志当以“直笔”为基本笔法。他说:修志“必传信而后可据,若掩前人之直笔,而妄以己意损贯其间,将何以传信也。”⑩杨敬德:元统《赤城志序》,谢铎编《赤城后集》卷29。无论是徐坚“直文”说、李冲昭“直书”说,还是杨敬德“直笔”说,都是对常璩“述而不作”说的延伸和发展。以今天科学观点去审视,尽管在东晋至宋元诸代修志界,普遍以述而不作为修志基本笔法,但这样做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以述作并重说为主流阶段
此阶段涵盖整个明代。从现存历史文献看,明代最早要求修志要用述而有作笔法的,并不是个别学者的意见,而是朝廷颁布的修志文件——永乐十六年颁降《纂修志书凡例》规定:“叙前代至今习俗异同。形势,论其山川雄险,如诸葛亮论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之类。”这里所用“叙”、“论”意近“述”、“作”。这实际上就是允许修志使用述而有作或述作结合的笔法。自此之后,许多学者都纷纷表明自己对修志笔法问题的看法。有的从“志者,心之所之”这种修志本质观念出发,认为修志行文必须酌加论断。如嘉靖《开州志》卷首《志例》曰:在修志中“每事或立论以断,广视听也”。嘉靖《徽郡志》卷首《志例》亦曰:“揭书事下间有肤见论断,尚俟后之君子正焉。”有的甚至还认为,在修志行文中“间附己说”是不可或缺的。如崇祯《潞城县志》卷首《志例》曰:“志之所载择其切要者,间附己说,不过镜前塗,规后效耳,故不敢缄默云。”黄佐还明确把修志笔法概括为“有作有述”。他总结自己编纂《广州府志》经验曰:“余辑郡志有作有述,作之目十有八,述之目十有七。”①黄佐:嘉靖《广州府志序》,《道光广东通志》卷191《艺文略》三。且从《广州府志》“作之目十有八,述之目十有七”看,还可推断黄氏在编修此志时,不仅采用了“有作有述”笔法,而且还是“作”“述”并重。其实在明代,也有人主张修志要采用述而不作笔法。如范镐称《宁国县志》行文基本笔法曰:“文匪敷藻,思非涌泉,述而不作,汇以成编。”②范镐:《叙宁国县志》,嘉靖《宁国县志》卷首。但因彼时持此主张者较少,故不能成彼时修志界的一种主流思潮。
(三)述而不作与述而有作说并行阶段
此阶段涵盖整个清代。清代既是客体说修志本质观念和主体说修志本质观念并行时期,也是述而不作笔法与述而有作笔法并行时期。彼时主张“述而不作”者有一批人。如乾隆《泾县志》作者述该志人物门行文笔法曰:“人物一门历史有专传、附传者,即据史文录入。无则采《一统志》、《江南通志》、旧府旧县志名人记载。近时则据采访册,以明述而不作之意。”③乾隆《泾县志凡例》,嘉庆《泾县志》卷首。蒋士铨甚至把修志使用“直笔”视为修者良好职业道德的集中体现。他说:“凡昭隐发潜,彰善瘅恶,务使笔削可质鬼神,论断无惭衾影。闻人之过固不能无疑,闻人之善亦难为遽信。是望和衷协一,持大体而不阿,守无欺而自谦。侃然以风化纲常为念,防微杜渐,成始要终,庶公心若石,直笔如山。”④蒋士铨:《南昌志局约言(代)》,蒋士铨著《忠雅堂文集》卷十二。彼时主张“述而有作”者也有一批人。同治《仁化县志》作者认为,修志行文当酌加议论。他们说:“作志者不无议论。修志者亦不无所见。有所见而为之论,正非徒费笔墨也,故则论悉为备载,新添者用案字以别之。”⑤《仁化县志凡例》,同治《仁化县志》卷首。有的认为,修志行文酌加议论是明辨是非的需要。如乾隆《绍兴府志》作者曰:“孔子云:述而不作。传云:言有物。又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旧志随事约举,殊难征信。偶引书名,株连割截,起讫茫然。寻其原本,往往缪戾。兹征引书册,悉取原文。至于互有异同,各形依据,然后附加案语,非取骋辩好奇。”⑥《绍兴府志略例》,乾隆《绍兴府志》卷首。彼时章学诚对于修志笔法问题的看法是动摇不定的。他先说:“讥贬原不可为志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直宽隐彰之意,固不可专事浮文,以虚誉为事也。”⑦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章学诚遗书》卷十五《方志略例》二。这里所言“据事直书”同“述而不作”是同义的。他后又说:“明祖纂修《元史》,谕宋濂等据事直书,勿加论赞,虽寓谨严之意,亦非公是之道。仆则以为,是非褒贬第欲其平,论赞不妨附入”。⑧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章学诚遗书》卷十五《方志略例》二。章氏所言“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直宽隐彰之意”与“是非褒贬第欲其平,论赞不妨附入”显然是互相抵牾的。
(四)以述而有作说为主流阶段
此阶段涵盖民国和当代。时至民国,在强大西学(含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国人修志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述而有作”说则迅速成为修志界的一种学术主潮。如《青县志》作者述该志行文笔法曰:“旧日方志大多重记述寡论断。前志之弊正复坐此焉。兹志一矫旧习,以夹叙夹议法行之。篇有篇之管见,目有目之微辞,务使易板以活化为灵。”①《青县志凡例》,民国《青县志》卷首。彼时寿鹏飞对修志笔法问题的论述最有见地。他总结修志历史经验,认为修志行文当采用述而有作或述议结合笔法。他说:“志者,史也。史以明治乱兴衰之故,志以补郡国利病之书。故于纪载正确之余,宜参以指陈得失之论。盲左腐迁均有此例,而《资治通鉴》一书每附以臣光曰云云,所谓别嫌疑,明是非,可以载道者此也。惟此乃不负作史修志之本旨,若仅案而不断,何以敷陈要义乎?”②寿鹏飞:民国《易县志稿·叙例》,1937年成稿,1990年学苑出版社影印版。寿氏这段话表明两个观点。一是认为志书欲“别嫌疑,明是非”和“敷陈要义”,必须采用述议结合之法。二是认为志文所用议论不是凭空而生,而是在“纪载正确之余”,再“参以指陈得失之论”。寿氏此说颇具学术见地,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始,就有许多人对修志使用“述而不作”笔法产生质疑,并主张对“述而不作”做变通理解。如有人说:“今天修新志,虽也讲‘述而不作’,但并非毫无观点、毫无立场地排比、堆砌史料,而是根据马列主义观点,有目的地选择史料予以记载。虽不直接阐明观点,但要将观点、立场和历史经验通过记述,通过选用的史实正确地予以反映。”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述而不作”条,黄山书社1986年版。显而易见,如此变通理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述而不作”笔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要求突破“述而不作”的呼声更加高涨。如有学者曰:“‘述而不作’至少有‘是非不明’、‘因果不彰’、‘规律不见’、‘真假难辨’等四大弊病。”“胡乔木同志早就指出,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要有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三新’的要求,首先在于要有新观点。如何表现新观点,首先要破除‘述而不作’的老框框,而赋予‘述而有作’的新方法。”④王建成:《“述而不作”析》,《中国地方志》1991年第3期。那么对于“述而有作”究竟该如何理解呢?有的学者说得对:地方志当以“述”为主,也不应排斥“作”。详而言之,一是“作”于修正传统的错误观点。二是“作”于揭示地情和人情的基本特点。三是“作”于志书的总体设计。四是“作”于志书的篇章设计,注意志书规范化的同时,突出自己地方的特点也是一种“作”。五是“作”于志书篇、章前的无题小序。⑤详见魏桥:《续志三思》,《内蒙古地方志》2005年第4期。当历史进入21世纪后,修志使用“述而有作”笔法已经成为广大修志同仁的基本共识。有的学者曾把“述而不作”和“述而有作”中的“作”理解为“论”。如有一学者说:“新编地方志书是否可以有点论,还是‘述而不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是主张新方志可以有画龙点睛式的评论乃至简短的评论,而不主张在方志的记述中发表长篇大论。因为长篇大论有乖志体,而简短的议论是符合志体的。”⑥饶展雄:《关于方志的“述与论”》,饶展雄著《史志文稿》,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此说有偏颇之嫌。因就现代汉语而言,“作”与“论”是两个不同概念,“论”仅是“作”一种,把“作”等同于“论”就是把整体等同于局部。换个角度也可这样说,“述而有论”是作史笔法。倘若修志可用“述而有论”笔法,那么修志与作史就没有区别了。
众所周知,修志本质观念和笔法问题都是方志编纂学中根本问题。修志本质观念问题是方志编纂基础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修志笔法问题是方志编纂法中的核心问题。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出版了不少名为‘方志编纂学’的专著,但其中多数专著皆未给‘方志编纂’这一基本概念做界定,这样该专著就自然缺乏所应有的理论支点。”⑦韩章训:《论方志学转型升级》,《浙江方志》2018年第6期。再说已有的那些方志编纂学专著,对于修志笔法问题的论述也多不甚理想。多数方志编纂学专著是避而不言,少数方志编纂学专著是言而不详或尽弹“秉笔直书”“述而不作”等老调。这些既是已有方志编纂理论存有粗疏之弊的具体表现,也是今后优化方志编纂学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