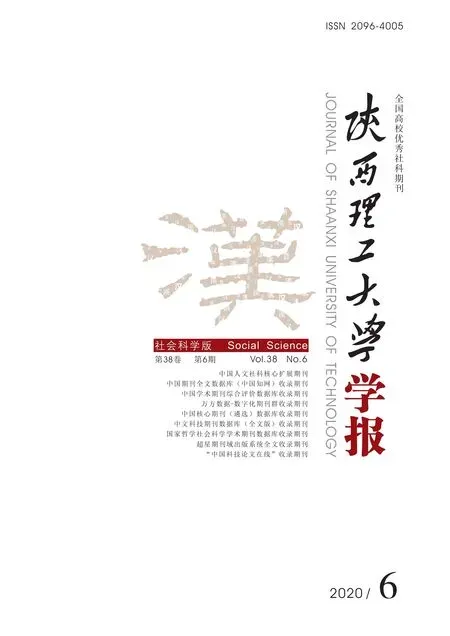基本功、教学与科研
霍松林
高等师范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过硬的基本功。以我个人为例,我自1957年后即受批判,“文革”前夕受批判,1966年第5期《红旗》杂志就点了我的名[1]。1978年我还不能开会、发文章,1979年开始勉强开会写文章,到1980年才完全自由了。所以,几十年间治学的时间是很有限的。那么,怎么出了些书呢?这得归之于我原来的基本功。
我出生于天水县一个偏僻农村,父亲在科举时代是秀才,废科举之后在家教书、行医。我家附近有一所小学,教师都是父亲的学生,所以,他不叫我上那所小学。大了一点,从学校外走过,听那些学生们念书:“人,一人唱,二人听。”“狗,大狗叫,小狗跳。”我父亲听见后认为此不足为训[2]。我从三四岁起就在家读《诗经》《论语》《孟子》《史记》《左传》等,到读《左传》时,就念高小。念的办法是背,父亲检查,虽然是背,死记硬背,但也有收获。有一次,我在家给母亲、姐姐讲书,父亲从外行医回来听见,说是还讲得可以,只是开讲得迟了。这时入学念四年级,先补齐算术,我学习起来是很轻松的。只要有了背的基本功,那么学新的东西是很容易的。
念高中,是抗日战争时期。上大学一年级时,朱东润先生看了我写的诗、文后说,你可以少上课。对罗根泽先生的文学批评课,也只听了一部分。在中央大学时,有很多名士,如汪辟疆先生,他是徐州人,土音很重,上课老骂人,但他骂人时,也是有水平的。上大学时,还学了点英语,勉强可以读懂原著。1951年3月到西北师院(现师大前身)教书,当时只开历代散文和文论,有两位老先生教,轮不到我,学校叫我教《文艺学》,我说没学过,他们说可以学。当时规定每个教师要教三门课,当时没有教材,我找了本巴人的《文学初步》,就把课教下来了。这说明有了基本功,学一门新的东西还是容易的。后来,我终于编起了讲义,1954年教育部将其铅印,后又出版[3],到1956年后又讲起了元明清文学,以后又改教其他好多课程。这些都说明不管干什么基本功要过硬。
一、什么是基本功
我理解搞古代文学的,所谓基本功指三点:第一,要有相当不错的阅读能力,即拿起先秦古籍,借助前人(汉人)的注释能读懂,不是看现注,不然会处处遇到障碍困难;第二,要有相当不错的写作能力,能写出精炼甚至有文采的文章来。搞古代文学的,能够写古文,作传统的诗、词、曲,符合格律要求。因为古人写文章用古汉语思维,如果懂得古人怎样写文章,那么自己也就会写了。一个有几十年创作甘苦的人,其体会与别人不同,还包括用古汉语写各体文。思维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无思路不清之弊。教学就能训练思维能力,读文艺作品,加上社会实践,还能培养形象思维、想象力。现在大学的课程太单一。解放前一个大学起码包括三个学院,那么学生除了必修课,可以有选修课;第三,要有专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学古代的社会史、思想史、艺术史,要有生活阅历,不然对古代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感情就不易理解[4]。
这些能力怎样培养呢?
阅读能力,不只是听语法、语音、文字,以前我就讲过学生听课太多,老师讲的太多。教师要少讲,学生要多读。阅读能力是在阅读实践中培养的,这是必由之路。我在小学的国语老师不错,重视作文,收后即批、发、评。那时就培养了我的写作、文学兴趣。我在初中时有一个老师,他教书是念一遍,说“好”,再念一遍,说“好,好得说不出,你们念去吧!”到下课时才来,这在当时传为笑柄。但念书却使人受惠无穷,因为听讲后不久就忘了,念熟后可以经久不忘。学生为应付考试,不是背原著,而是背笔记。我是反对背笔记的。名作是非念不可的,背名篇、背名著是一个看似笨拙、实为简捷的道路,花时少,收效大。古人对此有很多名言。如苏轼“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理自知”,董遇的“三余”。董遇是三国时陕西人,治《易》,别人读书有不解处,就去问他意思,他不回答,说:“你再读。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俗语有言“读书全凭苦用功,老师不过引路人。”教育学也认为,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上学时,老师讲的这些不够用,自己读了好多。读得多了,专业知识面就宽了。荀子曰:“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学问要渊博,而这主要靠自己读。没有开的课程,自己也可以学。请教老师之后自己可以阅读学习。
具备了基本功,可以进入任何新的学术领域,然后再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搞好教学,搞好研究。多读之后,再多写就能提高水平。
二、如何搞科研、学术研究
研究是什么?要研究什么?先要调查一下研究对象的情况,如,是什么书,有什么研究的书,有几种版本,后人研究的有什么文章,到现在共有多少文章?涉及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哪些个领域?把对象的所有资料收集起来,还有国外的研究资料,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情况,综合一下,看已提出多少问题,已解决多少,有什么问题你不同意,不轻易提出自己的创见。不然,有时提出了别人早已提出的问题,就会被动,这是占有材料的过程。如有学者研究《三国演义》上的曹操和历史上的曹操是否一致,研究以后认为基本是一致的,这就有了新意。研究前人没有解决或没有全部解决、或解决错了的问题,你能解决,这就有了新意,这就是研究。这是实事求是的,从详细占有材料、分析综合得到结论的过程,这个结论就是经得起敲打的。
1957年陈伯达提出“以论带史”,即以马列主义理论带动历史研究。到“文革”中,成为“以论代史”,变带动为代替。先确定结论,再搜罗事实,甚至不惜伪造。
1958年“文革”时,批判我的《文艺学概论》,罪名是“人性论”,其中有好些批判文章脱离我的原文,甄别时演《三岔口》。“文革”中郑季翘写文章点名批我说的“形象思维”[5]。
搞教学的人要搞科研,每讲一个东西,先要研究一通,把前人有关文章全部读一下。这一下讲出来的效果是不同的,如《离骚》。水平是可以提高的,就是以研究促进教学,然后以教学检验研究。有这样几个反复,表达自己见解的论述就出来了。我的《文艺学概论》《西厢记简说》等都是讲课的讲稿。前人也是这样。我的老师,把一门课讲过两三遍后,书就出来了。然后再另教一门课,再另出成果。教学对研究,有检验、提高的作用。有时讲课兴会淋漓时,会出现“灵感”,讲出备课时未准备的东西。
三、关于研究和教学的关系
有了基本功,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学问,如走路时,睡不着时,睡醒后。有人出了“牛棚”,成果也出来了,那是因为他记得很多。
汪辟疆笑话一位兼课的教师把书包掉在电车上而只好不上课。所以,上课时可以不带书和讲稿,那就得多积累。
现在有些人业务上不去,他也教一点书,散布教学和科研的矛盾很尖锐,忙于教学,没有时间搞科研。我就问他不搞科研,怎样搞教学?我说:教学是科研指导的教学,教学完了,成果也就出来了。几个学者在一起聊一会天,晚上加个班,第二天文章就出来了。说没时间搞科研,是水平低的托辞。上海华东师大五十岁左右的教师非常刻苦,怕接不上老一辈的班,教学可以督促科研。
教学的问题,高等学校的课程,老师应该少讲一些,具体如文学史和作品,哪个重要?作品重要,因为不熟悉作品,文学史是架空的。如对一个时期的作品读得多,自己可以写文学史,读别人的文学史也容易。要读原著,读名著。教院本科班,对名著的选读,要读旧注,有些旧注是很有名的。如《昭明文选》的六臣注,杜诗的钱谦益注、仇兆鳌注、杨伦《镜铨》、浦起龙《心解》等。注解要相当熟,特别是经典性的注解,这比鸡零狗碎地读、听,要实用得多。读完后要写读书报告,分段写。读《诗经》,可用《十三经注疏》本。在指导学生阅读过程中,老师也可学习,两年内精读了几部名著,基本功也就打得差不多了。基本功过硬了,那不管研究什么都会有成果。
我上大学时的文字学是张世禄老师上的,他当时讲的,我现在记不得多少了,汪先生曾说:“张世禄,连《说文》都没念会,会讲什么?你不要去听他的课,自己去读,写《说文》,写上七八遍,再看一些其他书,就行了。”我后来未坚持写完。如果写完,文字学的功底是会过硬的。所以,我的小学的基本功差,《说文》《广韵》《尔雅》都不熟。语言学上的章太炎、黄季刚,黄先生真正得力的是几部书,当然,他涉猎也广泛些。做学问在关键时起作用的只有几部书,与遇难时可救自己者相同。黄精通的有《说文》《广韵》《尔雅》《礼记》《文心雕龙》《左传》等不足十部书。仇兆鳌注我读得熟,因而也大大提高了阅读能力[6]。知识面开阔了,用力少,收效大。听的课,过后都不记得了,而读的书却经久不忘。要解决精和博的关系。博读的书要和精读的书联系起来。精读一部,就可以做研究了。
特别强调名著的通读。不然培养不出古典文学研究上很扎实的人才。我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但有一个特点,就是前边的影响后边的,特别是先秦两汉,对后代的影响尤大。如不熟悉先秦两汉,那读以后的东西就会步步是困难。因为后代的许多东西都是先秦诸子思想哺育起来的。从源到流,要了解清楚。
有些学生读不懂古文,怨古汉语老师没讲好。其实,讲古汉语的老师,不见得也能讲得清楚。光靠语法套是不行的,根本的是反复、扎实地读原著,记、背得多了,就可以活起来,其他都是辅助手段。读得多了,记忆力也就培养出来了。花时少、收效大的是通读原著,通读前人做的注解。
注:本文是霍松林先生1984年9月27日在全国教育学院系统《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研究会上的专题发言,由咸阳师范学院南生桥副教授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