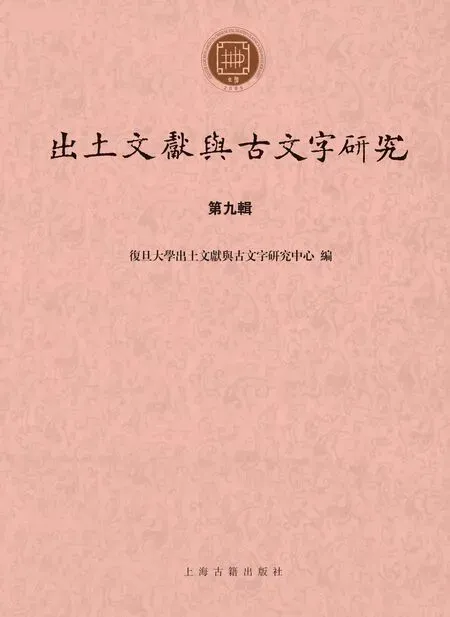從甲骨文的“矚”“燭”説到古代“燭”的得名原因及其源流*
郭理遠
一




但是,“蔣文”根據同作覆手於杖之形的“老”“考”“長”等字,推測A字所象也應是年老之人,結合其上文對“”的讀音的論證,認爲A字是“古書中訓爲‘老而無子’的‘獨’字的初文(引者按:似以稱‘本字’爲較妥)……是取年老孤獨之人的形象”(第71頁)。這一結論似可商榷。

在第20届古文字年會會前一日,陳劍和郭永秉兩位先生都曾向蔣玉斌先生提出A字當釋爲“矚”字初文的意見,並認爲其字形中除去目形外的部分如果獨立出來,可看作拄杖之“拄”的初文,“矚”“拄”聲韻皆近,這一部分可以視爲兼有表音的作用。(6)據郭永秉先生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古文字學”課上所講(2014年10月16日)以及蔣玉斌先生給我的電子郵件(2018年9月12日)。另外,網友“薛後生”先生也懷疑此字可與“矚”字聯繫,不過他認爲其字既表示“獨”,也表示“矚”(薛後生:《簡説甲骨文中的“燭”》,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論壇,網址: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219,2015年1月2日,下引該文相關討論皆見此帖,不再一一注明)。我們認爲這一説法更爲合理,兹補論如下。

有學者認爲“矚”字未見於先秦文獻,似較爲晚出,而對釋甲骨文A字爲“矚”表示懷疑。(10)見“薛後生”《簡説甲骨文中的“燭”》帖子下“武汶”先生的評論。這個問題需要加以解釋。
“矚”字在漢以前的文獻中僅見於《淮南子·道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不過“視焉無矚”句《道藏》本作“視焉無眴”,王念孫根據其他古書中的引文指出此句本來當作“視焉則眴”,“則”涉上誤作“無”,後人又改“眴”爲“矚”。(11)王念孫著,徐煒君、樊波成、虞思徵校點:《讀書雜志》卷十二“無眴”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49—2250頁。除去此例之外,“矚”字始見於漢代之後的文獻,如三國曹植《文帝誄》:“尊肅禮容,矚之若神。”諸葛亮《至祁山南北岈上表》:“矚其丘墟,信爲殷矣。”(《水经·漾水注》引)時代較晚之例甚多,不具引。今傳《説文》各本中無“矚”字,但《慧琳音義》數引《説文》“矚”字之訓,(12)見前引《慧琳音義》卷五十三注《起世因本經》第二卷“觀矚”條,又參徐時儀校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第2042頁。田潜《一切經音義引説文箋》認爲:“是所據古本碻有此字。”(13)田潜:《一切經音義引説文箋》,鼎楚室1924年刻本,卷四第六葉下。此書承李豪先生提示。其説可參。
先秦至漢代文獻中雖未見“矚”字,但有“屬之目”“屬目”的説法,如《左傳·定公十四年》:“師屬之目。”《漢書·蓋寬饒傳》:“坐者皆屬目卑下之。”《禮記·喪大記》“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隠者爲廬”鄭玄注:“不欲人屬目,故廬於東南角。”這些例子中的“屬”即爲“矚”義。一般認爲“屬”的本義是附屬、連屬,而“矚”是注視的意思,即目光較長時間停留在所看的對象上,二者詞義關係密切,學者多認爲“矚”是“屬”的引申義。(14)如胡吉宣《玉篇校釋》即結合“囑”字説:“‘矚’與‘囑’古止讀爲‘屬’,屬付委託即由連續義引申,接於目爲矚,口叮嚀爲囑,並後起分别文。”(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三册2218頁)“屬”“矚”二詞出現應該很早,甲骨文中未見“屬”字,可能由於“屬”的意思不好表示,就以字形表示“目光之屬”的A字來表示“屬”這個詞,這跟以字形表示犬之臭(嗅)的“臭”來表示“臭(嗅)”這個詞是同樣的情況,都屬於“形局義通”的例子。(15)參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44—145頁。A字的字形可以清楚地表示矚目的意思,以之表“矚”很直接,没有必要再另外造字。从尾、蜀聲的“屬”字出現之後,A字即遭廢棄,就用“屬”字兼表“屬”“矚”。隨着“屬”字字義、用法的增多,爲了明確“矚”義,就爲“屬”字加了目旁,産生了形聲字“矚”。不過目前似無法排除在語言裏先有“矚”,然後再引申出“屬”的可能,但即便如此的話,A字、“屬”字、“矚”字所表詞義的情況大致仍如上文所推測。
綜上所述,陳、郭兩位先生釋甲骨文A字爲“矚”字初文的意見是可以信從的。
二
“蔣文”還提到了甲骨文中如下之字(下文簡稱“B”):





1934年,在安陽侯家莊西北崗進行的殷墟第十次發掘中,一座編號爲1005、葬有六人的墓裏出土了一批保存較爲完好的器物,其中有形制特殊的兩件旋龍銅盂和一件中柱陶盂(見表一3—4)。(27)石璋如:《侯家莊(第十本)·小墓分述之一》,中研院史語所,2001年,第21、47頁。徐中舒《關於銅器之藝術》認爲旋龍盂是燈具,“四龍形相連旋轉之物,當即燃火之鐙心處”。(28)徐中舒:《關於銅器之藝術》,滕固編:《中國藝術論叢》,商務印書館,1938年,第127頁。此文原刊於1937年“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展覽期間的專刊中,負責這次展覽的梁思永先生此前當已知道此説,他在這次展覽會目録中殷墟發掘出土品的説明部分認爲同墓所出器物“以盂3(引者按:包括兩件旋龍盂和一件普通銅盂)、壺3、鏟3、箸3之雙配合觀之,似爲3組頗複雜之食具”,(29)梁思永:《殷墟發掘展覽目録》,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梁思永考古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156頁。並説“學者有認此器(引者按:指旋龍盂)爲殷人所用之燈者,但此説只着限於一器,而對於同組之其他器具,如鏟箸等,未加以適當之解釋”,(30)同上注。這應該是針對上引徐説的。小屯YH083窖穴出土的一件中柱盂,與侯家莊1005號墓出土的陶盂類似,李濟先生將其歸爲陶器蓋。(31)李濟:《小屯(第三本)·殷墟器物甲編·陶器上輯》,中研院史語所,1956年,第76頁。又《李濟文集·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3頁。上世紀50年代以來,二里崗時期至戰國時期的窖穴或墓葬中也出土了一些帶有空心或實心菌狀柱的盂形器(參看下表),考古學者對這些器物的稱呼有“陶器蓋”“中柱盂”“中柱盤”“中柱盆”“空柱盤”等多種,對其功用目前尚無一致意見。(32)各家説法可參看李麗娜:《試析中國古代中柱盂形器》,《中原文物》2015年第1期。此文贊同防蟲用器説,認爲盂中之柱用於承托裝有食物的盛器,在盂中盛滿水之後,可以防止爬蟲侵蝕食物。今按,器之中柱若用於承置其他器物,其柱頂應該較爲平整,但“中柱盂”的柱頂均向上微鼓凸起,顯然不適合承托其他器物。此説不可信。

表1

梁思永先生注重同墓共出器物的做法頗爲可取,但他提出的“食具説”並不可信。石璋如先生根據“各器相互”的原則把侯家莊1005號墓所出器物分爲兩組,認爲中柱盂與一件陶盆、三雙銅箸、三隻銅鏟、一隻銅鋤等爲一組。所謂銅箸其主體有四棱且一端有銎需裝圓柄使用,石先生指出當非食具,並對其功用提出過如下推測:“圓柄便於手執,或爲避免銅質發高熱而燙手所設。果然如此,則銅箸或與火有關。或從火中取物,或翻動正在燃燒的木材以調劑火勢”,(36)同上注,第30頁。這是很有道理的。但他後又假設了多種銅箸裝柄的方法,最終認爲此物應該是插蠟燭的“燭本”,銎中所插蘆葦桿是“燭心”,在此基礎上認爲銅鏟用來采伐、修剪蘆葦,銅鋤、中柱盂、陶盆則與采蜜、製蠟有關。(37)石璋如:《侯家莊(第十本)·小墓分述之一》,中研院史語所,2001年,第30—47頁。今按,石先生認爲這些器物與蠟燭有關,引用了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中“古大燭以葦製”的内容,但是此處的“大燭”並非蠟燭,並且他似乎回避了尚文“漢時中國尚無蠟燭”“晋初有蠟燭”等内容(38)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中國書店,2001年,第168頁。(我們認爲東漢時蠟燭當已出現,詳下文),他的説法顯然不可信。他把墓中器物分爲火器、水器兩組,分别爲墓中六人掌管,實際上是爲了與《周禮·秋官·司烜氏》“下士六人”“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牽合,(39)石璋如:《侯家莊(第十本)·小墓分述之一》,第5—6、55—56、85—86頁。也是不可取的。
綜上所述,我們認爲甲骨文“燭”字象突出目形之人手持工具矚視、照管火種,使其保持不滅。“燭”字字形中包含“矚”形,“燭”“矚”“屬”古音聲韻皆同,“燭”這個詞當與“矚”“屬”密切相關。從“矚”的意思考慮,“燭”應該就是指需要矚視、照看的火;從“屬”的意思考慮,則是指前後相屬、不斷增續的火。也可能“燭”是兼取這兩種意思的。這應該是我們現在能追溯的最早的“燭”字。(45)王獻唐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撰有一篇長文《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王獻唐:《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齊魯書社,1979年),集中考釋了甲骨文中的“燭”字以及與“燭”有關的字,以現在甲骨文考釋的成果來看,其所釋的“燭”字基本上都是有問題的。陳劍先生最近根據戰國文字中“蠲”字从“蜀”、从“皿”,指出“蠲”形中“水”旁爲後加,舊將其字分析爲从“益”聲不可信,並疑B字是“蠲”之初文,字形表示人持工具拨火使之明亮(“古文字形體源流”課,2019年6月20日)。今按:陳先生否定“蠲”字从“益”聲是有道理的,但釋B爲“蠲”之初文之説,尚待進一步研究,今姑仍從釋“燭”之説。此字在甲骨文中用爲地名,郭沫若先生僅籠統説是殷邑,陳漢平先生認爲春秋時人燭之武以此地爲氏,但未明確何地。(46)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617頁。今按,周初所伐之殷地有名“蜀”者,見《逸周書·世俘》:“新荒命伐蜀。”疑甲骨文之“燭”即此“蜀”。(47)《世俘》中“蜀”之具體地望迄無定論,或以爲是《春秋》所載魯地,或以爲其地在中原,參看周書燦:《〈逸周書·世俘〉所見周初方國地理考》,《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第54頁。前引周原甲骨文H11:68、H11:97的“蜀”字(辭例分别爲“伐蜀”“克蜀”),可能即《世俘》之“蜀”,參看李學勤:《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文物》1981年第9期,第11頁;龐懷靖:《周原甲骨文》,《文博》1993年第6期,第12頁。
三
下面討論先秦典籍中“燭”的含義。
《説文·火部》:“燭,庭燎,火燭也。从火、蜀聲。”《藝文類聚》所引《説文》“火”字作“大”,《詩·小雅·庭燎》“庭燎之光”句毛傳云:“庭燎,大燭。”前人多據以指出《説文》“火”字爲“大”字之誤。(48)丁福保編纂:《説文解字詁林》,中華書局,1988年,第9940—9941頁。
庭燎是設於庭中之燎,《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諸侯賓至,甸設庭燎”杜預注:“庭燎,設火於庭。”又稱“大燋”,如《儀禮·士喪禮》“宵,爲燎于中庭”鄭玄注:“燎,大燋。”賈公彦疏:“《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注云:‘未爇曰燋。’古者以荆燋爲燭,故云‘燎,大燋’也。”(49)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儀禮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805頁(“荆”字原誤作“剕”)。鄭注以及賈疏中“大燋”之“大”有版本訛作“火”(但疏文中“大燭”之“大”不誤。參看同頁注2、注3所引阮元校勘記),與上文説的今本《説文》的訛字同。“大燋”與“大燭”同義,賈疏下文即徑稱“大燭”。古書中又有“門燎”,《周禮·天官·閽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閽人“設門燎”,與下文所引《儀禮·燕禮》“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句正相對應,可見門燎也可稱“大燭”。《儀禮·燕禮》“甸人執(引者按:‘執’字疑有誤,詳下文)大燭於庭”句鄭注:“庭大燭,爲位廣也。”指出庭中設大燭是因爲其地廣闊。門外亦爲廣闊之地,同樣也需設大燭照明。(50)清儒馬瑞辰根據《燕禮》“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句唐石經本無“大”字,認爲“庭位廣,故特用大燭,足見其餘皆不用大燭”(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中華書局,1989年,第568頁)。今按:除唐石經本外,武威簡本《儀禮·燕禮》《詩·小雅·湛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句正義引《燕禮》文以及《儀禮·大射》與此相應的文句均無“大”字。從版本上來看,此句似當以“閽人爲燭於門外”似較優。但是,既有“門燎”之稱,則門外所設似亦當爲大燭,且“燭”前用“爲”此爲僅見,對比“爲燎”來看(燎即大燭),此處似仍當以“大燭”爲是。武威簡本等可能脱漏“大”字,也可能“爲燭”即指“爲大燭”而言。由此可知,用來照明的燎就是大燭,庭燎、門燎是設立在不同位置的大燭。
燎又稱“地燭”,《周禮·天官·閽人》“設門燎”鄭玄注:“燎,地燭也。”《儀禮·士喪禮》“燭俟于饌東”鄭玄注:“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説明燎是樹立在地上的大燭。
《國語·周語中》:“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又《晋語八》:“楚爲荆蠻……與鮮卑守燎。”可知燎是需要專人“監”“守”的。上文説過,“燭”的本義是需要矚視照管的、連續燃燒的火,燎的“監”“守”表明其也有這樣的特點,燎樹於地上、且較一般之燭爲大,故有“地燭”“大燭”之稱。《説文》是以“庭燎”這種設立在庭中的“大燭”來解釋“燭”的。
“燎/大燭”前的動詞多用“設”“爲”等。“設”是樹、立之義,《周禮·秋官·司烜氏》鄭玄注“樹於門外曰大燭”即用“樹”字。“爲”有製、作之義,《儀禮·燕禮》“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句鄭注:“爲,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先秦典籍中不加修飾、限定的“燭”指手執的火炬,《禮記·曲禮上》“燭不見跋”孔穎達疏:“古者未有燭,唯呼火炬爲燭也。”並常見“執燭”之語。前引《士喪禮》鄭玄注“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已經説明了燎與燭的區别,燎這種設立在地上的大燭是不能“執”的。但是《儀禮·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宫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中甸人句“大燭”前用“執”,(51)《儀禮·大射》也有相同的内容,但彼處“閽人”句内無“大”字。不合於常例。《周禮·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句賈公彦疏説:“《燕禮》云‘甸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彼諸侯燕禮,不樹於地,使人執。”以禮制不同來解釋,恐不確。我們懷疑這個“執”字是讀爲“設”的“埶”字之訛。先秦秦漢文獻中讀爲“設”的“埶”字在流傳過程中很容易訛爲形近的“執”,裘錫圭、郭永秉等先生曾舉出不少例子,(52)裘錫圭:《古文獻中讀爲“設”的“埶”及其與“執”互訛之例》,《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第451—460頁。裘錫圭:《再談古文獻以“埶”表“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論集》,中西書局,2018年,第185—198頁。郭永秉:《以簡帛古籍用字方法校讀古書札記》,《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論集》,第260—268頁。郭永秉先生文後“作者按”還補充了其他學者找到的這方面的例子,請讀者參看。已爲大家所熟知。“甸人執大燭於庭”句見於武威漢簡本《燕禮》《泰射》,《燕禮》簡45與今本對應的“甸人執”數字殘泐不可辨,《泰射》簡113的文字則與今本同。(53)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武威漢簡》,中華書局,2005年,圖版拾叁、拾柒。《燕禮》《大射》此句原應作“甸人埶大燭於庭”,現存版本中“大燭”前的“執”字皆涉上“執燭”之語而訛。
照明所用之燎的形制典籍未載,《禮記·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注:“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詩《庭燎》正義引此文之後説:“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周禮·秋官·司烜氏》賈疏:“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百者,或以百般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推測庭燎是用數十甚至上百支竹木等纏束而成似有道理,但古時是否灌之以脂膏、飴蜜則難以確知。
古書所載手執之燭多以麻蒸製成,故又有“麻燭”之稱,或逕稱“麻蒸”。“蒸”據《説文》本指去皮後之麻桿,其他材質之薪亦用此稱,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云:“蒸,一名菆,今俗謂之麻骨棓。古燭用之,故凡用麻幹、葭葦、竹木爲燭皆曰蒸。”
古書中又有“墳燭”之稱。《周禮·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鄭玄注:“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内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周禮》古本“墳燭”作“蕡燭”(詩《庭燎》正義所引與古本同),鄭司農將“蕡燭”解釋爲“麻燭”。鄭玄把“墳燭”解釋爲“大燭”,認爲“大燭”和“庭燎”的區别在於設立位置的不同。今按:上文已經舉出不少燎即大燭以及門燎、庭燎都可以稱爲大燭的例子,此處“墳燭”“庭燎”並舉,可知二者有别,鄭注的解釋顯然是有問題的,鄭司農之説可從。(54)參看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第568頁。《淮南子·説林》“黂燭觕,膏燭澤”中的“黂燭”,《易林·蠱》之《蹇》“執蕡炤犧,爲風所吹”中所執之“蕡”,均即蕡燭(麻燭)。(55)參看孫詒讓著,汪少華整理:《周禮正義》,中華書局,2015年,第9册第3509頁。其引《易林》之句“炤”誤作“然”,關於“墳燭”之義從鄭玄説,不確。
前人説解《説文》“蒸”字時多引用《管子·弟子職》“蒸閒容蒸”、《詩·小雅·巷伯》毛傳“蒸盡,縮屋而繼之”語,(56)參看《説文解字詁林》第1860—1861頁。這兩處内容有助於我們了解古代手執之燭的使用方法和特點。
《弟子職》云:
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横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57)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第3册第1154—1162頁。
其内容主要是講執燭者的職責,可分爲兩部分,“錯總之法”至“然者處下”主要講更續蒸燭之法,“捧椀以爲緒”至末句主要講清除燭燼之法。
《巷伯》毛傳云:
昔者顔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顔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
乾隆己酉年(1789)山東嘉祥縣出土的東漢武氏祠左石室“顔淑握火”畫像石亦有類似内容,其文作:“顔淑獨處,飄風暴雨。婦人乞宿,升堂入户。燃蒸自燭,懼見意疑。未明蒸盡,摍苲續之。”(58)參看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綫裝書局,2008年,第2册第120頁。較好的題銘拓本可參看天津博物館所藏有俞樾題跋的舊拓(王靖憲主編:《中國碑刻全集·戰國秦漢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252頁)。毛傳“縮屋而繼之”畫像石作“摍苲續之”,錢大昕指出其義爲“抽屋笮以當蒸燭”,(59)參看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第123頁。俞樾並指出孔穎達《正義》訓“屋”爲屋草之誤。(60)王靖憲主編:《中國碑刻全集·戰國秦漢卷》,第252頁。亦見俞樾《讀書餘録》(俞樾:《春在堂全書》,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2册第627頁),此處内容較簡,且“屋上簿”(《爾雅》:“屋上薄謂之筄。”郭注:“屋笮。”)誤作“屋下簿”。俞説出處《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第123—124頁誤爲《俞樓雜纂·讀漢碑》。
由以上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手執之燭在使用過程中需要專人照看,執燭者的具體職責是以新燭更續即將燃盡之燭以及清除燭燼等,以保證所執之燭在使用過程中能夠持續燃燒。手執之燭的這些特點與火種和大燭的需要矚視、照看或前後相屬、不斷增續的特點相合,所以古人也稱其爲“燭”。

武氏祠左石室“顔淑握火”畫像石(取自《漢魏六朝碑刻校注》)
接下來討論戰國和漢代出土文獻所見一些燈具名稱中“燭”字的含義。
包山楚墓遣策262號簡記有燈具名稱“二燭銿”,整理者認爲:“銿,借作僮,指未成年之童。燭僮,即秉燭之僮。岀土的實物中有二件童子秉燈,與簡文相符。”(61)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62頁注563。何琳儀先生讀“銿”爲“俑”,認爲“燭俑”是“秉燭之俑”。(62)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中華書局,1998年,第425頁。劉信芳先生也改讀“銿”爲“俑”,並説“俑謂擎燈之銅人”。(63)劉信芳:《包山楚簡解詁》,藝文印書館,2003年,第280頁。“俑”與“銿”聲旁相同,“燭俑”的釋讀目前較爲通行。(64)參看黄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188頁;田河:《岀土戰國遣册所記名物分類匯釋》,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吴振武教授),2007年,第270頁;朱曉雪:《包山楚簡綜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21頁。但也有在“銿”字後不加括注以存疑者,如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47頁;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馬王堆一號墓遣策239號簡、三號墓遣策375號簡均記有“大燭庸二”。一號墓遣策中的“庸”字原報告釋讀有誤,後周世榮先生據三號墓遣策正確釋出。(65)唐蘭等:《座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1974年第9期,第53頁。李家浩先生結合漢代燈具自名以及雲夢大墳頭一號漢墓木牘所記燈名有“燭豆”之稱,讀“庸”爲“豆”。(66)李家浩:《關於陵君銅器銘文的幾點意見》,《江漢考古》1986年4期,第85頁。劉釗先生則據漢代燈具名“燭鐙”讀“庸”爲“鐙”。(67)劉釗:《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考釋》,收入劉釗:《古文字考釋叢稿》,嶽麓書社,2005年,第339—340頁。三號墓遣策中的“燭庸”,原報告認爲“庸即僕庸,燭爲舉火者,今引申爲燭鐙之鐙”,(68)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67頁(周世榮先生執筆)。伊强先生認爲此説從文意及語法上看都不合適,從聲韻通轉角度看,“燭豆”之説較“燭鐙”爲優。(69)伊强:《談〈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遣策釋文和注釋中存在的問題》,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李家浩教授),2005年,第43—44頁。
上引諸家對馬王堆漢墓遣策的考釋意見,《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皆已收録,除否定“僕庸”説外,對其他説法未作評判。(70)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六)》,中華書局,2014年,第208頁。此外,周世榮《湖南出土漢魏六朝文字雜考》也對“燭庸”作過解釋,認爲包山楚墓遣策中的“燭銿”與馬王堆漢墓遣策中的“燭庸”同義:“……‘庸’乃僕庸之意。馬王堆M1僅見燭鐙。而不見庸人執燭,也許‘燭庸’似可泛指燭鐙。”(71)周世榮:《湖南出土漢魏六朝文字雜考》,周世榮:《金石瓷幣考古論叢》,嶽麓書社,1998年,第240頁。范常喜先生認同此説,並有補充論證。(72)范常喜:《馬王堆漢墓遣册“燭庸”與包山楚墓遣册“燭銿”合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西書局,2017年,第245—251頁。
今按:周世榮先生將“燭銿”和“燭庸”聯繫起來頗爲有見。“銿”與“庸”的基本聲符都是“用”,古音聲韻皆同,它們確有可能記録同一個詞。但把“銿/庸”解爲僕庸似可商榷。上引諸家意見對“銿/庸”的釋讀可粗分爲人俑、僕庸類和豆、鐙類,人俑、僕庸類意見的主要根據是“燭銿”指墓中所出“人擎燈”。但是包山楚墓出土了四件燈具,除了兩件“人擎燈”外,還有兩件豆形燈,(73)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89、194頁。似不能排除“燭銿”所指爲後者,果真如此的話,這種意見就失去根據了。“人擎燈”只是把燈的底座改造成人形,其燈盤仍與豆形燈相同,如果“銿”是豆、鐙一類意思,則“二燭銿”既可以指兩件豆形燈,也可以指兩件“人擎燈”。馬王堆漢墓出土燈具並無“人擎燈”之類,且“燭庸”前尚有“大”字,指燈盤的容積(詳後文),將“庸”理解爲豆、鐙一類意思顯然更爲直接。“燭豆”與“燭鐙”二説,伊强先生已從聲韻通轉角度指出前者爲優。綜合來看,我們認爲“燭銿”和“燭庸”皆應讀爲“燭豆”。“銿/庸”也可能是從“豆”這個詞分化出來專門表示燈具的一個詞,原在楚地通行,後來逐漸消失了。
“鐙”在漢代或假借“徵”字表示,如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竹牘中所記燈具之名“燭徵”,(74)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9期,第54頁。上引李家浩先生文指出當讀爲“燭鐙”。漢代燈具銘文中也有不少帶“燭”字的自名,如:(75)下引銘文參看牟華林、鍾桂玲:《漢金文輯校》,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第197—221頁。“□者銅金小立燭豆”之“小”原釋“大”,今據袁永明《河北省鹿泉市高莊1號漢墓出土部分銅器銘文的再認識》(《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第55—57頁)改;“栒家銅燭錠”重量前的銘文原誤作“栒家銅熙,定烏(焉)八方”,今改;“藍田鼎湖宫行燭登(鐙)”之“登”字原作“豆”,今據容庚《金文續編》(容庚《容庚學術著作全集第五册》,中華書局,2011年,第43頁、386頁)改。“銅行燭鋪”的釋文據郭永秉《〈陝西金文集成〉識小録》(《古今論衡》第32期,第115—132頁)改。
元成家行燭豆,重二斤十四兩。第十七。
常山宦者銅金行燭豆一,容一升。重一斤十三兩。
宦者銅金大立燭豆一,容四升。重九斤。
□者銅金小立燭豆一,容大半升,重二斤□兩。
苦宫銅鳧喙燭定(錠),重一斤九兩。徑五寸。始元二年刻。
栒家銅燭定(錠),高八寸,重七斤十二兩。
陽邑銅燭行錠,重三斤十二兩。初元年三月,河東造。第三。
藍田鼎湖宫行燭登(鐙)□□□重二斤十一兩。第十。三年。官弗買。
銅行燭薄(鋪),重二(?)斤九兩。九年,工從造,第二鼻。
這些名稱中不少帶有“行”字。一般認爲行鐙是燈盤下没有支柱的燈具,或有短足,或無足,燈盤多有鋬以便手執,郭永秉先生指出這種燈具由豆形燈具演化而來,“立燭豆”是相對於“行燭豆”而言的。(76)郭永秉:《〈陝西金文集成〉識小録》,第128—129頁。“立燭豆”之前的“大”“小”指的是燈盤的容積,“大燭庸”的“大”也應如此。(77)“大立燭豆”的銘文記“容四升”,盤徑18cm,“小立燭豆”的銘文記“容大半升”,盤徑10cm(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鹿泉市文物保管所:《高莊漢墓》,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39頁)。馬王堆一號墓出土兩件陶燈,其中一件高15cm,盤徑18.5cm(傅舉有、陳松長編著:《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70頁),盤徑與“大立燭豆”接近,且其燈盤爲碗形,其容積當比“大立燭豆”還要大。三號墓北室出土的陶燈與木燈燈盤的容積不詳,但其盤徑分别爲15.5cm和15.3cm(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第231頁),也都大於“小立燭豆”,而與“大立燭豆”接近。
這些戰國及漢代燈具名稱的基本結構都是“燭”加豆類器名,(78)“鐙”本來是豆形食器之名,典籍常見。“鋪”是一種淺盤、柄部(或稱圈足)鏤空的豆形食器,始見於西周中期,流行於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參看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9頁)。“錠”與“鐙”在《説文》中互訓,在燈具自名中也頗爲常見,但器名“錠”在漢代以前典籍中罕見。一件春秋晚期銅豆自名爲“行鉦”(吴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卷304頁530號),這個“鉦”字應該就是“錠”字異體(與樂器名“鉦”是同形字)。其中的“燭”是什麽意思呢?孫機先生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解釋:

孫先生指出燈具的燈炷可稱“燭”,很有道理。《楚辭·招魂》“蘭膏明燭,華鐙錯些”句中在“華鐙”前並言膏、燭,這裏的“燭”也應指燈炷。孫先生説“燭錠”之名是“將燭和燈連爲一詞”,解釋尚不夠明確。劉釗先生在解釋“燭鐙”含義時指出:“《説文·金部》:‘鐙,錠也。从金登聲。’徐鉉曰:‘錠中置燭,故謂之鐙。’‘錠中置燭’正是對‘燭鐙’最恰當的解釋。”(80)劉釗:《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考釋》,第339—340頁。“燭錠”即置燭之錠,“燭豆”等名可類推。
孫機先生並未揭示燈炷爲何稱“燭”。結合昭通東漢墓銅燈中類似麻燭的燈炷,我們推測早期的燈具很可能就是用以承置麻燭的,燈炷實由麻燭演進而來。(81)考古發現的那些燈盤中有支釘的燈具所用的燈炷,除了與麻蒸類似者外,還有其他形制的,如廣西合浦風門嶺一座西漢後期墓中出土行燈的“支釘上殘存有燈芯,燈芯爲三股絞纏而成,下部開叉搭在燈盤中吸油之用。燈盤内還有油料的殘餘”(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合浦縣博物館編著:《合浦風門嶺漢墓:2003—2005年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29頁),這種燈炷屬軟燈炷,當由麻蒸類的硬質燈炷演進而來。燈盤中没有支釘、或這一部分不是尖釘形的燈具也用軟燈炷(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説(增訂本)》,第405頁)。軟燈炷更適用於液體燃料,且不需要頻繁更换,爲後世以植物油爲燃料的油燈一直沿用。古代室内麻燭多用手執,但肯定也有將其固定在某處以取代手執的辦法,桓譚《新論》中有“余見其旁有麻燭,而灺垂一尺所”“余嘗夜坐飲内中,然麻燭。燭半壓欲滅,即自勅視……”等内容,置於人旁的麻燭或燭燼垂下一尺多而没有及時打理、或等到快滅時才發現其燃燒不完全,可見其並非執於手中。上文曾引到唐人所述灌以脂膏、飴蜜的製作庭燎之法,這種給竹木類添加脂膏等物以助燃的做法由來已久,如《史記·田單列傳》所記牛尾炬即“灌脂束葦於尾”,古代的麻燭當亦有“灌以脂膏”一類的改進,使用這種麻燭時其脂膏容易流淌,顯然不便手執,需將其置於容器之上,進而由此演進出以燈盤、燈炷、脂膏等爲基本構成的燈具。這一演進使麻蒸由主要燃料轉變爲引燃物,脂膏由助燃物轉變爲主要燃料。
由於燃料的改進,燈具比麻燭有更好的燃燒性能和照明程度,但在使用過程中要不斷增添燃料、修治或更换燈炷(如《新論》:“燈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同樣需人矚視、照看,與麻燭的基本特點相同。因此燈具還有一些與“麻燭”結構相同的名稱,除了見於上文引文的“膏燭”外,典籍中還有“脂燭”(82)見《東觀漢記·和熹鄧皇后傳》:“晝則縫紉,夜私買脂燭讀經傳。”又《孔奮傳》:“四時送衣,下至脂燭。”《論衡·幸偶》:“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三國志·吴書·韋曜傳》:“窮日盡明,繼以脂燭。”《漢語大詞典》釋曰:“古人用麻蕡灌以油脂,燃之照明,是爲脂燭。”(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第6卷第1250頁)恐不確,上引《論衡·幸偶》句所在一段專論事物的幸與不幸,其所舉之物的遭遇均以幸者在前、不幸者在後,“脂燭”“枯草”之比與《淮南子》“膏燭”“黂燭”之比近似,唯枯草比黂燭更爲下矣。又《淮南子·繆稱》:“膏燭以明自鑠。”其義與“爍脂燭”類同,更可證“脂燭”與“膏燭”均指鐙而言。《漢語大詞典》第6卷第1365頁又釋“膏燭”爲蠟燭,亦不確。、“脂火”(83)見桓譚《新論》:“余後與劉伯師夜脂火坐語,鐙中脂索,而炷燋秃,將滅息……”古代亦稱燭爲火,參看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第164頁。等。有時燈具還可以直接稱“燭”,如燈具銘文“曲成家行燭一”、鐙下承盤銘文“車宫銅丞(承)燭槃(盤)”。(84)牟華林、鍾桂玲:《漢金文輯校》,第215頁、219頁。

這裏附帶談一談信陽長臺關楚墓遣策中一般認爲與燈具有關的名稱。

五
接着再來説一説“蠟燭”。
我國古代較早使用的蠟爲蜂蠟(也稱蜜蠟、黄蠟),起初跟膏、脂一樣,在燈盤中融化之後用作燈具的燃料,後來才有可直接引燃的柱狀蠟燭。孫機先生對此有很好的介紹:
漢代燃燈還可用蠟。《潜夫論·遏利篇》説:“知脂蠟之可明鐙也。”出土的漢燈中有的尚殘留燈蠟。解放前商承祚在《長沙古物聞見記》中説:“漢墓偶有黄蠟餅發現”,“豈以之代膏邪?”解放後,在長沙楊家大山401號、沙湖橋A45號漢墓中,均於銅燈内發現殘蠟,可以作爲以蠟代膏之證(原注:見《長沙發掘報告》第115頁;《長沙沙湖橋一帶古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7年第4期)。晋·范堅《蠟燈賦》中描寫過這種燃蠟的燈:“列華槃,鑠凝蠟。浮炷穎其始燃,秘闈於是乃闔。”(《藝文類聚》卷八○引)。可見蠟燈内的蠟是融化後作爲油膏使用的。至東漢晚期,在廣州漢墓中最先出現燭臺(90-4)。説明細長柱狀的蠟燭這時已進入照明用品的行列之中了。(98)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説(增訂本)》,第412頁。
目前發現的最早的蠟燭實物出於南京江寧一座三國孫吴時期的墓葬,殘存半截,插於瓷辟邪形(或稱“獅形”)燭臺之上。(99)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江寧區博物館:《南京江寧上湖孫吴、西晋墓》,《文物》2007年第1期,第41頁。另外,河南陝縣一座唐墓也曾出土兩隻表面繪有黑、緑兩色的梅花圖案的蠟燭,其中較爲完整的一隻長43cm,直徑5.5cm(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陝縣唐代姚懿墓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87年第1期,第131頁)。由此來看,認爲蠟燭在東漢晚期就已出現是合理的。(100)西漢南越王墓出土屏風上的蟠龍形托座和朱雀形、獸首形頂飾均有管形插座,在初步報告中被誤認成燈具(參看麥英豪等《南越王墓出土屏風的復原》,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33—451頁)。有一些研究燈具的學者没有注意到正式報告的説明,認爲這些器物就是燭臺,用以證明西漢初期已有蠟燭,與下文所引《西京雜記》所載南越王獻蜜燭事牽合,是不可信的。廣州漢墓出土了三件盤中立長柱的陶製燭臺,分别出自三座規模較大的東漢後期墓葬中,可分爲兩種類型,一種是柱托型燭臺,在柱旁設置托和箍以插燭;一種是管狀燭臺,其柱的上半中空,用以插燭。(10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廣州漢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上册第412頁。報告還提到1959年發掘的一處東漢殘磚墓中出土的一件由柱和獸座兩部分組成的燭臺,其柱上共有四套圓箍。這兩種類型的燭臺在魏晋南北朝時期都繼續使用,管狀燭臺一直到隋唐乃至宋元都頗爲流行,其造型更爲多樣,插燭的管也可以有多隻,明清時期則多見立釺式的燭臺,(102)參看孔晨、李燕編著:《古燈飾鑒賞與收藏》,第98—168頁;徐巍《中國古代陶瓷燈具研究》,《文物世界》2004年第1期,第41—51頁。這可能與當時蠟燭由硬度較高、燃燒性能較好的白蠟製成有關。(103)張磊:《中國古代燈具形制和照明燃料演變關係考》,《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第191—193頁。
文獻中“蠟燭”之稱最早見於南朝劉义庆的《世説新語》,如卷三十《汰侈》:“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又卷六《雅量》:“周仲智……舉蠟燭火擲伯仁。”此事《晋書·周顗傳》記作:“(顗)以所燃蠟燭投之。”“蠟燭”這一名稱的結構與“麻燭”“膏燭”等相同,是指以蠟爲燃料的“燭”。蜂蠟的熔點較低,其燃燒過程中容易軟化和滴淌蠟液,使用時當然需要矚視、照管;有些柱托型燭臺的托可以上下調節,(104)孔晨、李燕編著:《古燈飾鑒賞與收藏》,第103頁。顯然是要隨着蠟燭燃燒變短而調節高度,以保持照明效果,這更能體現其需要矚視、照管的特點;蠟燭燒完之後同樣需要更續,只不過不必像麻燭那樣頻繁;並且蠟燭的外形及其與燭臺的組合分别與麻燭、燈具類似,當有演進關係,稱其爲“燭”是很合適的。
此外,蠟燭還有不少異稱。一般認爲是東晋葛洪所編的《西京雜記》載:“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古代的蠟爲蜜蠟,“蜜燭”與“蠟燭”同義,其以枚爲單位,當亦是長柱狀。但《西京雜記》多爲小説家言,其所記之事不一定可信,俞樾即已指出:“《西京雜記》雖有閩越王獻高帝蜜燭事,然雜記所言本非可據。”(105)俞樾撰,貞凡、顧馨、徐敏霞點校:《茶香室叢鈔》,中華書局,1995年,第738頁。不過這則資料至少可以説明東晋已有“蜜燭”這一名稱。唐代詩文中除了大量出現的“蠟燭”之稱(或作“燭”,見上文所引孔穎達疏)外,還有“蠟炬”“炬蜜”之稱(“炬蜜”即“蜜炬”之倒文),又簡稱爲“蠟”“燭”。(106)參看冉萬里:《唐代蠟燭小考》,《人文雜誌》1994年第1期,第97頁。“蠟燭”“蠟”“燭”這些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六
最後,結合本文的主要内容對古代“燭”的得名原因及其源流進行一下梳理。
蔣玉斌先生所釋甲骨文的“獨”字,當從陳劍、郭永秉先生説改釋爲“矚”,其字象突出目形的拄杖人形,表示長時間矚視之義。陳漢平先生所釋甲骨文的“燭”字,字形象突出目形之人手持工具矚視、照管火種,其上部突出目形的持杖人形即“矚”字,兼起表音作用。從甲骨文來看,“燭”的本義是需要矚視、照看的火,或前後相屬、不斷增續的火。古代照明用具燎、麻燭、燈具、蠟燭等也有需要矚視、不斷增續的特點,故皆有以“燭”爲中心語的名稱。燎樹立於地且形制較大,故稱“地燭”“大燭”。先秦典籍中不加修飾和限定的照明用具“燭”指手執的火炬,又有在“燭”前標明燃料的“麻燭”“蕡燭”等名。燈具可能在春秋時期出現,由食器豆轉化而來,燈炷係由麻燭演進,戰國及漢代出土文獻中多見“燭”加中心語豆類器名的燈具名稱,這類名稱中的“燭”指燈炷;典籍中燈具又有與“麻燭”結構相同的、標明其燃料的“膏燭”“脂燭”等名稱。蠟燭至遲在東漢晚期已出現,當由麻燭、燈具演進而來,“蠟燭”之名的結構與“麻燭”“膏燭”相同,指以蠟爲燃料的“燭”。
2019年5月12日修訂
2019年10月14日再改
附識:本文由2015年1月完成的一篇習作改寫而成,承裘錫圭、陳劍、郭永秉、蔣玉斌諸位先生審閲並提出修改意見,作者十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