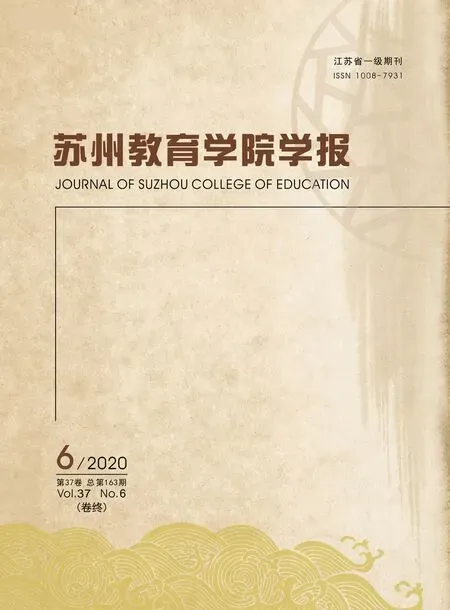青少年女性的数字影像操弄与自我建构
杜志红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根据《2019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5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7.25亿,占网民总体规模的87.5%;短视频应用用户规模增长迅猛,达6.48亿,占网民总体规模的78.2%。[1]同时,网络视频的主要用户为青少年,其中,青少年女性对网络视频直播和短视频的使用格外引人注目。
近几年学界对新媒介领域的影像传播现象的研究,要么从商业营销模式的角度去憧憬,认为其中蕴含巨大的商机和市场营销方式的变革;要么从内容规范性的角度去审视,认为其中有不少三俗、无聊的传播内容,需要进行监管或打击;而从传统的影视艺术审美范式看来,这种个体化、社交化、碎片化的影像操弄与把玩,似乎没有什么“营养”或内涵,更谈不上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因而,在网络视听研究中出现了对这类现象要么追捧、要么棒喝的两极化情况。对于网络视听传播现象,我们有必要跳出商业的或伦理的视野,跳出传统影视节目的审美规范,在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中展开研究,探讨和检视这些数量庞大的数字影像的生产者和使用者是如何在新的影像传播环境中制造意义、建构自我的。
从使用者角度看,无论是网络视频直播还是抖音、快手、微视等短/小视频应用的处理和上传,本质上都是普通人特别是青少年对数字影像的一种操弄与把玩。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影像传播现象,尤其当女性掌握了用来注视和拍摄的数字影像武器,能够自由地操弄自己的身体影像进行传播时,对于使用者本身将有怎样的意义?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笔者带领研究团队,对数字影像应用中的女性影像进行了文本考察,对一些青少年女性使用者和观看者作深度访谈,同时运用精神分析和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认真考察借助网络视频直播、短视频应用、美图软件等数字影像工具而展开的影像传播实践。在笔者看来,这些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女性影像操弄现象,并非没有“意义”。概括起来,这些“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媒介中的自我建构、面向社会的认同建构、审美意识中的服从与抵抗。
一、影像操弄中的女性自我认同建构
无论是自拍、“美颜”、视频直播还是短视频上传,都离不开一个核心的行为模式—观看。影像操弄是对观看的练习和传播,而观看行为则是一个人如何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重要方式。约翰·伯格曾说,“藉由观看,我们确定自己置身于周遭世界当中”,这是因为“我们注视的从来不只是事物本身,我们注视的永远是事物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同时 “在我们能够观看之后,我们很快就觉察到我们也可以被观看。当他者的目光与我们的目光交会,我们是这个可见世界的一部分就再也没有异议了”。[2]10-11
手机拍摄行为的日常生活化,也是观看世界和自我观看的日常生活化。女性尤其是青少年女性的日常影像操弄行为,包括了三个相互连带的观看行为:照镜子—拍摄—传播。其中,女性在不同层次上建构起自我的不同方面。
首先是照镜子。雅克·拉康曾说,一个孩子从镜子里认出自己形象的那一刻,对自我的形成是何等关键。由此发展出著名的“镜像”理论,他认为孩子在照镜子时,“认出自己时所感受到的愉悦,是出于他想象他的镜像要比他所体验到的自己的身体更完全、更完美。于是,认知和误认重叠了:被认出的形象来自镜中自身的折射,但是误认却优先地把这个折射的身体作为一个理想自我的外部投射,而这一理想自我乃是一异化的主体,它作为自我理想又被重新观照摄取,引发认同他者(others)的下一阶段”[3]525。如今,手机使女性的照镜子行为摆脱了空间束缚,从而在频次和时间上成倍地增多。虽然青少年女性已不再处于拉康所说的婴儿时期,但每一次照镜子的行为都是一次自我审视、自我“补妆”,同时也是一次自我塑造、自我肯定的契机。她们会按照理想自我的标准不时地修补自己的形象,使自我始终处于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其次是拍摄。当女性觉得自己形象的状态非常好时,她会拍摄并保存下来。当然,在实际操作中,不一定都是采取自拍的方式,也可能借助在场其他人的帮助来完成拍摄,但本质上女性还是处于拍摄行为的主导地位,仍然可以看作她在进行一种自我影像的生产和操弄。这种理想自我的影像生产和操弄,构成了女性对于自我想象的“基质”,“构成了认知/误认和认同的基质,以及由此构成了‘我’和主观性的第一次应和(articulaion)的基质”[3]525。也就是说,女性观看自我影像时带来的愉悦、快感及自我认同,是自恋和自我建构的重要来源。至于说为何这些影像能让女性感到愉悦和满足,主要归功于手机(相机)的各种美颜软件。女性在拍摄时,会主动选择使用美颜软件进行拍摄,或在拍摄后对影像进行加工和美化,如“瘦脸”“瘦身”“磨皮”“拉伸”等,这已成为目前女性操弄自身影像时的常见现象。
再次是传播。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发达与多元,使女性有了更多的平台和空间可以晒出自己的影像,甚至通过活动影像媒介(如视频直播)与外界沟通交流。在这些传播活动中,女性以自己的容貌和身体作为影像表现的“内容”,从而建立起(理想中的)自我与外界的关联,在传播网络的影像空间里,女性除了观看理想的自我形象外,还能观看到外界对自我形象的观看。与约翰·伯格所描绘的状态不同的是,女性的这种“观看着自我被观看”的状态是以影像方式呈现的,即这种观看行为是在网络空间中展开的,而不是在现实空间。换句话说,女性的容貌和身体被拍摄成数字影像后,这些影像就脱离了女性身体本身,成为一种可以无限复制的“影像面具”或“赛博面具”,成为她们的替身,出现在网络空间中。这种由于影像媒介的介入而导致的女性被观看的现象,比她在现实中被观看更有安全感—她清楚地知道,无论在微信朋友圈、“抖音”或视频直播中,人们观看的只是自己的影像,而不是自己。即使她知道自己的容貌和身体正被无数人“消费”,但那不是对容貌和身体本身的消费,只是对其影像的消费。但更重要的不同在于,女性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像在媒介中被观看的现象,这意味着女性可以自由选择呈现什么样的自我影像,即女性可以操控别人对于自己的观看方式。正如约翰·伯格所说的“每个影像都具现了一种观看方式”[2]13。那么,掌握了拍摄和传播自我影像的女性,其实就掌握了操控别人如何观看自己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的获得,也是操控者媒介使用能力的体现,女性为拥有这样时尚的媒介素养而骄傲,这也成为她自我建构和自我认同的重要方面。
那么,女性通过照镜子、拍摄和上传自我影像的系列行为,建构了一个怎样的自我呢?米德认为,“主我”是有机体对“其他人的态度”作出的反应,“客我”则是一个人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其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它们共同构成了出现在社会经验中的人格,却又并不是完全同一的。[4]女性对自我影像的操弄,本质上是通过对自我形象的符号化和媒介化,在网络空间建构起“第二自我”。这个“第二自我”看起来比现实中的“自我”更理想、更完美,能得到来自朋友或陌生人的赞美,她“组织”了这些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而这些态度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经常获得的,所以,她会更喜欢这个网络空间中的“第二自我”,会花大部分时间沉浸在“第二自我”的生活空间里,在那里她能得到现实生活中没有的自信和满足。
二、影像互动中的青少年女性社会认同想象
在米德看来,传播在本质上是不同生活经验之间的交流。女性通过操弄自己的身体影像在新媒介空间中交流互动,可以看作是她试图与他人展开生活经验的交流,这种交流由于新媒介的介入,而大大超出了其在现实空间中所能感受到的范围和强度。比如,在视频直播或者“抖音”等短视频应用中,有不少青少年女性拥有百万、千万的关注者,这是现实中无法想象也无法实现的,因此,她们会把这种互动作为探究社会对自己认同程度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她们试图通过操弄自己的影像与社会展开互动,并建构起社会对她们的认同。
互动需要内容,大部分青少年女性没有多少“内容”可以分享,她能分享的只有她自己,包括她的故事、形象、爱好或特长等。通过互动,她们在数字影像中讲述自己的故事,把日常生活状态或行为转换为一种景观,并试着与世界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完成了自己的社会化。借用迪尔凯姆的观点,女性在影像互动过程中,可以通过那些对话、“点赞”、转发、观看、“加关注”等数据指数,判断关注自己影像的人数和对自己的评价,她们聆听着这些评价,就仿佛在聆听社会(她们以为这些人就代表了社会),从而使“社会对个人的感情提升了个人对自己的感情”①转引自库尔德利著、何道宽译:《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93页。,她们从这些感情中体会到社会对自己的感情,从这些评价中感受社会对自己的评价。
为了获得社会认同,青少年女性会更多地以社会的眼光来审视自己,让自己成为符合大众审美的景观。由于影像媒介的介入,她们所操弄的自我身体影像,成为一种可以给自己带来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本的“象征性形式”,即“主要指通过印刷、照片、电影、视听或数码等技术复制和传递的人类交际的内容……这是象征性形式确定其个性和力量的重要方式的一部分”[5]。比如,在视频直播或“抖音”等短视频应用中,青少年女性会通过直播互动或短视频评论区来分享一些基本的生活或知识技能,比如化妆、美食制作、唱歌、跳舞、音乐演奏、健美健身、旅游见闻、专业知识等。作为普通人,这些技能和知识几乎没有机会在传统电影或电视上得以展演或传播,但在视频直播或短视频应用中可以轻易实现,甚至还可以与“粉丝”建立约会或朋友关系,这些都是她们通过这种象征性形式建立起的“象征性社会资源”。正如陈卫星所说:“在无数开放的社会传播的链条中,人们幻想自我拥有什么东西作为自己的象征资源。这个资源是象征权力实施的媒介者,是社会在物质和象征意义上得以再生产的组成要素。”[6]
通过运用不同类型的数字影像媒介所形成的“象征性形式”,青少年女性获得了自己的象征性文化资本,比如,她们会被称为“网红”“主播”,这些名称与先前的“网络红人”“电视主播”等的名望或地位相勾连,带有一种“成名的想象”的意味;同时,她们拥有的“粉丝”数和直播中的“礼物”“点赞”,甚至一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都是对她们拥有的象征性权力和资源的一种现实肯定。
三、青少年女性影像操弄中的审美顺从与抵抗
青少年女性如何能在影像操弄中扩大别人乃至社会对自己的认同呢?首先,自身容貌和身体的审美应符合社会的“主流观念”。那什么是关于女性美的主流观念呢?可以从女性在操弄自己的影像时经常使用的美颜相机来窥见一斑。
美颜相机有“美肤”“清晰”“瘦脸”“缩脸”“放大眼”“收下巴”“美牙”“长腿”等功能选项,“美肤”会使皮肤看起来光洁、平滑;“瘦脸”可以将面部两侧的部分向中间靠拢,使脸看起来更符合图像逻辑;“美牙”则使牙齿看起来更亮白、健康;“长腿”是简单粗暴的拉长腿部,调整比例。如果将美颜级别设置为“默认模式”,那么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一个“小脸、大眼、肤色白皙、鼻子小巧、唇红齿白、腿长”的典型的、去缺点化的“标准美女”形象。
那么这些影像处理功能又是遵循着什么样的逻辑而设置的呢?根据我国的女性审美史可以看出,这些功能的设置源于我国长期历史积淀的男权审美意识形态。从《诗经》里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7],到我国古代形容四大美女的“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再到《红楼梦》对美人的诗意描述,无不折射出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趣味,如肤如凝脂、唇红齿白、凹凸有致、体态轻盈、神态温婉,等等。这些审美趣味恰恰是美颜软件功能设置的潜在标准。也就是说,对自己身体影像的处理,看似是女性在媒介使用过程中主动选择的结果,但实际上还是在男权对女性美的审美框架中进行的。
正是通过使用美颜软件和对拍摄场景、方式的自导自演,女性发现可以通过操纵自己身体进入到类似“艺术再现”的领域,使自己超脱出物质的身体成为“艺术的身体”。在视频直播或短视频应用中,许多女性通过使用拍摄技巧和场景调度,把自己置于一种艺术化的氛围中,不管是美食制作、健身、舞蹈还是演奏、书画等,她们都把自己的容貌和身体通过表演而艺术化了,在这种艺术化的再现中,容貌和身体通过影像转换为符号,它承载着一系列关于美貌、美体和美好生活的想象与建构。这一系列复杂的符号体系,就构成了米尔佐夫所说的“身体图景”[8]5,在他看来,这些身体图景无疑寄托着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某种理想性审美。
然而这种理想性审美的获得,却往往难以跳脱出传统男权审美框架对于女性身体美的定义。因此,女性在对自我身体影像的操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被传统的男权审美框架所裹挟,这种“理想自我”的本质已不再具有主体性,而成为供男性凝视和赏玩的“女性身体景观”。米尔佐夫认为:“身体的符号也会对物质的身体产生非常实在的影响,尤其是在决定何种形态属于‘正常’这个方面。”[8]5也就是说,因为能够经常通过影像操弄进入理想身体的欣赏中,所以物质的身体反而被认为是有种种缺陷的、“不正常”的。“符号身体”成了现实身体的裁判,身体审美代替了身体自在,导致“女性越来越被混同于自己的身体”[9]。在这种符号身体的景观中,女性的身体完全沦为被消费的“物”,而不是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人而存在,她的才能、智慧、理性等无法通过景观呈现的品质都会被忽略、无视,这就导致女性的自我认知出现了巨大偏差。因为借助影像处理软件而建构起来的“美丽”,仅仅作为一种可交换、可消费的身体影像符号而存在,她进行的自我影像操弄不过是一场消费逻辑下的符号操纵而已。
当然,在这些影像操弄行为中,也有一种反向操作非常引人注目—女性会对自己的影像进行违背传统审美的丑化或怪异化处理,她们会选择图像处理软件中的“搞怪贴纸”功能,对容貌或身体进行怪异的“变形”,比如让脸部变形、变丑,缩小双眼、放大嘴唇、扭曲面部线条,或添加各种动物的面部特征等,将自己处理成一个“丑八怪”。这些影像操弄行为或可被看作是对“男权审美”“商业审美”裹挟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方式是拼贴、戏仿、揶揄、反讽式的,显得并不正面、强烈和严肃,仅仅带有某种象征性。但它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即她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对传统审美表达某种反抗性或戏谑性的话语,以拓展一个另类的、有多种可能性的女性影像审美空间。
综上所述,青少年女性利用新媒介平台对自身影像的操弄行为,能帮助她们更好地认识自我的多面性,扩大与社会的交流、对话,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性文化资源和权力。同时,她们也在其中经历了女性审美意识的社会束缚,以及通过抵抗带来的成长体验,从而为新的文化主体的生成奠定了可能性。所有以上这些“意义”,并不能用传统的影视艺术理论、影视创作理论或影视审美理论、影视产业发展理论等原有框架来理解,而需要借助多学科的理论工具进行考察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