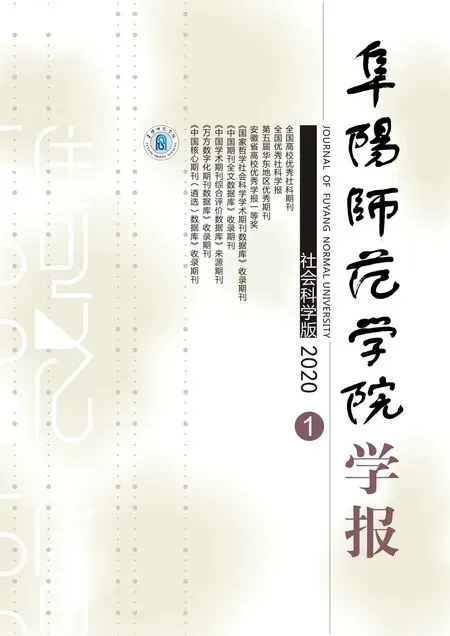从“春衫袖”管窥《生查子·元夕》的作者
肖汉泽
从“春衫袖”管窥《生查子·元夕》的作者
肖汉泽
(阜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安徽 阜阳 236000)
在唐宋诗词中,“春衫”多用来表示男性着装,尤其是青年男性的着装,也有用春衫直接指代男主人公的。春衫作为男性着装的说法,是唐宋诗词约定俗成的用词习惯,尤其是唐、北宋以及南宋前期,几乎成为男性着装的专用词语;直到南宋中晚期,才有极少数作为女性着装的说法,这种说法,应该是男性着装说法的后期演化用法。而“红袖”常被用来指代女性。用女性特征极强的红色作为修饰语,来描写女性衣袖,甚至直接指代女性,在唐宋诗词中屡见不鲜。还是用唐圭璋“春衫纵马,红袖相招”来概括最为精当,这“纵马”的“春衫”在《生查子·元夕》词里,只能由欧阳修来充当了。换句话说,“泪满春衫袖”的只能是“春衫”欧阳修,而非“红袖”朱淑真。
春衫;红袖;《生查子·元夕》;欧阳修;朱淑真
《生查子•元夕》是一首脍炙人口、意境优美的宋词珍品,其中“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又是表现爱情的千古名句。20世纪80年代,经一代歌后邓丽君演唱响遍全球,成为家喻户晓的千古绝唱。就是这么一首千古名作,数百年来,却在作者为谁的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来逐渐集中到朱淑真与欧阳修身上,邓丽君《人约黄昏后》的演唱及其《生查子·元夕》尾句“泪满春衫袖”中的“春衫袖”,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我们传递《生查子·元夕》词作者的某些信息。
一、从“春衫”看《生查子·元夕》的作者
衫,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衫,衣也。从衣,彡声”,述衫为上衣;汉末刘熙《释名·释衣服》云:“衫,芟也。衫末无袖端也”,述衫无袖端。“无袖端”并非无袖子,而是敞式袖口,或云广袖。《宋史·志第一百四·舆服五》云:“中兴,士大夫之服,大抵因东都之旧,而其后稍变焉。一曰深衣,二曰紫衫,三曰凉衫,四曰帽衫,五曰襕衫。”又云:
紫衫。本军校服。中兴,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绍兴九年,诏公卿、长吏服用冠带,然迄不行。二十六年,再申严禁,毋得以戎服临民,自是紫衫遂废。士大夫皆服凉衫,以为便服矣。
凉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礼部侍郎王严奏:“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陛下方奉两宫,所宜革之。且紫衫之设以从戎,故为之禁,而人情趋简便,靡而至此。文武并用。本不偏废,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害大体。”于是禁服白衫,除乘马道涂许服外,余不得服。若便服,许用紫衫。自后,凉衫祗用为凶服矣。
帽衫。帽以乌纱、衫以皂罗为之,角带,系鞋。东都时,士大夫交际常服之。南渡后,一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自是服帽衫少矣。惟士大夫家冠昏、祭祀犹服焉。若国子生,常服之。
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辟积。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服之。
这里述及“紫衫、凉衫、帽衫、襕衫”四衫,“大抵因东都之旧”,即承袭北宋旧制,“而其后稍变焉”。由绍兴“二十六年,再申严禁,毋得以戎服临民,自是紫衫遂废。士大夫皆服凉衫,以为便服矣。凉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又帽衫”。“南渡后,一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可知紫衫与凉衫同制,紫、凉、帽三衫皆为夏服;但均未述及衫袖的形制。唯独襕衫云及形制较清,述其圆领大袖,腰间有褶裥,下摆加横襕,大抵系上衫向下裳的延伸。《唐书·车服志》云:“士人以枲紵襴衫为上服,马周请加襴袖褾襈。”是说士人原以麻织襴衫为上服,唐中书令马周建议下摆加横襕,领、袖、襟、裙加缘边,以示不忘上衣下裳的祖制。宋承唐制,宋史《舆服志》所云襴衫“圆领大袖”,大者,广也,大袖也谓之广袖,或曰敞袖,非无袖也。
衫有单夹之分,短长之别。夹衫是在单衫的基础上缀以衬里;长衫系如襴衫那样,由上衫向下裳的延伸。
可见,在宋代,衫是一种敞袖单、夹上衣,或下摆加横襕的长衣。那么何谓春衫?《说文解字》等相关典籍中似乎没有专门的解释。近年来有人把它解释为“春天穿的衣裳”,或青颜色的衣衫;也有人把它解释为青年男子穿的衣衫。在唐宋诗词中,“春衫”则多用来表示男性,尤其是青年男性的着装。
(一)在唐宋诗词中,“春衫”多用来表示男性着装
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送魏四落第还乡》诗云:
东归不称意,客舍戴胜鸣。腊酒饮未尽,春衫缝已成。长安柳枝春欲来,洛阳梨花在前开。魏侯池馆今尚在,犹有太师歌舞台。君家盛德岂徒然,时人注意在吾贤。莫令别后无佳句,只向垆头空醉眠。
诗谓长安柳枝发青、洛阳梨花盛开季节,魏四落第从长安东归洛阳,心中自然不称意。作者作诗相送,以魏四祖上魏徴之功德,鼓励魏四奋发有为,切莫醉酒消沉无佳句,有失魏家盛德。诗中春衫系指为落第魏四所缝制的春衫,当为男性着装。
唐代诗人白居易《寿安歇马重吟》云:
春衫细薄马蹄轻,一日迟迟进一程。野枣花含新蜜气,山禽语带破匏声。垂鞭晚就槐阴歇,低倡闲冲柳絮行。忽忆家园须速去,樱桃欲熟笋应生。
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自洛阳返故乡下邽途经寿安时作。诗谓白居易返乡心切,着春衫跨轻骑,昼行夜宿。一路上,野枣花开,山禽匏叫,歇马槐阴,行迎柳絮,低吟浅唱。忽又想起故乡的宅院,欲熟的樱桃,初生的笋芽。想到这,便扬鞭催马向着家园加速行进。这春衫自然是男性着装了。
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饮席代官妓赠两从事》云:
新人桥上著春衫,旧主江边侧帽檐。愿得化为红绶带,许教双凤一时衔。
诗义说:新识春衫得意桥上走,旧交江边侧帽显风流。真想化作红绶带,系住新旧两相识。
这是一首李商隐代官妓写给李商隐两个同事的诗。这两个同事,即诗题所云两从事:一个是官妓的旧主,一个是官妓的新识。李商隐两从事,显然均为男性。新识身着春衫,正当青春年少。这春衫自然是男性着装。
五代词人孙光宪《谒金门》(《花间集》)云:
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纻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只。
词写闺人怨别离。意云,欲留而不得,即使留得也没有益处,记得初去扬州日,江头送别,他白纻春衫,莹洁如雪,潇洒飘逸,风神如玉。面对繁华去处,视别离如等闲、抛掷如儿戏,风帆满鼓,舟行如飞,飘然而去。我羡慕那江面上,双双对对的鸳鸯,而叹息自身之有如孤鸾。此处“春衫”,即指潇洒飘逸,风神如玉,然而又“轻别离,甘抛掷”的男主人公的着装。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持另外一种解释云:“此首写飘泊之感与相思之苦。起两句,即懊恨百端,沈哀入骨。‘白纻’两句,记去扬州时之衣服,颇见潇洒豪迈之风度。下片换头,自写江上流浪,语亦沉痛,末两句,更说明孤栖天涯之悲感。通篇入声韵,故觉词气遒警,情景沈郁。”[1]25其“春衫”也系指男性着装。
北宋词坛耆宿晏殊《采桑子》云:
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衫酒易醒。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
时光只管匆匆向前,催人容颜老去,哪里知道有情人留恋之苦,相思之痛,离别的眼泪滴湿了春衫,借酒浇愁,酒醉了很快就又醒来。春去秋来,西风梧桐,月色惨淡,好梦总被这无尽的思念、离别的痛苦、西风的骤起而惊醒。何处高楼,一只孤雁飞过,哀唳划破了黎明的寂静。
这首词轻巧空灵,深蕴含蓄,清丽哀怨,抒发了自己的人生感慨。词中“春衫”系晏殊的男性着装。
北宋豪放派词人苏轼《青玉案·和贺方回韵送伯固还吴中》云:
三年枕上吴中路,遣黄犬、随君去。若到松江呼小渡,莫惊鸳鹭,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辋川图上看春暮,常记高人右丞句。作个归期天定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
三年来,魂牵梦绕吴中路,如今你就要起程了。送只黄犬随君去,期盼回去常来信。若到松江,呼唤小舟前来摆渡,切莫惊吓了鸳鸯白鹭,吴中四桥、河湾渡口,都是我当年常去处。如今只能在王维的辋川图中,欣赏暮春风景,回味伯固、王维送友思归的诗句了。定个还乡的日子,上天必然会应许。身上的春衫,还是朝云当年针线,那上面曾被西湖的雨滴打湿过。
这首词为送友抒怀之作。苏伯固跟从苏轼三年,就要起程归吴中,苏轼和贺方回韵作此词送别,抒写对苏伯固归吴的羡慕和自己对吴中旧游的系念之情;表达自己希望归隐旧地的愿望和宦游难归的慨叹。末句云西湖雨打湿过的春衫,使人联想到送别时的雨景和惜别时的情谊;春衫上千针万线,皆是爱妾朝云串连,更增加了思乡归隐之意。这首词的春衫,自然也是男性着装了。
晏殊七子、北宋词人晏几道《鹧鸪天》云:
醉拍春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到夕阳。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
醉意中,拍打身上的春衫,散发出,往日与玉人欢乐,沾染遗留的缕缕馨香。我本是性情疏狂的人,上天为什么偏用离愁别恨折磨我。苍凉陌上,年年衰草滋蔓,清寂楼中,日日夕阳残照。云水渺茫,归路难寻,相见无期。相思本就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又何必重展花笺,枉流许多相思泪!
这首词,以作者醉拍自身春衫,嗅昔日佳人沾染遗留的馨香起笔,抒写绵绵离恨和对落拓平生的无限感慨,词中春衫自然是男性着装。
北宋末期著名词人、婉约派集大成者周邦彦《品令·夜阑人静》云:
夜阑人静。月痕寄、梅梢疏影。帘外曲角栏干近。旧携手处,花发雾寒成阵。应是不禁愁与恨。纵相逢难问。黛眉曾把春衫印。後期无定。断肠香销尽。
此词写于梅树盛花的春天, 夜阑人静,“月痕寄、梅梢疏影”,是从帘内起笔,至于帘外,则虽有近在咫尺的“曲角栏干”,却不敢凭依,因其为“旧携手处”“花发雾寒”,触景伤情,“不禁愁与恨”。换头“纵相逢难问”,增强渲染力度。随后用“黛眉”句寓意深长。墨眉具有印痕的特点,在晚唐,青楼女子中,流行把眉印和口红印送给心仪的男人,到宋代,赠送“印眉”之风尤其流行。欧阳修《玉楼春》,曾专门写“印眉”云:“半辐霜绡亲手剪。香染青蛾和泪卷。画时横接媚霞长,印处双沾愁黛浅。当时付我情何限。欲使妆痕长在眠。一回忆着一拈看,便似花前重见面。”“黛眉”三句意为,她依偎印染在我春衫上的眉痕,因时间的流逝已经香消殆尽,令人肝肠寸断的是,至今仍然无从确定与她重见的日期。这里的“春衫”便是被黛眉印染的男性着装。
北宋词人贺铸《忆秦娥·著春衫》云:
著春衫。玉鞭鞭马南城南。南城南。柔条芳草,留驻金衔。粉娥采叶供新蚕。蚕饥略许携纤纤。携纤纤。湔裙淇上,更待初三。
这是一首春游踏青词。上阙写柔条芳草、阳光明媚的春天,作者穿着春衫,手持玉鞭,策马城南,兴致勃勃去踏青。下阙写采桑女为新蚕采罢桑叶,在淇河水中洗涤裙子的情景。
贺铸《忆秦娥·著春衫》起句“著春衫”,是写作者春游踏青时的着装。自然是男性着装了。
北宋词人徐伸《转调二郎神·闷来弹鹊》云:
闷来弹鹊,又搅碎、一帘花影。漫试著春衫,还思纤手,熏彻金猊烬冷。动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来多病。嗟旧日沈腰,如今潘鬓,怎堪临镜?重省,别时泪湿,罗衣犹凝。料为我厌厌,日高慵起,长托春酲未醒。雁足不来,马蹄难驻,门掩一庭芳景。空伫立,尽日阑干倚遍,昼长人静。
心中烦闷,喜鹊却无喜偏叽喳乱叫。烦闷地弹走喜鹊,反而搅碎了一帘花影。春天到了,随意试着春衫,又想起她那双纤嫩的为自己缝制春衫、点燃香炉的手。如今熏炉的香料,已经灰烬变冷。动辄引起忧愁,却又不知该如何是好。奇怪的是近来多病,可叹本来就很瘦弱的身体,如今又添白发,竟至不敢照镜。重想起,临别时她痛哭流涕,泪水打湿了她的罗衣,想必至今还凝结着泪痕。料想她为我而相思成疾,终日精神萎颓,太阳升得老高,还不肯起床。无法把真情告诉别人,只能推托春饮醉酒未醒。她日夜把我等待,可是始终不见传递书信的鸿雁;也终究看不到我骑坐的马蹄,在她门前驻留。她的院门紧闭,掩住一院春景。她伫立空等,整日凝望;依遍了庭院里所有的栏杆;春夏天长,声消人静,一片空寂。
这首词通过具体细节的描写,表达离别后,男女双方的复杂心情和思念情怀。文思跌宕,曲折感人。词中春衫显系男性着装。
宋徽宗崇宁进士、南渡名相赵鼎《点绛唇·春愁》云:
香冷金炉,梦回鸳帐馀香嫩。更无人问,一枕江南恨。消瘦休文,顿觉春衫褪。清明近,杏花吹尽,薄暮东风紧。
金炉中的香料,已经灰烬变冷,低垂着的鸳鸯帷帐,散发着幽微的余香。梦醒忆梦无说处,欲说梦境无人问,难解一枕江南恨。形体犹如病中的沈约,日益消瘦,人儿憔悴,身上的春衫顿觉宽松。清明已近,薄暮来临,东风渐紧,杏花已被吹落殆尽。
这首词,通过室内室外景物的描写,曲折含蓄地表露出作者无可排解的离恨与春愁,孤独与伤怀。婉而不弱,约而不晦。委婉柔媚,意境幽美。词中的春衫即是其男性着装。
宋代诗人吴涛《绝句·游子春衫已试单》云:
游子春衫已试单,桃花飞尽野梅酸。怪来一夜蛙声歇,又作东风十日寒。
诗写春深夏浅,桃花已败,野梅已酸,蛙声此起彼伏。游子在外,已经尝试着,换上单薄的春衫。奇怪的是,忽然一夜蛙声骤停,东风吹来,乍暖还寒,又要冷上几日了。诗中游子春衫,自然是男性着装了。
南宋词人周紫芝《青玉案·梅花落尽人谁管》云:
梅花落尽人谁管。暗凄断、伤春眼。雪后平芜春尚浅。一簪华发,满襟离恨,羞作东风伴。斗花小斛兰芽短。犹是当时旧庭院。拟把新愁凭酒遣。春衫重看,酒痕犹在,忍放金杯满。
词中“春衫重看,酒痕犹在”,是“再看春衫,酒痕还在”之意,这春衫便是词人着装,即是男性着装。
南宋光宗状元、豪放派词人陈亮《南歌子·池草抽新碧》云:
池草抽新碧,山桃褪小红。寻春闲过小园东。春在乱花深处、鸟声中。游镫归敲月,春衫醉舞风。谁家三弄学元戎。吹起闲愁,容易上眉峰。
在这池草新绿,山桃褪红,鸟语花香,充满生机的春天,我骑马踏春,过小园一路向东,闲游野饮,不觉日没,方醉醺醺脚敲马镫响,踏月乘马归,身上的春衫随风飘舞。不知谁家学桓伊将军为王子猷奏笛三曲,吹起我闲愁在心,又上眉头。
词中“游镫归敲月,春衫醉舞风”,形象地描述了作者“脚敲马镫响,踏月乘马归,野饮醉正浓,春衫随风飘”的踏春回归情景。其中“春衫”自然是男性着装了。
南宋江湖派著名词人戴复古《木兰花慢》云:
莺啼啼不尽,任燕语、语难通。这一点闲愁,十年不断,恼乱春风。重来故人不见,但依然、杨柳小楼东。记得同题粉壁,而今壁破无踪。兰皋新涨绿溶溶。流恨落花红。念著破春衫,当时送别,灯下裁缝。相思谩然自苦,算云烟、过眼总成空。落日楚天无际,凭栏目送飞鸿。
要真正理解这首词的含义,还需要从“灯下裁缝”戴复古春衫的女主人翁谈起。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载:“戴石屏先生复古未遇时,流寓江右武宁,有富家翁爱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归计,妻问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释。尽以奁具赠夫,仍饯以词云(《祝英台近》)。夫既别,遂赴水死。可谓贤烈也矣!”
戴复古武宁妻的诀别词《祝英台近》云:
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如何诉。便教缘尽今生,此身已轻许。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
这位善良、宽容、坚贞、刚烈的女词人,在词中已透露以情赴死的决心,但戴复古还是走了。十年之后,戴复古来到亡妻的坟前,满怀歉疚地写下了这首《木兰花慢·莺啼啼不尽》词。
春日里,处处莺啼燕语,也道不尽我伤心事,更何况人鸟语不通。十年愁绪,四季不断,逢春格外撩乱。重来故地,还是这杨柳依依,小楼东畔,可是早已物是人非,不见故人。还记得,那时夫妻双双,粉壁题诗,可如今,只剩下这颓垣破壁,题诗早无踪影。草湾春水新涨,绿波荡漾,流不尽的落花残红,也带不走心中的旧恨新愁。想起临别前夕,妻子忍泪灯下连夜为我缝制充满情爱的春衫,如今,这春衫已经破旧了。相思只是徒然的内疚。想那夫妻恩爱的岁月,犹如过眼烟云,终是空空一场。凭栏远眺,落日苍茫,楚天无际,目送飞鸿,愁苦无极。词中念及被戴复古穿破了的春衫,是武宁戴妻“当时送别,灯下裁缝”的。这春衫,自然是戴复古穿的男性着装。
南宋词人史达祖《夜行船·正月十八日闻卖杏花有感》云:
不剪春衫愁意态。过收灯、有些寒在。小雨空帘,无人深巷,已早杏花先卖。白发潘郎宽沈带。怕看山、忆它眉黛。草色拖裙,烟光惹鬓,常记故园挑菜。
收灯已过,初春轻寒,伊人去了,意趣寥落,未剪春衫。帘外细雨,深巷无人,忽传叫卖杏花的声音,勾起无名的怅惘。鬓发斑白如潘岳,体瘦带宽似沈约。怕外出看山,想起伊人的眉黛,常记故园挑菜日,伊人绿如芳草的拖裙,透烟春光浴染的鬓发。
这首词起首便是“不剪春衫愁意态”,为什么“不剪春衫”?因为“愁意态”,因为伊人去了,史达祖意绪寥落,无心探春;因为伊人去了,无人为史达祖剪春衫。这里所指的春衫,自然是男性着装了。
史达祖还有一词《解佩令·人行花坞》云:
人行花坞,衣沾香雾。有新词、逢春分付。屡欲传情,奈燕子、不曾飞去。倚珠帘、咏郎秀句。相思一度,秾愁一度。最难忘、遮灯私语。淡月梨花,借梦来、花边廊庑。指春衫、泪曾溅处。
玉人轻灵地在四面挡风的苗圃花丛中穿行,身上沾满花香。每逢春暖花开,情郎总作新词,吩咐吟唱。多少次玉人欲托燕子为传情愫,无奈那燕子未曾飞去。玉人只有倚着珠帘,吟咏那旧日佳句。
每相思一次,便增添一分愁绪。最难忘记,当年与玉人,遮着灯光,幽会低语。淡淡春月,光洒梨花,小庭深院,如雪弥漫,这便是当初幽会处。如今天涯间阻,只有借夜来魂梦,重绕花旁回廊,寻见思念的玉人,把自己春衫上滴的相思泪痕,指给她看。
这首词先述对方,推想玉人思念的情态;后写自己,深化相思之情。但二人终不得相聚,只能拟以梦中,情郎指着春衫上的泪痕,表白自己的相思之苦。这春衫自然是男性着装。
南宋吴文英《三姝媚·过都城旧居有感》云:
湖山经醉惯。渍春衫、啼痕酒痕无限。又客长安,叹断襟零袂,涴尘谁浣?紫曲门荒,沿败井、风摇青蔓。对语东邻,犹是曾巢,谢堂双燕。春梦人间须断。但怪得当年,梦缘能短!绣屋秦筝,傍海棠偏爱,夜深开宴。舞歇歌沉,花未减、红颜先变。伫久河桥欲去,斜阳泪满。
湖山看着我醉醺醺的样子,已经习以为常了。啼迹酒痕渍遍了我身上的春衫。我再次客居临安,哀叹残破污浊的着装,无人缝补洗涮。门庭荒芜,井垣颓败,蔓草披离,在风中摇曳。对语旧居东邻的双燕,曾巢当年华屋。春梦是美好的,中断是必然的。独不解与爱姬的缘分,竟会如此短暂。那时绣屋筝声阵阵,依傍着娇艳的海棠花缠绵缱绻,夜深了,酒宴才开,轻歌曼舞,更增添了欢乐的氛围。如今舞歇歌息,花艳依然,而似花的人儿,早已不在。在夕阳的余辉里,我久久伫立河桥;要走了,眼中满含着辛酸的泪水,依依不舍地告别旧居。
吴文英一生不第,游幕终身,于苏、杭、越三州居留较久。在杭州居住时曾纳一妾,能歌善舞,相爱甚深,不幸别后去世。这首词为重过旧居时的悼亡之作。起句悲欢离合,酒痕啼痕,渍遍词人身上的春衫。这春衫自然也是男性着装。
宋末词人刘辰翁《摸鱼儿·酒边留同年徐云屋》云:
怎知他、春归何处,相逢且尽尊酒。少年袅袅天涯恨,长结西湖烟柳。休回首。但细雨断桥,憔悴人归后。东风似旧。问前度桃花,刘郎能记,花复认郎否。君且住,草草留君翦韭。前宵正恁时候。深杯欲共歌声滑,翻湿春衫半袖。空眉皱。看白发尊前,已似人人有。临分把手。叹一笑论文,清狂顾曲,此会几时又。
如何知道,那生机勃勃的春天归向何处?今朝相逢,只管尽饮杯中酒。你我少年初识,垂老邂逅,天涯漂泊,悠悠恨怨,总逢这西湖烟柳。不堪回首,旧地重游,不要再看那迷朦的烟柳,但见断桥,细雨迷朦,重归此处,人已憔悴。东风依然如旧。我问桃花,你前度容颜,刘郎犹记在心,而你还能认出,眼前苍老者,就是当年少年的刘郎吗?请君且稍住,我简单准备些家常饭菜款待你。前宵宴时,你我豪饮放歌,打翻酒杯,弄湿了春衫半截袖。对酒相视,均生华发,年华不再,徒生感慨。临别握手,可叹往日谈笑间评点文章,清狂地鉴赏乐曲。此等聚会,不知何时还会再有!
这首词,系惜别之作。当年与徐云屋同榜题名,多少壮志豪情。而今相逢,饱经忧患,情何以堪。于是起句,不管春归,但只饮酒。以致酒湿春衫半袖。此处春衫,自是男性着装。
宋末咸淳元年进士黄公绍《青玉案·年年社日停针线》云:
年年社日停针线。怎忍见、双飞燕。今日江城春已半。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畔。 春衫著破谁针线。点点行行泪痕满。落日解鞍芳草岸。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
年年春社之日,妇女们停了针线。怎忍心去看那成双成对的飞燕?江城春日已过大半,我仍羁身乱山,孑然桥畔。春衫穿破了谁为缝补?那上面点点行行,浸满泪痕。夕阳西下,我解鞍驻马芳草河岸。虽有鲜花,无人佩戴;以酒浇愁,无人陪劝;纵使醉了,也无人照管。
这首词写游子羁身乱山,驻马河畔,春衫穿破,飘零无期的思乡情怀。词中春衫是男性着装。
宋无名氏《闺怨》云:
有约示归蚕结局,小轩空度牡丹春。夜来拣尽鸳鸯茧,留织春衫寄远人。
这位闺中女子,连夜“拣尽鸳鸯茧”,目的是织成春衫,寄给远方的情人。这春衫自然也是男性着装了。
(二)在宋词中也有用春衫直接指代男主人公的
唐代诗人钱起《故王维右丞堂前芍药花开凄然感怀》云:
芍药花开出旧栏,春衫掩泪再来看。主人不在花常在,更胜青松守岁寒。
诗谓王维病逝后,住在蓝田山庄的生前好友钱起,念念不忘,来到王维故居,面对庭前芍药,凄然泪下。感念王维,人虽故去,但旧栏芍药,依然开放。赞叹芍药旺盛的生命力,胜过耐寒的青松。这里,春衫一词直接指代男性诗人钱起自己。
宋代词人邓肃《浣溪沙·宿雨潜回海宇春》云:
宿雨潜回海宇春。晓风徐散日边云。熙熙人意一番新。破睡海棠能媚客,舞风垂柳似招人。春衫归去马蹄轻。
词谓春雨初晴,经夜的雨水潜合汇聚,回旋迤逦流向宇内。晨风徐徐,吹散日边浮云。人们祥和欢快,感受大自然一片清新气象。醒来的海棠格外艳丽,向过往的人们竭尽献媚之能事。和风舞动着垂柳,宛如在向行人招手。我穿着春衫,骑着骏马,一路轻快地回归家园。
此词“春衫归去马蹄轻”句中的“春衫”,即代指男性词人邓肃。
南宋辛弃疾,于淳熙十五年(1188)作《水调歌头·送郑厚卿赴衡州》云:
寒食不小住,千骑拥春衫。衡阳石鼓城下,记我旧停骖。襟似潇湘桂岭,带似洞庭春草,紫盖屹东南。文字起骚雅,刀剑化耕蚕。看使君,於此事,定不凡。奋髯抵几堂上,尊俎自高谈。莫信君门万里,但使民歌五袴,归诏凤凰衔。君去我谁饮,明月影成三。
词谓友人寒食节也未能住下,千骑簇拥着身着春衫的郑厚卿,匆匆赶赴衡州上任。石鼓山畔,衡阳城下,我曾停过马。以潇湘桂岭为衣襟,以洞庭春草为衣带,衡山七十二峰中最秀丽、最高大的一座名紫盖的山峰雄屹东南,形成交互回环、俊奇险要之势。希友人到任后能振兴文化,发展经济,整顿吏治,富国益民,从而赢得百姓的歌颂和朝廷的重视。叹友人一去,我与谁饮,唯有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淳熙十五年(1188)春,时稼轩闲居带湖。友人郑厚卿赴衡州任过带湖拜别稼轩,此为稼轩送别郑厚卿之作。开头点题,留人不住。结拍惜别,饮邀明月。中间铺述衡阳山川形胜,友人非凡才干和对友人的美好祝愿,旨在冀希友人注重教化,关心农桑,严于吏治,政绩卓著。体现词人忧国怀民的思想感情。词中春衫,即指代辛弃疾所送衡州太守郑厚卿。
宋末词人张炎《声声慢·烟堤小舫》云:
烟堤小舫,雨屋深灯,春衫惯染京尘。舞柳歌桃,心事暗恼东邻。浑疑夜窗梦蝶,到如今、犹宿花阴。待唤起,甚江蓠摇落,化作秋声。回首曲终人远,黯消魂、忍看朵朵芳云。润墨空题,惆怅醉魄难醒。独怜水楼赋笔,有斜阳、不怕登临。愁未了,听残莺、啼过柳阴。
烟雨迷朦的堤边小船、夜雨淅沥的深院灯下,你尤其习惯客居于临安京城。你风流倜傥,倾倒多少窈窕舞女。疑心迷朦夜色,你梦魂所化的蝴蝶,直到如今还栖宿在窗前的花草丛中。我呼唤,想把你唤起,却只见红藻纷纷凋落,化作萧瑟秋声。你词篇遗笔声情佳美,终因你逝去而不忍续读,读之则不胜愁苦。我下笔题词,惆怅不已,神情沉醉,难以清醒。因有你西湖水楼赋笔,而怕在斜阳西照中登临。哀愁未了,柳阴中传来黄莺孤零的啼叫声。
张炎这首词是为凭吊南宋著名词人吴文英而作。词中“春衫惯染京尘”句,表示习惯客居于京城临安。句中“春衫”,便指代词作男主人翁吴文英。
(三)“春衫”作为青年男子穿的衣衫,在唐宋诗词中多有表述
唐代诗人张籍《舞曲歌辞·白纻歌》云:
皎皎白纻白且鲜,将作春衫称少年。裁缝长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复恐兰膏污纤指,常遣傍人收堕珥。衣裳著时寒食下,还把玉鞭鞭白马。
诗谓少妇要用白纻麻织的布料,为年少的夫君裁制春衫,白纻布洁白而光鮮,夫君很高兴。可是裁制时少妇长短尺寸拿不准,迟迟不敢动手,掂着剪刀和尺子向婆婆请教。又怕沃发的香油弄脏了纤纤手指,沾染了白纻布面。于是遣人,代为掇拾不慎落于白纻布面上的珥珰。称心如意的白纻春衫裁制成功,正当寒食時节。年少的夫君,穿上新做的白纻春衫,手持玉鞭,骑上白马,英姿飒爽,十分得意。这首诗描写少妇裁制春衫的慎重,表达了少妇对年少夫君的恩愛之情。这春衫便是青年男子穿的衣衫。
南宋词人吴文英《恋绣衾·频摩书眼怯细文》云:
频摩书眼怯细文。小窗阴、天气似昏。兽炉暖、慵添困,带茶烟、微润宝薰。少年娇马西风冷,旧春衫、犹涴酒痕。梦不到、梨花路,断长桥、无限暮云。
词云,我这个老头子年老体衰,两眼昏花,看书一久,就需要时时揉眼,更怕那些细小的文字;碰上阴天,犹如黄昏,读书更加不易。兽炉暖热,炖着茶壶,散发着湿润的茶味和麝薰烟香,时有困倦之感。回忆年轻时候,纵马迎风不畏寒冷。翻检旧日春衫,还残留着当年纵酒豪饮时留下的酒痕呢。如今做梦也到不了那时的梨花路,也断绝了长桥上,共赏美好晚景的雅兴。
词中“少年娇马西风冷,旧春衫、犹涴酒痕。梦不到、梨花路”所云春衫,即为青年男子穿的衣衫。
(四)在宋词中“春衫”也有作为女性着装的,但为数极少
遍寻唐宋诗词,以“春衫”作为女性着装的只找到两首。
其一,南宋中期词人严仁《醉桃源·春景》云:
拍堤春水蘸垂杨,水流花片香。弄花噆柳小鸳鸯,一双随一双。帘半卷,露新妆,春衫是柳黄。倚阑看处背斜阳,风流暗断肠。
湖水拍打着堤岸,杨柳垂拂着水面。花瓣随波荡漾,散发着阵阵幽香。一对对鸳鸯,在水面上追啄着花瓣,咬弄着柳梢。小楼珠帘卷处,露出淑女新妆,春衫的颜色是新柳的嫩黄。她背着斜阳,凭阑凝望,纵目观赏着眼前的春光。她那明丽、雅洁的装束,娇艳、端庄的仪态,隐藏着春怨和忧伤。这里的春衫是淑女的新妆。
其二,宋末元初词人陈允平《瑞鹤仙》云:
燕归帘半卷。正漏约琼签,笙调玉琯。蛾眉画来浅,甚春衫懒试,夜灯慵剪。香温梦暖。诉芳心、芭蕉未展。渺双波、望极江空,二十四桥凭遍。葱蒨,银屏彩凤,雾帐金蝉,旧家坊院。烟花弄晚。芳草恨,断魂远。对东风无语,绿阴深处,时见飞红数片。算多情、尚有黄鹂,向人睍睆。
燕子归来,穿过半卷的门帘,漏壶中标示时刻的竹签,显示临近傍晚,笙竹玉管,乐声依旧。心情不好,娥眉画得浅淡,再好的春衫也懒得试穿,灯心凝结,也无心修剪。梦中相见,香甜温暖,傾诉别后思念,却见芭蕉叶卷。渺茫之中,我望眼欲穿,江河无际,碧空高远,二十四桥踏遍,踪迹不见。青翠的屏风,彩凤翩翩,香雾纱帐,佳人独眠。故宅旧家,乐坊歌院。烟花渲染着夜晚,连芳草都深含着恨怨,恨这令我断魂的人儿,远不可及。面对东风我缄默无语,绿阴间时有落花数片,令人相怜。算来多情者,犹有黄鹂,它向人们鸣叫着,声音清脆圆润。
这首春闺怨词,塑造了春闺怨妇的形象,表达了其心理与实际活动。其“蛾眉画来浅,甚春衫懒试,夜灯慵剪”中的“春衫”即是指怨妇的未试新衣衫。
(五)“春衫”作为男性着装的说法,是唐宋诗词约定俗成的用词习惯
在有限的资料中,搜寻的上述29首唐宋诗词,其春衫的表述,有2首作为青年男子穿的单衫,占6.9%;有4首作为直接指代男主人翁的,占13.8%;有21首用来表示男性着装的,占72.4%;此3项共27首唐宋诗词,其春衫的表述,实际上都是指男性着装,占93.1%。只有2首作为女性着装,仅占6.9%;而且这2首词作,又都是南宋中晚期作品。春衫作为男性着装的说法,应该是唐宋诗人或词人,约定俗成的用词习惯,尤其是唐、北宋以及南宋前期,几乎成为男性着装的专用词语;直到南宋中晚期,才有极少数作为女性着装的说法,这种说法,应该是男性着装说法的后期演化用法。
这里不厌其烦地搜举这么多例子,虽不能因此断言春衫只能是男性着装,但从93.1%与6.9%这个比例看,在唐宋诗词中,春衫作为男性着装的可能性,远大于女性着装。从这个角度看,《生查子·元夕》中的“春衫”,系男性着装的可能性远大于女性着装,或者说《生查子·元夕》词系男性作者的可能性远大于女性作者。也就是说《生查子·元夕》词的作者是欧阳修的可能性远大于朱淑真。
二、宋代诗词中常用“红袖”来指代女性
宋代诗词中,尤其爱用红色作为修饰语,来描写女性衣袖,并且常用“红袖”指代女性。比如,北宋欧阳修《圣无忧》“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好酒能消光景,春风不染髭须。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中的“红袖莫来扶”,《答通判吕太博〈皇祐元年〉》“千顷芙蕖盖水平,扬州太守旧多情。画盆围处花光合,红袖传来酒令行。舞踏落晖留醉客,歌迟檀板换新声。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后无人看落英”中的“红袖传来酒令行”,《送沈学士康知常州〈嘉祐二年〉》“旧馆芸香锁寂寥,斋舲东下入秋涛。江晴风暖旌旗飏,木落霜清鼓角高。吟就彩笺宾已醉,舞翻红袖饮方豪。平生粗得为州乐,因羡君行首重搔”中的“舞翻红袖饮方豪”,《玉楼春》“去时梅萼初凝粉,不觉小桃风力损。梨花最晚又凋零,何事归期无定准?阑干倚遍重来凭,泪粉偷将红袖印。蜘蛛喜鹊误人多,似此无凭安足信”中的“泪粉偷将红袖印”;张先《天仙子(别渝州·仙吕调)》“醉笑相逢能几度,为报江头春且住。主人今日是行人,红袖舞,清歌女,凭仗东风教点取。三月柳枝柔似缕,落絮尽飞还恋树。有情宁不忆西园,莺解语,花无数,应讶使君何处去”中的“红袖舞”,苏轼《南歌子》“云鬓裁新绿,霞衣曳晓红。待歌凝立翠筵中,一朵彩云何事下巫峰。趁拍鸾飞镜,回身燕漾空。莫翻红袖过帘栊,怕被杨花勾引嫁东风”中的“莫翻红袖过帘栊”,黄庭坚《南乡子(重阳日寄怀永康彭道微使君,用坡旧韵)》“卧稻雨余收。处处游人簇远洲。白发又扶红袖醉,戎州。乱折黄花插满头。青眼想风流。画出西楼一帧秋。还把去年欢意舞,梁州。寒雁西来特地愁”中的“白发又扶红袖醉”,秦观《木兰花》“秋容老尽芙蓉院。草上霜花匀似翦。西楼促坐酒杯深,风压绣帘香不卷。玉纤慵整银筝雁。红袖时笼金鸭暖。岁华一任委西风,独有春红留醉脸”中的“红袖时笼金鸭暖”等,就是用女性特征极强的红色作为修饰语,来描写女性衣袖的。“红袖”常被用来指代女性。
三、春衫纵马,红袖相招
在前面两节里,分别论述了唐宋诗词中用春衫和红袖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指代或表述,这是春衫和红袖分别存在于不同诗词中的情形。还有一种情形是,春衫和红袖同时存在于同一首诗词或同一作者的诗词中,春衫和红袖对于男女两性的指代或表述则更为明显。比如:
宋代词人贺铸的两首《如梦令》云:
白纻春衫新制。准拟采兰修禊。遮日走京尘,何啻分阴如岁。留滞。留滞。不似行云难系。
彩舫解维官柳。楼上谁家红袖。团扇弄微风,如为行人招手。回首。回首。云断武陵溪口。
前首写词人以遮日走尘、分阴如岁的急切心情,穿上用白纻布新裁制的春衫,赶赴三月三除邪祈福的集会。这位耸目长身、铁青面色的青年人所穿的春衫,自然是青年男性着装了。
后首描写船家解开系在岸柳上的缆索,彩船徐徐离岸时,词人看那岸边楼上,轻摇团扇,好像在向行人招手的谁家红袖。此系用红袖直接指代女子。
昭宗乾宁元年(894)进士、五代前蜀宰相韦庄《菩萨蛮》(《花间集》)云: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如今才想起江南之乐,那时正值春衫少年,倚桥立马,凭水临风,英武潇洒;满楼红袖,殷勤盛意,妩媚相招。于是便有了翡翠画屏,曲折回护,醉宿花丛,闺房幽处。如果再有江南此遇,我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韦庄〈菩萨蛮〉》里概括云:“春衫纵马,红袖相招,花丛醉宿,翠屏相映,皆江南乐事也,而红袖之盛意殷勤,尤可恋可感。”[1]14-15很明显,这“红袖”指代年轻女子,“春衫”则系指青年男子。可见,《生查子·元夕》词里,“泪满春衫袖”的是“春衫”而非“红袖”。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查子·元夕》词,并非如季工《关于女诗人朱淑真的诗词》所云:“寥寥四十字,很细致地刻画出封建时代的一个少女,怎样约她的情人在元夜幽会。”[2]并非如胡云翼选注《唐宋词一百首·〈生查子·元夕〉》“说明”云:“写的是一个女子不顾封建礼教的约束,追求自由结合的爱情生活。”[3]并非如郑孟彤《唐宋诗词赏析〈生查子·元夕〉》所云:“这首词,写的是一个女子强烈追求自由结合的爱情生活,具有一定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意义。词的主题是通过这一女子对去年和今年元夜的景象是一样而她的感受已不同来表现的。”[4]并非如贺新辉、张厚余主编《宋词精品鉴赏辞典。〈生查子·元夕〉》所云:“这首词,写一个女子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结合的爱情生活。”[5]并非如《唐宋八大家大全集》编委会编《唐宋八大家大全集·欧阳修〈生查子〉》所云:“本词通过女主人公对去年元夕往事的回忆,抒发了物是人非之感概。”[6]也并非如诸葛忆兵、陶尔夫《北宋词史》所云:“《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词以少女口吻写成。”[7]
杨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图志·欧阳修开拓的文学大家气象》里,评论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云:“此词曾被宋明词集、词话误认为李清照或朱淑真的作品,可见它是不乏婉约倩妙的女儿腔的。”[8]“婉约倩妙的女儿腔”,未必就是女儿作。把“女儿腔”与“女儿作”划等号,这也许是《生查子·元夕》作者女性说的一个因素吧。还是用唐圭璋“春衫纵马,红袖相招”来概括最为精当,这“纵马”的“春衫”在《生查子·元夕》词里,只能由欧阳修来充当了。换句话说,“泪满春衫袖”的只能是“春衫”欧阳修,而非“红袖”朱淑真。
[1]唐圭璋.唐宋词简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季工.关于女诗人朱淑真的诗词[J].学术月刊,1963(3).
[3]唐宋词一百首[M].胡云翼,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4.
[4]郑孟彤.唐宋诗词赏析[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261-262.
[5]宋词精品鉴赏辞典[M].贺新辉,张厚余,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88.
[6]《唐宋八大家大全集》编委会.唐宋八大家大全集[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195.
[7]陶尔夫,诸葛忆兵.北宋词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42.
[8]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02.
10.14096/j.cnki.cn34-1044/c.2020.01.15
I207
A
1004-4310(2020)01-0085-10
2019-05-28
肖汉泽,男,安徽阜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阜阳市历史文化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宋代文化及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