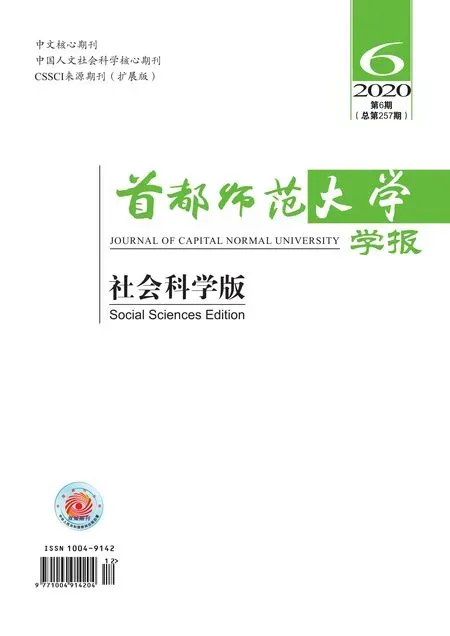《闲情偶寄·种植部》:中国古代自然审美的典范文本
薛富兴
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是一部妙书。20世纪后期以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其表现出极大关注。它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戏曲创作和表演理论的总结性著作得到尊崇,又以“生活美学”经典的名义受到更为热烈的追捧,因为它于传统的精英艺术——诗文、书画之外别开新径,在日常生活语境——吃、喝、玩、乐中表达作者的审美情趣,给当代美学理论带来新的启示,其于数百年后再次成为畅销书,良有以也。
《闲情偶寄·种植部》(以下简称《种植部》)是作者介绍其多年栽种与鉴赏诸多花草树木独到心得的一章,多被理解为李渔“园林艺术”或“生活美学”中的一部分。然而笔者以为:这一专章诚然不属于常规的艺术理论,将它理解为李渔的“生活美学”,即其日常生活审美情趣的一部分,虽然颇合作者本心(“不视为苦,则乐在其中。督率家人灌溉,而以身任微勤,节其劳逸,亦颐养性情之一助也。”①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颐养部·浇灌竹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对《种植部》专题性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王捷的《〈闲情偶寄·种植部〉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但作者主要将它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对待,讨论其审美理想、文化人格与艺术特色;黄雅利《李渔自然审美观中的物我关系——以〈闲情偶寄·芙蕖〉为论》亦主要将《种植部》理解为一种散文集,因而对作者“以物衬人”“以物写人”的文学手法给予积极的评价,见《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却会无意中遮蔽其独特的学术价值。《种植部》在某种意义上可完全独立,就像其戏曲理论之外的其他部分确实可独立成章一样。笔者在此特将此章单独拎出,将它理解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文本,理解为一部以自然审美,具体地以栽培植物之审美欣赏为主题的专著,一个关于中国古代自然审美经验的总结性典范文本,以之考察李渔在栽培植物的自然审美欣赏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及其局限,似亦别有意趣。①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颐养部·浇灌竹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对《种植部》专题性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王捷的《〈闲情偶寄·种植部〉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但作者主要将它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对待,讨论其审美理想、文化人格与艺术特色;黄雅利《李渔自然审美观中的物我关系——以〈闲情偶寄·芙蕖〉为论》亦主要将《种植部》理解为一种散文集,因而对作者“以物衬人”“以物写人”的文学手法给予积极的评价,见《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一、以物比德:自然审美之主导模式
立足于自然审美这一特殊视野,我们便会发现:李渔的《闲情偶寄·种植部》诚为中国古典自然文学精粹,这里所贡献的诸花草树木栽培与欣赏经验,诚可谓独到、细腻。再加上李渔往往喜欢托物言志,故而几乎每篇都是文情并茂,字字珠玑,自然引人喜爱。那么,李渔到底如何欣赏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之美?请看以下数例:
花之最不耐开,一开辄尽者,桂与玉兰是也。花之最能持久,愈开愈盛者,山茶、石榴是也。然石榴之久,犹不及山茶。榴叶经霜即脱,山茶戴雪而荣。则是此花也者,具松柏之骨,挟桃李之姿,历春夏秋冬如一日,殆草木而神仙者乎?又况种类极多,由浅红以至深红,无一不备。其浅也,如粉如脂,如美人之腮,如酒客之面;其深也,如朱如火,如猩猩之血,如鹤顶之朱。可谓极浅深浓淡之致,而无一毫遗憾者矣。得此花一二本,可抵群花数十本。惜乎予园仅同芥子,诸卉种就,不能再纳须弥,仅取盆中小树,植于怪石之旁。噫,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予其郭公也夫!②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山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页。
此乃赏其色。
树直上而无枝者,棕榈是也。予不奇其无枝,奇其无枝而能有叶。植于众芳之中,而下不侵其地,上不蔽其天者,此木是也。③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棕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338页。
此乃观其形。
秋花之香者,莫能如桂。树乃月中之树,香亦天上之香也。但其缺陷处,则在满树齐开,不留余地。予有《惜桂》诗云:“万斛黄金碾作灰,西风一阵总吹来。早知三日都狼藉,何不留将次第开?”盛极必衰,乃盈虚一定之理。凡有富贵荣华一蹴而至者,皆玉兰之为春光,丹桂之为秋色。④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此乃嗅其香。
“人类一切审美活动都从形式美开始,从对各类审美对象外在物理感性表象、声色形式的注意开始,自然审美也不例外。自然之美首先是大自然各类对象、现象所呈现出艳丽、悦耳的声色之美,自然万千对象的声色之美是这个世界对人类的最早审美诱惑。”①薛富兴:《画桥流虹——大学美学多媒体教材》,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前述三者构成李渔观赏植物之美的第一个层次——欣赏自然对象的物相之美,或曰形式美,这也是从古至今社会大众最为熟悉的自然审美模式。然而,这只是李渔自然审美欣赏的起点,若始终如此,其自然审美趣味便未免太单调、肤浅了。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有着丰厚人文知识与趣味修养的知识分子,李渔怎样表现其自然审美应有的深度与文化内涵呢?
冬青一树,有松柏之实而不居其名;有梅竹之风而不矜其节,殆“身隐焉文”之流亚欤?然谈傲霜砺雪之姿者,从未闻一人齿及,是之推不言禄,而禄亦不及。予窃忿之,当易其名为“不求人知树”。②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冬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
此言冬青实有松柏、梅竹之德,并为此而专为其赋予新名,曰“不求人知树”。与上面的仅仅赞赏诸花木之色相与香气相比,李渔在此对植物审美价值与内涵的阐释便有了不一样的深度和文化内涵,它使我们对冬青的审美魅力有了更为持久、深刻的印象。此种自然审美欣赏方法与对植物的形式美欣赏一样,乃从古至今最为通行的审美模式,至少对中国人来说如此,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更是如此:在自然审美欣赏中,欣赏者总是倾向于在所欣赏的自然对象的外在表象或内在特性与人类社会中的某种现象或价值观念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并会有意无意地将后者赋予所欣赏的自然对象,以之为其自身所固有的内在审美特性与价值,至少是该自然对象具备特定审美特性与价值之必要条件。我们可将此称之为关于自然审美欣赏的“以物比德”模式。
那么,李渔在其《种植部》中到底怎样用“以物比德”模式揭示众多花卉植物的审美特性与价值呢?盖有以下五种。
一曰以人面状物形色:
予之钟爱此花,非痂癖也。其色其香、其茎其叶,无一不异群葩,而予更取其善媚。妇人中之面似桃,腰似柳,丰如牡丹、芍药,而瘦比秋菊、海棠者,在在有之。若如水仙之淡而多姿,不动不摇,而能作态者,吾实未之见也。以“水仙”二字呼之,可谓摹写殆尽。使吾得见命名者,必颓然下拜。③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水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二曰以世情状物态:
菜为至贱之物,又非众花之等伦,乃《草本》《藤本》中反有缺遗,而独取此花殿后,无乃贱群芳而轻花事乎?曰:不然。菜果至贱之物,花亦卑卑不数之花,无如积至贱至卑者而至盈千累万,则贱者贵而卑者尊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者,非民之果贵,民之至多至盛为可贵也。园圃种植之花,自数朵以至数十百朵而止矣,有至盈阡溢亩,令人一望无际者哉?曰:无之。无则当推菜花为盛矣。一气初盈,万花齐发,青畴白壤,悉变黄金,不诚洋洋乎大观也哉?当是时也,呼朋拉友,散步芳塍,香风导酒客寻帘,锦蝶与游人争路。郊畦之乐,什佰园亭,惟菜花之开,是其候也。④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326页。
三曰以美德拟物格:
茂叔以莲为花之君子,予为增一敌国,曰“瑞香乃花之小人”,何也?《谱》载此花一名“麝囊,能损花,宜另植”。予初不信,取而嗅之,果带麝味。麝则未有不损群花者也。同列众芳之中,即有朋侪之义,不能相资相益,而反祟之,非小人而何?幸造物处之得宜,予以不能为患之势。其开也,必于冬春之交,是时群花摇落,诸卉未荣,及见此花者,仅有梅花、水仙二种,又在成功将退之候,当其锋也未久,故罹其毒也亦不深。此造物之善用小人也。使易冬春之交而为春夏之交,则花王亦几被篡,矧下此者乎?①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瑞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关于李渔植物审美中的拟人化倾向,可参见孟东生、贺城、王静静:《〈闲情偶寄·种植部〉中宅园植物审美的人格化品评》(《现代装饰·理论》2016年第5期),作者将此拟人化倾向当作一种积极的文化资源,将它借鉴于当代植物景观设计。
四曰以物态言人情:
秋海棠一种,较春花更媚。春花肖美人,秋花更肖美人。春花肖美人之已嫁者,秋花肖美人之待年者。春花肖美人之绰约可爱者,秋花肖美人之纤弱可怜者。处子之可怜,少妇之可爱,二者不可得兼,必将娶怜而割爱矣。相传秋海棠初无是花,因女子怀人不至,涕泣洒地,遂生此花,名为“断肠花”。噫!同一泪也,洒之林中,即成斑竹;洒之地上,即生海棠。泪之为物神矣哉!②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海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五曰以物为人之具:
茉莉一花,单为助妆而设,其天生以媚妇人者乎?是花皆晓开,此独暮开。暮开者,使人不得把玩,秘之以待晓妆也。是花蒂上皆无孔,此独有孔。有孔者,非此不能受簪,天生以为立脚之地也。若是,则妇人之妆,乃天造地设之事耳。植他树皆为男子,种此花独为妇人。既为妇人,则当眷属视之矣。妻梅者,止一林逋。妻茉莉者,当遍天下而是也。③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茉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页。
最后一种属于目的论式类比,实际上是一种对物我关系之阐释:为什么世上会有此物?必为人所设也。它很精准地符合了人类的某种特殊生命需求,此正该物之美妙处。以上五者正构成李渔《种植部》关于花草树木审美欣赏“以物比德”模式的方法系统。《种植部》共介绍木本24种、藤本9种、草本15种、众卉9种、竹木11种,凡68种,文67则。其中属于“以物比德”者为48则,占全章三分之二强。由此可见,“以物比德”模式乃李渔在《种植部》所应用的自然审美欣赏之主导方式。
李渔《种植部》所展示的自然审美模式,无论是浅层次的形式美模式,还是深层次的以物比德模式,若放在整个中国古代自然审美史上考察,均可谓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审美典范,反映了中国人对待自然的一种典型的审美趣味与眼光。从《诗经》至唐诗宋词,凡咏花言草篇什概不出此例。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将李渔的《种植部》理解为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之总结形态,李渔在此文本中所表达的自然审美经验,其趣味与方法都很传统、“很中国”,可谓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之主导形态。虽然名曰《种植部》,花草树木在此文本中是理所当然的主角,然而奇怪的是,李渔在介绍与描述它们时,总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冲动,总想将人事、人情与人理带入其中。于是,一部《种植部》同时也成了李渔表达其人生情感、阅历与智慧的绝妙场域。我们不禁要问:《种植部》到底是一部种树书,还是一本李渔托物以言情说理的花木散文集?立足于前者,我们可将《种植部》理解为一部中国古代优秀的林学著作、一部栽培植物志;立足于后者,我们又可将它理解为一部杰出的自然文学作品。这部著作到底跑题了没有?然然,否否。立足于作为科学著作的林学眼光,我们有理由相信李渔在本著中大规模地以物比德不仅不必要,甚至有害,因为它倡导一种对待诸树木花草的主观、非科学的趣味与眼光。然而,若立足于伟大的抒情言志文学传统,一部不跑题的纯林学著作对李渔而言很可能未能尽兴,对已然习惯于“万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文学读者们来说,则很可能显得索然无味。于是,《种植部》是一个极复杂的文本,其中隐然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科学与文学两种视野之间的张力。即使我们将《种植部》当作一个关于中国古代自然审美的典范文本,这里所呈现的自然审美经验也不纯粹,它所揭示的并非一种纯自然审美经验,而是一种非典型的、兼及人文与自然的综合性自然审美经验,一种高度人化或人文化了的自然审美经验。
二、香国平章:深识物性之美
将李渔的《种植部》理解为关于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之典范文本,因为它在形式美与以物比德两个层面均体现了中国古代自然审美的主导形态,很传统、“很中国”。然而这并非《种植部》之全部信息。《种植部》之珍贵,还在于它同时包含了几乎与上文所言者截然相反的另类信息,因而它又很前卫、很超越。
木香花密而香浓,此其稍胜蔷薇者也。然结屏单靠此种,未免冷落,势必依傍蔷薇。蔷薇宜架,木香宜棚者,以蔷薇条干之所及,不及木香之远也。木香作屋,蔷薇作垣,二者各尽其长,主人亦均收其利矣。①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木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310页。
杜鹃、樱桃二种,花之可有可无者也。所重于樱桃者,在实不在花;所重于杜鹃者,在西蜀之异种,不在四方之恒种。如名花俱备,则二种开时,尽有快心而夺目者,欲览余芳,亦愁少暇。②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杜鹃、樱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以上两条代表了李渔《种植部》的又一面,它是另外一种叙述方式或审美视野,即很克制地描述自然对象,仅呈现其自身所具有的特定外在表象或内在特性,而不及于人世人情。如此者在《种植部》中凡17则,涉及植物18种,居其整体四分之一。这一模式虽在《种植部》中并非主流,然极为珍贵。它代表了李渔描述或欣赏自然的另一种模式:客观地对待自然对象,满足于欣赏自然对象自身所具有之审美特性与价值,我们可称之为静观模式或客观模式。又比如,他虽然与大多数同胞一样喜欢以物比德,然而又主张独立地欣赏自然对象自身之美,认为天籁之美胜于人籁:
鸟声之可听者,以其异于人声也。鸟声异于人声之可听者,以出于人者为人籁,出于鸟者为天籁也。使我欲听人言,则盈耳皆是,何必假口笼中?③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颐养部·蓄养禽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常有奇花过目而莫之睹,鸣禽悦耳而莫之闻者,至其捐资所购之姬妾,色不及花之万一,声仅窃鸟之绪余,然而睹貌即惊,闻歌辄喜,为其貌似花而声似鸟也。噫!贵似贱真,与叶公之好龙何异?④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颐养部·看花听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若立足于当代环境美学理念,正确或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应当仅指那种能客观地对待自然对象,仅关注其自身所固有者,且能自觉地排除那些对所欣赏的自然对象进行的有意无意的主观价值赋予或附会。如何才能内在或有深度地欣赏自然,不主观地濡染或附会自然,不以欣赏者主观文化价值与趣味替换所欣赏自然对象自身所具有之表象与特性呢?关于如何客观而又有深度、完善地欣赏自然,笔者曾在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所提出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scientific cognitive theory)基础上,提出一个自然美特性系统,认为理想的自然审美欣赏应当能同时涉及物相、物性、物功与物史四个方面。①关于自然美特性系统,参见薛富兴:《自然美特性系统》,《美育学刊》2012年第1期。我们欣喜地发现:李渔的《种植部》其实也隐含着一个较为完善的自然审美欣赏系统,除了上面所论及的形式美模式(其主题是欣赏自然对象的“物相”之美,完善自然审美之第一个层次)与以物比德模式,它同时也涉及客观且有深度地欣赏自然之另外三个要素——物性、物功与物史。于是,《种植部》便具有了另一副面孔——预言性或超越性,因为它客观上符合了当代环境美学关于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的核心理念——客观而又有深度地欣赏自然对象自身所具有的审美特性与价值。下面就此简述之。李渔自视甚高,自命为“香国平章”,即花木知音:
予则不然,每值花柳争妍之日,飞鸣斗巧之时,必致谢洪钧,归功造物,无饮不奠,有食必陈,若善士信妪之佞佛者。夜则后花而眠,朝则先鸟而起,惟恐一声一色之偶遗也。及至莺老花残,辄怏怏如有所失。是我之一生,可谓不负花鸟,而花鸟得予,亦所称“一人知己,死可无恨”者乎!②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颐养部·看花听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在他写作与刊印其《种植部》之前,已有明代王象晋编纂的《群芳谱》行世。李渔对以之为代表的众花谱虽有所称引,然而往往对其中存在的诸多谬误表示不满。他宣称《种植部》不屑于重复关于花草树木栽培的已有常识,这部著作所描述与讨论的都是他自家体贴出来的独到见解。比如,他对许多已存的植物名称有意见,认为它们没有道理。于是,给他喜欢的众多植物重新命名便成为李渔的一种独特爱好,其甚为自得:
夹竹桃一种,花则可取,而命名不善,以竹乃有道之士,桃则佳丽之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合而一之,殊觉矛盾。请易其名为“生花竹”,去一桃字,便觉相安。且松、竹、梅素称三友,松有花,梅有花,惟竹无花,可称缺典,得此补之,岂不天然凑合?亦女娲氏之五色石也。③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夹竹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5-306页。
其他如李渔建议改“鸡冠花”为“一朵云”等,④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鸡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321页。均涉及一个严肃问题:如何恰当地给植物命名?其时,发明“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e,1705—1778)尚未诞生,李渔已提出一条给植物命名的正确原则:命名当或肖其形色,或深察物性,不能随意附会,名不符实。李渔对主观随意地为植物命名现象的反思,正是我们深入理解《种植部》最珍贵信息的一个极好窗口。李渔并非一般的植物爱好者,乃花草树木之痴迷者,自言以花为命:
水仙一花,予之命也。予有四命,各司一时。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秋海棠为命,冬以蜡梅为命。无此四花,是无命也。一季缺予一花,是夺予一季之命也。水仙以秣陵为最,予之家于秣陵,非家秣陵,家于水仙之乡也。记丙午之春,先以度岁无资,衣囊质尽。迨水仙开时,则为强弩之末,索一钱不得矣。欲购无资,家人曰:“请已之,一年不看此花,亦非怪事。”予曰:“汝欲夺吾命乎?宁短一岁之寿,勿减一岁之花!且予自他乡冒雪而归,就水仙也。不看水仙,是何异于不返金陵,仍在他乡卒岁乎?”家人不能止,听予质簪珥购之。⑤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水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实际上,哪怕用“最狂热的花木痴迷者”也并不能准确地描述李渔,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位在科学理性意义上观赏植物的培育与研究者。对于他所喜爱的众多花草树木,李渔下过长期的“格物致知”功夫,有数十年的花木栽培经验:
予播迁四方,所止之地,惟荔枝、龙眼、佛手诸卉,为吴越诸邦不产者,未经种植。其余一切花果竹木,无一不经葺理。①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
正因他是一位资深的植物栽培学家,对各式花草树木的生物习性有细致、深入的了解,所以他才能凭自己专精的植物学知识与经验,校正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欲艺此花,必求木本。藤本一样着花,但苦经年即死,视其死而莫之救,亦仁人君子所不乐为也。木本最难过冬,予尝历验收藏之法,此花痿于寒者什一,毙于干者什九。人皆畏冻而滴水不浇,是以枯死,此见噎废食之法,有避呕逆而经时绝粒,其人尚存者乎?稍暖微浇,大寒即止,此不易之法。但收藏必于暖处,篾罩必不可无。浇不用水而用冷茶,如斯而已。予艺此花三十年,皆为燥误,如今识此,以告世人,亦其否极泰来之会也。②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茉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页。
关于如何正确地养竹,李渔也提出极为宝贵的独到经验,以纠俗见。③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333页。
菊花者,秋季之牡丹、芍药也。种类之繁衍同,花色之全备同,而性能持久复过之。从来种植之书,是花皆略,而叙牡丹、芍药与菊者独详,人皆谓三种奇葩,可以齐观等视,而予独判为两截,谓有天工人力之分,何也?牡丹、芍药之美,全仗天工,非由人力。植此二花者,不过冬溉以肥,夏浇以湿,如是焉止矣。其开也,烂漫芬芳,未尝以人力不勤,略减其姿而稍俭其色。菊花之美,则全仗人力,微假天工。艺菊之家,当其未入土也,则有治地酿土之劳,既入土也,则有插标记种之事。是萌芽未发之先,已费人力几许矣。迨分秧植定之后,劳瘁万端,复从此始。防燥也,虑湿也,摘头也,掐叶也,芟蕊也,接枝也,捕虫掘蚓以防害也,此皆花事未成之日,竭尽人力以俟天工者也。即花之既开,亦有防雨避霜之患,缚枝系蕊之勤,置盏引水之烦,染色变容之苦,又皆以人力之有余,补天工之不足者也。为此一花,自春徂秋,自朝迄暮,总无一刻之暇。必如是,其为花也,始能丰丽而美观,否则同于婆娑野菊,仅堪点缀疏篱而已。若是,则菊花之美,非天美之,人美之也。人美之而归功于天,使与不费辛勤之牡丹、芍药齐观等视,不几恩怨不分,而公私少辨乎?吾知敛翠凝红而为沙中偶语者,必花神也。自有菊以来,高人逸士无不尽吻揄扬,而予独反其说者,非与渊明作敌国,艺菊之人终岁勤动,而不以胜天之力予之,是但知花好,而昧所从来。饮水忘源,并置汲者于不问,其心安乎?从前题咏诸公,皆若是也,予创是说,为秋花报本,乃深于爱菊,非薄之也。④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325页。
没有对菊花的长期细致观察,没有亲自栽种、呵护菊花的第一手经验,绝难说出如此精准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古代自然审美史上,真诚地热爱自然,具备赏花惜草审美情趣者,在在多有,以生花妙笔为花草树木传神写照,或以花草树木之景言情达意的画作与诗篇实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真正能忠实地贯彻宋儒“格物致知”精神,用心地作细腻、深入地了解自然之功课如李渔者则绝少。李渔之所以难得,就在于他并非一位自然美的旁观者,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地欣赏自然;他也并非最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美爱好者,粗观一花一叶便起托物言志之情,而是一位真正的尊重花木、爱惜花木,并因此而愿亲身陪伴花木的一位痴情者,一位大自然的恋人。他深知“能以草木之生死为生死,始可与言灌园之乐,不则一灌再灌之后,无不畏途视之矣”①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颐养部·浇灌竹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悉心照料群芳们的日常生活,呵护着自己所种植的每一个生命。为它们的饥渴焦虑,为它们的寒暑奔忙,为它们的健康成长而劳作,像一位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能发现每一种花的生长习性,从其当下情形探测其健康状态,明了其所恶所需。于格物和育物二端,或曰通过育物——栽培花木这一实践途径而格物——深度地了解自然,李渔可谓做足了功课,这是历代花鸟画家与借景抒情的诗人们所不可比拟的。到底谁才是大自然的知音?是李渔,而非那些以花鸟写意或抒情的画家与诗人们。
中国古代自然审美欣赏常常会陷入一种矛盾:要么只是肤浅地欣赏自然之外在形色特性,即形式主义地欣赏自然,要么主观地对待自然,人为地赋予自然对象本身并没有的一些人类文化观念,继而描摹、颂扬之,上述“以物比德”模式便是其典型形态。如此模式下的自然审美欣赏虽有深刻、丰富的审美意蕴与文化内涵,然而并不符合自然对象之事实,是一种与自然事实无关的欣赏,自然审美有名而无实。如何才能摆脱上述困境,既深入而又正确地欣赏自然呢?依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②“科学认知主义理论”是当代西方环境美学中极有特色的一种理论,其要义是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重要作用,参见Allen Carlson,“Appreciatio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Journal of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37,1979,pp.267-276.首先,我们必须从哲学立场上确立如此原则:客观地对待自然,欣赏自然对象本身自有之物,而非主观地附会自然,以欣赏自然之名行人类自我欣赏之实;其次,在更为具体的层面,应当将自然欣赏引导到深入地欣赏自然对象诸内在特性与功能上来,此乃超越自然审美欣赏中传统的形式美趣味、客观而又有深度地欣赏自然的唯一合法途径。李渔以数十年亲自栽培植物,对诸树木花草做格物致知功课为基础,能够细腻、深入地欣赏树木花草的内在之美,开拓出此内在之美的三个维度——物性、物功与物史,为中国自然审美开出新局面,将中国古代自然审美推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栀子花无甚奇特,予取其仿佛玉兰。玉兰忌雨,而此不忌;玉兰齐放齐凋,而此则开以次第。惜其树小而不能出檐,如能出檐,即以之权当玉兰,而补三春恨事,谁曰不可?③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此草植之者繁,观之者众,然但知其一,未知其二。予尝细玩而得之。盖此草不特于一岁之中,经秋更媚,即一日之中,亦到晚更媚。总之后胜于前,是其性也。④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老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
于花草树木之美,李渔此处可谓能言人所未能言,他精准地揭示出栀子与老少年两种花卉各自的生物习性——其区别于他者的内在生命特性之美。赏花至此,方可谓解人。某种意义上,《种植部》这部群芳谱为我们展开了满足于托物言志的诗人与画家们难以企及的工笔花鸟画卷,因为它以深察自然对象客观、内在物性为基础,所呈现者乃众花卉自身之美,而非诗人画家们的人文情趣。此乃李渔所揭示众植物深度之美的第一个要素——物性。
花之有利于人,而无一不为我用者,芰荷是也。花之有利于人,而我无一不为所奉者,玫瑰是也。芰荷利人之说,见于本传。玫瑰之利,同于芰荷,而令人可亲可溺,不忍暂离,则又过之。群花止能娱目,此则口眼鼻舌以至肌体毛发,无一不在所奉之中:可囊可食、可嗅可观、可插可戴、是能忠臣其身,而又能媚子其术者也,花之能事,毕于此矣。⑤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玫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312页。
此乃众植物深度之美第二种要素——物功,乃物性之所以然,荷花与玫瑰又一项深度事实——它们全方位地有益于人,“可囊可食、可嗅可观、可插可戴”的功能。当然,此处需作一项补充:李渔在此所揭示的物功,仍属于荷花与玫瑰有益于人类物质利用的“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而非其有益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典范的“物功”概念当指后者,而非前者。
李渔开辟出深度欣赏自然的又一新方向——从植物生活史角度动态地感知与理解物性变迁,探测众花木在一年四季,乃至更长时期内所呈现的生命特性,此之谓“物史”。首先,他为我们推荐了众花卉中极特殊的群体——花期极短者,要我们珍惜其瞬间之灿烂:
木槿朝开而暮落,其为生也良苦,与其易落,何如弗开?造物生此,亦可谓不惮烦矣。有人曰:不然。木槿者,花之现身说法以儆愚蒙者也。花之一日,犹人之百年。人视人之百年,则自觉其久;视花之一日,则谓极少而极暂矣。不知人之视人,犹花之视花,人以百年为久,花岂不以一日为久乎?无一日不落之花,则无百年不死之人可知矣。此人之似花者也,乃花开花落之期虽少而暂,犹有一定不移之数。朝开暮落者,必不幻而为朝开午落,午开暮落。乃人之生死,则无一定不移之数,有不及百年而死者,有不及百年之半与百年之二三而死者,则是花之落也必焉,人之死也忽焉。使人亦如木槿之为生,至暮必落,则生前死后之事,皆可自为政矣,无如其不能也。此人之不能似花者也。人能作如是观,则木槿一花,当与萱草并树。睹萱草则能忘忧,睹木槿则能知戒。①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木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303页。
动态观照的时间维度乃自然审美的又一基础性视野。李渔认为:生命之久暂当各以其类言之。以人为参照,花为短命,故观花常使人起生命苦短之情。然就其自身之生物特性而言,“木槿朝开而暮落”,“花之一日,犹人之百年”。在此意义上,木槿之贵正在其“倏忽”,并非一种遗憾。以人为参照起伤物之情,实乃一种误导,而非正确地欣赏木槿之恰当态度。玉兰之美亦如之。②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玉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页。问题不在于某些植物生命之短暂,而在于人类欣赏者能及时地感知与欣赏其灿烂,此之谓知音。
对于那些生命周期较长,生命画卷从容舒展者,人类欣赏者则需有一种耐心,能始终以一种尊重、崇拜与好奇之心持久地关注之,细察其在长时段内所发生的诸奇妙变化:
梧桐一树,是草木中一部编年史也。举世习焉不察,予特表而出之。花木种自何年,为寿几何岁,询之主人,主人不知。询之花木,花木不答。谓之“忘年交”则可,予以“知时达务”则不可也。梧桐不然,有节可纪,生一年,纪一年,树有树之年,人即纪人之年,树小而人与之小,树大而人随之大,观树即所以观身,《易》曰“观我生进退”,欲观我生,此其资也。③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梧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335页。
“编年史”是一个极精彩的概念,它是一种科学意识,而非文学情怀,它强调的是面对自然对象之客观、冷静、细腻态度,而非借物喻人的人文趣味。它又是一个长时段的时间概念,要求自然审美者有一种从容而又精准地感知和理解自然的文化能力与审美耐心。历史意识乃中国传统文化之重要因素,然而,绝大多数文人、诗人与画家只对人类自身的命运书写感兴趣,对自然界万千物种之成长史则往往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冷漠,虽然绝大多数人自以为热爱自然。在此意义上,李渔在此所提出的“编年史”概念,可谓是一项重要的自然审美意识启蒙,他倡导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趣味——客观、长时段地关注和欣赏自然,以一种科学研究的态度耐心、细腻地感知与探索自然界的深度奥秘。我们可在此对读利奥波德的类似考察:
每种松树都有它自己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为了针叶享用它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提出了一个“办公室任期”。因此,乔松保存它的针叶期限为一年半,多脂松和短叶松为两年半。新添的叶子在6月份进办公室,即将离职的叶子在10月份写告别演说词。所有离职的叶子写的是同一内容,都用黄褐色的墨水,这种墨水到了10月就变成了棕色。①奥多·利奥波德:《沙乡的沉思》,侯文惠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请问:有哪位抒情诗人或写意画家能准确地说出自己所喜欢的花木今年贵庚几何,或者对此类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绝少!某种意义上说,李渔“编年史”概念的提出,对他的绝大多数同胞而言很另类,显得匪夷所思。然而,立足于当代环境美学,我们会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历史的新信息,一种与“以物比德”人文化自然审美传统迥然有别的科学式客观自然审美的路径,一种促进客观、有深度地欣赏自然自身之美的有效途径。
对黄杨的欣赏亦复如斯。②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黄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页。此乃客观、有深度地欣赏自然的第三个层次,曰“物史”。欲赏“物史”之美,需要在自然变迁的维度下细察物性。“物史”角度的引入,将极大地改造我们对特定对象的审美经验,使静态空间感知下常以为“优美”的自然对象转化为“崇高”的对象。物史,即自然生命史的视野在李渔这里得到放大,他将众多空间上分布展开、各不相属的花草树木放在四季变迁的生命史交响乐中,为它们重新理出一种次第展示其生命节律的时间秩序。自此,所有物种似乎都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组成一个自然生命的接力赛:
合一岁所开之花,可作天工一部全稿。梅花、水仙,试笔之文也。其气虽雄,其机尚涩,故花不甚大,而色亦不甚浓。开至桃、李、棠、杏等花,则文心怒发,兴致淋漓,似有不可阻遏之势矣。然其花之大犹未甚,浓犹未至者,以其思路纷驰而不聚,笔机过纵而难收。其势之不可阻遏者,横肆也,非纯熟也。迨牡丹、芍药一开,则文心笔致俱臻化境,收横肆而归纯熟,舒蓄积而罄光华,造物于此,可谓使才务尽,不留丝发之余矣。然自识者观之,不待终篇而知其难继,何也?世岂有开至树不能载、叶不能覆之花,而尚有一物焉高出其上、大出其外者乎?有开至众彩俱齐、一色不漏之花,而尚有一物焉红过于朱、白过于雪者乎?斯时也,使我为造物,则必善刀而藏矣,乃天则未肯告乏也。夏欲试其技,则从而荷之;秋欲试其技,则从而菊之。冬则计穷力竭,尽可不花,而犹作蜡梅一种以塞责之。数卉者,可不谓之芳妍尽致、足殿群芳者乎?然较之春末夏初,则皆强弩之末矣。至于金钱、金盏、剪春罗、剪秋罗、滴滴金、石竹诸花,则明知精力不继,篇帙寥寥,作此以塞纸尾,犹人诗文既尽,附以零星杂著者是也。由是观之,造物者极欲骋才,不肯自惜其力之人也。造物之才,不可竭而可竭,可竭而终不可竟竭者也。究竟一部全文,终病其后来稍弱,其不能弱始劲终者,气使之然,作者欲留余地而不得也。③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金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323页。
这便呈现出一部宏伟、激越的大自然生命史诗。诸物种在时间节奏上发生了内在的生命联系,极类似于当今的生态学视野。当然,李渔的自然生命时间视野还是古典的——仅限于四季节律,他还不具备“进化史”的宏观自然史视野。到了利奥波德这里,自然审美欣赏便具备了另一种眼光——地球生命史的眼光:
随着地球史的展开,我们对鹤的欣赏与日俱增。我们现在知道,它的部落发源于始新世,它所发源的动物群的其他成员随地质运动早已被埋在山里。当我们听到鹤鸣,我们听到的不只是鸟音,我们听到的是进化之乐的凯旋声。它是不可驯服的过去之象征,是那奠定了今天鸟与人类生活基础的不可思议的千百万年地球历史之象征。④Aldo Leopold,ASand County Almanac:And ScketchesHere and The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p.96.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将李渔在《种植部》中所提出的“编年史”概念,以及它所代表的自然生命史审美视野,理解为一种以生态学核心理念为基础的当代环境美学“物史”理念之古典预言形态。至此,与其所开拓的“以物比德”模式系统相对比,李渔的《种植部》同时也开拓出另一自然审美欣赏系统,那便是以“物性”“物功”和“物史”为骨架的客观地呈现自然对象内在深度之美的静观或客观系统。
最后,李渔在描述众花木自身特性之时,尽可能摆脱人类功利主义地利用自然的传统趣味,表现出一种设身处地地从众物自身生命需求的角度阐释物性的新路径:
柳贵乎垂,不垂则可无柳。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致,徒垂无益也。此树为纳蝉之所,诸鸟亦集,长夏不寂寞,得时闻鼓吹者,是树皆有功,而高柳为最。总之,种树非止娱目,兼为悦耳。目有时而不娱,以在卧榻之上也;耳则无时不悦。鸟声之最可爱者,不在人之坐时,而偏在睡时。鸟音宜晓听,人皆知之,而其独宜于晓之故,人则未之察也。鸟之防弋,无时不然。卯辰以后,是人皆起,人起而鸟不自安矣。虑患之念一生,虽欲鸣而不得,鸣亦必无好音,此其不宜于昼也。晓则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数亦寥寥,鸟无防患之心,自能毕其能事。且扪舌一夜,技痒于心,至此皆思调弄,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者是也,此其独宜于晓也。庄子非鱼能知鱼之乐,笠翁非鸟能识鸟之情,凡属鸣禽,皆当呼予为知己。种树之乐多端,而其不便于雅人者亦有一节。枝叶繁冗,不漏月光,隔婵娟而不使见者,此其无心之过,不足责也。然匪树木无心,人无心耳。使于种植之初,预防及此,留一线之余天,以待月轮出没,则昼夜均受其利矣。①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
尽可能超然地体物之情,这已然是一种不自觉地超越古典人类中心主义视野、极为难得的环境美德。正是在此同情式观照自然的环境美德引领下,李渔提出了一种与物共处、分享的观念:
芥子园之地不及三亩,而屋居其一,石居其一,乃榴之大者,复有四五株。是点缀吾居,使不落寞者,榴也。盘踞吾地,使不得尽栽他卉者,亦榴也。榴之功罪,不几半乎?然赖主人善用,榴虽多,不为赘也。榴性喜压,就其根之宜石者,从而山之,是榴之根即山之麓也。榴性喜日,就其阴之可庇者,从而屋之,是榴之地即屋之天也。榴之性又复喜高而直上,就其枝柯之可傍,而又借为天际真人者,从而楼之,是榴之花即吾倚栏守户之人也。此芥子园主人区处石榴之法,请以公之树木者。②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种植部·石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上述观念已然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相一致,这正是李渔《种植部》所具有的生态启蒙意义、它的预言性或超越性。
三、结 论
某种意义上说,李渔的《闲情偶寄·种植部》并非一个关于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之完善文本,因为它的描述对象仅乃天地自然之极特殊部分——植物自然,而且是栽培植物,并非自然之全部,有机界之动物界与无机界之山水均不在其列。它只是为读者开辟了天地自然中一个小窗口而非其全景。即便如此,对考察中国传统自然审美基本特征而言,《种植部》依然极具代表性,因而是一个典范文本,因为它呈现了古代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文人观察和欣赏自然的基本趣味与视野,呈现了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之基本方式。在传统自然审美的浅层次上,它热情地传达出每个中国人面对自然对象之首要审美趣味——形式主义地对待自然,聚焦于花草树木的突出色彩、造型及其浓淡香气。实际上,面对自然的形式主义趣味,突出欣赏自然对象外在的物相特征——形式美,这并非中国人的特殊情怀,乃是一种国际性普遍审美趣味。即使在这一点上,李渔在其《种植部》中所传达的审美趣味也很经典。若不相信,我们可略回忆一下那些以摹物状景取胜的古代诗文名篇,以及花鸟画的典范之作,看它们是否确实与《种植部》共享了突出的形式美地看待自然物的审美眼光。
在深层次上,李渔的《种植部》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之主导传统——以物比德或曰托物言志。这突出地表现为在这部本来以植物为主题的林学著作中,李渔在描述诸树木花草各自生物外观与特性时,会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强烈文学冲动,往往喜以物拟人、借花说理,或托木言情。于是,一部经典的林学著作同时也就成为一部关于树木花草之美的文学经典——美文、浓情与至理兼备的优美自然散文集。《种植部》整体篇幅极为克制,植物乃其主角,然而我们却从中发现了几乎在任何一部传统诗词作品或写意花鸟画作中可以发现的东西——浓郁的人文情感与哲理表达趣味。实际上,《种植部》与传统抒情诗词以及写意花鸟画共享一种自然审美趣味,共享一种观察自然的路径或眼光,那便是“万物皆着我之色彩”的主观主义自然观。
应当如何认识这部成分复杂的经典?若立足于传统的以物比德审美趣味,我们不得不承认:《种植部》是一部理应获得所有读者喜爱与尊重的自然文学经典。然而,当我们立足于自然审美本身时,便会面临一些本质性困惑:这些所谓的德性或哲理属于诸树木花草本身吗?若它们确实并不具有李渔所强调的诸人文美德与哲理,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欣赏这些植物?李渔在其抒情言理的花木散文中所极力赞赏的,到底是这些树木花草本身所具有的客观事实,还是一些本属人文的趣味与观念?若我们仅以比德的心态观察和欣赏自然,那么我们所欣赏的到底是自然对象本身,还是一些人文价值观念?其实,我们还可在此提出一些更为根本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欣赏自然,自然美的真实内涵究竟为何物?当代环境美学认为:恰当的自然审美应当欣赏自然对象自身所具有的外在表象与内在特性,因此,客观地对待自然当是自然审美应当遵守的第一性原则。据此,《种植部》所突出表现的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主导模式——以物比德,便涉嫌以歌颂自然之名行人类自我言说之实,自然审美在此变得有名而无实,因此是一种不恰当的自然审美方式。①关于对中国自然审美传统的反思,见薛富兴:《自然审美“恰当性”问题与中国“借景抒情”传统》,《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儒家比德观的审美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李渔的《种植部》又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文本,它不仅因倡导以物比德自然审美模式而具传统性,同时也在客观而有深度地欣赏自然的道路上,取得了远超越于前人的不俗成就。具体地,在客观地对待自然的正确道路上,它于准确、细腻和深刻地呈现诸花草树木的内在特性方面,拓展出物性、物功与物史三个维度,与物相维度一起,构成一个完善地揭示自然美内涵的要素系统,开拓出中国古典自然审美新境界,客观上符合了当代环境美学关于自然美内涵的核心理念。某种意义上,李渔的《种植部》在中国自然审美史上的意义,极类似于奥多·利奥波德的《沙乡的沉思》在西方自然审美史上的意义,均具有鲜明的预言性,因而是一个超越性文本。
概言之,对于李渔的《闲情偶寄·种植部》,除了将它典范地从属于李渔的“生活美学”,即表现其日常生活审美语境与情趣的同时,还可对它作相对独立的审视,将它理解为一个关于中国古代自然审美的典范文本。这种典范性是双重的,充满张力。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古代自然审美的传统性,包括在当代环境美学视野下所呈现出的主观主义地对待自然、濡染自然的原则性缺陷;另一方面,它又在客观、有深度地呈现自然对象自身审美特性与价值上卓有建树,做出了超越前人的重大开拓,因而又成为一部先知性的自然审美经典。正因如此,李渔的《种植部》便与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以及徐霞客的游记一起,成为我们考察与反思中国自然审美史的最佳入手处,以及以新的环境伦理与审美趣味超越前贤,开拓当代自然审美新境界的正确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