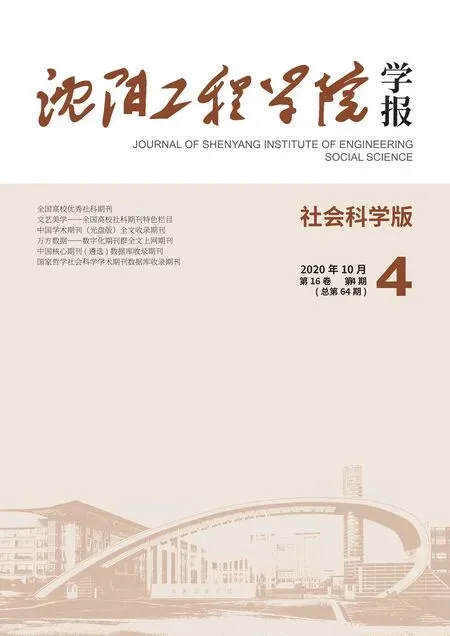冰山底下的谋杀案
——海明威《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解析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海明威一直被看作短篇小说的大师,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海明威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在短篇小说方面。”[1]这位短篇小说的巨匠在1933 年去非洲游猎之后,写出了数篇精彩的作品,其一名为《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讲述的故事以一桩出人意料又扑朔迷离的人命案收场,许多年来一直令人迷惑且引人入胜:“1981 年,海明威基金会成立,创办了《海明威评论》……在《海明威评论》及其他一些刊物中争议最多的是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争议的焦点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不是有意谋害自己的丈夫。”[3]这一争议至今未有定论。翻开这桩积年沉案,我们暂且不把自己当成文学作品的鉴赏者,而是当成一名侦探,目标为搜寻案卷中的蛛丝马迹,并凭借自己的推理与想象能力,查明其背后的隐情。
一、杀人者的动机与计划
我们知道,侦破一个案件的逻辑起点是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动机。可以肯定,麦康伯夫人玛格丽特具有谋害亲夫的明确动机,而这一动机源自二人并不平衡、牢靠的婚姻关系,以及玛格丽特对这种关系日益紧张的危机意识。
从表面上看,“他们有健全的结合基础。玛戈长得太漂亮了,麦康伯舍不得同她离婚;麦康伯太有钱了,玛戈也不愿离开他。”然而这里显然采用了反讽手法,因为金钱与美色的交换绝对不是男女结合的基础,所以他们的婚姻根本不够牢靠。而在这种不够牢靠的婚姻中,二人的地位也不对等。玛格丽特结婚之前的身份小说没有交待,但交待出这位身份不明的英国女子背井离乡嫁给美国富人而获得了社会地位和奢华生活,很有可能原本玛格丽特除了美色之外一无所有,所以麦康伯从一开始就占尽了上峰。而且“她嫁给弗朗西斯·麦康伯十一年了”,已经步入中年,过去尚可与麦康伯的金钱匹敌的美色当然也大打折扣,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丧失殆尽,但35 岁的麦康伯却正值春秋鼎盛。在这种一边倒的势力对比中,外强中干的玛格丽特必定受尽麦康伯的漠视。比如,麦康伯在暴露了自己其实只是一个没有男子汉气概的胆小鬼之后,仍然当着外人对妻子说:“别傻头傻脑,玛戈”“干吗不把那股泼妇劲儿收敛一点儿,玛戈。”——这种语气足显大丈夫平日的强势。但他不会知道,他的玛戈其实是那种“最冷酷、最狠心、最掠夺成性和最迷人的;她们变得冷酷以后,她们的男人就得软下来,要不然,就会精神崩溃”“她们控制一切,那还用说”。这样的女人绝对不会低眉顺眼地甘当丈夫漂亮的附庸,接受一点施予。之所以还“从来没有闹得不可收拾”,最终以“散伙”了之,对此麦康伯审时度势,心知肚明。
玛格丽特没有提出离婚,是有其不得已之处的。然而麦康伯条件优越,却也有所让步,以维持实际上早已破裂的婚姻。如果麦康伯另娶,玛格丽特就不仅摆脱了不幸福的婚姻,还会争得丈夫为之补偿的大笔财产。但是麦康伯“知道紧紧抓着他的钱不放,知道他那个圈子里的人干的大多数事情”,因此不会为把“仍然是一位大美人儿”的妻子换成另外一个,损失自己大笔的财产。所以,即使玛格丽特多次以自己似有若无的外遇来刺激、羞辱他,以迫使他提出离婚,他也一再显示出“宽容大量”,换句话就是“什么都会忍受”。其忍无可忍的界限,大概就在于他是否能确实抓住妻子的把柄,而玛格丽特又不可能让他得到明确的证据。个中难言之隐,在他虚荣的意识上势必要被美化成“他最大的优点”,但他也能感觉到其实为“他的致命的弱点”。而恰是这一“致命的弱点”把玛格丽特逼得实在别无他计可施,只能通过谋杀来改变控制着她的婚姻,获取金钱。
玛格丽特了解她的丈夫,包括“他的致命的弱点”,但麦康伯这个被金钱与地位宠坏的“孩子”不会了解他的妻子。在他眼中玛格丽特“傻头傻脑”,反不如猎人威尔逊看得清楚:“她有一张典型的鹅蛋脸,典型的你以为她是个蠢货。但是她不蠢,威尔逊想,不,不蠢。”不蠢的女人想要杀人绝不会采取愚蠢的办法,而要巧施妙计。把麦康伯带到“被称为最黑暗的非洲的那一部分地方来打猎”,让他死于意外,这不失为借刀杀人的上策。
在夫妻二人中,到底是谁先起意去非洲去打猎的呢?对此小说没有交待,但写到麦康伯在逃脱雄狮爪牙之后的意识:“正像有一个社交生活专栏的作者所写的,不是仅仅为了要给他们非常受人羡慕和始终经得起考验的爱情添上一层惊险色彩,他们才深入到被称为最黑暗的非洲的那一部分地方来打猎……”这时麦康伯也只是想到别人对他这次活动的看法,而且只有“不是仅仅为了”,缺了“还是为了”。这样含糊的半句话,说明麦康伯并不知道自己来非洲打猎的目的,那么他来非洲打猎就应该是经过了妻子的诱导、鼓动,甚至安排。
她的计划进展得相当顺利,但在即将成功时遇上了一个麻烦,这个麻烦绝对不是麦康伯到了狮子跟前由于惊恐而逃跑了。玛格丽特的麻烦是出在威尔逊身上。这位猎人的一项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证雇主的安全,他经验丰富,本领高强,准备充分,携带枪身短、口径大的“505 吉布斯”,使用爆破力强的空心弹,适于近距离射杀目标。因此,在威尔逊不失职的情况下,无论多近多猛的野兽,也越不过他这道防线而伤害到麦康伯。
一次失利当然不会让玛格丽特就此放弃她的计划,她的计划也不能因为一次失利就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个计划的高妙之处,就在于鼓弄麦康伯的“男子汉气概”,让他临危不顾,舍生忘死。玛格丽特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她十分了解这种“男子汉气概”,它就像那只雄狮,受伤之后会变得更加凶猛。而能够挫伤这种“男子汉气概”的,不是雄狮,唯有女人,因为它不是“勇敢”,只是在女人面前不能不勇敢,从本质上说,就是男人相对于女人必须维持的体面、虚荣。所以玛格丽特利刃在手,就继续戳向麦康伯的痛处。猎狮归来,“‘咱们别谈那头狮子’,她说。”这是因为“狮子”并非能够刺痛麦康伯的利刃,威尔逊的“美貌”才是此时她应该谈论的话题。她向威尔逊卖弄风情给麦康伯看,继之夜不归宿,还理直气壮地骂他是胆小鬼,麦康伯果然中计。在又去打野牛的过程中,他成长为一个不顾死活的男子汉,而一旁的玛格丽特则在冷眼欣赏着自己的成果:
“你变得勇敢得很,突然变得勇敢得很。”他的妻子轻蔑地说,但是她的轻蔑是没有把握的。她非常害怕一件事情。
那么她害怕的会是什么呢?她害怕的其实还是上次遇到的难题,如果威尔逊再次从中作梗,她就免不了要亲自动手了。对此,她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已经准备妥当。上次去打狮子的时候,威尔逊对麦康伯说:
“来吧,”他说,“你的扛枪人把你那支斯普林菲尔德和那支大枪都带上了。样样都在汽车里了。你有实心弹吗?”
“有。”
“我准备好了。”麦康伯太太说。
由此可知,麦康伯的枪弹是由他太太准备的,共有两支枪。而这次除了上次的两支,又多出一支“6.5 口径的曼利切”,这支枪也应该是他太太特意准备的。我们记得,威尔逊曾说:“在非洲没有一个女人打不中狮子”,其实玛格丽特就是这样的“女汉子”。“索马里有一句成语;一个勇敢的人总是被狮子吓三次;他第一次看到它的脚印的时候,他第一次听到它的吼叫的时候和他第一次面对着它的时候。”玛格丽特听到了狮子的吼叫之所以毫无惧色,说明这不是她第一次听到,那么她就曾经到过非洲。而且她也十分了解这里的狩猎活动,唯有如此,她才能在威尔逊违反狩猎规则的时候抓住了他的把柄。以此而论,玛格丽特应该枪法娴熟,只是这连同她的青春岁月已经被十一年美国生活隐藏了起来,麦康伯不知道,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所以,当她看到野牛正向麦康伯冲去时,“威尔逊在前面,跪在地上开枪”,野牛“那颗脑袋开始搭拉下来”,准备好的猎枪就必须派上用场了,这对于她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几乎所有人都会以为:她“眼看野牛的犄角马上就要冲到麦康伯的身上,就用那支6.5 口径的曼利切向那条野牛开了一枪,谁知道却打中了她丈夫的颅底骨上面约摸两英寸高、稍微偏向一边的地方”。
二、杀人者的从犯威尔逊
大概是为了使麦康伯太太的杀人计划更为深曲隐晦,整篇小说对威尔逊这个人物的描写几乎完全采用“外聚焦”,仅在一处使用了蜻蜓点水、半含半吐的“内聚焦”:
“那是一头好狮子,对不?”麦康伯说。这会儿他的妻子看着他。她看着这两个男人,好像她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似的。
这一个,叫威尔逊,是个打猎的白人,她知道她以前确实不认识他。
由于这个“内聚焦”,读者稍不留心,就会断定玛格丽特与威尔逊素未平生,是在这趟游猎中不期而遇的,其实未必如此,它只是作者的“文字游戏”给读者造成的“视觉误差”。从前面一段话来看,她以前是熟识这两个男人的,只是他们的所做所为使她觉得他们现在很是陌生。如果她以前不熟识威尔逊,就用不着一个“看着”之后再接上一个“看着”,拐带上威尔逊,威尔逊本来不就是“她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吗?第二段话尤其古怪,假如去掉其中的“她知道”,我们就可以大体上以之断定“她以前确实不认识他”,只是他似曾相识。但有了“她知道”之后,句子就歧义丛生。因为这种“间接引语”不可能忠实地记录人物原原本本的想法,只是对人物想法的转述,可以略去一定成分。所以,“她以前确实不认识他”既可以理解为她知道的一段“历史”,也可以理解为她知道的一种“现状”,也就是说,因为两人长期生活境遇不同,确实不会有人想到这位美国贵妇和那个非洲猎人很久以前的关系。
玛格丽特、威尔逊经常在无意中透露出他们互知底细,比如,当玛格丽特看到威尔逊因不自在偶尔摘下了帽子,“这是个非常奇怪的日子,”她说,“哪怕是中午待在帆布帐篷里,你不是也应该戴着帽子吗?你知道,你告诉过我。”
威尔逊不是一个饶舌的人,为什么会告诉刚刚结识的雇主的太太自己有这样一个习惯呢?显然这是她先前知道的,而且这又不是通过几天的观察就能知道的;后加的“你告诉过我”,是说给被蒙在鼓里的傻瓜麦康伯听的。在玛格丽特情绪恶劣突然离场后,“女人动不动就使性子,”威尔逊对高个子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来的。神经紧张,加上这样那样的事情。”
按照常理,妻子和丈夫当着客人闹别扭,应该是丈夫向客人解释一番,威尔逊此时却反客为主,就像玛格丽特是自己的太太一样。我们再看威尔逊的一段意识活动:
汽车出发的时候,威尔逊看到她站在一棵大树底下,穿着淡玫瑰红的卡其衫,她那副模样儿说她长得美,倒不如说她漂亮更恰当,她的黑头发从脑门上向后梳,挽成一个髻,低低地垂在颈窝上,她的脸色滋润,他想,就像她在英国似的。
威尔逊何以一回眸间由玛格丽特眼前的样子联想到她在英国时的样子,只能因为她在英国时的样子是他的脑海中不能被岁月消磨的一个印象。
玛格丽特要完成她的计划,必定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威尔逊这个老相识理所当然是她的最佳人选;在射杀狮子之前,他也一直尽心尽力地辅佐着玛格丽特:首先,必须由他把麦康伯引到最为凶猛的狮子出没的地点,“那帮手下人说,这儿附近有一头挺大的家伙呢。”从威尔逊的这句话,可知“这儿”并非他随意安排的宿营地点。其次,在出发狩猎之前,麦康伯曾向他请教瞄准的部位和射击的距离。对于瞄准的部位,他的回答较为明确,而对于射击的距离,他的回答则非常含糊,这不是仅仅因为“距离多少得由狮子来决定”,也是因为狮子的距离多少决定着猎人使用什么枪弹。子弹分“实心弹”和“空心弹”,实心弹适于远射,但没有爆破力,只能在动物身上留下“小窟窿”。威尔逊为自己装备了“短枪”和“大子弹”,而麦康伯则无论远攻近战一概使用他太太为他装备的“实心弹”。作为一个新手,麦康伯的枪法即使再好,也不会精准地击中狮子的要害,而威尔逊这位老手,就不用去瞄准狮子的两个肩膀之间或者脖子,只因为用了空心弹,所以能够一枪轰掉狮子的半个脑袋。再次,受伤的狮子潜伏到树丛中后,麦康伯这位雇主其实对自己的战绩已经非常满意,他手下的雇员们本该举手相庆,鸣金收兵,大可不必再去犯难历险,而威尔逊却撺掇他再到树丛中去看一看。麦康伯很不情愿,尽管威尔逊死拉活劝,“‘我可不愿到那儿去。’麦康伯说。他自己还不觉得,话已经说出口了。”就在威尔逊无计可施之时,“他突然感到好像自己在旅馆里开错了一扇房门,看到了一件丑事似的”,找准了麦康伯的软肋。麦康伯的软肋不是他的胆小,而是他怕被别人认为胆小。因此,威尔逊此后转而采取激将法:“不过你不一定跟它打交道”,这果然迫使麦康伯回答说:“不,我要去。”最后,在进入树丛之前,麦康伯没有回去和太太说一声,威尔逊却回去了,给麦康伯又带来一只“大枪”“麦康伯接过那支大枪”,岂不知这只大枪除了给他增添累赘,毫无用处。
当然,在麦康伯逃跑之后,威尔逊还是结果了那只狮子。如果不结果这只狮子,他的“准则”就要受到触犯,这个准则就是:“在非洲没有一个女人打不中狮子;没有一个白种男人逃跑。”威尔逊也和麦康伯一样,不愿意被人看成是胆小鬼,更不愿意被人认为还不如一个女人。
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威尔逊也要和其他人一样“装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但是他的心情应该是非常复杂的。此前,威尔逊大概因为玛格丽特的说辞及自己的妒恨,必欲置麦康伯于死地而后快。此后,他冷静下来,对他和她做出的事情感到悔恨。因此,他开始试图阻止玛格丽特的计划,至少自己能从他们的是非当中抽身出来。在她想要再和他们一起去打野牛时,他不顾自己是否显得无礼而一再突兀地说:“你别去。”他有意带领麦康伯到“空旷的地方”而不是“树荫稠密的隐蔽的地方打野牛”,可还是有一只受伤的野牛逃到了树丛中,他不得不再次去和麦康伯一起冒险。这一次,他没有像上次那样让麦康伯带着那支多余的“大枪”,而是交给了一个扛枪的人,另一支“曼利切”或许可以让另一个扛枪的人带着,但是那个扛枪人已经扭伤了脚,随行恐生不测,只好留下“赶鸟”,所以这支枪就没有带走。他也绝不会想到这是她特意准备的杀人凶器,因为她绝不会把自己的底细全都透露给他:“昨天夜晚,她说话不多。一想到这件事,看见她就高兴。”等到麦康伯死于非命,他才恍然大悟这支枪的用途。然而事已如此,他又不得不帮她隐藏真相。
威尔逊虽是小说的次要人物,或者说中间人物,却最为矛盾、复杂,整个作品的“张力”也由之而生[5]。从表面上看,他具有自由、冷峻的“荒野英雄”气派,而归根到底只是一个卑微、可怜的人,受尽剥夺、奴役、侮辱。这个“机关枪手”只能靠着一技之长孤独地在异国他乡以危险职业为生路,没有家庭、恋人和社会地位,与那些可以忍受鞭打的非洲仆人一样。
三、结语
海明威曾说:“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对象心里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4]《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就是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创作目标和方法的一部作品。由于它描写的真实,特别是对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语言、行为细微而传神的刻画,我们确实能够感觉到其言外之意,并以之完整现出这座冰山在水面之下的底基,而知作品的命意在于揭露当时西方社会以金钱、物欲为其维系的人际关系所包藏的罪恶,以及西方文化所鼓吹的“硬汉精神”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