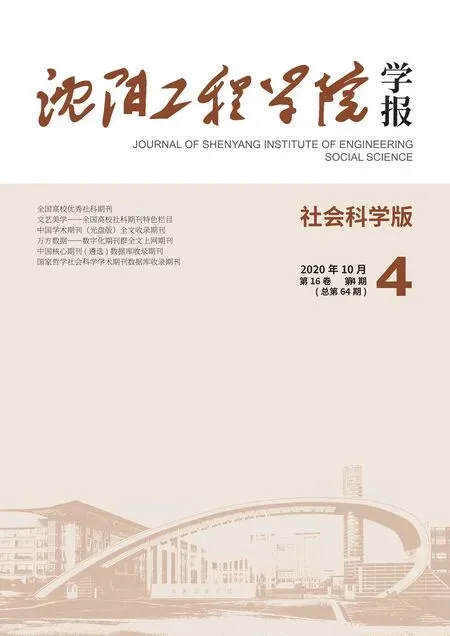窥探灵魂的摄影师
——论《七角楼》中的霍尔格雷渥形象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七角楼》是霍桑继《红字》之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取材于霍桑的家族历史故事。这是一个两大世仇家族罪与罚的故事,但却一改往日悲伤阴郁的风格,呈现出和美温情的面貌。国外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这部作品对摄影的独特关注及其文学书写。凯瑟琳·甘德就挖掘了文学大家霍桑与摄影之间的艺术碰撞与融合,指出霍桑及其妻子“经常忽略众所周知的照相技术的局限性,而是选择专注于其作为表示隐喻的能力”。尽管叙述者在文本中声称,摄影师只是霍尔格雷渥的糊口行当,并不具有任何特殊意义。然而,他在作品中的处理却与此相悖——他没有强调霍尔格雷渥的房客身份或莫尔后人的身份,而是用“摄影师”来完成身份认知;霍尔格雷渥作为一个银版摄影师出场,在文中霍桑甚至用“摄影师”或“艺术家”指代其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霍尔格雷渥通过摄影预示了平琼法官的最终命运,最终完成了家族诅咒。可以说,摄影实际上是霍尔格雷渥家族巫术能力的现代延续,也暗中揭示了他的莫尔后人身份。以摄影师的方式观看平琼家族的灵魂内质,霍尔格雷渥既冷漠地旁观了平琼家族的罪恶,又不无爱意地参与其中。随着观察活动的展开,霍尔格雷渥逐渐挣脱狭隘的复仇视角,意识到复仇行为本身的罪恶性。由此,两个家族的和解得以达成。
从“摄影师”的职业身份来观照文本,将有助于理解霍桑对霍尔格雷渥形象的独特塑造,窥见霍桑与美国肖像摄影共同的审美精神,以及霍桑对普遍存在的罪恶和赎罪之道的思考。
一、典型的美国肖像摄影师
霍尔格雷渥的摄影师职业,是霍桑对这一新兴行业认识的集中体现。文中的内容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肖像摄影当时在美国的发展情况,还承载了美国肖像摄影独特的审美理念。
霍桑对霍尔格雷渥的职业介绍使用的是银版摄影师(Daguerreotypist)一词,它来源于路易·达盖尔于1837 年发明的银版摄影法(Daguerreotype)。1839 年达盖尔摄影法刚刚公布不久就传入美国,那时就已经引起了霍桑的重视。同年12 月,霍桑就在与索菲亚的信中表达了他对银版摄影法的看法:“(它)可能会把我们最深刻、最微妙、最微妙的思想和感情打印出来,就像上面提到的工具描绘自然的各个方面那样细致、准确。”[1]384霍桑于1851 年写成了《七角楼》这部小说,在此前后,银版摄影正在取代传统肖像画,成为美国商业摄影的主流。1840 年波士顿就已经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商业肖像摄影工作室。40 年代到60 年代,新英格兰银版摄影技术经过多次更新,变得便携、方便,充分满足室内外的拍摄需求,专业的摄影公司和工作室遍地开花。也许霍桑本人都没有意识到,他在《七角楼》中不经意地呈现了肖像艺术从绘画走向摄影的巨大变革:霍尔格雷渥在镇上拥有一间专门的摄影工作室,以摄影为谋生手段;同时,霍尔格雷渥已经可以在工作室内和海边自由开展拍摄工作。平琼家族后人所有的肖像则展示了新旧肖像艺术形式的更迭——“凶宅”七角楼一直悬挂着平琼上校的巨型肖像,老处女赫普兹芭珍藏着具有莫尔博恩风格的克利福德微型画像,而富有的贾弗里法官则是到霍尔格雷渥的工作室拍摄袖珍银版肖像。这个家族的肖像从巨幅画到微型画像,最后到袖珍银版肖像,清晰地展现了新英格兰地区的肖像艺术演变。
除了技术手段的更新,肖像艺术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实现由绘画到摄影的跨越与转变,主要得益于摄影艺术的实践主体——银版摄影法的发明者达盖尔本人就是一位画家,新英格兰肖像摄影的先行者约书亚·哈维斯更是一个画家兼摄影家。约翰·卡斯帕·拉瓦特犀利地指出,绘画开创了以细节揭示人物内心的肖像美学传统①瑞士神学家约翰·卡斯帕·拉瓦特1789 年发表《论相面术》(Essays on Physiognomy)系列文章,提出了这个观点:“画家开发了透过人物外表洞察其内心的天赋,这种洞察要通过那些很自然的细节,而我们往往会不经意忽略他们。”。早期肖像摄影的实践中,摄影家与画家合作、摄影家本人就是画家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的摄影作品往往也总是以肖像画再现细节和展现人物精神风貌为艺术追求,仿佛肖像摄影不过是绘画艺术的衍生品。正如邓拉普评价作者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华盛顿肖像时所说的,肖像渗入人物的内心生活,具有“充分的洞察力和品格表现”[2]112。作为后起之秀,银版摄影恰恰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这种再现细节的基本要求——它成像细腻、清晰,细节处理能力较强,因而尽管最初达盖尔银版摄影法相比于卡罗尔摄影法有曝光时间长、费用高的缺点,仍旧能取代微型画像成为当时的主流。
罗森布拉姆指出了美国人独有的摄影审美:“美国文化崇尚没有修饰的真实感,不相信摆拍出来的所谓优雅和排场,所以美国肖像摄影没有过多修饰的细节和做作的表情。”[3]45我们对照一下霍尔格雷渥的话会发现,这简直是下面这段话的翻版:“我的大部分肖像都是绷着脸的,不过那主要是因为照相的人本来就是那样儿。……我们以为它只能描绘最表面的东西,其实它能把最隐秘的性格真实地表现出来,而这一点,没有哪个画家敢于揭示,即使他有这种能力。至少我这种微不足道的艺术不会美化什么。”[4]63霍桑借助霍尔格雷渥之口直接道出了当时美国肖像摄影的基本美学追求:不事外饰,力求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人物深藏的内心世界。《七角楼》里继承了平琼家罪恶的贾弗里·平琼法官平时隐藏颇深,连好人维纳伯伯都认为他与平琼家那些不随和、不友好的人截然不同。“照片永远是切片性的”[5]437,但在这张瞬间的“切片”中,无论平琼法官如何修饰自己,都只是一副阴险狡诈之态。“他本人(贾弗里·平琼)拥有一张令人十分愉悦的面孔,显示出他心地仁慈,心胸开阔,性情豁达,以及其他这类优秀品质。可是你瞧,太阳光告诉我们的却完全是不同的情况,阳光是不会受骗的,我试了五六次都无济于事。这个人狡猾、多疑、恶毒、专横,而且冷酷无情。”[4]64反观克利福德的微型画像:“身穿一件雍容华贵的老式绸晨衣,与他那耽于幻想的面部表情十分协调,那饱满柔和的嘴唇和魅力十足的眼睛似乎表明他这人温柔多情,却不善思考。”[4]19适当的外在装饰,在肖像画中是整个画面的一部分,与表情配合,将克利福德温柔善良的精神风貌展现出来。相比于绘画,摄影在洞察人心方面似乎更胜一筹。
正如艾伯特·桑兹·索思渥思所说:“第一眼就应当看出拍摄对象的全部特征……艺术摄影家的要求和目标应当是在照片上展现出每个特定面孔或形体的最明显的特征和最佳表情。但是在最终画面上,所有对美感、表情和特征的描绘和表现都不能背离真实。”[6]14《七角楼》里的摄影照片毫不留情地揭开了平琼法官苦心孤诣的伪装,将他最真实的内心状态加以呈现。由此,霍桑大胆地将摄影引入作品的做法,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摄影符合他刻画人物的一贯方式——将不可捉摸的内心世界化为外在形象,观览人物面容即可视及人物的精神世界。综观霍桑的作品,大部分人物形象都是以这种方式描绘的:《红字》中的赫斯特·普林“五官端正,面容姣好”,散发着端庄威严的气质[7]7;《胎记》里乔治亚娜“红扑扑的脸蛋变得像死一样苍白”时,消除胎记的恐惧就被表现出来[8]240;《拉帕西尼的女儿》中父女二人截然两分的性格也在“脸色灰黄、一派病容”与“活力四射、神采飞扬”的描绘中得以体现[8]249-250。
由是观之,如果说霍尔格雷渥的摄影师身份有什么特殊含义的话,首先应当是代表了霍桑自己,霍桑本人就是一个类似摄影师的观看者。就如他对自己的定位一样,他“生来就是一位生活中的旁观者”[9]639“人类生活的研究者”[9]837。
二、会“巫术”的莫尔后人
同祖先具有诅咒能力和催眠能力一样,摄影是霍尔格雷渥所掌握的“现代巫术”。在文中,叙述者甚至称其为“神秘的不法之徒”。霍尔格雷渥这位“巫师”后人正是通过摄影对光的操纵确证了自身的超验能力,还以一张银版肖像照预示了平琼法官的死亡。
祖先马修·莫尔被诬陷为“巫师”而死时,“上帝会叫他流血”的诅咒就降了下来。七角楼的主人邀请全镇参加庆祝活动时暴毙,坐实了马修·莫尔的巫师身份。从此,平琼家的人一直生活在马修·莫尔的阴影中。故事代代相传,最终形成了了马修·莫尔后人“催眠”能力的传说。木匠托马斯·莫尔就直接继承了这种特殊能力。当杰维斯·平琼提出以重金换取祖父死去时丢失的东区土地文件时,木匠要求与其女儿艾丽丝·平琼见面。高傲的艾丽丝看向托马斯·莫尔的眼睛,从此就沦为了他的“提线木偶”,直到死亡。霍桑以故事嵌套的方式讲述了这段传说,让霍尔格雷渥向菲比讲述了这个故事,并且企图催眠菲比。他就要做到了:“一层朦胧的纱幕已经开始笼罩在她的身体周围,在这层纱幕中她只能注意到他的存在,而且受到他的思想感情支配。”[4]144但霍尔格雷渥在最后时刻意志动摇了,在菲比这里主动弃置了祖传的催眠术。这部分由于他“为人正直”,对善良的菲比动了恻隐之心,也因为菲比并非真正的平琼家人。菲比是平琼家族的旁系,并不是“按照平琼的传统方式长大的”,她温柔善良,完全没有平琼家族的傲慢;赫普兹芭认为“菲比不能算是平琼家的人,她的一切都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来的”[4]55;霍尔格雷渥本人也说,“我并不把你(菲比)当作他们(平琼家族)中的一员”[4]127。
对比来看,老赫普兹芭和克利福德古板孤僻,但仍不失原罪意识和爱的能力,而菲比简直就是平琼家族的光明天使。与七角楼有直接关系的平琼后人中,只有贾弗里·平琼法官继承了老清教徒平琼上校阴险贪婪的特征,因而,他才是莫尔后代真正的复仇对象。霍尔格雷渥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在真正的平琼后代身上施展“巫术”,即通过摄影和照片揭露贾弗里·平琼丑恶的内心世界,并预示了他与祖先同样的死亡方式。在作品中,霍尔格雷渥说:“天上的阳光不论是灿烂还是柔和,都含有一种非凡的洞察力。”[4]64这种具有洞察力的光不单单是自然之光,它被升华为“神圣之光”,代表着最高的权威——上帝。因而,摄影才具有穿透伪装、显现人心的神奇力量。摄影这一科学技术手段就被霍桑赋予了“光”的象征意义,获得了超验能力。“我是用太阳光来制造相片的”[4]63“滥用上帝赐予的阳光,描绘人的相貌”[4]30,摄影师霍尔格雷渥就成了能够使用上帝之光的“巫师”,就如马修·莫尔能够让上帝听从他的诅咒一样,霍尔格雷渥也是能使上帝显现超验能力的人。在他的启发下,菲比才透过平琼法官慈爱和善的表情,看到他面孔上的冷酷、严峻和无情。而镇上的其他人,如维纳伯伯就不能明辨这一点。
菲比看了贾弗里·平琼的照片,直接将其误认为恶毒专横的老平琼:“这脸上那双严厉的眼睛一天到晚盯着我,他就是我那位清教徒祖先……去掉了黑丝绒帽子和灰白胡子,给他穿了件新式外衣,打了一条绸领带,代替了他原来的斗篷和授印。我看经过你这番修改,他也没好看多少。”[4]64照片一下子将贾弗里·平琼的灵魂呈现出来,无怪乎菲比在见到平琼法官时如此惊讶:“他的表情仿佛完全是画像上那位长着胡子的祖先的翻版,这位现代法官从表情到细微的特征都似乎像接受传家宝一样,彻底承袭了祖先的一切,好像法官的长相是按照某种预言安排的。”[4]83到这里,霍桑已经为下文平琼法官死在平琼上校的安乐椅上埋下了伏笔。直到最后,霍尔格雷渥受到一种神秘的灾难或者死亡意识的驱动,成了案发现场的第一发现者,还拍下了平琼法官的死亡照片。平琼法官的死仿佛是命中注定般无法避免,照片告诉我们,他完全就是祖先精神的现代传人。那么在拍下他生前照片的那一刻,霍尔格雷渥就已经提前给他的命运下了判决书。平琼法官以和祖先同样的方式死去、死在同样的地点颇有诅咒应验之感。霍尔格雷渥就意识到:“它与过去的事件交织的那么紧密,简直可以预言。”[4]209
按照凯瑟琳·甘德所言:“关于《七角楼》中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法的广泛研究仅以完整的方式反映出,霍桑一家在追求想象浪漫之媒介的过程中接触到了摄影。”[10]37那么,由摄影“用光”的特性出发,霍桑赋予了霍尔格雷渥神秘的预言能力,这就是霍桑对摄影的浪漫化书写的结果:摄影师的职业好似上帝赐予霍尔格雷渥的“现代预言家”身份,让他成功地施展了莫尔家族的巫术和诅咒。
三、人类灵魂的窥探者
苏珊·桑塔格认为,摄影师的非介入姿态仅仅是一种幻想。“使用相机(也)仍不失为一种参与形式。虽然相机是一个观察站,但拍照并非只是消极观察。就像窥淫癖一样,拍照至少是一种缄默地、往往是明白地鼓励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下去的方式。”[11]18这正是霍尔格雷渥面对平琼后代时的真正立场:他既是一个等待复仇实现的“过于镇定的冷眼旁观者”,也是一个积极干预其中的友人。
霍尔格雷渥保留了平琼法官的照片,一来因为他就是摄影师本人,有权拥有;二来是出于仇恨。阿加莎·克里斯蒂同样发表于1851 年的《麦金提太太之死》(又名《清洁女工之死》),探讨人们保留他人照片的原因时就指出了这一点:“为了保持复仇的欲望。有人伤害过你——你可能会保存一张照片来提醒自己,你觉得可能吗?”[12]188《七角楼》里霍尔格雷渥保留平琼法官的照片,多少就有点这种提醒自己“复仇”的意味。宋振军就指出,“摄影行为属于工作行为,但或多或少地有一些个人的喜好在其中”[13]211,此话用在霍尔格雷渥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与此相应的,与其说霍尔格雷渥回到这个小镇并租住七角楼完全是受到一种特别的兴趣吸引,毋宁说是复仇之心驱遣。菲比就意识到了他对她和克利福德兄妹的过分关注,认为他甚至“不让他们个性中哪怕是一点点细微的特征逃过他的眼睛”。霍尔格雷渥也宣称:“要是我有你那种机会,我准会毫无顾忌地测量克利福德心灵的深度,直到测锤的吊线放完为止。”[4]122由于同住七角楼,霍尔格雷渥对赫普兹芭、克利福德和菲比这三位品钦后人可以近距离观察,但品钦法官则不能如此,他与品钦法官唯一的交集就是摄影,这也是他观察他的唯一途径。由此观之,霍尔格雷渥不仅是一个记录现实的摄影师,摄影和照片不仅是他复仇意志的体现,也是他窥探平琼法官的方式。
霍尔格雷渥在窥探中发现了平琼法官的罪恶本性,也预感了法官会对克利福德施加迫害。但在面对菲比的询问时,他却言语暧昧。他宣称结局已经来临,但却说并不知道什么秘密,而只想旁观事态发展:“对这两个人(即赫普兹芭和克利福德),我既无意帮助,也不从想从中作梗,只是在旁观,自己分析、解释一些事情而已,还想体会你我此时所踩的地面上近两百年来缓慢发生过的戏剧性变化。假如允许我观察其结局,我毫不怀疑会从事情的发展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4]148霍尔格雷渥的观望态度默许了事态的发展,可以说是间接导致了平琼法官和克利福德之间的冲突。平琼法官的死和克利福德兄妹的出逃,尽管与霍尔格雷渥无关,但霍尔格雷渥却也是一个“共谋者”或者说“帮凶”。
在对待菲比、克利福德和赫普兹芭三人的态度上,霍尔格雷渥则介于冷漠与关爱之间。这样的观看方式恰似桑塔格所说的那种“受制于良心的需要”的结果[9]11。霍尔格雷渥持有这样一种摄影师的“人道”心态来观看他们三人的生活,就得以挣脱狭隘的复仇视角,对他们施以同情和关爱。在霍尔格雷渥的描述中,赫普兹芭是“观念陈旧、饱受贫穷折磨的老小姐”,克利福德是“受过屈辱的落魄绅士”[4]148,而菲比是“健康、舒适和自然的生活”的象征[4]147。这三个平琼后代,完全没有老平琼罪恶的影子,也没有犯下老平琼的罪孽;霍尔格雷渥通过对他们的观察意识到,他的“复仇”本身也是加诸无辜之人的一种罪恶。《圣经》中约翰一书5章17节说“凡不义的都是罪”,那么,莫尔家族的复仇恰恰也是莫尔家族的罪过。霍尔格雷渥的“正直”品性不允许自己犯下如此错误。因此,霍尔格雷渥并没有像那位催眠艾丽丝·平琼的祖先一样,采取积极的报复行动,反而在催眠菲比的最后一刻放弃了。霍尔格雷渥仅有的复仇行动是把一切交给最高的意志——上帝,而自己静观其变,暗暗等待命运的安排。
“一切苦毒、恼恨、忿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身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爱是化解仇恨的唯一方式。“要爱你爱的人,要爱你不爱的人,要爱你的敌人”,霍尔格雷渥就是一个践行者,尽管经过一番探索才达到爱敌人的程度。一开始霍尔格雷渥就像一个时而冷漠时而热情的邻人:帮助赫普兹芭照看花园、鼓励和开导赫普兹芭接待客人、参加平琼家的聚会,并尽力逗乐克利福德……菲比甚至感觉到:“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随时准备帮助他们,但是,他毕竟与他们算不上休戚与共,也不会随着对他们加深的了解而给他们额外的关怀。……从博爱的角度讲,他根本不关心她和她的朋友们,即使有过关系也十分微不足道。”但在克利福德兄妹染上杀害法官的嫌疑之时,霍尔格雷渥不再按捺自己对他们的关爱,拍下有利的现场照片,并主动与菲比商议对策。作为一个复仇者,霍尔格雷渥恐怕是世界上最具善意的了。最后,他也不再压抑自己对菲比的爱意,跨越家族仇恨的藩篱,与菲比实现了爱的结合。两个世仇家族以圆满的方式握手言和,霍尔格雷渥实现了自我和他人的双重救赎。相比于《红字》中的复仇者齐灵渥斯,霍尔格雷渥超越了他狭隘的复仇视角,成为一个人类灵魂的窥探者——他更像哈姆雷特——认识到了他人和自我的罪恶;但他也超越了哈姆雷特,凭借自己的行动拯救了他人,也拯救了自己。
四、结语
将霍尔格雷渥设定为银版摄影师,是霍桑借助摄影探索文学书写之内容与媒介的实践成果,也是霍桑与美国肖像摄影对话、寻求美学共鸣的体现。通过摄影,霍尔格雷渥成了揭示平琼法官灵魂罪恶、预言其悲惨际遇的现代巫师。运用摄影师独特的窥探之道,霍尔格雷渥对平琼家族的灾难保持缄默,实则是暗中鼓励复仇诅咒的实现;与此同时,他也能超越狭隘的复仇视角,反观自身复仇行为的罪恶性,主动以爱的方式化解了累世仇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