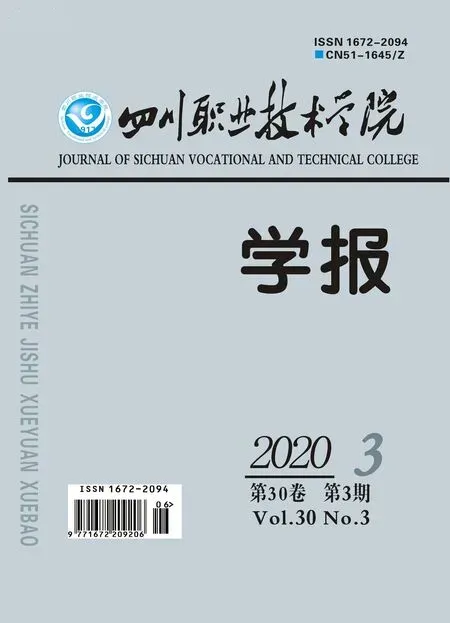“楚之骚文,矩式周人”辨析
韩明亮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97)
一、概念辨析
“矩式”这个词出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其文曰:“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1]520。在说明“矩式”的含义之前,我们先要来探究“楚之骚文”(以下简称楚骚)和“周人”的所指。
(一)“楚骚”辨析
楚骚的辨析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楚骚和楚辞的关系;第二,楚骚具体指哪些作品;第三,为何用楚骚之名。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白楚辞的内涵。其实学界对此存在一些概念不清的嫌疑。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所载:“屈原怀忠之性,而被谗邪,伤君暗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2]301-302
可见,王逸对于楚辞的范围理解为屈宋之作加上刘、王等汉代文人的作品,在其《楚辞章句》中也的确包含汉人作品。周勋初对于“骚文”的注释是“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3]504,又认为刘勰认同南北朝学术界的共同认识,即《楚辞》主要指“王逸编纂的以屈原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3]102。但是,我们会发现,这种认识和《文心雕龙》的文本发生了多处矛盾。
第一处矛盾,“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如果楚骚包含汉代的部分学习屈宋之作的文章,那么“汉之赋颂”又如何区别于楚骚呢?第二处矛盾,《辨骚》篇对于楚辞的界定是如下文章:《骚经》、《九章》、《九歌》、《九辩》、《远游》、《天问》、《招魂》、《大招》、《卜居》和《渔父》。据王逸的说法,这些文章全都是屈宋所作。而且《辨骚》篇在谈王褒的《九怀》时说“遽蹑其迹”,后面又说“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3]90。可见刘勰对于楚辞和汉代诸人的模拟之作是有着鲜明的区分意识的。更进一步说,刘勰所说的楚辞和王逸的楚辞具体指代范围不同。第三处矛盾,《时序》篇指出“爰自汉室,迄至成、衰,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3]685-686。这里刘勰再一次明白指出楚辞和汉代文章泾渭分明。
可见,刘勰认为的楚辞是指屈宋之作,而非包含部分汉代的模拟文章。把楚辞范围扩大化始于王逸的《楚辞章句·九辩序》,也就是“屈原怀忠之性……故号为楚词”。其《楚辞章句》也收录了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即庄忌,为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以及王逸的《九思》。后世的编排变化被清代的毛表一一道明。“其《九思》一篇,晁补之以为不类前人诸作,改入续楚辞,而紫阳(朱熹)并谓《七谏》、《九叹》、《九怀》、《九思》平缓而不深切,尽删去之。特增贾长沙二赋,则非复旧观矣。洪氏合新旧本为篇第,一无去取,学者得紫阳而究其意指,更得洪氏而溯其源流”[2]574-575。在朱熹看来,只有屈原之作才是可归入离骚,至于宋玉、景差、贾谊、庄忌等人之作均为续离骚[4]。而洪兴祖的编排收入了汉人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楚辞就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类书。是否正因为此,目录学书籍的集部总会设立楚辞类呢?这不仅仅是向《汉书·艺文志》致敬,更有其学理上的考量。当然,《汉书·艺文志》本就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会专门把屈原赋二十五篇单独列出。而刘勰是站在考察不同时代文学的立场上,因此他把楚辞定位屈宋之作,而非朱熹那样只选择屈原作品。
同时,刘勰笔下的楚辞和楚骚是一回事。很明显的例子是《辨骚》篇,直接就说“固知楚辞者”。刘勰的对楚辞的界定学习刘向。《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开篇就是屈原赋二十五篇[5]。而刘勰就把楚辞或者说楚骚界定为这二十五篇。《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楚辞类小序指出:“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6]133可见,“楚骚”即是《楚辞》。之所以在《文心雕龙》书中,刘勰多次以“骚文”代指楚辞,黄侃先生认为是刘勰为了表达对屈平的尊敬之意[6]133。
(二)“周人”辨析
“楚之骚文,矩式周人”。这里的“周人”不妨称为“周文”,指的是一个朝代的文学,但是楚骚也并非周代任何一种文学都去“矩式”。因此,又要把“周文”的概念限定为对楚骚有影响的文学样式。《辨骚》篇云:“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1]47。又云:“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1]46。可见刘勰认为《楚辞》对于《诗经》有着深刻的学习和继承。
同时,楚骚“矩式”的周文不仅仅是《诗经》。《祝盟》篇指出:“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者也”[1]176。而这里的祝辞便是源于《大戴礼记》和《仪礼》[1]181-182。再者,《辨骚》篇也提到“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6]146。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序》上说:“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6]147。可见这里“周人”不仅仅是《诗经》,还有《礼记》、《仪礼》和《尚书》等文献。但是,《通变》篇对于商周作品的概括是“丽而雅”[3]503。而能够代表周代雅丽文学风格的莫过于《诗经》。从逻辑上说,《诗经》属于周文,那么,楚辞矩式《诗经》自然也是成立的了。
(三)“矩式”辨析
《说文解字注》说到:“矩,法也,常也”[7]201。又说:“用矩之道。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湥。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按规矩二字犹言法度。古不分别”[7]201。又说:“式,法也”[7]201。可见“矩式”在这里是说楚骚以周人为法,具体指以《诗经》为榜样。《楚辞》对于《诗经》的学习策略被刘勰概括为“四同四异”①。“四同四异”告诉我们,刘勰认为楚辞学习《诗经》的方式是继承和创新并存,这一点,也就是刘勰理解的“矩式”之意。
正如《物色》篇说:“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凡攡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1]694。又云“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1]694。在对于颜色词的使用上,楚骚继承了《诗经》的发现,不多次使用同样的颜色词,以避免令读者厌烦的阅读感受。对情貌的塑造上,楚骚发扬了楚人的浪漫气息,“重沓舒状,葳蕤群积”,如此,超越了《诗经》的表现方式,而独创一条更加适合自身文气的描写方式。可见,在模物图貌上,“矩式”是继承和创新并用,而继承与创新的取舍便在于是否更适合自身的文学审美。也可以从中看出,《楚辞》对于《诗经》的学习带有鲜明的主体意识,是建立在自身风格基础上的主动学习。
二、《楚辞》“矩式”《诗经》的具体体现
在《楚辞》“矩式”《诗经》这一问题上,刘勰早已在《辨骚》篇说的很清楚了,即上文提到的“四同四异”。结合这些,我们通过分析《文心雕龙》全书对于《楚辞》学习《诗经》的相关论述,得出更丰富、更系统的“矩式”层面。
(一)表现方式上的“矩式”
分析楚骚在表现方式上对《诗经》的“矩式”,用《辨骚》篇中的一句话总结最是恰当:“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1]47。刘勰在这方面的描述可以归纳为比兴之用、夸饰之用、模物图貌、用事之法、章句之别这五点,以下分别论之。
《比兴》篇云:“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1]602。这句话道出了比兴的三个条件,首先是政治黑暗,即“楚襄信谗”;其次是有着心忧天下的忠臣,即“三闾忠烈”;最后是有着传统的借鉴,即“依《诗》制《骚》”,如此共同促成了一个结果——“讽兼‘比’、‘兴’”,那么楚骚中比兴手法的具体表现是怎样的呢?《辨骚》篇云:“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1]46。
夸饰手法并非是楚骚的首创。刘勰认为,自《诗经》便有文过其实的表现。《夸饰》篇云:“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1]608。而楚骚只是基于楚地的风貌和神话传统加以发扬。故《夸饰》篇又云:“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1]608。夸饰的表现就是在楚骚中充满着奇异的神话形象和不合正史的故事传说。正如《辨骚》篇云:“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1]46-47。
在模物图貌上也可看出“矩式”。论述如上文。
再说用事之法。《事类》篇云:“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1]615。朱星认为,刘勰这里所说的引事是广义的用事,广义的用事包括引事、引喻,而狭义的用事即用故事来代自己说的话,是魏晋之后的事[6]1413-1414。这里的意思是说,屈宋以不违《诗经》的立义为准则,文辞间常有用典,但这种典故只是事典,而非语典。
在章句上,《诗经》虽以四言为本,但也已经出现了其他句法。《修辞鉴衡》上说:“诗者,始于舜皋之賡歌,三代列国,风雅继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于此。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归之类。四字句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之类;五字句若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类;七字句若交交黄鸟止于棘之类,八字句若十月之交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类。汉魏以降。述作相望”[8]。楚骚在这一点更近一步。《章句》篇云:“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1]571。而且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楚骚不仅让一句的字数变得更加自由,而且积极利用语气助词“兮”。《章句》篇说:“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1]572。《诗经》的句法把“兮”看作是句限(固定字数的一句话)中的一环,而楚辞把“兮”用于句限之外,这样便大大增加了“兮”的自由性和句法的自由性。
(二)文体上的“矩式”
在文体上,楚骚“继轨”了《诗经》“六义”中的赋和颂。首先说赋。赋在《诗经》中历来被认为是一种表现手法,而到了汉代就成为了一种被士大夫广为使用的文体。《诠赋》篇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1]134。这中间的变化原因就在于楚骚。
从历史演变来看,楚骚是介于《诗经》和汉赋之间的文学样式。正如《诠赋》篇云:“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1]134。又云:“斯(楚骚)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1]134。一方面,楚骚已经超越了《诗经》中作为表现方式的赋,而进行了赋文体的写作实践,并且文学价值极高,即“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3]90。另一方面,楚骚时代并没有赋文体。楚骚的出现为赋文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汉人在楚骚基础上的仿作与对楚骚“奇”“丽”特点的学习,汉赋逐渐形成。因此,楚骚是赋文体的萌芽,但同时也是赋文学的巅峰。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对于赋的分类,屈子之赋赫然处于赋文体的第一类。
同样,楚骚在颂文体上也有所突破。一方面,楚骚承袭了《诗经》中颂的旨归,即“美盛德之形容”[9]。《辨骚》篇云:“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1]46。正如屈原的《橘颂》,以南国之橘象征君子高洁的品质。另一方面,楚骚又扩大了颂的叙事范畴。《颂赞》篇云:“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乃覃及细物矣”[1]157。
(三)精神内涵上的“矩式”
精神内涵上的“矩式”依然是继承与创新并用。首先,楚骚继承了《诗经》的讽怨精神。《情采》篇云:“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1]538。可见,讽谏之意自《诗经》已然有之。那么楚骚是如何表现的呢?《辨骚》篇云:“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1]46,又云:“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恕之辞也”[1]46。这种“规讽之旨”和“忠恕之辞”正是契合着《诗经》的“美刺”精神。实如刘勰所言:“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1]65-66。其次,楚骚的精神内涵中又有着不同于《诗经》之处。《辨骚》篇云:“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1]47。
三、“矩式”观念的产生原因
刘勰认为,《楚辞》从多方面学习了《诗经》,而且这种学习并非模仿,而是一种继承与创新意识并存的学习方式。其产生原因可以从三个视角加以探究。
(一)《诗经》和《楚辞》的产生时空
刘勰《物色》篇说:“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695。《辨骚》篇也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1]45。这种文学地理学的观念可见在刘勰那里已见端倪。刘勰认为,《楚辞》在依托楚地人情风貌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学习《诗经》。这种学习既没有抑制自身诡谲富丽的想象优势,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净化了内在的情志,使之“不失其贞”,“不坠其实”。
(二)“矩式”话语的存在语境
“矩式”观念是组成通变思想的关键一步。《文心雕龙·通变》篇:“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1]520。“矩式”和“影写”、“顾慕”以及“瞻望”都是不同的。“影写”显得太近,学到形似,却失去了自己的特色,“顾慕”和“瞻望”又显得太远,只能想望当年的风采,却不能走进以沉潜其中。唯有“矩式”是最佳的学习方式,也成就了楚辞能够达到“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3]82的高度。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句话推导刘勰对于“矩式”的认识。“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1]519。这段话就是“矩式”的纲领,即学其“体”,变其“数”。“矩式”首先是一种学习,即“体必资于故实”。对于先前的文体之法,楚骚采取的是开放的学习态度,其次,这种学习并不是模仿,也就是“数必酌于新声”,即楚骚是在以保持楚地人情风貌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归纳其来,通变是一种方法论,矩式是在这种方法论指导下形成的的最佳学习方式。如果没有矩式,通变将显得没有说服力,将变成空中楼阁。楚辞对于《诗经》的正确学习,给通变理论留下了一个历史的榜样。
(三)刘勰时代的文风影响
刘勰认为当时文坛学习风气和创作风气都有问题。周勋初认为当时文坛存在两种学习风气,一是“裴子野、刘之遴等人守旧”之风,二是“徐陵、庾信等人的趋新”之风。又认为,刘勰相比较守旧者,更重视“变”,相比较趋新者,更重视“通”。总之,其裁夺准则是“折衷”[3]501。
放诸语境,我们发现刘勰在《通变》篇对于当时的学习风气是这样总结:“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也就是说,当时文坛有刻意模拟之风,而且其模拟的对象是时文,而非汉代文章。其“矩式”就是给这两个膏肓之疾开出的一剂药方。对于刻意模拟,“矩式”要求带有主体意识地学习;对于竞今疏古,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详细剖析了楚辞如何学习《诗经》,给人以示范。
《序志》篇有言:“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可见,在刘勰看来,当时文坛创作风气是文风浮华,文体解散。而刘勰对于这种矩式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能够让当时文人能够明白取法之道,应该如何看待《楚辞》,而不坠于汉赋的样子。刘勰详尽地展示了《楚辞》如何创造性地学习《诗经》,以启发同时代的文士应该如何学习《楚辞》,又如何像《楚辞》那样学习《诗经》。
结语
“矩式”是一种主动地学习,楚骚是在保持楚地人情风貌的基础上学习《诗经》。《辨骚》篇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1]45。楚骚之“奇”就在于能够充分地发挥楚人诡谲富丽的想象,而又不逾风雅,思想纯正。
因此,这种“矩式”对于楚国文学是一种近乎“雅化”的过程,实现了“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1]45。风雅传统节制了楚地的感情之过度,而代以文字间讽怨精神的深沉。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这种“矩式”给《诗经》以来的正统文学带来了更大的创造力,既保存了精神内核,同时又在文学表现力上达到了崭新的高度。
注释:
①四同四异指“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恕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文心雕龙·辨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