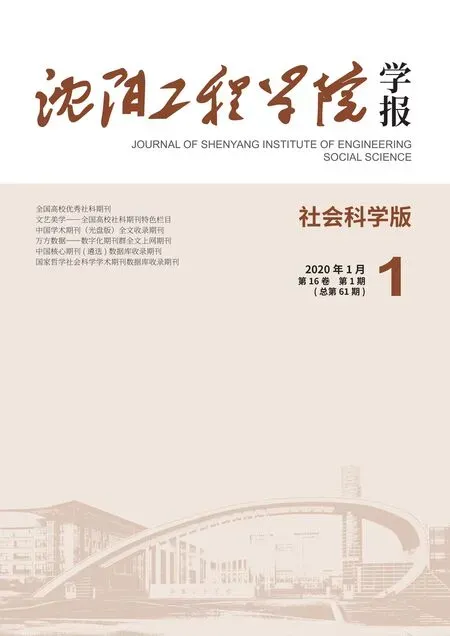新中国70年短篇小说中的国家形象
高雨婷,吴玉杰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形象”即对事物的一种“评价”“印象”“认识”,文学作品中的国家形象包括作品的题材、人物、创作思想等“唤起人们对一个国家社会生活的印象、评价和想象”[1]。根据文学自身的间接性特点,作品中的国家形象蕴含两个层面。一方面,作品中呈现出的国家形象基于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现实成就;另一方面,国家形象是由创作主体通过文学作品“重塑”得出的,在“重塑”中寄寓了对国家未来的向往与价值追求[2]。
短篇小说中的国家形象可以从题材、人物和创作主体的创作思想三个角度进行考查,根据小说中描绘的社会生活图景,能够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形象大致特点进行基本概括。
一、当代短篇小说中的社会生活史
小说的题材、人物、创作思想都具有在勾勒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史的同时,塑造和揭示国家形象的作用。三者如同三个不同层面构成的同心圆,小说题材居于外沿,人物形象居于中间,而创作思想则居于内在层次,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互为补充,共同完成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
1.短篇小说的题材能够反映国家的发展变革
以整体性眼光观照当代文学,文学题材总体上呈现出“动态的阶段性特征”[3]256。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矛盾,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描绘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瑰丽画卷的角度来看,新中国短篇小说题材的审美选择中,都镌刻着不同时代社会变革的烙印。
十七年文学中的城乡社会生活可以通过表现“现实生活及其矛盾冲突运动”的题材得到反映。描写农村现实生活的文学创作,如《“锻炼锻炼”》(赵树理)等,大体上“与社会政治生活同步发展”,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农民的解放,以及农村社会中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引发的不同阶级、不同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城市工业建设题材在这一时期相对于农村题材而言稍显薄弱,但也产生了一批以工厂生活为背景反映工业建设中的社会问题的短篇作品,如《改选》(李国文)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可以通过表现“现实改革”的题材得到刻画。在以农村改革为背景的作品中,《陈奂生上城》(高晓声)刻画了农民维持基本生活和生计要求的实现,而《乡场上》(何士光)等作品则在物质解放之外揭示了农民精神解放的迫切需要。在反映工业及城市改革题材中,则是以《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为开端,出现了一批洞察深切、影响深厚的作品。
2.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能够折射国家精神变迁
人物形象是国家形象最直接的构成与体现,可以说,“中国当代文艺已经形成了面向主流的积极向上精神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是一种道德积累和对文化的综合展示,而且还能够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来激励人心改造社会”[4]。
十七年文学中的文学形象,主要以英雄形象为代表,大多带有时代赋予的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烙印。从《草原上》(杨平)中为保护公共财产献出生命的教师刘昶生,到典型的“农村新女性”李双双,这些人物身上“折射出了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那种凛然的、庄重的、崇高的国家形象”。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人物从思想认识到道德观念再到行为逻辑,都成为塑造当时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因此,在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方面,十七年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更能折射出特定阶段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利益与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性的政治斗争领域的侧面反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形象不再局限于工农兵英雄形象走向多样化发展。从文学形象的身份类型来看,领袖形象、军人与知识分子等形象令新时期人物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丰富。在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方面,相同类型下的人物之间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性格特色,人物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与概括程度加深。无论是张贤亮《灵与肉》中兼具“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许灵均,还是高晓声笔下憨直、朴实的农民陈奂生,人物形象中对于人的情感与灵魂内在冲突的刻画,折射出新时期“人的自觉意识的觉醒”,人的自我价值开始得到确证。
3.小说中的创作思想能够对创作实践产生内在影响
无论是作品题材还是人物形象,都离不开创作思想的内在影响。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创作思想可以看作文学作品反映的客观的对象世界与创作者主观精神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的综合。不同时期的创作思想,都在以内在、隐含的方式联结、建构现实社会与文学审美空间。
十七年文学“以颂歌作为基本格调”[3]359。五十年代前期的文学创作体现出单纯明快的政治热情,例如《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时代变革与思想解放,“人的人文价值”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创作思想。在表现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方面,这一时期的人文价值主题同十七年文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但也蕴含着阶级关系之外更为广泛深刻的内涵。这一时期的创作在表现历史反思与人性关怀时,将人放在中心位置进行审视,在对人文价值的重新发掘中探索个人、历史、现实社会的复杂真实性,例如《伤痕》(卢新华)、《班主任》(刘心武)等。
二、当代短篇小说中的新中国形象
纵览新中国七十年来的短篇小说,通过对小说题材、典型人物形象与创作思想的分析,可以概括出三类主要的新中国国家形象。这些形象或是直接反映了新中国不同时期社会历史变革,或是寄寓了作家自身对于新中国的美好向往与希冀。
1.小说中展现了团结统一、充满凝聚力的国家形象
新中国七十年的短篇小说中,表现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充满强大民族凝聚力的国家形象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表现祖国统一方面,台湾作家陈映真的小说《将军族》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在对台湾的退伍老兵与台湾漂泊的一名底层妓女之间的爱情进行刻画的同时,传递了渴望海峡两岸团结统一的主题。正如作家陈映真本人所说:“一个分离和对峙的民族是一个残缺和悲伤的民族,作为一个作家,我对此十分敏感,一直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反映这种分离造成的痛苦。”“我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够重新团结。”这种真诚的中国情结,始终贯穿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之中,寄寓了作家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强烈呼唤。
在表现民族团结方面,高缨在五十年代创作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小说通过描写达吉与她的汉族生父与彝族养父三人的纠葛,揭露了彝族地区旧社会中人民受到的苦难与压迫,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凉山人民的解放,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5]。正如高缨所说,他的创作初衷来自他对当时社会生活领域的深刻变革的亲身感触,在当时改革基本完成的背景下,一些地区依旧存在着民族隔阂,因此他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激发下,通过这篇小说表现国家在民族团结方面的努力与成果[6]。
2.小说中展现了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国家形象
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始终贯穿在描写新中国的文学作品之中。以作家方之在六十年代初创作的短篇小说《出山》为例,小说中的主人公王如海身上凝结着热烈跳动的时代脉搏。在决心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贫困现状的小王庄,王如海被村民们一致推选出来做生产队长,他深思熟虑、周密妥帖的脱贫计划,以身作则、勇于担当的奋斗精神,使他成为富有代表性的农村新人形象。他本人乃至全家、全庄人们的进取意识和拼搏精神,都可以看作是当时伟大祖国的生动缩影。
七十年代末,《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的形象在当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小说发表之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纷纷将乔光朴誉为实现“四化”的先进带头人物。乔光朴精神之中始终保有的革命热情与“拼命精神”,使他不仅能够紧跟时代变革的步伐,还成为了推动时代前进的进步力量。这种“热烈、激昂、燃烧着生命”的奋斗者形象,适应了时代的迫切需要,也反映了国家的积极面貌。
从肖像来看,乔光朴有着“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双眼,颧骨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润脸”,显示出他作为“力量的化身”刻苦肯干又兼具改革雄心的特质。从乔光朴在机电厂推行改革的一系列举措来看,上任之初,他首先处理的是自己与工程师童贞的关系问题。乔光朴在童贞全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在厂中宣布二人已经结婚,即便他们会因此遭受更多不实的非议,将这次“先斩后奏”的婚姻作为自己在厂中开拓现代化生产方式变革新局面的序幕。身体政治的相互转换与紧密联结超越了个体身份命运同国家民族之间存在的对立与距离。上任以后,乔光朴充分展现了有令必行、敢作敢为的过人素质,“他说一不二,敢拍板也敢负责,许了愿必还。他说建幼儿园,一座别致的幼儿园小楼已经竣工。他说全面完成任务就实行物质奖励,八月份电机厂工人第一次拿到了奖金”。而最为关键的是,具备苏联留学背景的乔光朴凭借专业的技术知识与先进的管理方式,通过实行考评机制与整顿裁减管理机构,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实现了技术革新,更是在现代化探索中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获得了以霍大道为代表的上级的认可与支持。
小说中乔光朴作为新时期文学中的典型形象,寄托了当时“强国梦想”背景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想,也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路线方针的热烈回应。乔光朴思想精神中表现出的,正是整个民族的拼搏精神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同个体的价值命运紧密结合的典型。
3.小说中展现了勇于变革、善于反思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的塑造,“不仅是一个今天中国形象的呈现,而且是一个包括对整个中国历史在内的中国形象的重释”[7]。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文学作品对于国家在曲折前行的历程中展现出的变革精神与反思意识进行了充分的描写与刻画。
在全国首届短篇小说评奖中,《班主任》荣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榜首。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班主任》在小说中对生活现实进行了理性的审视,重拾起现代性思想启蒙的主题,充分肯定了知识与理性的宝贵价值,在反思中展现了新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层面的新气象。小说的思想内核主要围绕如何教育和改造问题青年宋宝琦展开,班主任张俊石老师作为叙述者反思的声音,连缀起四种不同的认识态度。其中,文章开篇的曹书记将教育与改造宋宝琦的任务交给张老师,并且向他提出了一个有意味的问题,即是否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与之朝夕相处,而小说结尾处张老师回忆中曹书记支部会议上的发言“现在,是真格儿按毛主席的思想体系搞教育的时候了”便是给出了一种肯定的回答。可以说,曹书记是当时教育思想层面党的先进方向的代表。数学教师尹老师与班级里一部分反对宋宝琦到来的女同学可以看作是不够清醒、尚存犹疑的群众意识的具体显现,但张老师的言说与结合先进著作的教育最终使得他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认识得以提高。满怀热忱但思想充满僵化色彩的团支书谢惠敏表现了亟需变革的“被愚弄的意识”与思想的盲从,而作为对照的石红及其父母则可以看作是清醒的意识与独立思维的代表。整部作品不仅敏锐传递了智性的反思与新时期带有启蒙色彩的呼唤,还以“春”的意象贯穿其中,刻画出中国新时期的社会气象。“1977年美好、幸福的春天”不仅带来了“迎向更深刻的斗争,付出更艰苦的劳动”的新的要求,更是新时期充满希望的具象象征。
总而言之,通过对新中国70年来的短篇小说文本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在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书写中概括出团结统一、充满凝聚力的大国形象;在农村新人与改革先锋身上感受到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在思想启蒙中体味到新时期勇于变革、善于反思的时代风貌。
三、国家形象的塑造方式
短篇小说基于自身的文体特点,往往采用独特的方式对国家形象进行塑造。考察分析短篇小说中国家形象的塑造方式,有助于进一步发掘国家形象的内在蕴含,同时能够在对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分析中拓宽对于国家形象的阐释角度。
1.个人化、诗意化的叙事方式对国家形象的塑造
相对于长篇小说能够在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中完成对国家形象的建构,短篇小说中的国家形象塑造常常渗透在个人化与日常化的叙事中。这种叙事方式一方面表现为小说中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个人主体性的张扬。以铁凝创作的小说为例,小说中以细腻入微的笔调刻画了生长在台儿沟的姑娘香雪个人意识的逐渐觉醒,继而反映了“启蒙思想”在当时乡村中的萌芽。火车每天停驻的那一分钟令香雪和其他农村姑娘与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微妙的联结,而“铅笔盒”则唤起了香雪对于台儿沟外面的世界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想象。即便尚未真正地接触到向往中的外部世界,但换来了“铅笔盒”的香雪却增添了难以压抑的活力与力量。个人意识的觉醒使得香雪在发现农村与城市现代文明之间的联结的时候,表现出一种“时代精神的美”,在历史的开裂处展现出对“现代化”纯真朴素的强烈渴望[8]。
而另一方面,新时期初张洁、林斤澜等作家的创作也为国家形象的塑造增添了一抹诗意的色彩。小说以诗意的笔调,在以小见大的构思中扩大了小说的社会审美空间与历史内涵。张洁在197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以抒情的笔调,表现了作家对美好纯真的人性的褒扬与守护,寄托了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代背景下的期盼和隐喻,以“向前看”的乐观姿态在促进历史与未来的和解中展现了文学作品疗愈的作用。从审美空间设置来看,小说题目中的“森林”承载着深厚的意蕴。对于主人公孙长宁而言,唯美自由的森林是他无拘无束的“乐园”,但同时也寓指他处于蒙昧状态下的精神世界。而对于孙长宁的音乐启蒙导师梁启明而言,森林则体现出“民间”与“人民”价值观念与道德伦理对他的接纳。“从森林里”走来的孙长宁的目的地,在小说中被设置为“北京”。梁启明在遗嘱中要孙长宁“到北京去”,“北京”作为国家光明和前途的象征由此得到凸显。而作为一篇“清新而细腻”的作品,从抒情风格来看,小说以诗性的语言风格和景观描写传递出一种“新生的喜悦”,孙长宁最终延续了梁启明音乐上的才华,继承了他服务人民的创作理想,见证并投身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小说中,孙长宁以“温暖”表达了自己对新时期国家的赞美。
2.创作主体情感经验对国家形象塑造的正向影响
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对新中国国家形象的想象与刻画是国家形象塑造的基本方式,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作家们的创作思想与主体情感都会对国家形象的塑造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创作实践中,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的情感经验能够影响其对创作对象与表达方式的选择。以表现新中国乡土社会生活的创作为例,相当一部分的当代乡土作家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乡土情结”[9],这种乡土生活与乡村经验带来的情感积淀与情感指向,在他们以文学创作反映国家形象时能够发挥深刻的影响作用,促使他们将关注的视线投向乡村的社会生活变迁,描摹不同时期乡土世界的文化精神。在创作实践中,周立波、高晓声、马烽等作家的创作都继承了前代乡土作家的写实风格,在创作中拓展社会生活描写的深度与广度,在凸显历史纵深感的同时,对乡土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揭示,继而寻求进一步的变革解放。此外,植根于不同地域的乡土写作也使得作家的创作带上了不同的地方文化色彩,展现出新中国多样化的乡村生活图景。例如,韩少功创作的带有“文化寻根”色彩的小说侧面展示了独具特色的荆楚文化风习,“山药蛋派”的小说创作深深植根于山西特色的文化氛围,而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则在勾勒东北地区的世俗民情中体现出厚重与活力。
同样,短篇小说在对不同时代社会生活变革的刻画中将国家形象定格成一幅幅“立体交叉桥上的剪影”。作家的描写勾勒从来离不开现实的厚重土壤,创作中对于真实性的秉承也是把握时代脉搏的应有之义。党中央、国务院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对一百名同志授予“改革先锋”的称号,其中一位便是“改革文学”的缔造者蒋子龙。改革开放以后,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对重型电机厂顺应时代潮流,推行生产与制度改革进行了生动翔实的描摹,而这种对于工业改革准确的体察与把握,源于作家当时面临的与“乔厂长”极为相似的现实境遇。当时的蒋子龙正在天津重机厂锻压车间担任车间主任,因此在写作过程中融入了现实的工作经验与经年的思考感悟,正如作家所言,“乔厂长”实际上是位“不请自来”的人物形象。在之后的不懈创作中,这种对现实的持续关注,以及对真实性呈现的创作原则,使得蒋子龙的作品成为反映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体制改革与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无论是工业题材、城市题材还是农村题材,都在虚构的一个个故事中真实地以文字记录下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保持真情,保持思想,淬炼语言”成为每一位作家在进行国家形象刻画时都需要注重的创作箴言。
总之,在承担叙事功能层面,短篇小说在“以小见大”中反映出广阔的国家形象内涵,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寄寓了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诗化表达,将对现实生活的赞美与对历史过往的追述交织在一起,真实地描绘了健康、美好的人性,在现代性的视阈下完成对国家形象的塑造。
四、国家形象塑造的价值与思考
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中,愈发成为值得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既包含着深厚的文化价值,也具有现实的迫切需要。面对当前文学创作中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局限,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新时代大国形象需要不断进行反思与创新。
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发展,这便对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尤其是文化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在思想价值方面,以文学作品作为载体进行国家形象的建构,反映新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塑造饱含时代精神的典型社会主义建设者形象,是文化建设的关键部分,也是充分发扬和彰显人民在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过程中主体作用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随着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文学作品成为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因此,文学作品对于国家形象的国际塑造与交流传播,也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在审美价值方面,从本质上看,文学作品中的国家形象凝结着创作主体生活日常中的审美感受与审美追求,是作家审美判断与审美趣味的外化。创作主体在对审美对象进行选择与褒贬中,完成对于当代中国的审美建构。在反映国家形象的作品中,既能发现具有文化价值的地域描写,也能够在变迁中体察日常叙事中包含的诗意与厚重的文化积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新的阶段,讲好“中国故事”,提升话语自信愈发成为当前的一项关键任务。早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便强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今后的工作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十九大报告中则进一步强调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意义,并提出了进一步的具体要求,即“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在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塑造国家形象时,一方面需要作家立足现实,在追求真实性的基础上,注重发挥批判意识与革新意识。在创作中既注重对新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刻画,也着眼于在问题的揭示中表现对新中国未来的期许。而另一方面,面对西方“他者”眼光的审视,中国的文学创作在表达自身时更需要坚持主体意识,牢牢把握主体话语地位,在客观的书写中构建新时代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