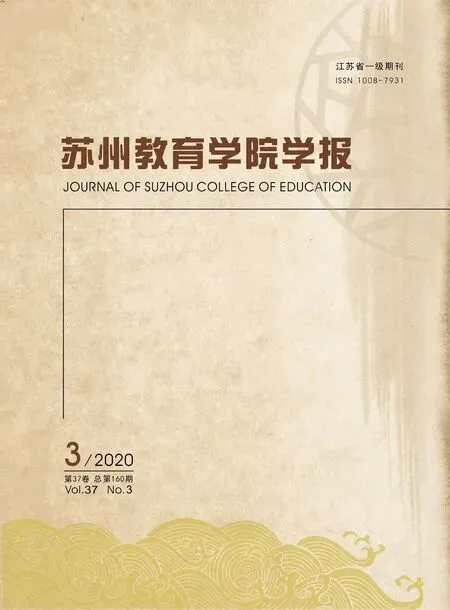王度庐“鹤—铁”系列小说中侠客主体意识的塑造
党雪晴
(香港大学 中文学院,香港 999077)
武侠小说在民国阅读者众多,乃通俗小说之大观。作为“北派五大家”①叶洪生在《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中首次提出“北派五大家”之概念,即李寿民、宫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为学界所认可。但叶洪生也在注释中指出,此概念衍生自张赣生的《中国武侠小说的形成与流变》一文。参见叶洪生:《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代表人物,王度庐“悲剧侠情”的写法被看作民国武侠创作的最高成就之一,而“鹤—铁”系列尤被认为是其武侠创作的巅峰。该系列有五部小说,合约270万字,情节先后承接,共同刻画出历时几代人、遍布大江南北的完整江湖。1938年,《宝剑金钗记》于《青岛新民报》上连载,拉开了“鹤—铁”系列创作的序幕;随后,《剑气珠光录》《舞鹤鸣鸾记》(后单行本更名《鹤惊昆仑》)《卧虎藏龙传》先后载毕;1944年初,《铁骑银瓶传》于《青岛大新民报》连载完毕,“鹤—铁”系列终于全部完成。②本文均采用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书名也遵从单行本—《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本文的讨论基于文本分析法,不涉及版本目录学讨论。
“鹤—铁”系列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始终不乏关注,但无论是对系列小说的探讨,还是在此基础上对王度庐创作风格的辨析,其落脚点往往集中在王度庐的满族身份上。如张菊玲在《“驱逐靼虏”之后—谈谈民国文坛三大满族小说家》[1]中,将王度庐与老舍、穆儒丐并列为民国满族小说家的代表。李宗昌的《简论著名满族作家王度庐》[2]和关纪新的《关于京旗作家王度庐》[3],将王度庐置于满族作家群的谱系中进行研究,继而探寻作为整体的满族作家所处的清末民初的复杂写作环境及其写作风格。张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亟待整合的三个板块—从具有三重身份的小说家王度庐谈起》[4]中,将王度庐作为打通文学史的典型个案来讨论,聚焦其少数民族作家、沦陷区作家和通俗作家的三重身份。研究者较多关注王度庐的这种外部身份,从民族文化角度阐释其作品的独特性,但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框定,也使得其作品的内部研究略显不足。即使聚焦作品,如张菊玲《侠女玉娇龙说:“我是旗人”—论王度庐“鹤—铁”系列小说中的清代旗人形象》[5]、刘大先《写在武侠边上—论王度庐“鹤—铁”系列小说》[6],仍然主要从其民族身份出发。正如刘大先所说,这些研究共同指向“王度庐小说是京旗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大众传媒融合的结晶,在满族文学系谱中占有重要地位”[6]。
相较之下,将王度庐置于通俗小说谱系中进行研究则薄弱很多。一方面,王度庐始终秉持现实武侠的写作,决不涉及剑仙,与想象瑰丽的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相比,似乎在传统武侠上没有明显突破;另一方面,王度庐的小说很少影射现实,与白羽擅摹世相的武侠相比,又似乎少了很多可探讨的空间。同样坚持将武侠世界置于真实世界中进行描摹,王度庐虽不像白羽那样将市民社会、底层规则融入武侠小说中去表现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偷拳》等作品,完全从镖局谋生、练武赚钱出发,颠覆了武侠世界的乌托邦,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很成熟,本文仅作涉及,不再展开讨论。,却建立了文本内部完整的逻辑与规则。如果说白羽是将侠客刻画成芸芸众生之不足道者,王度庐则仍然聚焦于作为传奇的侠客,通过情节解释行侠的自身逻辑,缔造了侠客出自市民阶层的朴素道德观,从而塑造了侠客的主体意识,有开创之功。在这个层面上,“鹤—铁”系列小说与新文学、新思潮也有最直接的交互,而不仅仅是迎合市民趣味的消遣之作。
综观《鹤惊昆仑》[7]、《宝剑金钗》[8]、《剑气珠光》[9]、《卧虎藏龙》[10]、《铁骑银瓶》[11]这五部小说,可以看出,在王度庐的小说创作中,对侠客个人生命意识与主体意识的探寻,逐渐代替了对“行侠”行为的聚焦,正因侠客主体意识的逐渐建构,情欲书写才在小说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乃至为王度庐赢得了“悲剧侠情派”的称号。侠客之主体意识的内涵为何?如何形成其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建立在何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侠客形象?与清代侠义小说及民初武侠相比,“鹤—铁”系列小说对侠客的身份有细致的规定,从职业身份、民族身份和性别身份等多个角度,试图解释侠客的行为。这种对行为逻辑的追求与探索,实际上完成了侠客主体意识的塑造。
一、镖头与盗匪:侠客职业身份的世俗化与阶层的固定
今人读武侠小说,往往认为武侠世界是与现实世界界限分明的桃花源,在这里,刑罚、道德、尊卑乃至经济来源皆有自己的规则,与真实世界相差甚远,这种想法并非无中生有。上溯至唐传奇,我们可以发现,从“侠”之观念进入虚构文学开始,就带有超越于现实世界的特征,如聂隐娘从师学艺,遁世五年;红线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但武侠小说与神魔小说毕竟不同,除了侠客的超人异禀之外,它所展现的毕竟是日常世界。只是当读者的目光聚焦于这个日常世界时,会惊奇地发觉这个世界不用为生计发愁,杀人不必受刑责,当权者对侠客都十分倚重。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武侠小说的虚幻性及由此带来的麻痹性才广受批评。“鹤—铁”系列小说的突破,首先在于它真正将侠客置于日常生活的规则之下。简言之,小说首先解决了江湖人的吃饭问题,赋予了他们正当的(未必是合法的)职业身份,从而赋予其行为以合理性。
综观“鹤—铁”系列小说,凭借技击能力谋生的侠客,无外乎两种身份:镖头与盗贼。之所以将这两种职业身份的设定看作是种突破,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武术被看作是养家糊口的技能,侠客凭武术获得经济自主权,进而获得人格自主权。在早期的侠客叙事中,许多侠客仅仅凭借个人的声望便能获得财富,如《史记》对朱家、郭解的描写。随着侠客形象进入虚构叙事性文学,像唐传奇中的《聂隐娘》《红线传》,以及清代《三侠五义》等作品,以武力傍身的人逐渐成为当权者的帮佣,通过食客的身份谋生。而在“鹤—铁”系列小说中,行侠的主要正当身份是镖头,也就是利用自己的技能(武术)做生意,属于市民阶层兴起后的正当职业。与贵族食客身份相比,镖头的职业身份是独立的。在这种设置下,侠客使用武力是为了做生意,也就是为了赚钱糊口,其中可能蕴含的价值意味被取消。因此侠客的行为获得了自由与自主权,情节的展开能够依托人物性格,侠客本人真正成为武侠小说的主角。
在《宝剑金钗》《剑气珠光》中,因为有了正当的职业,俞秀莲才能在未婚夫过世后避免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羞辱,通过走镖完成经济独立与人格独立,并在与李慕白的多次对话中完成对自己内在道德与情欲的升华。因为有了九华山卖桃的经济来源,李慕白才能从容拒绝铁小贝勒提供的护院工作,保持随时隐退江湖的能力,并在这个进退的过程中克服了自身的性格弱点。这种不再虚无缥缈的生活基础,展现了侠客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变化,沟通了江湖世界与市民阶层,使得武侠书写传递出更准确、更广泛的人类共情,从而传达了“鹤—铁”系列的审美品格。
第二,盗贼与镖头间形成对话,共同构筑了完整的江湖世界。民初武侠的写作,比起清代及之前已大大丰富,面向市民阶层的娱乐读物的定位,使其必然要搜集和展示奇闻轶事,这在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异人传》中尤为明显,其虽不像令作者蜚声的《江湖奇侠传》及后来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那样,建立了系统的、与现实有别的剑仙世界,却恰恰在传说与现实之间有微妙的平衡。但真正把绿林世界纳入江湖秩序中,展示其地位、行为和性格,从而作为整个江湖世界的组成部分,“鹤—铁”系列仍有开创之功。
在前代的叙事文学中,关于绿林世界的描写所在多有,《水浒传》可谓将绿林之江湖、人性之复杂写到极致。但“鹤—铁”系列的独特之处在于,绿林在这里并非作为官府的对立面而存在,这里的盗贼既没有梁山泊的浩大声势,也不完全是沿路抢劫、欺压良善的恶人,甚至不具有被逼落草的无奈。绿林完全是种职业选择,即使它是不合法的、被人摒弃的,卖武为生的人若不能找到镖店的营生,为生计所迫,仍然只能干起盗贼的生意。盗贼与镖头,作为两种主要的武人职业,共同构筑了形而下的世俗江湖。《鹤惊昆仑》中江小鹤学成归来,仍然向盗匪伍金彪寻求帮助;《铁骑银瓶》中韩铁芳与吴元猛虽假意相交,但也多次赞叹吴元猛是个有良心、是非分明的人。这些人虽然落草为寇,为法理道义所不容,并最终被翦除,但王度庐仍尽力呈现出他们多样化的日常生活,并未将其摒弃于正统江湖之外。这种设置已经带有“非道德”的倾向,并未囿于通俗小说简单的道德二分模式。
当然,“鹤—铁”系列五部曲中,描写得最深刻、最出神入化的盗贼,还是罗小虎。罗小虎与玉娇龙相遇时,身份是威震大漠的盗匪半天云。其实按他自己的剖白,做盗匪还不到一年,而根据身边唱曲的妇人评价:“罗大爷有钱,他并不是贼,他养着一千多匹马,他的人也很好,并不是恶人。”[10]214然而,短暂也好,收入正当也罢,都不能改变他的盗匪身份,也正是这个曾经的身份使得玉娇龙宁肯漂泊沙漠也不能与之结合,使得韩铁芳面对生身父亲却不欲相认。职业身份没有在文本之外规定罗小虎的行为,罗小虎的形象是丰满的,他善良、忠贞、坚强;可是职业身份在小说叙事内部却成了罗小虎毕生的枷锁,他解散山寨,贩马营生,乃至后来寻求做官,在道观中修行,都始终无法洗刷盗匪的身份,也始终无法从身份羞辱中走出来。玉娇龙的母亲临终嘱咐玉娇龙以门第为重,“罗小虎虽久已改了盗行,可到底还是强盗出身,她决不能作强盗妻子的”[10]700;韩铁芳最初听闻玉娇龙与罗小虎有情,便连玉娇龙也轻视,认为她不过是个盗妇。在“鹤—铁”系列小说中,盗匪身份一方面被江湖人所接受,另一方面又被轻视和侮辱,被预设成恶人。而随着情节的展开,真正的恶人可能来自正经的镖行,可能来自官府,绿林的身份预设被否定了,可是并不能被解除。
无论是有正当职业的镖头,或是流落绿林的盗匪,还是逢施舍度日的江湖客,他们共同展现出侠客群体作为社会阶层的下移,如前文所述,比起朱家、郭解的一呼百应,聂隐娘、红线的甚为节度使所倚重,“鹤—铁”系列小说聚焦的侠客靠卖武为生,受制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规则。《宝剑金钗》中,即使如李慕白这样在书中几无败绩的大侠客,内务府小吏德五与其交往,也是知遇之恩;而到《剑气珠光》中,当铁小贝勒在贵族身份之外又获得官职后,李慕白干脆不方便去拜访他。诚然,“鹤—铁”系列的大量篇幅仍然承继了《三侠五义》中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模式,但综观全书,这种除暴安良的故事更像主角行为的点缀,放在书中显得拖沓,从书中拿去也不影响主要情节的发展与全书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王度庐的确将侠客从行侠仗义的行为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以微妙、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独立、自由并仍在成长的性格特质。侠客形象的塑造不再是模式化和工具化的,而就像其他职业身份的人物一样,有共通的人类命运与悲欢。所谓言“情”,言的正是在卖武求生的过程中个人心性的变化。而这种对模式化的突破,正是武侠书写超越商品化特质而发展出审美特色的关键。
二、“京城”侠客:民族身份的凸显与小说的风俗趣味
王度庐是京旗作家,出身于一个贫寒的旗人家庭。“鹤—铁”系列描写了许多旗人的生活习惯,为小说增加了民俗学的价值和语言上的美感,而将飞檐走壁的故事安排在京城,也为江湖世界的世俗化提供了具体的背景,增加了小说的可信度,为通俗小说提供了更强的代入感。更重要的是,通过描写当时汉人社会与旗人社会的价值观及生活模式的差异,将不同民族身份的侠客区别开来,使玉娇龙、德啸峰诸旗人的面目更清晰,他们的生活经历投射在侠客身份上,成为其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宝剑金钗》从李慕白去京城谋事开始,写了北京城的烟花柳巷、茶馆戏台,也写了北京城的贝勒侯爷、高官巨商、贩夫走卒等各色人物,这些人物因个人的利益或情感与侠客发生种种关系,进而提供了从世俗生活观照江湖世界的角度。如德啸峰与李慕白去燕喜堂听戏,“才进了戏园门首,就见这里蹲着几个人,全都穿着灰布短裤褂,抹着一脸的鼻烟,象是北京城的流氓地痞;一见德啸峰来了,就齐都站起身来请安,笑着说:‘德五爷您好呀!’”[8]121。这段描写干净利落地展示了德啸峰在北京的交游圈子和势力,细节之丰富,可以匹敌北京本土作家老舍。又如写德啸峰的交游,“此时又有两个身穿绸裤褂,提着水烟袋,摇着绢扇的人,过来跟德啸峰谈了半天话”[8]122;写德啸峰的势头,“这里德啸峰向旁边看着的人抱拳,说:‘耽误诸位听戏!’这些人七嘴八舌地都说是那个人自找苦吃;德五爷本来很给他面子,他却不识抬举,把德五爷招恼了”[8]125-126,都是惟妙惟肖。这个在京城很有势力的德啸峰,武功却很普通,从书中可以看出,他的势力既不来自财产、官职,也不来自武功,而仅仅来自他因旗人身份而带来的贵族人脉和他慷慨好交游的性格。而且,这位从现代读者的眼光看来颇似地头蛇的德啸峰,在书中却完全是正面形象。德啸峰慷慨好义,遵纪守法,不但出于义愤收容了杨小姑娘,而且毫无门第观念,把她纳为儿媳。他的爱好交游、不务正业,与清朝八旗子弟只能当兵的规定是分不开的,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旗人在北京的生活状态。而德啸峰所展现的慷慨好义,来自他的贵族身份所提供的便利,他的环境和身份共同塑造了他最终展现出的形象,使得人物性格有脉络可循。
此外,小说中也有些细节描写,深刻揭示出旗人的生活方式如何影响或表现侠客的日常心理与行为。如玉娇龙的发髻是造成她心绪不佳的重要原因:“按照旗人的规矩,凡是姑娘在十三四岁时,便要留满了发,而一到十七八岁就要梳头,一梳上了头,就可以有人来提亲了。这种头与妇人的发髻无异,只是鬓角稍微有些差别,在家中时是挽着很高的云髻,出外会亲友,赴宴会,游玩等等,还必要戴上那黑缎子扎成了‘两板头’。一个旗人的女子到了这时期,那就如同是一朵花苞已然开放,所等待的是人的折取了。”[10]159-160这种对旗人生活方式的展现,给小说增加了生动与趣味,也更好地塑造了人物。细节的丰富和旗人生活方式的呈现,为紧张的江湖打斗加入了生活化的元素,更深层地将侠客生活融入现实世界。侠客的所作所为不再是为了除暴安良,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爱情、友谊乃至游玩的乐趣。这种生活化的描写为侠客行为提供了方方面面的参照,使侠客形象更丰富、更立体,而非仅仅作为打斗的符号。
除了对京城日常生活的描写之外,“鹤—铁”系列中有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细节—女性的缠足与放足。满清入关后,保留了汉人女子缠足的恶习。在《宝剑金钗》中可以看到,缠足本身并未被施加价值评判,俞秀莲虽然缠足,仍然单骑双刀,走遍大江南北,但女侠缠足的意象实在是充满了反讽。《卧虎藏龙》开篇写杨小姑娘出嫁之后,“放了足,换了旗装”[10]1,后面多次写杨小姑娘虽然放足,却没有放全,在路上引人注目。俞秀莲与玉娇龙初次相见,也是凭天足推测她是旗人,“对方却用脚蹬住,倒是只大脚”[10]118。之后玉娇龙出门行走,也是因未缠足而屡次被人怀疑身份。虽然王度庐写缠足与放足或许只是出于情节的需要,但从中可以窥见旗人与汉人在形容上便呈现出不同,以及那个时代两个民族之间虽不清晰却无法忽视的分别。与缠足和放足相呼应的是:玉娇龙秉性天成,至情至性,热烈追求自身的成长与爱情;而俞秀莲则深受男女大防、道德人情的束缚,与李慕白相爱却不能交往,正如缠足那般,她的情感也被深深束缚着。但是,俞秀莲虽未能突破这种束缚,却能从中不断审视和升华个人的爱情,在她的挣扎与进步中体现出主体意识的形成。
三、悲剧侠情:性别身份的丰满与侠客的自我成长
王度庐被称作“悲剧侠情派”,主要指他小说中丰富的情感描写。与“北派五大家”中的另外几人相比,这个特征尤其值得关注。白羽热衷于描摹人情世态,郑证因集中写武术技能,还珠楼主专心建构宏大的剑仙世界,总体而言,在这三个人的笔下,世俗男女的情爱基本是缺席的。只有朱贞木对感情有较多的描写,但《罗刹夫人》这类小说中性的因素远大于情,且这种情是“奇情”,而非普通人之间的相知。但王度庐写情,并不只是单纯写情,更重要的是展现人物在面临复杂情感抉择时的内心冲突,以及在冲突与挣扎中逐渐成长的过程。
所谓悲剧,在这个语境中主要指爱人不能相守。举例来说,李慕白和俞秀莲虽始终恪守礼制,克制内心的感情,但在这个过程中,两人不断地对话,从道德、情感和武术等方面互相启发,最终各有所成。所以这只是爱情的悲剧,并非整个故事的悲剧。玉娇龙与罗小虎虽然最终分开,但她因此从女德教诲里挣脱出来,从命妇的身份中挣脱出来,深刻反思了自己的爱情、生命欲望与追求。江小鹤与鲍阿鸾的确是真正的悲剧,鲍阿鸾因江小鹤而死的写法,充满了哀婉的美感和简净的力量,但也正是在对爱情的追寻中,江小鹤重新理解了自己复仇的使命,他不是放弃了复仇,而是对道德的复杂化有了自己的理解。“鹤—铁”五部曲由情感出发,在人性的复杂与人格的完整方面所作的探讨,完全超越了通俗小说快餐性的消费特征。特别是对女性的描写,已经呈现出新文化对旧道德的冲击,她们对自己的生命有追求,试着理解自己的情欲,展现出革新的力量。特别是在面对自己的家庭与爱人时,“鹤—铁”系列中的女性展示出内在的力量。
传统家庭对青年人的束缚,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武侠小说虽被“五四”新文学视为守旧不化,但王度庐在描写家庭与个人的关系时,尤其在对待女性的态度方面,却极为开明。如《鹤惊昆仑》中鲍阿鸾的出走,鲍阿鸾出去闯江湖的建议恰恰是家庭权威鲍老拳师提出来的,他对阿鸾说:“闯江湖去!高山大河随你便走,见些家里所看不见的事,会些咱们昆仑派以外的英雄。”随后又补充:“男大当婚,女大当聘,你也应当自己去寻一个好女婿。”[7]195考虑到武侠小说的商品属性和1930年代末的写作背景,或许鲍阿鸾自己寻女婿是迎合市场风尚的写法。但从小说后续的发展中可以看出,鲍阿鸾出走江湖不仅承担了家族的责任,更是她的自由选择。玉娇龙的逃婚则是女性自主权更有力的表现,她为逃婚作了周密的计划,提前安排人出去接应,而她逃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个人的爱情。她逃婚之后,风餐露宿,几番怀念家中的富足,却从未想过回去。在第一次逃婚被骗回并被挟持后,玉娇龙在情人的帮助下回娘家暂住,又设计了第二次逃婚。同样的设计缜密,甚至安排仆人去新疆接应。为了从家庭中、从命妇的身份中解脱出来,她不惜采用跳崖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堵住悠悠之口。这样的反抗,即使在新文学中都很少见。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玉娇龙也好,鲍阿鸾也好,她们逃婚是为了个人的爱情,这个爱情完全是她们个人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从父亲的女儿沦为丈夫的妻子。鲍阿鸾无法平衡亲情与爱情,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良心的安宁,但是在濒死之际,她仍然从容地对鲍老拳师表达了自己心中所想:“我十岁时就爱小鹤。你那时要明白点,大家都不至于有今日!……小鹤!你别松手吧!抱着我叫我死吧!”[7]561-562玉娇龙历尽千辛万苦从家中逃出,与罗小虎在京郊重聚,却主动选择离开。玉娇龙用自己的武术、道义与人格魅力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塑造,她的独立是完全而彻底的,养马于新疆,更从经济上解决了她出走的困境。虽然这个过程带有很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未尝不是对“娜拉走后怎样”的回答。此外,“鹤—铁”系列中的择偶观念也侧面反映出女性的独立意识。鲍阿鸾念念不忘的是武术未学成时的江小鹤,即使她后来遇见剑术高超的李凤杰、名门之后纪广杰,她的爱情也并未动摇;罗小虎之于玉娇龙,更是因为歌谣中的悲哀与美所激起的心灵震荡而相爱,无论是武术、出身或经济能力,罗小虎都不足以作为玉娇龙依赖的对象,但书中多次写到玉娇龙为罗小虎的遭遇落泪,为无法回报罗小虎的赤诚而羞愧。这种爱情观念折射出的女性独立意识实在难能可贵,即使在今日仍有其进步意义。女性侠客的塑造前所未有地饱满,与前述聂隐娘等人相比,玉娇龙首先呈现出了完整的人格,其次突出了女性特质,最后才是她出神入化的剑法。
王度庐初至青岛时,曾写过一篇《海滨忆写》的散文:“我要像王尔德一般的说:‘快活着!快活着!’”[12]从中可以看出,在“鹤—铁”系列创作之前,王度庐对于生活的理解便倾向于个体生命意识的张扬,以及他对西方文艺和新思想并无隔膜。因此,本文所说的侠客的主体意识之建立与张扬、情欲之解放,并非无中生有。“鹤—铁”系列小说虽然有大量篇幅承继了清代侠义小说中除暴安良的写法,篇幅冗长而脱离主线,但瑕不掩瑜,综观情节的发展与侠客的成长,仍然可以看出作者突破传统写法的决心与妙笔。而这种突破,不仅来自作者本人的笔力与对通俗小说模式革新的追求,更是时代思潮的微光照入市民文化的痕迹,值得详加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