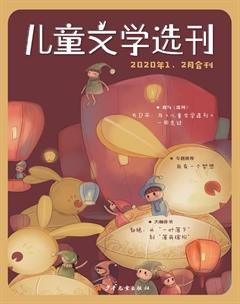醉枣
醉枣是鲁西北乡间的特产,也是我们童年的美食。
每年农历七月末八月初,在乡间随处望去,一棵棵枣树低垂着枝丫,一嘟噜一嘟噜的枣子泛着红光,远近弥漫着淡淡的清香。枣子不再躲躲闪闪,公然亮出一片艳红,繁密的树叶再也遮不住它们了,收获的时机到了。
而在打枣之前,母亲则让我们站在凳子上摘一些个儿头大、红透了的枣,一个一个地挑选摘取。我们在上面摘,母亲在下面接。枣子不能落地沾土,要放到盆里或篮子里,虽然枣子并不娇贵,但也不能随手乱扔,以免破损。母亲望着满树的枣子,指着这儿那儿的好枣让我们摘。有时我就爬到树上去摘。最好的枣往往长在树尖上,光照充足,得风气之先,色正体圆,看着眼馋。母亲嘱咐着要小心时,我已爬到树梢,像小猴一样,轻巧地在各个枝丫间腾挪攀援,她所说的那些好枣已尽在手中。
待摘得差不多了,母亲一手抓起三两个放到碗里洗刷一下,让枣在酒里浸泡一小会儿,再轻轻放进一个提前擦洗得干干净净的坛子里,直到坛子装满,最后一道手续就是封坛。为了密封严实,坛口蒙上一层塑料布,扣盖之后,还要涂上厚厚的黄胶泥,这泥胶性很大,又掺和了麦糠,不易裂缝,使盖和口之间严严实实、密不透风,里面的酒味逸不出来,外面的空气也钻不进去。据说,封不严实枣子就会烂掉,所以这一环节是不能马虎的。然后把坛子放在屋子里一角背光处,耐心等待就是了。醉枣醉枣,要等枣子都被酒气熏醉了,才算熟了。
而这一等就是数月。虽然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忍不住摸摸那坛子,总想偷偷开盖,看看枣子醉得如何,但想起母亲制作醉枣时的用心,就不敢轻举妄动了。直到有一天,我们把醉枣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而又馋巴巴没什么东西可吃時,母亲忽然说,看看醉枣能吃了吗?我于是立即抠去坛子上干硬的黄泥,揭开盖子,满屋子顿时涌出酒与枣混合的扑鼻的醇香,每人抓出一把欢快地大吃起来。这种枣比鲜枣还红润光鲜,阳光下晶莹剔透,皮是薄的脆的,而瓤是软的黏的,吃起来既有酒的香,也有枣的甜,还有蜜的绵,满口生津,回味无穷,浑身舒服。在大雪飘飞的冬日,在食物稀缺的数九寒天,一家人围坐桌前,品尝醉枣,实在是难得的奢侈。
好东西不可贪多。醉枣吃多了也会伤胃。一坛酸枣可供一家人慢慢品味,还可以作为待客的佳品,当然,主要还是拿给孩子吃。那时,一般家庭买不起糖果点心,客人来时抓一把醉枣,哄得孩子美滋滋的,大人自然也就高兴。这东西虽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但孩子多、吃得猛的人家,几天就吃光了,所以谁泡得多,谁吃得节制,谁就吃的时间长,就更显得稀罕。
泡制醉枣,不一定非要用坛子(但瓦罐是绝对不行的,它有透气性),也有用暖壶胆及其他玻璃器皿或搪瓷器皿的,无论怎样,器具要干净清爽,还要确保密封;时间不到而中途揭盖更不行,所以挺考验耐性的。
醉枣是不能批量生产的,集市或商店里有干枣、熏枣、蜜枣、冬枣,但唯独不见醉枣——不但那时没有,即使后来也没有,当下更不会有;我也从未见过有乡人用盛水或装粮食的大瓷缸等粗老笨壮的大家伙醉枣的,看来也只能适宜农户用瓶瓶罐罐等小物件土法炮制,小心伺候。其泡制过程虽不复杂,但须一颗颗挑选、摘取、酒泡、封装、发酵,挑剔多,周期长,皆手工,这些都注定了醉枣乃枣中精品。
后来,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乡人不再泡制醉枣了。现在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或许根本不知醉枣为何物。像我这被黄土埋了半截的人,对这小东西倒挺怀念的。有朝一日再炮制一坛,再品醉枣的美味,重温童年的记忆,也是一件趣事、一件乐事、一件美事。
选自《少年文艺》(江苏)2019年第9期
韦清,作家,作品发表于《青年作家》《散文》等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