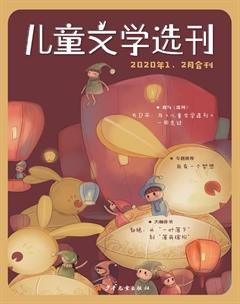来自赛汗塔拉的牧羊犬

我從来没有想过,围捕这头狗比猎狼还要麻烦。
我的童年,曾有机会看到中国北方狩猎时代最后的背影,我父亲的两个哥哥都是猎人,我曾经跟随他们一起围猎过狼。
与那些被捕获的狼相比,这头牧羊犬的智商确实太高了。
第一次围捕它,我找了四个年轻的牧人骑着摩托追赶。我的想法很简单——四个牧人骑着摩托排成线追逐,狗跑得再快,终归跑不过发动机驱动的摩托。我的想法确实不错,一开始四个骑手骑着摩托配合得十分默契,他们从不同的方向看似不经意地向这头正卧在高坡上休憩的牧羊犬接近,然后突然加快速度,四辆摩托排成弧形的包围圈兜着它向前跑。只一会儿它就明显放慢了速度,显然已经跑得快喘不上气了。我们感觉就快追上了。
随后我想得很简单,四个牧人围上去,用一块破毡子将它压在下面,防止被它咬伤,然后给它戴上项圈就行了。
不过,这只是我的想象。就在四个牧人收缩包围圈的最后一刻,它突然往斜刺里一冲,往一边跑开了。它是奔向了莫日格勒河的方向。
它直接跳进河里,轻松地游到对岸。
现在不是雨季,九曲回环以蜿蜒著称的莫日格勒河水最深的地方也不会超过一米五,但是,四个骑手出于安全起见,还是没敢骑着摩托涉水过河,先不说水深会没过排气管导致摩托灭火,河底也可能有铁丝网之类的东西绞住车轮。
我站在自己的营地里,用望远镜追踪了整个围捕过程。
在四个骑手望河兴叹的时候,这头牧羊犬已经爬上了对岸。显然,它很清楚骑摩托的牧人根本不敢尾随它过河,于是它甩掉身上的水,并不急于跑开,就卧在河的对岸漫不经心地看着四个牧人。
有了第一次的失败,第二次我选择了机动性更好的行进方式——骑马。
这确实是一种古典而传统的行进方式。
就在今年春天,我要离开营地外出参加书展。但是,就在我出发的前一天,草原刚刚下了一场暴风雪,我开着四驱的皮卡车竟然无法从营地里冲出来——雪太厚了。最后,迫不得已我还是选择了在草原上已经沿用千年的出行方式,骑马到公路边,再让朋友开车从城里过来接我出去。在如此现代化的时代,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有的时候还是最为原始的出行方式比较靠谱。
这一次加上我一共五个骑手,我准备骑马围捕它。
我的计划是——骑马追逐,然后用套马杆将它套住,再拴上项圈。如果它故技重施涉水过河也没有任何问题,马跟摩托不一样,过河相当方便。
这一次的想法仍然很好。
开始几乎成功了,是的,仅仅是几乎。
我们五个人配合得很好。骑手骑的五匹马中有两匹是杆子马,就是那种牧人训练出来,专门用来套马时骑乘的马,反应特别敏捷。两个年轻的骑手骑着它们手持套马杆冲在最前面,我和另外两个骑手在侧翼哄赶,阻止这头狗逃出包围圈。
有两次如果不是它反应比较快,在骑手探出套马杆的时候及时地趴在地上,几乎就已经被套住了。还有一次确实已经套住了,但是套马杆的绳套是为套马准备的,对于一头狗来说太大了,就在骑手用力捻动套马杆收紧绳套的最后一刻,它挣脱了出来,但还是被扯翻在地,颇为狼狈。
就在我以为已经稳操胜券的时候,它突然转头冲向两个手持套马杆的骑手,从两匹马的中间逃了过去。套马杆太长,根本无法应对近在眼前的对象。其中一个骑手因为过于心切直接探出套马杆,结果因为距离太短,套马杆折断了。
这一次,我不得不承认,这牧羊犬确实太聪明了。它没有向相反的方向跑,而是直接冲向两个骑手,让手持套马杆的骑手不知所措。这么做,除了足够的勇气,还需要的就是智商。
我们调转马头追赶,它正在奔向一道草原上的围栏。
我们打算在它跑到围栏之前截住它。我们还是慢了,就差一点儿。
跑在最前面的骑手套马杆的绳套几乎已经触碰到它的尾巴,它轻盈地一跃,跳过了围栏。
那骑手拼命勒住缰绳,才没有连人带马撞在围栏上,但是慌乱间他的套马杆也折断成两截。
这一次,它跳进了另一个草库伦里。
像上一次过了河一样,它知道我们无法骑着马跳过围栏,于是,并不着急逃走。
刚才它也确实被我们追得有些狼狈,此时就卧在草地上,伸着舌头喘息。
它并不害怕我们,甚至认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
没有办法,我们分出两个人,大概跑出去有一公里,到了那个草库伦的入口,从另一面兜了过去。
其实,到这个时候再去追逐这头牧羊犬,说来已经没有具体操作的实际意义了,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可以捕捉它的工具——套马杆。这么做多少只是为了争回一点儿面子,毕竟,没有抓住它,折了两根套马杆。
但是,它连给我们一点儿面子的机会都没有留下。
这一次,它直接冲向了河边茂密的柳树丛里。
它知道,马驮着骑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进入其中的。
它并没有直接钻进柳树丛的深处隐藏形迹,而仅仅是卧在外层几棵柳树的后面,望着外面无可奈何的骑手。
这简直是在挑衅。
我知道,必须采取其他的办法了。
这头黑色的雄性牧羊犬,叫做赛罕,名字是我取的。
它来自呼伦贝尔靠近蒙古国边境的新巴尔虎右旗的赛汗塔拉。赛汗,在蒙古语中是好的意思,是形容词;塔拉,意为草原,所以赛汗塔拉可以翻译为美丽的草原。在内蒙古有很多叫赛汗塔拉的地方,这是游牧人对自己家乡美好的祝愿,美丽的草原,丰美的草原。因为地处偏远,连那里的蒙古马都非常狂野,难以驯服,当然这也意味着血统更为纯正。另外,那里的草原因为盐碱地较多,也盛产呼伦贝尔地区公认最为肥美的羊肉。当然,也出产最为强悍凶猛的蒙古牧羊犬——因为偏僻,外来犬种难以进入,保留了最为原始的蒙古牧羊犬的血统。
说起来它能够来到我的营地,也是偶然。
那次我去新巴尔虎右旗看望一个朋友,返程的时候车刚刚驶岀旗所在地阿勒坦额莫勒镇就发现一个轮胎漏气,准备换上备用轮胎的时候才发现备用轮胎气也不足,索性就在镇外的一个汽车修理铺补胎充气。
在等待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修理厂院子一角的这头黑狗。当时,如果不是因为它脖子上拴着一根铁链,我还以为那只是一块修理厂的修理工用来擦手上油污的破旧衣服,灰乎乎,摊躺在午后炽热的阳光下,无遮无掩。那是呼伦贝尔近五十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最高气温已经达到42℃,当我站在阳光下的时候,感觉自己热得都已经快要昏厥了。
这头狗就躺在混凝土的地面上一动不动。
我观察了一下,看那根铁链的长度,它移动的半径最远处,也就是一个墙角算是有遮蔽物,不过在墙角那儿也仅仅是每天黄昏的时候能够给它提供一点儿清凉。在这种骄阳似火的季节,它能够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
我慢慢地接近它,很小心,接近到在铁链控制的安全半径时,我才停下。这应该是一头黑色的成年牧羊犬,但是它的皮毛因为满是灰尘根本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而且身上褪下却并未掉落的旧毛跟灰尘和泥土一起粘結在身上,纠结的死毛已经成为某种类似土块一样的东西,堆砌在它的身上。
它干瘪的胸腔在轻轻地翕动,而且,在我观察它的时候,突然发出一丝闪亮,那是它的眼睛。因为它全身灰黑,我几乎无法看到它的眼睛。
它正死死地盯着我。
我看到在它身边有缭绕不散的苍蝇,它的身上一定有外伤。
在它的身边,有一个破缸底,还有一点点儿水,是混浊的泥水,已经长了绿毛。
“嘿,离那狗远一点儿,咬人!”远远地,修车的工人不耐烦地冲着我大喊。
我知道,把狗养成这样的人,我如果建议他应该给狗提供一处阴凉,稍微喂得好一点儿,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他根本不会意识到,这头狗在太阳底下已经快要被晒死了。
我慢慢地蹲下,正如我预料的,我几乎没有看清它是怎么跳起的,它已经抻着铁链冲到我的身前。我的距离感很好,它无法触碰到我。
但是,它也没有像傻子一样狂吠,只是阴森地注视着我。
“没跟你说嘛,咬了不负责!”
我没有理会身后那工人的呼喝,轻轻地伸出了手掌心朝上。
显然,这头牧羊犬没有想到我会有这样的勇气。
当它站立起来,能看出这是一头成年的黑色蒙古牧羊犬,骨架还不小,但是太瘦了,如果不是有身上这像建筑砌块一样的死毛,估计看起来也就像灵缇一样了。
但是,它也并没有舔舐我的手,只是用鼻头轻轻地触碰了我的手指,它的鼻子干裂,并没有像健康的狗那样湿润。
我的手顺着它的下巴一直摸到它的脖颈,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皮毛下的骨头,一只狗可以瘦成这样却能够活下来确实不可思议。
它的身体在颤抖,显然,它从小到大几乎是从来没有被人抚摩过。它无法承受一种如同被雷电击中般的喜悦。
当然,它也从来没有吃饱过。在这里,它几乎得不到什么食物,估计偶尔会扔给它一块枯干的骨头,它要把骨头仔细嚼得粉碎,两边的股骨头那些略显疏松的骨质会被它咬碎吞下,而骨腔中还剩下的已经干透的骨髓对于它应该算是绝世美味了。
被人类抚摸,这种事情在它的世界里似乎从来没有想象过,也许只在梦里出现过,但是以它的成长经历来看,它贫乏的想象力无法织就这样的梦。
我起身时已经做了决定。
那个修理工显然已经发现了什么——我对这头狗感兴趣,我对这头已经快要死去的狗感兴趣。
看到修理工走过来,黑狗立刻低垂下头,轻轻地摇晃着尾巴。他伸出手似乎要抚摩狗,而就在狗以为他要抚摩自己放松的时候,他穿着靴子的脚猛地抬起踢在狗的下巴上,狗一声哀嚎之后拖着铁链逃开了。
他手脚的动作配合得如此娴熟,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
我真的感到无法想象的吃惊。面对狗,人竟然可以这样做。这种行为对狗的伤害比直接殴打还要严重,最终,它只会对人类彻底地失望,永远不再信任人类。
之后的事很容易,即使这修车铺的工人再狡黠,终归还是不好意思将这样一头瘦得如同纸片的狗叫上天价。
之后,修理工牵着它的链子交到我的手里。
也许是人类的本性,我付的钱已经足够多了,远远超出当地购买一头最好的牧羊犬的价格,他却仍然表现出吃了大亏的样子,一再向我表明这狗卖得便宜了。
他告诉我这头狗是边境赛汗塔拉的一位牧民送给他的。
“他家的狗都像黑熊一样。”这句话我相信了,之前我去过那片草原,那边的牧民普遍饲养黑色的牧羊犬。
尽管几乎饿死在这主人的手里,这头黑色的牧羊犬还是在我接过链子的一刹那冲向我,我早有准备,猛地抖动手中的链子,铁链不轻不重地抽在它的脸上。在它一愣神之际,我已经收紧铁链,趁势将它拎起,扔到了车的后备厢里,然后将链子也扔了进去,直接拉上车门。它太瘦了,几乎没有什么重量。
我的动作一气呵成,根本没有给它反应的机会。我见识的猛犬实在太多了,这头已经疲弱得连站立都困难的狗真的不会难倒我。
车重新上路。
搭车的一位当地的朋友,一路上都在抱怨不应该用这么贵的价格买下这条用他的话来说已经瘦得只剩下皮毛的狗。直到我们到了下一个小镇午餐之后,他上车开始昏睡,才终于闭上自己的嘴。
这头黑色的牧羊犬被我带到营地。
我就将它拴在我的房车外面。
因为考虑到它已经饿得太久,当天我没有给它喂太多的食物,只是喂了它半盆用牛奶煮的米粥。
因为考虑到它可能因为过于饥饿而疯狂进食,我将粥放冷之后才端给它。当我将粥放在它面前的时候,它惊呆了,不太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它灵敏的鼻子已经捕捉到了食物的味道。
怕它因为恐惧而不敢进食,我走远了一些。
但它仍然死死盯着盆里的粥一动不动,它的身体在颤抖,它在努力克制自己扑上去的冲动。这么美味的食物怎么会给它,它在猜测里面也许有比踢它的下巴更可怕的陷阱。
我又鼓励了它一下。
它沖了上去,我几乎无法用文字来形容它当时进食的速度。
有一个形容词——鲸吞龙吸,它极好地以自己的表现诠释了这个成语的内在含义。眨眼之间,它像一个超大功率的吸尘器,将半盆粥一扫而空。这种情景我只在动画片里见过,一般的情景是,某个老饕如同狂风卷过般将食物一扫而空扬长而去,当然,还会留下一个旋转的空盘子发出咣当的响声。
我给它取了赛罕这个名字,也是希望它今后能够快乐生活吧。
从第二天开始,我增加了喂它的次数,少食多餐。这些食物让它急需营养的身体以最快的方式分解转化进入循环系统,只是几天的时间,它的腰脊摸起来已经不再像枯木一样硌手,开始长肉。而它身上也滋生出黑得发亮的新毛。
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梳下它身上的死毛。当然,我保留了它尾巴、脖子下和耳尖的那些成绺的死毛硬块。尽管也许梳理干净看起来更为清爽,但在草原游牧人的传统中认为这些死毛有特殊的作用,牧羊犬在与袭击羊群的狼撕咬时这些死毛可以保护它们。尽管现在牧羊犬与狼打斗的机会几乎没有,但是保留这个古老的传统未尝不可。
在为它梳毛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在它身上找到一缕白色的毛,这很少见。所有的黑色牧羊犬,无论看起来黑得多么透彻,总会在尾尖、胸口或者爪尖有那些白毛,完全黑色的特别少。
将毛梳理干净,我也发现了它身上的伤口在左肩胛上。看起来应该只是很普通的皮外擦伤,但是没有经过处理,它自己又根本舔不到这个位置,已经腐烂生蛆。我仔细地清理了蛆虫,然后清洗干净伤口,用红霉素软膏涂抹。对于犬类这是最好的外用药,只要涂上,无须包扎,基本上苍蝇就不会再光顾了,而且敞开也更利于伤口愈合。
它的愈合能力实在惊人,次日我再查看的时候,伤口竟然已经开始收口。前后只用了四天的时间,它的伤口就完全愈合了。这是蒙古牧羊犬最强悍的体质,可以应对冬季低至零下50℃的酷寒,同样,也能够承受夏季40℃的高温,只有生命力最强悍的个体才能够在这荒寒的草原上生活下来。
我们相处得不错,它不再对我感到恐惧。我查看了它的牙齿,它应该四岁左右,是一头犬最好的年龄,但是,这四年它生活在一个从未被爱过的世界里,要想让它真正对人类重拾信任,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它刚刚来到营地一周左右,我就外出参加书展。
就在我离开的第二天,弟弟在喂它的时候,它因为过于紧张闪躲时撞翻了食盆,弟弟踢了它一脚。它当场挣断了项圈。
项圈断掉之后,它并未逃走,而是一直在营地的附近徘徊。弟弟尝试叫它回来吃食,它却一直未敢鼓起勇气回到营地。
本来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弟弟的一脚将它刚刚建立起来的对人类的信任又给踢跑了。
那段时间白天我在书展现场参加各种宣传活动,每天回到酒店都能看到手机上弟弟给我的留言。
一天晚上,它洗劫了附近一个旅游景区的厨房,将腌好准备第二天做烤全羊的一整只羊拖了出来,一个晚上将这只羊啃掉了一半。
距离我营地不远另一个营地的大妈刚刚做完的奶干,晾晒在蒙古包上,出来再看的时候,发现它正蹲在蒙古包上大吃大嚼。
它竟然找机会打开了我营地厨房的冰箱。里面的食物,除了蔬菜、罐头和一些装在瓶子里的酱料,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被它一扫而光。
附近的牧民开始提防它,把食物看得很紧。
于是有一天早晨,一个牧民发现自己的靴子丢了一只。牧民找了好久,远远看到赛罕正趴在一个坑里在啃咬什么,打马过去看,它落荒而逃,坑里只剩下一只靴子底。
为什么牧民家的狗不驱赶它?
我有些奇怪,牧民家的狗都是很凶猛的,一般不会让陌生的狗接近自己家的蒙古包。
“你回来看看就明白了。”弟弟无奈地回答我。
我是在两周后回到草原营地的。
在这两周的时间里,赛罕到处偷食,已经几乎让弟弟绝望,他不得不一次次去被它偷盗过的牧民家赔礼道歉。毕竟,赛罕是我的狗,我带回来的狗就是我的狗,我得对它的行为负责。
但是还好,无论它偷什么,却从来没有袭击过草原上的任何一只羊。这也是附近的牧民能够容忍它的原因吧。弟弟试着骑着摩托追过它两次,根本追不上。
就在我回到营地第二天的上午,弟弟将我叫到室外,将望远镜交到我的手里。
我按照他指给我的方向望去。
草原的初秋,天高地阔,阳光充沛,清风徐来,已经绿到极致的牧草即将泛黄,牧人已经早早将羊群赶到草场上,羊只头也不抬地啃食青草,它们已经开始贮存秋膘了。
在望远镜里,我看到一个纷乱的队列。
赛罕跑在最前面,在它的后面三头牧羊犬紧紧追赶。
那三头牧羊犬是通古勒嘎大叔家的。远远望去,大叔家的蒙古包上摊开晾晒着奶干,此时正是乳牛产奶的高峰期,大妈应该也在制作贮存奶食。想来是赛罕偷奶干的时候被发现了,三头牧羊犬兢兢业业,发挥自己驱赶的职能。
其实,牧民们的牧羊犬更多的时候是守卫犬,守护营地,驱赶野兽。
所以,它们将赛罕赶出一段距离之后,也就失去了兴趣,懒散地叫了几声,准备往蒙古包的方向返回。但是就在它们松懈的一刹那,赛罕突然回头冲刺,一口咬向走在最后面那头牧羊犬的后尻部。显然,赛罕并没有想真的下口,所以那头牧羊犬仅仅是受到了惊吓,一声怪叫。
于是,三头牧羊犬又咆哮着开始追逐赛罕。
在无边的草原之上,远远地观望这些牧羊犬追逐赛罕是一场好戏。八月的草原上,高空中有巨大的云团,微风吹过,巨大的云影从草原上缓慢飘过,如同阿拉丁的魔毯。
而很快,我就发现赛罕一个惊人的表现。
它竟然懂得在巨大的云影里奔跑。最初,我以为这只是巧合。
我又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它沿着云影在地面上飘过的边缘奔跑,巧妙地控制着速度和节奏,它在利用云影在大地上缓慢飘动时的弧度——它一直在云的阴影里,而那三头牧羊犬却暴露在阳光下。
终于,三头牧羊犬中的一头停了下来,它趴在地上,不再追赶,伸着舌头喘息,另两头也跟着趴了下来。
而此时,赛罕却兜了一个大圈,从一个高坡后面绕过,躲过三头牧羊犬的视线,又跑回蒙古包那边去了,
在我这里用望远镜看得很清楚,它绕到蒙古包的后面,一跃而上,蹿上蒙古包,在上面大口吞食晾晒后的奶干。
就在这时,大妈又端着刚切好的奶干出来,看到正在大快朵颐的赛罕,愤怒地大喊。
听到大妈的喊声,三头正在歇息的牧羊犬才恍然大悟,可是已经晚了。
以“鲸吞龙吸”之术狼吞虎咽地塞了一肚子酸奶干的赛罕跳下蒙古包,不慌不忙地跑开了。
而此时,三头牧羊犬正在舍命往回飞奔,但已经是望尘莫及,赛罕已经跑远了。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抓住它,那么只有一种办法了。我之前没有用,是因為这种方法会给赛罕带来一定的伤害。
我的营地里一直饲养着蒙古猎犬。这种古老的猎犬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我一直保留着三个血统十几条猎犬,只是希望这种猎犬不要就此消失了。
它们是猎犬,在培育的漫长过程中,被不断地定向繁育,最终成就这种强悍而凶猛,速度足以追捕野兔和狐,力量又能够围捕像狼和野猪这样大型野兽的猎犬。在中国已经没有狩猎了,而且我个人也不杀生,所以我饲养着它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努力挽留童年的那些回忆。有时我骑马领着它们在草原上奔跑,能够让我回忆起童年时跟随父亲的两个哥哥一起外出狩猎的情景。
这些猎犬在我的营地已经繁育到第四代,很好地经过了社会化训练,不会追捕袭击羊群和营地的猫。通过适当的克制性的训练,更多的时候,我努力将它们追捕的猎性转化为对奔跑的热望。
而营地里那三头最早来到的猎犬只要放出来,它们会追捕视野里出现的除了人类之外所有快速移动的物体。不仅仅是动物,是物体,就连汽车它们也追。
我事先做了一些准备。
早晨凉爽的时候,我拎了大概半水桶的剩饭还有面包点心之类的食物放在河岸边,我知道赛罕就躲在不远处的柳树荫里。
我回到营地之后用望远镜观察。我离开之后,赛罕在附近徘徊了好久,显然它不太相信有这种好事。它举目四望,周围是平坦的草原,不可能埋伏着骑着马或者摩托的牧人。
它踌躇了一会儿,还是未能抵挡住食物的诱惑。为了刺激吸引它,我特意在这些食物的最上面放了半块烤羊肉,经过烧烤的羊肉会散发出特殊的油脂芳香,没有几条狗能够抗拒这种美味。
是的,它也无法拒绝。
它很快地吃光了所有的食物,它的肚腹明显地鼓胀起来。
显然过多的淀粉摄入让它感到口干难耐,于是在河里喝足了水。吃饱喝足之后,它就在河岸边卧下,开始进入饱食后的昏睡。
我等了半个小时,然后带着四头选好的猎犬骑着马出发了。
有猎犬协助,只需要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一切。
我特意选了四头刚刚一岁左右的猎犬,它们的力量和撕咬能力还没有达到顶峰,不会对赛罕造成太大的伤害。而且,我整整饿了它们一天,它们肚腹空空,可以跑得轻盈。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等待这半个小时的原因,现在,刚才赛罕吃下去的所有淀粉已经遇水膨胀,那么一会儿带着一个巨大累赘的胃囊的它无论如何也无法跑得太快。
四头猎犬在犬舍里关得太久,放出来之后兴奋得狂奔乱跑,不过在短暂地放纵之后,我一个呼哨它们就跟了上来。
我不紧不慢地骑马引着它们往河岸的方向而去。
当我骑马领着猎犬距离河岸还有一百米左右的时候,赛罕方才发现,它有些惊慌地起身,但是膨胀的肚腹显然限制了它的动作。
在它起身的一刻,四头猎犬也发现了它。它们几乎同时屹立不动,头颅前探,鼻尖一起指向赛罕的方向,颈部的鬣毛凛然耸起,这是视猎犬发现猎物的标准动作。在它们很小的时候,我带它们出来就不断地训练它们,不允许它们攻击同类和牲畜。还好,它们还能控制自己,但是身体里那种捕猎的冲动还是让它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正慢颠着跑开的赛罕。
我发出了一个攻击的命令。
它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它们明白这个命令的含义;一般我发出这种命令,都是让它们驱赶那些接近营地偷食草垛上草捆的牛马。当然,只是让它们将牛马赶开就好,毕竟,它们也不能将这些大牲畜怎么样。
它们狂奔而去,我的命令似乎在一瞬间解开了它们追猎的封印,看着它们像猎豹一样奔跑的身姿我甚至为自己之前无数次限制它们捕猎的热望而心有愧意。确实,我已经将它们的天性限制得太久了,但是没有办法,我并不希望它们顺从内心完成杀戮,就像现在一样,它们只要抓住赛罕即可。
看到四头来势汹汹的猎犬,赛罕也确实乱了阵脚,直接跳进河里,向对岸游去。
但是,这种对付骑着摩托车牧人的办法对猎犬来说毫无意义,四头猎犬跑到河岸边根本没有减速,助跑着跳到河水之中。只是这一跃,它们已经完成了渡河的三分之一的距离,而此时赛罕才刚刚爬上河岸。
它显然被四头猎犬追捕的势头吓到了,上岸之后来不及甩掉身上的水就钻进了茂密的柳树丛里。
这种盘根错节的柳树也许可以让骑马的牧人望而却步,可是对于猎犬来说却如闲庭信步,它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哄赶野兔,更不用说追捕的对象是一头牧羊犬。
牧羊犬本来就不善于奔跑,跟专门培育出来精于追捕的猎犬相比,奔跑能力要逊色得多。
随着柳树林里几声负痛的咆哮,很快,赛罕就夹着尾巴从里面冲了出来,在它的身后,四头猎犬紧紧追随而来。它没有别的去路,只能再次跳进河里,向我这边游来。
它游了一半才发现我早已经等在河边,但它已经没有退路,因为就在它的身后,四头猎犬已经依次跳进河里,追了上来。
它颇为狼狈地爬上岸,仍然来不及甩掉身上的水。它挺直了身体,开始呕吐。
我趁机甩出一个绳套,将它套住。
爬上河岸的四头猎犬目光坚定,想要完成最后的捕猎。我取下马鞍梢绳上挂着的马鞭拿在手里。
这就足够了。
在它们还小的时候,突然攻击从营地附近经过的羊群,将羊只追得七零八落,我就是用这根皮鞭制止了它们模拟的狩猎。
往复涉过河水,刚才又在柳树丛中撕咬,它们身上暴力的热望已经挥发得差不多了,在皮鞭的威慑之下,它们也就放弃了继续攻击这头落水狗的想法。
同样是涉水,短毛的猎犬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而长毛的赛罕却显得极为狼狈。
赛罕的运气也算不错,如果是营里那几头第一代的猎犬,估计在柳树丛里它就被撕碎了。
被绳子套住的那一刻,赛罕立刻表现得特别顺从,我就这样骑着马将它牵回营地。
回到营地,弟弟将四头猎犬送进了犬舍,然后马上回来查看已经被我套上项圈拴上链子的赛罕。
“得好好懲罚一下它,这段时间它实在是把附近的牧民折腾得够呛。”弟弟看着被拴上的赛罕认真地建议。
“明天再研究一下怎么惩罚它可好?”确实,必须好好研究一下,这关乎它的未来。
第二天,我的达斡尔族朋友瓦然泰来访,我们三个人喝茶聊天,我终于想出一个惩罚赛罕的办法。
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就是让它大吃一顿。
我拿出了很多食物——两块烤牛排、一块手把肉、一袋油炸果子,还有一块我从北京带回来的瑞典产的羊奶酪。总之,这是一头狗几乎无法想象的饕餮盛宴。
在最初狂风骤雨般的“鲸吞龙吸”之后,赛罕完成了进食的前奏,它开始吃得仔细而缓慢。确实,在它的生命中,食物从来是来之不易的。
我给它食物的过程竟然也带着某种仪式感。
这样的机会实在不多,朋友已经好久不见,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看着赛罕进食,同时谈起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狗。瓦然泰回忆起在很多年前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在山中被野猪攻击,他的猎犬协助他脱险。
那天黄昏送走我的朋友,我又严厉地惩罚了赛罕一次。
惩罚具体是由弟弟来实施的,这一回是用牛奶煮的半桶米粥,还有酸奶渣、手把肉和月饼。
月饼是最后喂给赛罕的。弟弟一再强调,一顿完美的饭最后一定要有甜点。
赛罕因为吃得太饱而目光迷离,当它吃完所有的食物,就卧在我的脚边睡着了。
它只是被饿怕了。
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在阿拉斯加的淘金者,独自穿越荒野,在漫长的旅行中他甚至因为缺少食物而生吞雏鸟,最终他运气不错,遇到捕鲸船获救。后来,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以这个淘金者为原型创作了小说《热爱生命》。在现实中,这个淘金者上船之后,似乎永远也吃不饱。有一天,船上的厨师发现所有的面包都不见了,后来,人们在淘金者的船舱里找到了足够全船人吃的面包,它们被整齐地一排排码在淘金者的床铺下面。
想出这样一种所谓惩罚的方式,是因为童年的时候我读过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篇散文。
作家跟自己的朋友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村庄里度假,村庄里有一只喜欢偷东西的猫。终于有一天,他们将这只猫捉住,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知道惩罚无用,他们选择的办法就是让它饱餐一顿。然后,这只猫就开始义务地为他们服务,保护起他们钓鱼用的鱼饵,驱赶那些觊觎蚯蚓的鸡。这个故事,真的是给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当然,我没有想到,在很多年以后,我用同样的方法拯救了一条狗,一条牧羊犬。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赛罕已经在门口等待我了,我没有在它的脖子上看到项圈。很显然,它再一次挣脱了项圈。但是,这一次,它并没有逃开,就趴在我的门口等待我。
我呼唤它,它站在那里看着我,它在思考、权衡。对于一头受过伤害的狗,这个选择非常艰难,它无法猜测能够从我这个人类的身上得到什么,是爱还是伤害。
随后,它慢慢地走向我。似乎是为了掩饰自己拖延这么长时间的羞赧,它竟然假装自己的目光在追随一只骚扰它的蚊蝇。
它嗅闻我的手。我环抱住它的脖子,轻轻抓挠它的下巴和耳后。它惬意地摇动着尾巴。
作为一条狗,它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赛罕证明了自己是一条很好的护卫犬。
从此之后,每天它总是雷打不动地卧在我的门前,对那个专门给它用厚板钉成的结实温暖的狗窝根本不理不睬,无论风霜雨雪,它就一直卧在那里。当有客人来访,它高声吠叫示警,展现在客人面前的是一头凶悍可怕的恶犬,但是,只要我高喝一声,它就立刻噤声,闪到一边。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赛罕完美地发挥了自己作为牧羊犬的职责。一天晚上,一头狼进了羊圈,在雪夜里,我听到隐隐约约的纷乱和赛罕的吠叫,但温暖的被窝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
第二天早晨,寒罕像往常一样摇晃着尾巴在门口等待我,我看到它黑色皮毛上的血渍已经冻成红霜。它只是受了轻伤。羊圈外雪地上的印迹说明了一切,那头狼留下了巨大的爪印,显然是一头很少见的巨狼。但是,狼最终也未能进入羊圈,雪地上满是赛罕与它厮咬时翻滚的痕迹。
我查看了那头一路滴着血逃走的狼的爪印,显然它的一条后腿受了重伤。
选自《十月少年文学》2019年第10期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族,自然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庆油田作协名誉主席。出版有《黑焰》《鬼狗》《驯鹿之国》《黑狗哈拉诺亥》《狼谷的孩子》《叼狼》和《蒙古牧羊犬——王者的血脉》等作品八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