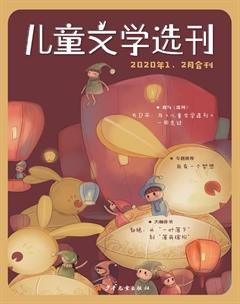老桦树上的小木屋(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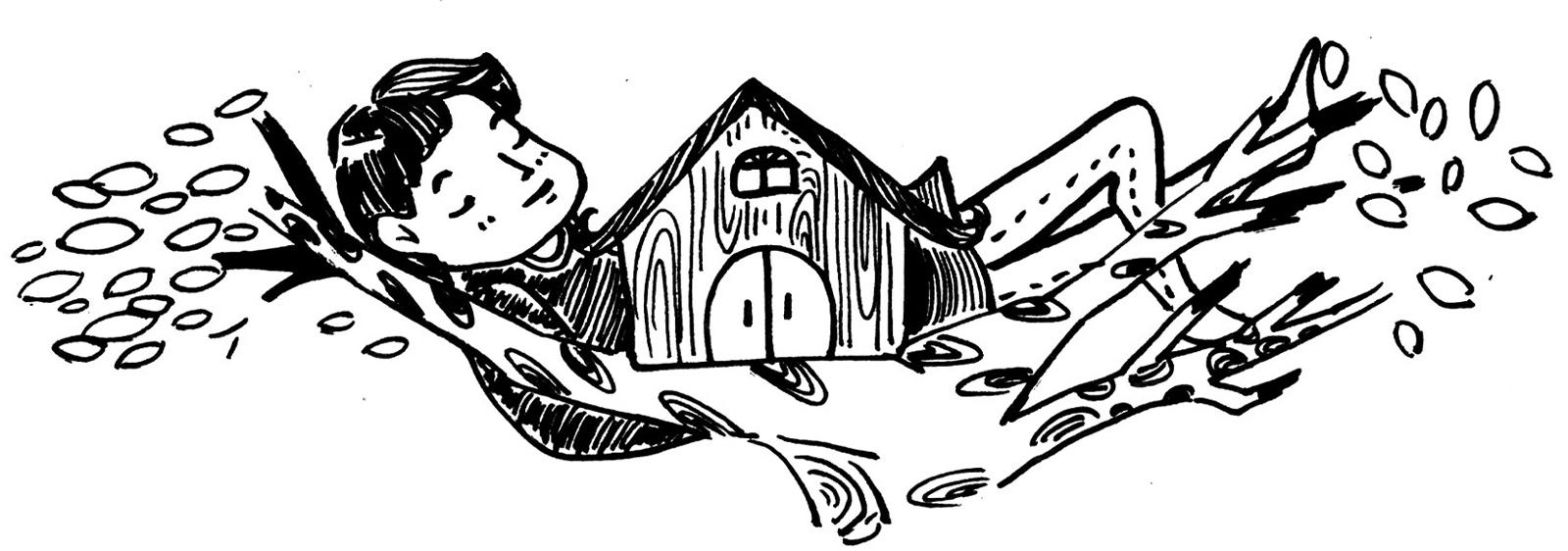
全寶要给自己树上的小木屋再搭个顶棚,让王伟伟好好看看!他家门前的老桦树可是出了名的好树,有好几十年了,又粗又高,主干得两人合围。在一人高处,主干分成四根粗大的分枝,四胞胎一般,爸爸用木头做了个平台,往上一架,顿时一个稳稳当当、格格正正的小木屋成了。
村里的孩子都眼馋,也想找树搭木屋,可哪能有全宝的运气好,有这么十全十美的好树?孩子们常常站在树下,仰着脖子对得意洋洋地晃荡着腿的全宝说:“全宝,全宝,让我上去玩一下,中是不中?”
中是不中,全凭全宝高兴。因为老桦树,全宝在村里可趾高气扬不少回,现在全宝又一路高歌猛进,风光到班里去了,你说,这是不是一棵金子一样的好树?
“小木屋再搭个顶棚,我夜里就能在树上睡觉了。”全宝美滋滋地说。
其实,他还希望能更了不起,能更镇住他们班的那些男孩们。
“不搭不能睡?”大水扭过头问。
“夜里露水阴气重,落在人身上,不长个子,我妈说的。”全宝对个子很在意,他要是有大贵那么高,跟王伟伟过过招就没问题了。
大贵跟大水都点点头,满意地嚼着锅巴。
“你睡第一晚,我睡第二晚。”大水说。他本来想说睡第一晚的,想想全宝大概不会同意,就忍了。
“我跟你一起睡。”大贵急切地伸过脸说。
“不中,太挤了,你那么胖,一翻身还不把我压扁。”大水一翻眼皮说。
大贵难过地缩回头,噘着嘴。他其实是怕黑,也怕虫子,怕虫子沿着树枝,一扭一扭的,爬到他身上,还不吓死人,况且还有蛇。
“四面竖上木板才好呢。”大贵说。
全宝眼睛立刻发出极亮的光来。“对啊!像真正的房子!”他“啪——”一拍手,“记得吗?教室后面贴过的报纸?哎呀,还哪张,不就贴过一张?对对,上面有个人造鸟巢?对,门是个圆圆的洞,对对,我们也把门做成圆圆的洞……”全宝眉飞色舞。
大水一听,跳起来直点头:“对,对,四面要板,像真正的房子。”
“安个木门。”大贵出于安全提议。
“嗯!”全宝、大水重重地点着头。三个人意气相投,心潮澎湃,点子一个接一个,妙极了。
“建筑师”们乱踢着腿,神采飞扬,想了又想,说了又说,小木屋于是越来越像样,越来越漂亮,连细腻的、女孩子气的窗户花纹都想到了。天哪,怎么这么美!
“建筑师”们怀着热情各自回家了,今天晚上,直到睡着之前,他们心中都被这个火热的念头塞满了,不能够再想一丝别的事情。
全宝把牛拴在屋前的牛笼屋里,隔壁矮一点儿的猪笼屋里猪满意地哼哼着,大概梦见什么美事儿了。全宝走上一截石头垒的台阶,把脚上厚厚的泥跺跺。
他口袋里装着刚挣来的五毛钱,是从鱼贩子那儿得来的。全宝高高兴兴地站在老桦树下,仰头看着,嘿嘿,笑出声来。
大门开着,灯光打在屋前的空地上,跟灶屋的灯光交错在一起,散发出温暖的黄晕,让人看着心安。
全宝听见妈妈在灶屋里气鼓鼓地高声骂他,可他呢,拎着鱼,抬手抬脚地,走得像得胜还朝的将军。
“哥,哥,这么多鱼,这么多!”成宝像只小狗,跳过来围着哥哥团团转。
大姐正坐在大门边的小板凳上一根一根理着稻草,搓草绳,看见全宝手里的鱼,笑了。
“嗨,你有本事,逮这么多!妈,你看三子,逮许多吸水鱼。”二姐从她跟大姐合住的房里跳出来,大呼小叫。
妈妈从灶屋探出头,一双手还滴着猪潲水。
“妈,给!”全宝很气派地把鱼双手一举,递给妈妈,底气足足的,不担心挨骂。
要吃肉,端午节;要吃鱼,河开坼。年早过了,节还远呢,他们一家都多长时间没正经吃过一顿荤菜了。
妈妈接过鱼,沙漠里的水一样,怒气瞬间不见了。
“都什么时候了,又疯忘记了,一身泥,去洗洗,吃饭!”话虽是一样的狠,音调却不同,全宝清楚,于是高高兴兴地进了灶屋。
锅盖边冒着蒸汽,饭菜还热在锅里。啊,碗里还有一小块鸡蛋羹,是特意留给他的。
全宝选了一个大蓝边碗,盛了满满一碗饭,把菜堆得高高的,端个板凳坐在大姐身边,小心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吸着鸡蛋。
成宝把那个挖空了的鸡蛋碗捧出来,蹲在哥哥身边,小脸埋在碗里,细细地舔着,咂着嘴。
“好吃佬吃细食。”二姐在一旁撇着嘴嘲笑弟弟们。
大姐双手一下一下,搓着手心里的草绳,笑着。“笑什么,有么好事?”全宝问。
“有么好事?男朋友呗。”二姐一扭脖子,坏笑。
大姐停了手,叫道:“再说我撕你的嘴!”看来真恼了,她长辫子一甩。
“大姐才不想男朋友呢!你想也没人要你。”全宝生气地瞪二姐。全宝可不想大姐嫁人,大姐嫁人了,妈揍他,谁开交(结束,意指劝阻)?跟二姐干仗,谁护他?
“你想也没人要你。”成宝也说。他是全宝的跟屁虫。
“妈,他们说我没人要!”二姐对着灶屋嚷嚷。
“这么大姑娘臊不臊,疯疯癫癫的样子总不改,真没人要了。”妈妈大声唠叨。
大姐对全宝说:“我刚才是高兴,咱家的秧最好,出得最齐,今年稻好,明年就能做新房子了。”大姐继续接着搓。
全宝家的土坯房子还是爷爷那辈做的,矮趴趴的,三小间,外加一个小小的灶屋。一家六口人,挤得房子鼓胀胀。
“真的?跟隔壁大贵家一样的?”成宝从碗里抬起脸,高兴地问。整个村子数大贵家的房子最好,去年新起的,高凛凛的四间红砖瓦房,屋前还箍个院子,就是深宅大院的感觉。
大姐笑了:“那恐怕不行,人家是队长,脑子活络,咱们没那么多钱。”
“咱家的牛再下一头小牛,卖了,明年再收一季,就能动土做新房子了。”在一边坐着抽烟,一直笑眯眯没说话的爸爸开口了。
爸爸歇息的时候,爱斜靠在一个竹编大椅上,半眯着眼睛,抽会儿烟。
“真的?”全宝像得了保证。
“真的?”成宝也跟着说。
“嗯。”爸爸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
“新房做好了,春芳一个人住一间。”妈妈提着一把扫帚,凑过来说,“春芳是大姑娘了。”
“不,我还跟大姐一间!”二姐扭着肩膀,腻到大姐身边。
“我还跟我哥一间!”成宝往全宝身上靠。
“去,谁跟你一间,你打呼噜能抬走人!”全宝学妈妈说爸爸的话,故意逗成宝,“我一个人一间,我都大了,大贵就一个人一间。”
大贵房里有面镜子,能对着仔仔细细地做各种鬼脸,还能看看发型,全宝也想有。
成宝痛苦地皱皱脸,一蹲身,舔第二遍碗。
这个小跟屁虫,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崇拜哥哥,爱缠着他。全宝却不喜欢跟他一块儿玩。大概是妈妈总说成宝听话,爱学习,全宝呢,淘气,没心没肺,学习也不上心,全宝心里就不高兴这个弟弟了。再说,成宝跟在他后面,他哪能玩得痛快。
“老桦树放倒,做阁楼的木板就够了。”妈妈喜滋滋地说。
“老桦树?要砍老桦树?”全宝可吓了一跳,大姐、二姐,连成宝都吃惊地看着妈妈。
“不能砍!”全宝急得一瞬间脸涨得通红。
三个孩子同时直着嗓门跟妈妈吆喝,反对她。
“不砍?你叫我拿柴火棍子做楼板?”妈妈脸一绷,反问。
“就是不中!”全宝捧着半碗饭,气得鼻子直抽气,“我们都没好玩的东西,也没养狗,猫也没!”
好玩是一点,名气地位的计较也是一点,就只说老桦树陪他长大,他也舍不得。第一次被天牛咬了手指,是在这树上,他气得掰下了天牛的大牙齿。他还在小木屋里打过瞌睡,尿过裤子,骗成宝把掉下的第一颗牙齿放进了树洞里,偷偷地藏在树上吃过一个糖……反正,全宝决不能答应砍树。
“嗯,就是不中!”成宝单手抱着空碗,一挺小胸脯,帮腔。
“玩,玩,就知道玩!这树你不是都玩了十二——十年了?”媽妈改口说,全宝十二岁,他不能一生下来就爬树,“一样东西玩十年还不够?”妈妈气呼呼地说,使劲儿扫着地。
全宝不吃饭了,把嘴噘得能拴一头牛,可是他没话回妈妈。玩十年了,也是够长的。
“我呢,我还没玩十年!”成宝朝妈妈尖嗓门叫。
“对,成宝才玩三年,他笨,四岁才会爬树!”全宝一下找到了理由。
成宝回头委屈地翻眼看着全宝,他讨厌哥哥又帮他,又损他。
“过日子要紧,还是玩要紧?”光是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就够妈妈忙的了,玩儿的事,她态度一贯消极。
“玩要紧!”成宝斜着右半边身子,气冲冲地往前一上,他还不懂生活的道理呢。
全宝却无话可说。唉,懂道理的人生活得就是累。全宝狠命地扒了一口饭,愤愤地嚼着。
妈妈懒得理成宝,把尘土扫得愤怒地飞扬起来。几个孩子“嗡嗡嗡”蜜蜂般围着你吵,你试试烦不烦?
全宝求助地看看大姐和二姐。
大姐闷头搓着草绳。她体谅妈妈的难处,也体谅弟弟妹妹的心思,不知道该说什么。二姐呢,坐在大姐身边的小板凳上,也阴着个脸,生气,可任她伶牙俐齿,也找不出一句话来反驳。
按理说,二姐十五了,不会太留恋小时候玩的东西,可这老桦树、小木屋不一样。知道他们村的小顺子么,眉清目秀,读书也好的那个。如今人家在城里读书,几个月才回来一次,一回来就跑到全宝家门口,为的是爬一回树,上一回小木屋。每到这时,二姐就变得斯文起来,笑盈盈的,脸红红的,仿佛里面有盏灯照亮了。她搬个凳子坐在门口,假装做事,跟他说话,心“噗儿噗儿”地跳。
你说,老桦树一砍,人家还来?
爸爸坐直身体,把烟头丢在地上,踩灭了,说:“阁楼的板要三百块吧?”
“么意思?要买?”妈妈扫帚一停,拿眼睛斜瞪着爸爸,“你是钱多了?三百块哎!”她知道爸爸有时候瞎惯孩子,大贵的大哥说他浪漫主义,妈妈却说,他那是猪脑筋。
“我跟你说,你别动什么歪脑筋,我这次不会依你们瞎来。”妈妈一抻脖子对爸爸嚷,凶悍得抱母鸡一般,护着一点点辛苦挣来的钱。家里的钱历来一个萝卜一个坑,少一分日子就过不转,她决不能让这些不懂事的家伙们糟蹋一丁点儿。
全宝、成宝跟二姐愤怒地看着妈妈。如此的“同仇敌忾”,三个孩子还从没有过。
全宝坐在他心爱的小木屋上,抽抽搭搭哭着。
大姐对他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他十二岁了,算得上是男儿,不能随随便便地哭鼻子。可是他一个人坐在小木屋上的话,想哭就能哭,算不得随随便便。他在心里算过,这世上三个人最亲,爸爸、大姐、老桦树,如果老桦树能说话,就算得上是个非常好的人,全宝能跟它说任何话。
全宝在小木屋上站起来,仰头看着老桦树的顶端。老桦树铁干虬枝,表皮粗黑厚实,四根粗壮的枝干直伸半空,铁塔般的一个“彪形大汉”。春天刚到,一个个圆满粉嫩的小小芽儿仿佛一夜间冒了出来,细细地缀在这大汉满身。老桦树就这么又稚嫩又粗粝,莽汉抱着婴孩似的,仔细一想,不协调得让人发笑。
小木屋的地板被孩子们磨得光溜溜的,赤脚踩在上面,很亲切的感觉。
它是爸爸做的,牢实得很。家里的孩子,除了大姐,都爱爬树。全宝能走路不久就会爬树,攀着一根软梯,一小步一小步地往上爬,看得人心惊肉跳。二姐在上面伸手等着,把他拉上去。后来成宝也这么一步一步地爬,全宝和二姐一个在树上候着拉他,另外一个在树下,防他摔下来。
“可以这么说,在那上面乘凉,说话,写作业,就像开了光点了睛,哪一样都比在地上有趣十倍。”二姐以前常这样跟人炫耀,不过那时她还扎着两个辫子,现在她十五岁了,喜欢把头发披散着。
你说,这样的老桦树,这样的小木屋,姐弟三人能不当宝贝?全宝抱着一根粗枝,把脸贴在上面,泪水流到树皮上,湿湿的。
树皮粗拉拉的,硌脸,可全宝不嫌。老桦树这会儿比任何时候都亲,他抱了一根,又去抱第二根,又去抱第三根、第四根,好像过了这一夜,明天一早,妈妈就会砍了老桦树,他就再也没有它了。
如果可以,他会把老桦树抟成一小团,护在怀里,不让人碰它一下。
“三子,三子。”树下黑黢黢地站着个人,是二姐,“你下来。”
“哥,你下来,有事情。”成宝也咚咚跑来仰脸喊着。
全宝垂头丧气地下了树。
“二姐说,我们商量商量老桦树的事。”成宝眼睛亮亮的,很快活,仿佛他们一商量,事情“吧嗒”一下,东西落地一般,就解决了。
是那么简单的事?他们家的孩子一年到头两手空空,没零花钱。其实全村的孩子也就大贵口袋里有钱。
他们家本来底子就厚,他爸爸又能挣些活络钱,而且两个哥哥比他大很多,一家人都惯他,常五毛、一块地给他。大贵也不小气,会到村头小店尽数换成各种吃食,跟大水、全宝分着吃。
可三百块啊,全宝总不能都让大贵帮忙凑吧。天早黑透了,月亮不知不觉到了中天,空气中满是油菜花馥郁的香味儿。一条黄狗咻咻地跑来,把大贵家的大狸花猫追得一头蹿到老桦树上,不敢下来。全宝姐弟三个站在老桦树的暗影里,愁眉苦脸。
“我们能不能求求妈不砍老桦树?”全宝愁眉苦脸地问。
二姐不回答,她蹲下身,用树枝在泥巴地上划来划去,拧紧眉头想着什么。
“能不能求求妈?”成宝凑过去也问一次。
“想都别想!三百块哎,你们一年的学费也就一二十块,妈肯定不干!”二姐一口否决了这个提议。三百块抵多少年学费?成宝想了半天也算不清,就请教哥哥。哥哥说二十年。成宝无力地蹲下来,呆眼看着前方,叹了一口气说:“我二十年不上学,才能把三百块省下来。”
全宝觉得他真傻,不想理他。二姐忍不住笑了,一拍他的头,说:“亏你想得出来,这么好的主意。”
求爸爸也许行,可是全宝担心妈妈会跟爸爸吵架,还是算了。他心里掂量了半天,探过身子,压低嗓门说:
“我知道妈把钱藏在哪儿——”
“嗨,亏你想得出!要偷家里的钱!”二姐厉声喝他,吓得他一缩头。
再想保住老桦树,也不能不顾道义。
“不能偷东西!”成宝竟然也对敬爱的哥哥嚷。全宝生气地鼓着嘴,咕咕哝哝:“我又不是为我自己。”
他心里突然很生老桦树的气,一棵老树,干吗要值这么多钱呢?害得人为它操心,还这么丢脸。他本来想狠狠地踢它一脚,结果呢,在树干上拍了一巴掌。
“要不,我们捡知了壳卖?”成宝又想了一招,小眼珠子亮亮的。
“知了壳?一屋子的知了壳也值不了三百块。”全宝冲他一句。
“要那么多?”成宝傻了眼,搔搔耳朵,再也想不出办法了。
月光朗照着,夜色澄明。萤火虫提着它的小灯笼,悠闲地在老桦树下来回溜达。
一个很响的声音从大水家的草堆边传来,是一种叫“黄狗”的很大的青蛙。全宝捡起一块石头,气恼地扔过去,“黄狗”顿时哑了口。
二姐突然扔下棍子,抬头问:“三子,你说,爸妈做房子是不是还得要一年?”
全宝眨了几下眼睛,说:“嗯,爸说要等下小牛呢!”
“三百块分十二个月,一个月二十多块。”二姐算起账来,“三子,这钱我们自己挣,中不中?”二姐“呼”地站起身,目光灼灼的,激动又坚定的样子。
全宝可吃了一惊,这是多少钱啊,自己挣?全宝也挣过钱,抓黄鳝、抓鱼卖过,偶尔也晃过妈妈的火眼金睛,偷个鸡蛋换了钱买吃的,但那也不过是一两块的。
三百多,山大的一堆钱,得几稻箩黄鳝、几稻箩鸡蛋啊,把他自己卖了,也值不了这个价吧。
“好,我们自己挣,自己挣!”成宝不知死活,举着小胖胳膊,热情洋溢地直跳。
“挣?你挣得到?把你卖了也不值这个价!”全宝瞪了他一眼。
“喂,李全宝,你是不是怂了,成宝都敢,你不敢?”二姐大声吆喝。她一跟全宝斗气,就叫他大名。
蛇打七寸,二姐一招击中了要害。大姐跟爸爸都说全宝是家里第二大的男子汉,他就常常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堂堂的,有名有姓的。世界上哪个男子汉不讲自尊?他全宝怎能认怂呢?
“谁说我不敢?”全宝把脖子一梗,“我是怕成宝不敢!”
“我敢!”成宝往前上一步,勇敢地说。
“这还差不多。”二姐笑了,拍拍全宝的肩膀,“不愧是男子汉二世。”她嘴一撇,调侃全宝。
全宝听了却颇为受用,得意地抿抿嘴,问:“你说,我们怎么挣?”
二姐很有把握地看看成宝,又看看全宝,“三子,你能做哪些挣钱的事?”
全宝翻翻眼睛,说:“抓鱼,钓黄鳝,还有鳖!”
“我也会。”成宝迫不及待地插嘴。
“去,你能做什么好事?”全宝翻他一眼。那次他跟成宝一起抓鱼,好好的几条大鲫鱼,成宝一跌跤,把鱼篓子摔到了河里,鱼跑得精光,气得全宝再也不带他抓鱼了。
“他不是小嘛!”二姐给成宝帮腔,“成宝,你别急,一会儿换你说。”二姐这个人就这样不公平,跟全宝像是前世有仇,对成宝却仁义道德地好。“爸爸还在山上下过兔子。”
她又说。
“嗯。”全宝直点头,“咱家田里麦子要熟的时候有野鸡、角鸡,罩着了也能卖钱。”
“还有刺猬。”成宝叫道。
“我呢,去山上挖草药。”二姐挥挥手,说。他们村大一点儿的女孩常过一条大河,到对岸的山边挖一种草药根,很值钱。
“天氣好的时候,一天一趟。我知道哪儿的草药多,一年下来,包能挖到两百多块钱的草药。”二姐胸有成竹。
两百多块,全宝一盘算,不算成宝,他自己一年只要挣个几十块。嗯,还不错。全宝看着二姐,咧嘴笑了,很满意她的豪气。
“那我呢?我干么事?”成宝着急了,跳起来,生怕没他的份。
“你就捡知了壳吧。”全宝说,倒是认真的意思。成宝皱着小脸,以为哥哥在蔑视他。唉,他才七岁,除了会捡知了壳卖给那些收杂货的,就是到田里捡人家收割后脱落的稻穗,可那是给鸡吃的,不能挣钱。
“成宝,你捡知了壳,也能卖钱的。”二姐说。成宝高兴起来,又嗯嗯直点头。
“家里的活,我们要重新分一下。”二姐接着谋划,“全宝,从明天起,牛归你放,我要腾出时间上山。”
“我要上学呢!”全宝急忙说。
全宝才不想放牛。大水家的牛归大水放,农忙的时候,牛一整天都吭哧吭哧地耕田、耙地,大水就要做它的炊事员,管好它的一日三餐。大水又要上学,又要放牛,忙得难开交,就觉得受了奴役,连连叫苦,说哪一天他要提出抗议。
“大水不也上学?”二姐翻眼抢白全宝,“成宝,你喂鸡,喂猪,扫地。”成宝乖乖地点头。这些本来就是全宝做的。
“洗衣服我一早一晚抓点紧。”二姐盘算。她大人一般,行事能干,又主动挑起大梁,要一年挣到两百多块,倒是很让全宝佩服,不好意思再躲懒了。就这样,从明天开始,以后的一整年时间里,姐弟三人要为老桦树和老桦树上的小木屋大忙特忙起来了。
连村里人都知道,老二家的三个孩子都忙着挣钱呢。
爸爸在家族里排行第二,人家都叫他老二。
选自《老桦树上的小木屋》,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8月1日版。
朱桥,原名罗小梅,安徽宣城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先后于小学、初中、高中任语文教师,现为安徽宁国中学语文教师。2015年开始儿童文学写作,在《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十月少年文学》《读友》上发表作品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