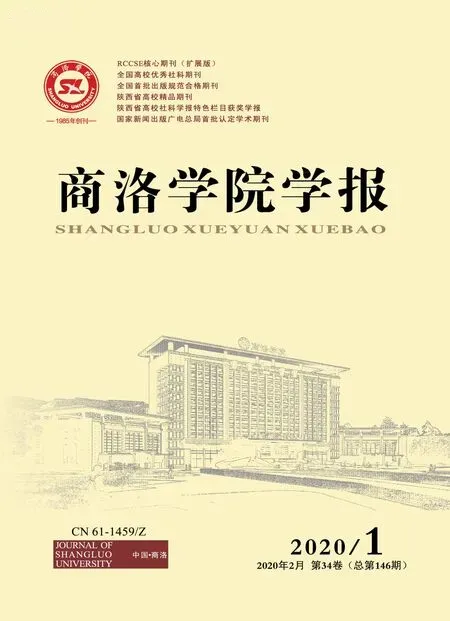传教士在近代西北的“赈灾辅教”研究
谢亮
(兰州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郑观应说洋人传教意在“服华人之心”[1]。章太炎言西人欲断“国学”而灭中国之种性——大抵指今日所谓文化——当自传教士始并是鼓动最力者[2]。西人盖茨言:商业、制造业、文学、科学、艺术以至情操、道德和宗教而非政治控制,是西方实现和平、征服世界之手段[3]。受宗教使命感驱使的传教士,曾决心要在“异端”世界中“传播福音”以拯救灵魂,而非创制一基督教的俗世社会[4]。在近代中国,传教士积极参与各地的赈灾,亦是为促成上述目的的重要凭证。此间,近代中国西北地区亦被传教士视为急需传播福音之地。如埃克瓦尔兄弟即在此境遇中于1896年从宣道会华中教区的芜湖入“甘肃教区”,并在临潭、岷县传教。因为此地是“急需(福音)的土地”①,传教士在西北“赈灾”辅教之举措亦与“俗利”或“实利”纠杂。有鉴于此,本研究拟就传教士以“实利服华人之心”中的赈灾辅教举措与前述命题之关系作一探讨。
一、“灾荒赈济”与“禁教”解除后传教士进入西北
“禁教”命令解除后,传教士大举进入西北当自咸同两朝始,至光绪之时则可谓是再次大举进入。而且,从“五口通商,五口传教”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传教士即已获得在内地传教的特权。如1873年有传教士在甘肃榆中大兴营村设坛传教[5]。在新疆,有研究虽称19 世纪初天主教已传入新疆[6],但《新疆图志》中则言“新疆教堂之设,实始于光绪十三年”,其时,“法国神父石天基、梁明德于宁远(伊宁)城外东梁上设天主堂”[7]。此外,1883年有圣母圣心会之传教士在伊犁传播福音者②——亦被视为是新疆近代最早的天主教传教行动[8]。1887年,除在伊宁(宁远)由石天基和梁明德建天主教教堂外,在霍尔果斯(绥定)、玛纳斯、乌鲁木齐(迪化)、呼图壁等地,天主教堂亦相继建立,“入教者无分(非)旗人汉人”[9]。在青海,穆敬远并非是过往公认的最早到达此地的传教士[10]。《青海省志·宗教志》和周振鹤所著《青海》 皆记录内地会传教士至迟当在1878年进入青海。其中,该宗教志称义敦巴、格达于光绪四年到兰州、宁夏、西宁布道传教,在西宁设总堂,湟源、贵德亦设福音堂。后者更言除兰州、宁夏、西宁之外,内地会传教士在青、藏一带传教[11-12]。另,有研究证明,内地会的义世敦、巴格道于1879、1884年即入青海[13]。
参与灾荒赈济是传教士进入西北后接近民众的重要途径。近代西北灾荒频发,堪称典型者则有波及陕西的“丁戊奇荒”和1899—1901年的陕西大旱等。“丁戊奇荒”之时,传教士即言陕、豫两省官员在赈灾时始“与西人不合,请西人不必散赈”——但一段时日之后亦有部分官吏认可西人赈灾[14]。《宁羌州乡土志》记载,1901年陕省大旱,宁羌州西爆发饥荒,传教士郭西德即“以赈济为名,诱民入教”[15]54。而且,传教士在参与灾荒赈济时除直接捐献钱物外,亦有实施医疗救助和收养弃婴和孤儿等善举。如同治回民变乱时,陕西天主教徒即在高陵县通远坊教堂创设孤儿院,收养弃婴和孤儿[16]。
庚子乱后,传教士在西北的“福音”传播活动得以恢复并加强,其赈灾的组织化程度和赈灾方式亦加速演变。如华洋义赈会较大规模地涉入西北灾荒赈济和慈善事务即在此期之后。事实上,创设华洋义赈会的机缘巧合即在于1920年北方五省的特大旱灾,其时2000 多万灾民,人口损失50 万[17]。其影响遍及包括陕、甘在内的全国16 个省份,其在地方分会、事务所、赈务顾问委员会总计达17 个。虽不可高估华洋义赈会在西北的赈灾实效,但它确实是参与近代西北灾荒赈济和慈善事务的最主要的专业性民间组织。其赈灾理念和积极施行工赈之举措,亦是传教士涉入西北赈灾事务之堪称典型者。例如,1928—1933年西北旱灾爆发,陕、甘两省尤重,整修渭北泾惠渠和西兰公路两件大事,即是该会所为。
二、传教士“赈灾辅教”的主要举措
李提摩太曾言,赈灾是“福音传播”的恰当方式之一。在近代西北,调查、报道灾情,捐献钱粮,煮粥活民,散发赈粮,兴办工赈,为民众治病和提供避难场所,是传教士进行“赈灾辅教”活动的主要举措。
(一)记录、报道灾情及引介“新知识”
在近代,国人多将西北视为边陲之地。即便如陕西者亦是如此。传教士亦言,西北作为世界边缘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皆难为外人知晓[18]288。西北每遇灾荒,内地民众无从知之,筹集钱、粮以赈灾之事亦无人问及[19]。基于此,传教士利用自身信息渠道将灾情及时报告外界,以利于赈灾。此行动类似于民间勘灾、报灾,是西北正在形成中的灾情信息传递、动员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含着“新知识”的引介。其关键理由有两点。
一是传教士撰写的灾区见闻常是《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新媒体报道西北灾情的重要信息来源。如“丁戊奇荒”中,传教士撰文描述陕省灾情,经由《申报》报道即被江南社会所知。尽管此类报道量小,信息有限,但这或可视为西北灾荒赈济中新的灾情信息传递机制的萌芽。再如,1893年,浸礼会在陕省仅有的2 名传教士虽尚未组织具体救灾活动,但其在《北华捷报》上撰文报告灾情,行募捐之事[20]。1901年,有强烈宗教背景的美国《基督教先驱报》派记者报道陕省灾情,并在美为陕西灾黎筹集善款;其记者在陕西还与郭崇礼等传教士合力赈灾[18]67。1927年,甘肃震灾爆发,蒲登勃洛克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撰文报道灾情,并被《东方杂志》翻译和登载[21];《大公报》直言传教士撰写的灾情调查或报道是其灾荒报道消息的重要来源[22]。《大公报》还翻译并刊载了传教士从武威发给上海《字林西报》的震灾情况及灾民生存状况的报道[23]。1928—1933年西北大旱,1928年10月,席尔池在《大公报》上撰文报告:旱灾使陕西千里皆成赤地,在陕北苦旱之地,村雨未滴使寸草难生[24]。
二是传教士在撰写的灾情报告或灾区见闻,以及其他著述或赈灾刊物中,分析灾荒成因,思考赈灾应对,抑或详细记述赈灾的实际举措等,这些内容在客观上形成了西北灾荒赈济“新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尤其是,传教士及其差会组织主动与报刊及其外派记者的合作,亦使其自身成为了建构新灾情信息传递、动员机制的实际推动者。需指出,传教士进行的各类调查虽然因超越赈灾的需要而常被过往研究所否定,实际上它不仅属普遍行为,亦在不经意间成为其“认识中国”和参与赈灾的知识“依凭”之一。例如,1922年问世的《中华归主: 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即是此类调查的实际结果。此调查自1918年开始,历时3年,涉及“各省的行政区域、面积、里数、边界、城市、人口、地势、山川、民族、语言、气候、物产资源、经济状况、水陆交通、邮电、学校、医药设施等以及传教历史和教会活动情况”[25]。
(二)捐献钱、粮
在清末陕、晋、直隶诸省的大灾中,在沪“西人出资助赈,为数达20 余万,并有西教士等,热心参加救灾工作,前赴灾区,共同放赈”[26]。1901年,陕省旱灾爆发,敦崇礼将第一笔善款带往西安后,《基督教先驱报》募得善款,仍陆续被汇往西安。据载,与是次赈灾拨付之500 万两官款相比,自美募捐所得6 万美金(合银8.6 万两)即占其总额的 1.7%[27]。1910年 9月,Gco.Andrew 在《教务杂志》撰写《甘肃救济金报告》一文,记述了传教士及各地信徒的捐助款项以及救济兰州、靖远等地灾民的实际情形[28]。
在民国时,传教士为西北赈灾而进行捐献的频度更高,规模更大。例如,1920年 12月 18日,宁夏海(原)固(原)震灾爆发,内地会迅即赈灾,于数月内即筹集善款12 万元,并从沿海调派安献令加强现场指挥[29]。最典型者:华洋义赈会在渭北泾惠渠工程投入资金391 635.12 元(1931年),西兰公路工程 1931年 350 000 元、1932年50 000 元,甘肃赈务 50 000 元(1931年),分别占当年赈款的 40.74%,36.39%、2.3%,5.22%[30-31]。此外,华洋义赈会在陕西三原将“赈洋1 000 元散给北社埝村一带灾民”[32];1928—1933年北方大旱,陕西成为重灾之地,美国民众即于1928年筹组设立美国华灾协济会③。截至是年12月31日,该会通过华洋义赈会向华拨付赈款260 724.68美金,其中54 750 美元用于建立掘井贷款基金[33]。1929年 2月 26日,华洋义赈会在《大公报》刊发“赈务重要文件”,报告“美国已捐到赈款11 万元”,其中 5 万元“购粮运陕西”[34]。另,1928年,该会亦为救济同官(铜川)灾民用银1 000 元[35]。1940年,华洋义赈会还向陕南施赈3 460.72 元④。
(三)煮粥活民、散发赈粮、兴办工赈
在 1928—1933年的大旱灾中,1929年 11月—1930年3月,百余天之内,天主教传教士丁午桥等人受官府所托,用所筹赈款在渭南下吉镇设“舍饭场”,“赈济生熟饭小米30 余万斤折合币三万多元”;而且,除委托地方名士在渭南吝店发放赈款5 000 元外,他们还向大荔、朝邑灾黎发赈款10 000 元。1929年,神父柏宜厦用华洋义赈会所拨赈款在商县东关娘娘庙内、白洋店(今白杨店)、夜村设粥厂,被当地民众称为“大善人”。在甘肃,1929年,天主教会不仅在武威放赈,亦在甘谷散赈款8 000 元,向灾民发寒衣2 697 件[36]。另,1929—1931年,甘肃救世新教会亦开办粥场,并在兰州的庙滩子、东关、南关三处按日均2 000 余斤标准设点专向贫民卖面⑤。再如,华洋义赈会在西安特设“工赈办事处”,招收约4 000灾民整修马路,每人每日发面1 斤12 两,并于省垣四关各设粥厂1 所,按日施粥1 次,日可赈济灾民 13 000 余口[37]。事实上,民国 20—30年代该会在西北实施的较大规模的施粥、散放赈款、赈粮活动对灾荒赈济确有重要贡献。而且,除西兰公路、渭北泾惠渠这类重大工程外,1921—1933年,华洋义赈会耗资320 859 元和711 587 元,在陕、甘两省分别修理、新建了14 条总长362.5 km 和 13 条总长 366 km 的地方公路[38]。除前述典型事例外,一些县志也记载了传教士煮粥活民、散发赈粮等举措。例如,1865年美国传教士在蓝田开办禁烟局,创设天足会,设施粥厂[39]。1929年,教会组织灾民在合阳以工赈修建金水沟石桥,并向灾民施粥[40]。1931年,在陕北延长县,神父向灾民散发粮食,助灾民活命[41]。
(四)合作思想之引介及实践
民国之期,合作思想及其运动的影响日益扩大,传教士在西北赈灾于此自不例外[42]。华洋义赈会曾耗资4 000 元在长安、咸阳等地开设农村合作训练班,并指导创办农业合作社[43]。陕省主席邵力子力邀该会在陕推动合作事业的开展。1933年,该会与陕省建设厅合办的合作讲习所,其培训之60 名学员——文化程度从小学到大学皆有——回乡亦确有组织合作社之具体举措。此外,长安、咸阳亦有一些信用合作社的创立。随着国民政府实施西北开发计划,1934年,华洋义赈会执委会副总干事章元善受宋子文之请,赴沪商议到陕发展合作事业。是年7月,以邵力子、章元善等为首的陕省合作事业委员会成立。经此推动,至1934年,陕省已有31 家信用合作社[44]。为推进陕省合作事业,1934年12月,华洋义赈会帮助草拟《本会推行合作事业方案》。该案言:其“目的在救济农村贫困,促进农业建设”; 其方法,“先从信用合作入手”,“全力灌输关于合作之知识、技能及供给资金之便利,以冀引起农民之兴趣与热心”,强调“应以物质增进及精神陶冶并重”;所以,“兴办切身需要各种公益事业,如提倡节俭、戒烟酒赌、举办民众学校、养老恤贫之类”[45]。
(五)战乱时救死扶伤、接济难民
近代西北,特别是陕甘一带,战乱频繁,匪患严重。而且,兵燹之祸与自然灾害叠加,民生至为困苦。白向义曾言:陕西兵匪之祸猛于灾荒。因为,举凡粮食、牲畜乃至运输车马或车辆无不为军队强占,民众外出则亦时常为盗、匪劫掠[46]。在此情势下,传教士在战乱时的救死扶伤和接济难民亦自然是一种赈灾善举。例如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潼关一带战事激烈。浸礼会即设5 处临时战地医院,教会医院英华医院亦成“军事医院”。此外,罗伯森、荣安居、贾尔德、荣安居夫人及1 名护士还汇同当地信众,在西安坚持救助600 余住院病患和数百位门诊患者[47]。1913年3月,罗氏因劳累染病而亡时,诸多受其救助的伤残军士在他的灵前痛哭感怀[48]。1926年春,陕西军阀混战,“民十五之役,西安围城八月,饿死人逾十万之上”[49]。其间,邵涤源、武诚齐等留守城内,救济难民。广仁医院的司徒礼克等亦积极救助伤员[50]。抗战时,浸礼会之广仁医院及城内和东郊的教堂皆毁于炮火[51]90,但传教士尤皮彻亦有冒险赴沪购药之善举[51]71。
为难民提供避难所、食品,收容孤、寡,也是传教士重要的慈善救助举措。在咸同回民变乱时,传教士在陕西高陵县通远坊教堂创办孤儿院,收养弃婴、孤儿;在1929年灾荒中,该院收养孤儿300 余名。而且,被收养的孤儿亦有被送入教会学校以培训其谋生技能者。同时,他们还创设养老院,收养孤寡老人⑥。在西安,1907年圣母圣心会设堂传教,在南堂、糖坊街教堂救济和收养孤儿。1929年,该会在东堂设孤儿院,其传教士彭琴堂亦在商县创办孤儿院。据统计,至1932年,前述三所孤儿院共收养孤儿138 人。1929年,张指南神父在扶风县绛帐镇设孤儿收容所——后成育婴堂,由圣女圣心会修女管理。1930年、1932年,安康、大荔、凤翔及陕北等地,传教士创办“保赤会”、孤儿院、残老会。抗战时,“(浸礼会在陕——引者注) 两所孤儿院收留战争中遗留的孤儿,浸礼会还资助学生完成学业,资助难民赈款购买粮食,并帮助失业工人寻找工作”[52]。1928年,在甘肃岷县县城和宕昌两地,辛普逊兴办贫儿院,收容孤儿600 余名,除供给食宿外,亦传授其制鞋、织毛毯等手工技艺。这是近代西北难得一见的新式赈灾实践之一⑦。在新疆,1920年,传教士在莎车设孤儿院1 所,收容回族儿童 12 名[53];1933年,传教士在此将其扩建成男、女孤儿分别收留,且有专人专责孤儿收留事务的孤儿院[54];至1938年经营停止之时,共收留百余孤儿⑧。
三、始料未及之后果与影响
1819年,传教士米怜曾言“知识和科学是宗教的侍女”[55]。在西北,传教士将赈灾、慈善救助事务与教育拓展相结合,冀望民众能知道“许多迷信思想的愚蠢和谬误”[55]。其本意亦是以“世俗知识”和“科学”,“根绝和摧毁他们对自己关于世界和自然理论的信心”[55]。然而,民众却常获“实利”而不真近“福音”,这也确非“福音传播”之所愿。传教士与官、绅、民间的“实利”纷争更是“福音”传播实效有限的重要原因。
灾荒频发,使民众入教的目的多是“吃教”“恃教”,非真为“福音”所动。以陕西为例,在城固,贫民入教为的是“得到一点慈善救济”[56]。1899年,凤翔教务因传教士向灾黎舍饭和捐献钱物遂“有所发展”[57]。在民初的周至,天灾兵祸叠加,传教士赈灾善举便使“信徒发展很快”[58]。1922年,兵、旱为灾,马石臣在洛川县城传教时,通过华洋义赈会赈济灾民,使信众“日渐增多”[59]。1932年,华阴爆发霍乱,传教士赈济灾、困之民,向参加礼拜者给粮一升。此举遂使信众大增[60]。在延长,初仅数人入教,其余则“奇看西洋景,无心听教”。1932年大旱成灾,传教士遂放粮赈济,入教者遂日众,达“40 户 100 余人”[61]。
“恃教”,亦称“依教”“靠教”。入教者多因“实利” 诱惑或为词讼争端中借助教士之特权获利而入教,非真信教。仍以陕西的平利、城固、兴平等地史实为例:1901年,意大利教士入平利“传播福音”,民谣亦常言“以十字,圣架号,不打官司不进教”[62]。城固之富者入教即成依教士之特权势力而蛮横乡里者[63]。1900年,孙牧师等在兴平县城传教,“入堂听讲虽不乏人,大抵依为护符耳”[64]。更需指出,“恃教”“依教”“靠教”者多以社会底层生活者为主。正如外人所论:最不幸阶层(贫民、小店主、零售商和流浪汉)是1900年之时中国70 万天主教徒的主要构成者,他们“在现存中国社会制度中的命运最不能经受波折”[65]。所以,传教士如诺神甫等在镇巴等地传教时,宣扬“劝善救世,脱灾升天堂,入教蒙惠,不遭祸殃”[66],契合灾荒之际的民众心理。社会心理学家麦可·阿盖尔言,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危机常是传统社会中宗教复苏的重要时机或动力来源之一。加之,定期参加宗教集会、唱赞美诗等形式,对习惯于单调、沉闷而甚少娱乐生活的西北农民而言,也确有新奇之感。
但“实利”纷争,即传教士干预地方词讼以及绅教、民教纷争等行为,亦使更多官绅、民众远离“福音”。以教案为例,1901年陕西宁羌州西饥荒爆发,郭西德以钱粮赈济灾民并发展信众,但“泊来者日众,供亿不支,乃纷纷苛派良民,主客交讧,遂起焚杀之祸事”[15]57。在“三边”——靖边、定边及其安边堡一带,1872—1898年,自叶茂枝在靖边宁条梁镇设坛传教始,为吸引贫者入教,传教士或收购土地供贫民租种,或供给其籽种、牛犋。庚子之乱前夕,传教士在靖边从“小桥畔起至城川口止”,已租地4 735.5 晌,并另开垦城川口500 晌;定边县北至城川口席箕滩的半数土地悉为传教士购买。这使地方官员担心此地田产可能尽入洋人势力范围[67]。1903年的“平利洛河教案”即由民教矛盾发展而成⑨。
若暂不论及文化竞争命题,可发现“实利”纷争使官、绅(民)、教三者间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多是教案的发生。在近代西北,此种“实利”纷争并无东部士、绅、商所持之“商战”心态。事实上,尽管他们作为矛盾共同体本在彼此产生兴趣并关注对方,各自调适和磨合[68]。而且,在晚清教案中,当冲突激烈时,官府在压力之下,为息事,常保教抑民,牺牲无辜,进行赔款,或贬谪地方官绅,绅(民)教间矛盾遂激化。前论陕西三边教案内含的绅教、民教冲突,在西北同样并非孤案。以1901年、1902年的甘肃秦州教案和宁夏三圣宫教案为例: 秦州教案中,200 名侵吞粮款的胥吏集体入教,以图避祸。教士亦声言“天主教徒,不应问罪”,公然袒护,包揽词讼。压力之下,州、道、省等衙府屈膝忍辱,不查贪污胥吏,却革去检举人士张思忠、白正玉、杨虎臣等的功名[69]。三圣宫教案因教民与乡民的用水纠纷而起。因处庚子之乱后,陕甘总督松蕃恐生是非,撤换知府,申斥士绅,并下令杀7 名无辜者,并赔偿白银4 万两(后以地作抵),以平息事端。在1905年的西和教案中,庠生张凤仪与教民李春彦发生纷争,教士即告张氏诋毁耶稣,以后者道歉而平息[70]。
四、结语
“禁教”解除后,为传播“福音”,传教士大举进入灾荒频发的西北。参与灾荒赈济成为他们传播“福音”的策略性手段。客观而论,此种策略性手段之运用也是近代部分民众“入教”的重要原因,而且,它作为赈灾“善举”,不仅救助了处于灾荒困境中的部分民众,其一些赈灾新理念和做法的引入亦丰富了西北民间赈灾向“近代化”的转型。但是,传教士的此种“赈灾辅教”本欲图以“赈灾”之“实利”“服华人之心”,却是总体成效有限。因为,受自身深厚传统文化化育的中国民众,在面对传教士的此种举措时,更多的是为了接受“赈灾”之“实利”,而非传播“福音”。而且,传教士与官、绅、民之间的关系演进显示,“实利”纷争更是导致“福音”传播实效有限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见Report and Retrospect of the work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ee 一书。
②圣母圣心会第一批到达新疆的传教士有三位:戴格物(De Deken Constant)、杨广道(Jansen Andries)和石天基(Steen-em-an-Baptist)。
③见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救灾会刊》(1934年11月)。
④见 1939年 10月 4日《西京日报(南郑)》。
⑤见1982年《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 辑)》贺笑尘的《救新教会甘肃分会纪略》一文。
⑥见胡世斌《陕西天主教634-1949》第574页。
⑦见1988年《岷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 辑)》周珍、陈子明、景生魁的《基督教在岷县的传教概况》一文。
⑧见 1980年《喀什市文史资料(第 4 辑)》第 161页。
⑨“平利洛河教案”的主要原因及过程:其时,洛河团保袁瑞林、刘子模向民众浮派烟地税钱形成民愤,民绅詹朝珠等将其告官问责。是年5月,二人遂投天主教堂,为报复而向教堂诬告詹氏等勾连窗省哥老会人何彩凤毁谤教会。安康教堂教士即函令平利县知县王宗镰彻查。后者遣县役梁升将何氏缉拿,致使哥老会首领王乱刀子率众夺人时焚毁袁家并击杀其父子和4名教民,调查洛河事件的教民叶大伏和清兵高奉图同遭砍杀。官府即弹压,何氏遂集合众人在洛河旁的太白庙发动“兴汉灭洋”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