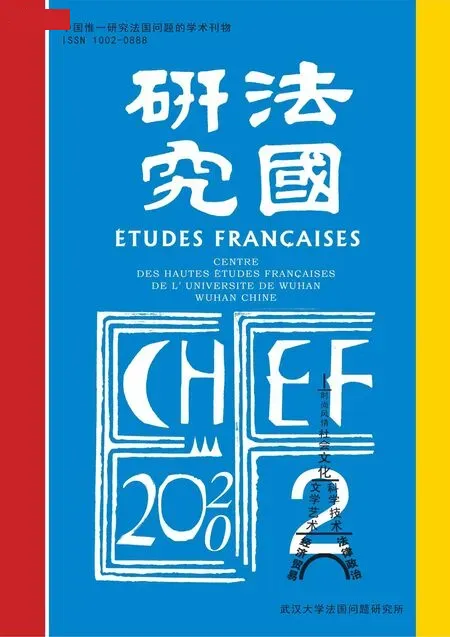托马斯·欧文奇幻小说中的写景策略
托马斯·欧文(Thomas Owen,1970年7月22日-2002年3月2日)是当代知名的比利时法语奇幻小说作家,著有《奇怪的路》(Les Chemins étranges)、《夜礼》(Cérémonial nocturne)、《母猪》(La Truie)、《夜墨小说集》(Contes à l'ancre de nuit)等奇幻小说集。
一、列举化写景
欧文在对环境进行细节描写时喜欢将日常生活中一系列不引人注意的未必有紧密关系的物品罗列在一起,在此基础上为各个物品补充相关的细节,形成一种欧文式的列举。《黑球》(La boule noire)的开篇对主人公居住的宾馆进行了描写,阳台、河流、窗户、瓶盖等日常物品被散乱地罗列在环境描写中,伴随着人们容易忽视但生活中常见的细节,描绘出了历史久远但略微年久失修的著名宾馆的样貌。
阳台新刷的水泥凹凸不平。铁制的阳台栏杆好几处地方都生了铁锈。三层楼下的河流有银刃一样的弧线。从外边看,房间的窗户缺乏保养。油漆开裂剥落,少量胶合剂从窗玻璃脱落。我们看见地上有一个人们忘了捡起的瓶盖。宾馆处在极好的位置,享有盛名。①Thomas Owen,La truie et autres histoires secrètes.Bruxelles:Labor,1987,p.25.
《雨之女孩》(La fille de la pluie)的开篇对主人公德佩尔刚吉(Doppelganger,德语中意为“幽灵”或“另一个我”)所处的宾馆房间内部进行了描写,“桌上,一小束铃兰在花瓶里完全枯萎。在房间的角落里,在窗户和上了漆的衣橱之间有两个叠放着的灰布行李箱”②Thomas Owen,Conte à l'ancre de la nuit.Bruxelles:Labor,1998,p.35.,短短两句话中涉及了桌子、花瓶、窗户、衣橱、行李箱这些日常物品,勾勒出了朴素的房间环境。德佩尔刚吉外出散步时遇到神秘少女拉米(Lamie),同她一起前往“一幢巨大的红砖别墅,别墅独自耸立在乡村中,处在野草蔓延的花园中心,四周被野树篱环绕”(Owen,1998:39)。在别墅中,“他们上楼,经过了肮脏的房间、空旷的浴室、散布着带插画的旧报纸的走廊、空的饼干罐、镜子的碎片、压扁的牙膏管。在一个有裂缝的壶中,一棵干枯的植物上挂着一条褪色的带子”(Owen,1998:39),琐碎物品的列举及其修饰语勾勒出了被弃置已久的荒凉的别墅,我们从中仍能感受到当年人们在此生活的气息。在《伺机者们》(Les Guetteuses)中,欧文对郊区的小公园进行了描写,公园、房屋、信号牌、树木、草坪、长凳、沙池构成了郊区荒凉的小花园。
他这次处在郊区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园中,小公园被高大的灰房子环绕着,被几块强制车辆突然转弯避开公园的信号牌与车流隔离开,这伴随着刹车声和轮胎的摩擦声。浅绿的小岛,有几棵积满尘土的树木,有被修剪得不怎们样的草坪,有没有椅背的长凳,以及在中央有一个方形的沙池。(Owen,1987:39)
欧文在环境描写中的列举不仅仅局限于物品,人也可以成为环境描写中的列举对象,如《死去蝴蝶的翅膀》(Une aile de papillon mort)中对上秤发现自己只有2.9 千克的主人公费多尔·格林(Fédor Glyn)所处公园的描写:“吵闹的、不知疲倦的孩子们在保养得很好的小径上玩耍,大喊着互相追逐。一条胆怯的、谨慎的小黑狗闻着纸篓旁的东西。一个老人坐在长椅上,抬着头,手拄着他细长的拐杖,平和地嗅着旁边椴花传来的芳香”(Owen,1998:131),孩子、小狗、老人这些有生命的物体与小径、纸篓、长椅、拐杖、椴花这些物品共同组成了环境描写的列举,描绘出了热闹的充满生机的公园。
法国文学评论家菲利普·阿蒙(Philippe Hamon)认为描述在现实主义文章中的作用是消除虚假与制造真实,在奇幻文章中起的作用也一样,“所有在文章中‘持续'的叙述系统,即'占据'和'利用'文章中或长或短的片段,以及所有'系列'的变化和构成,都旨在引发'证据效果'、权威效果、说服效果……”③Philippe Hamon,Du Descriptif.Paris:Hachette,1993,p.51.。因此,列举化写景增加了环境描写的真实效果,其结构功能之一是奠定现实世界的环境,令读者相信奇幻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欧文还在列举的基础上添加具体的地点名称、街道名称或场所名称,以此进一步增强环境描写的真实性与可信性。如《汽车旅馆派对》(Motel Party)中的“这个地点叫沙伦市(Sharon),是从伍德沃德(Woodward)到埃尔克城(Elkcity)的道路上一处偏远的十字路口。十几个似乎不太清洁的小屋,一个还挺像样的快餐厅和一个卖油桶、牲畜链以及橡胶长靴的店铺”(Owen,1987:110);《别人的事》(Les affaires d'autrui)中的“我在三色旅馆(Auberge des Trois Couleurs)里。几张桌子铺着干净的桌布。一个很高的黑木柜台。一个我本想看到炭火燃烧的废弃的壁炉”(Owen,1987:149);《爱尔纳1940》(Elna 1940)中的“人挤人的布鲁日(Bruges)在绚丽的阳光下看起来像一个悲惨的市集。混乱的炮兵部队从各个方向横穿城市。最意想不到的车辆们与最可怜、最滑稽的车队在漠不关心中相遇”①Thomas owen, Cérémonial nocturne et autres histoires insolites.Bruxelles : Claude Lefrancq, 1996, p.43.
欧文并不满足于通过列举化写景为奇幻小说营造现实世界的氛围,他有时刻意在奇幻高潮前后插入一段以列举方式进行的环境描写,其结构功能在于模糊现实与奇幻之间的界限,使读者陷入犹豫与怀疑之中。在《被强迫的女人》(La femme forcée)中,主人公贝拉·冯·于(Bella von U)接到一个神秘电话,生命垂危的布尔夫人(Madame Buer)托人转告贝拉希望她去探视,尽管不愿意,贝拉还是前往宾馆探望年迈的布尔夫人,在宾馆内昏睡过去醒来后贝拉发现自己变成了布尔夫人……她踏上寻找真相的旅途,决定回自己家一探究竟。欧文在此时用了一段较长的文字对贝拉居住的房屋进行描绘,“这是一处灰色的肮脏的巨大的住所。我们在笨重的阳台下的建筑正面砖块的涂料层中还能看见爆炸留下的深深的痕迹。但窗户都很干净,配有鲜艳的窗帘。涂漆橡木的大门中间有一个光滑的青铜门环。但是门上也有好几个电门铃,如今时代的记号”(Owen,1987:77)。写实环境的描述紧挨着奇幻现象的巅峰,贝拉按门铃后看见“自己”从房子里出来对“布尔夫人”进行热情的问候,而对话过程中“自己”突然冲向一辆疾驶的车辆并被撞死,自己变回了贝拉而贝拉变回了布尔夫人,两人身份重新互换回来。在《母猪》(La truie)中,主人公亚瑟·克劳利(Arthur Crowley)因为糟糕的大雾天气决定在一间乡村旅社中留宿,他和旅馆中的老板娘以及老板娘的一众朋友玩“母猪游戏”,他在游戏中胜出并获得前往谷仓看母猪的机会。欧文用简短的列举对谷仓内的环境进行了描写,省略动词,突出一系列名词,勾勒出用于储物的谷仓的环境:“在内部,类似一种工具库,他能分辨出一把悬挂在墙上的梯子、一些酒桶、一些空瓶子、一些小酿酒桶、一根浇水管,甚至还有一辆女士自行车”(Owen,1987:17)。随后主人公发现谷仓内的猪圈并在猪圈内发现一个赤裸着的介于女人和母猪之间的生物,奇幻现象达到巅峰。欧文在奇幻高潮结束后重复了一次列举描写,“同样的被存放的物品。墙上的梯子、小酿酒桶、酒桶、塑料水管、瓶子……”(Owen,1987:17)。《母猪》的奇幻高潮描写形成了现实-奇幻-现实的结构,现实与奇幻交替变换,起到证据和说服作用的列举描写与无法理解的奇幻事件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让读者感到无尽的焦虑与不安。
欧文通过将列举手法与细节描写手法相结合,以简单朴素的文笔描写日常的现实环境。列举化写景既起着建造现实世界环境作用,又起着模糊现实与奇幻边界、制造疑问的作用。
二、视听化写景
欧文擅于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奇幻灵感,这在环境描写中不仅表现为对物品的列举,还表现为对生活中常见的视觉和听觉现象的有意利用,注重视觉描写与听觉描写,昏暗与寂静构成了奇幻的前奏。
“必要的昏暗”①Charles Grivel,Fantastique-fictio.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2,p.119.是欧文笔下奇幻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文不仅利用黑夜的黑暗,还刻意利用场所特点制造黑暗。欧文笔下的奇幻故事往往发生在昏暗的夜晚。《一件真正的中国工艺品》(Une véritable chinoiserie)的开篇写道:“火车在黑夜中疾行。车窗上薄薄的水汽阻挡了看向窗外的视线。有时座位上会闪过转瞬即逝的光晕”(Owen,1987:61),在昏暗的夜色中,主人公在车厢内遇见了读着书的神秘女子,神秘女子在和主人公交谈后离奇消失,只留下身上的香气和她刚才读过的书。《夜礼》(Cérémonial nocturne)中的主人公每次晚归都要到父母的房间亲吻父亲的额头表示晚安,然而某天夜晚他决定省去这个习惯直接回自己的卧室,“现在一片漆黑,在我缓慢登楼梯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扇窗户从外界带来一丝微弱的夜间光亮”(Owen,1996:10),随后他在楼梯上感受到了一只无形的手的触摸,且这只手越过他敲响了父母房间的房门,主人公在惊愕与恐惧中和平时一样进行了夜礼,从此他也不敢跳过夜礼。在《空房子里》(Dans la maison vide)中,主人公在叔叔的引领下来到一个邻居的房子中借宿,“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走在空旷的道路上,叔叔告诉我家乡的新闻。夜空清澈但没有月亮,有时如同幽灵般安静的闪着蓝银光的萤火虫在空中划出奇怪的条痕,似乎是不详的”(Owen,1998:171),主人公当晚在房子内睡觉时果然遇到了不详的难以解释的事件,他听见有人进入了房子中却不见人的踪影,并在床单里发现柔软、湿润、粘稠的如同溺水者肌肤的东西。昏暗的夜晚渲染了异常与古怪的气氛,甚至于暗示奇幻事件即将发生。然而欧文不满足于利用自然的黑暗,他还乐于借助环境人为地制造黑暗:如封闭的门窗,“门被细心地关上,他们处在半昏暗中,已经微弱的日光几乎无法穿过闭合的百叶窗进入屋内。一切都阴暗而肮脏,带着悲剧或废墟的残迹。”(Owen,1998:40),或垂下的挡光窗帘,“黄绿条纹的绸缎窗帘削弱了日光,房间好像沉浸在蜂蜜与水族馆的温和中”(Owen,1987:71),又或是与光隔绝的地下室,“这处地下场所很暗。黄色的蜡烛让微弱的光亮跳动。人们在这里感受到的压抑难以描述”(Owen,1987:46)。
寂静的环境同样是欧文奇幻小说的重要部分,欧文注重听觉效果,经常描绘寂静的环境,但他似乎觉得直接描述寂静无法凸显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因此他更喜欢用单一的、机械的、容易被忽视但能牵动人神经的生活中常见的声音来突出环境的寂静,钟表、水管、供暖器、轮胎、酒桶乃至贝壳动物都被欧文用来构建寂静的环境。《夜礼》中的主人公在深夜回家时听见的钟表声使房屋更显寂静与肃穆,“门厅里的大时钟发出熟悉的滴答声,但在当下,这个声音使寂静的房屋内充满了不寻常的肃穆”(Owen,1998:20)。在《谋杀罗得女士》(L'assassinat de lady Rhodes)中,主人公受到酒馆认识的神秘青年的诱惑,和他一同前往罗得女士居住的别墅准备进行一场谋杀,他们潜入二楼的一个房间,“一张铺满全屋的厚地毯减弱了一切声响”(Owen,1998:144),即将作为命案发生场所的房间内寂静无声,他们能听见房间外传来的声响,“我们听见在别墅的某处水在水管里发出响声。随后,楼下传来了中央供暖的回声,像是有人在夜间开锅炉前给中央供暖通火”(Owen,1998:144)。在《别人的事》中的小酒馆里,客人们各怀心事地沉默着,“汽车启动,轮胎在道路上发出潮湿的声音。在酒窖里,有人重新在搬动酒桶”(Owen,1987:155),凸显出了酒馆里沉闷而古怪的气氛。《雨之少女》中的主人公在雨天独自到空无一人的沙滩上散步,“在被退潮的海浪压实的沙滩上,他听见脚下死去的贝壳动物碎裂的声音”(Owen,1998:36)。
环境中黑暗与寂静的描写常与人的消极情绪相联系,旨在为奇幻事件的发生营造令人感到不安与恐惧的环境。在欧文的奇幻小说中,明亮使人感到安全和平静,如《空房子里》中对光的描述,“当我不再抱有期望时,光线终于涌现出来。有了光线,我恢复了少许平静”(Owen,1998:178);而黑暗则使人感到不安、恐惧与绝望,如《谋杀罗得女士》中的描写:“酒吧外,我躲避的雨,湿淋淋的街道,积黑水的水坑,处在被抛弃的建筑、仓库和发霉的栅栏两旁的肮脏的小巷在黑夜中的绝望”(Owen,1998:142)。光亮和黑暗常常被同时提及,凸显黑夜带来的消极情感,欧文在小说中写道:“他下午打开朝向巨大而翠绿的山谷的落地窗时感到的惬意、放松和自由,当夜晚来临时,被一种奇怪的厌倦感和疲乏感所取代。他向往自由,但现在孤独令他难以忍受”(Owen,1987:26);“房屋正面昏暗、不透光、无动于衷。如果他能透过窗户看见亮起几束光,他会感觉更安心”(Owen,1987:145);“房屋外,新的一天透出光亮……夜间时分的恐惧消散一空。我最终不禁问自己是否是噩梦的受害者”(Owen,1987:180)。
同样的,声音使人感到安心,而寂静使人感到不安。如在《女乘客》(La passagère)中,主人公在大雨天里开车行驶在路上,路上几乎看不到其他车辆。欧文通过对轮胎声的描写突出车内雨车外的安静,“汽车轮胎在道路的混凝土上发出单一的吮吸的声音,偶尔被车轮挡泥板下突然发出的迸射声打断”,随后主人公想打开收音机打破这种寂静,但他开车前忘记拉出车上的天线,此刻也没有勇气下车,因此他不得不忍受这车内的安静,“只有发动机的隆隆声给我带来一丝微弱的安慰”(Owen,1998:150),主人公只能依靠微弱的噪音来保持内心的平静。欧文在《空房子里》中也着重对声音与寂静的关系进行了描写,与声响相连的是“解放”,而与寂静相连的是“压抑”、“恐惧”、“不安”与“窒息”,寂静为奇幻现象的出现渲染了阴森的氛围,奠定了人物恐惧的心理基础。
我好几次听见附近的教堂响起钟声,教堂的钟声好像向我的窗户倾斜,还听见一列远处的小火车在郊区费力地鸣笛,还听见锁链在开着门的马厩里吱嘎作响。在这些声音之中,空旷的大房子中寂静总是更令人感到压抑。这种寂静在我耳边以令人恐惧而不安的方式嗡嗡作响,这使我把接收到哪怕最细微的声音作为是一种真正的解放,这声音重新建立了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在寂静中的窒息与我听到细微嘎吱声时的喘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交替进行。(Owen,1998:173)
必要的黑暗与可怖的寂静成为了欧文渲染奇幻气氛、制造不安与恐惧情绪的视觉手段与听觉手段。
三、生命化写景
欧文在奇幻小说中通过比喻和拟人赋予环境中被描写的对象生命,这些对象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具有了奇幻色彩。欧文通过转变注视的方式赋予生活中常见的事物生命:橡树被比作“头戴浓密的绿叶般头发的怪物的躯干”(Owen,1987:47),被狂风刮起的旧报纸像“支离破碎的鸟”(Owen,1987:110),巨大的扭动着的海浪被比作“怪兽”(Owen,1998:36),截去顶枝的柳树被比作“黑色的哨兵”(Owen,1996:27)……这些本身不带情感色彩的本体被比作令人惊恐的有生命的喻体。欧文还通过拟人手法赋予物体生命。他在《被制服的美人和行吟诗人》(La belle vaincue et le troubadour)的开篇中写到:“如果竖起耳朵仔细听,我们能听到因流经清凉的森林而冰冷的跳跃的小溪让河床上的石头发笑和发痒”(Owen,1987:161),罕见的明媚愉悦的自然环境让人们放松了警惕,与后文中猎人的整装待发和行吟诗人之死形成对比。欧文在《汽车旅馆派对》中描绘了残忍的飓风与可悲的树木,“从这儿直到越来越远的一望无际的平原,所有的农场都一样,被艰苦的防风林环绕,这些可怜的树木被风吹弯、吹散头发和折磨,它们从开垦者时代就不停被重新栽种,但它们总是被如此虐待”(Owen,1987:109),飓风似乎暗示着后文中无情杀害妻子的男人而树木则代表着被残忍杀害的无力反抗的妻子。《15.12.38》中主人公彼得鲁斯·威尔格(Petrus Wilger)居住的街道也被赋予了生命,“它(痛苦)带着令人心碎的强度从几近相同、暗灰色的房屋正面中挣脱出来,房屋悲惨而忧郁的脸孔排成一条直线,带着突出的阳台的坏笑”①Thomas Owen,Oeuvres complètes.Bruxelles:Claude Lefrancq,1994,p.919.,且“一整条空旷的街从它一百多个伪善的窗户中望着他的后背,就像一块结冰的海绵贴在他微温潮湿的背上,他直至到达了市中心才感到终于可以呼吸”(Owen,1994:922),街道如同一个阴郁又危险的人,对主人公充满敌意,监视着主人公的一举一动。
赋予描写对象生命使现实世界的边界变形与走样,奇幻诞生于现实世界之中并不再受现实世界的约束,物品有了自己的意志,甚至于成为了奇幻现象的受害者、同谋或帮凶。《母猪》的主人公克劳利在开车途中碰到了大雾,“从乡野的各个地方生出,这些微小的絮团状的实体互相召唤,一同汇聚,逐渐形成难以穿透的整体”(Owen,1987:13),克劳利虽然减慢了车速但却仍因为大雾出现了种种幻觉,被迫在一家名为“丽春花”(Coquelicot)的小旅馆里寄宿,有生命的大雾似乎是有意识的引导克劳利来到这家旅馆,由此展开奇幻的旅程。主人公在见到母猪般的女人后做了一晚上的噩梦,第二天醒来后,“他向窗外望了一眼,看见了从大雾中抽离的原野,大的草原牧场上布满了铁栅栏造成的长条伤痕,在角落有一排长着浓密绿叶的短发的柳树”(Owen,1987:19),大雾消散,柳树重新让满是伤痕的草原显现出生机,一切都已经过去,恐怖的奇幻事件被留在了昨天。在《生命停止》(Et la vie s'arrêta...)中,某天夜晚,静谧的村庄里响起了男人沉重的脚步,男人高大的轮廓在月光中显现出来,村庄里的一切都生命随着男人的到来而停滞:热爱收藏钟表的男人因突然感到一阵令人恐惧的寒风而钻进被窝,发现自己的钟表突然停止;热爱收集古币的医生心脏病突发,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为自己注射救命的药物;年迈的女人在照镜子时发现自己全身无法动弹,自己心爱的宠物狗奄奄一息……随着她发出的一声尖叫,男人的脚步声逐渐远离并减弱,村庄被从停滞中解救出来,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与奇幻的发展保持着一致的步调,在神秘男人来临之前,“村庄一片寂静,死一般安静,沉默的房屋胆怯地排列在街道旁。装卸车向空中的星星延伸,臂膀举起,以一个无用的乞求的姿势……这不是和平,而是一种不安的等待。村庄并非在安详地沉睡。它闭着双眼,堵住耳朵”(Owen,1998:23),村庄如同已经感知到某种危险的受害者,又如同神秘男人的帮凶,在他来临之前选择缄默,做好周全的准备等待甚至迎接他的到来。温泉是村庄中唯一中立的角色,“没有判断力的喷泉继续流动着细细的水流。只有她,在清澈的夜色中轻轻地沙沙作响,充满自信,没有感受到忧愁。水银光闪闪而又洁白。她在歌唱……当男人经过她的时候,她停止流动……”(Owen,1998:24)。在环境描写中,她如同村庄里唯一无辜的存在,她善良而愉悦,却难逃停滞的命运,暗示着村庄中人们即将面临的厄运。当带来诅咒的男人因为尖叫声而离去后,“喷泉重新开始歌唱,白色的银光闪闪的水重新开始流动,什么都没有意识到……”(Owen,1998:33),村庄中的动物们也开始发出声音,村庄活了过来。
被赋予生命的环境构成了奇幻的一部分,现实在不知不觉中具有了奇幻色彩,它暗示着奇幻现象的发生,甚至引导主人公走入奇幻现象之中,又在奇幻现象消退化回归正常,仿佛一切都只是一场错觉。被赋予生命的环境让读者切实走进了小说的环境之中,紧紧跟随着环境的引导走入故事之中,如同段义孚(Yi-Fu Tuan)所说的,“事实上,如果不赋予物体人类属性,我们无法强烈地感受任何物体,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①Yi-Fu Tuan,Landscapes of Fear.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9,p.105.。
欧文的环境描写还现出欧文独特的叙述风格,无论是列举物品、调动感官还是使用拟人,欧文关注的重点始终是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事物。他从日常环境出发,注重观察与视觉效果,不断积累异常,最终实现颠覆,正如欧文所说:“我首先是一个视觉者,在小说中,观察的才能是必不可少的”(Kiesel:82)。“托马斯·欧文把我们关在伪装的环境中,成千的埋伏着的危险用恶意的眼光窥伺着我们。在平静的文章中,一切都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改变了征兆”(Kiesel:120),正因为欧文笔下的恐怖来自我们熟知的平凡生活,所以我们更难以逃脱这精心设计的恐怖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