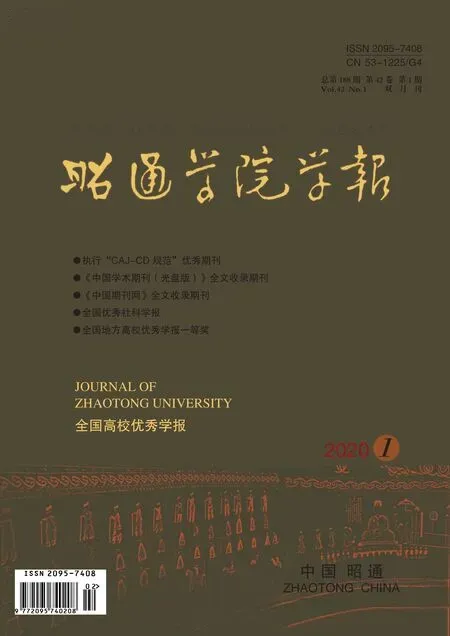近代昭通历史文物保护与云南地域文化研究
丁长芬,杨梦媛
(1.昭通市博物馆;2.昭通学院 学报编辑部, 云南 昭通 657000)
一、孟孝琚碑
孟孝琚碑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土于昭通白泥井,高1.33米,宽0.96米,出土时碑首残缺,碑底刻玄武,碑棱左雕青龙右雕白虎,直行十五行,字体为隶书,共计260字,是云南最早出土的汉代长篇碑铭,于地处偏僻、史乘不足之云南而言,其蕴藏的历史价值和承载的历史使命,能否为乡人识别并加以保护和研究,至关重要。关于这一点,孟碑无疑是幸运的。
第一位详细记录孟孝琚碑发现经过的是昭郡郡庠胡国桢,他在《孟孝琚碑发现记》中写道:余生平嗜学,情殷好古,暇时博访周咨,搜罗金石。光绪二十七年夏五月,有南乡回民马正卫至舍,间询及昭通梁堆,其中曾有汉洗、古镜、铜盘、宝剑等类,遂云:“离郡城十里白泥井,有一梁堆,堆前现一石,出土尺许,村中莫识者。”余乃以分书贴示之,即云:“与此相同。俟余乡试归来,再去往观。”晋省垣,乡试不售,旋归梓里,邀谢太史履庄往观,见其书法苍劲,文辞雅健,浑朴古茂。呼乡人锄地五尺许,果有五铢钱数十枚,遂移置郡城凤池书院藏书楼下。[1]4
移置凤池书院后,翰林谢崇基写了一篇跋文,刻于孟孝琚碑末行处,全文为:碑在昭通郡南十里白泥井马氏舍旁,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出土,同里胡茂才国桢为余言之,因偕往观。石高五尺,广二尺八寸,侧刻龙形各一,下刻物形若龟蛇,其文辞古茂,字画遒劲,方之滇中古刻,远过两爨诸碑之上。虽碑首断阙,间有泐痕,年代无考,然以文字揆之,应在汉、魏之间,非两晋六朝后物,洵可宝也。遂移置城中凤池书院藏书楼下,陷诸壁间,以俟博雅嗜古君子鉴订焉。
上述昭郡胡、谢二人对孟碑发现、保存的记述,未能在国内广为刊布传播,至今学界鲜有关注。文中实地调查核实的记述,是昭郡域内耆儒乡绅保护、研究孟碑之肇始。“移置郡城凤池书院藏书楼下”,虽略显简单,却使云南首次发现的汉代长篇碑铭获得初步有效的保护,为深入的考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孟碑出土时碑首残缺,作为云南首次出土汉代长篇碑刻,其立碑年代、碑铭补阙成为当时昭通学术界面对的费解而又必须解答的难题。昭通名儒谢崇基、陈爱棠、萧瑞麟等,都曾向域外友人寄赠拓片。随着拓片的流播,孟碑碑铭内容引起了清末民初国内金石学界的极大关注,硕学名家根据残存碑文拓片对孟碑的立碑年代进行考证。
由于残存孟碑卷首仅有“丙申”二字却无年号,而两汉又有八“丙申”。据民国昭通旧志载,当时学界考证孟碑的立碑年代,有以下六种意见:谓为成帝河平四年者,上虞罗振玉、滇袁嘉谷,新会梁启超、刘颐;断为后汉时不著年月者,钱塘吴士鉴;指名光武建武十二年者,善化黄膺、滇方树梅、袁丕钧;谓为桓、灵间者,宜都杨守敬;确定为桓帝永寿三年者,东莞陈伯陶、海宁吴其昌、郡人谢文冏;谓献帝建安二十年者,剑川赵藩。[2]诸家各执一见,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孟碑立碑年代考订结果的不同,导致学术界对其评价也不一样。持孟碑年代为西汉成帝河平四年的石屏袁嘉谷跋曰:“滇中古石,以两爨及王仁求、郑回诸碑为著,《孟孝琚碑》最后出恩安县,西汉物也,应定为滇中第一石。西汉碑海内罕传,传者亦多残石,或数字,或数十字。碑存字260,字字可辨,应定为海内第一石。[1]7考证孟碑立碑年代为光武建武十二年的善化黄膺鹿泉甫记曰:“建武去今将二千年……此石晚出,乃古汉碑第一,慨独滇南瑰宝,亦寰宇希世之琛矣。”[3]关于这一点,有学者已注意到,作为云南迄今唯一存世的东汉长碑铭,其滇中第一的地位,毋庸置疑;至于“海内第一石”“海内汉碑第一”的评价,则是基于年代推断为西汉至东汉初年的不统一所致。[4]
与学界对考证立碑年代给予极大热忱相比较,孟碑碑铭补阙却略显滞后,仅昆明陈荣昌和昭通谢饮涧两人对孟碑缺失碑铭进行了臆补。其中陈荣昌对孟碑的臆补似未尽如人意,昭通学者谢饮涧借鉴其他学者考证思路,旁征博引,以干支长历悉心研究考据,结合汉代碑刻、经籍,考证孟碑为东汉永寿三年物。在此基础上,拟补孟碑缺文88字。
谢饮涧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近乎一致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著名学者由云龙在《书谢饮涧先生孟孝琚碑考后》一文中有如下评价:“依原碑文字,补其上方剥蚀之88字,风格淳古,几与原文语气无别……列举数证,均极允当,孟孝琚碑得此考,可谓无遗憾矣。”[5]此后,聚讼纷纭的孟碑年代考订趋于平息。
时至今日,我们仔细梳理史料,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了学界考证孟碑的立碑年代:一方面是对孟碑碑体承载信息了解不完整,直接导致学界对其年代考订的纷讼及对其地位评价的分歧。孟碑出土后即收藏于凤池书院藏书楼,“陷于壁间,郡人亦无察觉”。刻于碑体左右两侧的龙虎纹,虽然谢崇基附嵌于孟孝琚碑原碑末行空隙处的跋文曾有提及,然并没有引起昭通学人的注意。直到1945年移出碑体时才发现碑两侧刻有龙虎,即汉代典型的左青龙右白虎,这一具有年代卡尺价值的刻纹,在这之前并未被学界所认知。另一方面是诸家考据,均凭拓片。流播域外的孟碑拓片拓工有精粗,稍不留意,便失本真。而本地学者则有机会亲触孟孝琚碑,对其进行近距离研究和考证。正如谢饮涧所说:冏也后学,何幸得与《孟碑》同里,爰取初拓精本,亲莅碑下,凝神伫视,以手摩挲再四,其古意真趣,皆非拓本可及。[1]16
自孟碑出土至1945年,其间共有三次决定孟碑命运的保护举措,至今仍未为学界所关注。孟碑首次藏于凤池书院藏书楼有九年时间,从现代保护文物的视角来看,这是一次略显粗放简单的保护举措,但其历史意义却不可忽视。
第二次是昭通士绅推动官方制定搨拓管理办法。因当时影印传播条件有限,无论是做研究还是收藏,对孟碑拓片的需求仍属首选,求者愈众。从光绪二十九年(1901)孟碑出土至宣统二年(1910)九年时间内,大量塌拓碑体拓片用于研究考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昭通士绅敏锐地认识到,无限制搨拓会导致碑体的永久损坏。宣统二年(1910),昭通邑绅黄绍勋呈请昭通府知府陈先沅,出示严禁,交议定印资,刊碣于碑侧。此即《孟碑旁昭通府陈氏勒石》全文如下:
花翎三品衔在任升用道调署昭通府正堂陈为給示勒石事。据籍绅黄绍勋、李临阳、王正观、耿存光等禀称,恩安高等小学堂旧藏谢检讨崇基、胡茂才国桢寻得汉隶孟孝琚碑,经京外通人博考,有定为建武时物者,有定为河平年物者,皆由碑首脱去年号数字,诸家考据莫衷一是,以字体而论的系汉物。窃思海内所存汉碑无几,识者比之“五凤”“地节”,故嵌之藏书楼壁间。乃历时未久,渐近模糊,推原其故,实因私搨太多所致。近日学堂随在需款,是以绅等公议,此后每张定价大龙壹圆,售价即作学堂购书报之资,他事不得挪用。惟搨碑时,必须学堂管教各员监视,每年只搨一次,得价若干,年终由堂填表汇报,不准私搨、私售。俾古迹得垂久远等情。据此除批定案外,合行给示勒石。为此仰学堂管教各员认真监视,以示珍重。倘有私搨私售,一经查出,定即议罚,切切特示。右仰通知 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示 发恩安高等小学堂刊石。
陈氏勒石是以昭通官府名义出示的保护孟孝琚碑的正式禁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对孟碑的保护并未达到预期,出现“迄今三十余年,时有所拓,字渐模糊。”[2]这种情况大概延续至上世纪四十年代。
第三次是建亭保护。民国乙酉年(1945),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捐资建亭于昭通民众教育馆,将孟碑从藏书楼迁置亭内珍护。这次保护孟孝琚碑的举措,是将孟碑碑体镶嵌于亭中墙壁内永久保护,直至今日。建亭永久保护孟碑,是包括省政府主席在内的社会各界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重要举措,其中的保护措施至今仍可圈可点:一是保护规格高,碑亭由皖籍书法家王景茀书“汉孟孝琚碑亭”[5];镶嵌于亭中墙壁内的孟碑碑首由民国国学大师吴敬恒题“汉孟孝琚碑”。二是保护研究两不误。碑亭建成后,考虑到方便搨拓研究,又筹资另在碑亭内刻立了一块与孟碑完全相同的复制碑,且在复制碑底座刻石将上述保护孟碑的经过完整地记录下来。
近半个世纪保护孟碑的历程,显示出云南及昭通各界保护历史文化遗存意识的加强、保护手段和理念的不断更新。尤其是1945年建碑亭保护并于原碑侧复制同样的“孟碑”供搨拓之用,禁止对原碑进行搨拓,至今仍是我国保护古代碑铭的重要理念。
如果说近代云南、昭通各界对孟碑碑体保护研究不断探索,改进保护手段和方法,是“庶原碑永垂不朽”的话,对于孟孝琚墓的保护则开创了近代云南历史文化保护及文脉传承的先河。
孟孝琚墓的保护源于云南晚清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在张希鲁《屏山师回忆录》中就详细记录:袁嘉谷曾委托李守庄“于白泥井补立墓石,题曰‘汉孟孝琚墓’。先生常念念于怀,恐其未立。己已冬初,连楙归里,特命访其石立否。迨访后,其石已立,因作七古诗一首以报。……偶游至城前元宝山南,见岿然丰碑,上刻‘汉经师孟孝琚故里’数大字,下署先生名,乃知先生于先贤表彰,无所不至也。”[6]袁嘉谷于此有跋:“碑之出土,……在县治南,七尺之封土隆然。今既移置县中凤池书院,爰与乡人醵资补立墓石,题曰‘汉孟孝琚墓’。樵牧护惜,士夫衿式,可忽乎哉?”[3]251-252
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仍能见到位于昭阳区城郊白泥井的孟孝琚墓前竖立的这一丰碑,刻颜体楷书,正中曰“汉孟孝琚墓”,两旁小字,首刊“原碑移置郡城内凤池书院”,末有“宣统元年(1909年)乙酉十月李临阳敬书补立”。袁嘉谷先生倡导对孟孝琚墓的这一保护措施,不仅使晚清发现的孟孝琚墓得以保存至今,起到“保卫先陵而禁樵牧,后起者其留意焉”之作用,而且对后世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有着深远的影响。
围绕孟孝琚这块补立的墓碑,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张希鲁有对其也有精彩的描述:“即马正卫自经他来城报告胡氏,将孟碑用牛车运到凤池书院,挂了他一匹红,又赏他几两银子。从此他在家,他的脚就大痛不已,时间延长到七八年。人人都说是孟孝琚的灵魂来问罪,为什么要掘他的墓志?把马正卫害得一个无法。为求脚的速愈,只好备香烛三牲去祭。可是祭后还是照样地痛,千方百计都治不好。直到宣统元年李守庄依袁树五先生的建议,去代孟孝琚补立了一块墓碑,马正卫的脚霍然好了。在一般人只知道袁、李两先生为昭通留了一个古迹,还不知道救了马正卫的脚,真可谓一举两得,雅俗并有的盛事。”[7]134无论马正卫的脚疾与补立孟孝琚墓碑有无关系,这都是云南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件趣事。
孟孝琚碑的研究保护成果,使近代以来国人重新认识了所谓“南蛮”或“蛮夷之地,几无文化可言”之云南的历史和文化,不但开创了偏远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先河,还开启了国人研究云南边疆历史和文化的大门。更为可贵的是,晚清民国以来包括省、地官员在内的云南、昭通各界保护孟孝琚碑、孟孝琚墓的举措,其保护理念和实施手段与21世纪国家文物保护的法则并无抵牾,对区域历史文物保护影响深远。
二、梁堆
“梁堆”指地表有巨大封土堆的古墓葬,因封土高耸形如山梁而得名,时代从东汉沿续至唐中期,主要分布于昭通、曲靖、昆明、保山等地之地势开阔的坝子、较为平缓的山间平坝或河流冲积地带。关于“梁堆”遗存,除向达《蛮书校注》有零星记载之外,其余史籍鲜有提及。云南近代文献称其为“梁王堆”“粮堆”“徭堆”“梁王塚”等。昭通乡人称其为“梁堆”,现代田野考古学沿续“梁堆”称谓,特指封土堆下的墓葬。
目前资料显示,“梁堆”一词最早出现于昭郡郡庠胡国桢光绪二十七年(1901)撰写的《孟孝琚碑发现记》里。[7]132-133文中详述孟孝琚碑发现经过的同时,还论及当时昭通四乡可见的汉冢——梁堆。胡国桢关于“梁堆为汉塚”的论断,由于其文当时未刊行,并不为学界所知,亦未引起昭通学者的关注。民国时期,昭通城外更多梁堆被发现,有人便认为“梁堆”是“傜堆”的转音,视其为傜人的窝棚,墓中出土的铜器、印纹砖和五铢钱也被称为傜铜、花砖和傜钱。[8]民国十八年(1929)张希鲁自省垣回昭,从胡国桢之子胡正陶处“得读胡君未发表过的《孟碑序》遗文,方悟得梁堆确有研究的价值。”[7]141其时,国内考古之风已盛,颇具学术眼光的张希鲁将其学术视野延伸至寻找、发掘梁堆,开启了云南梁堆的调查、发掘、研究和保护。
其时张希鲁受聘于昭通省立中学,“有暇则亲往四乡访问,拟再获汉物,将孟孝琚碑年代证明,以解海内学者之惑。”[9]通过下乡访问,张希鲁将梁堆、花砖、五铢钱之间的关联梳理清楚,同时又知道昭通的梁堆属特殊的古迹,不但全国所罕有,云南别方亦未闻(当时)。[7]142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张希鲁访问了数百个梁堆,认定昭通后海子一个梁堆有发掘的价值,并于1930年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从《昭通后海子梁堆发掘记》中,我们虽然看不到发掘过程之全程记录,但从张希鲁尽其所能的文字记述以及绘制的主要出土遗物的非测量略图来看,于地处偏远的云南而言,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至今仍为学界所关注。学者徐坚这样评价张希鲁发掘后海子梁堆:“不仅是历史上第一次发掘梁堆,也是云南的田野考古学的开端。”[10]
梁堆因其高大封土之形,很容易被盗掘或人为破坏。张希鲁在调查梁堆的过程中,发现了多例人为破坏的情况,基于强烈的乡土文物古迹之爱,呼吁政府对其进行保护。如1933年在洒渔河发现两座梁堆,“一为石砌,一为砖甃。入城即将此事告知李文林县长,李君一面命该地农民负责保护,一面请我同鄢若愚去照相”[11]。更有一例,1934年1月,张希鲁带领学生亲往洒渔李家湾实地调查《东昭新闻》登载之砖屋古穴(即梁堆),并手书《与李县长书》:望县长速令该区民众妥为保护,不得毁其原状,以备各方人士参观研究。[12]昭通政府及乡民保护以梁堆为代表的文物古迹的种子,在张希鲁不间断地从事梁堆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不断生根、发芽。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各地及昭通大量梁堆的发现和考古发掘与张希鲁调查、发掘和保护梁堆紧密相关。
基于对云南、昭通乡土史的挚爱,调查发掘梁堆之余,张希鲁撰写了一系列考古学文章,如《昭通后海子梁堆发掘记》 《考古小记》 《云南古物的价值》《西南古物的新发现》《跋汉建初画刻》《古物的搜罗与保护》等,这些文章使得张希鲁早期考古发现的汉代遗物及研究成果公之于众,更多的学者关注云南和昭通汉代的历史遗物。1935年发表于考古社刊第二期的《考古小记》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第一位云南人撰写的考古学文章在国家级专业刊物发表,在当时的西南地区也属罕见。其它未能公开发表的系列考古学研究成果,其内容随后大多编入《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原文在张希鲁逝世后,由昭通地区文化局集结出版了《西楼文选》。
近代昭通以胡国桢、张希鲁为代表的学儒,对梁堆即汉代墓冢内涵的认识,及其实地考察、发掘、研究,奠定了学术界认识云南梁堆墓这种古代遗存的基础,为解放后云南开展现代考古发掘、清理工作提供了重要资料。尤其是对这类分布于云南、具有典型特征的古代墓葬“梁堆”之定名,至今仍为现代田野考古学所沿用,这在国内考古学界亦是罕见的。
三、朱提堂狼铜器
朱提堂狼铜器,属东汉朱提(今云南昭通)铸造的青铜容器,学界习惯称其为“朱提堂狼洗”。因其器底部铸有“朱提”“堂狼”“朱提堂狼”“朱提堂狼铜官造”铭文而著称。从现存实物来看,朱提堂狼铜器,除数量较多的洗以外,还有釜、盘、斗、鋗等多类器型。[13]铜器铭文多由铸器年号和地点构成,年号如建初、元和、章和、永元、永初、永建、阳嘉、永和、建宁等,款铭涉及地名“朱提”“堂狼”。
关于朱提堂狼铭铜器,史无记载。据汪宁生考证,从宋代开始不断有人对传世的朱提堂狼铭铜器进行收集和著录。[13]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出土的朱提堂狼铭铜器的增多,收集和著录更加丰富,此时昭通四乡多有这类铜器发现,并为士绅所收藏。[14]昭通士绅收藏保存的本地出土的朱提堂狼铭铜器,对深入研究这一独特铭款的东汉铜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梳理史料我们发现,在张希鲁之前,并没有人对传世和出土的朱提堂狼铜器做过专门研究,著录、收藏者仅录洗的名称,如永元洗、建初洗等。考证昭通出土的朱提堂狼铭铜器以及由此延申至研究昭通历史,张希鲁为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张希鲁获取朱提堂狼铜器的渠道来自昭通的铜匠铺,据先生所言:“我个人物色的铜器,不得之农村,也不在古董铺中,往往发现于铜匠手里”[15]。通过这种方式,据张希鲁《跋昭通汉六器》一文记载,至1939年搜集铜器已达三四十件,其中“建盉重五十斤”朱提银、铜洗如“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和“阳嘉二年邛都造”等重要遗物,引起省内外同行高度关注。学界开始以朱提、堂狼、邛都造铜器以证《汉书·食货志》、《后汉书·郡国志》等史籍记载的地处偏远之朱提县、堂狼县的建置以及这个区域的重要资源——银、铜。昭通发现的署有明确纪年和地点的汉代文物,使得汉王朝开发朱提、堂狼(今巧家、会泽、东川一带)的历史为学界所关注。关于这一点,张希鲁曾指出“‘朱提、堂狼、邛都’诸器先后出土,……乃知昭通一带,在东西两汉间已大开发,古物与史乘一一吻合。昭通在汉代不仅与中原同风,且为银矿和铜矿的供给地,故自古银以地代别号‘朱提’”[15],这一论断亦是今天学者研究昭通汉代历史的基础。
张希鲁在1934年至1936年间域外游学,不但结识了滇中在京诸师友,还拜访了一大批学界宿儒,增长了见识,开扩了视野。1936年,张希鲁正式加入容庚创建的考古学社,成为第三期社员。同期会员还有于省吾、罗振玉、杨树达、陈中凡等学术名家。期间张希鲁撰写的《西南古物的新发现》一卷,刊于旅平学会季刊中,袁嘉谷评曰:“云南文物贡献与国人矣。”[16]这篇文章使地处偏僻的云南之汉代历史物证进入国人的视野。从上世纪30年代至解放前,张希鲁与国内学术大家探讨学术之书信往来可以知道,张希鲁的乡土史地研究并非独自一人闭门造车,其学术的深度、广度和视野为后世学者所称道。
上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的时期,张希鲁搜求、护藏古物不免受国内考古风气影响。诚然,乡土之爱成为其考证古物、研究昭通乡土历史之旨趣,正如其在文中描述的那样:“有科学趣味的人,遇古物出土,只问有无文字与花纹及风格等,不问它是金银铜铁或是砖瓦木石。有许多人不了解研究历史的旨趣,往往误认考古为想发猛财。”[15]不得不说,张希鲁这种寻求古物历史信息进而进行历史研究之理念,与现代考古学不唯遗物价值而重遗迹关系及其蕴含的历史信息的解读不谋而合。张希鲁这种几近自创的学术理念,使其每遇一件古代遗物,都作详细记录。比如在铜匠铺搜集到的汉代朱提堂狼铭铜器,张希鲁均要追溯铜器的来源,并亲临铜器的出土地进行实地调查,进一步核实其出土环境和同出器物组合。1935年秋,昭通郑家山后的皮匠地出土了一件“建初八年朱提造作”铜洗,两年后张希鲁收购了这件铜洗。之后便刻意打听它是何时何地何人发现的,有没有共同出土的器物组合等。在《记汉建初两器出土处》一文中,张希鲁详细地记录了他经过实地调查的这件铜洗的发现者、发现经过和共同出土的器物——“虫鱼洗”、枯木和被称为“汉白金”或者“汉银锡白金”的朱提银块。[17]此事并不是个案,在调查考证梁堆、石棺、五铢钱及花砖(汉晋墓砖)等汉代遗物时,张希鲁也是同样处置。[17]这种当事人所进行的田野工作流程记录的保存,为后人留下了不仅如铜洗、铜鍪、铜罐和银块乃至木块的共存关系,还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揭示这些遗物所包含的相关历史信息提供了重要资料。
正因为以探究云南及昭通古代开发的历史为始终的目标,张希鲁在对昭通出土的朱提堂狼铜洗等汉代遗物作研究后,得出“云南的开辟,要以迤东最早,而昭通为最”的论断。[18]126这也意味着,处于上世纪30年代搜求古物的张希鲁,与传统古董收藏爱好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他认为“古物并非古董,不徒用来赏玩,是要证明史地的。云南历史,文字记载既不详明,有了古物的发现,就不可望之流出。”[18]127张希鲁这种研究乡土史地使命情节之学术探索,贯穿于《跋汉金(二则)》《汉洗记》《书汉洗记后》《古物记(附昭通城东访古记)》 《滇东古物目略》 《跋昭通汉六器》 《跋蜀郡器》《跋汉朱提银锡合金》《汉建初器与虫鱼器跋》《记汉建初两器出土处》《跋汉阳嘉四年堂狼洗》等文中。张希鲁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以方国瑜为代表的云南学者的高度认同。其后,方国瑜将张希鲁搜集的朱提堂狼铜器及汉代重要遗迹遗物资料,吸纳到其编撰的《新纂云南通志》之《金石考》中。对此,方国瑜在为《西楼文选》所作的序中称:“瑜为《新纂云南通志》编撰《金石考》,得希鲁先生提供资料,多已收入,为世人所称道。”
张希鲁对朱提堂狼铭铜器之保护、收藏以及研究云南及昭通乡土历史的贡献,先生自传有述:“唯以二十年心力,博读群籍,搜罗金石古物,咸于云南文献有密切关系,此海内人士所称许,非个人自夸也”[9]。在与浦汉英书中,张希鲁将毕其一生对昭通历史文化遗产调查保护之成果写了出来:“……三十年来的文物研究,得了一个总结。围绕昭通飞机场的各乡,如白泥井、诸葛营、施家沟、水塘坝、甘河乡、曹家老包等地,都曾发现汉代明确的文物。可知一千八百年前,此地的农业生产和冶铸业是何等的发达。”[19]后世学者对张希鲁的评价是:“以朱提堂狼洗实证为特色的早期滇东考古研究不仅在云南罕见,在西南也属最早的。”[10]
张希鲁晚年病危时将自己保存的全部文物捐献给国家,并望责成专人管理,以免有失,“好让后来学人,对研究地方历史作出其应有的贡献”。籍此,1980年成立了昭通地区文物管理所,保护管理张希鲁先生捐献的所有文物。
四、唐袁滋题名摩崖石刻
唐袁滋题名摩崖石刻刊刻在盐津县豆沙关五尺道边的悬崖上,刻石高60厘米,宽25厘米,全文八行,直下左行,计122字,正文楷书,末行篆书“袁滋题”。石刻记载了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御史中丞袁滋率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一行到云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途经石门,刊刻纪事。南诏内属归唐,是唐中期的一件大事,袁滋一行赴云南册封南诏,新、旧《唐书》、《资治通鉴》、樊绰《蛮书》等史籍均有记载。然袁滋在石门题记并刊刻记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石刻,历代史籍罕见著录,不为世人所知。
清光绪元年(1875),赴京赶考的昭通籍举人谢文翘途经石门关时,在关前崖壁上发现了这一见证历史的千年石刻。谢文翘当即对其进行现场辩读并拓片。抵京后,谢文翘将其所携之拓片分送友人[20],袁滋摩崖石刻始为学术界所知。作为唐中期南诏内属归唐的重要实物证据,因其地处偏远,拓片难度大,不甚精致的拓片直接影响了学术界的关注度。
至民国,昭通学者张希鲁经过实地探查,探究到袁滋摩崖石刻保护研究的瓶颈:“余到豆沙关时,访其地人士,对之详释,并嘱共同保护。不但是西南有数的古迹,就全中国亦罕见。惜此处地大荒僻,拓本每多不精。……拟将来要特募人去精拓,介绍与国内学者,勿使此瑰宝久湮,亦证明其关系云南迤东史迹,不在孟孝琚碑下。”[7]132
张希鲁将精拓的石刻拓片远寄省外学者,袁滋摩崖石刻重要的史学价值和中唐大书法家袁滋之篆书墨宝,渐为国内大家所关注。如著名哲学史研究专家、民俗学家容肇祖于1939年11月致函张希鲁:“前兄赐赠之豆沙关题记拓本,已转赠陈寅恪先生。将来兄如有机会,可以购得或拓得豆沙关之题字时,万望代为购取或拓一份。”[21]
按张希鲁记述,注意此石刻最早者,为云南袁嘉谷、袁丕钧叔侄。[7]131之后由云龙、黄仲琴、方国瑜、向达、陈一得、张希鲁、谢饮涧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或序跋,或考证,或品鉴。对这项涉及唐中央政权与南诏地方政权关系史的重要实证文物,各家围绕以下方面进行考证:高度评价摩崖石刻的政治意义;书体方面,袁滋摩崖石刻内容为楷书,末尾袁滋题名则为篆书,由于袁滋书法世所罕见,其书法价值首为袁丕钧考证、确认,开启了后人对袁滋书法的研究;谢饮涧则从石刻刊刻形式方面进行了考证,其考证成果得到学界的肯定;摩崖石刻在西南古代交通史方面之意义,袁嘉谷、方国瑜、陈一得和向达各家分别进行了考证,意见略有分岐。
关于袁滋题名摩崖石刻所涉西南地区古代交通史之意义,直至上世纪80年代之后才又引起学界关注。于西南地区而言,袁滋题名摩崖石刻是唐贞元年间中原、巴蜀与云南交通史的重要实物证据,因其地处偏远,当时国内学界并未意识到其在西南古代交通史研究方面具有的里程碑式意义。
西南古代交通,史籍早有记载,如《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蜀身毒道”“牂牁道(夜郎道)”,《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志》《后汉书》《水经注》《新唐书》《蛮书》等文献中均多次提及的“步头道”和“进桑道”。梳理史籍可知,唐朝成都通往云南的道路共三条:一条从邛部旧路即经过凉山地区通往云南,一条从叙州经石门到云南,一条绕道贵州,其中前两条是主要的交通线,第三条路途险远。当时处于特殊战争时期,邛部旧路即经过凉山地区通往云南的道路由吐蕃把持,石门有乌蒙部落阻隔。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唐中央政府的册封使者能安全按时到达南诏,使臣南行的道路选择了从叙州经石门到达拓东(即今昆明)这条道路,即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蜀身毒道”。袁滋一行从宜宾经过石门到达拓东的这一段即“蜀身毒道”最重要的一段——五尺道。
对于袁滋一行行经道路关注最早的是袁嘉谷,但其意见后来被方国瑜所否定。1934年,方国瑜考证说:袁滋行经豆沙关,即取樊绰《云南志》卷一所谓之石门道……此道即汉之僰道,自来为滇、川间交通要道。又自成都至大理,别有一道经邛部,则樊《志》所谓之清溪道。《通鉴》大中十二年曰:“初,韦皋开清溪道,以通群蛮。”即邛部旧路。袁树五先生以为,袁滋使滇即取此道。然清溪道经今之建昌,石门道经今之昭通,不容相混,树五先生盖未考也。[1]145上述方国瑜的考证,明确袁滋使滇取道石门,纠正了袁嘉谷“清溪道”之说。继之,向达亦对唐时自四川至云南之南北二道进行了论证:“从黎州清溪关出邛部,过会通,至云南,谓之南路;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州,至云南,谓之北路。贞元十年袁滋诸人册封南诏,所取即北路也。”[1]146
方国瑜、向达两位先生从不同的视角对袁滋一行至云南册封南诏路线进行了研究,认为袁滋入云南取道今昭通之石门路,这一观点为后期发现的大量考古遗存所佐证,成为今天学界之共识。可以说,清末发现的袁滋摩崖题记,作为西南地区古代交通研究的第一实物例证,奠定了国内学术界关于《史记》所记载的“蜀身毒道”交通线路考证研究的基础,是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五尺道”的重要实物资料。
不得不提的是,唐袁滋题名摩崖发现之前,学术界对五尺道开辟历史、线路走向及其在西南地区古代交通史上的地位认识不足。这种情况甚至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有学者根据豆沙关唐摩崖所留当时袁滋题名,得出石门路是隋代为通南诏而开辟之判断。[22]
综上所述,唐代袁滋摩崖石刻,作为统一国家的唐中央政权与南诏地方政权关系史中一项重要的实证文物,与前述汉孟孝琚碑、梁堆、朱提堂狼铜器等汉代遗存相互印证,揭开了昭通乃至整个滇东北汉唐历史考古研究的序幕。其保护研究成果,奠定了古代云南在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并为之后发现更早的云南历史文化遗存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