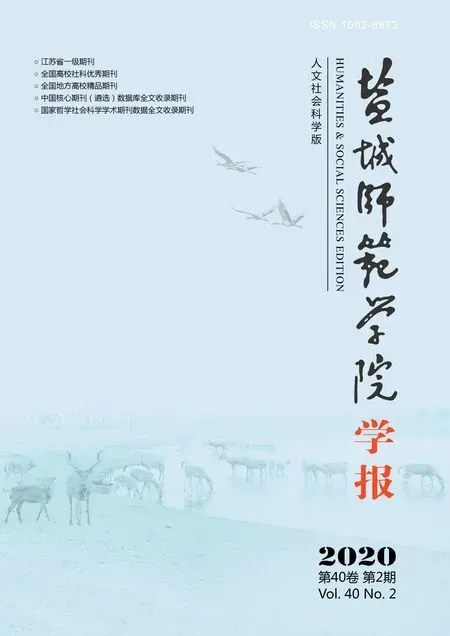论杜甫佛寺诗的多重文化意蕴
董利波,董利伟
(1.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山东 青岛 266003;2. 《山东通信技术》杂志社,山东 济南 250001)
唐代佛教盛行,广泛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唐代文人而言,其影响更为深广,“诗圣”杜甫与佛教之间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杜甫与佛教的关系,是杜甫研究中的一个大题目,同时一直是个纠缠不清的难题,需从多角度、多层面做进一步的探究。可喜的是,学界在这方面已进行了一些探索。如吕澂《杜甫的佛教信仰》[1],结合杜诗,概述了杜甫佛教信仰的种种现象;刘卫林《杜甫与禅学》[2]阐明杜甫与禅门、禅学间的密切关系;刘明华《佛教与杜甫及其晚年心境》[3],阐述了杜诗中表现宽容悲悯、博爱温情等人道主义色彩的宗教意义;朱学东《杜甫诗论与佛禅宗风》[4]探讨了杜甫与禅宗的联系,论述了南北二禅对其诗论的影响;于俊利《佛禅与杜甫的思想关系探析》[5]认为佛教思想是杜甫思想中的重要部分;孙昌武《杜甫与佛教》[6]通过对杜甫有关佛教、佛寺诗作的分析,具体展现了诗人的佛教思想;马新广《杜甫与寺观壁画》[7]详细分析了寺观壁画对杜诗的影响;鲁克兵《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8]一书,对杜甫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郑超《杜甫佛教思想研判----以杜甫游佛寺诗为视角》[9]简要梳理和分析了杜甫的佛寺诗;等等。这些成果,显示了研究者对该课题的重视程度。不过,此前的研究也告诉我们,直接或笼统地对杜甫与佛教的思想联系展开言说,不仅难以取得实效,还很容易滑入大而无当的泥沼。有鉴于此,我们以杜甫与佛寺的亲密接触为切入点,展开较为深入细致的梳理把握,以期有所创获。
一、杜甫与佛寺的接触情况
杜甫给我们留下了50篇左右涉及佛寺禅院内容的诗篇。孙昌武《杜甫与佛教》、郑超《杜甫佛教思想研判》等文章,已按时间顺序,对杜甫的佛寺诗进行了梳理分析。为避重复,笔者拟以杜甫留存于世的诗篇为依据,按照他出入佛寺的动机缘由,粗线条地将其一生与佛寺发生关系的情况分为酬唱、停住等五类,略作分析。当然这一分类未尽合理,它们之间的范围和界限并非截然分明,有些时候会相互重叠。但如此区分,除便于叙述外,也有助于大家对杜甫接触佛寺情况有个直观和基本把握。
(一)在佛寺会友赋诗、饮宴酬唱
佛寺中的自然、人文氛围优越,吸引众多文人墨客前往漫游集聚。唐代文人游聚寺院,已成习尚。他们在此相聚欢宴,登临凭吊,酬唱品评。杜甫是个喜欢交际和珍视友情的诗人,日常中自然也少不了这类活动。天宝十一载(752)秋,杜甫在长安与好友薛据、储光羲、高适、岑参等同游大慈恩寺,登上寺塔(即大雁塔),《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便是此次的唱和之作。长安作为唐都,也是寺院集中的地方,这里不少寺院有皇室背景,规模宏大,建筑壮丽,通常通过园林化手段,营造胜境,大慈恩寺便是其中代表之一。唐高宗作太子时,为其母文德皇后立寺。当时五位诗人登上寺塔,仰观俯察,感慨万端,各自写下了气势不凡的诗作。除薛诗失传外,其他四人同题酬唱诗均存。
杜甫避乱巴蜀,有机会与友朋官员在佛寺中酬唱欢宴。上元元年(760)秋,杜甫至蜀州,在时为蜀州佐吏的裴迪陪同下,游览新津某寺,并有酬唱。杜甫作《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题下自注“王时牧蜀”,王即王维之弟缙。新津唐时寺院大都不存,杜、裴同游的是新津寺还是在新津的四安寺、修觉寺或其它寺庙,不得而知。裴诗已佚,浦起龙云:“玩诗意,知题中‘登新津’以下八字,乃裴原题。”[10]410杜甫流寓梓州时,与州刺史章彝相善,曾作《山寺》诗,题下有“得开字,章留后同游”,反映了他们同游梓州真观寺及酬唱情景。杜甫还数次与友朋官员宴饮梓州惠义寺,《惠义寺送王少尹赴成都》题下有“得峰字”,明确透露了杜甫与友人在寺中分韵赋诗情况。惠义寺本名安昌寺,建在梓州城北。代宗广德元年(763)春,杜甫作《陪李梓州王阆州苏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义寺》,记录与几位官员的游览聚会。又有《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中军待上客,令肃事有恒。前驱入宝地,祖帐飘金绳。南陌既留欢,兹山亦深登。……羁旅惜宴会,艰难怀友朋。”写在惠义寺举行饮饯活动。《惠义寺园送辛员外》《又送》亦反映了在寺园与好友饯别情景。
(二)在佛寺停住
杜甫《游龙门奉先寺》云:“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言游览并夜宿寺中。在长安,杜甫还住过大云寺:“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夜深殿突兀,风动金锒铛。”(《大云寺宿赞公房四首》其三)透露了大云寺接受俗客住宿的情形。乾元二年(759)末,杜甫自同谷至成都,初到时便是寄居于寺庙。时任彭州刺史的高适有《赠杜二拾遗》:“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佛香时入院,僧饭屡过门。听法还应难,寻经剩欲翻。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获悉老杜暂居寺中,悬想其起居情景。杜甫作《酬高使君相赠》予以回答:“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双树容听法,三车肯载书。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读二人诗,除知道古寺空房,僧人无多外,寺其它详情却难知晓。或认为杜甫所居为浣花溪寺,黄鹤云:“公初到成都时,居于浣花寺。”[11]727事实上,此处之浣花溪寺乃指位置在浣花溪旁之寺院。唐人卢求《成都记》云:“草堂寺,在府西七里,寺极宏丽。僧复空居其中,与杜员外居处逼近。”[2]727今人多认为杜甫初到成都寓居的是草堂寺。
杜甫寄居佛寺一段时间后便搬进自己的草堂。之后又曾流寓蜀地绵州、梓州等地,也往往停住佛寺,如其所称:“老夫贪佛日,随意寄僧房。”(《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从严武幕府辞职,拟携家出峡。夏日至忠州,寓居当地龙兴寺,在寺壁写下《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忠州三峡内,井邑聚云根。……淹泊仍愁虎,深居赖独园。”“治平寺在城东门外,即唐之龙兴寺也。康熙辛亥年知州刘肇孔重修,康熙庚寅勅赐振宗禅寺。”[12]宋英宗治平年间,龙兴寺改称治平寺。陆游有《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诗。
(三)入寺拜谒名师大德,接交请益方外高人
杜甫一生结识不少僧人,仅诗中提及、酬赠过的高僧大德就有十余位。他常至寺院造访僧徒,研求佛理:“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谒文公上方》)至德二载(757)春,杜甫被困于安史乱军占领下的长安,曾到大云寺见寺主赞公,作《大云寺宿赞公房四首》。赵次公云:“今此大云寺赞公房,盖长安也。何以知之?后别有《宿赞公房》诗,本注:京师大云寺主谪此安置也。公家虽在鄜州,而公身转陷贼中,往来长安则过大云,见赞上人矣。”[13]178其一云:“洞门尽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开复闭,撞钟斋及兹。醍醐长发性,饮食过扶衰。把臂有多日,开怀无愧辞。……汤休起我病,微笑索题诗。”所谓“果幽期”,透露了此次入寺乃赴赞公约。僧俗二人把臂多日,十分默契知心。其二云:“细软青丝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顾转无趣,交情何尚新。”交情之深可见一斑。杜甫流落秦州时,又与先被贬在那里的赞公相遇,二人在偏僻之地同病相怜,相互体恤,友情进一步加厚。
宝应元年(762),杜甫游梓州中江县东的大雄山真武祠,作《题玄武禅师屋壁》:“锡飞常近鹤,杯渡不惊鸥。似得庐山路,真随惠远游。”赞玄武禅师情趣高雅,也表达了自己有意归隐的心愿。《方舆胜览》载:“大雄山,在中江,有真武祠,杜甫有《题玄武禅师屋壁》诗,即此。”[14]1091玄武禅师所在寺院,唐代称乾昌寺,宋时名大雄寺,俗名玄武观。今玄武山有玄武观遗址,尚存“大雄真圣像”碑一尊,为吴道子手笔摹本。稍后,杜甫又至射洪县北门外上方寺,拜谒文公和尚,作《谒文公上方》:“野寺隐乔木,山僧高下居。……吾师雨花外,不下十年余。”今射洪县金花镇(旧县治所)西南隅山坡上,有上方寺遗址。寺址背山面邑,处高临下,与“俯视万家邑”情景颇相合。大历二年(767)秋,杜甫居夔州,曾赴巫山寺院拜见大觉禅师未果,作《大觉高僧兰若》,题下自注:“和尚去冬往湖南。”诗云:“巫山不见庐山远,松林兰若秋风晚。”赵次公解:“大觉和尚虽是巫山之僧,而比之为远公。公往谒之不遇,故云‘巫山不见庐山远’。”[13]1151又有《谒真谛寺禅师》,或为夔州所作,言前往山寺向禅师问法。至于所拜谒禅师为谁,寺又何在,今尚难考。诗云:“问法看诗妄,观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流露了对佛法的皈依之心。大历元年(766)夏,杜甫居夔州,还到始兴寺,访问在此修行的居士,同时也是好友的李文嶷。作《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重闻西方止观经,老身古寺风泠泠。妻儿待我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寺位于夔州磨刀山虎冈岭下,北周时建。或言今奉节城西开元寺旧址即此寺。
(四)游览佛寺名胜,寻找精神寄托
杜甫一生经历丰富,所到处屡屡拜谒游览佛寺,品赏风土建筑之美。有时也因现实苦恼无法排解而到寺院亲近佛教,求得精神上暂时解脱。《游龙门奉先寺》是其开元二十九年(741)左右居东都洛阳,游宿奉先寺所作。“此诗非为龙门而作,盖为平昔在东都,大有不惬于心,乃今一游龙门,不胜洒然称快。……读其连揭‘招提’二字,且曰:已从此游,更宿此境,大有欣幸出于意外非常希有之乐者。”[15]注家一般认为创作于大历元年的《忆郑南》,乃写当初在华州游伏毒寺情景。杜甫早年往返于两都之间,常从华州经过。乾元元年(758)六月,诗人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居华州一年,有更多机会游伏毒寺。寺清代犹存,且有杜甫祠。王士禛《华州西溪》诗云:“江心伏毒寺,花外拾遗祠。”句下自注:“有子美祠。”[16]
乾元二年(759)秋,关辅大饥,杜甫不得已辞官,携妇将雏,一路颠沛,西赴秦州。有《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中不少写作地都与寺庙有关。其二云:“秦州城北寺,胜迹隗嚣宫。……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城北寺,又名崇宁寺,俗名城北寺,故址在今天水市秦州区北天靖山麓。杜甫还游历了南郭寺:“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秦州杂诗》十二)南郭寺位于天水市城东南二公里龙王沟慧音山上。乾元二年(759)秋冬之交,杜甫还到过太平寺,有《太平寺泉眼》:“招提凭高冈,疏散连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岁月古。石间见海眼,天畔萦水府。……取供十方僧,香美胜牛乳。”太平寺在今水市麦积区甘泉镇玉兰村,或称甘泉寺,寺门仍题“太平寺”。所言泉眼在寺中,现泉水依然,清澈甘美,至今为当地人饮用。《山寺》诗亦乾元二年作:“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寺为石窟寺,位于今天水市麦积区东南贾河乡麦积山上。该寺开凿时间从十六国后秦绵延至明清时期。乾元二年(759)十月间,杜甫从秦州赶赴同谷,路经法镜寺,顺便游览,作《法镜寺》。寺故址在今甘肃西和县城北十五公里石堡乡西山上。明清间殿宇被大水冲毁,寺院移建附近五台山,现存康熙、雍正年间重修法镜寺的三通石碑。
在四川,杜甫上元元年曾到新津,次年春再至,游当地昭觉山四安寺,《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云:“暮倚高楼对雪峰,僧来不语自鸣钟。”“雪峰”指雪峰山。《蜀中广记》云:“杜少陵《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即裴秀才迪也。寺在新津昭觉山,楼与雪峰相对。是时王缙为蜀州守,三人盖朝夕于斯云。”[17]杜甫还游览了新津修觉寺,有《游修觉寺》诗。修觉寺位置,在新津县南五里。《四川通志》载:“在县东南五里,山有修觉寺、纪胜亭,杜甫尝游焉。其上为雪峰,亦名宝华山,其下为三江渡。《唐志》:新津有主簿山,或以为即此。”[18]之后,杜甫又至新津,作《后游》和《登北桥楼》二首五言律诗。《后游》云:“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修觉寺今已改建为武阳中学校舍。据1989年《新津县志》,《游修觉寺》(前、后)二诗及《登北桥楼》在清乾隆时被刻于修觉寺内,称“杜甫诗碑”,现仍存新津武阳中学校内[19]。代宗宝应元年(762)春,杜甫来到绵州涪城,游香积寺,写下《涪城县香积寺官阁》。香积山在涪城县东南三里,北枕涪江,香积寺就坐落在江畔的山腰上。同年,杜甫至梓州通泉县,在惠普寺(后称庆善寺)看到薛稷书画,想起这位先贤,感慨万千,写下《观薛稷少保书画壁》,诗中有句:“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赵次公注:“‘青莲界’,佛寺也。”[13]528又云:“稷所书惠普寺碑上三字,字方径三尺许,笔画雄劲。傍有赑屃缠捧,乃蛟龙岌相缠也。今在通泉县庆善寺聚古堂。余尝到寺观之,三字之傍有赑屃缠捧,诗人道实事为壮观之句耳。”[13]528可知杜甫所至乃通泉惠普寺。
广德元年(763),杜甫羁留梓州,游历了牛头、兜率、惠义等寺。《太平寰宇记》载:“牛头山在(郪)县西南二里,高一里,形似牛头,四面孤绝,俯临州郭,下有长乐寺,楼阁烟花,为一方之胜概。”[20]长乐寺即牛头寺。据杜诗《上牛头寺》“青山意不尽,衮衮上牛头”,寺当在山顶。杜甫又有《望牛头寺》:“牛头见鹤林,梯径绕幽深。”鹤林,佛语指佛入灭之处,又名鹄林,娑罗双树林,故鹤林亦泛指佛寺之树林,杜诗此处即此意。鹤林亦用为佛寺名,有学者认为此指鹤林寺,《杜臆》云:“《志》:州南七里鹤林寺,牛头山在州西南二里,正与相望。”[21]162作于广德元年的《上兜率寺》《望兜率寺》,专写游兜率寺。兜率寺在郪县南二里南山上,又名长寿寺。《上兜率寺》写道:“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望兜率寺》又云:“树密当山径,江深隔寺门。霏霏云气重,闪闪浪花翻。不复知天大,空余见佛尊。”寺有高大佛像,站在寺内,还可俯视奔流的涪江。
大历四年(769)春,杜甫穿越洞庭、青草湖,南行至潭州(今长沙市),游览了岳麓山下的麓山寺和道林寺。《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云:“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诗中“寺门高开”,所言即麓山寺。《方舆胜览》载:“岳麓寺在山上,百余级乃至,今名惠光寺。下有李邕《麓山寺碑》。”[14]418游麓山寺前后,诗人还兼游道林寺。“道林林壑争盘纡”,写的即是道林寺的佳境。寺所建年代无考,今不存,故址在岳麓山下青枫峡东。“道林寺在岳麓山下,距善化县八里。寺有四绝堂,保大中马氏建,谓沈传师、裴休笔札,宋之问、杜甫篇章。”[14]416大历五年,杜甫又作《清明》诗,提到“此都好游湘西寺”。王嗣奭云:“湘西寺即岳麓、道林寺,踞长沙之胜。”[21]387
(五)其他
杜甫有不少诗篇虽非专门描述游览佛寺情景,却也从某个侧面言及佛寺。天宝元年(742)至四载间,诗人不止一次行走于由洛阳至龙门的驿路上,有《龙门》诗:“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仇兆鳌云:“其云佛寺,盖近驿之寺,元人《龙门记》谓旧有八寺,故不但一寺也。”[11]29天宝九载,杜甫应郑潜曜之请,为玄宗女临晋公主母淑妃皇甫氏作《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有“少室东立,缭垣西走。佛寺在前,宫桥在后”语。皇甫氏墓在河南洛阳市南龙门之西北原,此佛寺当在龙门佛寺群中。天宝十三载,杜甫作《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刘少府的山水画并无寺,但有少府小儿子画上的山僧和童子,诗人由此联想到当年游吴越若耶溪、云门寺时情景。云门寺在今浙江绍兴南云门山上。
天宝十三载春,杜甫游何将军山林,作《重过何氏五首》,其二云:“云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翠微寺,《元和郡县图志》载:“太和宫,在(长安)县南五十五里终南山太和谷。武德八年造,贞观十年废。二十一年,以时热,公卿重请修筑,于是使将作大匠阎立德缮理焉,改为翠微宫。今废为寺。”[22]在此前后,岑参兄弟曾携杜甫游渼陂,老杜作《渼陂行》,有“船舷暝戛云际寺,水面月出蓝田关”句。云际寺,指云际山大定寺,遗迹尚存,在今陕西户县东南焦西村。天宝十四载所作《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云:“许生五台宾,业白出石壁。”业白,即白业,净土法门中将修习净土叫做白业。石壁,或指山西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或谓泛指,未必定指某寺。乾元元年(758)春,杜甫送别拾遗许登,作《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回忆之前游吴越时参观瓦棺寺情景。瓦棺寺故址在今南京市秦淮河畔凤凰台西花露岗南。
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杜甫在夔州作《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觅使寄此二首》,其二云:“闻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赵次公云:“题止云‘五弟丰独在江左’,不指名其州,则亦传闻而未审,故今云‘闻汝依山寺’,其杭州邪?岂定是越州邪?”[13]995可见诗中“山寺”,并无定指,只是交待闻知杜丰淹留停住在佛寺中。二年秋,杜甫作《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中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双峰有二,蕲州双峰山有东山寺,曹溪宝林寺后亦有双峰。此双峰寺当指蕲州双峰山东山寺。《咏怀古迹五首》其四曰:“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永安宫,故址在今重庆市奉节县。野寺,杜甫自注:“山有卧龙寺,先主祠在焉。”又注:“殿今为寺,庙在宫东。”指宫殿改为佛寺。大历三年春,杜甫乘舟自瞿塘峡东下,希望能游览江陵天皇寺:“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画图。应经帝子渚,同泣舜苍梧。”(《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王嗣奭云:“宜都县属夷陵州,在州东九十里,而东抵江陵尚二百五十里。天皇寺、帝子渚,皆预言其所经之地也。未到寺而先披画图,知其装囊中携之以行;先披正见其喜。”[21]350杜甫曾在江陵逗留些许时日,当前往皇天寺游览,然未见有游皇天寺诗,殊不可解。在出三峡沿江东下途中,杜甫作《舟月对驿近寺》,亦有对佛寺的描写:“金刹青枫下,朱楼白水边。”言青枫林外是金光闪烁的佛寺宝塔。大历三年(768)年秋,杜甫从公安赴岳阳,作《留别公安大易沙门》:“先踏炉峰置兰若,徐飞锡杖出风尘。”希望在庐山置寺。大历五年,在耒阳北返的小船上,杜甫还念念不忘要终老于游寺:“灌园曾取适,游寺可终焉。”(《回棹》)他曾计划由湖南归襄阳终老,故此处“游寺”当指襄阳之佛寺。这也是诗人最后一次在诗中谈及佛寺。
二、杜甫佛寺诗的文化意蕴
佛寺与人们的文化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杜甫的佛寺诗,是我们把握诗人与佛寺关系最为原始和直接的材料,也是了解当时佛寺状况及相关文化风俗的窗口。透过这一窗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诸多鲜活生动、多彩多姿的寺院文化与风俗生活画卷。
(一)反映了佛寺的繁盛景象
杜甫生前所经历的开元盛世,正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壮大期。开元末,全国佛寺已达5 358所,“其时唐朝国势亦臻鼎盛,设州(郡)府328,县1 573,平均每州16寺,每县3.4寺,寺系网络益见致密。全国佛寺的这一基本数额(5 358),成为以后唐朝寺系规模的‘定数’”[23]。张弓根据当时寺系的网络布局,将其划分为五个疏密层区,其中最为密集地区是京畿(长安为中心)、都畿(洛阳为中心)和以江浙为主的江南东道,次密、间密区包括河南道、江南西道、剑南道中部等地区[24]148-150。杜甫长期居住的两京洛阳、长安和青年时期游历过的江浙地区,是当时佛寺发展最为繁盛的三个区域,而所经历过的陇右、巴蜀、荆襄、湖湘等地,亦多为佛教较为发达、寺院集中地区。所以,杜诗中涉及到了众多佛寺,如两京地区的龙门佛寺群、大云寺、慈恩寺、云际寺、翠微寺,陇蜀道上的城北寺、南郭寺、太平寺、麦积山石窟寺、法镜寺等。巴蜀佛寺入杜诗者最多,仅一梓州,便有牛头、兜率、惠义、惠普、真观、鹤林诸寺。杜甫笔下的佛寺,有的是皇家功德寺,如大慈恩寺、大云寺;有的是州府大寺,如梓州惠义寺、忠州龙兴寺;更多的是兰若、禅院等山野小寺。它们或在都市,或在乡野,或在原隰,或在青峰,或在高峡,或在河滨。宏伟奇丽、高大雄壮者有之,古朴幽深、妩媚静谧者亦复不少。这些瑰丽多姿,风格各异的佛刹形胜,历经千载,或改称,或再建,或败落,或不存,境遇不一,赖杜诗方一睹其唐时风姿。总之,杜诗文献史料价值极高,是后人研究了解寺院风貌、规模、分布,乃至佛寺文化、佛教传播等方面的重要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涉及不少石窟寺。中古时期,河南、秦陇、剑南地区,都是中华著名的石窟艺术区。杜甫写到的龙门奉先寺、麦积山石窟寺、西和县法镜寺、梓州真观寺等,均为著名石窟寺。杜甫不止一次游览经过的奉先寺,寺中石窟,乃中唐高宗咸亨年间开凿,主像卢舍那佛雄伟壮丽,两旁雕像布局严谨。在秦州写的《山寺》诗,记录的则是游览麦积山石窟寺的深刻印象,“悬崖置屋牢”,实是麦积山石窟的特色。法镜寺是陇南境内一处著名的石窟佛寺,创建于北魏时期。“愁破崖寺古”,称寺为崖寺,主要就其为石窟寺而言。蜀地山川陡峭,便于石窟开凿,因而也有不少石窟寺。“野寺根石壁,诸龛遍崔嵬”(《山寺》),所描绘的梓州真观寺,是典型的石窟寺。
(二)描绘了恢宏壮丽的佛寺建筑
寺院建筑本身,就是佛教文化的一种具象形式。杜甫诗屡屡写到寺院佛殿、楼阁、房、塔等建筑。《大云寺赞公房四首》描述殿堂的高大雄伟:“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黄莺度结构,紫鸽下罘罳”。杜甫所见的麓山寺殿堂,气势恢宏:“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形容秦州城北寺建筑:“苔藓山门古,丹青野殿空。”(《秦州杂诗》其二)佛殿是在当年隗嚣宫故基上改造扩建而成。隗嚣曾割据一方多年,其宫殿不同凡响。而杜甫眼中的山门佛殿,虽无当时盛况,却仍给人以高古空阔感。“朱甍半光焰,户牖粲可数”(《法镜寺》),反映的则是法镜寺殿堂建筑,因处山崖,愈显宏伟壮丽。牛头寺在山顶,殿堂也极壮观:“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阴。”(《望牛头寺》)建在山崖间的寺院建筑更别具一格,如写到的秦州石窟寺:“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山寺》)山势巍峨险怪,悬崖峭壁间附着的寺院建筑,有凌空飞跃之感。
佛寺楼阁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常用“楼台”“阁”“楼”等来代称。梓州惠义寺面积大,主体部分在长平山下,但其建筑一直延续到山顶。杜甫描述道:“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峰。阑干上处远,结构坐来重。”(《惠义寺送王少尹赴成都》)“谷中寺”所言乃山下寺院,往上看,满山葱郁的树木中,有房室依山形地势而建,宛在云中。“莺花随世界,楼阁寄山巅。”(《陪李梓州王阆州苏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义寺》)寺阁坐落于山之巅,虽有花草林木遮蔽,而建筑本身借助地势,显得高峻奇丽。寺中官阁主要是供来宾以及游客栖息之所。“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阁迥添愁。”(《涪城县香积寺官阁》)香积寺官阁倚山临水,称得上胜迹。郑南伏毒寺的亭阁建筑也非同寻常:“郑南伏毒寺,潇洒到江心。石影衔珠阁,泉声带玉琴。”(《忆郑南》)寺建在渭河之滨,寺院一直往江心延伸,亭台楼阁,散布在山石之间,一直绵延到渭河上。
佛塔在唐代寺院中很常见,杜甫《与诸公登慈恩寺塔》云:“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夸饰塔高和坚固。“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又从视角、听觉两方面,暗示了塔之高耸。杜甫湖南所作《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有“塔劫宫墙壮丽敌”句,显示了寺塔之崇高壮丽。
(三)体现了佛寺的园林趣味
唐代寺院兴盛是以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奉佛的社会文化为基础,不少寺院形制,有条件走园林化道路。事实上,佛寺的发展,本来便与园林有着天然联系。印度佛教传法初期,基本是居无定所,跟随释迦牟尼的僧众也多是同其居住在山林之间。佛教传入中土后,中国将僧人居处称为“寺”,同时也用“伽蓝”“兰若”等指代佛寺。这些名称本身,透露了佛寺与园林间的一体性。杜甫笔下的佛寺,园林味十足。它们或傍高山,或依修水,自然形成寺院的园林景观。如修觉寺:“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游修觉寺》),在方圆不足一里,但山势颇佳的修觉山高处,临峭壁,俯江水。寺院径石萦带,竹幽鸟语,川云自留,一片天然。诗人难以忘怀,再游后忍不住又对寺院进行了一番写意:“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后游》)秦州城北寺,直接建在原隗嚣宫处,更是得地势之利。魏庆之云:“秦川(州)北绝顶之上,有隗嚣宫;宫之宏丽,莫得状之,今为寿山寺。寺有三门,门限琢青石为之,莹彻如琉璃石。余尝待月纳凉,夕处朝游,不离于是。”[25]城北寺在山顶,景致绝佳,难怪作者会逗留不去。再如《法镜寺》:“婵娟碧鲜净,萧摵寒箨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泄云蒙清晨,初日翳复吐。”歌吟描述的是山水环绕的法镜寺和妩媚幽雅的园林景色。
杜甫笔下在山颠或悬崖上的佛寺着实不少。有的佛寺虽立在山顶,但也不会完全裸露在外,许多建筑都隐于林木之中:“野寺隐乔木,山僧高下居。”(《谒文公上方》)《望牛头寺》:“牛头见鹤林,梯径绕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阴。”云梯般高危的阶磴在山间曲折萦绕,青松雾霭间,巍峨壮丽的牛头寺隐约可见,一幅葱笼掩翳净域的图画。《山寺》写的是秦州石窟寺:“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寺园石清竹幽,鸟语花香,宛如仙境。佛寺园林脱离了尘世的繁杂纷扰,并不代表阒寂无声。“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何处莺啼切,移时独未休。”(《上牛头寺》)花浓竹细,莺啼未休,别有一番意趣。“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游龙门奉先寺》),山寺中会响起钟声,余音缭绕。
(四)再现了寺院中的绘画艺术
杜甫虽以诗称名于世,但其艺术爱好广泛,生前与许多画家过从甚密,且所交多为名家高手,如王维、郑虔、曹霸等,自然深受熏染。晋唐时期,中国宗教绘画发达,佛寺壁画数量多,质量佳。杜甫游历寺院多,所见佛教绘画作品不少。“天阴对图画,最觉润龙鳞。”(《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二)“龙鳞”指寺墙上吴道子所画五龙。杜甫印象最为深刻的,无疑是顾恺之所绘维摩诘画像,时隔近三十年,仍历历在目:“看画曾饥渴,追踪恨森茫。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提到“顾恺丹青列”,亦表达了对顾氏绘画的倾情。杜甫通晓画法,精于品鉴,发而为诗,不乏精辟见解,《题玄武禅师屋壁》:“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州。赤日石林气,青天江海流。”赞美的是玄武禅师所居寺屋内壁画。此是一幅山水画,未必是顾恺之所作,只是借此衬托壁画的精美生动。黄生所评极为生动:“赤日射而石林竟如有气,青天在而江海忽若奔流,妙画通灵至此,信非虎头不能作尔。”“咏画如真,画作怪,诗亦作怪。白日青天,壁上水流,此极奇极险之语,人多作寻常看过。”[26]在通泉县普慧寺,杜甫看到薛稷的书画,引起他极大兴趣,遂作《观薛稷少保书画壁》,云:“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遗迹,指通泉普惠寺薛稷所书匾额及壁画。诗先是总体赞薛稷书画,后又具体形容壁画:“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薛氏画的是西方变相,从地面起一直到屋椽,时间虽久,仍栩栩如生。杜甫还谈到薛书“普慧寺”:“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杜甫“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画图”诗,句下自注:“此寺有晋右军书、张僧繇画孔子洎颜子十哲形像。”《历代名画记》载:“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画卢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问:‘释门内如何画孔圣?’僧繇曰:‘后当赖此耳。’及后周灭佛法,焚天下寺塔,独以此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毁拆。”[27]杜甫所言“古画图”,应为僧繇画写本。
(五)展现了佛寺节庆等风俗习惯
节庆与寺庙间的关系很密切,在寺庙庆祝节日,是中土不少民族的传统。杜甫作于大历五年的《清明》诗,记录了长沙居民和城内官兵争游湘西寺的盛况:“著处繁花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此都好游湘西寺,诸将亦自军中至。马援征行在眼前,葛强亲近同心事。金镫下山红粉晚,牙樯捩柁青楼远。”清明时节景物繁华,生机盎然,鲜花与翠柳、明眉与朱蹄交相辉映,长沙父老齐出游寺,竟日踏春行乐。诗人用如花妙笔,将这一风俗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由此获悉,岳麓、道林等湘西寺院,曾是当年长沙士庶清明时节游冶的主体。
寺院多处山水幽胜地,加之园林化景观的营构,从而使其在宗教功能之外,兼有世俗享受的便利环境。所以,当时不少佛寺常为人们提供宴饮场所,众多朝野名流、文人墨客自然便将聚会饮饯等活动移于寺院。杜甫《惠义寺送王少尹赴成都》《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等诗,所反映的便是这类现象。另外,寺院还具有停住功能。中古时期,云游四方的僧侣,可在足迹所至任一佛寺挂单食宿。寺院接纳客僧之制逐渐扩及民间,遂衍生出新的功能----停客。南北朝时期,佛寺接纳外客之风即盛行[24]1018-1019。唐代海内一统,佛寺停住现象越来越多。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不安,俗人寄居佛寺现象更为普遍。“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28]杜甫为避战乱而奔走流寓各地,不时寄居佛寺,很有代表性。
三、杜甫佛寺诗的地位及影响
杜甫生活的时代,是佛教流行的时代,也是诗禅高度融合的时代,这对他的诗心影响深远。佛寺景观诱发了诗人的创作欲望,也直接影响了杜甫佛寺类诗歌的创作风貌。从大处讲,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佛寺题材开拓与丰富了诗歌内容。佛教寺院独特的场景,为诗人提供了与世俗人境殊异的创作诗思与素材。杜甫众多佛寺诗所反映和描绘的自然人文景观,所抒发的感慨领悟,客观上拓展了诗的境界,同时也为后世同类题材的诗歌写作树立了模板范型。
老杜的佛寺诗,几乎篇篇都有描绘寺庙及其周围景致环境的内容。如:“兰若山高处,烟霞嶂几重。冻泉依细石,晴雪落长松。”(《谒真谛寺禅师》)“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峰。阑干上处远,结构坐来重。骑马行春径,衣冠起晚钟。”(《惠义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得峰字)》)这类描写寺庙环境之美的诗句,在其佛寺诗中俯拾皆是。老杜用其细腻的笔致,将寺庙及其周边秀美的风光描摹得栩栩如生,令人神往。
杜甫佛寺诗中不断增添的佛趣佛理,也使作品意蕴丰厚,耐人寻味。杜甫无论是在年青时期,还是中年、老年时期,都表达过对佛教的向往之情。早年,他在《游龙门奉先寺》中就夜宿佛寺而有所得。困守长安时,他在《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中亦言:“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在现实苦恼无法排解的情况下去亲近佛教,用佛教中的义理排解烦忧。漂泊西南,流浪客居他乡,在贫困的现实面前,更是不免产生向佛、学佛之心,屡屡入佛寺寻求安宁:“老夫贪佛日,随意寄僧房。”(《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在《陪李梓州王阆州苏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义寺》亦感言到:“迟暮身何得,登临意惘然。谁能解金印,潇洒共安禅?”杜甫在佛教方面造诣颇深,对相关教义、思想亦颇有涉猎。因此,他的佛寺诗文中多有信手拈来的佛趣义理性句子。如《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三所言:“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这种独特体验,非深于佛理者不易获得。《谒文公上方》言文公道法高深,欲向其问法:“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望兜率寺》则直言:“不复知天大,空余见佛尊。”表达了诗人对佛陀的印象和对佛理的领悟与向往之情。
另外,佛寺作为宣扬义理的标志性建筑,往往修筑在清幽之境,茂林之中,精巧新奇,富有特色。正如上文所述,杜甫的佛寺诗,不少都涉及和描绘了寺院佛殿、楼阁、房、塔等建筑,从诗材、诗境的拓展角度来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是促进了杜甫诗歌风格的多样化。杜诗素以体制宏大、纵横捭阖、沉郁顿挫、矫健过人著称,但诗圣的佛寺诗却别有一番滋味风调。老杜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创造力的伟大诗人之一,在佛寺作品的创作上,他也决不甘于沿袭陈规,而是能够适应当时的空间环境和自己的情感心态,选择最恰切适当的方式,将眼前境界与心迹真实生动地书写记录展示下来。天宝十一载,杜甫与高适、岑参等在慈恩寺登塔同题赋诗,现存杜集中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便是此次的唱和之作。仇兆鳌有段佳评:“同时诸公登塔,各有题咏。……少陵则格法严整,气象峥嵘,音节悲壮,而俯仰高深之景,盱衡今古之识,感慨身世之怀,莫不曲尽篇中,真足压倒群贤,雄视千古矣。三家结语,未免拘束,致鲜后劲。杜于末幅,另开眼界,独辟思议,力量百倍于人。”[11]106仇氏认为老杜此诗曲尽其妙,雄浑自然,个性突出,足以雄视千古。从诗风看,杜甫更多的佛寺诗呈现为清丽婉转、意蕴悠长的特征。如《山寺》:“野寺残僧少,山园路细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野寺”“僧少”,“眠石竹”“啄金桃”,无不显出山寺之幽静,景色之明秀,心境之淡逸。《望牛头寺》前四句写牛头山上鹤林寺之景,空明澄澈,清婉多姿;“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更是一语双关,心裁别出,禅意盎然。《游龙门奉先寺》绘山寺高寒,钟声悠扬,诗境与禅境完美结合,韵味无穷,与王维《山居秋暝》《鸟鸣涧》等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杜甫佛寺诗洗尽铅华,特色鲜明,引人入胜,是我国古代诗歌的艺术奇葩。
佛寺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为杜甫提供了众多的创作灵感和源泉,相应地,创作主体也通过自身活动,特别是通过诗歌的中介,给当地佛寺空间注入了灵气和新鲜血液。李长祥曾言:“少陵诗,得蜀山水吐气;蜀山水,得少陵诗吐气。”[11]727其实不止巴蜀的自然山水和文化风俗感染着杜甫,凡“诗圣”步履所至处,包括诸多佛寺在内的各地自然人文环境,无不对杜甫的心态及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同样,杜甫及其作品也会反作用于各地文化,在自然和人文景观的传播扩散中,发挥自身独特和重要的作用。一句话,杜甫及其创作与所经过的各个区域空间或佛寺环境之间,存在相互生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
杜甫是中唐后历朝历代人们尊崇喜爱的对象之一,他以其生花妙笔,生动形象、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所经之地各类佛寺景观的特征与意蕴,展现了多彩多姿的自然人文之美。他的佛寺诗作,是奉献给后人珍贵的礼物。老杜曾因世无知己而悲叹:“词人取佳句,刻画竟谁传?”(《白盐山(白盐崖高千余丈,在州城东十七里)》)其实这一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事实上,对于杜诗,后人总是视为珍品,其佛寺诗同样受到重视。唐宋时期,梓州名寺不少,宋李焘《望川亭》就说:“潼川绕郭多名寺,都在少陵诗句中。”这自然是在借老杜之名之作,凸显当地佛寺的地位与影响。梓州清丽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佛寺人文景观,诱使诗圣举目四望,兴怀颇多,创作了不少佳作,客观上提高了寺庙的知名度,增添了寺庙的文化氛围。《方舆胜览》对此作了集中展示:“慧义寺。杜甫《陪章梓州》诗云:‘春日无人境,虚空不住天。莺花随世界,楼阁倚山巅。迟暮身何得,登临意惘然。谁能解金印,潇洒共安禅。’前人(指杜甫)《送王少尹赴成都》诗云: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峰。栏干上处远,结构坐来重。骑马行春径,衣冠起暮钟,云门青寂寂,此别惜相从。”[14]1092所引二诗即杜甫《陪李梓州王阆州苏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义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得峰字)》;“牛头寺。杜甫诗:‘青山意不尽,衮衮上牛头。无复能拘碍,真成汗漫游。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何处莺啼切,移时独未休。’《望牛头寺》诗:‘牛头见鹤林,梯径绕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阴。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休作狂歌客,回看不住心。’”[14]1092所引前首乃老杜《上牛头寺》诗;“兜率寺。在南山,名长寿。有刘蜕文冢碑及蜕三诗刻之石。杜甫诗:‘兜率知名寺,真如会法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庾信哀虽久,何颙好不忘。白牛连远近,且欲上慈航。’《望兜率寺》诗:‘树密当山径,江深隔寺门。霏霏云气重,闪闪浪花翻。不复如天大,空余见佛尊。时应清盥罢,随喜给孤园。’”[14]1092所引前首即《上兜率寺》;“香积寺。在涪城县,有官阁。杜甫诗:‘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阁迥添愁。’‘诸天合在藤萝外,昏黒应须到上头。’”[14]1092所引诗为《涪城县香积寺官阁》。南宋另一部地理学著作《舆地纪胜》,对杜甫在梓州所作的佛寺诗也多有引用和记载,内容与《胜览》所载大同小异,进一步证明了杜甫佛寺诗的价值和在后世的影响传播,也显示了作者欲借助名家声望和影响力,营造和提高地域文化扩散效应的努力。
从上面的简要梳理中不难发现,杜甫的佛寺诗篇,透露了他与佛寺的接触情况,并从特定角度,反映了佛教文化与风俗生活等方面的历史情形,含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当然,杜甫的佛寺诗篇不啻具有认识作用与文献价值,事实上,它们(包括杜甫的入寺活动)本身就已是佛教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对佛教思想的普及、传播中,发挥着积极和重要作用。杜甫一生与佛寺联系紧密,而作为具体承载和体现这一联系的主体----佛寺诗篇,内容广泛,含蕴丰厚,远非一篇小文所能谈透,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尚待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