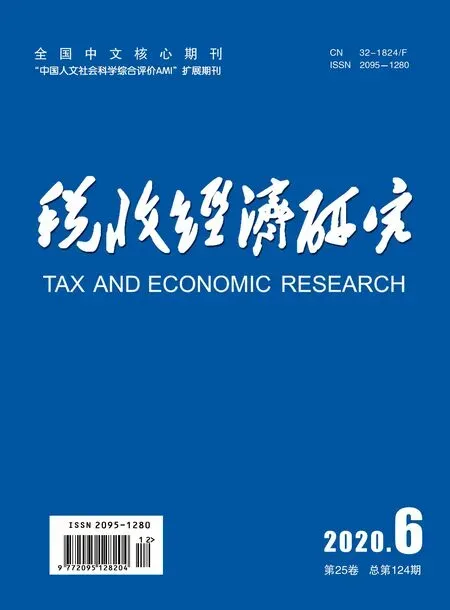国际合作税制的早期探索与启示*
◆林星阳
内容提要:20世纪20、30年代,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组织针对当时各国税制变化趋势以及国别间重复征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征税权分配的一系列原则及方案,为国际税收合作以及国际税收法律制度体系奠定了基础。当前,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勃兴,现行国际税收制度体系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数字商业模式具有的灵活性、流动性特征动摇了以传统常设机构理论为基础的来源地征税权制度体系。鉴于此,不妨回溯早期国际税收合作孕育过程,借鉴百年积淀的国际税制原则及价值内核,从中寻觅有益启示。
为了应对数字化浪潮带来的新的全球反避税与税收竞争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二十国集团(G20)启动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PES)项目,该项目是对近百年的国际税收制度及理论的全面改革。当前,国际税收改革步入深水区,国际各方对于税收协调问题的探讨陷入僵局。有鉴于此,回溯国际税收制度及理论产生的历史脉络,从中发现共通之处,或可为当前数字经济下税制设计的理论铺陈乃至国际税收治理规则的构建有所助益。
一、国际合作税制产生的背景
国际税收协定产生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最初主要用于解决两国之间的双重征税问题,而非出于全球税收治理的整体考虑(崔晓静,2015)。税收协定的产生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世界上最早的国际税收协定是1843年比利时与法国签订的,该协定主要是为了解决两国之间的税收合作及涉税信息交换问题。就税种来看,在遗产税方面,首个国际税收协定是1872年由瑞士沃州政府与英国缔结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在所得税方面,首个综合性税收协定是1899年由奥匈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共同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提出对不动产所得、抵押贷款利息所得、常驻代表机构所得以及个人劳务所得遵循所得来源国征税规则,其他类型所得遵循居住国征税规则(雷霆,2018)。
传统国际税收秩序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张泽平,2017),具有现代意义的对所得和财产价值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综合性税收协定起始于该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国际税收法律制度最为重要的原则——居民税收管辖权原则的确立期(Myszkowski,2016),也是以限制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为原则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的初创期。当时正值一战结束之后,全球尤其是欧洲各国为满足战后社会重建之需,竞相采取提高税率的方法解决本国财政短缺的问题。因此,在各国引入所得税税制后,纳税人从事跨境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国际双重征税问题日益严重,相应地,要求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在消除重复征税方面,国际商会(ICC)初期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一战后世界各国相继开征所得税,税负日益加重,资本输出国(当时主要为英国,此后为美国)纳税人面临的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日益严峻。为了维护从事跨境交易的纳税人的利益,ICC于1921—1924年连续四年组织成员国对双重征税问题进行专题讨论(雷霆,2018)。ICC专门成立了避免双重征税委员会,并于1924年发布研究报告,主张以纳税人居住国税收管辖权为原则来划分跨境交易活动所得的征税权,对所得来源国的征税权及纳税人在其境内的纳税申报义务进行严格限制。显然,这种主张比较有利于维护纳税人居住国在国际税收权益分配中的利益,而不利于维护所得来源国的税收利益,与当时各国的税收协定普遍尊重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实践不相一致。
二、《国联1923年报告》:倾斜的征税权分配规则和形成中的国际税收理论①League of Nations.Report on Double Taxation Submitted to the Financial Committe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mmission.(1923-04-05)[2020-11-20] http://setis.library.usyd.edu.au/pubotbin/toccernew?id=brulegi.sgml&images=acdp/gifs&data=/usr/ot&tag=law&part=1&division=div1。
合理划分税收管辖权是实现国际税收分配公平的最重要因素(刘永伟,2002)。为了促成国际双重征税问题的解决,一个由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任命的来自荷兰、意大利、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家们组成的专家组开展了对国际税收管辖权理论和双重征税问题的研究。专家组被要求调查(a)双重征税的经济后果,即福利影响,(b)一般原则,以及(c)征税权的分配应基于何种实用性规则(Rixen,2008)。1923年4月,该专家组发布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国联1923年报告》)。首先,该报告分析了东道国对非居民投资所得征税的缺点。一方面,东道国对非居民投资者在其境内从事的跨境交易活动所得征税会损害非居民投资者的利益,阻碍非居民投资者在东道国开展新的投资活动,从而影响东道国对境外投资的引进;另一方面,非居民纳税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东道国所征收的税收转嫁至东道国,从而增加东道国接受境外投资的负担。其次,该报告结合了当时盛行的传统课税理论即受益理论(The Benefit Theory)和开始流行的支付能力理论(The Faculty Theory or the Principle of Ability to Pay),作为解决各国征税权冲突问题的理论基础。报告认为,凡是能增加纳税人获取财富能力和消费财富能力的各种要素都应当成为拥有这些要素的相关国家对纳税人课税的依据,拥有此类要素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形成了该报告所称的“经济忠诚”(Economic Allegiance)。
《国联1923年报告》提出了确定纳税义务的两个主要因素,即财富所有人居住地(The Place of Possession of Wealth)和财富来源地(The Place of Production of Wealth),课税权主体应据此进行课税安排。此外,确定纳税义务的其他因素还包括国籍、临时居住地、课税主体实际所在地和课税主体登记注册地。
《国联1923年报告》阐明,传统交换理论(The Exchange Theory)包括成本理论(The Cost Theory)和受益理论,在国内税层面,它们已被支付能力理论所取代。受益理论认为,应该按照赋予个人的特定利益来征税,支付能力理论则更为全面,因为它包含了受益理论中有价值的东西,即根据个人获益的多寡课以相应的税收。个人负担能力与财富获取相结合,便组成了受益理论。在国际税层面,由于无法完全计算纳税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净所得,采用受益理论进行协调征税更为适用。
(一)税收人格问题——从政治忠诚向经济忠诚过渡
当处理税收人格问题时,《国联1923年报告》提出了个人政治忠诚(或国籍的原始观念,Political Allegiance)与个人经济忠诚。对于前者而言,其作为可以遵循的第一个原则,指居住在国外的一国公民通常要对母国负责,尽管他可能除了公民身份之外与母国没有其他联系。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政治忠诚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非居民与母国的政治关系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其一生在国外度过且真正兴趣可能与新住所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对母国的忠诚度可能近乎消失。在人员和资本国际化流动的现代社会,政治忠诚无法经受个人财政义务的充分考验,在实践中正在迅速崩溃,并且理论性显著不足。可遵循的第二个原则是暂时居住,即临时经过一国的每个人都需要在此纳税。然而,临时居留者与暂住国间联系甚微,无理由由暂住国来评估其全部财富。此外,对于频繁更换居留国的人,这样的纳税方式不论就纳税义务抑或税收效率而言,都是不可取的。第三个原则是住所或永久居留国,即在一国长期或惯常居住的自然人在该国具有纳税义务。显然,该原则正远离纯粹的政治忠诚并更趋近经济忠诚理念。但这一原则的缺陷是,当一国大部分财产由非居民外国人持有时,如果该国只依赖于对永久居民征税,可能无法获得足额税收。第四个原则是财富的位置,对于一个财产所有者来说,他被认为是与他的财产所在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具有明确的纳税义务。
在实践中,除了国籍仍作为次要考量因素之外,《国联1923年报告》首次指出课税应在住所地原则与所在地原则(The Principle of Location in the Case of Property)或原产地原则(The Principle of Origin in the Case of Income)之间做出选择。上述两个原则都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忠诚原则,被视为更广泛的经济利益或经济忠诚原则的一部分。理想的税收制度应一次性就纳税人的全部负担能力征税,前提是确定纳税人在其永久居所或住所、财产所在地或所得来源地具有某种经济利益。
(二)经济忠诚四要素——创造经济活动价值的源泉地
《国联1923年报告》接着质疑:若一个人接受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政府的服务,应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对上述国家承担各项应负责任?考察经济忠诚的真正内涵,有三个基本考虑因素:财富的产生、财富的占有及财富的分配①财富的产生指财富产生之前所涉及的所有阶段,即物质生产达到完全经济目的并可作为财富获得的所有阶段。报告举例,如加州树上的橘子在被采摘之前的整个阶段均不会获得财富,直至橘子被包装、运送到所需之处,最终置于消费者手中可被使用,经历了所有这些阶段一直到财富作为成果,可以被不同的地方当局分享。财富的分配是指财富到达最终所有者的阶段,他有权以他选择的任何方式使用它。他可以消费、浪费或重新投资,但其对于所处置财富的意愿均为意思自治,其纳税能力显而易见。财富的占有是指在财富的产生与分配之间,存在着与确立财富所有权并保有财富相关的一系列功能。财富的产生、分配、占有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的法律框架有关,在这种框架下,一个人可以合理预期自身所创造的财富。。除此之外,对于一国政府的财政而言,对财产只具备占有而不享有强制执行之特权,这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微乎其微。由此,产生了财产权在何处得以强制执行的问题。这样,经济忠诚的基本考虑因素实际上变成了四个,即财富的获得、财富的所在地、财产权的可执行性和财富的消费。与之相对应的取得原则分别是:财富来源地、财富归属地、对财富的强制执行权以及消费、占有或处分的居住地或住所地。
根据这四个基本因素,当考虑到经济责任问题时,有四个主要问题需引起重视:一是物理产量或经济产量位于何处(原产地);二是财富经过完整生产过程后,最终结果实际上在何处取得(归属地);三是对于这些结果,可以在何处享有强制执行权(可执行地);四是财富在何处被花费、消耗或以其他方式被处理(消费、占有、处分地)。对此,《国联1923年报告》认为可以制定原产地、归属地、可执行地和住所地四种属地联结方案,并试图将四种经济忠诚因素应用于每一类别当中。
(三)住所地课税倾向——彼时主流的课税权分配理论
《国联1923年报告》着重对原产地和住所地原则展开了深入研究。虽然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要求在原产地原则和住所地原则之间进行划分,但某些考虑因素发挥了作用,使住所地成为主要因素。首先,人格要素,如股东的人格要素,对住所地原则提出重要需求;其次,即使存在不同的公司注册登记地点,住所地原则仍然有优于原产地原则的优势;最后,住所地原则能够更好地符合现代生活的传统。综合上述论证,《国联1923年报告》更倾向于住所地课税制度。据此,报告进一步认为各类所得和财产的来源地、坐落地以及纳税人的永久居所或住所都属于反映该经济归属关系的主要因素,但针对各类所得和财产而言,上述各要素所反映的经济归属关系的强弱程度不同。报告就具体的财富种类展开具体分析后得出以下将经济忠诚在原产地和住所地之间理想分配的结论:比较适合采取原产地课税规则的是土地、矿井、油井、商业机构、农具、机械、羊群和牛群、已注册船舶及财产抵押等;比较适合采取住所地课税规则的是资金、珠宝、家具、所得抵押、公司股份、公司债权、公共有价证券、一般信用证和专业性收入等。
(四)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理论方案
《国联1923年报告》促使学术界就“原产地和住所地之间的征税权冲突与协调”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对于不同国家(地区)采取不同征税立场而引发的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报告提出了四种避免重复征税的方案,即居住国免税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一”)①居住国免税方案,指一国可从居民的应纳税额中扣除其因国外所得而先缴的任何税款,此亦称为国外所得扣除的方法。、来源国免税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二”)②来源国免税方案,指来源国应对非居民来源其境内的全部所得免予征税,亦称为“所得外流式”的免税方法。、抵税制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三”)③抵税制方案,指在两国之间分配税收的方案,即税收分割的方法。该方案可划分特定税种,以便一部分由来源国承担,其余部分由居住国承担,这是试图同时承认上述两项原则,并把负担分摊给两国政府。、分类和分配资源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四”)④分类和分配资源方案,指根据惯例对特定类别的投资或财富(如土地租金、房屋租金和不动产抵押)全面附加来源地税,但对非居民的商业有价证券所得免税。居住国将允许对这种所得来源的居民所得税的全部外国税收予以扣除,但对其他外国来源全额收费;来源国将保留其特定的原产地税收。。报告虽提出了可以通过全额扣税法(居住国免税)、全额免税法(来源国免税)、划分所得法(独占征税法)、税收分享法来消除国际双重征税,但最终还是主张实行建立在全额免税法基础上的全面的居住国税收管辖权。
首先,方案三和方案四并不切实际,因其未从“经济忠诚”的基本要素出发,而是采取宽泛划分税基的方式,并要求涉及所得的双重征税问题的各国均应放弃应得税收的一定或固定比例。这不仅要求特定国家之间就具体税收问题达成协议,很难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税收格局,而且是一种脱离“经济忠诚”理论的逆行。此外,方案三和方案四的实施需要耗费较大的财政成本。其次,对方案一的抵制,是由于语言、所得税制度及所得概念的多样性,加之政治联系不那么紧密的国家间采取来源国课税规则比较困难,比如英国就坚持采取“居住国课税规则”。最后,方案二获得广泛支持是由于其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符合当时资本需求国家的实际做法。来源国免税方案的优点有三:一是符合各国政府所专注之事,就政府无法获得的资本而言,只需将政府的关注超出其自身需要而扩展到资本所属行业本身即可(无须对来源地是否征税进行实证分析);二是符合国家投资的真正经济利益;三是在操作上具有简便性。
可见,受制于早期绝对税收主权观念的影响(刘永伟,2013),《国联1923年报告》的结论与ICC的立场相同,都是对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否定,倾向于维持资本输出国的税收管辖权。
三、《国联1925年报告》:修正的税权分配规则与国际税收理论的补漏订讹⑤League of Nations.Double Taxation and Tax Evasion Report and Resolutions Submitted by the Technical Experts to the Financial Committee: Document F.212.(1925-02-07)[2020-11-20].http://setis.library.usyd.edu.au/pubotbin/toccer-new?id=brulegi.sgml&images=acdp/gifs&data=/usr/ot&tag=law&part=2&division=div1。
虽然《国联1923年报告》的结论与当时德国及其他中东欧国家的国际税收协定普遍尊重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实践相悖,但是,由国际联盟召集的一个由欧洲国家税务官员组成的专家组仍以《国联1923年报告》为基础,于1925年又发布了一个关于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国联1925年报告》)。
(一)居民个人及企业、常设机构的认定问题
对于“住所”内涵的把握是所有问题的根本。一方面,从纳税人角度出发,存在居住国、债权人住所、债务人住所的辨析困难;另一方面,在自然人和法人之间对于“住所”的把握也是不同的。在国际化语境下,常常出现住所(Domicile)、居所(Residence)、仅仅停留(Mere Stay)和主要机构所在地(Locality of the main Establishment)等相近的词汇。对此,《国联1925年报告》指出,不论采用何种表述方法,“住所”都应当统一理解为财政住所(Fiscal Domicile)。
《国联1925年报告》得出与综合所得税(General Income-tax)有关的三个决议。其中,第二项决议指出在居民身份认定方面的困难和一些罕见情况①比如,定期出访另一国的本国居民,当时允许各国之间对此做出安排。捷克斯洛伐克曾与五个国家订立公约,在与奥地利签订的公约中规定一个纳税年度在其中一国居住满八个月为该国纳税人。意大利和波兰签署的公约承认在一种情况下实行分税制,而在另一种例外情况下按照在其中一国逗留的时间比例划分税收。。然而,与现代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投资所得适用的居住国课税原则不同,报告规定将财产投资于容易转让的证券的富人,若其从一国迁移至另一国并在每个国家作短暂停留,且在停留国无自己名义下的不动产,则其可规避条约中相关条款规定,不适用居住时间条款,因为这些条款须考虑到在外真实停留的迹象或相关证据。
企业方面,“财政住所”意味着构成一个居民企业不仅要符合某种组织形式上的要求,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法人等,还应当具有真实的管理控制中心。就公司法人而言,报告建议公司“财政住所”重点关注实际管理控制中心,企业名义上将其总部迁往税率低于其实际管理控制中心所在国的行为将被禁止。
除对居民的相关分析之外,报告还在随后的公约起草环节讨论并总结了“常设机构”问题。“常设机构”包括实际管理中心、分公司、矿山和油井、种植园、工厂、车间、仓库、办公室、机构、装置和其他固定营业地点,但不包括子公司(Subsidiary Installation)。
(二)从来源国免税到有限制的来源国征税权
为了避免国际重复征税,《国联1925年报告》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接受居住国课税作为所得税的基础,但同时不能依赖这一原则的适用完全排除根据其来源于土地财产甚至商业或工业企业的所得征收的所有税收。根据所得的性质,《国联1925年报告》认为必须区分影响其来源收入的税收和因居住而影响纳税人并按其全部所得征得的税收。与此同时,来源国应仅限于对在其领土内产生的所得征税,同时对税基予以严格限制。例如,意大利国家委员会对来源国免税方案作出保留。
各国政府在制定一般原则时,本能地将“原产地”视为征税首选,将“居住地”视为次要选择,因为政府的主要愿景是对非居民征税。也即,如果所得的来源在一国境内,则假定虽然该国境内所得归境外非居民所有,但其对该所得享有主要的税收权利。尽管有所修正,但这仍是重要本能性原则。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当涉及双重征税时,各国政府将准备放弃居住地并转而将原产地作为税收一般性原则。换言之,基于原产地观念的税收,特别是以非关税形式征收的税收,仍然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很难免除这些税收。此外,单一的来源国免税方案受到诟病的一个原因是:这种方法虽然是最简单的处理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但只能适用于条件相当平等的两个国家,很难适用于经济不平衡的国家之间。
《国联1925年报告》认为应该对来源国的征税权予以限制。报告通过例证Morania与Imeria两国之间在所得与财产上的税收关系,强调了居住国享有基础征税权。同时,当来源国在对非居民来源于其境内的所得和财产征税时,双方应当签署条约。重要的是,居住国在任何情况下对居民来自全球范围内的所得征税时,都应给予一定比例的自我限制,即为了避免资本输出非中性,应该允许一定比例的税收归于来源国,这是抵免法的雏形。
此外,该报告结合《国联1923年报告》重新审视了四种避免重复征税的方案,认为不应采取某种单一的方法来消除国际双重征税,对不同税种应适用不同的方法,结合多种税收管辖权原则来消除双重征税。因此,《国联1925年报告》认为应同时接受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存在,但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仅限于对非居民投资者位于其境内的常设机构及其他所得来源征税。对于可能产生的双重征税问题,报告建议居住国和所得来源国双方同时采取限额扣除法和部分免税法加以消除,即居住国在课税时扣除纳税人在境外缴纳的税款,但不得超过该部分境外收入在居住国的应纳税额,而所得来源国则仅就来源于其境内所得的一部分予以课税,剩余部分留给居住国课税。
(三)全球化下的逃税与信息交换制度雏形
《国联1925年报告》指明,由于住所方面的法律冲突,加重了双重征税的有害后果,为了避免加剧国际重复征税以及逃避税乱象,适当的信息公开是必要的。从国际观点来看,对逃税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办法,一种是税收评估,另一种是追回税收。前者的主要挑战是纳税人将资金投资于境外,致使其所在国的税务机关对其财产一无所知;后者的主要挑战是纳税人有可能在另一国避难,使向其追缴税款成为不可能。涉税信息公开主要指前者。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信息的相互交换可能使个人位于两国境内的全部财产在现行法律下负有全面的纳税义务,这对于两国的居民纳税人而言是公平的。
当时,在银行对涉税信息是否公开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1922年热那亚会议上明确要求国际联盟对“国际合作以防止逃税的措施”问题进行研究,同时提出对“任何妨碍交易市场自由或侵犯银行家与客户关系的秘密的提议都应受到谴责”的保留意见,即认为银行对涉税信息应当公开。支持银行涉税信息公开的理由有四:一是交换信息的官员受最严格职业保密规则的约束;二是银行掌握涉税信息是客观事实,公开行为并非银行参与估计客户财务状况;三是从爱国主义出发,当涉税信息将服务于他国财政需求时,银行家、商业公司的雇员和官员将不太愿意接受这些措施;四是信息公开制度应在尽可能多的国家间签署并生效的公约中体现,极少数国家的签署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反对意见则认为,上述信息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应随意公开,破坏银行信用。例如坚持银行信息保密的瑞士和卢森堡反对信息交换标准(Graetz,2003),认为征收预提税是信息交换的合法替代品,可以阻止逃税。而OECD则认为缺乏信息交换本身就是一种有害的税收做法,为有效打击国际逃税行为,应全面、完整地交换纳税评估所必需的信息。但由于法律限制及舆论压力,当时少有国家采纳该建议。考虑上述四点理由,可以明确所公开的涉税信息,实际上限于国家所掌握的信息或在其行政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这是打击国际逃避税的第一步。
《国联1925年报告》的研究结论虽然同时认可了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但其限制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立场与ICC和《国联1923年报告》的结论是一致的。《国联1923年报告》奠定了国际税收权益分配的基本理论,《国联1925年报告》在其基础上拟订了可执行的初步规则方案,两个报告对正在形成中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联盟随后制定的1927年税收协定范本草案和1928年税收协定范本草案都是以上述报告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当时的税收协定实践。而这些税收协定范本草案构成了后来OECD发布的《关于对所得和财产征税的协定范本》(以下简称“OECD范本”)以及联合国发布的《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以下简称“UN范本”)的基础。
此外,为研究国际重复征税和防止国际偷漏税的管理等现实问题,1922年国际联盟在财政委员会范围内成立了一个由英国、法国等七国高级税务官员组成的工作组,1925年德国、日本等五国代表加入该工作组,1927年美国亦加入其中。工作组自1923—1927年间共起草四份有关双边税收协定,即《关于避免对直接税重复征税的双边税收协定》《关于避免对财产继承重复征税的双边协定》《关于征税的行政管理援助的双边协定》以及《关于征税的司法援助的双边协定》。1928年10月,在日内瓦召开的27国代表专门会议形成了“1928年修订范本”,并首次提出“常设机构”在国际税收中的确切定义(雷霆,2018)。
四、《Carroll报告》:营业所得归属及利润分配规则的必要补充①Mitchell B.Carroll.Taxation of Foreign and National Enterprises - Volume Ⅳ: Methods of Allocating Taxable Income.(1933-04-01)[2020-11-20].http://setis.library.usyd.edu.au/pubotbin/toccer-new?id=cartaxa.sgml&images=acdp/gifs&data=/usr/ot&tag=law&part=1&division=div。
由于当时的税收协定范本草案以及税收协定实践都未能明确跨国公司在从事跨国投资活动中所产生的营业所得如何在跨国公司和其成员企业之间分配的问题,加上各国处理此问题的国内法就相关概念和标准的规定差异明显,以致跨国公司在从事跨境投资活动时面临着双重征税的风险。因此,通过税收协定做出统一规定以解决此问题就有了必要性。鉴于此,国际联盟税务委员会于1930年任命美国法学家Mitchell B.Carroll来完成一项关于所得如何在企业间分配的研究,以供制定相关的税收协定范本之用。
1933年,Carroll提交了一份题为《外国企业和本国企业征税问题》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Carroll报告》),在考察英、法、美、德等27个国家的法律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企业间营业所得分配规则以及与所得分配相关的会计规则的建议。《Carroll报告》将当时存在的各种交易所得分配规则归结为独立核算方法、以经验推算方法和按标准分摊方法三种类型,主张以独立核算方法作为企业间营业所得分配的首要规则,以经验推算方法作为次要规则,按标准分摊方法只作为例外规则。就独立核算方法,该报告进一步建议,将跨国公司的各成员企业以及常设机构作为独立实体对待,而彼此之间的交易或经济往来则参考美国国内税法实践,以独立交易原则加以确定。值得注意的是,《Carroll报告》在如何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归属时,提出了“服务补偿标准”和“独立销售标准”,作为独立核算方法的补充。前者将常设机构作为向总机构提供服务的实体看待,由总机构给予其服务报酬,企业的剩余利润由总机构享有。后者将常设机构作为独立分销商看待,在其承担成本、风险和损失的基础上确定归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尽管《Carroll报告》以“服务补偿标准”来实施独立交易原则较为简便为由,推荐其作为确定常设机构利润归属的方法,但显而易见的是,将剩余利润划归给位于居住国的总机构,而所得来源国的常设机构仅获得数额有限的企业利润,与在国际税收管辖权分配问题上限制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观点和立场是一致的。
《Carroll报告》的研究成果直接奠定了1933年国际联盟发布的《关于在国家间为税收目的分配营业所得的协定草案》(以下简称《1933年协定草案》)的理论基础,报告提出的各项主要建议均得到该协定范本的采纳。《1933年协定草案》第三条规定了对常设机构所得的征税,第五条规定了对跨国公司关联企业的征税,这两个条款对其后OECD范本和UN范本中关于常设机构营业利润的征税以及关联企业的征税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1933年协定草案在1935年、1936年做出了修订,规定了企业从事国际运输取得的利润由企业实际管理中心所在地的国家独占征税,以及规定了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常设机构利润归属的特殊办法,但是,关于企业常设机构和关联企业利润征税所依据的独立实体原则和独立交易原则维持不变。其后,无论是国际联盟在1943年和1946年分别发布的“墨西哥税收协定草案”和“伦敦税收协定草案”,还是OECD于1963年发布的OECD范本草案和1977年正式发布的OECD范本,关于常设机构营业所得和关联企业征税规则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五、启示与展望
早期的国际税收治理主要是以适当限制主权决策者税收政策裁量权的方式处理税收竞争中出现的外部性及集体行动问题(孔志强,2018;Laity,Eric,2009)。在20世纪20、30年代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的确立期,ICC和国际联盟的税务专家对于国际税收管辖权理论和消除国际双重征税方法问题的研究,奠定了之后一段时期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发展的基础。相关研究成果一般是在总结有关国际税收法律实践尤其是欧美等资本输出国国际税收法律实践的基础上,从有利于维护资本输出国税收利益的立场(蔡连增,2005),提出了构建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的建议。这些结论和建议在早期由欧美等资本输出国主导制定的税收协定范本草案所采纳,特别是1963年OECD范本草案和1977年OECD范本的吸收,对以双边税收协定为显著标志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确立了实行至今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基本格局。
早期国际税权归属和利润分配规则以倾向资本输出国利益为初衷,为此后作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OECD的相关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一时期对国际合作税制的探索和构建对于消除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及维护非居民纳税人合法税收权益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影响着此后近百年的国际税收制度及理论。譬如,其后正式确定的一些概念如居住地、来源地、经济忠诚、常设机构、独立核算方法等,以及一些税收协定范本如OECD范本、UN范本等,同时还包括基于税收协定范本演进的带有软法性质的受益原则、独立交易原则等国际税收原则,基本是在沿袭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的。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勃兴,现行国际税收制度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对此,不论是采取渐进式抑或革命式变革方式,均不可忽视传统国际税收制度及理论的基础作用。在征税权划分层面,数字商业模式具有的数字化、灵活性、流动性特征,动摇了以传统常设机构理论为基础的来源地征税权,而学者对数字常设机构、价值创造下的各种方案褒贬不一,尤其认为价值创造缺乏理论依据。对此,不妨明确传统常设机构理论系来源地征税权与居住地征税权的妥协和折中,并回溯与价值创造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经济忠诚理论。在利润分配方面,关注受益原则、支付能力原则、独立交易原则对基于价值链的数字利润税收分配的指导作用。此外,对于全球层面所倡导的国际税收治理的规则建构这一难题,或可反思百年积淀的税收协定范本及其“软法硬法化”之路,循其本源,从中觅得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