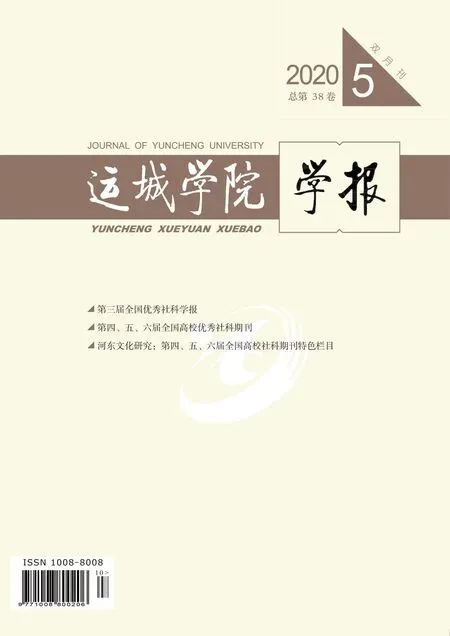博弈与协调:大学三大社会职能内涵的重审
王 强
(运城学院 基础教育部,山西 运城 044000)
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是大学公认的三大社会职能。自中世纪大学诞生起,培养人才作为首要职能是大学区别于其它组织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大学作为高深学问和学者大师集中的场所,拥有众多的学科专家、完备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推动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职能的相继产生。大学三大社会职能之间的递进发展,立足探讨高深学问,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专门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体现高深学问的传承和发展,科学研究体现高深学问的反思和创新,服务社会体现高深学问的应用和推广。[1]
一、布鲁贝克“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
“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源于布鲁贝克先生的封山之作——《高等教育哲学》(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作为西方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学命名的著作,布鲁贝克综合分析各哲学流派的观点,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从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出发,系统构建了高等教育的哲学体系,概括为“认识论”与“政治论”两种不同的哲学观。“认识论”强调:“大学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以“闲暇的好奇”精神追求为目的,力求保持“学术的客观性和独立性”,试图在“学术和现实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政治论”认为:“大学是统治阶级的知识之翼”,不仅把“闲暇的好奇”作为探索高深学问的目的,也强调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必须考虑价值问题。[2]
作为“生产”官吏、牧师、律师、医生的大学和学院,在美国建国初期以“政治论”为其存在的基础。受德国柏林大学改革的影响,约翰·霍普金斯等研究性大学相继成立,高等教育开始转向以“认识论”为其合法存在。19世纪末,“政治论”与“认识论”哲学并驾齐驱,甚至压倒“认识论”哲学,在不同学校或同一学校的不同系里分别起作用。[2]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之间的矛盾也在所难免,“认识论”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政治论”则必须考虑价值的影响。布鲁贝克认为:“两种哲学间的冲突是可以融合和协调的,即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必须以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为补充。”[2]
二、大学三大社会职能的博弈
1. 培养人才: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
培养人才是大学与生俱来的职能,只要大学的根本性质不发生改变,将始终是其首要任务,培养人才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改变。中世纪,大学以传授知识为重,在满足教会、政府对人的需求中不断发展。[3]工业时代,大学注重培养掌握和运用专门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更加侧重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培养人才需要思考和解决“高等教育为谁服务”,即谁能接受教育,接受怎样的教育。“认识论”认为:“大学以追求高深学问为目标,接受高等教育是上层社会的特权,由出身的偶然性所决定。”[2]在受教育者职业选择和社会阶层划分中的作用愈加重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接受高等教育是责任,但更是权利。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即便是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提供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全部经费。布鲁贝克认为:“当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后,将呈现更加多样化的特征,相较中学后教育仅存在程度上的差异。”[4]应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基础上,举办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尽可能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
受教育者“应接受什么教育呢?”即人才培养是普通教育还是专业教育,亦或是同时进行。传统自由教育注重人的理性训练,在“政治论”的影响下,自由教育向普通教育转变,通过学科教材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联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普通教育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强调内容的普遍性和广博性,而专业教育则是培养社会职业所需的专门人才,强调内容的专业性和职业性。普通教育赋予教育新的内涵,应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共同基础,使学生建立起伦理价值观、科学概论和美学观,更好的理解人类社会创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的目的和性质。[2]用范多伦的话说:“教育不仅要让人学会‘做事’,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人’,使受教育者成为有能力、有理智的人。”[2]因此,培养人才必须设法促使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携手并进,因为社会发展既需要专业方面的高深学问,也需要研究方面的高深学问。
2. 发展科学:学术自由与治学道德
在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洪堡提出“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强调教育真正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发展,培养学生探求真理的好奇心和方法,在科学探索中实现自我发展。洪堡理念的实施促进了科学研究和大学教育的联姻,彰显了学术自由的价值与意义,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术自由作为与大学共生的文化现象,是研究者在探索未知、追寻真理的过程中,不受外界的控制和威胁,对社会各方面进行的调查和评论。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人们对学术自由的理解有着较大差异,是建立在学术责任基础上的有限自由,“没有限制就像经济的不干预主义一样成为灾难。”[2]学者在享受学术自由的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有义务为研究所得结论的过程进行充分的表述,以便同行对结论做出准确性的评价和论证。[2]治学道德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保障,是学者研究高深学问的职业道德。学者“作为高深学问的看护人,也是道德的唯一评价者。”[5]需要在高等教育专门领域中进行长期系统的训练,努力献身学术研究,防止因纯粹的主观认识影响其价值判断。[2]学者们也要小心对待源于社会的研究捐赠,为确保不被利用和剥削,要公开感谢所得的资助,并扪心自问研究是否有价值、是否丰富了现有的学术成就。同时,也不能忽视教学工作,应将学生利益牢记于心,有责任和义务把学术界最优秀的著作推荐给他们。[2]
3. 服务社会:学术自治与政府治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大学越来越经常地被喻为“服务站”,在政府和企业的规划中也名列前茅。[2]“认识论”恪守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所,旨在追求学术自治。“政治论”认为大学要立足社会发展,意味着要受政府的约束。作为高深学问的守护者,学者应广泛控制学术和科研活动,因为他们最能深刻理解高深学问的复杂性。现实中,学者们往往自行其是,使得政府常需要借助法律对传统学术自治进行规范和限制,就像战争意义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或许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自治要求具备完全的经费独立,而这种独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2]“大学更愿意承担外部社会机构付钱的任何任务,如果单纯地以为政府和企业毫无私利地追求永恒知识而提供经费支持,纯粹是自欺欺人”。[2]
大学拥有服务社会的众多知识,参与社会服务事关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如果缺乏付诸实践的决心和责任的话,公众可能不会再为其提供经费,知识也将置于无人问津的空中楼阁。大学之所以能存在于社会,总是需要对社会外部集团的愿望和需求做出反应,更多归因于政治方面的考虑。[6]纵观历史上具有伟大影响的学术研究,往往不是来自目的明确的外部指令,更多是研究者对自由世界的理性探索。[7]大学参与社会服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认识论”哲学不能有效保持高深学问的纯洁性,促进高深学问的传承与发扬,反而会影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因此,从“政治论”哲学出发,对大学的学术自治施以内部的某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又受“认识论”的制约。
三、大学三大社会职能内涵的反思
哲学研究不仅要反思历史发展的经验,也要为未来教育实践指明方向。[8]大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三大社会职能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与完善。学科、专业、课程是大学的重要支撑,办学的水平、质量和状态决定着学校的类型、层次和特色,也决定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能力。辩证地分析大学三大社会职能的矛盾与冲突,立足社会与人的发展,以学科、专业、课程的优化与完善为目标,促进大学社会职能的有效融合。
1. 培养人才——以课程建设为基础
高等教育应以人的发展为根本,注重人的精神关怀和塑造,实现践行探索高深学问的使命。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才培养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变化,选择普通教育还是选择专业教育,以综合素质为本还是专业技能为重。纵观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多样化办学是必然的选择。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立足办学定位和社会需求,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知识结构和接受能力,彰显课程建设的重要性,优化人才培养的目标、内容和方法,努力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课程是教育学领域的概念,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有责任从前沿性的学科知识中选择“最有价值”的知识纳入课程,并将这些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服务人才培养的目标。[9]优质的课程资源需要高水平的教师团队将高深学问付诸实践。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指导者和学生发展的促进者,将人类已有的知识精髓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兼顾前瞻性、系统性和实用性,平衡好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学科专业基础与职业技能训练之间的关系。[10]同时,作为人才培养的实施者,应突出人才培养的重要地位,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和完善教学内容,关注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努力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专业化水平,积极开展课堂教学的改革与创新,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优化教学过程,为专门人才的培养保驾护航。
2. 发展科学——以学科建设为核心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不断地通过知识创新、学术探究、文化创造等方式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将科学研究引入教学过程,如何保障教师合法的研究权利呢?学术自由和治学道德作为科研的重要保障,在知识创新、学术探究和文化创造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科学研究自诞生起就与学科、专业、课程有着直接的联系。学科作为研究领域制度化的结果,是大学履行社会职能的重要结合点。学科的形成可以明确研究边界,规定学科内研究者的学术规范,对课程体系与专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发展科学应以学科整合为核心,在研究中践行学者的权利和义务,将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转化吸收,运用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领域。同时,要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和高水平科研队伍建设,以优秀学术研究成果的产出为目标,不断开拓新的专业和研究领域,促进学科资源向课程教学资源的有效转化。因学科门类齐全、学术氛围浓厚,大学历来是基础研究和教育改革的重要基地。基础研究产生的科学发现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应用技术赖以发展的理论来源。[11]受功利主义的影响,部分大学教师热衷于短、易、快的应用研究而忽视长、难、慢的理论研究,急功近利、学术造假、学术腐败频发,对课程建设和专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制约。纵观诺贝尔奖获得者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的贡献,极大地引领了学科的进步与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抛弃“纯学术”的研究,越纯粹的东西越具有原创价值,更接近科研的本质。探索和发现人类世界的未知领域,往往埋嵌在“纯学术”的研究中,这是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所在。[12]
3. 服务社会——以专业建设为根本
大学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必然的结果。学者作为高深学问的守护者,将高深学问以相对适当的方式应用到社会生活中,才能真正体现高深学问的价值,彰显学者自身的社会价值。直接服务社会作为大学的扩展职能是学术自治传统的继承,也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学作为“文化创新和知识学习的场所”,以专业建设为目标,推动科技成果的应用与转化,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服务社会发展与人才培养。
“专业”是社会学领域的概念,是社会需求与学科建设的体现和延伸。受产业结构升级和人才需求变化的影响,新专业不断产生、旧专业不断更新或淘汰,专业建设要立足社会发展需求,不断调整和更新专业的内涵,设置科学规范和灵活多样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培养基础知识宽广、实践应用能力强、具有较强就业竞争力的专门人才。[13]针对不同领域专门人才的培养,要坚持以课程知识结构为基础,一个或多个学科建设为支撑,及时补充课程教学的内容,调整科学研究的方向,推进科教融合与产教融合,确保人才培养的广泛适应性和针对性。
因此,大学参与社会发展互动,不仅要立场明确,更要科学理性。在充分考虑社会效益和自身办学实力的基础上,以社会和人的发展为根本,正确地理解和认识服务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不要盲目功利的参与社会服务,本末倒置、得不偿失。此外,为协调理论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受教育者在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注重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进行有效结合,理性反思知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推动课程专业知识的实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