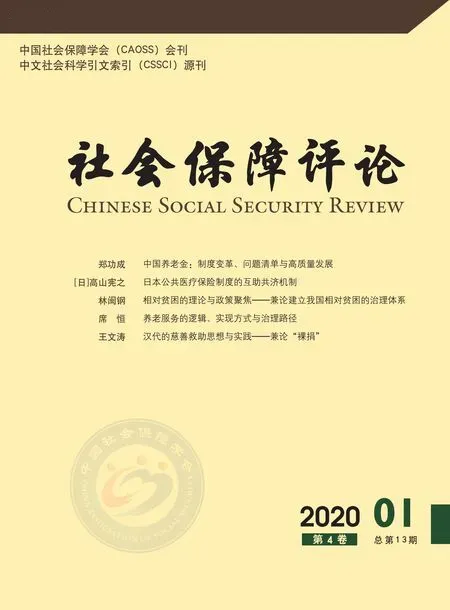汉代的慈善救助思想与实践
——兼论“裸捐”
王文涛
中国传统的慈善互助思想由来已久。《周礼·地官·大司徒》记有周朝国都和近郊的基层社会组织设置情况,“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周济,救济)”。郑注云:“此所以劝民者也。”就是说上述的救助事项虽然是由官府颁布命令,并派官吏协助实行,实际上都是劝导民众互相帮助,即所谓“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汉代学者的注释反映了汉代慈善救助的思想。《韩诗外传》说:“古者八家而井田。……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汉代思想家韩婴追述先秦时期基于“八家相保”的互助情况,赞赏和肯定之情溢于言表,认为这样做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由于君王“仁恩施行”,所以,“其民和亲而相好”。春秋以前,诸侯国国君经常号召家长收族(以上下尊卑、亲疏远近之序团结族人)、恤族,而《周礼》强调要教育民众自相抚恤,对不能相恤者,甚至主张要处以刑罚,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家族逐渐解体、个体家庭普遍化的事实。《孟子·滕文公上》中提倡:“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若能如此,“则百姓亲睦”。孟子的这种互助思想已经打破血缘关系的范畴,居住在同一乡里的人群,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也应友爱互助。降至战国,随着国家救济和收族制度的衰落,以里社为单位的民间互助自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至汉代,在国家的倡导下,宗族、邻里慈善救恤的思想和实践都有了很大发展。
一、西汉的慈善救助
西汉的民间慈善互助在武帝以前有一些记载。例如,韩信为布衣时,“常从人寄食饮”,漂母见韩信饥饿,给他饭吃,一连数十日。韩信大喜,对漂母说:“吾必有以重报母。”漂母大怒道:“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①《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609页。漂母的话着实让人感动,她用为人辛勤洗衣所得助人,却施恩不望报。历代学者多有诗文赞颂漂母的义举,历朝官府也纷纷建祠树碑以示褒扬。成语“一饭之恩”即是对此事的概括。刘邦做亭长时,到咸阳服役,同事和朋友出钱资助,“吏皆送奉钱三,(萧)何独以五”②《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2013页。。鲁国(治今山东曲阜)人朱家,是秦汉之际的侠士。他藏匿和救活的豪杰“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却始终“不伐其能”,有德于人,而不自美。“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以致家无余财,自己的生活很节俭,“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于己私”③《汉书》卷九二《游侠列传·朱家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699页。。此时以乘牛车为贱,而朱家所乘是挽軥之小牛,言其因助人而贫薄。
汉武帝以前民间慈善救助行为记载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经历秦朝统一、反秦起义和楚汉相争等长期战争致使民生困顿、经济凋敝,秦汉两朝又迁徙豪富于关中,经此种种打击与限制,战国以来的大家族已所存无几。汉初承秦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④《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17页。。社会贫困,富人不多,一般平民自顾尚且不暇,遑论以财物救助他人。第二,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恢复发展起来,“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⑤《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20页。。国家富裕了,但是,此时汉代的治民、安民、养民的政治理念将救助贫困视为统治集团应尽的责任,在观念和舆论上既不提倡、也不鼓励民间慈善救助。如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三月“振贷诏”说:“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⑥《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13页。皇帝将自己视为“民”的父母,“子民”有难,父母理当救助,而不假手于吏民。灾异发生,帝王首先检讨自己,主动承担责任,采取减免租税、开仓济民、收恤孤独、节俭备灾、督劝农桑等救助措施。
汉武帝为解除匈奴的威胁,发动了多次对匈奴的战争;又开疆拓土,用兵四夷,耗尽了文景时期积聚的财富,财政困难。《史记·平准书》记载:“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朝廷)助边”。武帝派使者去询问卜式,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目的?
“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捐献财物),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武帝听了卜式的答复,疑惑不解,不相信天下有思想境界如此之高的普通百姓。不想做官,不求出名,也不要朝廷帮助申诉冤情,只是认为抗击匈奴“匹夫有责”,就主动请求拿出一半家产资助边防,击败匈奴,保卫国家。武帝征求丞相公孙弘的看法。公孙弘为人多疑而妒忌,“外宽内深”①《资治通鉴》卷十九,汉纪十一,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615页。,也不理解卜式的义举,认为卜式之言不符合人情,有刻意获取民心的作秀嫌疑,彰显自己的道德高尚来获取民心,一定另有他图。武帝因此没有批准卜式的请求。天子爱天下,帝王爱其民,是先秦以来的礼法观念和执政信条。《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季孙做鲁国的相,子路为郈令。鲁国征发民众开挖长沟,子路认为仁义是“与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以其私秩(个人的俸禄)粟为浆饭,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餐之”。不料子路的善举却遭到孔子的批评和季孙的抗议,责备他擅爱国君之民,“以人臣之资,假人主之术”。恤民、爱民是“人主之术”,人臣不能擅用。所以,武帝时代的君臣恪守这一理念并不奇怪。
元狩二年(前121年),为安置归降的匈奴浑邪王,朝廷开支巨大,府库空虚,适逢贫民大量流徙,国家财政困难,无法满足需求。卜式又捐出二十万钱给河南郡太守,赈济流徙的贫民。河南郡太守上报富人救助贫民的名单,武帝还记得卜式要求捐献一半家财资助边防的往事,赐给卜式“外繇四百人”,即在免除自家徭役之外还可以免除四百人的徭役。“外繇”,指戍边的徭役。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就是赐给卜式十二万钱。卜式把这些赏赐又都献给了朝廷。武帝终于感受到卜式力行慈善的诚意,不再担心他的行为“不可以为化而乱法”,任命他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武帝此举的目的是为百姓树立榜样,教化鼓励天下人捐献钱财做慈善,帮助国家解决财政困难。
一介布衣卜式,致富不忘义,主动为国分忧,舒解民困,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不为猜忌和误解所动,坚持自己的慈善人生。卜式所捐献钱物与其家产的比例在汉代并非最高,数量也不是最多,但是,司马迁对他的善举却做了十分罕见的详细记载,《汉书·卜式传》也几乎全文照录。卜式的慈善事迹之所以如此受重视,主要是因为此时国家财政匮乏,而富豪皆争相隐匿钱财,只有卜式“尤欲输之助费”“数求入财以助县官”②《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第1167页。。
是接受百姓捐献以缓解国家财政困难,还是为防范“擅爱国君之民”而拒绝民间捐助,经过权衡,武帝选择了前者。元狩三年秋,诏令“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③《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7页。。这是汉代政府鼓励、褒扬吏民向贫民借贷、助民脱困的第一道诏令。面对突然变化的政策,即使有朝廷表彰卜式的事例,人们仍不免顾虑重重,响应者寥寥。社会风气和舆论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把金钱借给贫民,难免担心放债难收,仍然需要国家继续提倡引导。元凤元年(前80年)三月,昭帝首次下诏奖赏涿郡韩福等五人为“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每人赐帛五十匹。勉励他们“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①《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5页。。显然,昭帝的慈善政策比其父前进了一步。宣帝为推动“躬行仁义”,索性将“行义”作为察举选人的科目。地节三年(前71年),“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②《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50页。。“有行义”可以被举荐做官,是对行善好施的肯定和鼓励,当然令人动心,有吸引力。这里有必要引述“行义”的含义。一,指人的品行、道义。《荀子·礼论》说:“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汉书·辛庆忌传》:“庆忌行义修正,柔毅敦厚。”二,躬行仁义。《汉书·天文志》云:汉王“与秦民约法三章,民亡不归心者,可谓能行义矣”。《后汉书·鲁恭传》:“今边境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三,有行义的人。《汉书·龚舍传》:“使者与郡太守、县长吏、三老官属、行义诸生千人以上入胜里致诏”。颜师古注曰:“行义,谓乡邑有行义之人也。”
自宣帝地节三年诏后,赏赐和举荐“有行义”之事屡见于史册,直至王莽的新朝仍力行未辍。《汉书·宣帝纪》记载:神爵四年(前58年)四月,宣帝赏赐“颍川吏民有行义者爵,人二级,力田一级”。同书《元帝纪》:永光元年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又《成帝纪》鸿嘉二年(前19年)三月诏曰:“其举敦厚有行义能直言者,冀闻切言嘉谋,匡朕之不逮。”关东地区“岁比不登”,梁国、平原郡连年遭受水灾。永始二年(前15年)二月,成帝下诏奖励帮助政府救灾的吏民。对于主动收养受灾贫民和捐献谷物协助地方政府救济饥荒的人,官府赏赐与其花费相等的钱物。捐款百万钱以上者,授予爵位、低级官吏和免除租赋等奖励。这是汉代政府与民间慈善救助互动的诏令,成帝的奖赏比武帝仅“以名闻”实惠,收到良好效果。永始三年春正月,成帝又下诏:“存问耆老,民所疾苦。其与部刺史举惇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汉书·何武传》有“光禄勋举四行”之语。看来,举荐“四行”包括“有行义”者。同书《王莽传中》:天凤三年(16年)七月,“复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四行各一人”。十月,令“所举四行从朱鸟门入而对策”。《后汉书·吴佑传》:“佑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李贤注引应劭《汉官仪》:“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也。”
受先秦以来宗族互助和政府倡导躬行仁义的影响,西汉宗族大姓不仅在饥荒之年赈济贫穷的宗族、邻里,平时也与同宗共财,散财同宗、乡党、故旧。例如,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继承家产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杨恽的后母无子,财产也有数百万,她死后财产尽归杨恽,杨恽又全部分给了后母的兄弟。“再受赀千余万,皆以分施。其轻财好义如此”③《汉书》卷六六《杨敞传附子恽传》,第2890页。。宣帝时,舒县人朱邑,“存问耆老孤寡”,“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亡余财”④《汉书》卷八九《循吏列传·朱邑传》,第3636页。。出使匈奴二十年不降的苏武,“所得赏赐,尽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余财”⑤《汉书》卷五四《苏建传附子武传》,第2468页。。汉元帝的妹夫张临,“且死,分施宗族故旧,薄葬不起坟”①《汉书》卷五九《张汤传附孙延寿传》,第2654页。。西汉后期,太原人郇越“散其先人赀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志节尤高”②《汉书》卷七二《鲍宣传附唐林传》,第3095页。。
二、东汉慈善救恤的发展
与西汉布衣将相之局不同,东汉是豪强地主集团建立的政权。光武帝刘秀崇尚儒学,开国将领多受其熏陶,接受了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东汉豪强大族势力强大,散财救恤宗亲邻里的观念十分盛行,相关事例的记载也大大超过西汉。下面分三点论述。
1.乐善好施,为助人济困扶贫而倾其所有。马援认为:“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西汉末年,他已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绔”③《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828页。。东汉初,马援又将光武帝赏赐的数千头牛羊“尽班诸宾客”④《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第835页。班,本指分瑞玉,见《说文·玨部》。引申为赐予或分给。《礼记·檀弓上》:“请班诸兄弟之贫者。”。他的四个儿子产业庞大,受父亲影响,都能在每年青黄不接时赈济宗族乡里,“故人莫不周洽”。东汉开国功臣吴汉出征在外,妻子在家置买田产。吴汉回家发现后,责备妻子:“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将田产“尽以分与昆弟外家”⑤《后汉书》卷一八《吴汉传》,第683页。。建武年间,大司空宋弘以“所得租奉分赡九族,家无资产,以清行致称”⑥《后汉书》卷二六《宋弘传》,第904页。。光武帝时九卿宣秉,一生节俭,“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离世时,“自无担石之储”⑦《后汉书》卷二七《宣秉传》,第928页。。“担石”,意即一担,身为九卿的宣秉乐于助人,致使家中竟然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东汉初,鲁郡太守鲍永迁扬州牧,“会遭母忧,去官,悉以财产与孤弟子”⑧《后汉书》卷二九《鲍永传》,第1019页。。光武帝赐予太中大夫郭伋住宅一处,以及“帷帐钱谷,以充其家”。郭伋“散于宗亲九族,无所遗余”⑨《后汉书》卷三一《郭伋传》,第1093页。。右扶风平陵县人韦彪,官至大鸿胪,“清俭好施,禄赐分与宗族,家无余财”⑩《后汉书》卷二六《韦彪传》,第920页。。明帝时人张奋,“节俭行义,常分损租奉,赡恤宗族,虽至倾匮,而施与不怠”⑪《后汉书》卷三五《张纯传附子奋传》,第1198页。。章帝时,太守廉范“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好周人穷急”⑫《后汉书》卷三一《廉范传》,第1103页。。《后汉书·朱晖传》记载,章帝建初年间,南阳大饥,“米石千余,(朱)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焉”。列举这么多的“裸捐”善举,意在说明东汉慈善行为的普遍性和持续性。这些善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系宗族、减少宗里亲朋贫困家庭破产的作用,有利于教化乡里,弘扬社会正气。
2.散财同宗,救恤族人乡邻。汉代人大多是聚族而居,平时的慈善救助对象是由族人而及于乡里,即由血缘关系扩展到地缘关系。东汉初,京兆下邽人王丹“好施周急”,宗族乡邻“没者则賻給,亲自将护”。宗族乡邻有人去世,就送给丧家布帛、钱财,还亲自为他们办理丧事。王丹多年来一直坚持这样做,族人和乡邻“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①《后汉书》卷二七《王丹传》,第930页。。南阳郡宛县人任隗,“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②《后汉书》卷二一《任光传附子隗传》,第753页。,为明帝所敬重。樊宏的族曾孙樊准,“少励志行,修儒术。以先父产业数百万让孤兄子”③《后汉书》卷三二《樊宏传附樊准传》,第1125页。。章帝宗正刘般,“收恤九族,行义尤著,时人称之”④《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第1306页。。颍川郡舞阳县人韩棱,“世为乡里著姓”,四岁丧父。他奉养母亲,友爱弟弟,称誉乡里。长大后,将“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⑤《后汉书》卷四五《韩棱传》,第1534页。。南阳郡宛县人张堪,“为郡族姓”,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⑥《后汉书》卷三一《张堪传》,第1100页。。官渡之战前,袁绍的谋士沮授预断袁氏必败,“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⑦《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第2399页。。
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了族长救恤宗族成员的情况。救助贫困族人是宗族经常性的活动,一年有四次救恤宗族的事项,赈济活动通常由族长召集族人共同实施。三月青黄不接,“冬谷或尽,椹、麦未熟”,“振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九月天气转凉,慰问抚恤“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给予棉衣、口粮,“以救其寒”。十月,秋收农忙结束,帮助最贫穷的族人。“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宗人,共兴举之”。十二月,族长召集宗族、姻亲,“讲好和礼,以笃思纪”。
不可否认,汉代宗族制度有阴暗面,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儒家文化熏陶下宗族制度的积极因素。散财同宗、救恤邻里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贫穷族人乡邻发展生产的效果,有助于宗族邻里的团结和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穷族人乡邻的生活困难,保障了贫穷族人乡邻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和地方秩序的稳定,在抵御自然灾害和解决族人乡邻生老病死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汉的社会舆论倡导宗族内部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将属于自己的财产赠送给宗亲被认为是美德,甚至能以此博得声名入仕。会稽郡阳羡县人许武为了帮助两个弟弟成名,在分割家产时“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而二弟所分财产“悉劣少”,乡人赞其弟“克让”,鄙视许武贪婪,二弟“以此并得选举”。这时,许武会集宗亲,解释自己多占家产的原因,“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现在家产增值,三倍于前,全部让给两位弟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⑧《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许荆传》,第2471页。。东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与叔父堂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⑨《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第1980页。。
3.战乱、灾荒之际宗族乡里的经济救助。战乱、灾荒引发人口大量流徙,此时的救助对象发生变化,范围扩大,人数增加,多有突破血缘关系的慈善救助之举。王莽末年,爆发了长达数年的绿林、赤眉大起义,社会动乱,食物短缺,有些人将自己的粮食全部捐赠给乡邻,帮助他们维持生存。更始帝时,平原郡太守伏湛与妻子“共食粗粝,悉分奉禄以赈乡里,来客者百余家”①《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第893页。。南阳郡湖阳县人樊宏“赈赡宗族”“恩加乡闾”,救助乡里贫民。他借出的钱累计达到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勅,竟不肯受”②《后汉书》卷三二《樊宏传》,第1119页。。安帝时,巴郡宕渠人冯绲,“家富好施,赈赴穷急,为州里所归爱”③《后汉书》卷三八《冯绲传》,第1281页。。顺帝外戚梁商,“每有饥馑,辄载租谷于(洛阳)城门,赈与贫餧,不宣己惠”④《后汉书》卷三四《梁商传》,第1175页。。《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汝南郡平舆县人廖扶,“逆知岁荒,乃聚谷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又敛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琅邪郡姑幕县人童恢,在饥荒之年“倾家赈恤”,“九族乡里赖全者以百数”⑤《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童恢传》:童恢字汉宗,李贤注引《谢承书》,“童”作“僮”,“恢”作“种”也。。颍川郡颍阴县人刘翊,“家世丰产,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东汉黄巾大起义时,郡县饥荒,刘翊“救给乏绝,资其食者数百人。乡族贫者,死亡则为具殡葬,嫠独则助营妻娶”⑥《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刘翊传》,第2696页。。东汉末,遭岁大饥,弃官归家的京兆郡丞赵温,“散家粮以振穷饿,所活万余人”⑦《后汉书》卷二七《赵典传》,第949页。。河内郡获嘉县人杨俊,率领一百多家宗族邻里进入京、密二县的大山中躲避战乱,“振济贫乏,通共有无”。有六家被人抢去做奴仆,杨俊“皆倾财赎之”⑧《三国志》卷二三《魏书·杨俊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663页。。《后汉书·黄香传》记载:“时被水年饥,乃分俸禄及所得赏赐班赡贫者”。在他的影响下,“丰富之家各出义谷,助官禀贷,荒民获全”。富有之家“各出义谷”,反映了义捐谷米赈灾已经是一种普遍的慈善行为。
三、汉代行善去恶的慈善思想
汉代正史在记载慈善者的慈善行为时仅述其效果,未提或很少论及他们的相关言论和思想。前文所述慈善行为和慈善思想缺乏紧密的联系,需要从其他文献中进一步考察。马援的财富观弥足珍贵,历久弥新,一个人拥有财富的最大价值,在于“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慈善思想是慈善行为的内生性动力,考察指导和影响慈善行为的慈善思想,探讨慈善“道德资本”的理论与慈善实践是同样重要的,挖掘梳理和分析慈善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慈善行为。
“善”和“恶”是相对立而存在的,行善和去恶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汉代人行善去恶的议论是先秦时期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汉代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主张行善去恶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西汉初期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在《新书·审微》中说:“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大儒董仲舒认为:“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①《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17页。“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②[汉]董仲舒著,于首奎等校释:《春秋繁露校释》卷五《盟会要第十》,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第238页。。《淮南子·缪称训》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是故积羽沉舟,群轻折轴,故君子禁于微。”所以,做善事要坚持不懈,不要考虑回报。不能“行一日之善”,就希望有终身的荣誉。更不能没有得到荣誉,就说做好事无益,怀疑“圣人之言,背先王之教”③[汉]徐幹:《中论》卷上《修本第三》,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应该坚定善信,“为善若恐不及,备祸若恐不免”④[汉]刘安撰,张双棣校释:《淮南子校释》卷十《缪称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02页。。人活着就要做善事,“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人如果没有行善的志向,“虽勇必伤”⑤[汉]刘安撰,张双棣校释:《淮南子校释》卷九《主术训》,第1024页。。两汉之际的思想家桓谭在《新论·琴道》中主张,人们无论是在逆境还是顺境中都要坚持“善”行,“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达则兼善天下”。君子如何行善呢?《淮南子·诠言训》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布施而使仁无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来。”不善、无行义者,被视为恶者。《汉书·李广利传》中有,“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颜师古注曰:“恶少年,谓无行义者。”
不求回报的单向救恤、施舍思想,具有典型的慈善特征,这种思想源自先秦以来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观念。汉武帝时的宗室刘德,家产过百万,经常救助贫穷的宗亲,认为“富,民之怨也”⑥《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28页。。太傅疏广退休还乡,宣帝赐予大量养老金,他“乐与乡党宗族共享其赐”。有人劝他为子孙置办些田产。疏广认为,如果子孙勤力耕作家中旧有田产,足以满足衣食之需。为他们增置田产,是教他们懒惰。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⑦《汉书》卷七一《疏广传》,第3040页。。刘德和疏广济贫救困的动机源于担心因富有而招来贫穷者的怨恨,希望通过散财同宗、救恤邻里达到缓和贫富冲突、保障既得利益和保护家人的目的。
韩婴假借孔子与弟子的对话,阐述了处理“人善我”和“人不善我”的三重境界,主张“善有差等”,“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这是对待蛮貊之言。“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这是对待朋友之言。“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⑧[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九(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22年。这是对待亲属之言。善行不是无差别的,也要看对象。
《太平经·乐生得天心法第五十四》划分了三个层次的“善”。最善是“乐生”,“夫人最善莫如乐生,急急若渴,乃后可也”。其次是乐于助人为善,“乐成他人善如己之善”。第三是做善事,推己及人。“莫若善于仁施,与见人贫乏,为其愁心,比若自忧饥寒,乃可也”。
怎样引导人们向善呢?汉代很多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主张“赏善罚恶”,统治者应当以奖赏引导人民向善,用处罚警戒人民作恶。《汉书·贾谊传》说:“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同书《张敞传》云:“非赏罚无以劝善惩恶。”《潜夫论·爱日》指出:“赏不隆则善不劝,罚不重则恶不惩。”《论衡·非韩》认为,赏善罚恶要依据法律,这是十分重要的治国方略。“人为善,法度赏之;恶,法度罚之。虽不闻善恶于外,善恶有所制矣。”《黄石公三略·下略》说:“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如果能使“善者得其佑,恶者受其诛”,就会国家安定,“而众善至”。要保护善举,惩罚恶行。国君用奖赏劝人民行善要掌握好度,不能随意奖赏,“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随意奖赏,不是吝惜财物,而是因为随意奖赏起不到鼓励向善的作用;如果奖赏起不到鼓励的作用,“谓之止善”。“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治矣”①《后汉书》卷六二《荀淑传附孙悦传》,第2061页。。
尽管赏善罚恶很重要,但是,只运用赏罚来引导民众行善是不够的,还要教民行义,富民劝善。《汉书·董仲舒传》云:“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今世废而不修,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要改变这种社会风气,必须向古代的治世学习,重视教化,用德善教化百姓。《潜夫论·务本》曰:“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没有富裕的民众,民众即使有善心,也难以用财物助人。本文所举慈善者基本上是富人。富人不一定慈善,但不富有肯定无钱财行善。《申鉴·政体》说:“民不乐生。不可劝以善。”如果人民对生存都失去了信心,就很难用善行来劝勉他们。
行善者不应该讲求回报,即所谓施恩不望报。但是,行善并非没有回报,人不酬报,天报。《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思想对汉代人影响很大。《说苑·敬慎》直接将下面的话托为老子之言:“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类似的说法还见于其他文献,如《韩诗外传》卷七云:“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贼。”《汉书·吴王濞传》有类似的议论:“为善者天报以福,为非者天报以殃。”《太平经·经钞甲部》说:“天道无亲,唯善是与。”“善者修行太平”,行善者修行是为了实现天下太平。
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力行善事,“反常得恶”,有人为非作歹,“反而得善”。人们对这种社会现象不理解,也有不满和愤懑。《太平经·解承负诀》从宗教的角度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这种社会现象不是行善的过错,不能因此而动摇行善的信念。“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这种解释虽然没有科学道理,但劝人行善的积极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绝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宗教迷信而予以否定。《太平经》的“承负说”源于“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善恶报应论和天人感应思想,任何人的善恶行为不仅自身遭报应,对后世子孙也有影响,人的今生祸福都是先人行为的结果。祖宗有过失,子孙就要承负其善恶的报应。如果自身能行大善,积大德,则能避免祖先的余殃,并为后代子孙造福;如果怙恶不悛,神灵会赏善罚恶。这种思想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古代社会对倡导扬善惩恶具有特殊意义。
四、结语
分析西汉时期慈善救助的史例,可见赈济的对象是“宗族”“九族乡党”“昆弟故人”“宗族故旧”“九族州里”等。其中有血缘关系的是“昆弟”“九族”“宗族”。“昆弟”在这里的含义有两种,一是兄弟,二是指同辈的人。“九族”有两说:一,以自己为本位,上推至四世之高祖,下推至四世之玄孙为九族;另一说,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为九族。没有血缘关系的是“乡党”“故人”“故旧”“州里”。从“皆以分施”“家亡余财”等文字可知,这种善举就是前些年国内热议的话题——“裸捐”。有些企业家和热心于慈善的人士宣称,死后捐出全部财产。一时成为社会热点,引来世人关注,纷纷发表评论,反映了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裸捐”是指慈善家把自己的主要财富捐给慈善事业,并非让自己一贫如洗。当然,古今慈善有别。汉代的慈善对象有亲疏之分,《汉书·楼护传》有明确记载。谏大夫楼护出使郡国,与“宗族故人”相聚,“一日散百金之费”,不是平均给予,而是“各以亲疏与束帛”。这种情况在宗法观念盛行和同宗聚居的古代社会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和认知。尽管如此,丝毫不影响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汉代“裸捐”是中国古代慈善互助精神的突出体现。自汉武帝时起,西汉统治者的慈善观发生变化,汉武帝不再担忧臣民与天子争夺民心,鼓励、褒扬吏民向贫民借贷,帮助他们脱困。汉宣帝下诏举荐“有行义”者为官,这是对行善好施的最大肯定,“有行义”被列为察举科目终汉不辍,意义深远。汉成帝下诏奖励帮助政府救灾的吏民,是汉代政府与民间慈善互动的体现。
东汉时期的慈善救助史实充分反映了时人的慷慨好义,乐善好施,有关“裸捐”善举的记载多于西汉,为济困扶贫而倾其所有。为说明问题,有必要再次引用前文所举史例。东汉马援尽散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给昆弟故旧。吴汉将田产“尽以分与昆弟外家”。宋弘以“所得租奉分赡九族,家无资产”。宣秉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去世时“无担石之储”。韦彪将俸禄赏赐分与宗族,家无余财。张奋赡恤宗族,“虽至倾匮,而施与不怠”。廉范“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朱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伏湛与妻子“共食粗粝,悉分奉禄以赈乡里”。童恢“倾家赈恤”,“九族乡里赖全者以百数”。梁商“每有饥馑,辄载租谷于城门,赈与贫餧,不宣己惠”。刘翊家世丰厚,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效果最突出的是赵温,“散家粮以振穷饿,所活万余人”。
汉代慈善思想内容丰富,涉及慈善的思想根源、动机、目的,以及如何行善和统治者应该怎样引导人们向善去恶等问题。关于如何行善,很多思想家都主张行善去恶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拥有财富,贵在能够布施赈济,这样的财富观堪称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不求回报的单向救恤和施舍主张,具有典型的慈善特征。这种思想是先秦以来不患贫而患不均观念的发展,均贫富、乐施向善的动机本源于人类固有的同情心,也反映了驱利避害的心理,因为富有往往会招来仇富。为了缓和贫富冲突,维护既得利益和保护家人,因而散财同宗,救恤邻里,乐于为善。行善不应求回报,要坚持不懈;应该树立这样的信念:行善是有回报的,人不报天报,不报己身报子孙。“赏善罚恶”是引导人们向善的重要举措,用奖赏鼓励人民向善,用处罚警戒人民作恶。不能只用赏罚引导民众行善,还要重视慈善教育,教民行义;更重要的是发展社会经济,增加社会财富,富民劝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