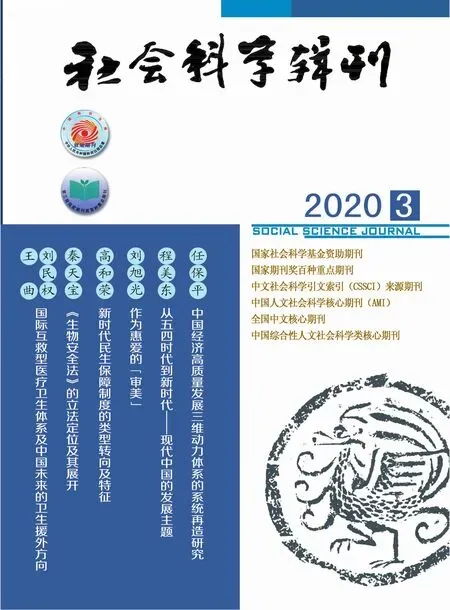《申报》对于洋务民用企业的评论
——以对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的社评为例
李 玉
作为晚清国内最大的媒体,《申报》 一直是中国变革求强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引进西方技术以发展本国经济方面,鼓吹尤多。该报对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关注与评点,就是例证。该局两次颁布章程均得到 《申报》 的专门点评,其他重要事宜也被后者多所评议。全面厘清 《申报》 对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报道与评论,不仅对于中国近代新闻史与企业史研究而言,有一定的价值,还有助于叙说晚清 《申报》 等媒体之于洋务运动的关系。
囿于中国近现代史与新闻史的学科分野,洋务运动与晚清媒体基本是两个独立的学术视域,虽然研究前者少不了从后者征引史料,但对两者关系进行专题考察的成果则不多见。①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主题、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2020 年3 月18 日下午5 时),共得67 篇论文,再佐以“《申报》”作为“题名”或“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结果为零。同样的方式,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前者检得10 篇论文,后者没有。事实上,就洋务新政而言,并非限于洋务派的事业,它之所以能成其为“运动”,说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作为公共舆论平台之一的 《申报》,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社会”的代表之一。系统梳理 《申报》 之于晚清洋务企业的报道与评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窥视晚清“社会”运动“洋务”的努力。
一
中西通商之后,作为西方工业化成果之一的纺织品开始大量输入中国,其影响渐从国计民生拓展至思想领域。
中国被洋枪洋炮打开国门之后,复被各色洋货打开市场之门,继洋纱之后,洋布渐成大众消费品。时人曾对于洋布如何进入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有过这样的描述:“中人之家每因物力艰难,不用绸罗改用洋布者有之。至夏布一物,向来南北通行,自洋布日廉,北方之人不用夏布。盖夏布仅能夏秋炎热之时用之,洋布则自春迄夏,自夏迄秋,可以用之久也。”〔1〕
如同其它洋货一样,近代国人对于洋布爱恨交加。郑观应在其名著 《盛世危言》 中说道:“自洋纱、洋布进口,华人贪其价廉质美,相率购用,而南省纱布之利半为所夺。”〔2〕实际上揭示了一种颇为矛盾的社会心理,一方面是喜欢洋布的性能与价格优势,另一方面是担心对于传统产业乃至民族经济的冲击。
洋布之来华,既造成了中西因商业消费而引发的民族心理对垒——当然,主要以中国方面的后退为主——也造成了现代生产方式与传统产业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国人议办机器织布局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既看到不能禁洋布之来,就只有自办洋布厂,采用机器织布,学习西方的生产工艺与管理方法,在本土生产“洋布”,实行“进口替代”;但同时又担心此举会进一步加重对中国土布业的打击,使旧式机户与织工大量失业,终至利未得害先尝。在此情境之下,《申报》 对于华商自办机器织布局,转变纺织产业发展路径的鼓吹,就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申报》 同人较早呼吁华商:“于上海附近之地集一公司,盖造机房,购齐西国织造各布机器,延请西国织匠来沪,以教授华人织造之法”;认为“仿织洋布定易销售,此实生财之大道也,其获利也必能过于西人”。但有人驳斥其倡办机器织局的真实用意在于“为西国出售机器,不顾有害于中国女工”〔3〕。提出此议者是另一家中文报纸 《汇报》,暗指 《申报》 为英国人出资,所以有助英之嫌。为此,《申报》 力证其非,指出:“不知英国所以执欲立通商和约,盖大半欲使英布来中土,英民有以广织布之业。华布既为手力所织,故难抵英布,若设法以机织,始可抵英,中国可以免每年出大项以购其布,以减英人之利。夫买一机器能费几何?较之年年买布,用银孰多孰少,不待智者而后知。反谓本馆助英,有是理乎?”〔4〕该报强调,之所以宣传中国广购外国机器,创办工厂,“非夺中国之利,实分西人之利也”〔5〕。
《申报》 先就机器纺织之利说起,将耕种机器与纺织机器在中国的优劣与得失进行了比较,以确立使用纺织机器有利无弊、有益无害之念:
西国之机器固无事不用之以代人力,若中国耕种之事,余故未尝劝世改用机器也。诚以中国四民,农居其半,承平之日,农多于田,倘亦改用机器,则农更无地以处置之,不将驱民为非乎?……故耕种之机器,诚可不必也。若夫织布之机器则不然,以洋布之价值,用中国之人力以为之,其势不但无益,而且有损,故欲纺织洋布,必须广购机器而后能有益无损。且此事之利如日前所论,固已了如指掌,既可以分西国之利,又可以为中国多加一项工匠。其一局所用不下数百人,即可以养赡数千人,推而广之,其利可胜言哉?是诚有益无损于中国者也。即以凑集股份之人言之,每年二分利息似可操券而得,若再善于经营,其利息恐尚不止于此。既可使一己博得厚利,且可使众人广沾余利,较之他项贸易,似更稳妥,人果何所畏忌而不为哉?〔6〕
虽然文中说农业种植可以不用机器,表现了作者的认识局限,但其对于机器纺织行业的宣介则是较为领先的。这种比较,可能既是为了突出开创机器纺织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也是为消除民众对于机器纺织会排挤人工、妨害民生的担心。《申报》 申论指出:“有人言中国若用机器织布,是夺男女人工,此言未免不情。现在多用洋布,而土布依旧不废,岂有自造洋布必须添用多人,反致有夺人工之理?夫洋布有碍于他料,无碍于土布,人尽知之,故与其买自西人,何如造自中国?”〔7〕
《申报》 还就推广机器织布的步骤进行了建议:
惟是织布之事,创行之始,似尚不宜过大,少则十万,多则廿万,先行试办,得手之后,再行扩充。何也?此事中国无人见过,须延西匠教授,陡然大举,即须多延西匠,其费用必大;且恐一时之间须用数百华人,其中必至驳杂不纯,恐妄费亦多。不如先行小试,延西匠数人、用华人数十,非徒省费,且易经理。俟办有成法,则扩充更不难矣。……况如此事实为利己利人之举,办有成效,则效办者必多,将来凡江南、浙江、湖北向产棉花之处,皆可各设一局。吾故曰创行之始,似尚不宜过大也。特未知何时始有创行之者耳。〔8〕
可见,《申报》 不仅评介现代机器纺织的产业优势,而且宣介建厂办法,以期调动华商创业之念,俾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效。该报反复论述,洋布“与其买自西人,何如造自中国”,既带动本国新兴产业,又能挽回已失利权。故此,对于创办机器织布业之举,“日论之,而日望之”〔9〕。
《申报》 的期盼没有落空,1878 年,在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下,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机器棉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发起创办。当该局向社会公布章程之后,《申报》“不胜忻然”,“知此事将就绪基”〔10〕。该报不仅将织布局章程全文刊登,而且配以评论,俾资鼓吹。
该报认为上海机器织布局“详订章程,细加勾稽,严行督课,明定赏罚”,皆“足以杜其流弊”。尤其是其“所订招股章程,以及开销经费,皆属悉心推敲、细针密缕,无隙可乘;所言利弊亦明白晓畅,使人一览了然,必非空言无补,致贻人以口实也”〔11〕。
该局章程涵盖投资分配、成本与收益预算、人员雇用、生产规程和公司管理等专项,内容详备、条理清晰。尤其是该局的成本预算,颇得《申报》 评论员赞赏:“所估计之数,棉花价本则以中上为准,洋布售价则以中下为准,延请洋匠、督教工资则计其丰者,雇募散工、学习人数则计其多者;一切开销皆从宽计算,而每岁尚可余银七万数千,则其利劵之操诸己者已不待再费踌躇矣。”〔12〕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成本预算方面尽量取中上标准,而在产品售价方面则取中下等级的做法,即使放在当今,仍然值得肯定,《申报》 对其“点赞”自在情理之中。
《申报》 还就该局高管素质进行评析,认为李鸿章委任的戴恒、龚寿图等人“富而好善”“顾念时局”“提倡群贤”;经元善、郑观应等人“熟谙洋务商情,而洞达事理,且公正诚笃,朴实耐劳”。李鸿章“以此局委诸君,诚可谓得人也”〔13〕。此语既是在肯定戴、龚、经、郑等人堪当斯任,也是在表扬李鸿章知人善任。
但是,没想到在建厂过程中意外迭出,各种事宜一再蹉跎,特别是经历了1883 年前后的上海股市风潮之后,筹办进程陷入停顿。
二
4 年之后,该局重定章程,再次启动建厂事宜。《申报》 于 1887 年 7 月 30 日对于该局章程又一次发表评论,其文如下:
中国自仿行西法创设公司而后,凡事之不能一人成者,往往集数千百人之资而为之,此固事之至善也。然数年以前,煤铁铜锡诸矿纷纷并起,股票四出,股价时涨,势亦就成矣。而兴焉勃焉,亡焉忽焉。至于今日,除开平煤矿、云南铜矿、利国铁矿而外,无一有成者。所设公司,则自已成之招商局外,其余亦皆成画饼。是西人合股集事之法,似未尽善矣。夫西人之为此者,未尝有倏成倏败之虑,是岂真人心之不同耶?财力之不若耶?盖亦办理无人、章程不善耳。夫公司之设,学西法也,乃学其开公司而不学其章程,但学其形似而不求夫神似,是犹东施效颦矣。
……
夫机器织布之说,吾闻之久矣。数年前,织布股票行出之际,原价百两者亦曾涨至百十五两,西国机师亦曾聘定,外洋机器图样亦曾寄到,房屋亦曾动工。当轴者方冀其蒸蒸日上,旁观者亦谓其汲汲将成。乃未逾数月,竟尔冰消瓦解。机局之旧基在下海浦,仆尝过其地,见数十万之资财、数千人所期望者,惟余扶疏破屋、零落颓垣尔。时股票之说久矣 [已] 歇绝,虽欲成其美举,谅无具此大力之人,亦徒增浩叹耳。不意今日竟有续成之者,昨见新章十八条,每阅一条辄为称快。而其中撙局用以节费、除情面以用人、去私见以济事、严功程以习勤四者,尤为得公司之本者矣。
前之所以败于垂成,以局面过大也,以所用多私昵也,以诸股东、诸董事意见不同也,以学洋行之法而办事之时少、游戏之时多也。局面过大则费用浩繁,资本必将不继;用多私昵,则才不任使;意见不同,则事多掣肘;游戏时多,则正业不精。踵此四弊,又安得而不败?不特织布一局也,即诸矿局之败,亦莫不由此。今既有鉴于昔,力反前非,当事既能定此章程,则办理谅亦不忧无人,布局之成固可操夫左券。〔14〕
之所以连篇累牍地将这篇评论摘出,是因其所论并不完全着眼于上海机器织布局,而是关于晚清公司制建设的深刻检讨。
晚清公司制企业以轮船招商局开其先河,继起者除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之外,还有上海电报局、津沪电报局、开平煤矿、平泉铜矿、长乐铜矿、鹤峰铜矿、顺德铜矿、施宜铜矿、三山银矿、金州煤矿、池州煤矿、荆门煤铁矿、徐州煤铁矿、贵池煤矿以及仁和保险公司与济和保险公司等。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官督商办公司”曾经在上海股市之中大显身手,当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之际,《申报》 曾对其股票市价的上涨情况进行了报道与评论:
中国人虽间多因循苟且之习,而近来风气日开,殊大异乎曩日,集股纠分视为故常,凡西人之股分皆竞愿投附,岂有中国自创公司而反不愿附股者哉?或者以为西人信义素著,创设公司必无欺罔之弊,故华人乐为附股,若华人自创,则人反有所疑阻,恐贻后日之悔,故裹足不前者有之,夫是以难于集事。然机器织布一节,则创议已久,人亦信之,现在股分早经满额,所云股分票价涨至一百十五两者,盖此项股分虽原价一百两,仅取五十两,以五十两之原价涨至一百十五两,则合之一百两之数已增至二百三十两,较之招商局之原价百两照数收足,今增至二百四五十两,开平煤矿原价百两照数取足,今增至二百二三十两者,殆亦不相上下。〔15〕
织布局股票确实在市面大受欢迎,该局原拟集股 40 万两,分作 4000 股,但“因附股者实多,不得已公议加收一千股,预备扩充机张之用”。但未过多久,加招之股“亦已足额”,创办者特地自1882 年5 月12 日起连续数日登报声明,不再接受投资。〔16〕由于所招商股总额远超预想,织布局总办郑观应等公议之后,禀告李鸿章缓领官款。〔17〕
但是,股市风潮接踵而至,各“官督商办公司”莫不损失惨重。上海机器织布局在1882 年所招 50 万两股本中,现银只收 35.28 万两,其余14.72 万两或系抵押在局中的股票,或系认股单(该局规定认股者分两次缴银,每次各缴五成)。而已收之35 万多两,除支付购买机器等项花费20.9 万两外,其余银 14.3 万余两,或已贷出,或购股票,“均无实银存局”〔18〕。股价大落之后,押股者不肯来赎,认股者也推宕不付,随着上海股市风潮的加剧,织布局原本百金之股,市价仅为十余两,公司与股东俱受重创。资金链断裂之后,该局筹办陷入停顿,一搁多年,“不但有股诸人不胜恨恨,即局外旁观者亦未尝不深为之扼腕也”〔19〕。
织布局等“官督商办公司”在19 世纪80 年代初的倏成倏败,引发了国人对于中国公司“东施效颦”的检讨。正如 《申报》 在评论织布局新章程时所指出的,中国仅“学其开公司而不学其章程,但学其形似而不求夫神似”;尤其是公司经理层,“既合众人之赀,竟慷他人之慨,花天酒地,一任遨游,视公司之财如内库之藏,所办未就,资本已亏”。这些不良操作严重败坏了公司机制的社会信誉,“如是而曰兴公司以获利,是犹赵人至楚而北行也”〔20〕。
经过此次风潮,“人皆视集股为畏途”〔21〕,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22〕。时人多以为织布局的“烂尾”工程恢复无望,“虽欲成其美举,谅无具此大力之人,亦徒增浩叹耳”〔23〕。
令 《申报》 同人欣喜的是,织布局建厂事宜在1887 年再行启动,重定的章程较前颇有改进,以致作者“每阅一条辄为称快”,“其中撙局用以节费、除情面以用人、去私见以济事、严功程以习勤四者,尤为得公司之本者”。作者由新章程判断织布局经营管理将大为改善,对其前景充满信心,用作者的话说,“当事既能定此章程,则办理谅亦不忧无人,布局之成固可操夫左券”〔24〕。
此次织布局的重组方案涉及老股与新股的关系,局方定出方案,将此前的老股以七折计算,限每股补缴30 两,与新股等同。此举一出,一些股东认为开办有期,特在 《申报》 发表公启,表示支持。〔25〕《申报》 专发社评予以呼应,认为旧股七折之法,系体恤旧股、折服新商的“公平”之举,“当亦为闻者心折矣”〔26〕。
同时,《申报》 对于官宪的支持与经办人员龚寿图等人的坚持不懈表示赞赏,认为此局在蹉跎多年之后再次启动,全赖北洋大臣为之作主,有关道宪为之督办。〔27〕《申报》 同人毫不掩饰对于织布局尽快建成的殷切期盼:
以华人而仿外洋制造之物能成者固不多见,能精者益复寥寥,西人笑之,华人非之,此景此情,殊为愦懑,倘有一事一物而足以告成,藉以杜众人之口,则亦足以一吐其气,是何等快事耶! 仆于机器织布局之成,望之已非一日,一旦而有成功可望,不禁拍案大喜。〔28〕
但是,织布局的旧股七折之法也招致一些老股东的强烈反对,他们发布“公启”予以谴责,要求任事者“必须先将旧账揭清,昭示众商,追还侵挪之资,明示实存之数,无力者给还余本,有力者听其加银”〔29〕。此举使织布局复建难度增加,而 《申报》 则力挺局方,发表专评,认为该局“兴复”之举筹划周详,其“酌加旧股、继招新股”的方案,“实事求是,井井有条”,所以相信“其获利可期,而成功可卜也”〔30〕。
三
在 《申报》 的支持表态方面,还有许多要求政府为该局减免厘税的呼吁。国内议办机器织布企业甫一发端,该报就直言,“欲自造(洋布),必须减其税厘而后可成也”〔31〕。该报在1876 年专门发表社评,呼吁政府为机器织布厂之设而修改税则,其言曰:
夫设厂仿织洋布,原欲以分西人之利,而富中国之民,其法可谓善矣。然仿织之布既多,不能专售于一地,必须分贩于他乡,亦明矣。其完纳之税厘亦应与西商运来之布事同一律,而后人民方可望沾利益,亦至显矣。乃传闻所定征抽税厘科则又有大不然者。盖西商运来之布进口输正税后,则可发往通商各口,不须再输半税,此和约所定也。新关己定税则,中国所织之布视同本国货物,若上海之布运往汉口、天津各处,除完正税之外,又须另加半税,岂非保护外国制作之物,而疾视本国制作之人乎?是于理则之大道未免难言其得平也。
夫富国之道莫要于扶持国人之艺作,俾国人皆有所用力,以臻殷富,故他国运来制作之货税宜加重,而本国运出之货税宜减轻,如此则国人方获厚利,而国家亦可增富……孰意中国反昧于此理,往往致百工束手而不为,众商裹足而不进。〔32〕
该报在评论织布局新章程时进一步建言,创企业办公司,光靠内部治理远远不够,外部环境,尤其是政策环境亦至关重要。作者对于中外纺织企业的技术与市场优劣进行对比后指出,减免税负对于中国纺织企业的发展尤为关键:
欲收回外洋之利源,则犹有进焉者。就大势而论,洋人远隔数万里贩至中国,一切水脚诸费固已不资,出售之际其价必贵;华人于内地自行织造,则地既近便,价必从廉,此洋人所不能与华人争者,利源之收可必在此。然不知华人之价有不克廉于洋人者。中国之例,一切货物过关则有税,遇卡则有捐,商人运货他往,既纳捐税之后,苟以销场稍滞折而复回,则所过关卡必再纳捐税而后可行。如此数回,货未及售而货本已销于捐税矣。贩运洋布亦犹是,然则其价又安得不贵?价贵则销滞,销滞则利微矣。
外洋则无此患,闻泰西诸国之法,本国所出之货物苟非天地生成而有藉于人力者,则除烟酒之外,悉予免税。是洋人贩运水脚虽重而捐税轻,华人自造,水脚虽轻而捐税重,二者相权,则华人之价安能廉于西人乎?运至中国之货,自正、半两税而外别无所费,则成本轻而利自厚。且洋人事此已久,业此必精。此时闻中国自行织造,恐利源或为所夺,谅亦必更加整顿,其出货必速,其布疋必精。中国此时乃初次仿织,既不能与彼久习者相颉颃,苟复加以捐税之重,而犹曰可以价廉物美、销场日广、获利日多,其谁能必之?是中国而欲收回洋布之利源,必先轻税免捐,以苏商困而后可图,不仅章程美备,办理得宜已也。……今日之商务固已远不如昔矣。茶也,丝也,皆中国所恃以与泰西争通商之利者,乃近年来中国之丝、茶销场日滞,推原其故,皆由于捐税之重。夫商务既衰,独重捐税,亦有何益?然已往之事不必言矣,若能于洋布一事而开减捐之端,则亦未始非有益于商务之全局也。〔33〕
企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商务大局,更关乎国家财政基础。如果一味加捐增税,无疑于杀鸡取卵;适度减免税负,则会起到广开利源、培本固基的效果。《申报》 的这一态度,也见诸对待其他新式企业的兴办方面,呼吁减免厘税,以助新式企业发展,是该报自创刊之后一以贯之的态度。正如其评论所言,“无横征暴敛、朘削民人,是不徒机器布厂大得其利,则天下兆民皆享美利矣”〔34〕。这说明,《申报》 对于机器织布局的支持,实际上是立足于近代纺织业的整体发展而言的。
李鸿章在督饬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之际,为其奏准“十年专利”,此举自然有利于企业发展,但对于其他民办纺织厂、对于整个纺织行业而言,则并非佳音。《申报》 虽然支持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建,但对于“十年专利”背后的政府垄断意图不表赞同,该报曾借“友人”之口,表达了相应的观点,其言曰:
中国于一切制造之事,往往官场中大权独揽,不肯任商民之自为;商民受制于官,虽有赀财,亦不能大兴贸易。即如纺纱一事,官既集赀以设局,即不准商人之仿行。然窃以为官固不应压制夫商人,且其职当保护商人,使民富而国亦因之以富。乃官明知纺纱之可以获利,而偏不许商人分其利,其心惟图一己中饱,独不顾利之流至外洋。嘻,是诚何心哉?〔35〕
《申报》 提出了鲜明的官商职责分工论,其评论中有这样的内容:
殊不知人各有能、有不能,官惟知守官常,断不能明商务。譬之建屋而委其任于陶工,譬之造船而责其效于医士,谓其能胜任乎、不能胜任乎?今以官而经理纺纱之事,即令雇西人襄办,而事多隔膜,迄于难成。即使有成,而靡费既多,成本自贵,安望其能各路畅销耶?……总而言之,官惟宜尽官之所应为,不必越俎而谋商务,庶商人得以展其抱负,尽力经营。凡百贸易皆然,岂独纺纱一事?迨商人富,而国家不患不足;国既足,则自能日底于强。〔36〕
可见,《申报》 不仅站在纺织行业全域,而且延展至民族经济大局,发表重工重商、富民强国的言论。《申报》 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相关评论,正是其重工重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总体而言,《申报》 在晚清时期,对于以运用新式生产设备、体现新型生产力、产生强大经济与社会功效的洋务民用企业多所鼓励,除了机器织布局,该报还分别对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平泉铜矿、云南铜矿和漠河金矿等洋务企业发表过专评,同样是肯定多于批评、鼓励多于指责。
《申报》 是晚清新媒体的代表,也是主要的公共舆论平台,该报对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民用企业的积极关注,并未停留于单一的新闻报道,而是进行深度评介,并代为呼吁,体现了对于中国近代新式企业创建与发展的大力支持。此举无疑有助于拓展洋务民用企业的社会性。
首先,有利于扩大这些企业的社会传播面。《申报》 创办于上海,面向全国乃至海外发行,其固定发行点初期集中在江南乃至沿海地区的通商口岸,后来渐拓渐广。例如1887 年时在北京、天津、保定、营口、烟台、南京、武昌、汉口、九江、广州、安庆、扬州、镇江、南昌、杭州、常州、苏州、嘉兴、福州、厦门、宁波、温州、西安、重庆、长沙等 20 余个城市设有“售报处”,而其他各埠则可由信局及京报房代售。随着 《申报》 阅读版图的不断扩大,其信息传播面自然相应扩充。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除了在该报刊登广告之外,还被该报以社论形式多所评点,其社会传播面自然进一步扩大。其次,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民族性。洋务民用企业的创办背景是中西商战日烈、传统产业经受不了西方工业产品的冲击,民族经济遭到严重威胁,《申报》 反复阐述中国创兴新式产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强调各企业肩负着堵塞漏卮、挽回利权的重要使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强洋务人员对于企业创办目标、职责与使命的认识与认同。第三,有利于增加企业社会形象的公共性。《申报》 在显著位置,以社论方式对相关企业的多次评述,不仅有助于民众对于各企业内部情况的了解,而且使其各方面的影响与意义得到传播,提高了各企业在社会舆论场中的地位与分量,使其受关注的广度与深度都超越了一般的工商企业。凡此种种,都使得洋务企业产生不同于普通工商企业的社会性效应,进而有助于“洋务”扩展为一场“运动”。
只可惜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成后不久,遭受了火灾①即使在该厂遭遇火灾,致“数年之功隳于一旦”,该报在“为之扼腕”的同时,仍多发表鼓励其再起的言论,表明不愿“追咎办理者之前失,而惟冀规复者之有人。诚以此事为中国所创办,足以大开风气,宏扩规模,收外洋之利权,裕中国之财赋,其所关者殊非浅鲜”。该报还借评论员之口叮嘱织布局同人复建之时,“用人必量其才,勿以情面是徇也;理财必审其宜,勿以算小为尚也;筹度不可不周,勿挂一而漏万也;防备不可不预,勿临事而仓皇也”。其良苦用心,于此可见。参见《论织布局规复之可喜》,《申报》1893 年 12 月 26 日,第 1 版。,后来虽然改组成华盛纺织总厂,但毕竟没有像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一样形成较大气候,在一定程度上“辜负”了 《申报》 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