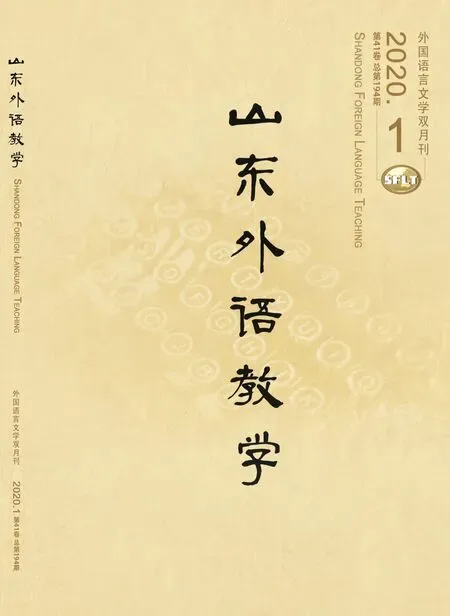简·奥斯丁小说中的农村经济叙事及道德主题
张鑫
(江苏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1)
1.0 引言
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出生于牧师家庭,终生居住在乡间小镇。她的创作时期适逢英国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经历巨大变化的阶段。基于生活环境、居住空间、阅读认知和实地考察,奥斯丁了解和洞悉其时代的农民和农村经济舆情。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奥斯丁时刻关注农村和农业经济,她的作品里充斥着与农村经济有关的叙事。在塑造新型农民形象的基础上,奥斯丁不但表达了自己对时代农村经济发展和理想农民形象的观瞻,而且基于农村经济叙事对传统农村社会解体前的道德主题作了富有现实主义意义的建构。
2.0 农村经济和农民形象概况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英国的农村经济和国民的吃饭问题,都要依赖由地主(landowners)、农民(farmers)和工人(workers)构成的“三驾马车”(triumvirate)的共同驱使(Curtler,1979:68)。地主通过向农民出租土地而获得最大的收益,是三驾马车中最富有、最稳定和最有权势的阶层,他们的乡间村舍一直都是奥斯丁小说的主要故事发生地。土地工人(主要包括签约干活的田地工人,按日或工作量计酬的普通农工)的工作是照看牲畜、种收庄稼和除草赶车等。农民是处于地主和工人之间的阶层。他们虽然没有地主的稳定,但是又比工人拥有更多财富。在奥斯丁的时代,农民经历了无数激烈的变化,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地位也是反复无常。农民阶层包括佃农和自耕农。前者从地主那里租地耕种,后者虽拥有小块土地但并不会像地主一样出租土地。由于并不会完全依赖或归属地主,自耕农一般比佃农的地位要高一些。
自中世纪晚期开始的圈地运动到18世纪终于被法制化了。少量土地的拥有者被剥夺了土地拥有权,依靠共有土地而生的农户失去了生活稳定性,地主阶层的受益日益增加。技术革新和运用使得农民的耕种效益大幅提高,他们可以在自家土地上进行新式农耕。播种、收割、脱粒、灌溉和施肥等工序都用上了新技术,曾经荒废的土地又被开垦出来,农业产量得到大幅提升,小麦的亩产量突破了历史极值。农业大丰收促进了人口的急速增长,英国人口从1720年代的530万猛增到1800年的870万(Overton,1996:64)。随着农业技术的运用、农业产量的增加和农业管理的科学化,社会对农业工人的需求则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1800年前后,只有30%到35%的人口受雇于农业,降到了历史最低值。
因短期供应不足和英法战争造成的长期通胀,带来了商品价格的飞速上涨。在这样的时局下,农业生产更像是一种投机性冒险而不是传统职业。“丰收的农作物很快就转化成了资本,当聪明才智与资本联姻后,耕种土地的费用比以前降低了一半”(Willis,1813:236)。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富于冒险与创新精神的农民开始租种更多田地,其他商人和不谙熟农业的人也都在利益驱使下开始租地业务。囤积大片土地的佃户不但可以在市场上呼风唤雨,还可以在乡村出人头地。自耕农依靠租来的土地扩充自己的耕种面积,还有一些自耕农也在土地买卖上投资。于是佃户和自耕农之间的界限就愈加模糊起来。19世纪早期的新型农民“一般都是有聪明才智和有活力的人,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思想自由,富有创见,兼有佃户和自耕农的富足与体面”(Vancouver,2002:80)。在民众的眼里,那些比较富有的农民的社会认同感得到了提升,“一个拥有不菲资产的农民,通常都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有更加广阔的思维。他一般会有优质的教育,更强的进取心,对于克制隐忍也更加宽容,更易于接受进步和革新”(Sinclair,2010:33)。
3.0 小说中的农村经济叙事
奥斯丁之所以能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对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有令人信服的叙述和道德主题思考,首先得益于她对农村和农业的熟悉。她在书信中频繁提及父亲饲养的家畜和他在斯蒂文顿经营农业的情形。在乔顿的日子里,奥斯丁对农村生活的兴趣未减,时常在书信里提到当地的农业生产和农民境遇。1813年7月在给哥哥弗兰克的信中,奥斯丁饶有情趣地大谈乔顿的天气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前几天天气晴好,对那些家里有草料和牧场的人来说非常适宜。总体看来,这一定是一个适合收割草料的季节”(Austen,1995:214)。第二年6月奥斯丁又在给姐姐的信中赞美乔顿乡村的好天气:“这是一个美好的乡村之日,我期望城里不要太热。……傍晚的空气更加清澈了”(Austen,1995:240)。奥斯丁对农业生产的熟悉和关注在小说文本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她的小说中可以发现所有18世纪末以来关于英国农业生产的因素:萝卜、苜蓿、农作物轮作、排灌系统、农业机械改良和家畜饲养等。从格雷厄姆雇佣来自苏格兰的管家那里,可以看到苏格兰对英国农业生产的影响。从马丁先生主要阅读《农业报告》的细节上可以看出当时农业出版物的重要性。
奥斯丁对视野开阔、思想先进的新型农民一点也不陌生。她的邻居哈里·蒂格伍德(Harry Digwood)和威廉·蒂格伍德(William Digwood)兄弟就是这类农民形象的典型代表。蒂格伍德兄弟在斯蒂文顿和乔顿经营农业生产和土地租赁等业务,经济基础好、社会地位高。他们在1811年举家搬迁到乔顿农庄选购家具一事曾引起奥斯丁的极大兴趣。在购买家具时,蒂格伍德兄弟极尽时尚之能事,选取的尽是希腊式的沙发、特拉法格式的红木椅子、布鲁塞尔地毯等物件。他们家里还有一套马车和一头驴子。蒂格伍德家的男孩子被送到牛津大学读书,蒂格伍德先生经常参加当地郡县的政治和慈善活动,在那一带颇有名望(Slothouber,2015:73)。从小说中的新型农民角色塑造来看,奥斯丁对她的这个绅士农民邻居的情况想必是非常熟悉的,对他们的身份变迁和地位蹿升也持赞赏态度。
奥斯丁在作品中进行农村经济叙事时,极少对农村和农业发展进行论述,而是假以新型农民角色的塑造,精准再现当时的农村经济现状和趋势。谈及奥斯丁小说中的新型农民形象,首先出现在脑海里的应该是《爱玛》中的乔治·奈特利了。他和别人的谈话都是关于农耕活动的内容,他在和哈丽埃特聊天时,告诉对方的也是“各种耕作方法”(《爱》:366)①。爱玛听到奈特利与人谈论农耕或农业的话题如此之多,尤其是谈论“牲口展览啦,或者新的播种机啦”(《爱》:476),以至于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关心她的内心。奈特利虽身为一个农民,但是在社会地位上却属于地主阶层,“作为一个农场主,家里的登威尔农场由他经营着”(《爱》:102)。
《爱玛》中的罗伯特·马丁是另一个典型农村经济代言人和具有现代精神的新型农民形象。马丁“租了奈特利先生的一个大农场”(《爱》:22),是奈特利的主要租户。他不仅有租种大型农场的魄力,而且有实干精神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在他的经营下,农场处处是“兴旺美丽的附属设施”(《爱》:366),在“丰饶的牧场”里有“遍地的牛羊,花儿盛开的果园”(《爱》:366)。他同时还是一个谙熟时代农业政策的新型农民。据哈丽埃特回忆,马丁对当局农业报告和相关政策的了解,使得“他的羊毛售价比这一带任何人的都来得高”(《爱》:27)。所以他有能力将妹妹们送去上学,家里“有两间非常好的客厅”(《爱》:26)。奥斯丁的未尽之作《桑迪顿》中的西里尔(Mr. Hillier)是另一位具有现代农村经济特色的农民。他从租种帕克先生的大部分土地开始,步步经营努力生产,最终接管了帕克先生的祖宅。《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也提到了一些没有姓名的农民,他们对玛丽·克劳福德意欲雇手推车来运竖琴的想法嗤之以鼻。玛丽原本以为雇一辆手推车是给当地农民提供一个挣钱的机会,近乎一种半慈善的行为,因为她一直牢记着一条格言:“一切都可以用钱买到”(《曼》:55)。但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当地农民的“习惯竟然与它背道而驰”(《曼》:55),直接拒绝了玛丽高傲的“施舍”,维护了他们不同寻常的农民形象。这些农民的异乎寻常之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自主性和社会地位的变化”(Gilbert, 2008: 102)。在《理智与情感》中,颇有经济头脑的约翰·达什伍德先生对农村产业的投资就颇有心得,他深知这种投资即使短期转卖依然“可以有赚头”,于是就“买了一处小产业——东金汉农场”(《理》:219)。这也反映了新型农民对重商主义倾向的敏锐感知和对农村经济发展——尤其是投机性经营——的深入了解和高度自信。
除了那些能适应时代发展、抓住机遇获得成功的新型农民之外,还有一些只拥有小块土地、依然坚守传统农村经济模式的旧式农民存在。当扩大农田面积越来越成为时代潮流的时候,拥有小块土地的旧式农民的境遇就变得艰难起来, “小型农民正趋于灭绝,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也沦落成了教区贫民”(Stephen,1901:88)。自耕农尽管依然存在,但是“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数量繁多受人尊重了”(Dickson,1989:90)。奥斯丁在进行农村经济叙事时,已经关注到了英国传统农村经济正处于解体前的挣扎这一现实,她作品中思想落后的农民已经不见踪影了。农田的合并和圈地的进行就意味着农舍的减少。《劝导》中的墨斯格罗夫夫妇就在从前的一处农舍里住过,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又住进了更好的房舍。墨斯格罗夫太太的妹妹海特夫人因没有贵人相助,她的“子女几乎难以入流”(《劝》:79)。海特的家舍“既不美丽,也不庄严。一幢普通的、矮小的农舍,四周是谷仓和农场建筑物”(《劝》:91)。在小说里,海特夫妇并不属于佃户农民系列,他们在上克罗斯有250多英亩的土地,在汤顿还有一个农庄。尽管如此她们依然被处理成在财产上无足轻重、在社会地位上乏善可陈的模样,这至少表明像海特夫妇那样在农村经济高速发展、新型农民快速积累财富的进程中,已经沦为被抛弃群体的事实。
奈特利、马丁和西里尔等新型农民形象及他们在农村的经济活动,并非全部来自作者的凭空虚构,他们大多是有现实原型的。邻居蒂格伍德兄弟和哥哥爱德华及其在高德米尔舍姆(Godmersham)经营的农场都是奥斯丁取才的源泉。奥斯丁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小说所需要的农村经济再现精华,对其时代农村经济概况的描述具有于史有据式的呈现。
4.0 农村经济叙事的道德主题
奥斯丁笔下的农村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状态。传统农村经济日趋衰退,受重商主义影响的新型农村经济开始大行其道。在这种分化的社会经济中,以奈特利和马丁为代表的新型农民,抓住了时机开拓了产业,一跃成为农村资本的精明代表,也就是19世纪早期在身份上富有争议的农民形象——绅士农民。凯姆斯认为:“绅士农民就是一个像奈特利一样的人物,他在进行农业生产时获得知识、愉悦和锻炼,还不忘投身社交和其他一些绅士们所热衷的活动”(Kames,2009:16)。司各特笔下的伯特伦(Lewis Bertram)因为受困于经济压力而不得不屈身务农,在“他的职业被侵蚀后,他发现自降身份远离原先的社会已是当务之急,并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绅士农民”(Scott,2012:218)。
在绅士农民生活状况得到好转、地位得到提升的真实语境中,也不乏一些对此种巨变表示担忧的声音。有人担心绅士农民财富的过分增长,可能会摧毁社会阶层存在的根基。更有甚者谴责绅士农民,“让比他们优越的阶层担惊受怕,使比他们低下的阶层忍饥挨饿”(Stephen,1901:91)。绅士农民们跻身上流社会的诉求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常常成为被攻击的标靶。在财富和影响力上愈加有分量的绅士农民的出现,正在使传统上泾渭分明的关于农民和农村经济道德主题上的阶级界限趋于模糊。
面对社会上对新型农民身份及其价值观的质疑和诋毁,奥斯丁站在了绅士农民拥护者一边,并对农村经济进行了深层道德思考和观点阐发。在描述马丁一家经营的埃比磨坊农场时,奥斯丁以极富爱国主义的情调赞扬那里“景色美丽”,特别对“英国式的树木、英国式的农艺、英国式的舒适”情有独钟(《爱》:366)。这正应和了19世纪的农业作家辛克莱对绅士农民的欢迎态度。他认为英国绅士农民的体面和独立使他们卓绝于其他国家的农民,“大宗田地在富有的租户手里,是文化繁荣和仓廪充实的保障,是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物质堡垒和国家富强的真实基础”(Sinclair,2010:344)。奥斯丁以新型农民角色的演进和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来证实,绅士农民在农村经济的转型期是有资格走向历史前台与其他阶层分庭抗礼的。爱玛和奈特利对像马丁那样的新型农民进行评价时,选用的都是比较模糊的词语。在爱玛看来,马丁充其量是一个与她无关的“自耕农”(yeomanry),“一个地位低一二等而外貌看来还可靠的人”(《爱》:28)。在奈特利眼里,马丁是一个“既可敬又聪明的、绅士般的农民”(《爱》:63)。马丁在财富积累的路上始终是正直而稳健的,在成为绅士农民的品质过程中,也没有逾越规矩和受人诟病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丁身上所具备的绅士般农民的道德取向和价值判断都是无可挑剔的。
在爱玛和奈特利对马丁身份转型的争议上,体现了奥斯丁对农村经济所透射的道德主题的思考。奈特利认为他的租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绅士般的农民”,而爱玛则反对这种定位。奈特利在评判和定位马丁的身份时并没有考虑爱玛坚持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男性气概等道德取向,而是看到了马丁身上的婚姻适当性、社会责任感和个人教养。奈特利告诉爱玛,他“从没听到过有谁说话说得比马丁更加通情达理。他总是说得中肯、坦率,而且很有判断力”(《爱》:60)。他进一步指出,爱玛之所以诋毁马丁,那是因为她“爱那个小姑娘爱得入了迷”,从而“像瞎了眼似的”(《爱》:61)。当爱玛贬低马丁仅仅是一个有“头脑”有“优点”的庄稼汉、哈丽埃特“嫁给他会是贬低身份”时,奈特利再次以教养和见识为道德中心,对爱玛反唇相讥:“一个愚昧无知的私生女嫁一个既可敬又聪明的、绅士般的庄稼汉,算是贬低身份!”(《爱》:63)。奈特利褒奖马丁是一个“感情真挚”、“最不自负”的人。就马丁的品格来说,“他具有通情达理、为人诚恳、性格善良这些值得推荐的地方”,而且“他那真正高贵的心灵”是哈丽埃特难以企及的(《爱》:65)。
就像奈特利和马丁具有先进的思维、精明的头脑和科学的管理水平一样,绅士农民在农村经济叙事所包含的道德主题中也是正面形象。莱尔指出:“一个绅士农民,……通过率先垂范,以制止而非惩罚罪恶的形式,给社会谋更多福祉。在治理乡村事务时,他做出决断而不发牢骚,展示好恶而无怒气和诅咒,基于正义和平等做出精准的界限之分。……他们内心充满智慧和善意”(Lisle, 2010:11)。对莱尔来说,一个绅士农民就是乡村关注的对象,他的言行举止就是公众瞩目的焦点。以“毫无个人情绪的秀美与优雅”处理乡村事务,他们集实用性与审美性于一体。在奥斯丁的农村经济叙事中,绅士农民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道德主题建构的关键角色。通过典型绅士农民的塑造,奥斯丁表达了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理想农民形象的观瞻,并在道德主题构建上形成了驳斥贬抑新型农民的落后思想和赞赏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进步主义。
5.0 结语
农村经济叙事中的新型农民敢为天下先。在道德思想和身份意识上,他们兼具爱国主义情怀和骑士精神,顺应了从传统到更先进的经济变革,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心路变化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连续性(Duckworth,1971:156),他们才是奥斯丁心目中的理想绅士农民代表。在经历巨变的英国乡村,新型农民引领村民在变动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去感受和蜕变,去顺应农村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潮流,在重商主义的氛围里融人性光辉和绅士风度于一体。毋宁说这正是奥斯丁所期望建构的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道德主题。
利维斯指出,学界奥斯丁研究出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奥斯丁的作品被从其时代背景中剥离出来,而造成了数量庞大的新论脱离创作历史背景的局面(Leaves,1983)。而真正的文学研究要有历史的厚度,研究专门课题必须要梳理出它的历史(王卓,2016)。在讨论奥斯丁作品中农村经济叙事及道德主题透射时,既不能忽略当时的农村经济发展史,也不能无视作者一贯坚持的写实风格。奥斯丁对时代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巨变所作的精彩叙事和由此而作的道德主题再现,都再次验证了其作品中的历史意识和道德关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的每一部小说,都可以看作是对她所生活时代的社会素材的广泛扫视,其中就包含着对当时政治、经济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含蓄品评”(希尔兹,2014:4)。
注释:
本文引用奥斯丁的小说均采用缩写模式,即在正文中的引文后标出该小说名称的首字和页码。完整信息如下:
奥斯丁. 爱玛[M]. 祝庆英,祝文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奥斯丁. 曼斯菲尔德庄园[M]. 项星耀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奥斯丁. 理智与情感[M]. 武崇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奥斯丁. 劝导[M]. 裘因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