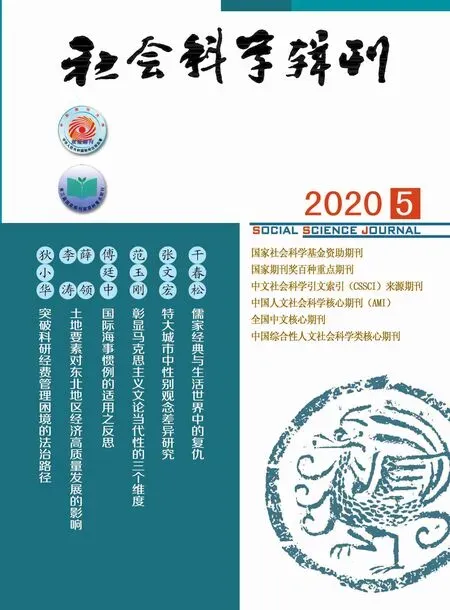事件的影像—剧场维度与历史主体经验建构
刘 阳
20世纪后期以来学术范式的醒目变化是逐渐从自明性走向建构性,将知识视为话语建构的事件 (Event)。事件,指正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丰富谱系的、以超越形而上学因果预设并重建创造性独异力量的新思想方法。迄今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哲学理论方面,对其中十分重要的影像—剧场维度的探讨相对薄弱,很需要我们来做这项深入开掘学理的工作。
事件的影像—剧场维度的奠基人可推至尼采。尽管亚里士多德也在 《诗学》中探讨了戏剧,并注意到了偶然发生的事件 〔1〕,但要求突转与发现必须以 “一系列按可然或必然的原则依次组织起来的事件为宜”,而 “不是得之于偶然的体积”〔2〕,这与他对求知作为人的天性的强调和知识论追求联系在一起。即使对于性格,他也认为是供我们判断行动者属类的。这些传统观念引发了尼采的反思。通过细致考察古希腊戏剧,尼采反拨了亚里士多德的戏剧观,指出 “戏剧” (drama)发源于 “对处于整体狂喜状态中的神性类型的当下观看”〔3〕,“发现”这个词的多立亚语来源进而证明了戏剧与事件在源头上的一体性 〔4〕,由此总结出了“戏剧这个词来源于多利亚人,按照多利亚人的用法,它表示古埃及僧侣语言中的 ‘事件’‘历史’二词的意思” 〔5〕的结论。作为现代思想先驱的尼采,由此直接影响了影像—剧场事件维度的正式起点——法国当代哲学家德勒兹。
一、起点:发自驱动影像的事件
德勒兹是事件思想在欧陆的一座重镇。他明确表示: “在我所有的书中,我都试图发现事件的性质”,因为 “我花了很多时间写关于这个事件的概念” 〔6〕。在 《意义的逻辑》中,他引入了“事件”概念,描述各种力的相互作用固有的瞬时产生〔7〕,指出“尼采的透视主义——他的透视主义——是一种比莱布尼兹的观点更深刻的艺术;因为分歧不再是排斥的原则,分离也不再是分离的手段” 〔8〕。他将动词视为语言的整体表征,赋予 “分离”以最高的肯定力量,以拓扑方式对事件进行图绘,认为动词不定式有助于开启线条的极限,“在这条线的极限处,事件出现了;而在这个不定式的统一性中所发生的事件,则以两个系列的振幅分布,而这两个系列的振幅构成了形而上学的表面。这个事件与这两个系列中的一个联系起来,作为一种无逻辑的属性,而与另一个联系起来,作为一种无逻辑的感觉”〔9〕,由点、线、面共同构成的这一系统,代表了意义的组织。紧紧抓住他在事件与意义逻辑的关系上的这一论述核心——因果的异质性及其在无限细分中形成的分歧性综合效应,便可以理解他对 “事件的独异性在普通点的直线上延伸时所形成的一系列集合”〔10〕的向往,从根本上首先看清他的事件思想。
这种事件思想也体现在他对电影的研究中。①对德勒兹事件思想的总体论述,囿于题旨与篇幅而暂不构成本文的任务,可详阅笔者即将出版的专著《事件思想史》第五章。我们可以借助汤姆·康利 (Tom Conley)1997年发表于 《耶鲁法国研究》的 《从影像到事件:通过德勒兹阅读日奈》这篇重要论文,并通过拓展性比较,来梳理德勒兹这方面的见解。让·日奈(Jean Genet,1910—1986)为当代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与荒诞派戏剧家,著述甚丰。通过观察其文学作品与电影影像的某种相似处,德勒兹深入探讨了事件与 “驱动影像” (drive-image)的渊源关系,深化了他的事件论架构。
康利引导人们注意德勒兹是在关键的哪一点上产生出对日奈及其作品的兴趣并进而为他所用的。他发现,日奈总结了图像中的物体停滞而产生的暴力,这启发了德勒兹思考电影如何改变绘画与小说的制作与接收方式。日奈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为依据,相信人们可以将图像理解为这样的一种方式,即当内容耗尽时会产生事件,这个事件,扩张性地通过一种意料之外的、不可预见的语言与可见性关系,激发了将身体散布到新空间并由此创造出新空间的感觉。始终保持为即时运动状态的图像,不呈现为静态,本质上从不对其表示的内容进行任何固定化的处理,而在散播能量中超出任何预先的时间框架,诱发出事件。电影从一开始就继承了这种摄影图像的运动传统。当运动耗尽自我后,它开始反思自己与时间的关系,逐渐发展出了基于影像特殊性的事件。
人们观看电影的过程,一般都被解释为跟着画面图像或者说影像走,很自然地不知不觉地陷入影像所展示的世界。德勒兹认为,这属于电影观看行为中的感官运动机制。如果说在1945年之前凭借这一机制观看电影已经是充分的,那么到了1945年后,即二战以后,受到战争以及德国灭绝营地的发现等因素的影响,观众的认知与电影的主题之间的联系正在削弱,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自治的甚至是流动的实体,其对电影的观看引入了包括但不限于感觉运动的认知机制,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行使小说或诗歌那样的阅读。对德勒兹而言,意大利新浪潮电影在这方面便具备充分的条件,可以通过一种无拘束的风格,更好地传达时代带给影像的危机,巴赞便通过重建影像事实来探究无名的、寻常的常规悲剧如何得到电影的速写。在德勒兹看来,战争的创伤感觉集中或散布在词句之中,后者被看成是阅读的东西,只有当它们被理解为 “驱动影像”时,它们才真实地记录了生活的混乱与历史的危机,从而拒绝将战争的历史轻易安顿在因果关系中。康利引述了德勒兹在 《电影1》一书第八章中对日奈的引用〔11〕,这一引用,展示了叙事性电影中感觉运动的计划如何以及在何处开始发生动摇,而逐渐导致在行程中的每一个点上电影影像都受到阅读的影响并与固有之物脱离。此时影像已变成了一个过滤器,而拒绝再将情感力与词汇形式区分开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驱动影像,是指在观影时以阅读介入影像,同时反思时间的连续性,它因而有别于连续式理解电影的传统做法。可以通过简要的对比看清这一点。电影是建立在特殊化学感光技术基础之上的摄影艺术,而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摄影又是一种造成主客观连续性的现代艺术,其决定性时刻作为时间相交的时刻,是观察到的场景的内部元素在主观上出现的、以图形方式结合的时刻,那个想象介入了的融合性时刻必然具备 “经验的连续性” 〔12〕,它通过时间的推拉去构成照片的事件,以及摄影的历史性语法。这种习惯性理解,导致电影研究者们在探讨电影时尽管认为电影制片人要利用影像事件来突破叙事,允诺影像事件违反日常期望从而增加观众对电影的参与度的反常规特征,相信对于不寻常的不平衡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独特转变的刻画会构成优质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强调事件提升到平凡水平之上而超越习惯时,他们每每只是从某种暂时性打断与变化的角度来描述影像事件作为一系列违反或增强电影节奏的镜头的一面,因而仍然容易从某种整体主义的立场出发,认定经过了这般处理后的电影 “产生了一种有节奏的结构,使电影叙事充满了连续性与生命力”〔13〕。节奏成全了结构的连续性。这与德勒兹的思路正好相反,后者向往的经由驱动影像发生出的节奏,是反连续性的,惟其不连续,才在虚拟化进程中具有了折返本体的变化性动力。
德勒兹认为,现代电影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驱动影像。在现代电影中人物与空间成倍增长,以往在叙述中获得决定性位置的事件,开始变得分散或无法识别,相机处于永无止境的运动中,并倾向于在记录方面获得自主权,这都导致了驱动影像作为电影的标志,去形成电影的新定位,即从感觉运动转向对残酷的时间真相的揭示。康利发现,这种揭示以及由此而来的风格,至少以两种方式导致了运动影像的崩溃。首先,对时间顺序的自然理解发生了熵变与退化,其目的是分裂历史的连续性。因为在一个自然主义的世界中,部分对象与暴力被固定在等待性的时间中,而这些等待性的时间却并没有发生出什么,没有任何记录可以构成历史。相反,驱动影像承认,在电影中散布着需要观众自身来承担的各种冲动。其次,驱动影像的视角还有助于感知相对于整体的细节,从而发生出大量事件,它们普遍存在并且扩散着,隐含于言语—图像的语法层次中,决定着一部电影的品质。德勒兹特别指出,驱动影像会产生一种性欲电荷,其顺序分散于文本上,引起人们对电影叙述者及其年代也即阅读与图像之间交换的眼动注意,这个过程实为一种广义的性欲驱动。
将驱动与性欲相联系,进而融合精神分析学说,是法国理论谈论事件的某种常态①如利奥塔1974年出版的《力比多经济》中引入弗洛伊德有关性欲能量的理论,特别是“死亡驱动”(death-drive)概念,见Geoffrey Bennington,Lyotard:Writing the Event,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p.17。朗西埃也以死亡驱动描述事件的原动力并直接使用了“死亡冲动”这个词,指出历史学家需中和“过度言说”与“主控内在于历史学术信念中死亡冲动之概念部署与叙事部署”。参见〔法〕雅克·朗西埃:《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魏德骥、杨淳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6页。,其当然受到了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深刻影响。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对一种对象的观看和接受,不是处在真空中的过程,而总是带有我们的立场与先决状态,这种状态进一步决定了我们的所见。比起稍后的话语政治学和反思社会学从话语权力来探讨这种先决状态的做法,精神分析直接将之与性欲联系起来,认为我们对戏剧的观看,不是在单纯进入一个作为概念性结果的对象,而是受性欲的驱动、调控而展开着观看它的过程。这在实质上和尼采攻击理性、发动非理性转向的初衷是一致的:理性的主要标志是知识与逻辑;人们之所以赋予知识与逻辑以力量与信任,是因为相信它们都旨在达成人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一致,而使人获得自我保存的安全感;理性对这种自我保存的安全感的追逐,这种趋利避害的动机,属于强力意志的生命冲动,因而是非理性的;理性从而源于非理性,是被非理性这个更具先决地位的根子派生和演化出来的。可以看出,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和那些从精神分析角度来阐说戏剧性的理论家比如利奥塔所说的性欲同属于非理性学理序列。如利奥塔所言,虽然概念性构成了我们在现实中看见的那座剧场,但任何概念都会降低性欲强度而带有否定性,这就需要推翻 “观看主体不证自明”这一点,而承认主体始终是欲望能量塑造的结果,尽管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又无法被自己所认识到: “如果剧场实际上是利比多能量的产物,那么,它对能量的明显反对也是能量本身的一部分。”①Geoffrey Bennington,Lyotard: Writing the Event,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p.25.举例来说,后理论者有鉴于理论发展至今的某种总体化趋向而提出走向“理论之后”,但对这一趋向的概括,显然又恰仍是总体化而为后理论者自己所未察觉的。比如语言,其在表达上诚然会受到各种方式的影响,根本的影响方式则是死亡驱力,那肇因于原初的性欲,正是它使我们在讲话之际已经处于话语系统中,无从挣脱而只能在无意识中接受其管辖。
可以从与传统观影方式的比较中确认这一点。传统的看法维系于观众的感觉运动,仿佛观众置身于任何驱动体系之外在单纯观看影像,但德勒兹提醒道,感觉运动的反应,是一种由微笑产生的心理形象在促使观众进行阅读的行动,驱动影像与观众伸出的手交换语言,并转变其视觉形式,使其在渴望中与自己汇合,并通过其凝视的混乱,引导其接受影像的吸引,此时这种吸引力不受意识形态的任何束缚,发出了一种类似于性欲的引诱。
电影意识便基于此。康利总结道,在日奈的话语中,电影影像引发了事件,这些事件驱散并耗尽了欲望而产生了文学光环,包括其色彩、言语乃至令人叹为观止的效果。影像事件由此比比皆是。康利特意指出,德勒兹在对电影的研究中引用日奈的 《小偷的日记》,暗示了日奈的作品是如何产生出超越电影传统框架的事件的。德勒兹基于电影哲学的这一事件理论因而具有颇为鲜明的时代生命力,影响了不少当代电影研究者。被作了上述分析的驱动影像事件论,其实质是要解决电影观看过程中影像引诱与阅读介入的关系问题,事件便产生于这种关系中。阅读介入,就是在事件对影像内外的驱动和贯穿中融合个体的主观经验与历史的客观进程,从而将主体建构为历史主体。德勒兹由此指出了事件思想谱系中一个可持续生长的重要方向。
二、推进:从不纯性到影像事件对恩典的穿透
醒目地推进德勒兹以上影像事件思想的,是当代法国理论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巴迪欧。他将事件看作一种存在本质的断裂,与这断裂时刻相伴,“无所不在,亘古如斯,难以瞥见”的真理从隐蔽状态中显露出来。〔14〕在此,事件被巴迪欧赋予绝对的超越性,人类在事件面前不具有主导地位。在德勒兹的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 “事件是连续性中的一种无法理解的断裂,是与存在的一种分离,是一种无根无据的杂多,从中新事物之创造得以涌现”〔15〕。与德勒兹带有显著后现代色彩的事件思想相比,巴迪欧有关事件的论说相对显得传统,是与哲学的真理性 “存在之所为存在”这样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16〕不过他不再从诗的隐喻角度去论述客观化问题,而试图从数学(哥德尔与科恩)的角度实现这种捍卫,认为柏拉图理念学说背后的深层支配力量是数,由此吸收康托尔集合论思想等现代资源,提出数学本体论并以之为事件思想的动力。
巴迪欧认为哲学不是一元化的存在,而是一种让思考变得可行,由 “真理程序”充当前提条件的集合,在 《存在与事件》这部充分使用数学方式来论述的著作中,他试图建立 “空”(数学上的空集)与 “存在之所为存在”之间的根本关联,将上述程序性集合分为四个前提——数元、诗、政治创造与爱,它们依次对应于科学真理、艺术真理、政治真理与爱的真理,而 “真理之源(origine)就是事件的秩序”〔17〕,它是当下的一种新的、例外的事物。事物的状态作为 “情势”(这是巴迪欧独创的术语,指所有展现出的多元),代表了任何样态之 “多”,在其中实现着事件对真理的补充。这意味着事件在遇到其额外状态时才使真理降临:“事件的本质是相对于它属于情势而言的不可确定性。”〔18〕“不可确定性是事件的理性属性,是对其非存在的救赎性保障。”〔19〕“这种不可确定性是事件内在固有的属性,它是从规定事件的多之形式的数元之中演绎而来的。”〔20〕早在出版于1985年的 《我们能思考政治吗》中,他已这样界定事件:“我所谓的事件就是大一机制的辨识定性留下了一个剩余,这个剩余让大一的机制失效了。事件不是预先给定的,因为大一的体制就是全部给定物的法则。事件也就是一种解释的产物。”①转引自蓝江:《忠实于事件本身:巴迪欧哲学思想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9页。事件的独特 “溢出”性决定着哲学的重构,在巴迪欧看来至少引发了三方面的积极后果:客体的毁灭;二的情形的颠倒;对不可认识之物的思考。第一点受到了拉康等思想家的影响,反思并克服那种让唯一的主体受益的客观性。第二点是巴迪欧着意强调的,二的情形让人想起各种传统辩证法,它们在根本上却是偶发性的,属于事件的衰退,进而使真理沦为可描述与命名的。第三点则与维特根斯坦有关在不能言说处保持沉默的观点决裂,保证了 “多的柏拉图主义”的实现。〔21〕存在、主体与真理,在事件的溢出中成为三位一体。
这提供了事件的影像维度的理论前提。在谈论电影时,巴迪欧也相应地涉及了事件问题,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他发表于1998年的一篇问答文章中,该文后被收入2010年出版的 《论电影》中,三年后即有了英译本。文章是从回答提问者有关巴迪欧自己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的经历切入的,这当然是一个事件,由此引出事件的话题。巴迪欧不回避有关的经历,坦承当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个人被某个事件抓住时,鉴于其新颖性,是很容易有一种不打算反对它的状态产生的。他认为这种经历对他探讨事件问题有刺激作用,自己事实上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关注事件问题:
事件概念的重要性主观上取决于我的经历。它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确,在上一时期,包括我在内的每个人都更倾向于结构性概念,而不是事件性概念。②Alain Badiou,Cinema,Cambridge: Polity,2013,pp.110-111.并可参看中译本〔法〕阿兰·巴迪欧:《论电影》,李洋、许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62页。
这里把事件与结构明确对立并举,显示出事件的反结构 (主义)、后结构 (主义)色彩。不过巴迪欧承认,身份的历史认知是复杂的,一个学者完全可能既是结构主义者,又是激进的某主义者,中间可以存在转变,拉康与阿尔都塞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前者反对美国的精神分析学,试图重返弗洛伊德,后者旨在更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它们却都同时得到了精神分析学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认同。巴迪欧挑明这点是想强调,电影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完全可能在电影中看到结构主义倾向与事件的并存,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破裂的肯定与对激进政治承诺的渴望。
这自然与巴迪欧对艺术的总体看法有关。他回忆道,早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时就常去影院并热衷于观看电影,从 《寂静的时代》开始,一批伟大的经典电影,是他终其一生的思想力量的一个来源,这股热情一直延续至新浪潮电影在法国兴起。虽然他从不以电影评论家自居,但在成为一位忠实的电影爱好者这点上毫不含糊,甚至还饶有兴味地提到了侯孝贤与王家卫等华语电影导演的作品。在他眼里,艺术是哲学的条件之一,为他的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使他始终对当代各种有关 “艺术的终结”的主题保持警惕。这细究起来又是由于艺术在塑造主观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能起一种浸渍作用,具有强大的潜意识功能,对欲望的一般结构具有独特的阐释能力。在这样的思考背景下,提到电影便是很自然的事。在回答提问者有关对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评价时,巴迪欧表示,自己与之渊源颇深,后者构成了他对政治秩序的哲学思考的一部分。因为新浪潮电影不同于传统电影,它与游荡心态以及游离某个既定领域的感觉有关,往往围绕着强烈的自我审问展开,而不像一般电影那样,习惯于通过既定角色来生发出世界,仍属于连续性与整体性作用下的结果,在其中事物的构造方式都是从整体着眼的。对包括新浪潮在内的电影的这种旨趣,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德勒兹。巴迪欧认为,德勒兹讨论电影的初衷是哲学,提出的相关问题完全是哲学上的,电影最终与时间和运动有关,是阐明这些关键问题的极其重要的领域,这种旨趣在某种程度上和自己是一样的。那么,巴迪欧从事件进一步谈及电影的理据何在呢?
他抓住了电影是不纯的这一点来谈,认为这门富于杂质的艺术,从杂质中既获得了优点也形成了缺点。优点在于,电影有能力吸收非常广泛甚至十分遥远的资源。缺点则在于,电影具有“潜在的折衷性” 〔22〕,即虽然可能在观看与接收的效果上很出色,在成分上却不免是琐碎的,比如依靠其它地方的东西,又使它们结合在一起,或给出某种暗示等。尤其是在今天,电影几乎已扩展至最大容量,在显示出绝对新颖性和富于原创性的同时,也常显得过于繁琐。巴迪欧援引安德烈·巴赞的一个说法——“事件即恩典”(event as grace) 〔23〕,来说明这种繁琐带给人们的恩典效应,指出长期以来,由于电影发展的上述状况,要获得恩典就必须生活在禁欲中,这个非常古老的想法实际上造就着观众里的穷人。但影院不应当成为穷人俱乐部,使影院变得贫穷的动因说到底都是人为的。巴迪欧尖锐地发问道: “这种想法作为恩典和通道仍然有效吗?这就是我要探究的。”〔24〕他对巴赞这一事件论的保留意见,可以结合前面德勒兹的驱动影像论来理解,即倘若囿于恩典性,电影会遭遇被动的无效接受。介入相当于德勒兹所说的阅读环节,才有助于打破恩典所预设的纯粹被动的参与特征;驱动性地穿透恩典,直击作为事件的电影,而那也就是历史。正如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所强调的那样,“每个重大事件都会在其内部生成自己的反对数据。这就是我目前正在尝试分析的内容。事件的主观产生一方面涉及保真度,另一方面涉及本身就是真正发明的反作用的创建。必须发明行动,但反应也必须发明”,这种不断进行着的反作用阅读,是在一个为影像所生发出来的审美世界中注入解码的热情,必然触及话语文化政治,而证明了 “将政治视为事件发生的条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25〕鉴于巴迪欧自己明确表示在这一点上他与德勒兹形成了共鸣,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符合其本意,能让人从中看到从德勒兹到巴迪欧的一条事件思想演进线索,它把电影与事件性思考贯合起来了。
这条线索由此也深刻阐明了一个道理:电影在时空形式上已逐渐走出现在进行时的框架,而被与主体对历史的当下真实经验深度联结起来,从银幕上走到观众席中,打破演戏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根本上说,这与美学精神的现代转型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再囿于化丑为美的、纯粹的趣味式审美鉴赏,而正视作为现实生活与历史的、非纯粹的、广义的丑。如果说其它艺术因自身悠久的历史,都较为显著地存在着这一美学转型,电影在这点上则相对具有轻松的优势,因为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完全是现代的。
三、延展:超戏剧事件及震惊美学
驱动性地介入影像并生成事件,这一被德勒兹与巴迪欧主要围绕电影艺术展开的角度,在更为晚近的今天也获得了剧场理论的响应。从戏剧角度深入研讨事件,乃事件思想的顺向进展方向。这种方向其实在20世纪初的残酷戏剧及其代表阿尔托那里已然有了萌芽。受到印度教宇宙论的影响,阿尔托认为戏剧舞台所要表现的是自然力量与强烈的宇宙冲突,每一场演出都不是在重复剧本的内容,而是一个基于精神性力量召唤的事件,其震撼性使 “当前事件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它使人们陷入某种精神沸腾的状态,即极度紧张的程度。事件不断地使我们处于有意识的混沌状态”,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残酷戏剧则 “正是为了使戏剧重建其炽烈而痉挛的生活观”〔26〕,它以代表宇宙固有残酷性的宗教仪式方式,在戏剧的上演过程中猛烈袭击观众,并迫使观众面对它,突破自身心灵上的戒备,而将自己暴露在被无意识所隐藏了的罪恶中。这触及了戏剧超出剧本、直指现实生活的震撼性力量,但仍着眼于戏剧活动本身的现代变革,没有直接切入思想史的用心。大半个世纪后,两位加拿大戏剧学者约瑟特·费拉与莱斯利·威克斯,于2011年发表 《从事件到极端现实:震惊美学》一文,探究了幻觉与无中介事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戏剧舞台上出现的一种特殊形式:暴力与极端场景的呈现。两位学者认为,这些场景将艺术尤其是戏剧艺术带出了戏剧框架,通过引出暴力的表演性行为以及与这种暴力面对面时所体验到的极端临场感,来创造出 “一个真实的事件” 〔27〕。他们从剧院、电影院以及视觉艺术与表演中选取例子,揭示了事件与这种震惊美学的关联:观众赤裸裸地面对暴力,面对凝视所进入的吸引力,让自身的动作获得与事件齐头并进的通透性,也使舞台突然失去幻觉性,改变其最初与观众的契约:
一个戏剧事件可能是戏剧幻觉被打断并且舞台由无需调解 (但并非没有框架)而出现的动作所塑造的那一刻,它从而留下了机会或风险的时刻。〔28〕
这样,在舞台上创建事件,能克服戏剧幻觉而引发一种即时的存在,消除故事的介导与演员的对话。两位学者指出,这种做法的指导思想是德里达与菲利普·拉库-拉巴特 (Philippe Lacoue-Labarthe)所广泛讨论的关于重新审查代表制的对话。两人接着强调,尽管舞台上出现了现实,但这并没有否定戏剧性,观众从未超越戏剧的框架,后者仍然存在并制约着事件的出现,正是这种框架赋予了事件以意义。这意味着在戏剧舞台上(无论是剧院场所还是公共场所),戏剧动作的执行性只能从戏剧性中读取,后者是戏剧美学维度的体现,观众在这种审美调解中吸收事件及其暴力。
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不在审美距离的拉开中变事件为艺术,而是藉此重读残酷现实的形象,避免将现实事件戏剧化、艺术化所必然带出的对这个主题的不屑态度。视事件的瞬间为艺术品,在两位学者看来是面对成千上万的死亡而保持沉默,是停留在强烈暴力的外面而变相羞辱受害者。唯有在事件超出戏剧表现形态的震惊层次上被激怒并唤醒自己的感官,才能脱离幻想、虚构与一度期望的艺术表现上的舒适感,而在遭遇戏剧事件中重新排列感官与知觉的框架。从广义上看,对事件的这种理解,是在试图走出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悲剧净化理论传统,而与20世纪不少学者的类似见解构成了互文。他们中肯地指出 “移情作用并非导致一种 ‘思想转移’,而是引起一种有意识活动或体验的虚假转移”,虚假就虚假在 “只要能够为你提供充分的线索,你便能以移情的方式来感知他人”〔29〕。即是说,移情的指向仍是发出着移情行为的主体单极,它是以主体单极的自我安全感为潜在前提的,类似于美学上起于原始人类祭祀活动的 “内模仿”行为,这种行为的性质“也存在于他与自己的动物猎取对象之间”〔30〕,因而仍未摆脱二元论色彩,其实质是 “我们直觉的第一反应,多半是在利用他人——即便出发点是为对方福祉着想。我们以扑向世界、人和事物的方式,来获得对事情的掌控,这种近乎动物性的直觉反应在我们内心根深蒂固”〔31〕。这样,移情就不仅 “不能构成审美态度的本质”〔32〕,而且极端言之,便不能不导致 “正是由于观众本身的绝对安全,他的严肃的人类关切会轻而易举地堕落为对恐怖和残忍毫无人性的欣赏”的消极后果。〔33〕对事件思想的这种理解始终仍在持续发展,这一点本身就表明人们对此的问题意识是相当重要的。几年后,在阿德里安·基尔等学者有关戏剧对历史主体经验的建构的细致阐释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更趋深入的回响。
四、深拓:在剧场事件中将当下历史化
超戏剧事件及其带出的震惊美学,是与历史的主体经验联系在一起的,震惊,就意味着主体在戏剧中经验到了自己所处的历史。英国学者阿德里安·基尔 (Adrian Kear)在2013年出版的 《剧场与事件:欧洲世纪的上演》一书,综合吸取了现象学和本雅明、巴迪欧与阿甘本等哲学家的思想,继续从戏剧的角度对事件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前沿阐释。这部著作旨在对选定的戏剧事件作详细的批判性描述,检审戏剧的特定配置,从而考察当代戏剧事件所处的历史形势,辨明戏剧事件的哲学与史学运作,而不是反过来将哲学或史学的框架强行加给它们。鉴于基尔的这一事件思想颇具有新颖之处,为读者查证方便,这里不妨引述浓缩了其事件论的核心表述:
本书采用的方法是在巴迪欧与阿甘本的阅读材料之间往返。通过研究当代欧洲戏剧制作人回顾与探询二十世纪事件的方式,它试图研究历史事件是如何使当代历史化的。因此,它试图将当代表演定位为一种特殊的政治与美学思想的史学模式的轨迹,使沃尔特·本雅明所描述的 “戏剧的伟大的古代机会——揭露现在”得以实现。……这本书旨在以探索的方式分析事件 (以及与其它事件相关的事件)对美学—政治 (aesthetic-politi-cal)建构的贡献。……这本书的目的是想探讨,对近期历史事件的批判性与创造性戏剧视角的构建,是如何使一种批判性与创造性的关系在当代政治中得到揭示和发展的。〔34〕
人们一般会认为,观看戏剧中上演的事件,是一个与现实生活发生间离的过程,此事件非彼事件。但基尔在本雅明等思想家的成果基础上试图破除这种常识性理解,而把对事件的理解引向更深处。固然,历史学家倾向于在取代原生态事件的事后操作中勾勒历史发展轨迹,拒绝叙事作为具象的思维方式介入历史并使之迷惑人,他们并且容易有一种支撑自己这样做的信念,即相信事件的意义随着事件的发生才逐渐清晰起来。基尔反对这种流俗之见,认为事件现在的样子与过去大不同,主张建构对 “当代历史的主体经验”(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5〕,或者说 “戏剧动态下的历史的主体经验”〔36〕,通过展示而非说的方式,在剧场内的戏剧事件的展示中使人们理解自己正处于其中的历史 (比如20世纪)事件。
基尔由此主动与德勒兹与巴迪欧这两位思想家对话。在1968年的访谈 《戏剧化的方法》中,德勒兹认为任何概念其实都不乏戏剧性,失去戏剧性动态,概念将无法在其物质体系中发挥作用,这与他有关 “一个概念应表达一个事件而不是本质”的著名观点前后相通。[1]Gilles Deleuze,Negotiations1972—199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25.并可参见 〔法〕 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9页。中译本此处译作:“概念应该说明事件,而非本质。”他以树为例说明这一点。这个概念不是简单记录一个事件,而是在替代性位置上起着建立新场所、诱发这棵树出现的作用,代表了一个过程性事件。将制造作为概念的来源,由此成为德勒兹的一种新发现。他与瓜塔里表示“哲学的伟大性是以其概念对事件本质的召唤来衡量的,或者它使我们能释放概念”(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i,What is Philosoph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34.),概念允许并在客观上产生出了思想与经验的变革时刻。巴迪欧则在 《世纪》等著作中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将戏剧从一种表演的思维转变为艺术本身,即主体的历史经验。观众在戏剧前如何不再充当旁观者,而随着情感创造事件本身,是上述对话的问题脉络的直接展开。
基尔引述巴迪欧对曼德尔斯塔姆诗作 《造物》的解读来说明这一旨趣。巴迪欧认为这首诗通过审美思维的操作,对时代进行着建构,建构出了一个有机的而非机械的世纪愿景,这展示了 “主体化”本身的一种矛盾过程。基尔引入阿甘本的分析来描述这一过程。他指出,继福柯之后,阿甘本确证了主体通过生物与幻影的无情斗争而创造出来,反对主体不去面对历史性,即不去感知与把握主体自己的时间,认为这将导致现存的历史主体假定自己作为政治代理人的存在,相反主张在文学作品比如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中窥见与“自己的时间”——即当代时间——相关的美学模式的潜质,这种模式在接近与间距、亲密与分离之间,维持一种视觉上的相互作用,从而在批判与创造的结合中有效地实现当下的历史化,开创性地产生出作为历史存在的政治主体化进程。另一位当代法国理论家朗西埃借助政治与美学工具进行的去主体化与再主体化研究及其沿此对“美学政治”工具与体制的重新配置,同样为基尔思考戏剧事件对历史主体经验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照。
具体地说,基尔指出,戏剧在美学领域中已扩展到了政治与历史的领域。结合阿甘本的有关阐释,基尔揭示了当代戏剧事件如何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凸显历史经验的现在空间。在他眼中,观看一幅风景画之际,人们往往得不断转移焦点,在接近与间距之间交替,而不把整幅画视为一个光学整体。这种变形性的中断作为视觉领域的一种干扰,由此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幅画赖以生产与运作的物质基础上,即创造出一种使观众能看到某些东西的方式,这些东西倘若失去中介的干预,就会流失于前者的视线之外。恰恰是它所没有或者说似乎存在的东西,才发生出了对历史的主体经验。基尔指出,在风景画中这种神秘的存在感通过表面上的不存在而变得明显,通过强化配置,图像汇聚不透明之处而营造出一种特殊的环境,无形的缺席感连接起戏剧与历史、审美与政治。他提醒道: “在我与卡迪根郡山脉的相遇之中,正是对这种关系的识别与建构,既暴露了绘画中历史内容的物质性,也暴露了它提供给当代历史性的情感框架。” 〔37〕这意味着剧场中呈现的场景,以一种看似延缓、迟钝的形式呈现出另一个场景,它们之间的联系,需要富有想象力的舞台表演与愿意参与审美的观众来共同创作。
这样,基尔通过对选择出来的特定戏剧作品及其表演实践比如 《悲伤的脸/快乐的脸》等的细致阐释,尝试将本雅明在 《摄影小史》一书中提及的 “微妙的经验主义”付诸实践,这种经验主义使批判性的情状与其对象密切联系在一起[1]基尔举出的这方面例证有:《伊莎贝拉的房间》展示了一个盲目的预言家从现有视角回顾她生活中的事件——一种经历了欧洲世纪事件的生活;《龙虾店》通过聚焦龙虾盘子被打翻这个单一事件,展示了现存空间崩溃为多个重叠的事件;《鹿屋》通过回顾亲历的自相残杀的暴行,反映了当代欧洲持续的巴尔干化局势;《索尼娅》展示了一张老照片,令人从中看到了包含在其中的历史索引如何使它在当下空间中迸发出生命,揭示出这两个时刻的意识形态偶然性;等等。Adrian Kear,Theatre and Event: Staging the European Centur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3,pp.219-220.,让当代戏剧事件在构成上成为一种直接或间接地接近20世纪欧洲历史的事件,从而实现存在与表现、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结合,历史性的主观经验也就形成于这种政治—美学的复合效应中。这是一种观看的政治,它成为理解主体与戏剧事件相遇并产生历史性经验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基尔重新探讨了 “表演史学”(performative historiography)的概念,明确赋予其双重内涵,即戏剧事件关联起一个本体论上不可决定、历史上则不可避免的事件,历史经验的主体性,就发生在作为现存事物暴露的剧场以及我们与历史共存的本体论暴露之间。由此,基尔将戏剧明确视作 “对事件的思考”〔38〕。他仍然结合巴迪欧的论述阐述道,剧场中的事件在中断中通过其发生的创新,引入了全新的可能性,它确实必须被理解为偶然性的,之所以不可预测和不确定,是由于它留下的痕迹的影响追溯性地构成着它。在此意义上,这一事件开启了对历史的一种主观的、主体化的关系,它以美学—政治行动为基础。戏剧作为思想的一种形式,促使思想以事件的形式政治化、历史化地运作,同时也作为一种美学事件而存在,基尔重申这 “虽然这是通过阅读哲学文本与戏剧文本来支持的,但始终关注的是通过戏剧事件本身的形式来检验事件的思想。……把戏剧作为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来考察,把戏剧的创造性政治作为一种 ‘实践的学科’来考察” 〔39〕,也即 “事件的本质是由感知行为 (act of perception)与主观干预(subjective intervention) 共同决定的” 〔40〕,这种性质使戏剧事件具备了创造性政治,人从中体验到了历史。
何以能如此?基尔吸收了现象学的思想,指出这是由于戏剧装置的设置产生了一种令人信服的感觉,即过去与现在、记忆与幻想、历史与戏剧性的相互决定以及最终的不确定性,都通过事件本身的主观效果,比如叙事的缺憾与时间形态的转变等起作用,这就使表演不断地向观众的参与性敞开大门,使之通过想象、联想与语境化的智性活动共同创造戏剧事件。他借用本雅明的分析,指出历史的隐意义唯有通过戏剧上演才能被连接出来,对戏剧的这个自觉操作过程,使观众同时占据了故事的时间与观看的时间,创建了一个分离地经历当下的历史奇异性过程: “这种戏剧隔阂的产生,试图调动表演者与表现对象的距离,使他们能采用一种类似于历史戏剧的 ‘立场’。这一手势的表演性——向观众延伸,使距离与亲密、接近与政治批判的情感相互作用加倍——促进了空间、时间与情境的拟态的实现,并开始使它们随后的重新配置成为可能。”〔41〕在这个过程中 “主体化的机制在政治与历史之间运作,将过去动员起来,形成一种与先驱者的表演关系,这种表演关系改变了所代表事件的性质,也改变了其在文化记忆中的形象。因此,巴迪欧提出的‘艺术可以且必须站在历史的立场上,对过去进行盘点,并提出新的感官形式的思想’似乎是在向聚集在这本书中的戏剧制作人发出召唤”〔42〕,这既确保事件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为主观效应,也最终形成了具备美学—政治形态的事件。它同时在方法论上规定了批判性与创造性相交错的积极劳动特征。“事件的发生,换句话说,构成历史存在的发生——存在暴露于事件中,它由历史构成。”〔43〕这一结论因而颇为耀眼地显示出了事件思想的历史感。
五、结语
从以上图绘可以看出,从德勒兹、巴迪欧对影像驱动生成事件的论述,到费拉、威克斯以及基尔关于剧场超越戏剧表演框架而折返现实、获得具备政治维度的事件并带出震惊美学的分析,整条运思脉络从影像—剧场的审美效应中及时引入政治关怀,兼容而统一看似对立的两极:主体经验与历史进程。换言之,为什么人能在历史的洪流挟裹下保持对历史的经验与历史现场本身的融入性一致,而不是相反满足于主体经验与历史进程在表面上所必然造就的时间性隔阂?这就是贯穿上述走向的问题意识。事件在这里对于两者的联结,与事件思想史上其他思想家的类似考虑产生了共鸣。因为如何确保对时间现象 (历史)的理解成为一种时间内现象,进而使时间的主观化成为可能,这是事件研究中始终绕不过去的关键。既然从原则上看,一个事件本身就是它所能发生的可能性条件,它产生的架构应该是已取消了所有的先决条件,“事件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尺度和条件”〔44〕,那么,面对影像与剧场,我们的任何试图将它们作为事件来把握的努力,都必然蕴含着打破观看它们的装置结构方式的要求,而逐渐走向历史与主体经验的融会,也就是历史主体经验的建构。伴随全球化进程,它同样有理由构成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理据,以及我国当今大众影像—剧场文化得以创新发展的一个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