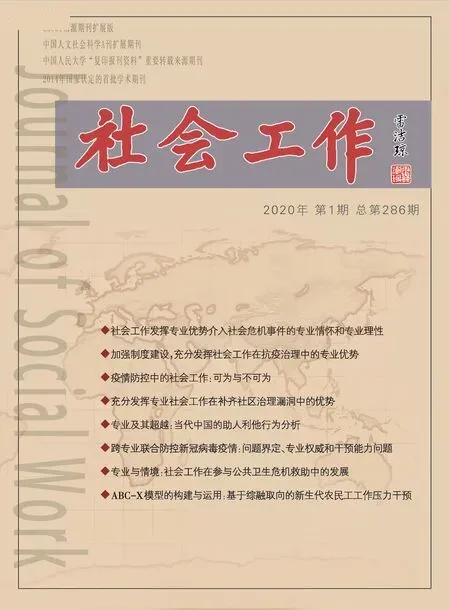文化生产与预防欺凌:基于一个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案例研究
杨梨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校园欺凌问题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6年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多项防治校园欺凌的政策文件,要求学校、家庭和社会组织等加强防治校园欺凌,保障学生健康和校园安全。校园欺凌受到学生个体、同伴群体、学校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规范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因此,针对个人、班级、学校等多层面因素开展整合性欺凌预防和干预被认为是有效的欺凌服务措施(Cross et al.,2011;Richard,Schneider,&Mallet,2011)。具体来看,这些欺凌防治措施包括:个体视角将欺凌看作是个体之间的人际交往问题,预防欺凌主要采取对策让欺凌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被欺凌者学习应对技能(杨婕、马焕灵,2017);群体视角将校园欺凌归结为“病态”的群体互动,主要采取措施改变支持欺凌的群体规范和培养积极的旁观者(周华珍、何子丹,2009)。社会结构-文化视角主张社会规范与制度才是校园欺凌问题的症结所在,预防欺凌的重点在于改变社会不平等、竞争权力等社会文化(德伯、马格拉斯,2017:267-270)。然而,既有研究要么将卷入校园欺凌事件的学生们看作是消极的个体,要么过于关注导致校园欺凌的社会环境因素,却较少从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同伴群体文化内在逻辑方面去寻找防治欺凌的对策。
已有校园欺凌的社会工作服务往往把学生作为被服务对象,学生的能动性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学生们生产欺凌的群体文化机制被忽视。既有的大多数社会工作服务以校园欺凌问题化视角为介入点,以改变欺凌者的消极行为,帮助无助的被欺凌者为服务目标,一方面从宏观上着眼于改造社会环境系统,构建“家庭—学校—社区”三方互动的预防校园欺凌体系等(朱琳、齐华栋、梅芸芸,2017);另一方面从微观上旨在帮助校园欺凌当事人解决问题,比如被欺凌者的园艺治疗小组(黄丹、林少妆,2018),卷入欺凌学生的个案辅导(闫智楠,2018)。已有社会工作服务研究和实践都太急于体现专业服务解决问题的功效,采取先入为主的“问题视角”,反而难以维持长久的预防欺凌效果。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倾向于教导学生理解欺凌知识、学习欺凌应对技能,试图对卷入欺凌的学生进行行为矫正、观念疏导,学生没有机会发出他们的声音,就很难知道他们如何理解欺凌,如何生成支持欺凌或冷漠旁观欺凌的群体文化。这样的服务阻碍社会工作者真正理解孕育学生欺凌行为的群体文化,很难保证社会工作服务撤离之后学生仍然会自觉保持反对欺凌的行为。
校园欺凌群体互动视角的相关研究强调同伴群体文化是欺凌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土壤。欺凌是不同角色之间群体互动的动态过程(Salmivalli,2010)。校园欺凌根植于同伴群体所建构和认同的校园文化之中,与此同时,欺凌成为传播同伴文化的一种方式。英国社会学家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描述工人阶级出生的“小子们”欺负“书呆子”来获得优越感,欺凌成为“小子们”在校园里寻求乐趣、保存自尊的一种“生活方式”(威利斯,2013:13-23)。因而,要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前提是深入理解滋生欺凌的群体文化。
“文化生产”理论可以为理解这一群体文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社会工作服务指明实践方向。威利斯提出的“文化生产”是洞察学校生活的重要理论工具,它更是一种分析学生群体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丁百仁、王毅杰,2017)。“文化层面也有生产过程,即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它体现为社会行动者通过斗争、竞争以及对社会结构的部分洞察,积极地开展“意义创造”的过程(威利斯,2013:2-3)。文化生产关注行动者在结构中创造意义的过程,强调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熊春文、丁键,2019;秘舒、苏春艳,2016)。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应用“文化生产”研究范式,基于对农民工子弟、底层青年、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等儿童等开展田野研究,分析他们的抵制行为、群体亚文化和反学校文化,倡导以文化生产为核心,正面描述和理解儿童能动建构的意义系统,从而实现一种积极的儿童群体文化研究范式(熊春文、丁键,2019;秘舒、苏春艳,2016;程猛、陈娴,2016)。实践层面上,有学者提出了流动儿童服务需要关注儿童主体性的回归,注重儿童赋权方法,尊重流动儿童原有文化、发掘其文化动力,从而影响儿童的知识生产、重建自我身份和社会关系(秘舒,2016;刘玉兰、彭华民,2014)。这些研究对于当前创新校园欺凌的社会工作服务具有积极的启示。
沿着文化生产的视角,本文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是:预防欺凌的社会工作服务是否可以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开展相关实践?社会工作者如何运用文化生产视角理解学生群体的欺凌文化?社会工作服务又怎样借助文化生产过程来开展预防欺凌实践?本文以C市某社会工作机构的预防儿童欺凌服务项目为案例,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期为开发有效的预防欺凌社会工作服务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达成一项基本共识,即校园欺凌是一个群体过程(group process)。日本社会学者森田洋司(2017:150-153)提出校园欺凌的定义:在学校学生群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处于优势的一方,刻意地或者群体造成他人精神上、身体上的苦痛。可见,欺凌行为存在于群体互动过程中。只有将校园欺凌行为置于同伴群体背景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个人欺凌他人的动机,旁观者很少支持被欺凌者的原因,欺凌不断发生并持续的机制等。
欺凌者采取欺凌行为的动机是为了追求同伴群体中的地位、权力,或者同伴群体的身份认同。学生在同伴群体中通过欺凌等竞争行为建立支配与被支配的等级地位关系(Adams,Bartlett,&Bukowsdki,2010)。Milner(2016:97—103)运用地位关系理论呈现美国学生群体的地位分化,那些衣着潮流、外表出众、有性吸引力,家庭背景好及运动能力强的学生更可能成为校园“风云人物”,他们经常采取捉弄、轻蔑对待、贬低、排挤、嘲笑、羞辱和拒绝弱者、传播流言蜚语等欺凌行为来获得及维护自己的地位。在群体互动过程中,被标签为“不合群”“不一样”的同学更有可能遭遇欺凌(Thornberg,2015)。欺凌者的行为往往被群体默许,其他人往往将欺凌行为归因于“被欺凌者的错”(Tershjo&Salmivalli,2003)。被欺凌往往意味着“不酷”,被欺凌者在群体中处于弱势地位(Graham&Juvonen,2002),其他学生往往表现出对被欺凌者的不友好或不关心,以此获得群体认同(Garandeau&Cillessen,2006)。在同伴群体生产的欺凌文化中,欺凌行为被看作是群体互动中的炫酷行为。
旁观者角色对校园欺凌事件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而针对旁观者的预防和干预服务成为很重要的内容。校园欺凌中包含了多种角色,除了欺凌者与被欺凌者,还有众多的旁观者。Salmivalli等(1996)对芬兰573名11—13岁的学生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学生(87%)在欺凌事件中扮演着旁观者角色,这些旁观者包括:跟随欺凌者参与欺凌的协助者(assistants);给欺凌者鼓励信息的强化者(reinforcers);支持和帮助被欺凌者的保护者(defenders);漠视欺凌行为的局外人(outsiders)。即便学生知道出手帮助被欺凌者是对的,但很少有学生愿意成为被欺凌者的保护者,却有不少人成为欺凌的协助者或强化者,这样欺凌行为得到鼓励,很可能继续维持,甚至升级为更严重的欺凌(Beasley,2015)。学生是根据参与欺凌的人是谁,我和欺凌当事人的关系等情境做出的欺凌角色选择的(Forsberg,et al.,2018)。不过,他们可能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行为对欺凌发展方向的影响力,而仅仅希望自己在同龄人眼中显得很“酷”,在同伴群体中更受欢迎或获得更高地位(Strindberg,Horton,&Thornberg,2019)。已有的欺凌预防和干预项目聚焦于让学生懂得自己的做法对欺凌事件的影响,鼓励和指导学生成为能够真正帮助被欺凌者的积极旁观者(Salmivalli,2014)。但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触及同伴群体的亚文化,因而很难真正改变学生欺凌角色选择的行动逻辑。
目前来看,已有研究对同伴群体文化如何生产出欺凌行为这一过程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尚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欺凌会被视为“酷”,甚至在同伴文化中很受欢迎,因为同伴群体层面的欺凌过程还没有解开生产欺凌行为的同伴群体文化提供有意义的分析工具。威利斯非常重视工人阶级子弟充满“洞察”的文化生产过程,他通过深入地描述行动者的“洞察”来阐释“他们在结构中创造意义的过程”(吕鹏,2006)。这一“文化生产”过程涉及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意义生产(meaning making)、自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生产(程猛,2017):首先,文化世界是充满了意义创造的过程,社会能动者的意义创造过程生产出文化的特性(威利斯,2013:2)。意义生产的核心体现在人们对于符号所附加的内隐或外显的意义与价值。其次,在不断生产符号和意义的同时,也生产出了自我。威利斯提出文化生产实践本质上也是为了制造身份和建构自我,因而文化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自我生产。最后,文化生产本质上是生产一种生活方式,在日常行为和琐事中都包含着人们内隐的一种意向,文化生产的意义和价值外化于可见的生活方式,体现于日常行为。这三个层面的文化生产将为校园欺凌干预实践提供参考。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同伴群体的文化生产过程有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学者们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细致地描述群体文化生产过程,总结底层儿童或青少年的群体文化与威利斯笔下工人阶级的小子们之间的“形似而质异”(周潇,2011);他们采取的是“缺乏反文化的抵抗”(Ling,2015);他们只在微观层面抵抗学校日常教育实践及其意义系统,却没能抵抗宏观层面的阶级关系和文化霸权等社会再生产,是一种“片面抵抗”(李淼、熊易寒,2017)。有的研究总结农民工子女同伴群体“混日子”背后体现出“义”的双重涵义,即平等的义气伦理和不平等的差序体验,并最终形成影响他们行动的一套“意义—规则—行动”系统(熊春文、史晓晰、王毅,2013;熊春文、王毅、折曦,2014)。这些研究对理解同伴群体的“文化生产”下的意义生产、身份建构和生活方式形成有着重要启示,也为开展校园欺凌防治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解视角。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本文以C市YS社会工作机构的预防儿童欺凌服务项目为案例,采用穿梭式行动研究深入项目服务过程,展现文化生产这一理论指导下预防欺凌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过程(任敏、吴世友,2018)。笔者以服务者(研究者/督导者)的身份穿梭于实务、研究与评估3个情境之中,力图实现多重角色相互促进,在反思中探索理论视角与实践服务相结合的预防欺凌社会工作服务内容优化和效果改进。从2018年10月到2019年10月,在C市儿童救助基金会的资助下,本研究团队和YS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合作在重庆某公租房配套的X小学共同开展预防儿童欺凌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项目所服务的学校为公租房区域配套的新办小学,学生合计约500余人,学生以流动儿童为主,他们多来自低收入家庭,大部分学生的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家庭往往经济状况及社会地位低,且多从区县或其他省份流动到C市城区,还面临方言和地方文化的融入等问题,这些因素增加了校园欺凌风险。
在提供服务之前,项目组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对X小学的校园欺凌状况和服务需求开展了调研,掌握了项目所服务学校的欺凌总体状况、学生对校园欺凌认知、态度、应对效能及已经开展过的校园欺凌服务等情况。项目基于儿童为中心以及文化生产的理念,试图创新预防欺凌社会工作服务内容和方法,推动学生主动参与到预防欺凌的行列中来,提升其欺凌认知,促进积极旁观和传播善意的同伴群体文化生产,进而预防欺凌。项目的服务内容包含了3个方面:第一,覆盖所有小学生的预防欺凌课程,旨在让学生真正理解欺凌,形成正确的欺凌认知;第二,发掘和培育优秀同伴教育者的小组活动,希望由参加了同伴教育小组的同学去辐射其他同学,影响同伴群体文化朝着鼓励同伴争做积极的旁观者方向发展;第三,开展学校社区活动,为学生提供平台和机会,感受和体验欺凌,调动学生参与预防欺凌的主动性,形成友爱相处的校园氛围。
项目团队由专职社会工作者、小学教师、社会工作专业大学生和专业教师等组成,并采用穿梭式行动研究方法不断优化项目服务内容。社会工作服务采取讨论、体验、戏剧等参与式方法,以鼓励学生参与其中,充分调动他们的能动性。项目设计、实施和评估过程中,高校社会工作教师、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充分沟通,致力于破除研究者的理论权力,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权力,服务对象的消极抵抗权力,充分给予各方表达的权利,并借助“文化是生产出来的”这一触发机制,引起多方共同参与反思实践、优化服务(任敏、吴世友,2018)。实际上,目前国内预防欺凌的社会工作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项目团队在开始服务之初也并没有成熟的服务方案。笔者是该项目的研究者和评估者之一,凭借对已有校园欺凌理论的理解,确定了“文化生产”取向对预防欺凌服务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并尝试将意义生产、自我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这3个方面的文化生产内容贯穿于预防欺凌的社会工作服务之中,但具体的服务方案则是在不断反思中调整的结果。研究资料包括了该项目的所有服务过程记录与管理资料,社会工作者、种子老师、志愿者的工作记录、工作会议记录、总结报告等材料,同时还包括研究者对服务过程的参与观察、与服务对象的闲谈、服务效果评估数据和对整个过程资料的总结等。整个研究过程都遵照知情同意、信息保密等研究伦理,文中涉及的机构、人员等均采用匿名。
四、意义生产与欺凌认知生成
学生理解什么是欺凌是改变校园欺凌文化的第一步。项目组针对项目所服务学校学生的基线调查发现,学生对欺凌行为的认知比较模糊,这导致他们很难准确判断某类行为是否属于欺凌。对于“同学嘲笑说话有口音的小刚”、“给同学起难听的绰号”等行为,65%和62.1%的同学认为它们属于欺凌,但也有26.7%和24.8%的学生认为这不属于欺凌,还有8.3%和13.1%的学生不知道其是否属于欺凌。针对“把同学的‘丑照’发到网上”这一行为,有15.5%的学生认为这不是欺凌,还有7.3%的学生不知道这是否属于欺凌。对于“鼓动同学不跟穿着‘土’的同学玩”这一现象,22.8%的学生认为这不是一种欺凌行为,13.6%的学生不知道这一行为是否属于欺凌。不过学生为何如此理解这些行为?他们对于欺凌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呢?回答以上问题是开展有效的欺凌认知教育的前提。为此,项目团队并未着急开展预防欺凌教育,而是先深入学生群体,了解他们的想法。
项目团队志愿者WJ在访谈学生时,了解到这样一个案例:
有一个女生,身材偏胖,她被同学取绰号“蒙牛”,她觉得这个绰号对女孩子来说很刺耳、很难听,被同学叫这样的绰号,让她感到很羞耻。最开始只是一些男同学会这样叫她,后来她的朋友也会跟着这样叫她,其他的同学要么跟着这样叫她,要么就只是听着。她感觉非常崩溃,却又不愿意求助。她说:“大家可能都觉得只是一个绰号而已,不至于这么较真吧。”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类案例,项目团队通过入班闲聊的方式了解同伴群体对于“绰号”的意义生产过程。有同学表示“绰号就是大家叫着玩的”“觉得好玩而已”“同学之间开玩笑”……从类似的案例中,项目团队发现同伴群体赋予“取绰号”的意义是“开玩笑”,即便被取绰号的人认为这个绰号难听或无法接受,也不能说出来,因为说出来就表明这个人“开不起玩笑”,而这很容易导致其他同伴认为这样的人“不合群”“太较真”。在同伴互动过程中,“取绰号”“嘲笑”或“排挤”他人的同学在同伴群体中被视为幽默的、会开玩笑的、受欢迎的人,大家跟这类同学玩,附和他们的行为,以此结交朋友;而因为害怕被认为“不合群”,欺凌的同学选择默默承受;为了防止被拉入“不合群”的小圈子,旁观的同学则否认欺凌的存在。
基于“文化生产”的视角,提升学生对欺凌的认知能力并不仅仅意味着增加他们有关欺凌的知识,还需要与同伴群体一起生成正确的“欺凌意义”。为此,预防欺凌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确定了预防欺凌课程的授课内容和方式,试图通过课程促进同伴群体的交流,反思群体的某些意义生产过程,从而回应目前学生们界定欺凌存在的误区。预防欺凌课程并没有直接给出欺凌的定义,而是先给出案例,然后小组讨论,鼓励大家说出自己的观点,然后逐渐形成对欺凌的共识。本文以课程对于“取难听的绰号是否属于欺凌”这一问题的辨析为例,来说明项目服务如何运用同伴群体的“意义生产”过程来促进学生们对欺凌的认知。
项目组提供关于“取难听的绰号”的案例开展小组讨论。大家在讨论中出现了分歧,否认它是欺凌的一方提出这只是开玩笑,小事而已,不至于上升到欺凌的高度;认同这是欺凌的一方则表示谁都不愿意接受难听的绰号,不过是碍于同学情面,不好意思强烈反对。在对话中,他们发现,大家误以为同学不在意被叫绰号,开着他们以为的“玩笑”,而实际上这个同学可能非常难受,只是在这样的群体氛围中,他(她)不好表达自己的感受。课程老师总结双方观点后,澄清双方存在分歧的关键在于大家对于“绰号”的意义理解存在差异。判断某类行为是否属于欺凌,要看这一行为背后的意义,比如“取绰号”的动机(开玩笑或伤害他人),拒绝“被取绰号”的涵义(开不起玩笑或表达感受)。当学生群体赋予“取难听的绰号”是玩笑的意义,并认为拒绝接受“绰号”是“开不起玩笑”的表现时,“取难听的绰号”得以持续,从而演变成欺凌;反之,当学生群体认为“取难听的绰号”意味着伤害他人的自尊心,并鼓励和接纳被取绰号的一方表达负面感受的时候,偶然一次的“取难听的绰号”行为在同伴群体里会很快消失,欺凌也便消失于无形。这样,便引出了欺凌定义:“一方重复地遭受另一方的负面攻击行为,这一行为造成他人身体、心理伤害或困扰,可是对方却无力自我保护。”它包含3个重要要素:造成负面影响,重复发生和遭受欺凌的人处于弱势地位(Olweus,2013)。
项目从群体文化生产的角度,开发和推行预防欺凌的课程,从而实现提升学生欺凌认知,改变不利于欺凌预防的同伴群体生产的“欺凌意义”,形成新的欺凌共识。这是预防欺凌社会工作服务深入影响同伴群体互动过程以达成服务目标的积极尝试。当然,由于服务对象所处同伴群体的差异和项目执行周期短等原因,这一“意义生产”的良好运行并不是总是有效。仅仅依靠几次课程,还很难彻底改变同伴群体已经建构起来的某些欺凌意义,未来需要探讨更加持续地影响同伴群体欺凌意义生产过程的相关服务。
五、自我生产与欺凌角色选择
培育积极的旁观者是欺凌预防和干预的重点环节。项目组的需求评估调查表明,学生在面临校园欺凌中的旁观者角色选择时,有61.2%的学生表示自己肯定会帮助被欺负的人(保护者),但也有31.1%的学生会参与起哄(强化者),另有23.8%的同学会跟着参与欺负他人(协助者)。尽管学生选择成为保护者比例较高,但学生在面对欺凌行为时的实际行动与预期行为之间很可能存在差距。学者胡芳芳和桑青松(2011)的研究表明学生对受欺负者表示出更多的同情,但实际去采取行动帮助受欺负者的同学较少。预防和干预欺凌服务需要注意对学生欺凌角色选择的行为引导。
根据需求评估结果,项目组在设计项目框架时便确定了培养积极旁观者这一目标。项目在预防欺凌课程中设置了“做积极的旁观者”相关教学内容,通过学生角色扮演,练习积极应对欺凌的方法;通过观看欺凌实验视频,引导学生讨论和学习帮助被欺凌者的行为,提升大家帮助被欺凌者的意识,并让学生学会旁观欺凌时采取积极支持的行为。在课堂教学后,评估者在与同学聊天中发现,学生们虽然认同课堂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但却表示如果真的要自己面对欺凌时,不起哄,还要“出手相助”,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样的行为不符合自己在同伴群体中的自我定位,还可能让自己丧失朋友。可见,旁观者角色选择行为显然受到学生在同伴群体中建构的自我身份和群体规范的影响。
于是,项目团队希望与学生一起,寻找真正能够让学生实现积极旁观者的自我身份建构的社会工作服务路径。项目组通过聊天、观察等方式了解不同类型的学生如何在同伴群体互动中建立和维持自己的形象,理解和运用群体文化中的自我生产过程,为开展相关服务提供重要依据。
以下是一个同学与社会工作者聊天的时候提到他们班上的欺凌案例:
有一群学生在班里比较厉害,总是去找王贺的麻烦,比如从背后敲一敲他的背,然后突然跑开,其他同学就会在这个同学回头的时候哈哈大笑;过一会儿,他们又会继续,比如拿走他的书藏起来,或者是嘲笑他今天穿得衣服很奇怪……他们经常找各种方法去捉弄王贺。那天他们约着放学一起出去玩,李栋也想去,他们要求李栋想一个新招儿来整蛊王贺,如果大家都觉得他这个方法好,那么他就可以放学后跟他们一起玩。李栋同意了,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给王贺的衣服上偷偷贴上画了乌龟图案的小纸条……从那以后,李栋就加入了欺凌王贺的这个小群体。(案例中王贺、李栋均为化名)
一个人没办法制造乐趣、氛围以及社会身份,要融入某个圈子,就要认同这个圈子的文化,与群体内其他人打成一片(威利斯,2013:30)。如果在一个群体里欺凌意味着正式进入某个同伴群体,自我身份得到承认或维持,那么它便意味着即便欺凌行为是错的,希望融入或已身处这个群体的人也要跟着加入,拒绝参与这些行为只会让你损失成员身份(威利斯,2013:47)。有的同学可能并不认同这样的同伴群体文化,但他们为了融入同伴群体、获得朋友的认同,仍然会运用同伴群体所创造的欺凌文化,选择扮演“强化者”或“协助者”的角色;而另外一些跟王贺一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同学,面对强势同伴群体的欺凌,“敬而远之”“莫管闲事”是他们最大化自我利益的选择。可见,同伴群体文化下“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是影响同学面临欺凌时的角色选择的关键。
基于此,项目组决定采取青少年影响青少年的同伴教育小组,寻找关键人物深度参与预防欺凌,让他们引领其他同伴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达到预防欺凌的目的。同伴教育者是同伴教育小组的关键人物,对小组是否能达成引领良好同伴关系、预防欺凌的目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社会工作者首要的工作是招募合适的同伴教育者,社会工作者发现前述案例中同伴群体中的领头人物对参与反欺凌的同伴教育小组有着一种排斥心理,而那些扮演“强化者”或“协助者”的角色的学生在同伴群体中比较受欢迎,且他们往往扮演着消极旁观者的角色。社会工作者决定同伴教育小组定位于培育他们为积极旁观者,因为他们的行为转变将显著改变旁观者的角色分布。小组基于理解同伴教育者的自我身份生产而展开,社会工作者首先着手于充分了解组员的经历。他们表示希望自己学习进步,也曾努力好好学习,但仍然面临巨大的学习困难,干脆选择加入“以玩为主”的同伴群体。他们跟许多农民工子弟一样,在社会结构劣势和自我主动适应失败后,最终选择“自我放弃”,转而投奔“混日子”的同伴群体(丁百仁、王毅杰,2017),最终形成“我属于欺凌者群体”这一自我身份建构。因而,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同伴教育小组活动过程中,重点是鼓励他们,增强他们的自信,让他们相信只要有目标,他们也能够成长为同伴的榜样。同伴教育小组共设计和实施了5节,主题分别是“我们一起防欺凌”“身边的欺凌”“榜样的力量”“小卫士在行动”和“分享联欢会”。
小组结束后,这些同伴教育者逐渐感受到自己的成长潜力和在同伴中的影响力,逐渐改变了“自我形象”,成长为掌握校园欺凌专业知识和预防欺凌技巧的积极旁观者。他们在参与小组活动中,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和推动着更多的同学参与预防欺凌,积极主动的改变促使他们收获更多的友谊。针对“协助者”和“强化者”的同伴教育小组成功地扭转局外人的消极围观对欺凌行为的“升级效应”(柯斯林,2016:171-172)。在缺乏助威者和响应者的情况下,欺凌者难以通过欺凌获得成就感,这也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欺凌的发生。
不过,同伴教育小组的辐射范围有限,且学生的自我生产受制于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多种因素,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组服务的影响范围和效果稳定性。另外,尽管社会工作者积极支持同伴教育者,让他们能够在活动中体会自己成长为榜样的力量,重新定位自我身份,但是自我生产更多受到同伴群体文化的影响,小组结束后,如果同伴教育者的学业不见起色,改变自我身份遇到困难,他们是否重回原来的同伴群体?他们是否有可能面临过去群体的不接纳,而新群体又难以进入的尴尬境地?未来项目服务需要持续支持同伴教育者的自我生产转变,并联合学校和家庭等外部环境,为他们的身份转变寻找可获得的社会支持,这样才能培养出持续、稳定的积极旁观者。
六、生活方式生产与友好和谐相处
从同伴群体生活方式的内在逻辑出发,将有助于探索预防欺凌的根本路径。欺凌作为学生采取的一类外显行为,其背后可能深藏着学生们内化的、习以为常的群体规范和生活方式。同伴群体生产的生活方式对欺凌行为有着根本性的影响。项目组在开展服务过程中,通过观察和访谈,逐渐了解到一些被群体生活方式“隐藏”的欺凌现象。
当社会工作者看到孤单身影的雅妮,脑海里总是萦绕着她告诉社工的这句话“我在班里没有朋友。”雅妮从C市偏远山区农村转学来X校,她很懂事,老师说她上课很认真,成绩也还可以,就是比较内向,好像跟同学交往比较少。社会工作者私底下找雅妮聊天,她告诉社会工作者她觉得现在班上的同学和家乡的不一样,她很难跟同学们有共同话题。班级里有同学告诉社会工作者,大家觉得雅妮比较“土”,平时总是穿得破破旧旧的,放学路上大家都偶尔买点小零食,交换着吃,她从来也不买;体育课大家都穿运动鞋,她老是穿着同一双布鞋,所以大家就觉得很难跟她做朋友,有的同学还会在背后说她“老土”“抠门”……
社会工作者注意到陈辉,是一次预防欺凌的课堂上,玩“串名字”游戏,当同学提到他的名字,他们的表情显得很别扭,其他同学发出哄笑,当陈辉提到其他人名字的时候,同学又会露出一副不太喜欢他的表情。老师告诉社会工作者陈辉平时话少,说话声音很小,一般不会主动回答问题,成绩也不太好。社会工作者私底下问了班上的几位同学,为什么大家跟陈辉的关系会是这样?他们的说法基本一致:“他特别不讲卫生”,“他身上有股味道,很难闻”,“他好像总是在流鼻涕,也不用纸巾擦”,“他的衣服看起来好脏”……。总之,没有人愿意跟陈辉做朋友,他在班里就像是可有可无的存在,除非老师指定的任务必须让陈辉加入,否则没有人跟他说话,他的座位调到谁那里,谁就会特意把桌椅拉开一点,路过他的座位,有的同学甚至会捂着口鼻,这时候有的男生就会起哄,大声说:“还不跑快点,不怕熏到自己呀!”(案例中雅妮、陈辉均为化名)
可是,所有学生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并未提及“欺凌”,当社会工作者询问他们“你认为这个事情算欺凌吗?你怎么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当然不是呀”,“我们只是不喜欢这样的同学”,“这样的同学真的很奇怪呀,我们很难跟他们做朋友”。正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不算欺凌,因此这样的事情很容易一直持续。实际上,森田洋司(2017:176-178)称这种现象是符合常规的“正义的欺凌”。这些常规可能是大家约定俗成的各种规则,包括价值观、伦理观、信念体系、惯例、习俗和流行文化等。学生们按照同伴群体形成的习惯看待和处理同伴关系,在不经意间否定另一个人,无视他人的痛苦,这实际上就是在制造欺凌文化①沈旭、黄烜,2018,《关系让校园更美好:减低校园欺凌一线实践者分享报告》网络出版报告。。但是,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欺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依着同伴群体生产出的生活方式来选择和结交朋友。
可见,同伴群体的生活方式生产深刻地影响了学生们对欺凌现象的“洞察”能力,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学生们发现和防范欺凌的可能性。已有实践经验表明,如果只是提供欺凌知识,或者提高学生反对欺凌的意识,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往往收效甚微②沈旭、黄烜,2018,《关系让校园更美好:减低校园欺凌一线实践者分享报告》网络出版报告。。社会工作服务必须要开拓服务范围和深度,深入了解并介入同伴群体的生活方式生产过程,给每个学生机会“洞察”、发现和干预那些被他们生产的群体文化所“隐藏”的欺凌行为,形成尊重差异、友好相处的同伴交往习惯,才能有效预防欺凌。
为了让同辈群体形成自觉防范欺凌的生活方式,项目组从倾听被欺凌者的感受和创建尊重友爱的校园氛围两方面着手,促进同辈群体养成预防欺凌的生活方式。项目组在学校设置了“心语信箱”,欢迎大家投递任何有关自己或他人的故事。为了消除他们的顾虑,社会工作者鼓励孩子们匿名投递信件,不需要说出故事中任何人的姓名,只需要说出感受。信箱里的故事大多数来自被欺负的同学或者旁观欺凌希望帮助同学却不敢出手的同学。他们有的讲述自己每天被同学叫着难听绰号,却只能无奈苦笑的烦闷;有的写下了自己被曾经的朋友孤立,朋友之间的秘密突然成为了谣言的开始,其他同学都听信朋友的谣言,远离她,让她感受着四面楚歌的悲哀;还有的记录了班级里不受欢迎的同学遭遇了大家的嘲笑、冷落,她知道大家那么做是不对的,但却还是不由自主地附和,故意表现出不友好,因为她不希望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同学……
项目组糅合了这些来自孩子们的故事,编写参与式、沉浸式的预防校园欺凌剧本。项目组希望通过采用形式新颖、内容有趣、参与广泛的“改良式论坛剧场方法”(Toole,Burton,&Plunkett,2007:29-30),让每个同学有机会倾听这些故事,学习理解经历这些事件的同伴们的不同感受,与他们一起揭开隐匿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欺凌故事。戏剧由大学生志愿者(主要扮演欺凌者)参与排练,邀请小学生参与表演(主要扮演被欺凌者和旁观者)。在剧场排练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随时会聆听演员们对戏剧故事的理解、表演的感受;在戏剧表演中,演员会随时向围坐在表演舞台旁边的小学生互动,提问“如果有同学这样对待你,你会有什么感受?”,带领学生体验被欺凌者的感受,理解欺凌者、强化者和协助者的立场和心理,懂得支持欺凌的同伴群体氛围对事件的影响。最后,社会工作者倡议每个人行动起来,为营造友善温暖的同伴群体而努力。社会工作者与孩子们一起憧憬尊重友爱的日常生活:校园里没有排斥、造谣、冷漠、歧视、暴力;充满了尊重、欣赏、鼓励和友善。
项目评估发现,促进倾听的信箱与鼓励参与的戏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了解欺凌的机会以及形成对于欺凌的深刻认知,带动了更加积极的同伴群体生活方式的生成。项目实施后的评估显示,尽管不同的学生对于欺凌的看法及同伴相处的方式还是存在不同的理解,但都表示参与项目促使自己比以前更多地观察和思考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如五年级的李辰(化名)提到自己参与项目后,当开始出现不喜欢某个同学的想法时,会思考“如果其他人这样看我,我会有什么感受”;当同学之间出现不友好,出现所谓的“过分的玩笑”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想“这是不是可能给别人带来烦恼?有没有更好的相处方式”等。在访谈中,六年级的吴巢(化名)则表示他并不认为给别人取不太好听的绰号这样的行为属于欺凌,不过既然有同学会因此感到不舒服,他还是会注意和同学相处的方式。可见,项目服务有助于同伴群体养成尊重差异、友好相处的交友习惯,从群体的生活方式角度进行预防欺凌干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不过,项目对于同伴群体生活方式的影响和预防欺凌的作用还有待加强。在服务开展中,社会工作者和评估者观察到一些同学在平时的同伴相处中却继续保持过去的行为习惯,比如“拉帮结派式”交友、以“幽默”之名行欺凌之实。项目只是尝试性地开展了影响同伴群体生活方式的短期干预,设置心语信箱和开展戏剧活动的服务内容仍然显得单薄,无论是掌握欺凌知识还是形成温暖有爱的同伴群体都需要长期、反复的练习与巩固。从同伴群体的生活方式角度预防欺凌需要开展持续性、丰富化的服务。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C市预防儿童欺凌的社会工作项目为例,探讨了以文化生产视角开展预防欺凌的社会工作服务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基于项目的案例研究发现,首先,同伴群体互动中学生能动的文化生产过程是理解校园欺凌的群体过程的有益视角,也是社会工作开展预防欺凌服务的有效切入点。其次,从意义生产的视角出发,预防欺凌课程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群体互动重新生产“欺凌”意义的机会,在讨论、辨析欺凌意义的课程教育过程中,同伴群体逐渐形成新的“欺凌”意义,提升了学生对欺凌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再次,以同伴群体文化中的自我生产过程为切入点,同伴教育小组服务对培养积极的旁观者有着正向的影响,学生在小组服务中逐渐转变消极围观欺凌的旁观者身份,开始用自己的行动建构积极的旁观者形象。最后,深入到同伴群体生活方式生产过程的预防欺凌的社会工作服务,有助于学生“洞察”被群体文化“正常化”的欺凌,通过鼓励学生发声的“心语信箱”和学生参与的“改良式论坛剧场”,项目促进了学生形成尊重差异、友好相处的生活方式,从而实现预防欺凌的目的。
项目的实践探索表明,群体文化生产视角对于预防欺凌的社会工作服务设计和实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方面,威利斯的文化生产非常强调青少年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这能够促进社会工作者从学生自身所处的同伴群体出发,理解校园欺凌的群体互动过程这一“黑箱”,推动校园欺凌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根据意义生产、自我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这三大文化生产内容,开展预防欺凌的社会工作服务,是一个寻找可行的预防欺凌路径的尝试。不过,文化生产视角下预防欺凌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服务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服务效果也需要持续跟进评估。由于经验不足和项目时间、经费限制,这一文化生产视角下的探索式项目的服务内容还不够丰富,覆盖对象也相对有限。项目的效果评估主要采取定性方法,以服务对象的主观评价为主要依据,未来还需要采用科学的干预研究设计及相关评估方法来验证项目服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