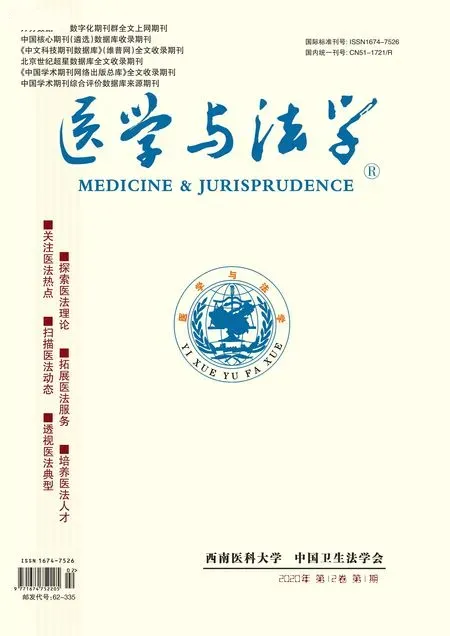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法律及伦理规制探析
——以CRISPR/Cas9技术为例
姚山春
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及其现状
(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
从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打破“人是由上帝创造的”神话传说开始,人们对进化的研究就未曾停止过。孟德尔神父在种植豌豆的过程中,发现了遗传的秘密;一百多年过去了,人类不仅破解了遗传的密码,还尝试着通过基因改善动植物乃至人类的缺陷,因而在一次次的大胆猜想和实践中,基因编辑技术①应运而生,并且在几十年内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减少油炸土豆中的致癌物质的产生,到帮助小麦免受白粉病的困扰;从增强蘑菇抗变质的能力,到生产出瘦肉型的瘦猪;从植物实验到动物实验,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领域日益扩大……
在动物胚胎基因领域,应用基因编辑技术所获得的显著成果给了人们莫大的信心;在治疗单基因遗传性疾病的尝试上,基因治疗也给科研工作者们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更有甚者已经跃跃欲试,尝试通过基因治疗预防疾病的出现,即“把基因编辑从‘治疗’范畴推广到‘预防’领域”,然而这“看起来有着毋庸置疑的合理性”,“操作起来却大大延伸了这项技术的适用范围。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基因治疗和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边界在哪里呢?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提醒自己,不要轻易挥动上帝的手术刀呢?”[1]从基因编辑到基因疗法技术的转变、应用,其中间间隔的不仅仅是技术的鸿沟,还有伦理和法律的天堑。2018年,一对基因编辑女婴在中国悄悄诞生,来自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教授贺建奎宣布:她们出生后就能天然免疫艾滋病。这一举动已远远越过了2015年在华盛顿举办的“首届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为基因编辑技术研究所划定的“禁止出于生殖目的而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的红线。“贺建奎事件”引致学术界的恐慌和躁动,亦引发了科研工作者和立法工作者的深省。于是,为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划清伦理边界、法律边界,探索如何规范应用基因编辑技术,从而让科学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服务于社会的需求,被重新推上台面。
本文拟以现今已较为成熟、应用更为普遍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为例,通过该技术目前在人体基因编辑领域影响力较大的实例,分析其在应用中所面临的伦理和法律难题,探索如何在制度层面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进行规制。
(二)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及应用现状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在2012年由张锋、Jennifer Doudna等团队研发。相较于以往的技术,CRISPR/Cas9有着明显的优越性:首先,从工具准备的角度看,设计和制造一个用于基因组定位的RNA片段,对于任何一个稍加训练的生物学研究人员来说都是易如反掌的事(甚至说,一个受过基本训练的生物学高年级本科生都可以进行操作);其次,从工作效率的角度看,张锋、Doudna等的实验室工作也证明了该技术的工作效率远高于其他技术。在工作和临床应用中,易如反掌就意味着低门槛,高效率就意味着低成本和短周期;而这些优势,就意味着这项技术能够将许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2]
2014年4月至9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范勇博士的研究团队从87名捐赠者里收集了213枚废弃的不能正常发育的受精卵。他们使用CRISPR/Cas9技术,使得26个编辑胚胎中有4个被成功编辑,实现艾滋病免疫。次年4月,中山大学黄军就的团队又运用该技术,为治疗地中海贫血症提出了新的思路。尽管范勇、黄军就等人所使用的是废弃胚胎,这些成果发表后仍在科学界和伦理界激起波澜,因而直接在受精卵上进行基因编辑的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实验,就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恰如范勇所言,“研究成果的临床应用还言之尚早,一方面取决于技术层面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还需要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伦理层面的突破。首先,要在技术上很完美才可能普遍应用,不能说有可能成功有可能不成功,这时候肯定不能应用到人上面。国家在这方面有要求,实验数据、发表文章大家公认,做了完整评估后,才能再去向国家申请。在国家层面,法律层面,制定了很多相应规范,按照规范来才有可能。至少在基因编辑方面,国家层面还没有放开,所以只能停留在实验室研究水平”[3]。
二、CRISPR/Cas9技术的应用难题
(一)该技术应用的潜在风险
尽管,CRISPR/Cas9技术是为当下所公认的最为简洁、高效的技术,但它并不是一项完美无缺的技术,至少,现在还不是一项可以大胆应用于人类生殖细胞及胚胎编辑的技术。CRISPR/Cas9技术存在着较大的脱靶风险②——即使是在贺建奎本人对于双胞胎女婴的基因编辑中,其中一名也产生了脱靶现象;而当下的技术,尚不能为修复这些错误基因找到很好的修复工具。因而,盲目进行人体基因编辑的风险是不可预估的。“瑞典洛林斯卡研究所和剑桥诺华生物医学院于2018年6月11日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子刊《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的成果中也有提及,CRISPR编辑成功可能会增加患癌风险。”[4]
科技的发展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迅速,或许在未来的某一日,基因编辑技术能够成熟到足以规避技术上的错误,精确剪辑,进而实现从治疗到预防的跨越。我们不仅仅可以把基因编辑应用于预防疾病,甚至可以将其应用于改良下一代的基因——谁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有过人的才智、高直的鼻梁、水汪汪的大眼睛?但倘若基因编辑真的被应用于此,那么能够进行此类选择的,却依然仅是经济实力雄厚者,故这样不加规制的应用,必然导致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再想一想,这样被基因编辑后所生育下来的婴儿,是否又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困惑呢?可见,基因编辑技术在应用时,不仅要考虑技术的成熟度,还应考虑到是否符合伦理。
(二)模糊的伦理审查
从2016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以下简作《伦理审查办法》),是目前关于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规范之一。根据《伦理审查办法》,对实施相关生物医学研究进行伦理审查的监督管理机构,主要分为国家级、省级、县级三级。但这三级监督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如下一些缺陷:
第一,伦理审查流于形式。根据《伦理审查办法》第七条,从事此类医学研究的机构均设有相应的伦理委员会,且该伦理委员会负责对此类研究进行相应的、独立的伦理审查。这样的规定看似天衣无缝,但实际上,这恰恰是让伦理审查流于形式的“便利条款”——因为伦理委员会隶属于本单位,其很难独立地进行审查判断。虽然《伦理审查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利益相关回避制度,但是其所要求回避的人员并非整个伦理委员会,而仅仅是与待审查的研究项目存在利害关系的委员。此外,当涉及风险较大的或者比较特殊的研究项目时,《伦理审查办法》所给予的回应也十分含糊,并不具有刚性的约束力。根据其第二十八条,对于此类项目,“伦理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申请省级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协助提供咨询意见”,但根据语义学的解释,“可以”并非强制要求,且其所设置的申请前提“根据需要”更是扩大了申请的弹性!换言之,即使是风险较大的研究项目,本机构的伦理委员会仍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批准,而省级伦理专家委员会的意见对之不具有实质的约束力。
第二,对特殊项目、风险项目的具体标准,规定得并不明确。如前文所述,“对于可以申请省级或国家级伦理委员会协助”的那一类项目的具体“特殊”“风险较大”的情形,《伦理审查办法》并未规定有明确的标准,这给本级伦理委员会解释此类项目的特殊性、风险性提供了极大的弹性空间,因而在实际应用中很可能出现各伦理委员会对同一类研究项目的风险评估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从而影响进一步的审查。
第三,跟踪审查制度往往形同虚设。跟踪审查制度的设立与贯彻,有利于对研究项目的合伦理性和合法性进行核实。《伦理审查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了跟踪审查制度,但是该制度的设计比较粗略,没有明确跟踪审查的时间节点,也没有对如何安排特殊项目的跟踪审查进行进一步的细化规定。在实际中,跟踪审查制度也很难具体落实。如前述,本机构内的伦理审查都有走形式之嫌,更不要说后续的跟踪审查。据悉,在由贺建奎公布的信息里,也没有披露后续跟踪审查的文件。此处暂且不论贺建奎伪造伦理审查文件一事的真实性,而仅以跟踪审查制度的落实对于防范违规进行人类基因编辑的科研活动来进行讨论。侥幸通过伦理审查的涉及人类基因编辑的研究项目,如果违背“14day原则”,妄图使基因编辑婴儿诞生,那么在跟踪审查制度中,假如我们设置了14天内、14天至1个月内、3个月内的审查时间节点,就完全有可能发现并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三)科研自觉的淡漠
贺建奎团队的那次基因编辑实验,反映出极少数科研人员在进行研究工作时,其科研自觉性极其淡漠、只为追名逐利而罔顾他人权益和伦理道德的情况,其具体表现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现行规范。根据《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第六条的规定,进行相关研究所使用的囊胚的体外培养期限不得超过14天。英国也有类似的“14day准则”,并要求编辑后的胚胎不许植入生殖系统。[5]受限于当下技术水平的发展程度,科研工作者们并不能对生殖系细胞及胚胎编辑的安全性作出合理预期,这类实验的走向如何、风险多高、安全与否,目前尚不能完全回答。过去的两届人类基因组峰会的声明也一再强调: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之下,对于生殖系编辑的任何临床应用都是不负责任。
第二,在已有其他医疗手段③可以帮助男方艾滋病抗体呈阳性的志愿者夫妇生育健康婴儿的情况下,贺建奎仍坚持进行基因编辑;并且在其团队实验中,被选取敲除的CCR5免疫蛋白不仅仅是HIV病毒入侵的辅助受体,还是参与机体免疫应答的重要蛋白,敲除后极有可能会造成实验对象(也就是露露和娜娜)一定的免疫系统功能缺陷。[6]尽管有调查显示,全世界有10%左右的人群存在CCR5免疫蛋白缺失而天然免疫艾滋病,但这样的突变(我们称之为“CCR5Δ32”)在欧洲人群当中更为常见,而在亚洲CCR5的突变率极低。贺建奎选择了这个在亚洲人群中并不常见突变的基因进行编辑,并且还选择在亚洲志愿者提供的胚胎中编辑,这样组合下的实验结果,在此类研究领域里,并不具有多大的参考价值。
第三,贺建奎的伦理审查许可涉嫌造假。试验启动前,须经试验所在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但据悉,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号为ChiC-TR1800019378、名为“HIV免疫基因CCR5胚胎基因编辑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的试验,研究负责人是贺建奎;而按照注册信息,该试验的主办单位(项目批准或申办者)以及研究实施地点,为深圳和美妇儿医院,可是在当年的11月27日下午,该院紧急发布声明,称其伦理委员会的文件上的签名有伪造嫌疑!并且在贺建奎所提供的文件中,并无跟踪审查、复审的信息![7]
第四,受试者知情同意的过程存在瑕疵。据报道,贺建奎团队并未向受试志愿者说明有关编辑人类胚胎的伦理问题,而只强调参与试验将会得到的经济利益,并表示生下不健康婴儿的可能性非常低、且已经在动物试验中取得很高的成功率等等,然而却未说明具体的试验内容。[8]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受试的志愿者夫妇的知情同意存在着瑕疵,并且很有可能其在贺建奎团队的夸大之下并不了解、也难以再去了解此项试验会产生的风险,进而怀着产下健康婴儿的愿景才签署了同意意见书。
第五,贺建奎本人并不具备与艾滋病、不孕不育方面有关的相应科研经历。根据南方科技大学官网原有的贺建奎的个人主页显示,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博士期间攻读的是生物物理方向,从其履历看甚至是没有生物学方面的科研基础的;另外,贺建奎研究室的研究方向,则是基因测序、CRISPR基因编辑等,这些经历并不涉及艾滋病防治和人类生殖领域。由此,我们不得不细思贺建奎一开始决定对CCR5基因进行编辑的目的,究竟是利益驱使,还是医者仁心?
(四)法治建设滞后
目前,我国对于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并无专门的法律,相关的规定都主要以“办法”“条例”等文件形式呈现④,不具有较强的约束力,故在法律责任的设置上存在着空白地带,即没有完全针对性的立法,还是以伦理准则为主;即使是涉及滥用基因编辑技术的法律责任,也以行政责任为主。因此当基因编辑技术滥用事件出现,法律监管层面存在空白区间,对于研究者的责任,我们很难予以厘清。就以“贺建奎事件”为例,暂且不论作出伦理审查的医疗机构的责任,仅对于贺建奎及其团队主要实验人员的行为该如何究责,法律监管也是十分苍白无力的。
1.惩罚形式比较单一,且主要以行政责任为主。
纵观我国对于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一些相关规范,有关技术不当应用的处罚形式比较单一,以行政责任为主;涉及民事责任,大多以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民事赔偿的形式表述;涉及刑事责任的,则大多表述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规定看似把责任归属落实到了方方面面,实际上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不当应用所产生的后果,在民事立法上,没有寻求赔偿的依据;在刑事立法上,也没有可以据此究责的罪名。故总体而言,配套的立法尚不完善。
2.没有明确、严格的民事立法规范。
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人体应用,目前并没有明确、严格的民事法律规范[9],而只在《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的第二章“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中,以基因科研活动“不得违背伦理道德”等表述一笔带过[10];尽管,这是二审稿的一大亮点(相较于一审稿),但笔者认为,对于规范基因科研活动、保障受试者的民事权益而言,这样的表述还是太过笼统。基因编辑的不当应用,或会导致被基因编辑的胚胎发育成的人的身体机能受到影响,因而会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原则,但该规定却仅仅模糊表述为“不得违背伦理道德”!因之,应当在未来立法中明确提出对基因编辑不当应用活动的禁止。此外,就民事赔偿而言,有学者认为参与试验的志愿者夫妇可能存在合同法、侵权法两方面的请求权,可以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及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探索求偿的路径。[11]但笔者认为,此类试验因为在民法上没有被明文规定为“违背公序良俗”,且现在仍无法对受试产生的双胞胎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故使得诉求在实际操作中依然存在一定的难度。
3.刑事立法亟待设立相应的罪名。
纵观我国《刑法》,截至目前也没有设置与滥用生物技术相关的罪名,亦没有关于对由人类生殖细胞进行编辑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按照上述规范所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先在现行刑法的架构之中来探寻贺建奎团队及其实验主要责任人员的行为所可能触犯的罪名,根据犯罪构成分析其行为所会否被纳入入罪门槛之内,尝试据此来追究其所可能要承担的刑事责任。
第一,对于贺建奎及其团队主要责任人员是否构成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分析。要构成本罪,行为人主观上要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其在客观上所使用的危险方法也需要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并且该行为要达到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12]然而,在主观上,我们很难认定贺团队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即使贺建奎从一开始就知道试验所存在的风险,但就其追名逐利、罔顾道德的动机而言,贺建奎也并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在客观上,贺团队所作的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试验从本质上说并不属于危险方法,被基因编辑过的婴儿更不属于“危险物质”。尽管从长远来说,经过基因编辑过的婴儿在未来或有可能影响人类的基因池,但是在目前看来,并不能认定该项试验已危害到了公共安全。
第二,对该团队主要试验人员是否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分析。从客观行为层面而言,该团队主要试验人员主要对受精卵胚胎进行了基因编辑,目的是使经过基因编辑生下的婴儿对艾滋病天然免疫,因此将该团队的行为解释为投放危险物质,实在是有些勉强。况且,我们也无法将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定性为危险物质,因为首先,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会否对公共安全产生影响仍是未知数;其次,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若被解释为危险物质,无异于将其视作一件物品,这在伦理和法律上都是十分不合理的。
第三,该团队主要试验人员难以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该罪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行为对象是“他人”。首先,对于主观的认定而言,即便我们以贺建奎明知CRISPR/Cas9技术的不安全性、不稳定性及其动物试验中已经出现了脱靶现象为由,推断其已经预见到这对双胞胎姐妹很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隐疾或基因组改变的情形,但我们难以断定其对双胞胎姐妹具有伤害的故意,即使是间接故意。其次,试验的对象是双胞胎的胚胎时期,并不符合我们对于“他人”的一般认识。
第四,该团队的主要试验人员能否被认定为构成医疗事故罪的分析。根据“贺建奎事件”中贺建奎及其团队主要的试验人员对于CRISPR/Cas9技术存在不确定性、但却仍违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基因编辑试验的行为,我们可以认定其主要试验人员的“严重不负责任”,但是本罪的行为主体被限定为医务人员——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其主要的试验人员并非医务人员,而是高校的研究员。另外,即便主要试验人员已取得了医生执业资格,此处也没有事实表明该团队的试验造成了“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结果”——就该事件所涉及的主体而言,能被定义为“就诊人”的,应该是参与本次研究活动的志愿者夫妇,但是他们所参与的也只是试验的第一个步骤即人工授精环节,而真正受到基因编辑影响的是当时尚在发育的受精卵胚胎,而我们不能也无法将胚胎划入“就诊人”的范畴。
第五,该团队主要试验人员或可被认定为触犯非法行医罪,但是需要进一步推论。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关于非法行医罪的规定,从行为主体上看,该团队的主要试验人员的确不具有医生执业资格;但其行为因不是单纯的基因编辑基础研究,而涉及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的临床应用,也可以解释为“帮助生育”行为,据此,可以认为该团队的主要试验人员的行为属于非法行医。
如前文所述,想要认定贺团队主要试验人员构成非法行医罪,现在只剩下了一个要件,这就是该次试验是否情节严重?综观“情节严重”的几种情形,能够进入我们考量范畴的只有最后一种情形,即“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的兜底性的描述。首先,因为此处的“就诊人”应被解释为接受非法医疗行为的对象,即基因编辑婴儿的父母,该次试验并未造成他们轻度残疾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此外,尽管被编辑的胚胎出现了脱靶现象,我们也不能将胚胎的脱靶现象界定为器官组织的损伤,否则会出现解释上的漏洞和不合理。其次,尽管我们知道,敲除CCR5基因并不能完全预防艾滋病,“由于艾滋病毒的高变性,除CCR5基因外还有其他基因可使用”[13],故此次试验并没有达到“天然免疫”的目的;但由于并未有其他的证据确定此次试验对这对双胞胎造成了什么具体损害(至少现在看来她们是健康的),因而通过推测未来这对双胞胎可能会出现健康问题来认定此次试验的后果属于“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是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最后,从刑法的谦抑性角度出发,也不能贸然断定该次试验行为已经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除非在本事件的后续跟进调查中,确实出现了具体损害,且这个具体损害经过认定,并且应当是强有力的认定,证实该具体损害是由于不当的基因编辑造成的,尝试以非法行医罪进行究责才会有相应的适用空间,然而这样的情况,可能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
综上,在刑事责任上,对此类行为进行究责并没有适当的法律依据;至少就现行的法律框架而言,想要对此类行为进行定罪,需要非常充分的说理和解释,稍有不慎就会掉进类推解释的圈套中。但笔者认为,使解释达到这样严谨的程度是极其困难的;即使我们清晰地知道,此类行为已经突破道德和伦理,冲击着科研的底线,其甚至在与我们邻近的亚洲国家,或者是远隔重洋万里的欧美国家,此类行为是受到刑法规制的,我们依然无能为力。
三、基因编辑技术应用规制的未来探索
“贺建奎事件”的披露,让我们看到了贸然运用不成熟的科学技术所会带来的恐慌和后果,但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我们也大可不必因噎废食。正如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发明者Doudna博士所认为的,对伦理问题的忧虑不应当是阻碍科学进步的路障,而应该是科学进步的动力,因为基础研究恰恰是帮助科学家解决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前提,但在鼓励基础研究的同时,科研工作者也应该肩负起审慎科研、科研自律的责任。[14]对于基因编辑技术在我国的未来应用探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当予重视:
(一)鼓励基础研究,提高技术水平,加强科学伦理教育
如前文所述,“贺建奎事件”只是极少数,在基因编辑领域,更多的是兢兢业业,刻苦探索的科学家团队,我们不能因为贺建奎一个人的不当行为就否认基因编辑技术在未来的广泛应用。因此,仍应当支持、鼓励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基础研究;同时,加强科学伦理教育,提高研究者的科研自觉性、自律性,让基因编辑技术得以发展成为更稳定、更安全的技术。
(二)完善伦理审查制度,落实跟踪审查
“贺建奎事件”折射出我国科研项目伦理审查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故在未来,有关人体试验的科研项目的伦理审查,应当更为严格。首先,建议设立自我审查和交叉审查二重审查制度,在本单位伦理委员会审查完毕后,再报同级其他机构伦理委员会或省一级伦理委员会审查,以利于避免本单位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的随意性。其次,当科研项目涉及人生殖细胞、遗传资源的研究时,应当报国家级伦理委员会备案,再申请相应的行政许可。其三,落实跟踪审查制度,在初次伦理审查通过后,根据项目的预期时间,应在立项后由本级负责交叉审查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进行跟踪审查,以考察项目是否依照原先的计划进行,并将跟踪审查的结果报告给上一级伦理审查委员会进行备案;在项目研究中期,由上一级伦理审查委员会再次进行跟踪审查,以考察项目的进程和备案的真实性。通过跟踪审查制度的落实,防止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表面一套,操作一套”的现象,以避免有些科研团队为了实施不被允许的试验项目,用合理的试验项目作掩饰来获得伦理审查许可。
(三)加大执法力度,加快相关法制建设
1.加强行政处罚的力度。
2019年,我国通过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对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不当科研行为加大了行政处罚的力度。这在规范涉及人体的试验、涉及人类遗传的试验或曰涉及基因编辑技术的试验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高额的罚款和较重的资格处罚,对于妄想通过不端科研行为追名逐利,罔顾科学伦理和道德的研究者来说具有相当的威慑力。建议对于有过不端科研行为的研究人员,可以根据其行为的恶劣程度进行从业限制和从业禁止。
2.加快人格权立法。
对于此类科研行为,在未来的人格权立法中,建议明文禁止,以便为民事追责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依据;并且,承认“不当出生”的诉讼请求,在民事侵权领域承认对基因编辑婴儿的权利保护。
3.设置有关基因编辑技术不当应用的犯罪罪名。
我国现存的刑法框架中并没有关于基因技术应用方面的犯罪,但基因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因此,我国刑法应加快有关基因技术不当应用的罪名设置,以应对未来有可能出现的犯罪事件,同时也起到预防和震慑作用。
4.制定专门的《基因法》。
基因资源涉及人类的遗传、发育,有关基因资源的使用和研究同样对人类的未来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仅有一些零散的规范并不足以保护基因资源,要推动基因编辑技术的规范应用,就应细化有关基因资源的管理、应用规定,故制定专门的《基因法》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四、结语
新事物的诞生,往往伴随着质疑的声音,但我们不能否定其对人类生活的可能益处,基因编辑技术亦如是。新事物的发展是呈螺旋上升式的,发展过程中或许会遭遇波折,但并不会停滞不前。对于基因编辑技术,我们应当持肯定态度,同时为这项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提供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和伦理审查保障,以让其在医学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未来的世界,人们将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治愈罕见的疾病,且不用担心脱靶所可能造成的后遗症。上帝的手术刀真正地用于治愈人类的痛苦,潘多拉的灾难魔盒亦将被关在科研自觉、科研伦理和法律保障的笼子里。
注释
①目前这些技术主要有锌指核酸酶(ZFN)、转录激活子样效应因子核酸酶(TALEN)、基于规律性间隔的短回文序列重复簇(CRISPR/Cas9)系统的基因组编辑技术,以及应用格氏嗜盐碱杆菌的NgAgo基因编辑技术。
②详见王立铭著《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1~272页:“人们认为,这是因为CRISPR/cas9系统对错误的容忍度比较高,即便向导RNA序列和目标基因组DNA序列并不是完美配对,存在一个或几个碱基配对的差错,cas9蛋白也仍然有可能我行我素地启动DNA剪切程序。在浩瀚无垠的人类基因组里,很难说没有一些大体相似的DNA序列存在。因此,高容错性的CRISPR/cas9系统就会导致难以避免的脱靶效应。”
③这些技术主要是母婴阻断、洗涤精液等,但由于国内医学伦理方面规定HIV感染者不能使用试管婴儿技术,贺建奎的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对志愿者而言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认为这能构成贺建奎贸然行动的理由。
④这些文件主要有《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干细胞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前研究指导原则》《生物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