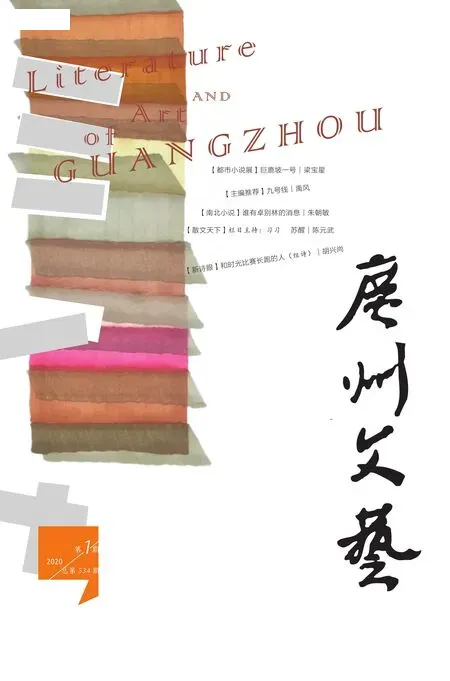耳鸣症
严 泽
一
跟以往一样,没有任何征兆,它又杀了李长林一个措手不及。
路牌显示离机场出口还有两公里,李长林像突然遭到了电击,几乎无法把持了。他握紧方向盘,在心里默默地说,稳住,稳住!奥迪Q7在救援道停下,双闪也忘了打,李长林趴在方向盘上,等待着这遭受电击的时间过去。
仅两分钟,一切烟消云散,红尘俗世又回到本来模样,李长林却已大汗淋漓。这时,一辆警车靠过来,喇叭朝李长林喊,不要占用救援道!高分贝的喇叭跟刚才的山呼海啸比起来,简直显得有些温柔。李长林打开车窗,指指汗淋淋的头。
需要帮助吗?交警例行公事地问。
谢谢,不用了。李长林朝一脸严肃的交警感激地笑笑——似乎刚才的解脱跟他们的到来有关。
李长林把车开往前面的临时停靠点,然后打电话告诉老婆,原计划取消,改道回老家。老婆听到他有气无力的声音,问发生了什么事。李长林说了声没事,就把电话挂了。
李长林这次本是应朋友之邀去云南消遣几天的,刚才突如其来的耳鸣让他那点好心情荡然无存。可以这样说,近来频频发作的耳鸣症已经严重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了。
其实,耳鸣症也只是李长林自己一厢情愿的命名。
李长林看过很多中医,也查过百度,耳鸣根据病变部位分血管性耳鸣与肌源性耳鸣。虽然分为七级,但最高声调的表现也就如鸣蝉、吹哨和汽笛的响声。他的症状可不是这样,一旦发作,就像耳朵两边各附了一个歼击机,每发作一次都像要他的命。
算起来,李长林的耳鸣症不多不少整整三十八年了。刚起病时,差不多是每年发作一次,中间也有过那么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发作,似乎已经痊愈了。但其实不然,就像所有的顽疾一样,在你快忘记它的时候,它却死死地惦记着你,时不时猝不及防钻出来。每当耳鸣发作一次,李长林就要回老家一次,因为在这山呼海啸中他会听到耳边另有一个蜜蜂似的声音——那是刘五林在跟他说话。
猴子,你把我忘了?
猴子,你怎么这样长时间不来看我了?
……
跟李长林说话的是发小刘五林。只要李长林超过一年时间没去看他,刘五林就会按一按手上的遥控器,通过一股超频率的电流让李长林的耳鸣症发作,耳鸣之后的李长林就会乖乖地回去一次。每回去一次,李长林的耳鸣就会好上一年,好像达成了默契。
大前年,李长林的父母相继离世,老家再也没有至亲了,春节他就没有回老家。去年清明,他本来是要回老家扫墓的,父母的第一个清明也是无论如何要回去的,顺便也去看看刘五林。但商场如战场,临近清明,由于一宗重要的生意签约,李长林没有回去成。当时他心里还惶恐着,过后也就淡然了。没想到,不多久耳鸣症就发作了。恐怖的是,这一发竟不可收拾,有时一个星期发作一次,甚至不分场地也无任何征兆。一旦发作,他的脑子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共鸣箱振聋发聩,那几分钟让他去跳楼的念头都有。
就在上个周末,李长林跟相好在酒店里缠绵,正要入港的时候,突然就耳鸣起来,那话儿疲软下去就再也没有直起来,这让李长林恼羞成怒。越来越频繁的耳鸣让李长林痛不欲生。他明白,耳鸣的频频发作不是上了年纪肾精亏损的原因,而是因为他的失信,刘五林在念紧箍咒。
三十八年了。这三十八年来,耳鸣就是刘五林加在李长林头上的一道紧箍咒。只要李长林超过一年没去看他,刘五林就会念上一遍;像孙悟空被如来佛祖念紧箍咒一样,李长林的头在那巨大的轰鸣中一点点被铁箍压缩、压缩,让他上天不得钻地不能。
这么多年来,一旦耳鸣发作,李长林就面向北方,双手作揖,喃喃地祷告,祈求刘五林宽恕,告诉他马上就动身回来看他,就像欠债人祈求债主放宽还款的期限。
但最近越来越频繁的耳鸣已把李长林彻底地激怒了。李长林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像一枚软柿子任刘五林捏来捏去了。这三十八年来,李长林觉得自己已做到仁至义尽、问心无愧,不再亏欠刘五林的了。而刘五林,一个游荡在洞庭湖里的水鬼,缠了他整整三十八年还不罢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了。
在李长林看来,是作了断的时候了。
一个小时后,李长林坐上了回家的高铁。
和谐号如一条巨龙轰然腾飞,也把李长林的思绪带到那灰色的往事中。
二
四十多年前的李长林是板粟村的一个顽劣少年,他的顽劣很大程度上与成长环境有关。
李长林不到五岁时,娘就跟一个耍猴的跑了,有人甚至怀疑他娘原来就跟那个耍猴的有一腿,以至小名就叫他猴子。当然,李长林并不知小名的由来。李长林有一个好吃懒做的爹。俗话说,有范学范,无范看样,李长林长到十来岁时便成了害人精。凡他出没的地方,地里长不成瓜,树上结不了果,再大一点,村里的鸡狗也养不成器。李长林的爹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哪里又治得了儿子?对儿子的行为,他不是教育阻止,而是睁只眼闭只眼。李长林也就更加放纵。板粟村的人无奈,一旦有鸡鸭丢失,唯有通爹日娘自认倒霉,而肇事者十有八九是李长林。
十四岁时,李长林已开始在队里出工,因为还未成人,跟大人劳动一天只记半个工。但这小子猴精马怪的,只要是多劳多得的活,他比大人拿的工分还多。有一次生产队里集肥,凭秤记工分,谁收的肥多谁工分就高。肥分等级,一担狗粪的工分抵十担牛粪。但狗粪稀有,要收集一担狗粪谈何容易?李长林为了多拿工分,想出了一个鬼都想不出点子:他把一根细小的竹筒打通关节,将牛粪从竹筒上面灌下去,牛粪出来便成了细小的条状,一担牛粪眨眼就变成了狗粪。
李长林十四岁那年就尝到了女人味,做了一件让他单身爹也流口水的事。
女人才三十出头,长得颇有姿色,因为新寡,村里几个光棍,包括李长林的爹都还没敢打主意。当然,对于看到母猪也是双眼皮的李长林爹来说,这女人也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哪个女人会瞎了眼,看上一个一日三餐都得不到口的懒汉呢?没想到这漂亮寡妇竟然被他才十四岁的儿子日了。闲话传出来时,李长林的爹兴奋得像是他本人日了一样,一个劲儿地问别人,真的日啦?真的日啦?
当然是真的。那天,李长林本是去寡妇家偷鸡的,没想到刚好碰到寡妇洗澡。李长林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第一次看到女人曼妙的身体,身子顿时就定格在那儿。而那寡妇,早就知道窗外有一双少年的眼睛,她也知道是村里那个顽劣少年。李长林像他爹,虽然才十四岁,却长得人高马大。寡妇自从老公死后,也有几个月没尝男人味了,她突然就起了邪念,想老牛吃吃嫩草。她衣服也不穿,故意在油灯下晃来荡去,然后就仰躺在床上,山是山水是水的。万籁俱寂,外面的李长林早已春心荡漾、魂魄出窍了,哪里还偷什么鸡?次日夜,李长林又像被强大的磁场吸引到窗户边,两只眼睛正要贴到窗子上,突然被人从后面一把抱住了。月光下,正是那一丝不挂的寡妇。当夜,寡妇手把手教这个十四岁的少年成了男人。
不过,当事情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时,李长林的爹还是把儿子狠狠揍了一顿。他不是觉得儿子亏了,而是自己心里不平衡,觉得在儿子面前太没面子了。寡妇没过几个月就嫁到外村去了。板粟村只是多了一则笑谈而已,而很快又被一个个平淡的日子抹得了无痕迹。
也许正是李长林的坏,村里一班少年都服他。李长林手下常有一群跟他玩耍的少年。刘五林就是其中一个。刘五林小李长林一岁,孤儿寡母过日子,长得瘦不拉叽,站在李长林一起简直要矮一个脑壳。从小老实本分的刘五林对李长林言听计从,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要偷出来孝敬李长林一口。但可以这样说,虽然刘五林跟李长林学了一些坏道道,但他善良、厚道的本质还在,不像李长林坏到了骨子里。
转眼,李长林十八岁了,刘五林也十七岁了。三岁牯牛十八汉,只看哪里有重担。到了这个年纪,牛轭子上了颈,都成了生产队里的甲等劳力。李长林随着年龄的增长,顽劣之态虽有所收敛,但仍是个不折不扣的刁民。
在以粮为纲年代,为了多产粮食,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湖洲要田。具体做法是发动人海战役,趁冬天湖床干涸时围湖造田。这年冬天,李长林所在县发动数万土夫子,硬是在广袤的洞庭湖中圈出了一块绿洲。但到次年夏天,一场洪水又变成了水府泽国,洪水把大堤撕开了一个两公里长的口子。为了与大自然抗争到底,冬天到来时,县里又发动全县青壮劳力苦战一冬,倒口缩小了,填起来了。但倒口所处位置原是一条叫宝塔河的河床,是汇入洞庭湖的一条支河,由于底下全是几十米深的淤泥,填在倒口的土就是堆不起来,一天一天往下陷,形成了倒口比大堤要矮很多,又比大堤要宽很多的现象。春节过后,县里只好再次组织全县土夫子,对倒口进行再加高加固。
李长林、刘五林就是在这时加入土夫子队伍的。
这一年是一九七四年的春天。
板粟村的土夫子集中住在湘江河道与宝塔河之间的一个小岛上。这个小岛叫作黑泥堡,岛上用芦苇搭建的工棚密密麻麻,一排排一行行。一个工作队由十六个人组成,其中一个炊事员、一个采购员、一个队长,除炊事员和采购员不用上工地外,其余人都得上工地。李长林和刘五林就是这十六个土夫子中的一员,他们的任务就是在春水到来之前,担土往倒口堆,形成一条大堤。李长林所在的工作队和其他工作队一样,每天分成两个组,一个组从驻地黑泥堡上取土,一担担挑到机帆船上,机帆船再把土运到倒口停下,另一组又从船上把土一担担挑下来倾倒在不断塌陷的倒口上。倒口上架着竹排铺设的长长浮桥,桥下是清澈的湖水,隐隐约约显出塌下去的堤基,人走在浮桥上,晃晃悠悠。
日子一天天过去,两公里长的倒口,在几千土夫子的不停奋战下,一天天地升高、加宽。
参加运土的船都是政府征用的大渔船,船上都有一根很高的桅杆,无风时就机动,有风时就扬帆。板粟村土夫子跟的这艘船的老大姓连,老婆姓王,他们有两个孩子。大的女孩十八岁,名叫桃芳,她身材高挑,皮肤黝黑,眼睛漆亮。桃芳很少说话,土夫子们说什么她只是点头,眼睛很少视人,总是低着头做自己的事;小的是一个叫长发的八岁男孩,白白胖胖的,说话很有意思,把钱叫作“连”,贰角钱叫“两个连”,土夫子们喜欢逗他玩,叫他“两个连”,要他叫“姐夫”。每遇这时,桃芳就远远地锐声喊弟弟到船舱去,不许他跟土夫子说话。连老大四五十岁的样子,长得结实高大,古铜色的脸上沟渠纵横,一看就是个奔波在洞庭湖上的老把式。
连老大的船晚上收工就靠在工棚旁边的湖面上。
由于连老大有个十八年华的女儿,李长林、刘五林晚上都喜欢到船上坐夜,一来二去,刘五林对打鱼人的女儿着了迷。
三
这三十八年里,李长林就像一只候鸟,每年都会来到洞庭湖边的一个小垸子;跟候鸟们不同的是,它们是有规律的,会待上一个季节,而他,大半天后就飞快地逃离。
这是洞庭湖边千百个垸子中的一个,已看不出有什么特殊了。但原来它是很特殊的,因为每到汛期来临,住在垸里的人都会胆战心惊,担心一旦决堤,瞬间就会成为八百里洞庭的水鬼。因为这里原是一个倒口,再往早里说,是一条叫宝塔河的河床。但这点担心现在完全多余了。由于长江上游葛洲坝的修建,千百年来喜欢兴风作浪的洞庭湖已变得静若处子。垸里绿树成荫,鸡犬相闻,像所有青壮年都出去打工的村子一样,这个垸子安安静静的,也看不到几个年轻人了。
三十八年来,李长林见证了这个垸子沧海桑田的变化。由于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次,垸里那些上年纪的人都认识他,知道这个叫李长林的人以前在这里当过土夫子。在他们看来,这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们并不讨厌他的到来。李长林每次来到这里,认识他的人会主动喊他吃饭,李长林也不会客气,解开自己的背包,把里面的烟酒倒出来,很随便地坐到某户人家的饭桌上,也不管主人醉不醉,他一定会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去湖边转悠,谁也不知他去干什么。但人们会发现他会一去不返,招呼也不打一个,直到第二年什么时间又出现在垸子里。垸里人当然也不会计较他的不辞而别,也没人打听他从哪儿来,去了哪儿,没有人会关心这个。但细心的人会发现,从早些年看,这个叫李长林的人比垸里的人强不到哪儿去,但后来——也就是在十多年前,他跟原来有了大变化,那一年他是开小车来的。由此看来,这个叫李长林的发了。
是的,李长林在四十多岁时就发了,有了自己的公司、秘书,现在他的事业还在蒸蒸日上,他每天都忙得要命。但不管如何忙,他会在每年的某个时间,一个人,有时是开车,有时是坐高铁悄悄潜回这个垸子。什么也不做,仅仅是转上一圈看上一眼。很多人记得,早些年李长林还会向他们打听一个姓连的船老大,也许是根本打听不到什么,后来就再也没打听了。
其实,没有人知道,李长林每次来这个垸子都是看刘五林的。他欠刘五林的债,他是回来还债的。每回来,他都要在一个小小的土包前燃上几炷香,烧上几张纸,还要烧上几包烟,倒上两瓶酒。现在想起来,刘五林学会抽烟喝酒都是他李长林教的。那时候,刘五林常常把他娘几个换盐的鸡蛋偷去买烟给李长林抽。世事就是这样怪,欠人家的就得还,现在李长林就是来还债。在那袅袅升腾的蓝色烟雾中,李长林好像每次都看到刘五林从土包里走出来,挨着他坐下,接过他的烟,喝着他的酒。
猴子,你日子过得还好吧?
还好,儿子去年结了婚,讨了一个深圳本地媳妇。

我要是还活着,侄子结婚是要去喝喜酒的,你知道我喜欢喝酒。
刘五林你不要骗我,你肯定还活在阳世上,你是想让我这辈子总是还你的债!
哈哈猴子,你怎么会这样想,我要是还活在世上,难道连自己的亲娘老子也不养老送终?
……
刘五林到底是死是活?至今是一个谜。有人说,他跟姓连那家人走了,做了连家的上门女婿;也有人说,他早就被洞庭湖里的鱼吃掉了。只是三十八年过去,这个谜仍像洞庭湖上雾月里久聚不散的雾团。很多时候,李长林希望刘五林还活着,但他又千百次的否定,这是不可能的,那样大的风浪,刘五林不可能生还。刘五林的死是无疑的,是他害死的,之后刘五林阴魂不散,这么多年一直缠着他;只要忘记他,刘五林就会念上一遍紧箍咒,让李长林的耳鸣症发作,使他痛不欲生。
这个小小的土包在大堤前面的一片防浪林里,是李长林当年挑了几十担土堆起来的。里面埋着刘五林的几件破衣服,用过的箢箕扁担,还有桃芳送给他的一个搪瓷杯。李长林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当时要把桃芳送给他的那个搪瓷杯埋进去。或许他是希望刘五林死后有一点念想,因为他是那么喜欢桃芳。要不是这样,刘五林再蠢,也不会连性命也不顾,扎进惊涛骇浪中去救她。
李长林现在想来又觉得好笑。狗日的刘五林,你他妈的真是蠢猪一个,桃芳怎么会看上你呢?也不屙泡尿照照自己,你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你是蠢死的啊。
要是桃芳不出现,刘五林当然不会死。桃芳当年是看上李长林的,但桃芳那天获救后,再也没有看李长林一眼,第二天就消失在黑泥堡。她去了哪里?那户连姓的渔家去了哪里?也一直是李长林心里的一个雾团。三十八年了,李长林很多时候都在想,要是刘五林还活着,或者做了连姓船老大的上门女婿就好了,但这仅仅是假设。刘五林肯定死了,要不然不会缠他三十八年。再说刘五林是个有孝心的人,他不可能连亲娘老子也不顾。
猴子,去看看我娘,她天天哭,眼晴都哭瞎了。
你把点钱给我娘用,她这辈子就靠你了!
……
那天晚上,李长林怎么也睡不着,耳朵里全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还伴着桃芳绝望的呼救。恍惚中,他突然看到湿淋淋的刘五林冲进工棚,直奔他身边,两只比牛卵子还大的眼睛就那样瞪着他,里面像要喷出两团火来。李长林吓得一声大叫,再睁眼时刘五林却不见了。李长林浑身哆嗦,像从一条水里捞上来的鱼,连床上的被子都湿了。土夫子们被他的大声喊叫惊醒,都说是落水鬼刘五林回来了。李长林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顽劣青年,就是从那天晚上起,对这个世界有了畏惧。他畏惧刘五林,怕刘五林找他索命;也就是从那天晚上起,他心中埋下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这秘密像一块巨石沉重地压在他心头。
也就是在那个晚上,他的耳鸣响彻通宵。
四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三十八年过去,李长林又怎能忘记?每一次耳鸣轰过之后,他的眼帘就会重现那难忘的一幕,心会压榨性地收缩。
连桃芳的出现,无疑给单调的、和尚一般的土夫子队伍注入了鲜艳的色彩。土夫子们的说笑多了,担土的干劲足了,这在李长林和刘五林身上表现得尤其充分。已婚的土夫子们都拿两个后生开玩笑,说谁找到桃芳做老婆是福气,这妹子前有奶后有摆,保证一生一窝崽。船老大老连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心里美美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找个女婿帮他打鱼,是他求之不得的。船老大一旦喝了酒,甚至还当着土夫子们说,哪个后生愿意跟他去湖上打鱼,就收谁做上门女婿。李长林和刘五林听了心里都痒痒的,都巴不得遇上这样的好事。因为凭他们两人的家境,找不找得到老婆都难说,要是能讨到连桃芳这样的老婆,不说是祖坟开了坼也是祖宗修了德。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连老大似乎对老实本分的刘五林有点意思。这其中可能是某个土夫子多嘴,暗地里说了李长林的坏话。这一切,刘五林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也许是受到鼓励,刘五林每天晚上洗完澡,就搽上雪花膏,把头发梳成三七开,跑到连老大船上去坐夜。去时总要带点小东小西,有时是一包舍不得吃的白糖(土夫子们发的),有时是一双白纱布手套。每天,刘五林口里哼着小调,干起活来浑身是劲,像进入了恋爱状态。
但连桃芳跟当爹的意见恰好相反,看上的却是李长林。在旁人看来,这也再正常不过。哪个女子不喜欢能说会道又长得高大标致的后生呢?李长林的斑斑劣迹又没人跟她说过,做爹的即使听说了这些也不便告诉女儿吧。当然,作为从小在船上长大的桃芳,她对李长林的那点喜欢也是相当含蓄的,要是真的论起婚嫁大事来,她也不敢违拗当爹的意愿,好在这些事都还只是说笑而已。桃芳每次对刘五林的到来都不冷不热,看到李长林时就脸红心跳。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连老大对他的选择变得左右为难了。
岛上原本就是老鼠的家园,现在被土夫子占领后,它们时不时会开展报复。土夫子晚上在工棚里睡觉,经常有被它们咬伤脚趾手指,甚至咬伤耳朵鼻子的事发生。工棚里开的是统铺,十几个土夫子并排睡在一起,一只老鼠捣乱,整个工棚的人就不得安宁,甚至前后左右工棚也一起哄闹起来。抓老鼠、打老鼠也成了土夫子空余时间的娱乐节目。幸亏上岛之前,县里给每个土夫子打了防疫针。
一天,大家正在吃晚饭,突然从厨房蹿出一只大老鼠,它口里还含着一只土夫子的袜子。大家顾不得吃饭,把碗一丢就去围捕,很快就网住了大老鼠。这时,连老大的儿子长发刚好经过,便要拿老鼠去玩,李长林就把老鼠送给了他。长发虽然才八岁,却聪明异常,玩老鼠的花样也跟别人不同。他把老鼠从网兜里拿出来,在尾巴绑上棉絮,浇上煤油,然后绑在一根木棍上,用火柴点燃老鼠尾巴。不想这一下闯了大祸。老鼠挣脱后,带着着火的尾巴拼命往工棚里跑,几个人拦也没拦住。工棚都是芦苇稻草盖起来的,遇火即着,且无法扑救。果不其然,老鼠一钻进工棚即引起明火。那天恰巧刮着五六级老北风,眨眼间,风助火势,火烧连营,南面的十几个工棚变成了火海。土夫子一个个逃命,有些人连衣服也来不及拿。不到一根烟的工夫,灰飞烟灭,黑泥堡变成了真正的黑泥堡。刘五林吓得浑身发抖,连老大更是面如土色,连老大的老婆和桃芳、长发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哭作一团——这可是天大的祸事,哪怕用十艘帆船也赔不起的啊。就在连家哭作一团的时候,李长林挺身而出,他把胸脯一拍,对船老大说,老连,你不要怕,责任由我来担!李长林主动向怒不可遏的大队长承认,火是他点的,他的好意是为了灭鼠,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大家都可以作证。
在当晚有几千土夫子参加的大会上,李长林被押上台,随后被公安局带走了。
放牛娃哪能赔得起牛?拘留十天后,李长林就笑眯眯地放回来了。他知道他是凯旋的英雄,等待他的是想不到的好事;他的义举会征服连老大征服桃芳,会把刘五林打得一败涂地。
果然,当晚连老大就邀请全组的土夫子到他船上喝酒。酒桌上,刘五林的形象矮到了尘埃里,李长林却愈发高大起来。连老大夫妇看着李长林满脸都是笑,他们要女儿桃芳亲自给李长林倒酒。桃芳更是如沐春风,面如桃花,两只含情脉脉眼睛全在李长林身上。刘五林虽然感觉到了,但他并不十分难受,他觉得李长林的确是英雄是好汉,今晚应当受到这般礼遇。
日复一日,数千土夫子和上百艘帆船在河套上穿梭,塌陷的倒口涨高了许多,但还是比两边的大堤矮。时间也转眼到了三月,黑泥堡上到处长出紫色芦笋,堡外的桃花都打苞了。春耕生产在即,但全县的土夫子还奋战在围湖造垸的工地上。
这天下午跟平常一样,船在航行,土夫子在装卸。突然,连老大高喊:“不好了!风暴要来了,土卸不赢了!”其他十几艘船上的船工也高喊:“怎么得了啦!快抛锚!把船固定好!”李长林朝河心望去,二十多艘船都拉响了警报。土夫子都笑,看看天空还有太阳,风也只比平常大了一点,他们觉得这些吃水上饭的人真是大惊小怪。
连老大拼命地把土往船两边卸(为了减轻船的吃水量)。土夫子见状,也只好跟着卸,但还没卸几下,连老大把锹一丢,大声喊道:“来不及啦,大家赶快上岸!”他大声喊老婆把孩子拉上岸。说时迟,那时快,连老大刚把老婆儿子推上岸,一阵狂风吹来,人都站不稳,土夫子们的箢箕扁担像树叶一样飞过堤坝,飞到湖中。堤上土夫子滚的滚,爬的爬,眨眼间,天上像有一口大黑锅扣下来,仿佛黑夜就要来临。风更猛了,地上飞沙走石,堤边的船被风浪一下子推到倒口的顶部,一下子又随水降到倒口的底部,幸亏倒口的堤脚由于蹋陷后很宽阔,要不下面的土夫子早已见洞庭王爷去了。这时,又一口更猛的风吹来,连老大的船一下子就吹离了堤岸,向湖中漂去。
“啊呀,桃芳还没有上来!”连老大大叫一声,赶紧飞身上船。一个巨浪把船打到了离岸几十米的地方。
大家好不容易翻到大堤的背面,刚站稳脚跟,豆大的雨点就像机关枪一样从天上扫射下来,大家都不敢抬头,把头埋在泥土上,任凭“子弹”扫射。
风雨越来越大,浪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山头向堤脚扑来,每一个大浪都要吃掉堤上几百方泥土,几个月来数千土夫子用箢箕扁担担起来的土堤眼看就会夷为平地,情况十分危急。李长林这时站起来,以手作喇叭状大喊:“大家快跑!”然后拉住连老大老婆跟长发的手往工棚撤。刘五林却不撤,他扯住李长林,几乎是带着哭腔说:“桃芳还没上来啊!”
风雨中,土夫子们护着连老大的老婆和儿子一步一步地向工棚走去。李长林和刘五林却停了下来。他们艰难地越过堤坡,伏在堤面。
眼前什么也看不到,只有风声雨声波涛和雷电声。
就在这时,李长林忽然听到了呼救声,是桃芳的声音。他听得很清楚,是桃芳在向他呼救。李长林心里一沉——桃芳难道看到了他?
李长林记得好几次在桃芳面前吹嘘自己是浪里白条,水性了得,讥笑刘五林只会狗爬式。又一阵风吹来,雨似乎小了点,那呼救声李长林却听得更真切。没错,是桃芳在叫他,向他呼救。李长林心里打起鼓。
刘五林这时也听到桃芳的呼救。
“听,是桃芳在喊!”他说。
“是她在喊……听……她在喊你——刘五林!”李长林不假思索地说。他的牙齿有些抖。李长林这时是多么庆幸他跟刘五林的名字都有一个“林”字啊。在这风雨声中,就是再认真听,也分不清是叫谁。但他心里清楚,连桃芳绝对不会叫只会狗爬式的刘五林。李长林感到彻骨的冷,他抖得更厉害了,他是害怕。他知道,在这样的时候下水救人会是什么后果。
“真的?桃芳在喊我?”刘五林也在发抖。
“她不喊你还喊……我……我啊?你是她爹看上的……女……婿,你快去救……救她!”李长林紧定地说。
“桃芳,我来救你!”刘五林悲壮地叫了一声,三下两下脱掉衣服,冲下堤去。
李长林冷笑了一声,赶紧向工棚跑去。
这场风暴来得快去得快,不到半个小时雨就停了,风也小了。土夫子全走出工棚,来到湖边。眼前情景让大家惊呆了:河面已没有一艘船的影子,只看到水面上竖着的一根根桅杆,每根桅杆的顶端都吊着一团东西,有吊一个的,有吊两三个的。李长林从别人嘴里知道那上面吊的都是船家的孩子。连老大的儿子长发眼尖,一眼就看到吊在湖中间的姐姐还有抱着桅杆的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桅杆还在风中左右摇晃,一会儿向南倾斜,一会儿向北倾斜,桅杆上的人就像风球在空中晃荡,下面是波涛汹涌,求生的本能使他们死死抱住桅杆,情形很是危急,让岸上的人看得心都碎了。连老大的老婆不停地哭,李长林一边劝一边问:“桅杆上的人是怎么上去的?”
她抽泣着说:“这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救命法宝,是把扯风帆的绳子割断后,用绳子捆住人的腰,把他们扯上桅杆的。”
风至少还有四级,天色越来越黑,河中的桅杆越来越模糊,救援船还没有来。李长林擦了擦眼睛,他想看看桅杆下面有没有刘五林,但是没有,每一条桅杆上都没有,岸上也找不到。这时他才向大家报告,刘五林不见了。
终于,远方传来几声尖锐的警报声,水警来了!三艘快艇飞过来围着这十几根吊着人的桅杆转,但就是靠不过去,快艇不是靠偏了,就是靠过了头。俗话说,八百里洞庭无风也有三尺浪,何况现在还有这么大的风。岸上黑压压的土夫子心急如焚,一个个用双手合成喇叭状朝他们喊:
“坚持住!你们坚持住哇!”
“桃芳,坚持住,坚持住啊!”李长林这时也大声喊。
喊也是白费劲,风浪太大,湖水太宽,水里的人听到也没用。
夜深了,黑泥堡岛上没有一个土夫子睡觉,都在担心桅杆上吊着的人们。眺望河面,也看不清什么了,大家都只希望风快停下来,桅杆上的人能救下来,送到土夫子的工棚里来,快给他们披上棉衣,端上热水。
十二点的时候,桅杆上的人们都终于成功获救了。
只有刘五林没有回来。
那天晚上,李长林怎么也睡不着,耳朵里全是狂风暴雨和电闪雷鸣,还伴随着桃芳尖锐绝望的呼救。恍惚中,他突然看到了湿淋淋的刘五林冲进工棚,来到他身边,一句话都不说,朝他瞪着两只比牛卵子还大的眼睛,里面仿佛有两团火要喷射而出。
就是在这个晚上,李长林的耳鸣响彻通宵。
五
这场特大的暴风雨把土夫子们辛苦了差不多半年的大堤一举摧毁。
再也不能误了农时,土夫子像溃不成军的逃兵各回各的村子。
李长林回来后,耳朵里通宵都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直到后来去刘五林家看了他的老娘后,耳鸣才奇迹般平息。这看似无关却又有联系的事,让李长林更加感到了惧怕。
那时,刘五林的娘眼睛已经哭得看不见了,她抓着李长林的手半天不放。她的儿子不但没有评为什么见义勇为的烈士,就连先进土夫子的奖状也没有一张。没有人知道他是去救人失踪的,李长林当然不会说。再说,刘五林连尸体也没有捞到,谁又知道他去了哪里?
连老大呢,他又带了妻子儿女去八百里洞庭湖上讨生活了。至于那个要谁做上门女婿的话题,就像大风刮过了一样。那个连桃芳,上岸后只深深看了李长林一眼,那一眼就像锥子一样扎在李长林的心上。
接下来的十年,李长林的耳鸣总会发作,每一次发作,都仿佛在提醒他要尽到一个儿子的孝道,去看望那个失去儿子哭瞎了眼睛的老娘。奇怪的是,每去看过刘五林的老娘后,李长林的耳鸣就会偃旗息鼓,半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不发作。
可以这样说,自从患上耳鸣症后,李长林再不是十八岁前的那个不良少年了,他彻头彻尾在改,改变成一个良民。他后来事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跟他的改变有关。是频频发作的耳鸣在提醒他,要做一个良民。只要他在生活中再做一点点违心的事,耳鸣就会无来由地轰然而响,让李长林不寒而栗。李长林知道,不管他走到哪里,刘五林都像幽灵一样跟随他,看着他。都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他头上这个神明就是刘五林。
是的,李长林以前不是好人,他有罪过,他不该骗刘五林,他害死了刘五林。恶有恶报,他要赎清罪孽,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从此再不做半点违心事,每年乖乖地去给刘五林上坟,把刘五林的娘当作自己的娘,直到她给送终,直到她入土为安。
三十岁那年,李长林的爹去世,次年他讨了一个四川来湖南逃荒的女人。这是一个清秀又贤淑的女人,他们很快有了一双儿女。因为生活的担子更重了,李长林跟随打工潮只身来到深圳,先是在一个工地当保安,后来因为表现好,被选进社区治安队做巡防员,再调到治安队负责后勤工作。有了一桶金后,脑子灵泛的他瞅准机会,请了几个模具师傅,租了一间房子,搞起了模具加工。从此事业蒸蒸日上,很快步入成功人士行列。
其实,刚来深圳的那些年,李长林并没有赚到什么钱,但他每年都会回去看刘五林的老娘,一年给她三五百块钱,清明节给刘五林上坟烧纸。那些年,他的耳鸣症也像无影无踪了。刘五林的老娘死后,李长林一度以为责任已尽,次年清明因为太忙没有回去,没想到当天晚上耳鸣又呼啸而至。
猴子,你又来看我了?
是的,刘五林,老子来看你了。
你是越老越没记性了。
是的,我倒是想没记性,奈何你总提醒我,告诉我吧,怎么样才能了结。
……
四个小时后,李长林下了高铁,然后打的到了那个垸子。
已是冬天,万物消瘦,八百里洞庭也瘦得不成样子了,看到的全是杂草丛生的湿地。垸子里许多老人不见了,或许是死去一些了,或许是天冷窝在家里了。李长林没有像过去那样,随便上一户人家吃饭、聊天、喝酒,去当年围湖的黑泥堡旧地重游,去打听连姓渔民的情况。在他看来,这些就像一场梦。
李长林来到大堤下那片树林里。这里的意大利杨长高长大了,它们掉光了最后一片叶子,从上到下直裸裸的;地上是尺多厚的树叶与杂草,一阵风吹来,把地上的叶子卷得满天飞舞。李长林准确无误地找到那个小土包,他挥动从五金店买来的锄头,很容易就挖出了几件破衣服,还有一个搪瓷茶杯。
李长林把它们堆在一起,大哭一场,哭醒悟了,也哭释然了。 他要把这些东西打包带走,把刘五林安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李长林仿佛看到刘五林在面前看着他,直至像一缕青烟一样消散。
三十八年来,李长林终于又回到了他的十八岁——只有十八岁前的他是唯一可以改变这个结局的他。
奇怪的是,回深圳后,李长林的耳鸣症不治而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