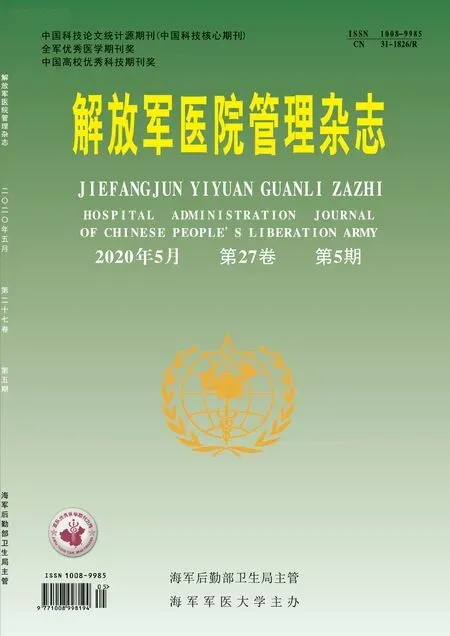植入性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
马 源,刘建超,葛丽丽,李 林,刘丽华
(1.解放军总医院医院管理研究所ERP办公室,北京 100853;2.京弘达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 100853;3.解放军总医院医院管理研究所,北京 100853)
当前,植入性医疗器械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诊疗过程中,成为继药品之后重要的医疗物资,在疾病诊疗及患者健康维护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植入性医疗器械具有直接作用于人体、单价相对较高等特点,与医疗质量、医疗费用密切相关,是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通过对中外相关文献的研究,梳理国外植入性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的经验做法及国内临床应用管理现状,以期为建立系统性、适用性的植入材料临床使用管理规范提供参考。
1 国外临床使用及管理发展历程
1.1 临床应用和管理探索期19世纪末人们已经开始着手植入材料临床应用的研究,骨科用材料的应用是其中主要代表,1890年德国Gluck医生用象牙制作股骨头完成世界上第一例人工髋关节置换,到20世纪40年代金属、有机玻璃等材料开始应用于骨折治疗[1]。此时期是植入性医疗器械临床应用的探索阶段,医疗器械的临床管理也较为简单。美国是第一个以国家立法形式对医疗器械进行管理的国家[2],1938年的磺胺药事件促使国会通过《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ederal Food,Drug and Cosmetic Acts,FDCA)修正案,第一次提出医疗器械管理的概念,并确立由政府行政部门负责医疗器械监管的原则[3]。
1.2 临床应用和管理发展期20世纪下半叶,植入性医疗器械临床应用的范围愈加广泛,到20世纪末临床中已广泛应用,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起搏器、人工耳蜗等材料的应用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应用。为能更好地满足临床需求,植入性医疗器械的材质、结构、功能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单就支架而言,经历金属裸支架(BMS)、药物洗脱支架(DES)等更新。但此时期,植入性医疗器械的安全性问题日益引发关注,例如相关研究发现,植入DES后血栓发生的高峰时间明显滞后于BMS,DES安全性仍需随访验证[4]。
美国1976年版的FDCA修正案,是第一部全面的医疗器械法规[5],以产品风险为依据建立的医疗器械分类和管理制度,其中植入性医疗器械按Ⅲ类管理。FDCA是美国医疗器械管理体系的核心,着重于医疗器械的安全性管理,采用严格的药品管理模式。美国的医疗器械法规因其科学性、系统性而影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医疗器械法规的修订[6]。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由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政府主管部门和产业界组成的“全球医疗器械协调组织(GHTF)”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研讨和交流各国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球医疗器械管理的趋同[7]。
1.3 临床应用和管理的持续深入进入21世纪,新型医用材料如金属钛、高分子材料及生物材料技术在植入性医疗器械的制作中广泛应用[8],3D打印等新技术为个性化假体和植入物的制造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医疗器械已超过50万种[1],植入性医疗器械品种规格近20万种[9]。
当前,临床合理用药已有较为成熟的规范,但植入性医疗器械合理使用的统一标准尚未建立[10],临床使用中的安全性问题依然严峻,同时临床使用合理性的问题日益凸显。有研究显示[11],临床中医务人员存在选择偿付价格和购买价格差距大的植入物的动机,43%的心脏病专家表示,即使认为不会对患者有益也会继续进行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治疗;JAMA杂志的报告显示[12],PCI治疗中仅有50%是适当的,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ICD)手术中20%的患者不符合指南[13]。植入性医疗器械不合理使用的问题已成为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以下是几个主要国家为加强植入性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所采取的措施。
1.3.1 美国
① 医院卫生技术评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主要采用医院卫生技术评估(HB-HTA)对新材料的准入和使用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可用作医保支付政策制定、医疗器械购买决策的判断及制定规范化的临床指南[14]。在医院层面则可根据循证依据,与临床科室及医师约定植入物使用适应证,采用限制使用数量或比例以及使用后检查病历等手段控制植入物的使用范围以减少不必要的使用[15]。
② 医保控费及医师行为分析。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以DRG打包付费的方式为患者植入物买单[16],促使植入材料在临床中的应用,对此,Medicare采取对成本较低的医师奖励,对成本较高的医师进行惩罚的措施[17]。政府认为医院应主动跟踪分析临床使用行为,如果一名医师比同行置入更多的支架,医院需要监测并作出调查,医师需要陈述理由,否则医保部门将拒付费用。
③ 植入物“目录集”和“支付上限”模式。植入物技术相关因素,供应商提供的激励措施,植入物成本相关因素,基于医院的经济政策等非临床因素,被认为是影响医师选择的可能因素[18-19]。在国外,诸如膝关节和心脏支架等植入材料被称为“医师偏好项目”(Physician preference items ,PPI)[20],PPI占据医院供应成本的40%到60%[21],一直是医院和外科医师之间博弈的焦点,医院积极指导外科医师采用更具成本效益的植入物,大体上通过“目录集”模式和“支付上限”模式来实现这一目的[22]。前者限制PPI制造商的数量或者给定购买的产品范围,类似于医院内药品的标准化策略;后者并未明确限制特定产品或制造商,只要是在一个价格限制以下的同类产品,医师都可以选用。
④ 医疗器械唯一标志。为加强医疗器械信息化管理, FDA已正式发布医疗器械唯一标志(Unique Device Identification,UDI)法规和相关指南,美国是第一个在政府层面实施UDI的国家[23],为信息化管理奠定基础。
1.3.2 英国 英国国家卫生与保健评价研究院(NICE)对许多手术提供指南并对植入物推荐目录,但临床医师实际使用情况与目录有差异,与美国同行一样,医师在产品选择方面保留较大的自主权,许多医师并未遵循循证医学的实践指南和方案。由NICE资助的一项研究报告称[24],推荐的髋关节假体“目录”超过50种,但只有66%的髋关节置换患者使用“目录”内假体。英国与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等组织建立高值医用材料分类编码系统,不仅可以对不良事件或医疗安全事故进行追溯,而且形成编码统一的网上产品目录,优化植入物的使用管理过程[23]。
1.3.3 澳大利亚和日本 在澳大利亚的国民健康体系中,植入物同样被打包入DRG付费,在私人保险体系中,则通过植入物目录的方式规定可用的植入物品规及保险公司所需支付的补偿金额[25]。日本国民保险系统以按服务付费的方式支付包括植入材料在内的费用[26],政府作为付款人向医师支付较高的固定工资,较大医疗中心的医师不会因经济利益的考虑而进行支架等治疗。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制定医用耗材的补偿价格时,都以循证评价和经济学评价的结果为依据制定补偿价格[27]。
2 国内临床使用及管理发展历程
我国医疗器械的临床使用与管理起步相对较晚,在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方面仍有待提升。
2.1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国内植入性医疗器械的研制和临床应用逐渐展开,20世纪70年代初,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完成国内第一例人工关节置换手术[28];改革开放后,国内植入性医疗器械在生产和临床应用中获得长足发展,常规植入性器械如关节置换和冠脉支架介入等产品基本能做到自足。
临床应用管理方面,1988年成立“全国外科植入器械和矫形器械标准化专业委员会”,开始和国际标准化专业组织官方接触;1991年我国发布第一个医疗器械政府规章《医疗器械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医疗器械管理的职能部门,医疗器械监管体系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完善。
2.2 第二阶段21世纪初,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使得国内脊柱矫形、心血管介入等操作项目进入蓬勃发展时期[28],2011—2017年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年增长率超过18%,成为世界第二大医疗器械市场[29]。此阶段,植入性医疗器械的安全性和合理使用是政府管理的重点和难点。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奠定国内医疗器械管理的法律地位和基础, 2010年颁布的《医疗器械临床使用安全管理规范(试行)》,加强对医疗器械临床安全使用的管理,相关手术操作的发展逐渐趋向于规范化,但专门用以规范植入性医疗器械的法规或规章依然缺乏,临床合理使用监测、风险控制的管理规范和技术规程不够健全,没有可量化的操作规范或指南,与严格的药品管理模式还有差距。
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医疗资源总量的 20%~30%用在过度医疗上[30],例如国内药物洗脱支架(DES)植入的比例从2001年的18.2%增至2011年的98.4%,而这其中多达76%的稳定性冠心病患者可避免PCI,按照临床指南,狭窄程度<50%的血管不主张植入支架,而临床上很多狭窄程度只有30%~40%的病变也被植入支架[31]。医生在植入性医疗器械选择过程中占主导地位,除去患者临床指征、材料学科技术先进性等客观因素,医院对材料收入的分配机制,材料加价率和加价水平等非临床因素对临床材料的使用也产生一定影响[32]。
近年来,植入性医疗器械在临床中适应证不适当扩大、过度使用等问题已引起政府部门重视。2012年版的《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从控费角度对各手术操作可使用的植入材料种类做出规定[33];2017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医疗机构逐渐取消医用材料加成;2018年国家医保局提出开展按DRG付费试点,植入材料打包入组不再作为单独的收费项目。同时,国内也有部分医院采用卫生技术评估方法,对介入器械与材料的性能、特点及适用范围作出评估,并根据临床专业特点建立各类植入材料的临床使用规范和使用目录的探索。
3 总结与展望
借鉴国外经验,积极利用医保的第三方控费作用,推进按病种、按DRG付费方式改革,促进医院和医务人员以“疾病为导向”的材料使用原则,使医务人员成为控制费用、节约成本的主角。探索利用信息化手段,对植入材料的适应证、使用数量等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使用标准,建立院内、院际间的医用材料合理、合规使用分析评价机制,促进临床中植入材料的合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