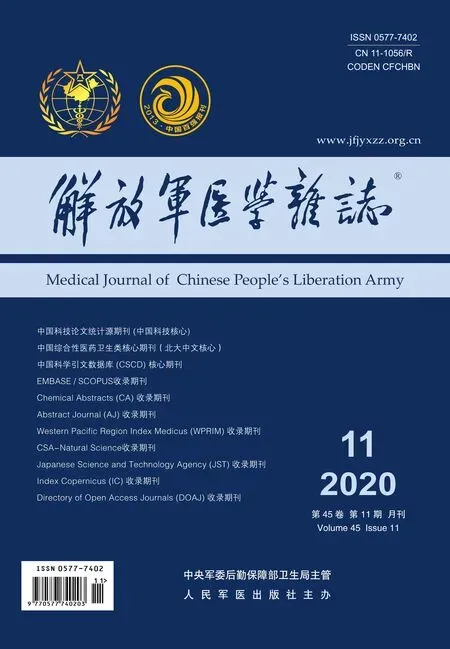“肠-肺”轴与肺部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慕之勇,魏艳玲,李宁,许凤华,阮广聪,肖志凤,范利琴,陈东风,崔红利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内科,重庆 400042
哮喘、感染性肺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等慢性肺部疾病患者常伴有肠道症状,且肠道损害的严重程度与肺部病变的严重程度高度一致[1]。此外,肺部恶性肿瘤患者亦常伴有胃肠道症状[2]。罹患胃肠道疾病者同样可伴有呼吸道症状,如炎症性肠疾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患者即使肺功能正常,且不伴随任何呼吸道症状,其气道也常存在轻微炎症,且与缓解期患者相比活动期患者肺部损害更为明显[3]。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二者在生理病理上有密切关系,但其具体机制尚未明确。近年来,随着对肠道微生态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肠道菌群稳态对全身各脏器系统功能的重要影响,并提出了相关学说,如“肠-肝”轴、“肠-脑”轴、“肠-心”轴、“肠-肾”轴及“肠-皮”轴等学说[4-5]。消化道与呼吸道作为人体最重要的两个与外界相通的脏器系统,肠-肺之间的联系目前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形成了“肠-肺”轴学说。肠道菌群与肺脏疾病是否有关联以及“肠-肺”轴在肺脏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值得关注。
1 肠-肺之间的联系
中医学认为,肺为脏,属阴,大肠为腑,属阳,两者虽相距甚远,但通过经脉的相互络属,构成脏腑表里关系。因此,二者在生理病理上有密切联系。而肺主气,主行水,大肠主传导,主津,故肺与大肠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传导和呼吸方面,均属管道样器官,皆司传输运化[6]。从胚胎发育的角度来看,肠道与肺脏具有共同的胚层来源。人胚胎在第3~4周时,胚盘向腹侧卷折形成圆柱状胚体,内胚层被卷入胚体内形成原肠。原肠可分成前肠、中肠和后肠三段。前肠逐渐分化形成口腔底、舌、咽、食管、胃、十二指肠上段,以及喉以下呼吸管道和肺脏等器官;中肠主要分化为十二指肠中下段、空肠、回肠、盲肠、升结肠和右2/3段横结肠;后肠则主要分化为左1/3段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和肛管上段等器官[7]。肺泡及细支气管上皮细胞与胃肠道上皮细胞均有分泌和吸收功能,同时具有神经内分泌细胞的功能。从免疫学角度来看,肠道是免疫细胞发育的关键部位之一,肠道微生态不仅可影响肠道免疫,还可影响肠道外免疫。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在增强肺部抗感染能力中起重要作用[8]。呼吸道免疫反应属黏膜免疫反应的范畴,人体各部位的黏膜免疫是相互紧密联系的,肠道黏膜免疫系统中激活的淋巴细胞能够到达包括呼吸道在内的多个黏膜相关淋巴组织,发挥针对相同抗原的免疫反应,被称为共同黏膜免疫系统(common mucosal immunological system,CMIS)[9]。从疾病学角度来看,消化系统疾病往往伴随呼吸系统症状。临床常见的胃食管反流性疾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不仅可独立引起呼吸道症状,还可加重已有的呼吸系统疾病[10]。此外,部分胃肠道疾病可通过呼吸功能进行筛查诊断,如临床上13C、14C呼气试验即通过吞咽含有放射性元素的尿素,再检测呼出气体中是否含有特定剂量的放射性元素来判断患者是否存在幽门螺杆菌(HP)感染,以指导临床诊疗。动物实验发现,对大鼠进行不同时长的肠缺血实验,松解肠绞窄后肺脏均出现充血水肿、炎性细胞浸润以及肺泡不张等病理变化,且严重程度与肠缺血绞窄时间呈正相 关[11]。此外,肺部疾病亦可导致消化道症状,如肺部感染、肺癌等患者常出现纳差、恶心、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因此,从中医学、胚胎发育、免疫学及疾病学等角度来看肠与肺之间均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
2 肠-肺间微生态的交互作用
肠道微生态由细菌、病毒、真菌及寄生虫等构成,健康成人肠道中存在1013~1014个微生物,大部分位于结肠,其中肠道菌群数量级最大,起主导作用。根据确定的细菌含量和结肠容积推算,人体结肠内的细菌约3.8×1013个。肠内细菌种类至少有上千种,可分为拟杆菌和厚壁菌两大类,其中以乳杆菌及双歧杆菌为主,这类G-杆菌在宿主抗击慢性炎症和病原体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12-13]。肠道菌群多样性受诸多主要生活事件(如分娩方式、抗生素应用、摄食)及个体健康状态的影响,而肠道菌群多样性减弱(尤其在婴幼儿期)与哮喘、呼吸道感染、肺结核等多种肺部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14-15]。
呼吸道微生态主要由细菌、真菌、病毒等构成,其中呼吸道菌群占优势。健康人群肺部的主要菌属与肠道相似,均为厚壁菌和拟杆菌,其次为变形杆菌和放线菌,数量级可达104。细菌通过群体感应系统和局部产生的抗菌多肽调节细菌总体的动态平衡。呼吸道菌群在呼吸道黏膜免疫系统发育和成熟中起重要作用[16]。呼吸道定植的细菌可为呼吸道黏膜内免疫细胞的分化成熟提供必要的刺激信号。肺组织内记忆B细胞的形成需要肺微生物菌群的抗原刺激[17],而肺部炎症可导致呼吸道菌群失调[18]。 呼吸道菌群失调是呼吸系统疾病进展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调节呼吸道菌群生态平衡能够改善肺部炎症[19]。呼吸道菌群的定植不仅取决于其内部的结构特征,同样取决于外部和内在因素(如吸烟、疾病和免疫功能等)的相互作用。微抽吸(microaspiration)在健康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现象,也是呼吸道菌群来源的一种常见形式。在胃食管反流性疾病患者中,微抽吸可导致肠道菌群直接迁徙至呼吸道,从而破坏呼吸道菌群生态的稳定,进而导致呼吸系统疾病恶化。此外,呼吸道菌群生态失衡亦可影响肠道菌群生态的稳定。既往研究发现,急性肺损伤可导致动物盲肠细菌负荷急剧增加[20]。因此,肠、肺微生态的稳定不仅对维护自身正常的生理功能有重要意义,还会对彼此产生影响。
3 “肠-肺”轴的相互联系
许多胃肠道疾病在呼吸道都有表现,消化道菌群组成的改变可通过黏膜免疫系统影响呼吸道菌群的组成。在小鼠中,胃肠道微生物生态失衡可导致异常的呼吸道过敏反应,而补充乳杆菌菌株和特定的细菌代谢产物可改善肺部过敏反应[21]。循环运输是可溶性微生物组分和代谢物在肠道与肺部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微生物成分包括微生物相关的分子识别模式,如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肽聚糖等,对建立和维持黏膜固有免疫反应具有重要作用。微生物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吲哚丙酸(IPA)等可影响宿主免疫系统的发育和成熟。SCFAs在胃肠道合成后经门静脉运输到肝脏进行代谢,未被代谢的SCFAs经外周循环到达肺脏等组织,从而影响肺组织内免疫细胞的分化成熟。在肺内,SCFAs作为抗原递呈细胞的信号分子,参与调节肺部炎症及过敏反应[22]。 肠黏膜固有免疫细胞经外周循环迁移到呼吸道,可直接参与呼吸道免疫细胞活化及免疫稳态的维持,如ILC2s、ILC3s和Th17细胞从肠道迁移到肺部参与对病原微生物的免疫监视、应答和清除。此外,肠道细菌代谢产物脱氨基酪氨酸(DAT)能够通过增强Ⅰ型干扰素(IFN)的效应来保护宿主免受病毒感染[23]。肺部疾病可同样对肠道菌群产生影响。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肺炎小鼠的研究发现,MARS能够诱导小鼠肠细胞线粒体中促凋亡蛋白Bid、Bax和抗凋亡蛋白Bcl-xL的表达上调以及受体介导途径中Fas配体增加,从而导致小鼠肠细胞凋亡以及肠道菌群组成发生改变[24]。因此,肠道菌群与呼吸道菌群可调节黏膜免疫应答,且二者细菌代谢产生的小分子代谢物彼此互相影响。肠道和肺脏的黏膜不仅具有独立的系统功能,还可共享免疫监视和形成宿主免疫反应。
4 肠道菌群与肺部疾病
4.1 肠道菌群与支气管哮喘 支气管哮喘是呼吸系统的常见疾病,主要症状是发作性的喘息、气急、胸闷、咳嗽等。其发病与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T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气道上皮细胞等多种细胞和细胞组分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有关,这种慢性炎症可导致气道高反应性。哮喘患者的呼吸道微生物群和肠道微生物群均会发生变化。婴儿早期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减少与儿童哮喘表型存在密切关系[25]。既往多项研究发现,早期抗生素暴露导致肠道菌群数量和结构的改变会使支气管哮喘等变应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增加[26-27]。近期一项研究发现,孕期使用抗生素与子代哮喘严重程度呈剂量依赖关系。怀孕期间母亲使用万古霉素会在几个不同的时间点引起母亲和子代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显著变化。子代哮喘严重程度与肠道菌群的改变和盲肠SCFAs浓度的降低明显相关[28]。以上研究表明,肠道菌群生态失衡与哮喘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调节肠道菌群生态平衡或许有助于哮喘的治疗。Sagar等[29]的研究发现,鼠李糖乳杆菌可通过调节Toll样受体、NOD样(NLRs)受体、细胞因子和T细胞转录因子的表达抑制气道炎症、肥大细胞脱颗粒、T细胞活化及气道重塑,从而降低慢性哮喘小鼠的肺阻力;短双歧杆菌可通过诱导肺组织中Foxp3和IL-10的表达上调抑制哮喘发生。在小鼠哮喘模型中,致敏前补充鼠李糖乳杆菌或乳酸双歧杆菌可诱导肠系膜淋巴结中分泌TGF-β的CD4+/CD3+T细胞数量增加以及支气管周围淋巴结中Foxp3的表达上调,从而抑制过敏原诱导的致敏反应[30]。
4.2 肠道菌群与肺部感染性疾病 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影响和调节共同黏膜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和功能,对机体抵抗病原体入侵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通过对黏附位点和营养物质的竞争以及合成某些抗菌肽构成竞争抑制效应保护宿主免受病原体的侵害;另一方面可以合成SCFAs、吲哚衍生物等活性物质调节机体免疫反应。更重要的是,肠道菌群能够激活人体内的自然杀伤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产生大量免疫因子,刺激肠道内免疫细胞产生多种免疫球蛋白参与维持正常黏膜免疫。呼吸系统急性炎症在影响呼吸道菌群平衡的同时也会对肠道菌群产生重要影响。Sze等[20]研究LPS与PBS灌肺诱导的小鼠肺脏急性炎症模型发现,灌注24 h后小鼠盲肠细菌总数明显增加(P<0.05)。而正常小鼠接受抗生素处理后,其肺部病毒负荷、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数量也会明显增加[31]。抗生素是治疗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的基础用药,然而抗生素在治疗肺部感染性疾病的同时也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Rosa等[32]的研究发现,万古霉素治疗急性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小鼠可诱导肠道菌群失调,导致小鼠肠道中变形杆菌数量增多、拟杆菌数量减少,肠道出现炎症性改变。给予粪便菌群移植后,小鼠的易感表型和组织损伤表型能够逆转。既往研究发现,长双歧杆菌可通过激活TLR信号通路,诱导肺泡内巨噬细胞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ROS)生成增加,有助于减轻肺部病原体感染引起的炎症反应[33]。此外,双歧杆菌能够通过调节小鼠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反应,平衡Th1/Th2免疫反应,增强小鼠抗H1N1病毒的能力[34]。因此,肺脏的急性炎症会影响肠道菌群生态的稳定,而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有助于保护肺脏免受病原体的侵害。
4.3 肠道菌群与COPD COPD是一种具有气流阻塞特征的慢性支气管炎和(或)肺气肿,可进一步发展为肺心病和呼吸衰竭。COPD患者病情进展不仅与肺部菌群相关,与肠道菌群亦具有密切关系[35]。 肠道菌群微生态失衡主要是指肠道菌群的数量和比例失调,表现为G+杆菌相对G-杆菌减少,这种变化对COPD的病理改变及病情进展具有重要影响。肠道潜在的致病菌增多,显著增加了细菌移位导致COPD急性加重的频率。此外,G-杆菌增多致使肠源性内毒素释放增加,可对肺脏造成间接损伤,加快COPD病情进展。肠道菌群可代谢胆碱和磷脂酰胆碱生成三甲胺(TMA),TMA吸收入血后经肝脏黄素单加氧酶(FMO)催化氧化生成氧化三甲胺(TMAO)。研究发现,循环TMAO水平与COPD患者的长期全因死亡率相关,6年全因死亡率约为55.6%[36]。与健康者相比,COPD患者的体育活动相关代谢需求的增加导致肠灌注减少,从而造成肠组织缺血。肠黏膜上皮对缺氧极为敏感,机体缺氧早期即会出现肠黏膜损伤以及黏膜屏障功能障碍。进行液体复苏后,肠道发生缺血再灌注损伤,黏膜屏障功能进一步破坏,肠道内毒性物质通过门静脉途径和(或)淋巴途径导致远隔脏器损伤,而在此过程中,肺脏通常是最先受累的器官[37]。此外,肠道完整性损伤可能与COPD相关的胃肠道病变相关。一项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发现,COPD患者患克罗恩病的风险是健康对照组的2.72倍,COPD和IBD可能有共同的炎症途径,包括诱发疾病的基因变异等[38]。 因此,研究肠-肺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临床从整体把握疾病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新思路。
4.4 肠道菌群与肺癌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治疗包括非小细胞肺癌在内的恶性肿瘤显示出较好的疗效,但仍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对免疫治疗无响应。来自芝加哥大学Gajewski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招募的42例接受抗PD-1单抗或抗CTLA-4单抗治疗的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中,仅16例对免疫治疗有响应。治疗前对患者肠道菌群进行分析发现,对免疫治疗有响应的患者体内富含肠球菌(Enterococcus faecium)、产气柯林斯菌(Collinsella aerofaciens)、青春双岐杆菌(Bifidobacterium adolescentis)、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小韦荣球菌(Veillonella parvula)、粪副拟杆菌(Parabacteroides merdae)、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 species)和长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longum)等8个菌种,而对免疫治疗无响应的患者肠道内则富集卵瘤胃球菌(Ruminococcus obeum)和罗斯拜瑞氏菌(Roseburia intestinalis)。为进一步探讨肠道菌群对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影响,研究人员将对免疫治疗有响应和无响应患者的粪便分别移植到无菌黑色素瘤小鼠模型体内,结果显示,移植了对免疫治疗无响应患者粪便的小鼠体内肿瘤生长更快,给予抗PD-1或PD-L1单抗治疗后,移植了对免疫治疗无响应患者粪便的小鼠治疗效果更差[39]。说明肠道菌群不仅能够影响肿瘤的生物学行为,还能够影响抗肿瘤药物的疗效。有研究报道,肠道内G-杆菌产生的LPS可通过诱导炎症反应促进黑色素瘤发生肺转移,而维持肠道菌群生态系统的稳定可有效抑制肿瘤转移[40]。此外,Routy等[41]的研究发现,在抗肿瘤治疗期间服用抗生素会降低免疫治疗的疗效。相比总体人群,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明显缩短(P<0.05)。这与抗生素诱导肠道菌群失调导致晚期肿瘤患者接受免疫治疗的临床获益降低有关。因此,由肠道菌群衍生的粪菌疗法(cancer fecal microbiota therpy,CFMT)可能用于肿瘤的辅助 治疗。
4.5 肠道菌群与肺结核、急性肺损伤、呼吸窘迫综合征等 肠道微生物成分作为配体作用于免疫细胞上的各种模式识别受体(PRRs),从而调节宿主的免疫反应。树突细胞(DC)在机体抗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b)的免疫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对维持由Mincle介导的针对Mtb的DC依赖性肺免疫应答至关重要,而抗生素诱导肠道菌群失调可中断该过程,从而导致T细胞参与的免疫反应受损,增加机体对Mtb的易感性[42]。此外,肠道菌群代谢产物IPA在体外和体内均显示出有效抵抗Mtb的作用,Mtb感染后的疾病严重程度也与肠道微生物组明显相关[43]。抗生素是治疗肺部疾病的常用药物,对肠道微生态平衡影响甚大。肠道微生态失衡可导致肠道细菌多样性减少、致病性菌群增加、SCFAs生成减少、黏膜屏障破坏、肠源性感染、炎性介质大量释放,以及肠道营养吸收障碍等,这与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肺部疾病的病情进展及转归具有密切关系[44]。
5 益生菌在肺部疾病中的应用
肠道菌群微生态失调与肺部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通过补充益生菌维持肠道菌群平衡或有助于肺部疾病的临床管理。补充益生菌是指给予一定数量的、能够对宿主健康产生有益作用的活的微生物,如双歧杆菌、乳酸菌、肠球菌等。与肠道菌群相同,益生菌不仅在胃肠道发挥免疫作用,还可影响全身免疫系统,发挥抗炎、抗菌、抗毒素等作用。既往相关研究发现,益生菌能够通过诱导产生调节性T细胞,降低过敏原特异性IgE和Th2细胞因子分泌,减轻靶器官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和过敏性炎症反应,从而改善过敏表现[45]。给小鼠喂食加氏乳杆菌SBT2055可诱导其体内抗病毒基因Mx1、Oas1a的表达,通过抑制病毒复制对抗呼吸道流感病毒的感染[46]。此外,摄入益生菌还可减少呼吸机相关肺炎的发生[47],但也有系统回顾性研究报道,没有证实或排除补充益生菌对哮喘以及临床危重患者的有益作用[48-49]。因此,益生菌治疗肺部相关疾病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综上所述,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变化与肺部疾病密切相关。肠道菌群在肺部免疫稳态的建立和维持中起重要作用:一方面可通过菌群代谢物实现,这些代谢物在结肠产生,通过血液循环到达肺脏,在肺脏发挥抗炎作用;另一方面菌群刺激肠道黏膜免疫反应,通过共同黏膜免疫系统影响呼吸道功能。此外,肠道细菌还可直接迁徙到呼吸道作用于呼吸道黏膜免疫细胞,从而促进肺组织内免疫细胞的分化成熟。近年来,“肠-肺”轴在呼吸系统疾病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但目前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其分子通路、效应介质及机制。然而重要的是,“肠-肺”轴为肠道微生物群的研究以及益生菌用于肺部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