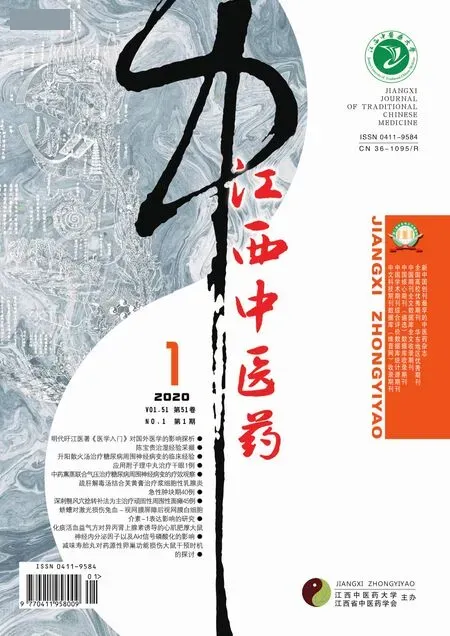陈宝贵治湿经验采撷*
★ 刘佩瑶 续海啸 陈宝贵(1.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300193;.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武清中医医院 天津 301700)
1 湿邪致病理论
湿邪致病,首载于《五十二病方·婴儿索痉》[1]:“索痉者,如产时居湿地久。” 是病当指小儿风痉,即现代医学中的小儿破伤风,病由出生时久居湿地,症见口唇紧闭、肌肉强直、筋脉挛缩而难以伸展[2]。《黄帝内经》则详论湿病:“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湿盛则濡泻。”“湿伤肉,风胜湿。”“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等。《黄帝内经》论湿多从病因病机阐发:湿为六淫之一,易致痿证、咳嗽、腹泻、水肿等病[3],治疗上主论针刺疗法。而药物施治则详论于《伤寒杂病论》。张仲景论湿辨证施治,扩充病种;周于寒湿,略于湿热。湿热理论在金元时期得以扩充,具有代表性的有刘完素的“湿自热生”,李杲的“脾胃元气虚损,湿热内生”,朱丹溪的“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丹溪提倡三焦分治,创立二妙散,并善治痰证[4]。及至明清时期,理论趋于完善,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湿证》系统论述湿病,叶天士提出“外邪入里,里湿为合”,薛雪著湿热病专著《湿热条辨》,吴鞠通、王士雄则在叶、薛基础上系统总结湿病,完善三焦辨治。
2 湿邪致病特点
湿邪言其来路,分外湿和内湿。外湿与气候、地域密切相关,长夏季节和江南、沿海地区易滋生湿邪;饮食失宜,脏腑功能失调,津液代谢障碍,内湿由生。二者病因虽迥然不同,但常相召相引,相兼而发[5]。内湿素盛之体,易感外湿;而外湿伤脾,脾失健运,亦可滋生内湿。陈宝贵教授认为,湿邪具有隐匿、黏滞、重浊、趋下之性[6]。隐匿——湿邪伏于机体,常积久而发。沈芊绿《杂病源流犀烛》:“湿病之因,其熏袭乎人,多有不觉。”故很多患者就诊时不能准确说出自己何时起病。黏滞——症状黏滞不爽,病程缠绵难愈。吴鞠通《温病条辨》:“其性氤氲黏腻,非若寒邪之一汗而解,温热之一凉即退,故难速已。”重浊——重指患者沉重及附着的主观感受,如四肢酸沉、头重如裹等;浊指分泌物、排泄物污浊的客观体征,如面垢、溺浊、便溏等[7]。趋下——湿邪易袭人体下部。《素问·太阴阳明论》:“伤于湿者,下先受之。”陈宝贵教授认为,湿邪较少单独致病,常随环境气候、先天禀赋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兼化:寒冬随冰坼而化寒,炎夏又随暑温而化热;《温热论》认为“阳旺之躯,胃湿恒多;阴盛之体,脾湿亦不少”,前者湿邪多从热化,留恋阳明胃,后者多从寒化,归于太阴脾[8]。
3 临证治疗特色
陈宝贵教授治湿强调从整体出发,抓主症、辨舌脉、定处方。陈教授认为,湿病的病机关键为脾虚。《医宗必读》:“脾土强者,自能胜湿……若土虚不能制湿,则风寒与热,皆得干之而为病。”然湿病又不单纯与脾一脏有关,关于津液代谢,《素问·经脉别论篇》中有较为系统地论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津液代谢与肺、脾、肾三脏关系密切,亦有赖于肝主疏泄、三焦通畅等。五脏六腑功能协调,津液方能正常生成、输布与代谢,湿亦无由而生。治疗上,陈教授主张协调脏腑功能,临证常针对不同病机施以不同治法,或宣肺健脾,或疏肝调脾,或脾肾双补,以取“正本清源”之意。临证喜用风药,善用芳香药。因风能胜湿,此乃木能克土,五行相克之理;又风性辛散升浮,功能健脾升清;又秉肝木之性,兼疏肝解郁。临证常用防风、葛根、柴胡、升麻等。然风药性多辛燥,不宜久服,多为佐使,久服恐耗气伤阴。芳香药功擅醒脾开胃、化湿去浊、行气活血,临证常用藿香、沉香、郁金、佛手等。
4 验案举隅
4.1 湿犯上焦案 张某,男,35岁。2017年4月15日初诊。症见咳嗽痰多,痰白清稀,晨起为甚。患者体胖,平素嗜食肥甘,寐可,便溏。舌淡,苔白腻,脉滑。处方:半夏10g,陈皮10g,茯苓15g,厚朴10g,苍术10g,砂仁6g,细辛3g,甘草6g。7剂。水煎服。嘱戒肥甘。2017年4月22日二诊:咳减,便溏改善。续服7剂。后随访,告知病愈。
按:此病证属“脾虚湿盛,痰湿蕴肺”,治以“健脾除湿,理肺化痰”。《医述》曰:“人之病痰者,十有八九。”脾胃为气机升降要道、气血生化之源。患者体胖,平素嗜食肥甘,积久脾运不健,水谷不能化为精微上输以养肺,反而聚生痰浊,上干于肺,肺气不宣,发为是证。《医宗必读·痰饮》中“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即此意也。方用二陈平胃散加减,肺脾同治。二陈平胃散出自《症因脉治》,功擅宽中行气、化痰止咳,合用砂仁芳香醒脾、斡旋气机,杜“生痰之源”;由患者舌脉和痰液性质得出病未化热,仍属单纯的痰湿,配伍细辛温肺散寒,疗“贮痰之器”。《本草经疏》:“细辛,风药也。风性升,升则上行,辛则横走,温则发散,故主咳逆。” 全方配伍精当、药少力专,配以膳食调养,待脾气复旺,余邪自去。
4.2 湿阻中焦案 王某,女,61岁。2016年8月8日初诊。症见胃脘胀满不适,恶食生冷、油腻,食后恶心,口黏、口干,平素情志不舒,纳呆,寐可,二便调。舌淡红,边有齿痕,脉滑稍弦。2016年5月14日胃镜示:慢性浅表性胃炎,胃底小息肉。处方:党参20g,砂仁10g,陈皮10g,清半夏10g,佛手10g,香橼10g,茯苓20g,焦三仙各10g,鸡内金10g,荷叶20g,沉香5g,郁金10g,莪术10g,甘草10g。7剂。水煎服。2016年8月15日二诊:胃脘不适减轻,口中乏味,纳呆,久坐后头晕,双眼模糊,寐安,二便调。舌暗红,苔白腻,脉弦细。守上方,党参改为30g,加连翘15g。14剂。水煎服。2016年8月29日三诊:纳食改善。续服7剂。
按:肝主疏泄,调畅气机,喜条达而恶抑郁[9]。患者情志不遂,肝失疏泄,乘脾犯胃,中焦虚损,纳运失司,升降失常,生湿夹积,证属虚实夹杂。湿壅中焦,土为湿困,致纳呆、恶心;口黏——脾开窍于口,脾虚生湿,上泛于口,导致口中黏腻不爽,恰与“湿性黏滞”相扣;口干——脾气不升,津不上承,其津液并非缺乏,而是并未布散至应至之处;痞满——胃气不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浊气在上,则生胀。”结合患者症舌脉,辨为“肝郁脾虚,气滞湿阻”,治以“疏肝健脾,理气除湿”。处方由陈师经验方化裁而来。方中党参健脾益气,荷叶升举清阳,沉香芳香醒脾、调畅气机、兼以化浊,三药相合,裨益正气,治病求本;砂仁、二陈、佛手、香橼调补中焦,理气化湿,补而不滞;焦三仙、鸡内金宽中健脾、消食导滞;同科植物不同部位的郁金、莪术,功擅行气解郁、消积化瘀;方中沉香、郁金是陈教授疏肝解郁的常用药对,临证配比1∶2或1∶1。二诊时患者口中乏味、头晕、目糊,皆为清阳不升、清窍失养之象,党参加量以健脾,溯本求源;舌暗提示体内有瘀,加用连翘“散诸经血凝气聚”。此案陈师紧扣“肝郁脾虚”之病机本质,强调疏肝以调脾,重视脏腑生理功能;又因湿性黏滞,阻滞气机,临证提倡调气以治湿,气行则水行。
4.3 湿注下焦案 付某,男,35岁。2016年5月16日初诊。症见小便频数、溺道涩痛反复发作4年,昼1~2小时1行,夜1行,余沥不尽,尿色黄,小腹拘急引痛,早泄,胃脘灼热,下午尤甚,后背畏风、不畏寒,平素嗜酒,急躁易怒,纳可,多梦。舌暗苔腻,脉滑数。处方:葛根30g,泽泻15g,车前子30g,猫须草20g,金钱草30g,女贞子15g,旱莲草15g,琥珀3g冲服,甘草10g,沉香10g,鹿角片20g先煎。7剂。水煎服。嘱戒酒。2016年5月23日二诊:溺痛愈,仍尿频,少腹不适,多梦。舌红,苔薄黄,边有齿痕,脉数。守原方,加延胡索10g、川楝子10g、仙灵脾15g。14剂。水煎服。2016年6月13日三诊:诸症减,舌暗红,苔黄厚,脉弦滑。守上方,加黄柏10g、黄连10g。7剂。水煎服。
按:患者以尿频、尿痛来诊,当辨为淋证。《诸病源候论》:“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 陈师认为,此病以肾虚为本、膀胱热为标,临床多见虚实夹杂证[9]。《证治准绳》:“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水下涩,数而且涩,则淋沥不宣,故谓之淋。”患者平素性急、嗜酒,土德不及,湿动于中,久酿湿热,下注膀胱,肾与膀胱气化不利,发为是证[9]。治以“补肾,清热通淋”。重用葛根主解酒毒,升阳除湿,亦通利太阳膀胱;泽泻、车前子、猫须草、金钱草利尿通淋、分利湿热,因势利导,“其下者,引而竭之”;肾主水、司开阖,方中二至丸、鹿角片补肾求本,调燮阴阳;《本草备要》:“凡渗药皆上行而后下降,故能治五淋。” 渗药琥珀甘淡上行,使肺气下降而通膀胱,与津液代谢中“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之生理功能相契;沉香调气以化湿,暖精又助阳;甘草调和诸药。二诊少腹不适,加延胡索、川楝子,为金铃子散组成,该方出自《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功擅疏肝利气、活血散瘀、气血同调;仍尿频,加仙灵脾入肝肾、补命门。三诊苔黄厚,加黄连、黄柏清泄中下二焦湿热,巩固疗效。全方用药考究,紧扣病机,标本同治,切中肯綮。
5 经验小结
湿病作为临证常见病,其辨治巧妙多变,不可拘泥一法。陈教授认为,治湿不应单纯地针对病邪,一味地或燥、或化、或渗,此举只能治其标,对于脏腑功能失调所致湿者,非但不能治本,更是用药之戒[10]。治疗上应从整体出发,重视肺脾肾等脏功能的协调,谨守病机、各司其属。陈教授还提出,治湿应注重调摄,即在药物施治的同时结合食疗、养生等非药物疗法: 节饮食、畅情志、酌起居,以竟全功。陈教授这种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值得吾等后辈努力学习、研精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