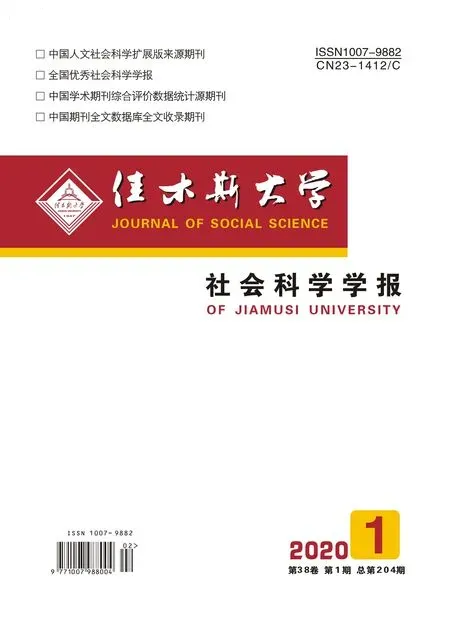探究《我弥留之际》中的奥德赛之旅*
姚小娟
(东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000)
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暨美国南方文学泰斗威廉·福克纳毕生致力于书写与探究人的内心冲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福克纳的杰作亦弥漫着人类精神的异化与孤独。1930年,福克纳发表了他的第二部杰作《我弥留之际》,小说神话原型来自荷马创作的史诗《奥德赛》。小说讲述了美国南方农民本德仑一家为了将刚逝的本德仑夫人的遗体送往家乡安葬的艰苦而又荒诞的十天旅程。故事由15位叙述者所进行的59次内心独白构成,采用了诸多令人称道的现代派艺术手法(如内心独白、意识流、多视角叙述、时序颠倒、闪回和倒叙等),被评论家称为“最复杂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小说之一”[1]278,同时也被众多电影人士认为不可能电影化的小说。然而,2013年, 美国著名演员兼导演詹姆斯·弗兰科不惧压力对《我弥留之际》进行了改编并最终搬上了荧幕。为了原汁原味地保留小说的艺术形式并突显小说深刻的主题,弗兰科采用多种电影技巧(如分屏、黑屏、独白、多种镜头)来重现小说艺术形式和强化小说主题。《纽约时报》称赞道“冲进一般‘明智’的人会畏惧避开的领域,弗兰科先生取得了一次严肃而有价值的成功。《我弥留之际》是一部绝对有野心的电影,但同时带着令人钦佩的谦逊”[2]。因其深刻的主题和特殊的电影技巧,电影《我弥留之际》最终获得了第66届戛纳电影节关注大奖提名。
福克纳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者和传统的南方道德家,他关注人类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在小说《我弥留之际》中,他探讨了人类精神的死亡、人类的孤立和异化、生存的虚无、南方道德的堕落和人性的沦丧等主题。在电影《我弥留之际》中,导演弗兰科为给这部晦涩的名著注入更多的生命力,通过采用时空交错式的电影结构和其它重要的电影技巧,成功地演绎了一部美国普通穷白人经历死亡、生存、道德堕落、人性丧失、人生毁灭的奥德赛之旅,从而让更多的观众对这部文学经典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一、死亡之旅
《我弥留之际》的故事发生在一战后的美国南方农村山区。一战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绝望、焦虑、抑郁、荒谬及死亡。著名评论家沃尔普强调小说《我弥留之际》的“主题是死亡,其中心意象为一具死尸”[1]281。导演弗兰科在电影中更是将死亡渲染到了极致:电影以全黑图像中弥留之际的女主人公艾迪自白开幕“我父亲总是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为死后的长眠作准备”;电影中不断出现的黑屏提示着观众死亡的阴影;电影中昏暗不明的光线处理亦是象征着死亡的来临以及无处不在。死亡意象也贯穿电影始终:母亲临终前,大儿子卡什在垂死的母亲窗前敲木锯木做棺材的呱哧呱哧声音充溢着电影的开端预示着真正死亡的临近;痴傻小儿子瓦德曼所带回的那条大鱼在泥地里的挣扎也即是母亲死前的抗争;被剁得七零八碎的盘中鱼不仅仅象征着女主人公艾迪·本德仑的死亡,而且也预示着家人在她死后所要面临的分崩离析;始终盘旋在空中的秃鹰亦使电影充溢着尸体的腐臭味。
不论作家福克纳还是导演弗兰科所表达的死亡决不只是女主人公艾迪个人肉体的死亡,也包括她精神的死亡。婚前,作为一位教师,她并不爱自己的学生,相反,她恨不得拿鞭子抽打孩子们。与安斯结婚也只是因为无法忍受令人窒息的孤独。婚后,她认为“生孩子是结婚的报应”,一度想宰了自己的丈夫。而且生完孩子后,她就开始为死亡做准备,从未给六个孩子仁慈的母爱。在全剧高潮片断中,家人带着她的死尸与洪水拼搏,遭遇灾难之际,导演将家人在洪水中挣扎的镜头与艾迪的画外音同时并存,一边是洪水肆虐本德仑家的孩子们在洪水中拼命护住她的棺材,另一边却是艾迪对孩子和丈夫爱无能的表述以及对牧师的迷恋。分屏的镜头展示让观众更深层地体验到了艾迪精神死亡的过程,同时更强烈地感受到了本德仑家人分崩离析的状态。
福克纳是一位传统的道德家,他在小说中还痛斥了南北战争后南方传统价值观的逐渐衰亡。导演弗兰科在电影中亦向观众传达了南方价值观沦丧的现实。本来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美好的美国南方在影片中荡然无存,观众所看到的南方在导演的镜头下却只是单调的灰色和褐色再加上些许的绿色,一派萧条、了无生机。南北内战前,家族是美国南方的中心,“家族是最能表现南方文化的机构”[3]112,然而在电影中所看到的家族却让人触目惊心:儿女仇恨父母、夫妻形同仇人、手足相惨。艾迪·本德仑仇恨自己的父亲,想宰杀自己的丈夫,安斯·本德仑冷漠无情根本不顾儿女的死活,本德仑兄弟姐妹间互相隔阂仇恨。家族道德伦理的丧失即是南方伦理价值观消亡的写照。
二、虚无之旅
伴随着南北战争中南方的失败,南方人引以为傲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也随之坍塌,南方人纷纷陷入虚无与异化的精神荒漠。福克纳在《我弥留之际》中着重刻画了南方人荒诞的生存状态:冷漠、孤独、自暴自弃、异化等。为了突出现代人的隔离与异化生存状态,福克采用了诸多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如意识流、多视角、时序交错等。作为福克纳作品的忠实读者,导演弗兰科在影片《我弥留之际》中为了突出人类的封闭状态以及精神上的孤立和异化,采用了分割画面、独白以及时空交错式结构等多种现代派电影技巧。首先,分割画面或分屏的采用可以营造一种隔离感,“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动作被框定在各自的窗格中,因此即使不同的人物在画面中的物理距离十分贴近,他们仍因画框的阻隔无法分享彼此的心灵空间,处于一种彼此隔绝的状态”[4],因此,这种隔绝感正好印证了《我弥留之际》中异化的主题。其次,面对镜头的独白以及大量的画外音也与小说意识流的艺术手法相吻合,同时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隔阂以及情感的冷漠。再次,时空交错式结构的“主要特点是根据剧中人的心理状态、情绪变化,将过去、现在、将来交错进行叙述,突出主观意识和内心剖视”[5]152。导演采用时空交错式结构与福克纳采用的多视角叙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强调了人物的内心审视,更增强了弥漫于电影中的孤独感和异化感。
电影中,本德仑一家荒诞又艰难的送葬过程也是人类精神逐渐陷入异化与虚无的奥德赛之旅。首先,这场旅程的缘由是恶意报复。女主人公艾迪由于感觉受到了丈夫安斯的欺骗而设计报复,提出要求自己死后运回自己的家乡杰弗逊安葬,所以十天的送葬旅程是毫无意义的。女主人公艾迪深受父亲虚无思想的荼毒,她眼中没有上帝,疏离自己的孩子们,迷失在自己的孤独世界中,认为自己的人生只是为死做准备。本德仑家的孩子们也各自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性格乖张,体验着虚无的人生,尤其是二儿子达尔。达尔·本德仑本是本德仑家最有知识、最有思想的人,他参加过第一世界大战,去过法国,比其他人更有见识,他爱思考、敏于观察。但是由于生来就被母亲拒绝,成长中一直受到母亲的排斥,而且长期以来得不到双亲的爱和家人的关心,他逐渐变得孤立。事实上,前往杰弗逊的旅程对于他而言本是打开心扉获取家人温暖的旅程,他深受着自己的母亲,渴望得到母亲的爱,所以电影中他时刻关注着自己母亲的生存状态,但母亲始终关注的是三儿子珠尔。达尔生性敏感,感知家人的精神异化:杜威的未婚先孕、母亲的婚外情、珠尔的私生子身份等等。他渴望与家人沟通交流,但“在一个冷漠孤独的异化世界,他的努力只能以悲剧收场”[6]64。他深知送葬旅程的无意义,旅程伊始,他用尖利的笑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随着尸体的腐烂发臭,为了阻止全家人荒谬的旅程,他纵火烧了棺材却烧毁了好心人的谷仓,他的做法遭到了严重的误解,最终被家人当成疯子送到了精神病院,而最后达尔也正式陷入了无尽的疯癫。本德仑一家的旅行给观众带来的却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7]18的体验。
三、堕落之旅
美国内战之后,随着北方工业对南方的入侵,为数众多的南方人逐渐成为金钱的奴隶。福克纳痛心于南方传统道德的崩溃和人性的沦丧,在他的诸多作品中对道德和人性的堕落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在《我弥留之际》中,福克纳借本德仑一家十天的旅程向读者展开了一幅南方现代社会道德堕落的画卷。弗兰科在电影中更是选取了精华片段和经典语句向观众展示了一帧帧南方道德堕落缩影。为了实现本德仑夫人生前的遗愿,本德仑一家踏上了前往杰弗逊的送葬旅程,但其实一家人各自心怀鬼胎,想借送葬的机会进城办自己的私事:丈夫安斯为了去镇上装副假牙,大儿子卡什想得到一部留声机,女儿杜威·德尔要买打胎药,最小的痴傻儿子瓦德曼希望能买到商店里为庆祝圣诞节的玩具小火车,因此,通过本德仑一家的故事,导演向观众昭示了传统的南方伦理道德已然丧失。
安斯·本德仑身上体现了福克纳头号反面人物的典型特征,他懒惰吝啬、自私自利、冷酷无情,南方农民的美好品德在他身上全然丧失。为了拒绝劳动,他谎称自己出汗就会死,但却让孩子们拼死拼活的干活;为了付医生诊费、有钱装幅假牙,在妻子临终之时让孩子们(二儿子达尔和三儿子珠尔)拉货去挣三块钱,最后,孩子们没能见到临终的母亲;面对生病的妻子,他一直捱到妻子弥留之际才请医生,面对医生的责备,他却冷酷的说道“她反正是要去的,不是吗?”妻子刚过世,安斯便刮了胡子,穿上礼拜天才穿的衣服,还显得有点儿高兴,因为他终于可以去城里装假牙了;在大儿子卡什腿断后,为了省钱不看医生,他甚至用水泥固定卡什的断腿;在达尔纵发烧谷仓时,为了逃避赔偿,他将达尔视为精神病,让人将孩子绑送到了精神病院;当他发现女儿杜威·德尔用来打胎的10块钱时,他拼命抢了过来,还骂孩子不念自己的养育之恩;在安葬完妻子的第二天,他便装上了假牙并领回来一位新的本德仑夫人。因此,通过前往杰弗逊的送葬旅程,弗兰科向观众呈现了一帧帧人性堕落的画面,“暴露了本德仑这个没有爱、没有传统精神的家庭的脆弱,提示了这家人在灾难中道德堕落、人性沦丧的悲剧”[8]7。
四、毁灭之旅
《我弥留之际》可以算是一部历险记,但并没有奥德赛的英雄壮举,而是本德仑一家人“集体的堂吉诃德式的历险闹剧”[8]7。严肃的电影画面以及演员们精湛的演绎使得电影成为一部反讽的寓言。随着母亲本德仑夫人的去世,本德仑家人赖以维系的传统支柱坍塌,在前往杰弗逊的旅程中 “‘疯狂和毁灭的威胁’总是如影相随”[9]241。一路上,他们长途跋涉,遭遇暴风雨洪水,过河的桥梁被淹没,他们试图绕道从滩地过河,但奈何洪水肆虐,拉车的两头骡子淹死,车子翻倒,棺材差点被水冲走,尸体被水浸泡,大儿子卡什摔断了腿,为了有牲口拉车再次上路,三儿子珠尔失去了视为母亲的马,一家人带着发臭的尸体再次上路,行程中忍受着邻居和路人的白眼、指点和咒骂,还有如影随形的秃鹰困扰,甚至还遭到警察的出面干扰,但这家人还是未停止疯狂的举动,结果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为了结束这荒唐的旅程,二儿子纵火烧棺材但却烧毁了他人的谷仓,最终使自己被家人视为疯子而绑送到了精神病院。历时十天的旅程并没能给本德仑家人带来新生也未能解决他们的困境,反而让他们各自遭到了毁灭的灾难:大儿子卡什断腿后家人用水泥固定,请兽医治疗,最后溃烂疽坏失去了一条腿;二儿子达尔失去了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历时5月每晚为人收拾新地)而挣得的花斑马(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东西,他视为母亲的马);渴望得到关爱与人交流的三儿子珠尔最终被人当作疯子关进了疯人院;女儿杜威·德尔本想借这次旅程买药打胎,但药没买到还遭到药店伙计的欺骗凌侮,钱也被父亲抢走,最终可能会未婚生子,而遭到乡邻的鄙夷和耻笑;痴傻的小儿子瓦德曼也希望在旅行中买到心爱的小火车,但最后连到商场橱柜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得到。电影中珠尔得知马被抵押时万念俱灰的背影,卡什腿坏疽而被锯掉时的痛苦唉嚎,达尔被家人当作疯子死死按在地上要送往疯人院时发出的尖利笑声,杜威·德尔被药店伙计奸污时如同死尸般的表情,所有这些画面同最后一幕(焕然一新装上亮白假牙的父亲安斯带着抱着留声机的新本德人仑夫人一同出现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给观众带来了更加强烈的视觉和心灵的冲击。
五、结语
导演弗兰科改编的电影《我弥留之际》以影像的方式成功的呈现了福克纳的文风,而且采用多种现代派的电影技巧来表达小说的技巧和深化小说的主题,通过本德仑一家人的送葬旅程隐喻了现代人精神湮灭,传统价值坍塌的现实,采用分屏和旁白的电影手法强化了送葬之行的虚无以及南方人的异化和孤独,同时也表明传统价值丧失后道德的堕落和人性的沦丧,以及因此带来的毁灭和疯癫,向观众展示了人世的苦难。电影《我弥留之际》成功地让观众经历了一场死亡、虚无、堕落和毁灭的精神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