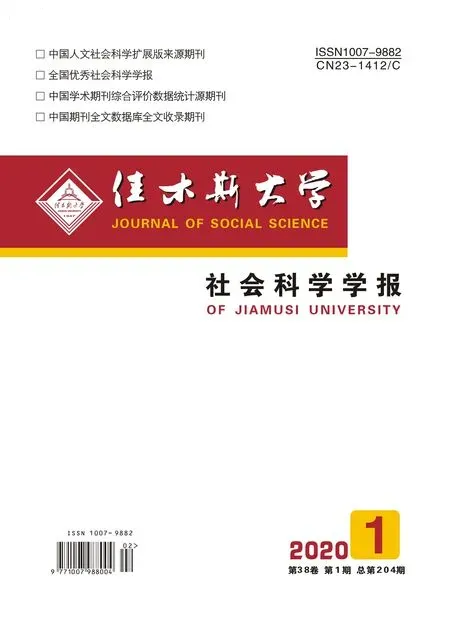论“五四”乡土小说的情怀*
杨 筱
(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五四”文学发展到今天,已有百年历史之久,然而时至今日它仍保持着迷人的魅力,兼备着现代文学发展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学术界一直保持着高度重视。特别是其作为现当代乡土小说的开端,时常吸引着人们对其进行探源般地探索:“五四”乡土小说究竟具有怎样的吸引力?和当代乡土小说相比,它究竟具有怎样的情怀与情感寄托?本文试图从“五四”乡土小说的情怀出发,来探析其深层的精神指向,对“五四”乡土小说的发生、发展及其相关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以期在细微方面丰富对于“五四”乡土小说的研究。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掀起了一场场革新,不仅有着“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宣传,更是提倡白话、新诗,并将小说这一边缘化的文学体式推向文学革命的前线。鲁迅于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上的《狂人日记》是我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之后鲁迅又发表了《孔乙己》《药》《兄弟》《明天》《一件小事》《风波》《故乡》等作品,将审视中国的眼光汇聚在知识分子与农民身上。鲁迅之所以以农民的精神状态为着眼点,将“乡土”作为载体,正是其清醒却又犹疑的选择,鲁迅曾在《狂人日记》自序中将整个社会环境比作“铁屋子”,而人们在其中熟睡并不感到死的悲哀,他对国人死水一般的精神状态感到失望甚至绝望,内心深处却又希翼能毁坏这铁屋子,终于在朋友劝说下执笔创作小说。从本质上来说,鲁迅的乡土小说正是其矛盾的思想与情感在文学形态上的反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从人员上来说,“五四”乡土小说是以鲁迅为代表并且在其影响下诞生的小说创作群体,鲁迅不仅是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同时开创了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先河,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王鲁彦、蹇先艾、彭家煌、许杰、许钦文、戴锦明等一批令人瞩目的“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尽管“五四”乡土小说的诞生稍晚于“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但在创作上具有鲜明的“五四”反封建、反传统的特征,仍属于“五四”文学思想体系之内。这些乡土小说作家们将创作视角伸向广阔的农村生活,密切关注乡风民俗与农民的精神状态,他们所开辟的乡土艺术世界,处处彰显着“五四”乡土小说的独特情怀,不仅囊括着爱国主义情怀生发下的启蒙与革命的历史任务与状态、知识分子为人生的文学写作态度,还包含小农经济传统影响下乡土情怀的自然呈现:“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理论的宣传以及文本对象的自然下移。
一、爱国主义情怀:启蒙与革命
今天我们所说的“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可以说是我们对于“五四”思潮的总结与界定。然而,在鸦片战争或者说闭关锁国被打破以前,国人对于国家这一概念没有明确的认识,正如梁启超所言:“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其不知爱国者,由不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 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 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今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必对于他国,然后知爱吾国。”[1]66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遭遇西方的侵略,并节节败退,使得以我国为中心的世界观逐渐瓦解,才睁眼看世界,产生对于国家民族的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促进思想解放,促进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所以,对于“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来说,爱国主义情怀的滋生与探索救国之路的行动便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对于“五四”知识分子来说,以往救国的经验启示他们思想解放是第一步,所以文学便成为启蒙与革命的载体,是爱国主义情怀的承担与寄托,陈独秀、胡适等发动的文学革命,其根本目的也在于“救国”。鲁迅在经历了1906年的仙台幻灯片事件之后弃医从文,并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417于是,便开始了文艺救国的道路。
也正是鲁迅的乡土小说,开始了对于国民性的冷静审视,阿Q的“精神胜利法”、对别人伤痛保持看热闹的“看客”意识等,都是鲁迅对国民性格劣根性的经典再现,作家冷眼观察并诉诸笔下,是希翼通过改造国民性来改造国人精神状态,达到国家自强昌盛的目的。鲁迅是站在知识分子启蒙的立场上来书写农民生活与性格特征的,在“俯视”的视角下对“乡土人”在现代变革面前的沉默与麻木的状态进行痛心的批判。《阿Q正传》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经典,便是鲁迅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对国民心理的全知全能的窥探与批判,并在哲学意义上对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作出全方位的价值判断。[3]32在鲁迅的影响下,一大批年轻作家在寻找创作方向时立足乡土,进而出现了乡土小说作家群,并由此形成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同鲁迅一样,“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群所持的也是启蒙者的文化批判立场,他们大多在农村度过童年生活,而在城市接受的现代思潮与文明带给他们新的看待“乡村”的视角,“乡村”作为封建积习最为严重的蛮荒之地,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他们进行批判以达到启蒙、革命甚至救国目的的场域。不论是王鲁彦的《柚子》、许钦文的《鼻涕阿二》还是彭家煌的《怂恿》、许杰的《惨雾》、蹇先艾的《水葬》等,都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与揭示古老中国的文化形态与病态灵魂,带有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与历史意识。
“五四”乡土文学,是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下出现与发展的,它不仅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同时也是启蒙主义与思想革命的手段,蕴含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正如林虹所认定的那样:“爱国主义,是一个在中华民族传统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主题。她在近代以来的演绎与传统有着天然的衔接:在忧患中萌芽,在求索中成长。”[4]92只是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同传统相比,是在西方强制打开中国大门下的国家意识觉醒后的爱国情怀,“五四”知识分子不仅要着力清除强大的封建势力,同时也致力于建设可以与西方抗衡的现代化中国,承担着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封建的任务,更为复杂和深沉。
二、知识分子情怀:为人生的写作态度
对一阶段文学进行研究总是离不开对于这一阶段作家的考察,作家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对“五四”乡土小说情怀的研究离不开对于作家本人即鲁迅与“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群的关照。如果说“五四”乡土小说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在西方国家的侵略下国家意识的逐步觉醒,对乡土的关注与书写是进行启蒙与革命的有意为之,那么作为书写乡土的文学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选择乡土作为他们创作的落脚点,则包含着一种主动性,是知识分子情怀作用下对时代责任与使命的自觉承担,秉持的是“为人生”的写作态度。而且,正如上一部分所说,“五四”乡土小说是在水深火热中孕育出来的,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国家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所以不管是知识分子情怀还是爱国主义情怀,均体现了作家的理想寄托与人格色彩。同时,“为人生”的写作态度不仅是“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的选择,这种创作上的指向其实贯穿整个“五四”文学发展始终,甚至宣称“为艺术”的作家作品中也有着对社会政治关注的现实侧重。
如果细细追溯,“为人生”的创作指向也有其历史渊源:“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功能观。从本质上看,“文以载道”的思想内核是实用主义的,强调文学的功用与现实指向,“为人生”的态度也是从文学的功利性出发,强调文学的功用,两者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可以说“为人生”是“文以载道”思想内核在“五四”时期的发展与新变。虽然“五四”知识分子曾明确反对“文以载道”的思想,但他们反对的是古代文学所载之“道”,反对“为圣贤立言”的泛泛空谈以及作为封建思想载体的文学,提倡真实、真切的情感与生命体验,并非反对文学的功用,而且曹丕也说过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正是对文学价值的重视。“经世致用”确实也是中国文艺的特点之一,正如朱光潜所言:“中国民族向来偏重实用,他们不喜欢把文艺和实用分开,也犹如他们不喜欢离开事实去讲求玄理。”[5]294
对“人生”的强调也使得知识分子将“为艺术”的写作态度与文学的游戏消遣功能作为批判的对象,鲁迅从一开始便反对游戏、消遣的文学态度,他对于晚清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等的批判,表露的正是他对文学功用的重视,以及为人生的写作态度。鲁迅也曾公开表明他之所以做小说,是“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6]85正如鲁迅所表明的那样,对“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关注便是鲁迅“为人生”的写作态度下对人物类别的选择,希望通过对国民劣根性的描画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群大多是在鲁迅的影响下进行文学创作的,他们中有鲁迅的同学、也有鲁迅的同乡,或者在创作上直接模仿鲁迅的手法,他们虽未公开表明自己的创作立场,却在创作上表现出某些与鲁迅的“为人生”态度相通的选择与表现。他们在创作中时刻关注农民的精神状态与乡村变化,不忘在作品中对于社会和人生的介入,王鲁彦、台静农、许杰、彭家煌等所创作的乡土小说在主题上都表现出了对于封建礼教、习俗以及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具有鲜明的“为人生”的特征。而且他们大多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正如文学研究会宣言所宣称的那样:“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如劳农一样。”[7]3他们皆是将文学视为紧要的工作,以文学作为解救乡村与社会的武器。此外,在“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群中,许钦文与蹇先艾早期乡土小说多表现对于故乡的回忆与怀念,充满了田园牧歌的眷恋与哀悼之情,后来的许钦文则从“父亲的花园”中走出来,关注“疯妇”和“鼻涕阿二”的悲惨命运;蹇先艾也从充溢着田园牧歌的“朝雾”中挣脱出来,饱蘸泪血书写“乡间的悲剧”[3]53。他们这样的转变,无不说明“五四”乡土小说作家“为人生”的写作态度的自觉性与逐步深化的过程。
三、乡土情怀:理论倡导与怀乡心理结构
“五四”乡土小说的出现与发展,不仅是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作家的自觉选择,往深层探究,它的诞生更是蕴含着深沉的乡土情怀。这种乡土情怀包含着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与乡土文学理论的宣传、建设,以及作家怀乡的深层心理结构。
一方面,乡土小说的发展与繁荣,正是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转向。当时文坛上风靡“问题小说”,许多作家都将小说作为社会问题的载体,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然而由于“问题小说”作家生活经验的缺乏,使得此类小说存在着着题材狭窄与“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端。周作人就曾撰文批判问题小说“太抽象了,执著普遍的一个要求,努力去写出预定的概念,却没有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果是一个单调。”[8]124所以,追求真实、个性便成为文学发展的内在追求,这一目标要求作家克服“抽象”,回到熟悉的题材,表现“有血有肉”的生活感受。乡土题材便成为许多来自农村或城镇的青年作家们的选择,他们熟悉乡土生活,有着充足的经验来书写,乡土小说也就应时而生。另一方面,“五四”乡土小说的产生离不开乡土文学理论的宣传与介绍,茅盾、闻一多、王伯祥等人都曾在文章中讨论或解释过“地方色彩”,都在理论上为乡土小说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助力。但是,最早以及自觉建设乡土文学理论是周作人,他的影响最大。早在1911年,周作人在翻译匈牙利作家育珂摩耳时写的《黄蔷薇序》中最早使用“乡土文学”一词。[9]491923 年前后,周作人又先后发表了《地方与文艺》以及《旧梦序》等文章论及“乡土艺术”与“地方趣味”,进一步建构起以“地方性”为特色的趣味主义乡土观。首先,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从各国文学具有不同的特点出发,提倡本国文学的独特风貌,进而表示即使在本国文学中不同地区的文学也可具有不同的地域色彩,“譬如法国的南方的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10]38其次,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要求新文学必须“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10]41,“土气息”与“泥滋味”不仅是对当时问题小说弊病的纠正,同时更是作为对乡土小说的企盼提出的。最后,周作人在给刘大白《旧梦》做的序言中强调“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并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11]733可以说,“五四”乡土小说的发展不仅是文学自身求变发展的要求,也离不开周作人等的理论倡导。
乡土小说的发展也反映了作家的深层心理结构,这一结构可以说是在中国传统经济(小农经济)作用下所形成的作家的怀乡情绪。梁漱溟曾指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是。”[12]10-11在这样的环境依托下,乡土小说的出现便不足为奇。自古代先民开始,中国人就在华夏土地上繁衍生息,世代以农业为本,并形成了热爱土地与重农的精神,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是对土地依恋、对家乡怀念的思想内容。“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大都来自城镇或乡村,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远离家乡到北京、上海等地求学,以获取现代化的教育和知识,也就是鲁迅所形容的“侨寓者”。正如蹇先艾所说:“据我所知,“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作者,大都是在北京求学或者被生活驱逐到那里,想找个职业来糊口的青年,他们热爱他们的故乡,大有‘月是故乡明’之感,偏偏故乡又在兵荒马乱之中。‘等是有家归未得’,不免引起一番对土生土长的地方的回忆和怀念。”[13]296彼时的他们带着现代性的眼光关照故乡,故乡是那封建愚昧的一片遥远荒芜之地,不禁产生巨大落差,然而另一方面,故乡作为自己过往童年和亲近之人的全部记忆的承担者,在精神上又觉得分外亲近,所以在“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的笔下,对故乡的回忆和怀念大多具有文化批判的悲剧色彩。不论是鲁迅的《故乡》、《社戏》还是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蹇先艾的田园牧歌,亦或其他乡土小说作家笔下批判的家园,都体现着这种“理智上面向未来,情感上回归传统”矛盾的怀乡心态。
此外,“五四”乡土小说作家们普遍经历的是“五四”退潮后的失落与彷徨,他们所热衷的“科学”、“民主”、“自由”等仅仅作为工具理性来信奉——主要是作为救亡图存良方而运用它们[14]217,而现实以及出路方向都是茫茫然没有结果,所以故乡便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在对故乡的书写中慰藉失落的心灵。“五四”乡土小说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是自身发展的要求使然,同时也离不开周作人等人的理论宣传,为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指导。同时,在小农经济传统影响下的作家怀乡的深层心理结构与现代性眼光结合的复杂心态,也为乡土小说增添了多义性内涵。
对“五四”乡土小说的情怀进行研究,我们可以从深层把握乡土小说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因,进而对乡土文学发展的历史有一个清楚的理解与把握,从而建构起明确的线性文学史观。另外,对“五四”乡土小说的情怀进行研究,对当下乡土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乡土小说发展到今天,虽然仍有一席之地,但也面临许多困境:现代性发展下的乡村与城市的同化、大量农民进城、城市文学的兴起等,甚至出现了“乡土文学消亡论”。虽然乡土文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与新问题,但同样也提供的新的可供书写的图景,比如乡村的现代转型,当代乡土小说作家应立足前人经验,审视当下乡土发展现状,整合现实,从深层探寻民族意识与文化的独特性,建立中国形象,进而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