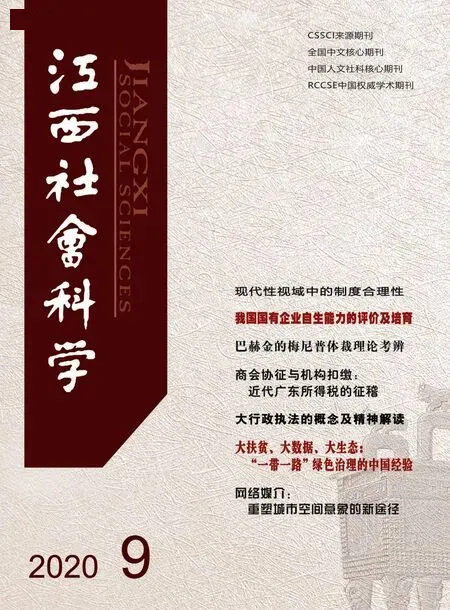比较哲学视野下心的标准问题
心与非心的区分标准问题既是重要的心灵哲学理论问题,又是重要的工程技术学实践问题。西方心灵哲学围绕它已做了大量探讨,形成悲观主义、单一属性论、多属性论、单一系统观等大量理论,出现了包括比较研究在内的多种走向。尽管比较研究这一进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西方已有的研究由于存在着对东方心理标准理论的误读、不到位的解读乃至解读的空白,因此中国哲学工作者有发出中国声音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基于跨文化研究不难看到,作为整体的、矛盾统一体的心除了有样式多样性、性质差异性的特点之外,还有共同的本质,那就是所有心理现象都有其觉知性或能为主体自己认识的自知性,都有对物质实在的不同形式、程度的依赖性,都是同与异、生与灭、连续与非连续、变与不变的矛盾统一。正是它们,把心与非心区别开来。
心理现象肯定不同于非心理现象,即使三岁小孩也不会说桌子的运动是心理现象。但是,这不同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把心与非心区别开来?亚当斯(F.Adams)说:“在有心的生物系统与没有心的生物系统之间存在着自然的界限。如果这不是幻觉,那么就能找到造成这种区别的东西。”[1](P54)这就是心理的标准或标志性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所有心理现象个例成为一个类别,同时使所有心理现象与别的现象区别开来。很显然,这个问题与心是什么的问题(本质问题)密切相关,其现实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是重要的哲学理论问题,又是重要的工程技术实践问题。就后者来说,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人工智能就没有前进的方向。因为关于心理标准的理论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性、前提性的理论。对它的回答不同,人工智能构建的具体的方向、思路、工程技术实践就不同。心理的标准问题当然是一个极为困难、聚讼纷纭的问题。
西方哲学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心灵哲学自觉而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甚至已将它建设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这在今日的心灵与认知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为推进有关认识,人们绞尽脑汁,设想种种可能方案,甚至用上了比较研究。在笔者看来,尽管比较研究的进路在这里可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西方已有的研究由于存在着对东方心理标准理论的误读、不到位的解读乃至解读的空白,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大显身手。
一、中国哲学的心理标准探索
要想通过对中、印、西的心理标准理论的探讨来找到对心理标准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对被比较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思想有客观到位的把握。首先,我们来考释中国的心理标准探索及理论贡献。
中国哲学的心理标准论主要包含在它的心性论中。“性”是中国心灵哲学独有的课题。从词源上可以看到,它指的是心一生成时所具有的东西。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说心有其不同于非心的本质构成及特点的话,那么,它在生成时就铸就了这种区别,因为它所禀赋的东西不同于非心所禀赋的东西。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说,这既是中国心理标准探讨的特点之表现,也开创了心理标准研究的一个独有进路。在中国哲学中,许多人都有从这个角度揭示心与非心区别的尝试,如明代心学家汪俊说:“虚灵应物者心也,其所以为心者,即性也。性者心之实,心者性之地。”[2](P1144)意思是,心与性相辅相成,心是性的依存之地,而心之性是心的实质,即是决定心之为心的根本、初始条件和资源,例如,心之所以是有虚灵应物这一为心所独有的作用和标志性特征,决定因素是心有其独有的性。不难看出,心性论不仅包含显明的心理标准理论,而且从内在本质的角度揭示了心的外在标志的内在根由,因此可看作深层次的、发生学意义的心理标准论。心性论的特点在于,一是从心的发生学(生)上揭示了心的特点,即它之所以为心,是因为它有非心所没有的特殊的性。换言之,心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它有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原初的性或心。二是像探矿学一样,试图在心中找到它的最深、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亦即区别于非心的深层本质。这个东西就是性。
中国哲学专门把心性作为一个对象来加以探讨,肇始于儒家,而孔子又是其当之无愧的祖师。之所以说孔子的心性论是中国心性论的源头,主要是因为他把性与天道、性与仁关联起来。如果孔子所说的天道或天命是指道德的超越性,就不难理解孔子为什么把性与天道关联在一起。徐复观说:“性与天命的连结,即是在血气心知的具体的性里面,体认出它有超越血气心知的性质。这是在具体生命中所开辟出的内在的人格世界的无限性的显现。”[3](P78-79)孔子认为,性就是人天生就有的道德本性。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孟子的人性论才能够开始对性做具体的开发和挖掘。他认为,心之性即是人心共同具有的道德本原,足以把人与非人、心与非心区别开来,是人之所以然,内容主要是道和义:“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此义、理不是现实性的东西,而是生时被先天赋予的“端倪”,即种子一样的东西,具体表现为仁、义、礼、智四端。孟子不仅明确提出性善论,而且强调性与心的下述关系,即“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上》)。牟宗三认为,孟子思想的纲领在于:“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孟子·告子上》)荀子也承认性是自然赋予人的本性,所不同的是,他认为此性是本恶的:“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篇》)不仅如此,人的诸器官先天就有其特定功能,如五官有其认知功能,这也是生而就有的本性。“目辨黑白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痒,是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
朱熹的心性论全面而清楚地表达了儒家在心的深层本质特征问题上的看法。他认为,心是体与用、静与动的统一体。而性则是心的体、理。如果说理是太极,那也可说,心之理是太极,心之动静是阴阳。性也可称作明德。在凡圣心中,此明德是一样的,在凡不增,在圣不减。之所以在凡夫身上看不到,是因为它被染欲等覆盖住了,因而只以潜在的形式存在。这类似于莱布尼兹所说的真理的种子,它们以大理石花纹的形式存在。只要条件具备,可能性即能转化为现实。朱熹说:“人皆有此明德,但为物欲之所昏蔽,故暗塞耳。”[4](P315)如果说情是心的已发,即现实表现出的实际心情,那么,性就是心的“未发”,即以天赋原则的形式存在。从认识上说,性不可见、不可言。情是可见可言的。因为发者情也,其本则是性。
朱熹还认为,心有两个特殊标记,一是灵,二是性。而这两者中,性是实,是本。他说:“灵底是心,实底是性。灵便是那知觉底。如向父母则有那孝出来,向君则有那忠出来,这便是性。如知道事亲要孝,事君要忠,这便是心。”[5](P323)“主宰、运用的便是心,性便是会恁地做底理。”[4](P90)心是执行系统,其作用的根本之处是灵明,而性则像程序、条理一样制约着心的运作。以庄稼为例,它们的种子是性,种子决定了一植物长成什么样子。现实的庄稼即为心。“包裹的是心,发出不同的是性。”性与心的区别还表现在:性是心的静的一面,而心有动有静。朱熹对张栻下述思想的肯定也表达了自己的上述倾向:“自性之有动谓之情,而心则贯乎动静而主乎性情者也。……心之所以为之主者,因无乎不在矣。”[6](卷二十九,P1129)心与性的差异还表现在:性决定了人与人的同一性,而心与气、形一道决定了人的个体性、人与人的差异性。
心与性又有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关系。这首先表现在:“心以性为体,心将性做馅子模样。盖心之所以具是理,以有性故也。”“心与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4](P89)不可分离还表现在,舍心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性之所以是心的根本性的深层标志,是因为它是心的“馅子”。这个比喻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中国心灵哲学注重从内而非外揭示心的标志的特点。朱熹的这些思想代表的是中国哲学在心的标准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根据这一标准论,心的内在的深层的、让它与非心区别开来的本质特点是心的独有的性,而心的外显的、功能上的标志性特点则是心的灵明不昧的作用。
道教至唐代重玄学的成玄英,便加大了对心性问题的关注和探讨的力度,从此以后,道教的心性学与中国佛教的佛性论、儒学的心性论并驾齐驱。重玄学之后的心性学的基本观点是,性是心中的所藏,心是性的载体。“心者,神(性)之舍也。”(《道德真经广圣义》卷四十九)而性就是真心。当然,这是有多种说法的。一,性即是神。“神者,性之别名也。”二,性指人的先天之神。如张伯端认为先天之性即“元性”。“神者,元性也。”“元神者,先天之性也。”(《道德真经广圣义》卷四十九)三,性即道德修养功夫和心理的稳定状态。
尽管有不同的心性论,但它们中一般包含这样的思想,即心之性既是心的原初的东西,也是心之为心、心区别于非心的本质特点。不仅如此,有的人还更进一步探讨心性之为心本、为心的标志性特征的所以然。如张载在论述性时,以气来释性。所谓气有体、用两面,体即气的虚静、本然状态,换言之,气的本体是太虚:“太虚者,气之体。”(《正蒙·乾称》)太虚之用即气的聚散变化。此气即质料性的气。太虚相当于德谟克利特所说的虚空,质料性的气相当于原子。物质之质有阴阳、刚柔、缓速、清浊等差异。就一般的性的起源和本质而言,它由气所决定、所使然。他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正蒙·太和》)性本身不是心理,是无意识的,但作为体性的性可成为心理的基础,知觉、情感就是如此。“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感皆出于性,性之流也。”(《横渠易说·系辞上》)性只是心的基础,如果没有别的因素起作用,就不会有心出现,即只有性与知觉结合时,才会有心出现,故可说:“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从性与心的关系说,心根源于性,性与知觉结合便有了心。性与神一样,是气所固有的东西:“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7](P63)“其成就者性也”[7](P187),有两种性,一是天地之性,二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由于禀赋了太虚本体之气而成的性,气质之性是禀赋了构成人身的具体的聚散之气的性。心之所以不同于非心,主要是由它的特性决定。
中国哲学的心理标准理论除了上述重视从发生学和内在深层本质的角度加以揭示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即强调把心与非心区别开来的标志性特征是多。这些特征的每一个都是心的必要条件,但单个地看,它们又可成为别的事物的特征。换言之,非心事物可以具有其中的某一特征,但不可能同时具有心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只有心才同时有这些特征。
中国心灵哲学所说的“精”有时是心的同义词,有时指的是心中的、以动力资源形式表现出来的根由,有时指的是心的精微的特点。很显然,精至少是心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不具有精这一特点的事物肯定不是心,当然它不是心的充分条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哲学在论述精与心的关系时隐含一个有多重意义的宝贵思想,即现实地显现出来的、在运转和起作用的心一定有自己的能量之源或“心理力”,一定有其精,一定以精的形式存在,只是它极其微妙,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不仅有本体论的地位和作用,就像物理的电子信号等微观实在一样,是心的构成上的特点,而且是心现实存在和有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不仅以中国的方式回答了心的标准问题,即心一定有自己的独特的能量形式、作用力,一定表现为精,而且解决了古今中外都没有很好解决的心理因果性难题。
“神”像“精”一样,也是一个极富歧义性的词,其中有些意义表述的是心的标志性特征。就词性而言,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作形容词使用的,指的是事物的玄妙、变化、神奇、难以测知的特点。在人身上,神既指身体各部位的最佳状态,如面有其神,又指整体的最佳状况,有时也用来形容心、魂、魄、精神这些心理主体的神奇作用。就此而言,神也像精一样,是心的一个必要条件,即一切心都有神的特点,当然有神的特点的东西不一定是心。神除了表现为高级的智慧作用之外,还有较低级的认知作用,其表现之一是,负责人的日常认知,如视听言动,邵雍云:“尽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聪明犹不可欺,况神之聪明乎!”[8](P372)中国哲学从心灵哲学角度对神的论述无疑有回答心理标准问题的意义,只是它用了中国特有的象征方式。根据有关的思考,心之所以不同于非心,是因为它有它不为其他事物所具的作用及其方式,即神或神妙,用今日哲学的话说,即有特殊的能动性、不可预测性、神秘莫测的变化性、创造性。例如,心能超越时空,与过去、未来发生关系,与身体没法进入的空间发生关系,甚至与不存在的东西发生关系,如思考方的圆、创作虚构对象等等。神是心的能主宰一切的作用,如神能决定思想和行动。“故神制,则行从,形胜则神穷。”“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宝也。”[8](P374)质言之,看一个对象是不是心,可从它是否有神妙的能动作用这个角度加以观察。
“灵”与“精神”除了有表述心理王国中具有主体性地位的实在的意义之外,还有表述心的特点与条件的意义。正是这一方面的意义,使中国对灵的说明有时具有心理标准理论的意义。“灵”作为名词有时指能照、灵明之觉。这种明和觉的特性就是心区别于非心的特性。当然有两种明性,一是真心的本明之性,二是妄心的低层次的反省特性。用西方心灵哲学的话说,这里的灵明相当于西方常说的自我意识中的一种形式,即不依赖于主客二分、无须通过反省或反思作用的前反思性自我意识。“灵”还常作形容词用,指的是“灵活”“灵敏”等作用。用于描述心时,强调的是心识的不可思议的功能,如“六灵”说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的灵明之性。这种特性是中国哲学发现的心具有的标志性特点,即心有灵的特点。尽管有的非心事物也有灵的性质,但心之灵的程度是他物所不具的。心之所以灵于万物,是因为它具有非心事物所不具有至精至灵的作用。中国哲学所说的精神有时指的是心的一个标志性特点,即“有精神”。因为只要有心,只要心存在着、活着,就一定充满着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心力旺盛的人,则精神充沛,人死了,则无所谓精神。陆九渊说:“收拾精神,自作主宰”[9](卷三十五,P454),意为把精神收摄向内,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任其向外驰求,人就作不了主,就是凡夫一个。他说:“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时,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9](卷三十五,P454)
总之,精、气、神、灵、精神,特别是它们作为形容词的所指,尽管也可为非心的事物所具有,但一方面,它们表现在心之上,在程度上乃至在实质上是根本有别于非心事物所表现的同类的性质的,另一方面,只有心才可能全部具有这些特点或条件,因此由它们的共具和高层次的表现所决定,心便与非心判然有别。质言之,根据中国一般的心理标准论,判断一种现象是否是心理现象,一要看它是否有性这一初始的、内在深层的“馅子”,二要从外的方面看它是否有精微、弥散、形而上的存在方式和相状,是否有神、灵这样的作用方式和特点。
二、古印度的心理标准理论
心理现象的标准问题与心理现象的范围及分类问题是密切联系、相互纠缠的问题,尤其是范围和标准问题之间似还存在着“问题循环”。古印度哲学对这些问题都有以特定方式表现出来的探讨。我们这里关注的主要是佛教在这个问题上的哲学思想,而不涉及它的宗教内容。另外,这里之所以以佛教为考察印度思想的案例,主要是因为它继承、囊括了古印度其他宗派的有关思想,同时又有自己的创新。我们将先考察佛教关于心理范围的思想,再阐释它基于它所发现的最为广泛的心理样式对心理标准的探讨,最后讨论佛教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贡献。
我们在探讨佛教的心理标准理论时之所以从心理范围这个问题出发,是因为对心理范围的看法不同,对标准的看法必定有别。佛教之所以有极其独特的心理标准论,是因为它对心理的样式、范围的看法极其特殊,最突出的是,它看到的范围是现今我们所知的最为广泛的,同时还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强调心理现象本身具有变化性、生成性的特点,例如,随着修行的深入,随着由凡向圣的转化,随着成圣的心理过程的进步,会陆续派生出许多以前所没有的心理现象,因此,心理现象的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例如今后还会有以前所没有的心理样式出现。
佛教关注的心的范围大于世间心灵哲学关注的范围,其表现之一是,佛教不仅像一般心灵哲学那样承认人和高等物身上会出现心理现象,而且认为他们之外的许多生命体都有心理现象。世间心灵哲学充其量只关注人及高等动物的心,而佛教心灵哲学除了承认低等动植物有心之外,还广泛论及三界范围内的心。佛教心灵哲学认为,除欲界众生有心之外,色界的天、无色界的圣者都有心。无色界的众生尽管没有有形体的色身,但也有一种特殊的心,甚至特殊的身,如意生身,更重要的是,超越三界的圣人也有其心,这心主要表现为无漏心以及带有现象学性质的真心。“无色既无通(神通),唯是定力”,由入定力所变。因为神通力离不开色身,由“先加行思维方乃得生,故心引起变化事等,定力但是任运生故”。“无色现色,但定所生”,即是说无色界也可有所变身器,不过它们是无形质的,而且“内身多续,少分间断”。[10](P325)
佛教心灵哲学关注的心理范围大的第二个表现是,承认在死亡进行时仍有识神存在。从历时的过程看,众生的生命尽管是一个从生起到转灭、再生再转灭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但生命的心理和意识既有灭的方面,如许多念头刹那生灭,又有不灭的方面,这就是神识或阿那耶识。由于有它的支撑、摄持,众生的心理才能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如一期生命的意识可分为14个阶段,觉音说,89种心“依十四种行相而转起”。它们分别是:(1)结生,有情生于六欲天或人中,转起8种有因的欲界异熟。其他诸界都有其结生、转起:(2)有分;(3)转向;(4)见;(5)闻;(6)嗅;(7)尝;(8)触;(9)领受;(10)推度;(11)确定;(12)速行;(13)彼所缘;(14)死。[11](P423)
佛教心灵哲学关注的心理现象范围大的第三个表现是,由于佛教看待心理现象早就用上了现象学的视角和观点,因此看到了自然、素朴观点没有看到的大量带有现象学性质的心理现象。它们是自在世界所没有的,是人在进入与世界、人、别的心理现象的关系时所派生出、突现出的心理现象。这些现象大致有两大类:一是带有现象学性质的妄心,这相当于今日西方心灵哲学重视的以感受性质、现象学经验表现出来的心理现象,例如人当下经验到的疼痛、痛苦、烦恼等;二是带有现象学性质的真心,即在禅修等心理操作中出现的不同程度的真心显现。
在心理标准问题上,佛教的看法十分特殊,同时根本有别于无限制地放宽标准的自由主义和只承认人有心理现象的沙文主义。由于佛教有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两种表现,看问题有体与用和理与事两个维度,因此佛教对心理标准问题的回答就自然有两方面。一方面,从理体上说,佛所证的真理、法性、实际,看到的整个世界一如一体,众生平等,没有心与非心的差别,因此自然无所谓区分标准可言。如经云:“于菩提胜义谛中,即不能说。何以故?彼胜义谛,非语言、非诠表,亦非文字积集所行,尚非心、心所法而可能转,况复文字有所行邪(耶)?”[12](P492)另一方面,佛出于大悲心,为救度众生,又不得不说,于是便有了有言之教。经云:“为不可思议一切众生大悲转故,……于无文字、无语言、无记说、无诠表法中,为他众生及补特伽罗,假以文字,建立宣说。”[12](P494)如此建立的宣说,即在有言之教中。从事上看问题,才有心与非心的区别,才有标准需要讨论。在这个层面,佛教强调心与非心之间有明确的界线。这界线是什么呢?
佛教认为,心理现象有两大类,一是真心,二是妄心或众生能知觉到的处在生生灭灭中的表层的心,它们共有的不同于非心的本质性特点是具有明性,或觉性。所谓明是指心理现象发生时,心不仅知道它发生了,而且只要愿意,就能明白其发生的过程、相状、特点等。这种明有两种表现,一是真心的本明,此明与真心的寂然的特点一如一体。圆瑛法师说:“心以灵知不昧为性,有觉明之用。”[13](P12)寂然不动的真心之所以是心,是因为它也有明或知的特点。只不过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明或知,即不依赖心之动变的知,可称作良知或灵知。祖源禅师说得好:“真心灵知,以寂照为心。”[12](P593)其特点是,无知而知,知而无知。“真心应物,如镜照像,无心而知故为真。”[12](P594)二是妄心的明或知,即依赖于心之动的明,亦即西方人常说的反思性自我意识。这种意识离不开能(主)与所(客)的关系,即只要有此种明发生,就必然有能明与所明。
从本质构成上说,所有心都有四分的构成。所谓四分,即把有意向特性的任何一个心理事件区分为这样四种构成: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至少有见分和相分。应该承认,佛教内部对此问题是有争论的。概括说:“安惠立唯一分,难陀立二分,陈那立三分,护法立四分。”[10](P320)四分说是“正义”,即被认为是正统的、标准的、正确的看法。根据四分说,所谓意向性、攀缘,其实是让有关的境相显现在心中。这显现出来的东西尽管不是外在对象本身,但由于它是代表,心通过它可关联于外在对象,因此至少是“似尘”,是心相。这显现之相即相分,能识知此相分的东西即见分,对这一过程之结果的把握是自证分,清楚意识到全部过程尤其是自证分,则是证自证分。这就是关于意向性结构的“四分学说”。
严格地说,见分和相分等构成只是八识心王的行相。但由于其他心法,如情、意、信等以及被归入心所法的大量心法,也都有一定的了别和被了别的成分,因此,在宽泛的意义上也可说它们有同心王一样的行相。《成唯识论述记》云,“心、心所必有二相”[10](P317-318),即见分和相分。
另外,见分是能量,相分是所量,不是只有八识才有量的作用,所有心所法也是如此。故可说,心王、心所在量境之时,其行相有见分和相分等不同方面。佛心、清净真心有无此四分呢?回答是肯定的。当然,这里没有这样的能所关系,即把妄心当作能,把真心当作所。因为佛心的特点是:自明、体明、本明,性觉妙明,本觉明妙。但如果为言说的方便或教化的需要,我们是可以从外面对之作出分析的,如说它有能明与所明。不过,应记住的是,这样的描述及说明,都是在俗谛、比喻的意义上说的。由于心理现象主要以妄心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佛教讨论得较多的是这种心理现象的区分方法。基本观点是,判断一种现象是不是妄心,除了要根据上述标准区分,还可用这样一些辅助性方法去做出区分。
心的第一个标志性特征可从整体性关系上把握。例如,世界上不可能有孤立的心理现象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不可能只出现一种心识,而不同时伴有别的随附性的心所法(情感、情绪、意愿、信念等)之发生。这就是说,心、心所法是和合而起、相辅相成的,就像束芦(一捆茅芦)“要多共束方能得住”一样,单根不能站立。心、心所法也是这样,“要多相依,方能行世”,其根源生于:“诸有为法性赢劣故,辗转力持,方能起作。”[14](P80-81)质言之,一个人不可能只出现一种心理现象。有一心生,必有别的心同时生起。任何一种心理都是作为一心理网络或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的要素而出现,离开了它的系统,它便不复存在。这是心不同于非心的一个特点。“此心若依、若缘、若时起,彼心共俱心数法等聚生。”[15](P810)意为若某心在某时依某些缘出现了,与此心相应,一定还有别的许多心一同发生了。
心的第二个标志性特征是辗转相因,即前心是后心的因,就像羊圈中只有一个小门,众多羊必须一个接一个出来。这当然是从现象学角度说的。对于内觉知或意识而言,只能有心念的接续出现,而不可能有两个心念同时出现。用现代心理学的话说,心具有“意识流”的特点,如不具有此特点,就不是心理现象。这至少是判断具有现象学性质的心理现象的一个辅助性标准。
心的第三个特点是,心只要处在清醒状态,就总要攀附在一个东西上。这个特点类似于西人所说的意向性。“一心不专定,心亦如是,前想后想所不同者。以方便法不可摸则(测),心顠转痴,是故诸比丘凡夫之人不能观察心意。”[16](P561)另外,心还有等无间、随转的特点,即随别法的作用而生、住、转,同时又作为因影响别法。心不同于有质碍性、占有空间的身体和外物,无形无相。这是佛教的近于现代量子力学本体论的思想。这种本体论对立于以有形体特性或以广延性为判断存在与否的标准的本体论,而认为无形之物也有存在地位。佛教还认为,心对身有一定的依赖性,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切心都离不开身,必依身而转,而只能说在有色形的有情众生身上有如此现象,在无色有情身上则不存在心对身体的依赖性,因为他们没有色身,但照样有心。他们的心依赖的是“命根、众同分”。
最后,佛教还找到心的“遍行”特征。所谓遍行的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切心理现象的普遍特性,当然也是非心事物不具有的东西。从字面上说,“遍行”即遍在于、遍行于八识心王法之中。作为心所法,遍行心所法像别的心所法一样,也是为心王所拥有的,是伴随心王而发生的,因此是心王的随附性现象。还要注意的是,遍行心所法,不仅遍行于心王,而且遍行于别的一切心所法,因此是一切心理现象中共同的、“遍行的”或普遍的特征。这样说的根据在于:心所法必然伴随心王而发生,既然如此,心王有遍行的特征,伴随它们的心所法也一定如此,因此,遍行心所法也可理解为遍行于一切心所法之中。玛欣德说:遍行心就是遍一切心,“一切心就是所有的心、任何的心,即89种心。遍(sadharana)的意思是全部都有”[17](P160)。大乘一般说有五个遍行,即作意、触、受、想、思。上座部主张有七个,即在这五遍行之上增加了一境性和名命根,从而成七遍行。用现代心灵哲学的术语说,作意、触、想有与意向性一致的内容,也有佛教独立发现的东西。受也是如此,它近于西方心灵哲学所说的“意识”或感受性质。
总之,根据佛教关于心理标准的理论,只要抓住心的“明性”这一根本特点,再辅之以上述附带的标准,就能建立说明心与非心之区分的标准体系,就能把心与非心区别开来。因此,心与非心的区分也是一种整体论性质的工作。
三、基于比较的思考
由于我们专门研究过西方心理标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主要理论形态[18],这里只概述它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以作为我们比较研究的逻辑铺垫。毫无疑问,西方心理标准理论既有悠久而持续的历史,又有十分发达的当下。另外,它在西方既被当作重要的理论问题来对待,又被当作重要的实践问题来外置。许多人认为,心的标准因人而异,有的还持悲观主义态度,如金在权认为,不可能形成关于心灵的统一的概念,进而就没法找到它的区分标准。因为心理现象有不同的样式,既然如此,就没法在它们中找到共同的属性。[19](P26-27)赞成能找到区分标准的人是以这一问题为出发点的,即它们是一还是多?换言之,有没有所有心理共有的、非心理现象所没有的属性?如果有,这种属性是一还是多?如果对第一个问题作了肯定回答,即为乐观主义,作否定回答,即为悲观主义。如果对第二问题说一,即为“单一属性观”。如果为心所共有的属性是多或一组属性,则为“多属性论”。最后,有一种理论,可称作“单一系统论”。它认为,有一组属性是所有心灵必有的,但是,作为心灵系统的组成部分的某一个状态或某一心理样式不一定具有所有这些属性。因为该状态可能由于对整个系统的属性有因果作用因此成了这个心灵系统的组成部分。[19](P56)
基于对中、印、西三种文化中心理标准理论的比较研究,我们有理由说,它们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理论建树,可以互补,成为进一步探讨的基础和资源。中国哲学的心理标准理论最宝贵的地方在于,强调要揭示心不同于非心的标志或特征,既应从心理的构成、外在表现和所起的功能作用等方面加以探讨,更应关注内在的特别是心的初始的东西。而这又是基于这样一个极有见地的形而上学原则或预设:包括心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在它们生成时,在由大自然塑造出来的那一刹那,就被铸就了、铁定了。因为每个事物在那一刻都被赋予了一种像种子或种子的集合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性”。它既决定了拥有它的事物后来的可能发展变化甚至不可能的范围,也决定了该事物与别的事物的共同性,还决定了该事物与别的事物的不同。孟子认为,性是“天之降才”,荀子认为,性是人与物的“本始材朴”(与西方今日原初主义所说的心形成时的“原初的东西”何其相似!)。有此性,事物形成后就以此为规律、准则而运行,因此事物能各循其道,“各正性命”(《易传·乾象》)。既然如此,要认识世界,按规律办事,就必须认识这个性。既然性是本性,是体、是道,因此,认识世界的主要任务就是“穷理尽性”。总之,性与生密不可分,只要有产生的事物,就都有性。
这种形而上学的“性”论为探寻心与非心相区别的标准指明了前进方向,铺平了康庄大道。这是因为,心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有其生,而有生就一定有其禀气而有的性,有其不同于别的事物的初始的东西。如果真的找到了这性,那当然等于找到了心与非心相区别的东西,至少找到一种条件或标志。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心灵哲学便开辟了一个独有的探寻心理标准的路径。换言之,着眼于性的探讨,这既是中国心理标准探讨的特点之表现,也开创了心理标准研究的一个独有的进路。中国哲人认为,要找到把它们区别开来的东西,关键是到它们的生成过程和内在根底中去找那个最关键的“本始材朴”或“性”。心之所以为心,是因为它被大自然禀赋的东西一开始就不同于非心被禀赋的东西。
中国哲学从初始条件和内在根由对心理标准的探讨,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要找到心的独有的、客观存在的标志性特点,不应忘记它生成的那一刹那,以及它最内在、最根本的东西。无独有偶,这一道理在今天也为西方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中的原初主义者认识到了。原初主义者在对“天赋”这一从常识中借来的不严谨的哲学概念进行“自然化”时认为,天赋即个体在开始他的心理发生发展时最初为大自然所馈赠的、作为前提与出发点的东西。事实上,人出生后,心理都是有规律地发展的。这充分说明心在形成之初都被赋予了特定的东西,此即原初心理。[20]
印度和西方的许多论者如布伦塔诺等都认识到,心理标准的探讨以对心理范围及其包括的心理样式的全面而准确的认识为前提条件。因为对范围的认识不同,对标准的认识自然大相径庭。印度看到的心理现象的范围及样式远大于世间心灵哲学的认识,因此揭示的标准与后者相比就有极大的一同。由于有这样的体认,他们在探讨标准之前都花大力气研究心理现象的范围与样式。当然具体进路又不尽相同,印度借助其基于禅定的地毯式的观心方法和描述现象学方法,对心理现象的样式做了全面的扫描,找到了生灭心的几乎一切样式,并从价值角度对它们作了分类,如有的归纳为89种,有的归纳为120或者160种,等等。布伦塔诺用的方法不同,即用的是抽取典型样本的方法。他认为,由于心理的样式太多太多,因此,揭示心理现象独特本质的方法只能是先列举明白无误、谁都会承认的心理现象的“实例”,然后从中分析和抽象心的本质特点。很显然,印度的方法更为可取,因为抽象心理标准所依据的样式、个例越少,犯以偏概全的错误的可能性越大。
东西方心灵哲学还有这样的共识,即要使对心理标准的探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仅要对心理样式及范围有足够全面而充分的认识,而且要弄清它们有无统一性,即诸多心理样式有没有共同本质,或者说,个体或整体的心理世界是不是一个统一体。如果有统一性,就有望找到统一的标准,如果没有,就必须改变揭示和概括心理标准的方法。一般而言,东方心灵哲学尽管承认心理世界有不同乃至异质的样式和成员,中国哲学甚至认为里面有不同的主,如魂、魄、神、精、灵等,但由于强调它们有共同乃至唯一的体或本,如印度哲学强调它们都根源于真心和阿赖耶识,中国哲学认为它们根源于性或理,因此都相信心有统一性。既然如此,就能找到统一的标准,如中国哲学认为心之所以为心,是因为它有不同于物性的心性。印度哲学认为,心的最根本的标志是明性。西方哲学的看法则比较复杂。如前所述,有的认为有统一性,有的认为没有。
从比较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心理标准问题探讨必然会碰到“范围—标准的循环问题”,这是一个兼有心灵哲学和形而上学双重性质的问题。布伦塔诺已踩上了这个地雷,当然他没有自觉地做进一步的形而上学探讨,如他认为,要研究心理现象,首先要知道心与非心的区别,而要如此,又必须知道心的范围。他的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不知道提出和探讨进一步的问题:怎样才能弄清心的范围?其方法论程序是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下去又会陷入循环,即要如此,必须弄清心的标准或本质。布伦塔诺没有认识到这里的麻烦,只是武断地提出:通过考察典型的心理样式或个例可找到心理的标准。
笔者认为,要想让这一领域的探讨取得真正的进展,就不能回避这里的问题特别是麻烦,回避是没有出路的。这里必然碰到这样的范围与标准的循环问题,要找到心理现象的标志性特征,或找到心区别于非心的标准,要抽象出这样的标志,首先必须有关于心理现象的大量样本,有关于心理范围的全面认识,而要如此,我们必须先确定它是否属于待研究的那类现象,即在把它纳入心理的范围而作为其中的样本或个例时,我们首先要判断它是不是心理现象。要如此,又必须知道判断的标准。而要揭示标准,又必须考察个例及范围。如此递进,以致无穷。
我们这里将省去具体分析的步骤和细节,直接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要跳出上述循环,消除有关麻烦,第一步是通过语言分析,澄清“心”一词的基本词义和指称,进而建立关于心的本质和标志性特征的理论预设。第二步是据此去搜罗心的尽可能多的个例和样式,并在这个过程中修正、检验前面关于以下的理论预设,建立进一步的理论预设。第三步再根据新的理论预设去做样本、范围研究,尽可能全面地找到心的个例,特别是样式。这些样式是心的主要表现形式,也可看作心的不太严格的子类。这种研究包括布伦塔诺所说的研究心的典型样本。我们认为,经过前面的试错性认识,我们可以在对心的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努力完成这样的任务,即尽可能全面地认识心的样式和范围。只有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对标准和本质的认识才会有比较扎实和可靠的基础。因此这一步极为重要。大致说,可这样开展工作:先运用描述现象学方法或类似于地理大发现的方法,对共时存在的一切心理样式及其性质,进行心理个例的“普查”,对表层心理后的深层心理做进一步的勘探和挖掘,关注长期尘封的东方心灵哲学宝藏,再来做关于心理一般标准和共同本质的抽象。
在这里之所以应关注东方心灵哲学,是因为东方心灵哲学在这一领域确实做了大量工作,足以弥补西方哲学的不足。东方心灵哲学关注的心理范围之大、涉及的个例之多都超过了西方。例如,中国心灵哲学在这方面就有不凡的表现。它对心、性、情、志、才、精、气、神、魂、魄等的挖掘和探讨就极具特色。尽管它对其所作的解释、对其本质的揭示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心理图景还值得研究,但造出的这些词绝不是无病呻吟,而有其真实的且不能为其他心理语言所涵盖的所指。质言之,东方文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远超西方的工作,因此我们要推进这一研究,就应下大力气挖掘其中的积极成果,然后在综合西方心灵哲学成果和现代有关科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心理世界的人口普查,或心理地质学、探矿学研究,直至建立全面而科学的心理地理学、地图学。
怎样看待西方人看重的意向性这一标准呢?我们知道,这一为中世纪哲学家提出、为布伦塔诺具体展开和阐释的心理标准,尽管现在出现了一些争论,但最低限度上,即使是批评者一般也不否认它是部分心理现象独有的特征,因此可看作一种局部的标准。我们认为,只要深入研究下去,对心的每种个例和样式的内在本质作出探讨,就能发现许多心理现象的确具有意向性。但我们又同时认为,意向性只是心的浅表的特征,因此不是把心与非心区别开来的真正的标准。就此而言,一些人对它的非议是有道理的。在我们看来,一切心理现象里面都有这样的本质,即以进化积淀的“前结构”为基础的、主动有意识的关联性或关联作用。这种性质表面上看近于西人所说的意向性,其实有根本的不同。因为我们强调的意向性既以对心的深掘为基础,也受到中国心灵哲学心性论的启发。从发生学上说,每个人出生时被自然授予的东西(性或前结构),不仅确实存在(当然是倾向、禀赋或知识能力的种子,而不是先验论所说的现成的知识或能力),而且决定了我们后天可能和不可能的范围及程度,甚至决定了我们每个人与他人的区别,决定了心与非心的区别。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整体的、矛盾统一体的心除了有样式多样性、性质差异性的特点之外,还有其共同的本质,那就是所有心理现象都有其觉知性或能为主体自己认识的自知性,都有对物质实在的不同形式、程度的依赖性,都是同与异、生与灭、连续与非连续、变与不变的矛盾统一。正是它们,把心与非心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