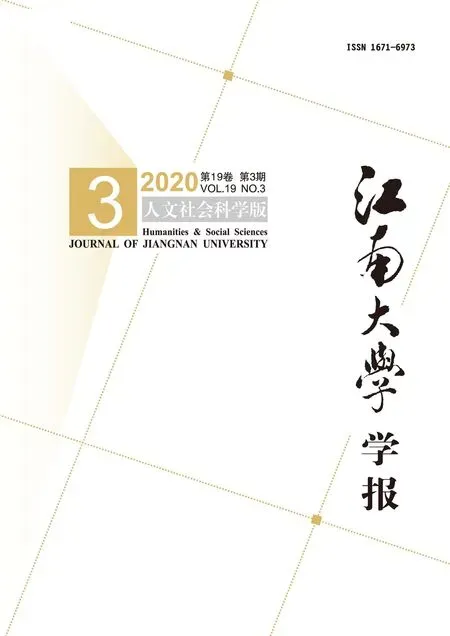以赋载史 借古喻今
——庾信辞赋与《左传》
程景牧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庾信辞赋素有“穷南北之胜”之誉,铺陈事典即为庾信辞赋能够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一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庾信辞赋之用事又以《左传》为最显著。庾赋大量征引《左传》辞章典故,寓意深刻,寄托遥深,借《左传》事典以慨叹自身遭遇之苦,阐明梁朝治乱兴亡之由,从而达到抒情写志之目的,使辞赋情感与典故相结合,呈现出史化倾向,提高了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具有丰厚的赋学价值与文艺价值。就目前来看,关于庾信辞赋与《左传》的关系这一课题还是有一些研究成果的,如罗玲云的《庾信与〈左传〉》一文探究庾信诗文与《左传》的关系[1],但考察文献仅局限于《哀江南赋并序》与《拟咏怀》二十七首,论述虽有新意,但缺乏详实的论据支撑。刘雅娇的《庾信的“善〈左传〉”》一文主要探讨了庾信后期作品对《左传》思想的汲取情况[2],意在借此探究经学与文学的关系,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例证不足,个案分析不够深入。韩鹏飞的《庾信对〈左传〉的文学接受动机探析》一文主要探赜庾信诗文创作对《左传》的接受的内外缘由[3],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对庾信辞赋创作与《左传》的关系的探究相对薄弱,未能深入挖掘。胡优优的硕士论文《庾信对〈左传〉的接受研究》全面论述了庾信辞赋、诗歌、骈文三大文体对《左传》的接受情况[4],系统性与理论性较强,但问题意识不够明显,论述略显泛化。上述研究成果均涉及庾信辞赋与《左传》的关系,或以之为研究中心,对于庾信辞赋征用《左传》的历史因缘、方法模式、目的主旨以及艺术价值虽有涉及,但缺乏系统性的论述与学理性的考察,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就这一论题做一个粗浅的探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文源《春秋》:庾赋用《左传》之因缘
历代文人如班固、左思、挚虞、刘勰、颜之推等人皆强调辞赋源于诗,这自然是举世公认的真理,但是一味地强调古诗与辞赋的渊源,则会弱化辞赋与《春秋》等其他四经的关系。宋人在《册府元龟·总录部·文章》中指出:“辞赋之起,原乎六义。”[5]即是强调辞赋与五经的渊源关系。辞赋固然主要源于诗歌,是古诗六义之二,但不可忽视的是其发展成熟离不开对五经文辞、经义的兼收并蓄,不能忽略其他四经的影响。考察辞赋的发展历程即可发现,自汉代以降,辞赋即深受五经之影响,承载经义,彰显礼乐,呈现出经学的思想特质。降及魏晋南北朝,虽然玄佛盛行,儒学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儒家经学仍是在不断地发展之中,于汉代章句训诂之学外,别开义疏之学,为唐初《五经正义》的修订奠定了基础。在《春秋》学方面,西晋即有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与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南北朝时期,南朝推尊杜预《左传》学,北朝盛行服虔《左传》学,虽师法不同,但《左传》学成为《春秋》三传之显学。南朝有沈文阿《春秋左氏经传义略》,北朝有苏宽《春秋左传义疏》。梳理魏晋南北朝辞赋可以看出,引用《左传》典故,不在少数,而尤以庾信辞赋征引为最多。这是庾信辞赋用《左传》的经学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治动荡,为了总结治乱之因果,为统治阶级提供治国经验,因此史学极为发达。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正史类著作的修撰。如列入二十四史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等著作。其二,史学意识的觉醒。如刘宋元嘉时期,史学馆的设立,使史学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西晋荀勖《新簿》设立丙部,即为史部;东晋李充调整《新簿》分类次序,确立经史子集之序;梁代阮孝绪《七录》之《纪传录》即为史部。其三,史注的兴盛。如裴松之《三国志注》、裴骃《史记集解》、晋灼《汉书集注》、刘昭《后汉书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孙盛撰《晋阳秋》、习凿齿撰《汉晋春秋》、刘宋檀道鸾撰《续晋阳秋》,从书名即可看出作者有意识地承袭《春秋》笔法,书写当时史事。而由于重在叙述史事,因此这些史书主要绍承《左传》之传统。《左传》在当时史学界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左传》固然是《春秋》三传之一,是经学,但同时亦是史学著作。《左传》相对于《穀梁》《公羊》二传来说,更具有史学特色。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6]叶梦得《春秋传序》指出:“左氏传事不传经,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7]可见,《左传》在具备经学这个身份的同时,更具有史学这个性质。六朝重视史学,《左传》又成为史家效法之对象,此即庾信辞赋用《左传》的史学背景。
如果说,上述经学与史学背景是外在因素的话,那么庾信本人对《左传》之爱好,即为内在因素。《周书·庾信传》指出:“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8]可见他的《左传》学修养极深,这就为其在进行辞赋创作时大量征引《左传》之语汇典故提供了学养基础。此外,庾信由南入北,与北方文人学者进行交流,亦有利于其对南北不同的《左传》学进行整合融通,由此深化自己的《左传》学。此即庾信辞赋用《左传》的内在因素。
总之,内外两种因素共同构成了庾信辞赋用《左传》之因缘。需要指出的是,外在因素,即学术文化背景是主要因素,内在因素也是在大的经史学术等外在因素的作用之下形成的。作为文学的辞赋,虽然起初依附于经史著作,然后逐渐自觉独立,但是从经史著作之中汲取养分,锤炼艺术手法,也是其谋求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取辞用义:庾赋用《左传》之方式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指出: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9]614-615
庾信辞赋继承了汉魏辞赋引用经史之范式传统,旁征博引儒家经典,展现出深厚的学术韵味。就其用《左传》之方式而言,亦不外乎取辞与用义二端,这亦是庾赋修辞手法之体现。
所谓取辞之法,即是取用《左传》之辞章,化为辞赋之语汇。如《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中有“玄鸟司历”[10]4,取辞于《左传·昭公十七年》:“玄鸟氏,司分者也。”[11]836“即同酆水之朝,更是岐山之会”[10]8,取辞于《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11]730又如《小园赋》中的“非夏日而可畏”[10]23,取辞于《左传·文公七年》:“赵盾,夏日之日也。”杜预注:“夏日可畏。”[11]4007而“尔乃窟室徘徊”[10]22,则取辞于《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11]682再如《哀江南赋》中的“华阳奔命,有去无归”[10]94,取辞于《左传·成公七年》:“巫臣自晋遗二子书,曰:‘……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子重奔命。……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11]443-444而“居笠毂而掌兵”[10]108,则取辞于《左传·宣公四年》:“射汰輈以贯笠毂。”[11]370由上述数例可见,庾信在赋中或直引、或化用、或兼用杜预之注,体现了不拘一格的取用手法,丰富了辞赋之辞章,增添了文学之意蕴。
所谓用义之法,即是援引《左传》事典,以阐发己意。如《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中的“唐成公之肃爽”[10]7,用义于《左传·定公三年》:“唐成公如楚,有两肃爽马,子常欲之,弗与,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与谋,请代先从者,许之。饮先従者酒,醉之,窃马而献之子常。子常归唐侯。”杜预注:“肃爽,骏马名。”孔颖达疏:“贾逵云:‘色如霜纨。’马融说:‘肃爽,鴈也。其羽如练,高首而修颈,马似之,天下稀有。’”[11]944作者用以形容北周皇室华林园骏马之罕有。
又如《小园赋》:“余有数亩敝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况乃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10]20此小段中三用《左传》典故。“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用义于《左传·昭公三年》:“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溢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11]723以阐明自己安贫乐道,不求名利,只愿隐居以避祸患之心态。“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用义于《左传·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11]191“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用义于《左传·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11]303此两处用典用意如何呢?倪璠注云:“言懿公好鹤,故鹤有乘轩,而黄鹤非有意于轮轩也。臧文不知,故祀爰居,而爰居本无情于钟鼓也。以喻魏、周强欲己仕,而己本无情于禄仕也。”[10]21可见,作者用《左传》典故之义,表明自己无意于功名利禄,但被迫仕周,情非得已,抒发哀怨忧伤之情。
再如《象戏赋》中的“白凤遥临,黄云高映,可以变俗移风,可以莅官行政”[10]69,用义于《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纪师而云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11]835-836倪璠注云:“《河图》曰:‘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万接,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皞氏也。’以白帝朱宣有凤瑞,故曰白凤。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云黄云。服虔曰:‘黄帝以云名官,中官为黄云。’”[10]70此处用《左传》之义以颂美北周朝廷能够绍承远古遗风,官制政令,颇具法度,彰显出盛世祥瑞之气象。
由上述诸例可见,庾信在赋中援引《左传》事典之义,或颂美当世,或抒发感情,增强了辞赋的思想深度和辞赋语言的寓意深度。而无论是取辞还是用义,都是庾信辞赋的修辞手法,是其进行文学创作时借鉴《左传》而采用的方式方法。作为方法来说,取辞与用义并无高下之别。但如果从义理层面来看,则用义远远高于取辞,因为取辞是停留于文辞表面的现象,而用义则是基于言辞表面,产生形而上之义理。因此,用义更是值得探究,而《春秋》本身即包含着大量的微言大义,《左传》虽然与《公羊》《穀梁》二传比起来重在传事,但于义理亦是十分重视。所以,庾信辞赋用《左传》之义是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的,这也是其用《左传》的主要意图所在。
三、借史喻今:庾赋用《左传》之目的
庾信辞赋援用《左传》之义,究其目的乃是借史喻今,以春秋史事来暗喻当下之事。刘勰《文心雕龙·宗经》在论及五经与文学之关系时指出:“《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9]22可见,《春秋》具有深刻幽邈的意旨,适合引用以抒己意。约略而言,庾信辞赋用《左传》之义借史喻今主要有两层内涵:一曰慨叹自己身世之苦,一曰阐发梁朝治乱兴亡之由。就实际情况来说,庾赋用《左传》主要集中体现在《哀江南赋》之中,而此赋又是庾信晚年最著名的长篇大赋,下文即以《哀江南赋》为例,探究庾信辞赋借史喻今之义。
感叹自己身世之苦者,如“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10]99一段用《左传》凡四处。“载书横阶”,用义于《左传·襄公九年》:“晋士庄子为载书,曰:‘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杜预注:‘载书,盟书。’”[11]528以喻自己出使乞援。“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用义于《左传·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郑,……郑共仲、侯羽军楚师,囚郧公钟仪,献诸晋。……晋人以钟仪归,囚诸军府。”[11]443又《左传·成公九年》: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従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11]448
倪璠注云:“言己本楚人,今来秦地,若南冠之囚矣。”[10]100可见,此处即是用楚囚钟仪南冠之典故以喻自己羁留北朝,若囚徒一般,但自己心系梁朝,可是却不能像钟仪那样能够重返故土,表达出深深的忧怨之情。“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用义于《左传·昭公十三年》:“同盟于平丘。……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归。”[11]804“叔鱼见季孙曰:‘昔鲋也得罪于晋君,自归于鲁君。微武子之赐,不至于今。虽获归骨于晋,犹子则肉之,敢不尽情?归子而不归,鲋也闻诸吏,将为子除馆于西河,其若之何?’”[11]814倪璠注云:“言己遂留于长安也。”[10]100可见此处用典以喻自己滞留长安而不得南归。“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用义于《左传·定公四年》:“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庚辰,吴入郢。……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11]951-953倪璠注云:“言使魏之后,江陵遭兵革之患,己无处求救也。”[10]100此处对申包胥求秦救楚之事典,作者反用其意,以喻自己无处求援,更添几分悲哀之情。
由上述可见,庾信辞赋援用《左传》之义以慨叹自己遭遇侯景之乱而孤苦微弱、孤立无援、羁留北地,遂产生无限凄凉沧桑之情感,典故的运用使得情感具有历史的厚度与长度,跨越了时空的畛域,将古人的悲苦移植到自己的辞赋中来,提高了辞赋语言的艺术表现力与张力。
讲论政治,阐明史事,总结治乱兴亡之由,自然是《春秋》及《左传》的撰写宗旨,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而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2]452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13]
由是观之,《春秋》重在以“春秋笔法”来宣讲“微言大义”,那么《左传》绍承《春秋》之旨,以史事与史论并重,臧否时事,以明治乱,其文辞语义自然为庾信辞赋所引用。如“晋郑靡依,鲁卫不睦。竞动天关,争回地轴。探雀鷇而未饱,待熊蹯而讵熟?乃有车侧郭门,筋悬庙屋。鬼同曹社之谋,人有秦庭之哭”[10]133一段,用《左传》凡六处。
“晋郑靡依,鲁卫不睦”,用义于《左传·隐公六年》中的“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11]71,以及《左传·定公六年》中的“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11]299。倪璠注云:“谓台城陷后,诸王不急讨贼,自相猜忌也。”[10]133“晋、郑、鲁、卫,皆周宗姬姓,以喻梁朝宗室,所以深责诸王也。”[10]134可见此处用晋、郑匡卫周室和鲁、卫的和睦来谴责梁朝宗室诸王在台城陷落之后,不顾梁武帝与社稷之安危,无意勤王,反而互相猜忌攻伐。“待熊蹯而讵熟?”用义于《左传·文公元年》:“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太子商臣。冬十月,(商臣)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杜预注:“熊掌难熟,冀久将有外救。”[11]299倪璠注:“谓武帝晏驾也。……《左传》云:‘宰夫胹熊蹯不熟。’知熊蹯为难熟之物也。”[10]134-135“乃有车侧郭门”,用义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氏侧庄公于北郭。丁亥,葬诸士孙之里,四翣,不跸,下车七乘,不以兵甲。”杜预注:“侧,瘗埋之,不殡于庙。”[11]619-620倪璠注云:“谓侯景恶葬武帝,又弑简文也。”[10]135以上两处用典,喻指武帝、简文帝相继遇害而死,且葬不以礼,以此谴责侯景之罪大恶极。“鬼同曹社之谋,人有秦庭之哭”,用义于《左传·哀公七年》:“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强,许之。旦而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我死,尔闻公孙强为政,必去之。’及曹伯阳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孙强好弋,获白雁,献之,且言田弋之说,说之。因访政事,大说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行。强言霸说于曹伯,曹伯従之,乃背晋而奸宋。宋人伐之,晋人不救。……遂灭曹。执曹伯及司城强以归,杀之。”[11]1011《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师,……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11]953倪璠注云:“二语伤梁亡,建邺为侯景所据也。按:‘秦庭之哭’与序内‘忽践秦庭’事同,而取意各异。彼言入长安,此言金陵失守,二帝遇害,己有乞援之志,故逃奔江陵矣。”[10]135由倪注可见,虽然此处与前文均用申包胥哭秦庭之典故,但取义不同,此两处之典故意在哀悼梁朝灭亡亦是劫数使然,然自己有赶赴江陵乞援于湘东王之志。
综上可见,庾信《哀江南赋》用《左传》之义,慨叹自己遭遇之苦,阐发梁朝治乱兴亡之由,抚今追昔,居今怀古,哀思怨愤、痛悼叹惋跃然纸上,极为形象。其成功地借史喻今、借古抒怀,使其辞赋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具有深远的感染力与影响力,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四、以情纬文,以赋载史:庾赋用《左传》之艺术价值
庾信辞赋用《左传》之语辞与事义,具有多维的意义价值。约略而言,主要有两层艺术价值,一曰以情纬文,情采并茂,富有情感的穿透力,展现出六朝辞赋的抒情特色;二曰以赋载史,使辞赋呈现出史化现象,具有诗史性质。此二者共同构成了庾信辞赋用《左传》之艺术价值。
齐梁时期的一代文宗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14]的文学创作思想,强调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认为文学创作重在抒发情感,以情感抒发的需要来选定表达形式、进行辞藻的润饰,将情感贯穿于全文之中,用形象传神的文辞来表达思想感情。与沈约观念一致,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提出了“为情造文”的观念,他说: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9]538
刘勰认为情理是经、是主,文辞是纬、是次,为情造文、以情纬文才是文章的正宗所在。吟咏情性,寄寓讽喻者即是为情而造文;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者即是为文而造情。反观庾信辞赋即是与诗人什篇取法一致,用《左传》语辞与事义,抒发情志,宣泄哀思,以明治乱,以情志为本,情理合一,绝非无病呻吟的“辞人赋颂”。庾信辞赋根据写作思路与文章内容的需要,借助征引《左传》之事典语义以抒发自身的黍离之哀、亡国之恨,以及对侯景乱梁的痛恨、对梁武帝晚年昏聩的扼腕痛惜,这正是典型的以情纬文、为文造情,将浓郁的悲苦之情寄寓于辞赋之中,而辞赋的语义又大量脱胎于《左传》。在辞赋文本中,辞赋语言与《左传》语义融合于一体,文学与史传巧妙地勾连起来,文义与经义也在不知不觉中水乳交融。换言之,庾信辞赋对《左传》的征用是根据内容情节的具体安排、情感抒发的实际需要来进行的。如此一来,即将情与文协调得极为恰当,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情理与词采的统一,对《左传》的征引化用不但没有妨碍辞赋本身情感思想的抒发表达,而且更加促进了情感理念的书写与宣泄。总的来说,艺术形式是用来润饰内容的,是为了充分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庾信辞赋用《左传》即是运用了用典使事这一艺术形式、表达手法,将自身的哀怨之情、乡关之思抒发得淋漓尽致,以此实现了辞赋作品的艺术价值。
自东汉中期以降,辞赋体制渐小,以抒情写志为主;及至南北朝,辞赋愈发缘情绮靡。庾信作为南北朝诗文辞赋的集大成者,巧用典故,以情志统领典故,将辞赋抒发情感的功能推向极致。是以,近人刘师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的《各家总论》中说:“《哀江南赋》等长篇用典虽多,而劲气足以举之。”[15]153又在《论文章之音节》中说:“庾子山等哀艳之文用典最多,而音节甚谐,其情文相生之致可涵泳得之,虽篇幅长而绝无堆砌之迹,……故知堆砌与运用不同,用典以我为主,能使之入化,堆砌则为其所囿,而滞涩不灵。”[15]16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入北之后所作的《哀江南赋》等赋作更是以情纬文的鲜明代表,是以《四库全书总目》云:“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徐)陵之所能及矣。张说诗曰:‘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其推挹甚至。”[16]清人魏谦升《赋品》“感兴”条云:“江关萧瑟,庾信伤神。《小园》《枯树》,哀江南春。”[17]436清人侯心斋《赋笔尾评》对庾信《小园赋》的评价为:“子山以出使见羁,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此赋已情见乎词矣。”[17]771对《哀江南赋》的评价是:“密丽典雅,纬以精思,驱以灏气,上结六代,下开三唐,不止子山集中压卷。”[17]771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说:“子山《哀江南赋》,则不名为赋,当视之为亡国大夫之血泪。”[18]50由上述评论可见,清代学者对庾信后期辞赋的抒情写志——抒发乡关故国之思,慨叹梁朝治乱之悲——极为推崇,认为其辞赋在六朝与隋唐之间处于承上启下之地位。庾信辞赋获得清人高度的评价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左传》事典语义的征引实现了以情纬文的艺术效果与价值。
除了以情纬文,以赋载史亦是庾信辞赋用《左传》的另一维意义价值。庾信辞赋征用“亦经亦史”的《左传》,不仅具有儒家经典的魅力与权威性,更是具有历史特质,呈现出史化现象,具有诗史性质。近人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中指出:“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19]可见,庾信辞赋用《左传》之古典以叙述当时之事,融合古典与今事之异同,将古典与今事进行跨越时空的组合,以古喻今、用古证今,使得辞赋具有古今玄幻之觉、历史沧桑之感,既是一种文学性质的自我书写,又是一种经史性质的《左传》注疏,从而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而究其实质,即是以赋载史,以赋写史,使赋史化,引《左传》事典对梁朝兴亡之史事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不但与正史相合,亦补正史之阙,体现出作者明晰的历史意识。这亦体现出南北朝辞赋发展之最终趋势与终极目标。
总之,庾信辞赋用《左传》语辞与事义主要体现出以情纬文与以赋载史二维意义价值,此二维艺术价值密切配合,构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性价值。庾信辞赋将自身个体的遭遇与梁朝的治乱兴亡交织在一起,将历史的深沉厚重与情感的浓郁强烈高度地结合在一起,使历史显得形象具体,使辞赋显得灵动典雅,铸就了辞赋雄浑刚健、文质合一、秾丽富赡的艺术风格,产生了极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以,将情感、史事、道理三者高度融合在一起,呈现出立体化之特色。虽大量用《左传》典故,但却不流于板滞、繁琐,相反却极为灵动、巧妙,呈现出极高的用典艺术,是以能够“穷南北之胜”。
五、余 论
杜甫在《咏怀古迹·其一》中称“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20]1499,在《戏为六绝句》中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20]898,在《春日忆李白》中说“清新庾开府”[20]52。可见在艺术方面一向追求新变的庾信之文章尤其得到杜甫的赞赏。庾信之所以在艺术上愈老愈好、清新密丽,能达到极高的造诣,与其辞赋之用典艺术是分不开的。可以说,用典是庾信辞赋最为耀眼的艺术技巧。而用典又是其本身才学的发挥,是其才学的集中体现。清人刘熙载《艺概·赋概》云:“赋兼才学。才,如《汉书·艺文志》论赋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传》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学,如扬雄谓‘能读赋千首,则善为之’。”[17]449可见,才学对于辞赋创作是极为重要的。《文心雕龙·事类》篇指出:
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以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9]615-616
刘勰强调才能是主宰,学问是辅助,有才能方可使得辞情充溢,有学问方能使得引证事义游刃有余,主宰之才与辅助之学相互配合,作品方能有文采而称雄天下。由是观之,庾信辞赋大量征用《左传》等经史典籍,抒情写志,托史喻义,使得辞赋显得格外厚重精深、博大幽邈、气势雄浑、绚烂多彩,正是其才与学的完美弥合之集中体现。因此,从用典艺术这个角度来探究庾信辞赋的艺术价值是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庾信及其辞赋,尤其是其晚年辞赋的艺术价值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