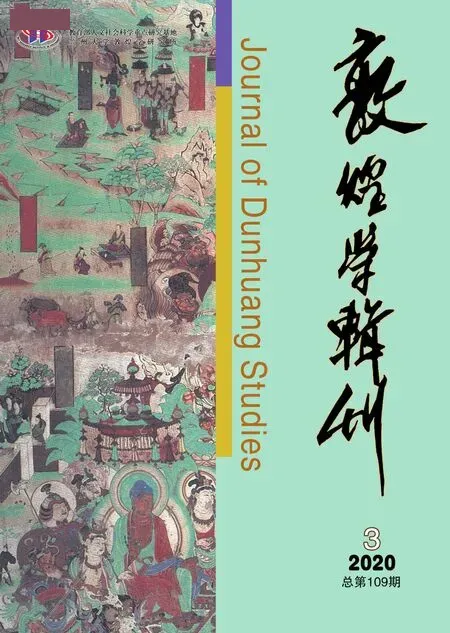敦煌《尔雅注》写本相关问题研究
许建平 王 鹤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8)
《尔雅》一书,其作者与成书时代今不可考,说法众多(1)卢国屏《〈尔雅〉与〈毛传〉之比较研究》列有13种说法,收入《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8编第10册,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第13-29页。,但为“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累积编写而成”(2)周祖谟《尔雅校笺·尔雅校笺序》,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页。,应是大多数学者能接受的说法。《汉书·艺文志》将《尔雅》附于六艺略孝经类后,《隋书·经籍志》附于经部论语类后,是皆以《尔雅》为释经之书。至《旧唐书·经籍志》,以《尔雅》为经部小学类之首,则已视为辞书矣。据《经典释文》载,为《尔雅》作注者有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三国魏孙炎以及晋郭璞、南朝梁沈旋,另有孙炎、郭璞、施干、谢峤、顾野王的注音。但在《宋史·艺文志》里,仅存郭璞《尔雅注》一种,其余皆亡佚。是到宋朝时,南北朝以前的《尔雅》著作仅存郭璞注本一种。
陆德明云:“《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辩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先儒多为亿必之说,乖盖阙之义,唯郭景纯洽闻强志,详悉古今,作《尔雅注》,为世所重,今依郭本为正。”(3)[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页。唐开成石经所收《尔雅》,虽是无注白文本,但其前有郭璞《尔雅序》,则所据即郭璞《尔雅注》。盖唐人平时所读者即郭璞所注《尔雅》。如唐玄宗时徐坚、康子元建议封禅之礼时,引郭璞《尔雅注》:“祭后方燔。”(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3《礼仪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95页。今本《尔雅·释天》“祭天曰燔柴”郭注:“既祭,积薪烧之。”“祭后方燔”盖用简明句子转写引用。唐肃宗宝应二年(763),谏议大夫黎干诘难润州别驾归崇敬及水部员外郎薛颀“配昊天于圆丘”之说,引用《尔雅·释天》“禘,大祭也”及郭璞注“禘,五年之大祭”(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1《礼仪志一》,第837页。。但到清代时,传世最早的经注兼备的郭璞注本《尔雅》是南宋刻本,距郭璞作注已有七八百年之久,故清人每疑所见郭璞注本有脱漏,今本已非郭氏原书,如王鸣盛云:“《尔雅》郭璞注,不知为何人删削。”(6)[清]王鸣盛《蛾术编》卷8《说录八》“郭注不全”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38页。王树枏云:“今世所行郭注,证以他书所引,多从删节,非足本也。”(7)[清]王树枏《尔雅郭注佚存补订》“弁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9册,第59页。周祖谟云:“这种说法是否可信,一直悬而未决。”(8)周祖谟《郭璞尔雅注与尔雅音义》,《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下册,第685页。即谓王氏所言缺少直接版本依据。
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了《尔雅》写本残卷,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第一位注意到《尔雅》写卷校勘价值的学者是董康,他在1927年1月9日的日记中说:“阅敦煌影片,内六朝本《尔雅》一卷,存《释天》八、《释地》九。首尾残缺,取与阮刻本互校,除别体字及注语尾增加助词从略外,可以是正刻本者约三十四条。”(9)董康《董康东游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页。董康所见者即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P.2661号郭璞《尔雅注》写卷。王重民于1935年4月21日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撰写《尔雅注》提要,将P.2661与P.3735缀合为一,并作校记数条(10)此提要后收入北平图书馆于1936年出版的《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1辑,收入黄永武主编《敦煌丛刊初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9册,第127-128页。又收入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4-75页。。P.2661+P.3735,存《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五篇,共161行。1938年1月26日,王重民撰P.3719《尔雅白文》提要(11)后收入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第74页。,作校记3条。此写卷存《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共84行。1946年,谏侯作《唐写本郭璞注〈尔雅〉校记》(12)谏侯《唐写本郭璞注〈尔雅〉校记》,《图书月刊》第1卷第5期,1946年,第1-6页。,在王重民的基础上,又对P.2661+P.3735作了数十条校记。周祖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撰《尔雅郭璞注古本跋》(13)后收入《问学集》,下册,第676-682页。,从经文与郭璞注两个方面对P.2661+P.3735的校勘价值作了说明(14)但周祖谟认为这是P.2661+P.3735+P.5522三个写卷缀合而成,不知其说何来。。1951年5月,陈邦怀据《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影印的P.2661+P.3735写卷,撰《敦煌写本丛残跋语》,其中“唐写本尔雅残卷跋”一条(15)陈邦怀《敦煌写本丛残跋语》,《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第3-4页,后收入氏著《一得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343-344页。,对写卷有所校勘。1984年,周祖谟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尔雅校笺》,在校录中充分吸收了P.3719与P.2661+P.3735的内容。1989年,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编辑部出版的《古文献研究》收入李丹禾《敦煌本〈尔雅〉残卷初识》,除了抄录王重民所撰的“提要”内容外,没有什么新的见解。1997年,许建平发表《读卷校经札记》一文(16)许建平《读卷校经札记》,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杭州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编《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7-83页。,其中有8条关于《尔雅》的札记,乃是P.2661+P.3735可纠今通行本之误者。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之“群经类尔雅之属”,对P.3719、S12073V(17)S.12073V存五残行,为白文本《释言》。、P.2661+P.3735作了全面校录。李倩的《敦煌本〈尔雅〉P.3719白文写卷校录疏证》(18)李倩《敦煌本〈尔雅〉P.3719白文写卷校录疏证》,《燕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28-31页。,谓对于P.3719“至今未见详尽校理”,是未见《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也;又以P.2661+P.3735+P.5522为一卷之裂,则承周祖谟之误。2016年,刘芳硕士学位论文《〈集韵〉引〈尔雅〉研究》(19)刘芳《〈集韵〉引〈尔雅〉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第21-31页。第三部分将《集韵》所引《尔雅》与敦煌本作了比较,并对有异文处作了校勘。2018年,瞿林江发表《敦煌〈尔雅郭注〉写本残卷考》(后简称“瞿文”)(20)瞿林江《敦煌〈尔雅郭注〉写本残卷考》,《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20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228-249页。,从写本钞写年代、用字、注音、校勘价值四个方面对P.2661+P.3735作了研究,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此写卷最全面的研究。
本文拟在诸家研究的基础上,再对诸家未及或尚可深入的问题作一番考察。
一、从题记看《尔雅注》写本与科举考试的关系
《唐六典》卷2《尚书吏部》“考功员外郎”:
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中、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21)[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5页。
唐玄宗开元八年(720)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璀上奏:
《三礼》、《三传》、《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道不坠。……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2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55页。
是唐代以三礼、三传、《周易》《尚书》《毛诗》为九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而《孝经》《论语》则需兼习。而《尔雅》纳入考试内容,则迟至天宝元年(742)。因为朝廷设立道举,以《道德经》作为必试科目,明经、进士二科考试就以《尔雅》代替《道德经》,“天宝元年,明经、进士习《尔雅》”(2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24《礼仪志四》,第921页。。但这一规定只延续了四十几年,《唐会要》记载:
贞元元年四月十一日敕:比来所习《尔雅》,多是鸟兽草木之名,无益理道,自今已后,宜令习老子《道德经》,以代《尔雅》。(24)[宋]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374页。
到贞元十二年(796)三月时,国子司业裴肃上奏:
《尔雅》博通诂训,纲维六经,为文字之楷范,作诗人之兴咏,备详六亲九族之礼,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今古习传,儒林遵范,其老子是圣人元(25)“元”当作“玄”,讳改字。微之言,非经典通明之旨,为举人所习之书,伏恐稍乖本义,伏请依前加《尔雅》。奉敕。宜准天宝元年四月三日勅处分。(26)[宋]王溥《唐会要》,第1374页。
是《尔雅》与《论语》《孝经》一样成为科举考试必考科目的时间是在天宝元年到贞元元年(785)以及贞元十二年以后,在唐朝290年的历史中,只占一半,而且在中后期。故赵和平教授说:“唐代前期,《尔雅》未成为儒家经典,敦煌本所存不多,不足为奇。”(27)赵和平《敦煌儒家经籍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第61页。现在所见敦煌写本的九经中,以《尔雅》写本所存最少,可以说反映了其在科举考试中之地位。
P.2661+P.3735号写卷,因为未见避讳字,董康、王重民皆认为是六朝写本(28)董康《董康东游日记》,第12页;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第74页。。写卷尾题“尔雅卷中”,后有题记五条:
大历九年二月廿七日书主尹朝宗书记
□别去不分君□意
大历年月日尹宗记
天宝八载八月廿九日写
张真乾元二年十月十四日略□乃知时所重亦不妄也(29)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9页。
从字体来看,这五条题记分别为四人所写,瞿文已有详辨。时间最早的题记是“天宝八载”(749)条,周祖谟因而认为是钞书者所记。但这条题记的字体与正文完全不同,不可能是一人所书,而且不能据“写”字即判定其为书写正文者。如P.2643《尚书》写卷卷末题记“乾元二年正月廿六日义学生王老子写了故记之也”,题记与正文文字的用笔完全不同,说明此题记非抄写者所为。今此卷“天宝八载”条题记的抄写者,应非正文书手,其所以用“写”字,盖写卷中某些旁注改字及增字出于其手。天宝八载时,《尔雅》已作为明经、进士的必考科目,所以张真的题记说“乃知时所重,亦不妄也”。唐时书籍获取不易,常有一件写卷前后递藏,多人使用,如P.2681+P.2618《论语集解》写卷,其抄写者为“沙州灵图寺上座随军弟子索庭珍”,但又有“乾符三年学士张喜进念”、“沙□敦煌县归义□学士张喜进”、“维大唐乾符三年三月廿四日沙州燉煌县归义军学士张喜进书记之也”的题记,说明索庭珍的抄本后来归张喜进所有,这与今之宋元善本钤有历代收藏者之藏书印的情况相似。张真以后,《尔雅》写卷流传到了尹朝宗手上,尹氏在写卷正文之后书“尒雅卷中”四字,并书题记一行。第三条题记“大历年月日尹宗记”挤在“□别去不分君□意”与“天宝八载八月廿九日写”之间,应是尹朝宗之涂鸦。至于“□别去不分君□意”为何人所书,则不知也,或许是尹氏之前的某位持有者所书。王重民谓卷末题记“并是阅者所题,不得据以定为唐写本也”(30)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第74页。,王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为法藏敦煌写卷编目,有机会亲自观摩写本原件,并缀合此两号为一件,其说较为可信。而且据题记所记时间,天宝、乾元、大历,均在天宝元年与贞元元年朝廷下令《尔雅》作为明经、进士考试必考科目的时期内,故束之高阁的一百多年前的《尔雅》写本又被翻出来阅读以应付考试了。
二、《尔雅》写本中的旁注音

《尔雅音图》一书,清曾燠在《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中认为其音与《经典释文》所载郭音多不合,而其卷数正与后蜀毋昭裔所作《尔雅音略》相同,应即毋氏之《尔雅音略》。冯蒸从音韵角度考证,认为此书的作者应该就是毋昭裔;冯蒸还通过《尔雅音图》与《尔雅音释》注音用字异同的分析与两书之音韵特点的比较,认为《尔雅音图》的编撰早于《尔雅音释》,而《音释》的注音多有承袭自《音图》的(33)冯蒸《〈尔雅音图〉与〈尔雅音释〉注音异同说略》,《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黄御虎通过对陆德明《尔雅音义》与《尔雅音释》注音的比较,发现《尔雅音释》有近51%的注音抄自《尔雅音义》(34)黄御虎《〈尔雅音释〉音切的来源》,《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9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31页。。

写本旁注音、《尔雅音义》《尔雅音释》《尔雅音图》注音对照表(35)《尔雅》经注及旁注音据IDP网站的高清图片(《尔雅》经注中的被注音字加黑),《尔雅音义》据中华书局影印通志堂本《经典释文》(1983年),《尔雅音释》据《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尔雅》(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每卷后所附版本,《尔雅音图》据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

15谷者,溦亡悲亡悲反又音微眉音湄16鋭而高,峤桥渠骄反郭又音骄乔音乔17卑而大,户音户音魁18小而众,岿丘轨丘轨反丘鬼19小山岌大山,峘丸胡官反一音袁又音恒桓音桓20谓山峯头巉嵒牛今五咸反21不知堂密之有美枞七庸七容反序号尔雅经注旁注音尔雅音义尔雅音释尔雅音图22峦,山嶞他果汤果反汤果23左右有岸,厒口荅口阁反口合音湿24小山别大山碑列彼列反彼列25多小石,磝五角五交郭五交五角二反苦交音尧26多礓砾居羊居羊反27多大石,礐苦角胡角又觉郭苦角反又户角反殻音殻28泉一见一否为瀸胡燕贤遍反现音现29泉一见一否为瀸子兼息廉反又子廉反纤音纤30井一有水一无水为瀱汋□例①居例反孙许废反计音计31井一有水一无水为瀱汋野斫仕捉反又上若反仕捉音卓32滥泉正出舰胡览反33氿泉穴出轨音轨音轨34湀辟,流川揆郭巨癸反孙苦穴反字林音圭揆音揆

35过辨,回川片普见反片音片36潬,沙出徒坦徒坦反但音但37瀵,大出尾下匹问敷问反义或方问反粪音粪38水醮曰厬轨音轨轨音轨39汶为灛昌善昌善反阐音谄40濄为洵古和谢古禾反又乌禾反乌禾音过41直波为泾古定俓,古定反字或作径②42言泾涏也徒丁侹,他定反又徒顶反序号尔雅经注旁注音尔雅音义尔雅音释尔雅音图43并两舩蒲茗步丁反44小沚曰坻直基直基反池音池45汩漱沙壤于笔于笔反46简、絜、钩般胡结户结反
1.写卷旁注音与相关音义书的关系
(1)旁注音与《尔雅音义》的关系
写卷46个旁注音,其中第2、3、7、8、14、15、17、18、26、33、36、38、39、41、44、45共16个注音与《经典释文·尔雅音义》中陆德明的注音完全相同。
其中第3个是为《释天》“风而雨土为霾”句之“雨”注音,写卷与《释文》均音“芋”。然《诗·邶风·终风》“终风且霾”毛传“霾,雨土也”句,《释文》音“雨”为“于付反”。作去声读之“雨”,《释文》出注37次,其余36次注音皆为“于付反”,唯此一处用直音“芋”。则此“音芋”应该是有所承袭,而恰与写卷之注音同。
又第7个是为《释天》“夏祭曰礿”句之“礿”注音,写卷与《释文》均音“余弱”。经籍“礿”或写作“禴”,《说文》有“礿”无“禴”,“禴”为后起换旁异体字。《释文》“禴”出注11次、“礿”7次,或音羊灼反,或音余若反,或音药,唯此一处音“余弱反”,而恰与写卷之注音同,《释文》此音亦应是承袭而来。
以上两条注音,虽然在《释文》的注音中属于首音(首音就是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标准音(36)邵荣芬《经典释文音系》,台北:学海出版社,1995年,第5页。)。但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确定,这不是陆德明自己制造的反切,也不是陆德明以前比较流行的那些反切(37)《经典释文》的首音,往往不标主名,但并非说这些反切都是陆德明自己所制,其实很多反切是摘自其它音书,其《自叙》里说:“若典籍常用,会理合时,便即遵承,标之于首。”,而是承袭自特定音书。
第14个是为《释丘》“涘为厓”之“涘”注音,《释文》注云:“旧音仕。”这一条陆德明说明了是从其它音书摘抄而来,而写卷旁注音为“仕”,正与《释文》所引旧音相同。
(2)旁注音与《尔雅音图》《尔雅音释》的关系
写卷旁注音与《尔雅音图》注音相同者有第2、8、33、34、35、38共6个,与《尔雅音释》注音相同者有第2、8、34、35、38共5个,与此两书注音均相同者有第3、8、34、35、38共5个。
从以上数据可见,写卷旁注音与《尔雅音义》、《尔雅音图》、《尔雅音释》相同之注音,应是有相同之来源。尤其是与《尔雅音义》相比,其中一部分注音极有可能即转抄自《尔雅音义》。第12、25、27三个旁注音与《尔雅音义》引郭璞《尔雅音》相同,瞿文已谈到,认为写本注音者可能参考了《尔雅音》。至于这些旁注音中,还有哪些是来自郭璞音,由于郭璞《尔雅音》已佚,我们已无从知道。
2.旁注音中的特殊音切
旁注音中有几个音注与《尔雅音义》、《广韵》的读音不同,考之如下:

(2)第9个“乌侯”是《释地》“秦有杨陓”之“陓”的旁注音。《广韵》“陓”音忆俱切,《释文》云:“陓,孙於于反,郭乌花反。”《释文》所引孙炎之“於于反”,即《广韵》之忆俱切。周祖谟《尔雅校笺》云:“《御览》卷七十二引亦作‘纡,音讴’。‘音讴’盖亦郭注原文。唐写本‘陓’字旁注‘乌侯’,即郭璞《音义》之音,‘乌侯反’与‘音讴’正合。《释文》云:‘郭乌花反’,与唐本所注音不同。”(42)周祖谟《尔雅校笺》,第273页。
案:《太平御览》卷72《地部三七·薮》下引《尔雅》“秦有杨纡”,小注:“音讴,今在扶风汧县西也。”(43)[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38页。
臧琳《经义杂记》卷8“秦有杨纡”条云:
《周礼·职方氏》“冀州,其泽薮曰杨纡”注:“杨纡,所在未闻。”《淮南子·地形》九薮:“秦之阳纡。”高注:“阳纡,盖在冯翊池阳,一名具圃。”又《修务》“禹之为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注:“阳盱河,盖在秦地。”《说文·艸部》:“薮,大泽也。九州岛之薮,冀有杨纡。”《竹书纪年》:“周穆王十三年春,祭公帅师从王西征,次于阳纡。”又《风俗通·山泽》引《尔雅》“秦有阳纡”,刘昭注《续汉·郡国志》引《尔雅》“秦有杨纡”。则《释地》旧本皆作“纡”字,陆德明所见本尚然。郭璞改为“陓”,音“乌花反”,陆氏据之,反以作“纡”为非。不知孙叔然“於于反”,亦作“纡”不作“陓”也。考《吕氏春秋·有始览》九薮:“秦之阳华。”高注:“阳华在凤翔,或曰在华阴西。”华、陓音相近,盖郭氏或有所本。”(44)[清]阮元编《清经解》,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1册,第838页。
郝懿行《尔雅义疏》云:“《尔雅释文》:‘陓,郭乌花反。’则与‘华’音相近,似杨陓即阳华。”(45)[清]郝懿行《尔雅义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14页。
俞樾《群经平议》“秦有杨陓”条云:“即经字亦当从《吕氏》作‘阳华’。《周礼》之杨纡,《尔雅》之杨陓,并‘阳华’之假字。《释文》曰:‘陓,郭乌花反。’则‘陓’与‘华’音固相近矣。”(46)[清]俞樾《群经平议》,《春在堂全书》,南京:凤凰出版社,1988年,第1册,第575页。
王书辉云:“郭音‘乌花反’,疑是读‘陓’为‘华’……惟《广韵》麻韵‘华’一音‘户花切’,一音‘呼瓜切’,均与郭璞音‘乌花反’声纽略异。……《御览》所引注文虽与今本郭注近同,惟并未明云何氏之注。周氏以‘音讴’二字为郭注原文,又以唐写本‘陓’字旁注‘乌侯’为郭璞《音义》之音,均无确证,今暂存疑。”(47)王书辉《两晋南北朝〈尔雅〉著述佚籍辑考》(上),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第161页。
诸家皆以郭音“乌花反”,乃是读“华”之音,然王书辉谓其声纽有异,盖尚有疑也。
通志堂本《释文》“郭乌花反”,宋元递修本作“乌俟反”(48)[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下册,第1649页。。瞿文因而谓写卷“乌侯”之“侯”字模糊不清,疑为“俟”之讹(第237页脚注⑦),其意盖谓写卷应是作“乌俟”,今诸家误为“乌侯”。其实写卷此字左半“亻”部及右边上半是清楚的,只是右边下半模糊,而“俟”与“侯”的区别就在右边上半。《仪礼·既夕礼》“属纩以俟绝气”胡培翚正义:“俟字,据郑注当为候之误,二字形相似故也。”(49)[清]胡培翚《仪礼正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册,第1918页。侯、候二字古常混用也。所以此字录为“侯”是没有问题的。“乌俟”之音韵地位为影纽上声止韵,《广韵》小韵“於拟切”、《集韵》小韵“隐已切”下皆无“陓”或“污”字,而且俟、侯形近,宋元递修本之“乌俟反”,当为“乌侯反”之误。通志堂本作“乌花反”者,疑“花”亦“侯”之误。《集韵·模韵》小韵“汪胡切”下有洿、污、陓、乌等字,“陓”下注云:“杨陓,秦薮名。”(50)[宋]丁度《集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2页。是“陓”亦有“乌”音也,此即《尔雅音图》所以音“乌”也。
写卷旁注音“乌侯”,乃是读“纡”为“讴”音。郭璞注中有音,其体例王国维已详言之(51)王国维《书尔雅郭注后》,收入氏著《观堂集林》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6-233页。。然观宋本《尔雅》,注中之音皆在释义后,未见有在释义前者。此《太平御览》所引之音,乃在释义前,当非郭璞之音。写卷旁注“乌侯”,所音即同《御览》所据之《尔雅》文本,其“音讴”应是后人所羼入。
三、《尔雅》写本的校勘价值
关于《尔雅》写本在校勘上的价值,学者已多言之,这里再举两例前人考证未精者。
1.《释天》“济谓之霁”郭注:“今南阳人呼雨止为霁。音荠。”
阮元《尔雅注疏校勘记》云:“雪牕本同。注疏本删下二字。”(57)刘玉才主编《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第11册,第141页。卢文弨《尔雅音义考证》云:“宋刻郭注本有‘音荠’二字,俗本多删。”(58)[清]卢文弨《经典释文考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册,第353页。P.2661+P.3735“音荠”下有“菜也”二字。陈邦怀《敦煌写本丛残跋语》云:“或疑‘菜’为衍文。余曰:景纯举物名以注音不仅见于此。《方言》注中则数见之。”(59)陈邦怀《敦煌写本丛残跋语》,第3页。
案:其实不必以《方言注》为例,郭璞《尔雅注》中即多有此类注音方式,如:《释诂》“嗟、咨,也”郭注:“今河北人云叹。音兔罝。”谓河北人读“”如“兔罝”之“罝”。《释草》“出隧,蘧蔬”郭注:“今江东啖之,甜滑。音毡氍。”谓江东人读“蘧蔬”为“毡氍”之“氍”。《释草》“莞,苻蓠。其上,蒚”郭注:“今江东谓之苻蓠,西方亦名蒲中茎为蒚,用之为席。音羽翮。”谓西方人读“蒚”为“羽翮”之“翮”。《释鱼》“鰝,大鰕”郭注:“今青州呼鰕鱼为鰝。音酆鄗。”谓青州人“鰝”读作“酆鄗”之“鄗”。《释鸟》“鴢,头鵁”郭注:“江东谓之鱼鵁。音髐箭。”谓江东人读“鵁”为“髐箭”之“髐”。写本作“音荠菜也”,谓南阳人读“霁”为“荠菜”之“荠”也。准以以上诸例,写本之“也”当是衍文。而宋本无“菜”字者,应是不知郭璞注之体例而删。至于以后版本又删“音荠”二字者,则以为郭璞有《尔雅音》,因而注中不应有音而遂删之。其实,作《尔雅音》是一回事,在注释中随文作音又是另一回事。郭璞《尔雅音》,又叫《尔雅音义》,可见其注音之书也有义(60)周祖谟《郭璞尔雅注与尔雅音义》,《问学集》,下册,第683-686页。。是郭璞作《尔雅注》,其释义之中兼有注音;其作《尔雅音》,注音之时也兼释义,故不可以其书名而臆断也。
2.《释丘》:“宛中,宛丘。”郭注:“宛谓中央隆高。”又“丘背有丘为负丘”郭注:“此解宛丘中央隆峻,状如负一丘于背上。”
邵晋涵《尔雅正义》释经云:“《说文》云:‘陚,丘名。’武、负声相近,陚丘即负丘也。”又释注云:“丘背有丘,疑于‘后高陵丘’,郭以丘背即丘上也,故定为重释宛丘之义。”(61)[清]邵晋涵《尔雅正义》卷11,乾隆戊申(1788)邵氏家塾本,第7B叶。《经义述闻》曰:“此曲为之说也。‘后高陵邱’(62)此以下作“邱”者,即孔丘之“丘”的避讳改字。,谓邱形后高而前卑耳,非邱背有邱之谓也。且上言‘邱背有邱’,下言‘邱上有邱’,则邱背之非邱上明矣。邵又曰:‘《说文》云:陚,丘名。武、负声相近,陚丘即负丘也。’尤为皮傅之说。”故王氏曰:“‘邱背有邱’者,谓邱之后又有一邱,如背有所负然,故曰负邱,负亦背也。邱背有邱为负邱,宛中为宛邱,二者迥不相涉。郭不解负字之义,而以为宛邱中央隆峻,状如负一邱于背上,遂与上文之‘宛中宛邱’,下文之‘邱上有邱为宛邱’,混为一义,其失甚矣。”(63)[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57页。郝懿行云:“‘丘背有丘’者,背犹北也。言丘之北复有一丘,若背负然,因名负丘。古读负若陪,二字义相通借。陪训贰也、重也,皆与丘背有丘义合。此自别为一丘,郭意欲为‘宛丘’作解,盖失之矣。”(64)[清]郝懿行《尔雅义疏》,第862页。徐朝华《尔雅今注》注云:“背,后面。”(65)徐朝华《尔雅今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31页。胡奇光、方环海《尔雅译注》把“丘背有丘为负丘”译为“土山背面还有一个土山的称为负丘。”(66)胡奇光、方环海《尔雅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4页。皆从王氏《述闻》也。
P.2661+P.3735“丘背有丘为负丘”作“丘背负丘”,无“有丘为”三字。王重民云:“丘背负丘,今本作‘丘背有丘为负丘’,郭注云:‘此解宛丘中央隆峻,状如负一丘于背上’,郝懿行《义疏》云:‘此自别为一丘,郭意欲为宛丘作解,盖失之矣。’今按郝意,盖不知郭本经文有误,因疑其失;下云‘丘上有丘为宛丘’,正为上之经文作注,故郭注又云‘嫌人不了,故重晓之’也。”(67)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第75页。谏侯《唐写本郭璞注尔雅校记》云:“王重民先生解释得非常好。……这正是千年未宣之秘,不然不但‘嫌人不了故重晓之’二句无所属,试问,‘丘背’‘丘上’亦有何分别处,其中毛病是出在中间隔了四句,后人读‘丘背负丘’不解,于是添了‘有丘为’三字,这里一定是有了脱简,连郭璞也没有见到的。”(68)谏侯《唐写本郭璞注尔雅校记》,第2页。
案:笔者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的校勘记中已对此提出看法,只是没有作详细论证。今尝试论述如下。“宛中宛丘”与“丘背负丘”乃是一句,不可分为两句,“丘背负丘”是解释“宛丘”的,细味郭注,明白无误。“宛谓中央隆高也”释“宛”字之义,后“此解宛丘中央隆峻,状如负一丘于背上也”方是释“宛丘”也。丘背负丘,谓宛丘之形如丘背上又负了一丘,这句不是出“负丘”之丘名,乃是释“宛丘”之形的。由于后人以为《释丘》均释丘名,以为“负丘”亦是丘名,故于“丘背”下添“有丘为”三字,遂使诸家均误。查《诗·陈风·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毛传:“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孔疏:“《释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为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谓中央隆峻,状如负一丘矣。(69)“负”字原无,据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刘玉才主编《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第2册,第153页)补。’为丘之宛中,中央高峻,与此传正反。”(70)[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7之一,《十三经注疏》本,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250页。《尔雅》中“宛丘,谓中央隆峻,状如负一丘矣”乃“丘背有丘为负丘”之注文,而孔氏用来释“宛中,宛丘”句,是孔氏以“丘背有丘为负丘”与“宛中,宛丘”为一条,非释两丘。看来孔氏所见本尚未衍“有丘为”,故他引“丘背负丘”之注以释“宛丘”也。后人不知经文有衍文,反而对孔氏颖达以“中央隆峻,状如负一丘矣”释“宛丘”表示怀疑,王树枏《尔雅郭注佚存补订》以为孔所引郭注有脱漏(71)[清]王树枏《尔雅郭注佚存补订》,第162页。。薛芹以为“状如负一丘矣”为孔颖达自己之言:“《正义》在引文之外用‘状如负一丘矣’进一步说明了‘宛丘’的形状,是阐述更丰富、具体。”(72)薛芹《〈毛诗正义〉引〈尔雅〉与〈尔雅注〉考辨》,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5页。其实“中央隆峻,状如负一丘矣”即孔氏引郭注“中央隆峻,状如负一丘于背上”句,只不过古人引书不严格,取其大意而已。
四、结语
本文首先对一百年来敦煌《尔雅》写本的研究状况作了一个学术史梳理。接着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P.2661+P.3735《尔雅注》写卷从三个方面作了探索。
一是把写卷卷末题记的时间与唐朝以《尔雅》作为明经、进士考试必考科目的时间相比较,发现写卷五条题记的前后时间正与朝廷下令《尔雅》作为考试科目的时间相吻合,因而认为这是一件因科考需要而被举子重新拣起来以供阅读应试的六朝时期的写本。
二是将写卷46个旁注音与《经典释文·尔雅音义》《尔雅音释》《尔雅音图》进行比较,认为它们的相同注音有共同来源,而且其中一部分注音可能即抄自《经典释文·尔雅音义》。又对其中三条特殊注音作了详细考辨,分析其音之特点及来历。
第三部分是关于写卷校勘价值的说明,关于校勘价值,前人的研究已多所论及,本文又举了两条例子,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又对其异文作了更详尽的考定。第一条对郭璞注中举物名以注音的体例作了说明,第二条对《尔雅·释丘》中一条因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人为造成的增字情况作了考订,分析其致误之由,以见写本之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