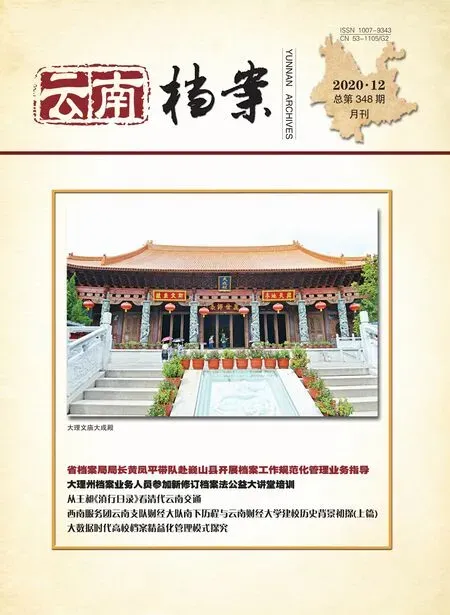从王昶《滇行日录》看清代云南交通
■ 黄建红
一、《滇行日录》的创作背景
与同时期的官员学者相比,王昶的人生阅历显得尤为丰富,为官期间,他先后从军云南、四川,参与过清缅战争与大小金川之役,宦途遍及北京、江西、直隶、陕西、云南、江西等地,“两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兴桓而北,以至往来青、徐、兖、豫、吴、楚、燕、赵之镜。”(《金石萃编自序》)。王昶博闻强识,著述丰硕,堪称“通儒”,“邃于经,健于文,富于诗词,精于考证,达于政治韬略,研穷于性理。”(《王兰泉侍郎事略》)。每到一地,他都会详细记录当地的山川途程,撰写详实的笔记。王昶去世后,后人将他生前撰写的八种纪程作品刊印成书,取名《春融堂杂记》。《滇行日录》为《杂记》中的开篇之作,是研究清朝云南交通的重要档案资料。
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两淮盐运使提引案发,王昶与好友赵文哲因“言语不密”被罢职,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王昶自幼家贫,发奋读书,投身科举,18 岁即取得院试第一的成绩,34 岁时被乾隆帝召试为一等第一,授内阁中书舍人。王昶仕途一路顺畅,提引案发前身居刑部江西司郎中,入直清王朝的核心权力机枢军机处。
一夕之间,从朝廷重臣变为戴罪之身的白衣,王昶内心充满失落与悔恨。在写给同因提引案被革职的挚友赵文哲的诗歌中,王昶对自己的官场生涯进行了深刻反思,甚至对自己进入仕途的选择作了否定:“前生出家人,一念逐仕宦。天将警其贪,遂使历忧患。”(《送升之回腾越》)。罢职对王昶的打击是巨大的,从军云南期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表露了对之前平顺人生的深刻反思:“始知违悖道理,不可擢发数过,益省益多,由此益愧且恨。”
王昶被革职时,在帝国的西南边陲,清廷与缅甸的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兵部尚书阿桂时任定边右副将军征讨缅甸,阿桂素知王昶学识丰富、办事干练,于是延请王昶为幕僚,随军赴云南。对王昶而言,前途虽然凶险,却也是一次戴罪立功的良机,宦途衰荣起伏不定,戴罪官员通过立功重新进入仕途的例子比比皆是。再则,作为文人,他一定能意识到,从军边塞的经历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学术生涯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王昶的云南行程及《滇行日录》内容
王昶一行于1768年农历十月初十日从京都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而入云南,于次年三月初五日抵达腾越(今云南腾冲)。行军途中,王昶逐日写日记记载每日的行程,对沿途的水陆地形、山川风貌和交通状况也详细记录,整理为《滇行日录》。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如此概述自己的旅途及写作过程:“途次所历,为驿一百二十余,为里九千一百余,为日一百有二,有所见辄书之,以志其略。”《楚雄县志》也有记述可以作为佐证:“王昶佐将军幕,自京自老官屯,所遇靡不刻划其形状。”
《滇行日录》对日程的记述十分详尽,对路线及所经驿站也有清晰的记载,为便于直观地介绍其行程,笔者根据《滇行日录》的记述将王昶一行在云南的日程和行程梳理如下:

时 间 天 气 途径地 宿 地 行程及交通状况十七日 青华海 永昌府 自官坡行十余里至青华海。正月十八日至三月初一日 永昌府三月初二日 微雨旋霁,颇蒸热 孔雀庙、蒲缥 萧公庙 出永昌府南门四十里,过孔雀庙,又三十里至蒲缥。初三日 黎明微雨,蒸热殊甚观音寺、冷水箐、打板坡、干沟、潞江 八湾自萧公庙行二十里至观音寺,又十里至冷水箐,又十里至打板坡,又十里过干沟,过潞江十五里,至八湾。行十里至蒲蛮哨,又十里至太平坡、又十五里至分水岭,入腾越州界,又三十里至龙江桥,又二十余里至橄榄坡。初五日 芹菜塘 腾越城 自橄榄坡行三十里至芹菜塘,又三十里入腾越城。初四日 雷雨高黎贡山、蒲蛮哨、太平坡、分水岭、龙江桥橄榄坡
王昶一行每天的行程经常超过一百余里,有时甚至达到一百八十余里,其效率远非寻常行旅所能比。当时,清朝与缅甸的战事正紧,王昶一行的整个行程均属于军务,对每天的行程有严格要求,民夫、轿马充足,沿途物资供应及食宿也有充分保障。云南山高谷深,较之中原地区,路况要差许多,王昶一行的通行效率,充分体现了清代云南邮驿体系的完备。
三、王昶与云南的深厚渊源
王昶的人生与云南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因罪从军云南,在军中因勤勉得力、屡立功劳而恢复了官员身份,之后虽历尽艰险,但官运畅通,还担任过云南布政使。除了《滇行日录》外,王昶还在其他著述中对云南的交通、地理进行过记述,如《征缅纪闻》《蜀檄纪闻》《雪鸿再录》,它们同样是研究云南交通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
王昶赴从军前已被罢职,对他而言,云南之行是一场戴罪立功的考验。乾隆三十六年,尚书温福代阿桂为总督,王昶仍在军中效力。当时,四川小金川发生叛乱,而清缅战争已近尾声,朝廷派遣温福由云南赶赴四川督战平乱,温福向朝廷请旨,以王昶熟悉军务及边情为由请求携王昶同往四川。王昶一行于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自云南保山启程,向东经赵州、楚雄、宣威等地进入贵州,再经威宁、毕节,北上赤水河进入四川,赶赴战争发生地小金川。王昶在《蜀檄纪闻》的开篇记述了由云南保山至四川成都、金川的行程。当时,从保山到四川有偏僻小路可以通行,但道路崎岖狭窄,沿途人烟稀少,食宿及征调民夫、牲畜十分不便,不利于行军。温福、王昶一行于是选择绕道贵州威宁、毕节进入四川,这条路是历史悠久的乌蒙乌撒道。在《蜀檄纪闻》中,王昶记述了从云南保山经乌蒙乌撒道进入四川成都的途程:途中共计55 个驿站,累计耗时21 天。王昶对此次行程的记述详尽而真实,是研究清代西南交通地理的重要史料。
王昶在军中颇有建树,乾隆三十六年十月,朝廷下旨将他由“革职郎中”擢升吏部考功司主事,从军的第五年,王昶升为员外郎。乾隆四十一年,时年53 岁的王昶已在军中效力九年,朝廷授他为鸿胪寺卿。乾隆五十一年,王昶到云南任布政使,有感于云南铜政的重要性,他编著了《云南铜政全书》。
乾隆五十三年,王昶由云南布政使调任江西布政使,原因是朝廷“以云南路远,量移近省。”三月初二日,王昶以验收腾越城工赴迤西,二十九日还至镇南州,待六月初一日新任李君至,初五日交印,遂以十二日自云南启行,进京述职,途经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王昶在《雪鸿再录》中记述了这段经历,与《滇行日录》相似,《雪鸿再录》也是一部纪程之作,该纪程始于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二日,终于是年十月二十八日。
四、王昶对云南交通地理的认知
王昶集官员、学者、文人、诗人等身份为一身,他从军、从政云南期间,除了创作或编著《滇行日录》《雪鸿再录》《云南铜政全书》等偏重纪实性的著作外,还创作了大量诗歌,这些诗歌虽然是文学作品,但都是王昶的亲身经历与体验,比较写实,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云南交通地理的认识。
在王昶的认知里,云南是偏远的瘴疠之乡,他笔下的云南充斥着危险、蛮荒的气息。“瘴疠”是王昶关于云南的诗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意象之一,如“炎风瘴雨炫蛮花”“腐肠古所云,引瘴实其理”“瘴岭千重绝域邻”“朝蒸炎烟暮毒雾,瘴气如虹乱花絮”“瘴雾炎云极望同”“天知炎瘴无由著”“瘴疠困徒旅”“毒泉兼热瘴”“人传瘴疠频”“瘴云杀气漫空黑”“炎陬瘴疠蒸”“瘴烟入夜缘壕起”“日晚黄茅蒸雾起”“念我经时涉炎徼,要使毒瘴春来空”“烽火频年历瘴乡”。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于中原而言,云南一直是边僻之地,位于滇西的保山则更加边远。清代,从北京到云南保山的路途虽然漫长而险阻,但却是畅通无阻的,而且沿途都设置有驿站。出发不久,王昶在写给友人的诗歌中记述了从北京到保山的路程:“邮签一百廿程遥”,这句诗后,作者自注:自京师至永昌凡一百二十驿。
云南山高谷深,王昶用诗歌记述了通行的困难:“天梯石栈通逶迤,三尺一级侔累棋。骏马行此旋倭迟,十步五步鸣酸嘶”(《经高黎贡山》)。云南的道路不但险峻,还泥泞难行,王昶曾坠马受伤,“东风吹雨湿青壁,泥融于胶滑于漆”(《龙江道中坠马,有作》)。过澜沧江铁索桥时,王昶心惊胆战,“昨过澜沧森欲坠,铁索千寻颤如颠”(《过龙江铁索桥》)。除了铁索桥,云南的江河上还有独特的绳桥,“绳桥斜日驻征蹄”《重宿龙江税房》。
在王昶笔下,云南是名副其实的“穷边”,如“炎徼烽烟静,穷边景象新”(《入虎踞关》),“岂知更一笑,棲托来穷边”(《复至腾越示黄兴》)。因交通险恶,环境险象丛生,从军云南期间,王昶的内心时时充溢着一种苦闷、抑郁、忧愤的情绪,在他的诗歌中多有反映。如:“药碗经旬旅病淹,心如黄檗几时甜”(《除夕口占》),“循陔将践三年约,绝塞仍为万里行……故乡却望今谁是?回首哀牢涕泪横”(《同副将军温公福赴蜀发永昌》)。
五、《滇行日录》与杨慎《滇程记》的关联
王昶《滇行日录》的创作初衷与行文风格,明显受到明代戍滇状元杨慎《滇程记》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受到《滇程记》的启发,王昶才创作了《滇行日录》。
1524年秋天,被罚戍滇云南永昌(今保山)的杨慎从北京出发,途径河北、湖北、湖南、贵州,由平夷所(今曲靖富源)进入云南境。后经交水、南宁驿、马龙州、木密所、杨林所、板桥,到达云南省城昆明。稍作停留后,杨慎一路向西,经楚雄、大理,到达戍地保山。在赶赴戍地的途中,杨慎从陆路起点江陵(今湖北公安)开始,逐日记述每天经过的驿亭里程,对沿途地名、山川形势、气候物产、风土民情等也详加记录。抵达戍所后,杨慎将手稿整理成书,即《滇程记》,这是一部日记式的书,详细记载了他自江陵至永昌驿站的旅程以及沿途见闻。
距离杨慎戍滇两百余年后的1768年,王昶从军云南。王昶与杨慎有许多共同点:同时具备官员、学者、文人的多重身份,同为戴罪之身,出发地(北京)、目的地(云南保山)相同,甚至连心境都类似。到了保山,王昶还专程去探访了杨慎戍滇时的居所,并作诗《过杨升庵故居》纪行,发出了“祖豆知何日,松篁不记年”的感慨。从杨慎的人生经历中,王昶仿佛看到了自己命运的投影。
虽然自成一体,但《滇行日录》的创作初衷、内容、体例,都与《滇程记》相似,前者甚至可以视为对后者的延续、验证。云南的邮驿建设始于元朝,明朝时期,路线、驿站的设置更加丰富,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到了清朝,云南的邮驿体系完备、运转有序,达到了封建社会时期的巅峰。比较《滇行日录》和《滇程记》的异同,可以清晰地感知到明清之际云南陆路交通的发展变迁。
结语
在王昶眼中,清代时期的滇缅边境是瘴疠盛行的蛮荒之地,加之军事凶险,时刻可能遭遇不测,艰难险阻的境况,让王昶身心俱累,在写给友人曹来殷的书信中,他对在云南的军旅生涯作了总结:“去年七月出铜壁关,迄十月抵老官屯……其间历毒阳,陷泥淖,厉怒湍,逾重岨,险恶万状,非耳目所恒闻见……三年中,备阅艰苦,精神消耗过半矣……”
在如此艰难险阻的军旅生涯中,王昶仍创作了《滇行日录》,同时写了大量关于云南与军旅生活的诗文,为后人留下了重要的文献档案资料,他的精神令人钦佩,他的作品值得后人进一步挖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