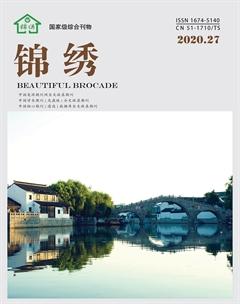抵抗“平庸之恶”
徐亚都
一、判断的困境
个体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在共同体和周围成员已经预先做了判断的前提下,我在何种程度上还能做出自己的判断,我在何种程度上能辨明是非而不被欺骗,何种程度上我能作为当前判断的发出者而认领这个判断。这里我们将能看到阿伦特对于那些自动脱离共同体退回私人领域,也即那些逃避责任的人所持有的赞赏。
在阿伦特看来,上述那些只关心自己的清白和灵魂救赎而选择逃避所谓责任的人恰恰是仅有的能够做出判断的人。对于每一个作为单数存在的人做出判断之前就面临着跟从还是自行判断的困境,跟从意味着以周围大多数人和外部环境认可的判断为判断,他不需要将自己置于孤立的领域而冒险谋求与自己的一致性,只需要顺手将别人那里的东西拿过来自己使用就好,无论如何这都要容易的多,“与其说一个人从经验中学习相比,控制人类的行为,并使他们按照最感意外和最不公正的的方式去行动,看起来要容易的多;从经验中学习就意味着开始去思考和判断,而不是去应用那些范畴和公式,那些范畴和公式深植于我们的心灵,但其经验基础久已湮没,并且在表面的合理性在于他们理性上的一致性,而不在于能够充分解释实际事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常人”和“此在”之间“性格”鲜明的痕迹。对阿伦特来说,正是那些对现存道德和知识强烈的拥护者反而在纳粹上台后瞬间就倒戈了,像换掉一件衣服那样,用眼前新的一套价值观更换了以前那套旧的。我们总是将已知的东西(后天学习的和先天就有的)运用在未知的上面,将此处的预判添加到彼处上,这样一切新情况就被提前预判了,剩下的就只是埋头行动。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关于沉思和行动二者的分野在这里又出现了。而那些所谓逃避责任的人恰恰是良知和道德情感不能像上述那种自动自发的方式发作的人,对他们而言,以往的任何经验都失效了,他们的判断标准毋宁是没有在手的标准依照、时时刻刻都要跟自己在一切、与自己和睦相处、不违背自己的倾向反而让他们远离了作恶,“……他们自问,在己犯下某种罪行以后,在何种程度上仍然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而他们决定,什么都不做要好些,并非因为这样世界就会好些,而只是因为仍然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故而当他们被逼迫去参与时,他们就会选择去死。不客气地说,他们拒绝去杀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仍坚持‘你不得杀人这一戒条,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一个杀人犯——他们自己共存。”
二、苏格拉底和思的活动
阿伦特在考察意志的这种自我分裂现象,理性和意志之间的究竟是何关系?理性是否能命令意志时,首先求教的是苏格拉底。我们在拾捡苏格拉底学问的残章断片时总是被柏拉图所纠缠着,和那些发出伟大声音的导师耶稣、孔子一样,他也是述而不作,我们只是在柏拉图复活的苏格拉底形象中获得一知半解。通常对苏格拉底“无人有意作恶”那句古老的名言的解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只会选择对自己好的事情,那些选择恶的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好的(获得好的知识的能力便显得尤为关键),批评来自于他混淆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将知识和作为实践的道德混为一谈了,道德在他那里还窒息在获得善的知识的内部而没有培育出来。这样的解释部分原因是受到了柏拉图自己发明的理念论的影响,认定苏格拉底的理性是一种具备推理、判断的铁板一块的致力于获得知识的能力(柏拉图从此基础上将人的灵魂结构三分),或者在那里还有一种倾向,柏拉图在洞穴比喻中隐含的人的心灵之眼对真理的一种观看。阿伦特则将苏格拉底的这种理性能力做了存在论意义上现象学式的阐释。
在他看来苏格拉底的那句“遭受不义要比行不义好”的公式表述的是这么一种倾向或者说活动,是一个人不与自己自相矛盾,自己和自己处在的无声言谈中的倾向。这个我一方面是作为一的我(从我作为一个整体的外部来看),另一方面又是作为二的我(从内部结构来看),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自己内部将自己一分为二,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和另一个自己言谈,我才能时刻感觉到我和另一个自己在一起,处在另一个自己的陪伴当中。她将这种活动称之为思的活动,这种二而一的思的活动是一个人没法逃离的,不可能像我们可以从别人身边逃开一样,我们可以从自己那里逃离。当我们思考时,另一个我在陪伴着自己,当我们行动时,我在见证着我自己的一举一动。正是这种时时刻刻都与自己相伴,都想谋求和自己的一致和和谐的思的活动让我们处在安全的领域,因为如果我是一个罪大恶极之徒的话,就意味着我时时刻刻都和一个魔鬼(另一个自己)同处一室,站在一起,这是难以忍受的。如果我们将此处阿伦特所说的思等同于意识和自我意识,我认识到我的意识是我的意识(意识的同一性),问题就被平庸化了,因为就像阿伦特说的思首先是一种自己与自己展开的无声的言谈,自己和自己的交流和对话。自我对自我的关切和陪伴。“……或者更专业地说,他相信所有人都是二而一的,不仅是在意识和自我意识(即无论我在做什么,我总是同时意识到在做这件事)的意义上,即无声对话、持续交流和与他们自己的谈话关系。”
三、抵抗平庸之恶
阿伦特在出席了艾利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之后,这个曾经的纳粹魔鬼在她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和我们一样平庸的人。在这样一个人身上,丝毫找不到魔鬼般“凶神恶煞”、“青面獠牙”的特征,如果不把他和那个签发毁灭无数犹太人生命指令的人联系在一切的话。正是这样一个放在人堆里都难以辨识的不起眼的庸人却在大屠杀中充当着关键的角色。阿伦特定是从一个平庸的艾希曼身上看见了无数的艾希曼,每一个好像都无甚差别,每一个都是贫乏无趣、近乎乏味的。甚至我们在拐过街角后都能随时跟他们中一个迎面相撞。他们没有把灵魂卖给魔鬼,也丝毫认识不到自己是与谁在同行。与其关注那些名副其实的罪大恶极之徒阿伦特显然更希望把目光放在那些如何作为的普通人身上,因为前者从来都不会有道德或者良知上的发作,即使失败也只能感觉到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挫败感,如果不发自真心的忏悔,一切都他们而言都是无用的。正是那些我们称作芸芸大众的概念掩盖着一个个让我们时时刻刻都处于危险抑或安全中的关键个体。唯有他们的加入才让罪恶在二十世纪的德国看起来成了谁也无法理解的现象。
阿倫特用罪恶的肤浅性来解释艾希曼的所犯下的恶行,她无意在我们庞杂繁复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上添加一块概念的绊脚石。“对阿伦特来说,恶的平庸性不是一种理论或者教条,而是表示一个不思考的人为恶的实际特征,这样的人从不思索他在做什么,无论是作为掌控犹太人的盖世太保官员还是作为监狱里的一名囚犯。”这就意味着“恶的平庸性”被用来描述作恶者带有的思维匮乏特征,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停下来,想想,自己在干什么,他与自己的陪伴者、倾听者、言谈者处在谁也不过问谁,谁也不理睬谁,甚至谁也不知道谁的隔离中,只要这个我和另一个我之间的栅栏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拆卸,我就不会自问,我到底是谁?我在干什么?我就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丝毫的忏悔还歉意,因为良知和一系列的道德情感只有在扎根于我与自己的无声言谈之中才能显现出来,否则便是一些今天是这些、明天是那些的飘忽不定的东西,就像一场晚宴后粘着呕吐物的可以在无声无息和众人的一片赞叹声中换掉的桌布。用阿伦特自己的话说:“从这种不愿或不能选择自己的典范的同伴的情况下,从这种不愿或不能通过判断力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的情况中,产生了那种真正的skandala,那真正的绊脚石,人类的力量也不能移动它,因为它们不是被人类和人类可以理解的动机所引致的。在那里存在着恐怖,也存在着恶的平庸性。”“取代罪大恶极的纳粹,她给我们的是“平庸的”纳粹;取代作为高尚纯洁的犹太殉教者,她给予我们的是作为恶的同案犯的犹太人;而代替有罪与无罪的对立的,她给了我们是犯罪者与受害者的‘合作。”对于一段苦难历史的批判反思,阿伦特是丰富的,深刻的,但确实是惊世骇俗的。由于她,无情地撕破了一些政治体的卑鄙的伪装,撕破了人们借以掩盖自身的人性弱点的外罩,所以备受攻击和诽谤也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反抗“平庸之恶”》 [德] 汉娜·阿伦特著,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