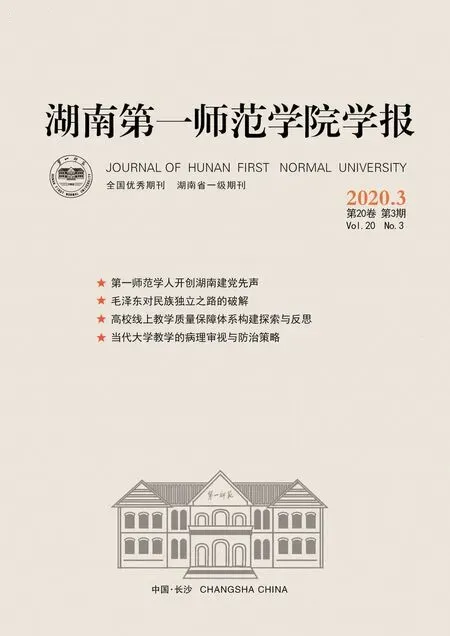顾炎武政治思想的近代意蕴
欧阳斐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对于秦以后的传统政治制度,学界惯常以“君主专制”视之。究其政治哲学基础,既不能等同于“封建”,也不能等同于辛亥之后的主权在民。从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建构来看,这种判断确有一定合理性;然若转向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建构视角,则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在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历史大变革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新民本主义思想家,开始从政治哲学的高度猛烈抨击、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他们不仅从理论上解构了先秦以降的传统政治哲学,而且开启了全新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反映出儒家传统政治思想新的发展动向。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十五、十六世纪以降的儒学在其内在动力和社会、政治的变动交互影响下,发展出一种“基调转换”。这种“基调转换”的历史意义不止在于反映儒家思想传统的活力,并在于其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选择性接受西方思想所发挥的“暗示”或“导向”作用[1]。本文以顾炎武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政治哲学揖别专制制度趋向近代平等政治的理论转向,以求教于方家。
一、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对传统儒家公私观的批驳
公私观念是传统儒家的重要课题,也是从古至今社会伦理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基础性的道德命题。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并获得一定发展,早期启蒙思潮萌动,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学者的学说集中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而顾炎武对传统儒家公私观的批判,尤能反映其时社会道德观念上的新变化以及由生产方式变化折射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变革要求。
顾炎武认为,以“理”为基础的程朱理学和以“心”为基础的陆王心学,都是先验本体论,其后果是使人们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偏离实践、走向空疏。他的《日知录》“河渠”条对明朝治河一事分析后发现,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和强调“致良知”的阳明心学,并没有在政治生活实践中起到良好作用。相反,明朝腐败不堪,官员贪婪无度。他认为,这种情形的出现,虽与国家法律不完善有直接关联,但也与忽视了“百官有司”人人都有“计其获者”的现实倾向有关。除此以外,他还在《日知录》“宋世风俗”条中指出,“政治之乱,在于人心”,宋明儒学高唱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人心风俗和政治生活百害而无一利,以至世风虚妄,道德沦丧,最终导致国家灭亡。
顾炎武对程朱理学、阳明心学进行了猛烈批判,有力掀翻了宋明儒学中玄之又玄的道德本体,彻底抛弃“谈心论性”的虚悬工夫,将儒学拉回生活本身,倡导从现实的人性和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基于实践来讨论人性的善恶和公私关系。顾炎武认为,“私”本来就是人之“常情”,他说:“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2]14-15顾炎武所说的“常情”是指“人之常情”,与“性”具有同一性。从上述引文可知,顾炎武认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的“自为之心”是“天下之人”普遍之“常情”,这种“私情”早在三代已有,至今未变。他进而指出:“‘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后私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先私而后公也。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故先王弗为之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世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也。”[3]148他的这一论述,更是为“私情”的合理性找到了现实依据,它的存在是由“天下为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顾炎武的论说,显然没有突破时代的限制,但他立足于社会现实大胆阐释私有观念的做法无疑是具有超越性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全国的土地和所有的臣民都归君主所有。儒学作为专制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出于对统治者的维护,首先要做的是为统治者拥有的所有权正名,因而,在公与私关系的讨论中表现出“有公而无私”的显著特征。程朱理学尤其到了其末流,已然发展成为抹杀个性、否认“私”的合理性的学说,为专制主义作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其霸道的辩护。程颐指出:“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专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4]朱熹则反复强调“克去己私,便是天理”。而顾炎武明确提出了与程朱理学相对立的公私观念,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先王不但没有“禁之”,反而予以“恤之”,因而,“私”不应是“克去”的对象;第二,“有公而无私”是“后世之美言”,并非“先王之至训”,衡量王政的标准不再是“有公而无私”,而采取“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的政策来维护和保障国人的私利,以实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才是“王政”的本质;第三,在不同的情况下,“先公后私”和“先私后公”都具有合理性,由此说明,“公”与“私”并非截然对立,在一定条件下“私”可以与“公”统一起来。
从上可见,基于不同的阶层立场,顾炎武的思想在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上都与程朱理学发生着激烈冲突,尤其是在公私问题上。在顾炎武看来,“私”的存在合理且正当,公与私的关系也并非必然对立冲突而不能互相统一,“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论述正是有力的说明。顾炎武的“私”观念,表面上是对宋明理学“有公而无私”的虚伪说教的批驳,实质上是对传统儒学公私观念和封建专制发出的强烈挑战,其思想的启蒙性质和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近代思想家严复认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思想,本质上与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理念相同,并把它视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理念。
二、区分“国家”与“天下”:对传统国家观的解构
秦朝建立的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被视为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基本形态。秦朝的政治制度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废除分封,设置郡县,以往世袭的诸侯、领主成为由中央直接指派任免的地方官员,这些地方官员只是享有朝廷的俸禄代管地方,而不像诸侯、领主具有封地的主权;二是建立皇帝制度,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采取家族世袭的方式进行传承。皇帝制度高度强化了君主权力,导致了国家和天下都是君主个人私产的倾向,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一家一姓的“私天下”。而古代儒家学者在阐述其思想时,往往也将“君”与“国”混为一谈,将“国家”与“天下”视为同义。
顾炎武通过区分“国家”与“天下”,对“君国一体”的国家观念进行了解构。他在《日知录》“正始”条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5]756-757由这段话可知,“亡国”是指改朝换代,帝王“易姓改号”;“亡天下”是指道德沦丧、文明堕落,人将不人,率兽食人,人人相杀相食。两者并非同一概念。在顾炎武看来,“国”是一家一姓之国家,具体指的是王朝,是政治上的概念。而“天下”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全民族命运共同体,一是指文明共同体,它既是政治上的概念,也是文化上的概念。由此可见,顾炎武所指的“天下”是一种更具整体性的“国家”概念,其意涵是高于王朝之“国家”的。进一步说,顾炎武所谓的“天下”是比“国家”更大的概念,“天下”涵盖了“国家”,“国家”从属于“天下”。
顾炎武在区分“国家”与“天下”的基础上,进而论之,对“保国”与“保天下”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的责任主体作出说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5]756-757
首先,是两者的关系问题。顾炎武认为,“天下”包含“国家”,“国家”从属“天下”。“保国”的前提在于知晓“保天下”的意义和价值,“保天下”方可“保国”。“保天下”与“保国”之间是前后与因果的关系,“保天下”在前,“保国”在后;“保天下”为因,“保国”为果。进而可知,“天下”若保,“国家”犹在。“天下”不保,“国家”孰存。在这里,顾炎武着重强调的是文明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没有文明也就不可能有国家。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都是以文明共同体作为前提和基础。他还以“正始玄风”和“魏晋清谈”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顾炎武指出,正始名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胡互僭,君臣屡易”[5]756-757。现代之人对颇具思辨与超越性的“正始玄学”喜爱者居多,但顾炎武对此则是根本否定,认为当时的国家破灭、教化沦丧、社会动荡、生民凄苦,其原因在于士大夫的理论关切背弃了儒家经典,脱离了现实生活,导致“国家”消亡。这个责任应当由士大夫承担,故而有“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的论断。顾炎武又通过山涛劝说嵇绍入晋为官一事指出,自正始以来,魏晋文人游谈无根,不守信义,致使“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山涛用不必计较杀父之仇劝说嵇绍入仕的“邪说”,竟然被传颂为“名言”。受此影响,贤人“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顾炎武认为,“败义伤教”“率天下而无父者也”的“邪说”,正是魏晋时期“亡天下”的根源所在。这是顾炎武将士大夫“尚老庄、崇放达”导致“国家”消亡放大至对文明社会的整体关切的高度,进而申述得出的结论,“亡天下”也就是文明道德的丧失与堕落。该段引文出自“正始”条,“正始”条处于《日知录》第十三卷,该卷所论皆在风俗、清议、名教、廉耻等有关伦理道德的问题,这也可以看出在“国家”与“天下”之辩中,顾炎武是要突出“天下”的重要性。
其次,是两者的责任主体问题。顾炎武认为,“保国”的责任主体在于君、臣,也就是“肉食者”。换言之,对于王朝兴亡一类的“国家大事”,普通百姓没有参与的责任。普通百姓的职责在于“保天下”,也就是维护文化道德和伦理规范。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联系其对“国家”与“天下”概念的辨析。他认为,“国家”是一家一姓的王朝,“保国”是朝廷君臣自己的事情;“天下”是文化道德,与所有人有关,“保天下”则普通百姓都应当承担责任。不过,“保国”和“保天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可能截然分开。身为“匹夫之贱”的顾炎武在面对朱姓王朝“国家”灭亡时,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投身“救亡”事业,其原因在于他救“天下”的志向。顾炎武此举志在救“天下”,实际上也是在救“国”。顾炎武对“国家”和“天下”作出的内涵区分以及对“保国”和“保天下”作出的责任主体区分,不是为了给君臣和普通百姓在“保国”和“保天下”的问题上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其目的在于明确社会各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职责,特别是对社会之人所应承担的文化职责的明确。
顾炎武从文化意义上定义天下,用“文化本位”取代了“君国本位”,构建了“文化亡则天下亡,文化存则天下存”的文化天下观,实现了对传统“君国一体”观念的超越,转而以民生和文化传承为本位。他区分一家一姓私有的“国家”与普通百姓赖以生存的“天下”,也蕴涵了“民本位”的深义,皆为具有近代性的民主主义政治理念。
三、君、臣、民平等:对传统政治关系的突破
在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君主是天子,即天帝之子。君权源于“天赐”,具有神圣性。董仲舒有“屈君而伸天”之说,认为君主要绝对服从“天”的意志。程颐则认为“王与天同大”,君权是至高无上的。在君与天的关系中,君权或“屈从”于天,或与天“同大”。而在君臣、君民关系中,君权始终至尊至高,君尊民卑乃是天经地义。顾炎武对此进行了否定。
首先,从君主的称谓入手,祛除其“尊”。儒家礼制对“称谓”的使用具有严格规定,体现出强烈的等级差别。“君”“万岁”“陛下”等词语被视为对君主的尊称,专其独有,以体现对皇权的尊重和崇尚。顾炎武运用溯源考察的方法,揭示词语的本来涵义,从而消解其等级特征。他指出,“君”字作为天子尊称的特殊用法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先秦时期,“君”字可以称指臣,也可以是女儿对父亲、妻妾对丈夫、妇人对舅父的称谓,不过是一个用来表示尊敬的普通称谓,并非君主专用词语。他说“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并非自古如此,古时“万岁”是“庆幸之通称”,并以先秦两汉文献加以论证:战国时,冯煖“为孟尝君以债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东汉时,马援“击牛酾酒,劳饷军士,吏士皆伏称万岁”;冯鲂“责让贼延褒等,令各反农桑,皆称万岁”[6]1396。由此可知,“万岁”可以是民众、吏士对主人、大臣的称颂,不仅仅只有“天子”才能享用。至于“陛下”一词,顾炎武认为它是对皇宫前台阶下“执事”的称呼。古时臣子不能直接与君主对话,须由站在“陛下”的侍卫者转达,后经演变“陛下”才成为对君主的尊称。顾炎武对“君”“万岁”“陛下”等儒家礼制约束下的特殊用词进行溯源释义,带有对君主至尊至贵地位的批判意味。
其次,从君主的位序入手,消解其“殊”。对于“周室班爵禄”儒家通常认为,公、侯、伯、子、男是依次递进的五个等级的爵位,而天子则是在“公”之上的绝世之贵。也就是说,在社会身份普遍等级化的社会关系中,天子地位独尊、至高无上。顾炎武对“周室班爵禄”作了另外的解释:“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原注:《黄氏日钞·读王制》曰:‘必本于上农夫者,示禄出于农,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3]433在他看来,天子与公、侯、伯、子、男同处于班爵之列,不过是这些爵位中的一种,并非至上的“绝世之贵”。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农耕者)同处在班禄之列,天子与官员皆为“代耕”,其俸禄是为农耕者服务所得,并非“无事而食”。顾炎武进而指出,如果君主明白了“天子一位”之义,则不会“肆于民上以自尊”;明白了“禄以代耕”之义,则不会“厚取于民以自奉”。顾炎武对“周室班爵禄”的阐释实际上是把君主视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一个职务,反对其“肆于民上”的特殊地位。
再次,从政治生活实践入手,指出君臣民的合理关系。其一,君主应该以谦卑的态度待人。顾炎武认为“人主之德,莫大乎下人”,“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他在《日知录》“人臣称人君”条中论及:“汉文帝问臣子冯唐曰:‘父老,何自为郎?’是称为父也。赵王谓赵括母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是称其臣之母母也。’”[6]1391汉文帝称臣下冯唐为父,赵王称赵括之母为母,可以看出两位君王对臣下的尊重。其二,君主应该尊重人民,主要表现在对人民讲信义和善于倾听人民声音。顾炎武在《日知录》“去食去兵”条中指出,“足食”“足兵”都很重要,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取信于民,使“民无贰志”。如能做到这一点,在遭遇外敌入侵时,即便食不足、兵不足,人民也会誓死保卫。他还从古代典籍找到君主善于倾听民言的例子,如汉文帝“止辇受言”,尧舜“询于刍荛”等等。与之相反,如果君主“居心以矜,而不闻谏争之论”,则“灾必逮夫身者也。”其三,君主应该先于臣民,从事最辛苦、最卑贱的事务。顾炎武在《日知录》“去食去兵”条中说:“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旧劳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烦缛之事。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王业之所由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务也。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后能使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而后可以胜天下之大。舜之圣也而饭粮茹草,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济天下,而为万世帝王之祖也,况乎其不如舜、禹者乎!……”[3]441他认为,上古的君王皆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舜帝“饭糗茹草”,禹帝“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武丁服劳于外,由此知道了劳作的不易、民众的疾苦,所谓“能事人而后能使人”。君主应当在实际生活中“先天下之大劳”“执天下之至贱”,才可以“道济天下”。
顾炎武认为传统君、臣、民关系的最大弊病在于君权至高无上,导致君臣、君民关系失衡。他提出的“天子一位”“禄以代耕”的思想,实则是把君主置于与普通民众同等的地位,以表达君臣民在政治上的互相平等,这与近代民主观念是相通的。
四、“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对传统政治制度的改革
顾炎武生活在专制政治时代,矫治专制之弊,是顾炎武及其同时代思想家关注的基本问题。此时的专制之弊实质上是郡县之弊。郡县制是在封建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于封建制而言,其优点在于权力集中和统一。但问题也在这里,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在君主和中央,地方没有积极性,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只是被动地执行上级政令,不能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作出调整和变通。
顾炎武深刻指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7]12因此,他在《日知录》“守令”条中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3]541主张把君主的权力逐级分配下去,使“公卿大夫”至“里宰”在内的百官得到相应权力,“各治其事”。而实现“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政治主张的改革方案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也就是把封建制的精神融入郡县制之中。顾炎武在《郡县论》中阐述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具体内容:“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7]12也就是,提高县令的级别,把七品知县改为五品县令;赋予其自主管理当地经济、财政、民政等一切事务的权力,即“县令于县政有专断之权”,不必受制于中央;罢黜向县里派出的监司,保证县令能够自主行使治理权;允许县令世代相传,由父亲推荐儿子、兄弟或旁人继承自己的县令职务;除了县丞由吏部“选授”以外,县丞以下的各级官吏都由县令自主任命,只须向吏部备案即可。这一制度的实质是将中央的权力分配给地方,而重点又在加强县令的权力。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体现为对县令的选任。
欲成其事,必赋其权;既赋其权,当责其效。顾炎武赋予了县令县域之内的“专断之权”,也相应设置了一套考核标准和奖惩机制,他说:“何谓称职?曰:土地辟,田野治,树木蕃,沟洫修,城郭固,仓廪实,学校兴,盗贼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则人民乐业而已。”[8]13他列出十条考核县令的具体标准,概而言之,人民安居乐业,才算得上称职。至于奖惩问题,他这样写道:“其初曰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又三年,称职,封父母;又三年,称职,玺书劳问;又三年,称职,进阶益禄,任之终身。其老疾乞休者,举子若弟代;不举子若弟,举他人者听;既代去,处其县为祭酒,禄之终身。”[8]13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县令从试用开始,每三年需要接受一次考核,如果十二年中经过四次不同的考核均为“称职”,则可“进阶益禄,任之终身”。县令若因事、因病不能任职,可推荐儿子、兄弟或旁人代行其职。代行职务者为“试令”,其正式任职后,原县令也可任该县“祭酒”,受禄终身。而“令有得罪于民者,小则流,大则杀。”[8]13县令如果得罪县民,视其情节,或流放,或杀之。“夫使天下之为县令者,不得迁又不得归,其身与县终,而子孙世世处焉。不称职者流,贪以败官者杀。夫居则为县宰,去则为流人,赏则为世官,罚则为斩绞,岂有不勉而为良吏者哉!”[8]13
这一制度下的县令实质上与封建诸侯无异:手握一县专断实权,职位可世袭,赋税可自留“一县之用”。顾炎武难道不担心重蹈“封建之失”的覆辙吗?对此,他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其一,“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2]14-15县令的利益与地方利益一体,县令就会把县域之内的公共事务当作自己的事情实心实意来办,把县域之民视为自己的子女看待,遇外敌来犯则县令必率民众拼死自卫;其二,县域最大不过百里,其实力不足以称兵作乱。况且邻有他县,上有太守,县令欲起兵谋反,太守会调用其他县的兵力对其讨伐,县令几乎没有作乱空间;其三,完善巡按制度。安排官秩七品的官员担任巡按御史对地方进行考察和监督,职位不高的巡按御史到了地方,不至于对职位比他高的地方官员过分放肆,但又能起到监督作用。地方官员也有实力制衡比自己职位低的巡按。这样的方法蕴含“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有助于防范地方郡县过于强大。其四,为了防止县令权力过于集中,进而提出“再设县内分权之制”,“以县治乡,以乡治保,以保治甲”[3]477-478,把权力一直分到乡里保甲。他认为“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9]。
“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分权思想是顾炎武政治思想的核心,其用意是通过“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政治制度改革,在不打破现有国家治理结构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建立起一种整体平衡的公共权力运行机制。顾炎武的分权思想并没有突破封建主义的范畴,但其中涉及到的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变化和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的反映,体现出由专制主义向近代民主过渡的明显特征,其理论价值应当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