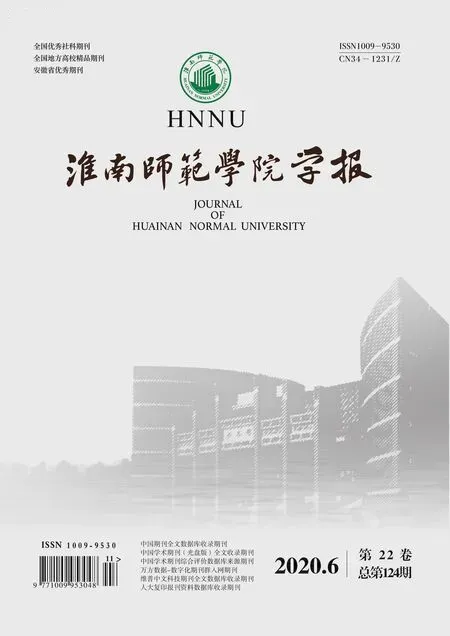桑梓情下的新安画派与徽商
朱 丹
(淮南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8)
徽州,古代又称新安郡。“新安画派”盛于明末清初,成员主要是徽州籍的画家(包括当时寓居外地的徽州籍画家)。他们善用笔墨,貌写家山,其作品与地缘有很大的关系,在艺术风格上趋向于减淡幽冷。黄宾虹曾评价,“明代之后,独新安画派识力过人,继承了中国文人画的正统”[1](184),可见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新安画派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两个重要条件:一方面是徽州地区文人荟萃,宋元文人的隐逸思想得到新安画派的推崇和继承,这对徽州画家在艺术思想上继承文人画的传统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富甲一方的徽商有着丰富的书画收藏,这给画家提供了优越的文化艺术学习环境和学习艺术先贤们技艺、思想的契机,使画家们能便利且近距离地看到传统文人画的笔墨技巧从而得以继承。当然新安画派也存在发展上的障碍,比如在复古思想盛行的清代,摹古是新安画派的主流,肯向自然取法并取得成功者较少,这影响了新安画派的整体艺术水平。此外,徽商参与画事活动虽然成就了众多徽州画家,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画家艺术的自由发展。新安画派发展道路上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对当今中国文人画的发展都有启示作用,对此可以辩证分析全面考衡,以此引导当代文人画朝着健康的道路继续发展。
一、新安画派对中国文人“隐逸”思想的继承
“隐逸”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种独特的处世方式,“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这只是孔子对文人在仕途上进与退的一种解释,事实上中国古代文人选择隐逸的生活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大体来说,不寻求认同为“隐”,自得其乐为“逸”。在中国古代漫长的朝代更迭中“文人隐逸”思想逐渐演变成文人气节,或是文人品质的象征。而文人画的出现与隐逸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绘画艺术与思想形态的结合,必须提到(宋)苏轼对文人画作出的贡献。苏轼是第一位把禅宗思想、隐逸情节化为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投入到创作中的书画家,因其自身又是一位在诗词、文赋等方面取得的卓然成就的大家,从而奠定了文人画的精神内核。在他之后中国文人画又历经宋元画家的努力,使其内涵不断丰富。到了元代,文人画成就达到了高峰,而新安画派的发展正是因为继承了宋元文人画的隐逸思想,使其笔墨减淡、萧瑟直追前人精髓,才有黄宾虹认定的文人画正统之说。
新安画派盛期也是明清文人隐逸之风最为繁盛之时,此时的隐逸之风一部分是承接明代风尚,主要是遭受政治迫害者、屡试不第者或是喜好佛道、追求隐逸生活者,由这部分文人形成的隐逸风尚。另一重要原因是在国破家亡之时,对于不能征战沙场的文人而言,做“遗民”是他们民族气节的体现。像傅山虽有“学而优则仕”的愿望却不能实现,最后选择归隐,这是受遗民思想影响而选择隐逸的文人。清初“新安四家”也多是因为人生中各种人生境遇与遗民思想交织在一起而最后选择隐逸生活的文人。渐江屡试不第,又好佛理,而有了归隐佛门之心,随后画风冷寂;查士标因明亡而弃举子,专事书画,画风清淡简远;孙逸因世路纠纷而以云山寄意,画风简淡疏离;汪之瑞避居新安山中,闭门绘事以表文人气节,画风平淡天真。他们在政治上基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书画表达自己的人生观。所以文人画家选择隐逸并非因某一种原因,常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新安画派卓越的代表画家——渐江(1610-1664)中年出家,一些研究者判断他出家是受儒家“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儒家思想影响,把渐江出家的具体时间当成是佐证其绘画风格受遗民身份影响唯一重要证据,是有悖历史考证原则的。关于渐江出家的时间,历史文献上有两种记载,一种是明亡后出家,周工亮《读画录》记载“甲申后弃去为僧”;汪泰徵《渐江和尚传》记载渐江出家是在“乌聊既定之明年”,清兵已经完全占领徽州的顺治2年,也就是1647年出家,这部分研究者据此推断,明亡后渐江不愿与清朝合作而出家,随后画风冷峻直追元人;另外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渐江是明亡前出家,主要根据渐江的好友程守《故大师渐江碑》载“报龄五十四,僧腊二十一”中依据亡年推算渐江是在崇祯16年(1643)出家,依此认定他是明亡前出家。认可明亡前出家的研究者认为程守与渐江是好友关系,而周工亮与汪泰徵二人与渐江虽是同时代的人但并无交集,推理出程守的记载更具有可信度[2](P24-28)。事实上无论渐江明前出家还是明后出家都不能据此一点说明渐江的绘画风格仅受遗民思想影响而形成萧瑟、清冷、减笔风格的唯一证据。因为,此时的渐江已过而立之年,尚未婚娶,这绝非是受三纲五常儒家之理约束的文人所为,而是他早已有了归隐佛门之心。汪泰徵《渐江和尚传》载“幼有远志,不入队行”[3](P3),从中可端睨出渐江出家可能是人生的一种选择。所以徽州文人隐逸的思想在明代经过时间的温润,已经在文人心中扎根,徽州本就是读书人重多之地,明代中期以后科举道路的堵塞使得大量的文人不能入仕,读书人的无奈、不得志使得隐逸思想自然的汇入到文人的生活和艺术创作中。随之朝代更迭所致的遗民隐逸思想对新安画家画风又产生了冲击,遗民思想也进入到文人画家的人生选择和艺术表现里,所以此时的文人隐逸思想汇聚了多种因素而形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一种是文人不得志的无奈,一种是国破家亡文人气节的体现,在特殊历史时期它们交织在一起混合体现于新安画家的艺术追求中。新安画派所在的徽州黄山一带,千百年来这一区域恰是江左士夫在战乱时的避居之所,使得黄山呈现书画名家辈出的景象,这一现象导致在文人隐逸之风尤为盛行之时,文人画创作也迎来了繁荣的景象。新安画家描写的家山水以减笔、冷清笔墨表现创作的品格,以清淡高逸为胜,这是隐逸思想对新安画派指导作用的体现,是对倪黄一脉文人画的继承与发展。
二、徽商收藏对新安画派在发展上的影响
(一)徽商藏品与新安画派继承中国文人画衣钵之关系
书画收藏与艺术潮流有着紧密的关系,明清文人雅士热衷收藏古代书画,有实力的徽商也参与到雅道行列,由于他们经济实力雄厚,使得大量元代绘画精品汇流至徽商家中。盐商子弟王学儒多蓄元明书画;程正吉家中藏有赵孟頫《水村图》的手卷和倪云林四幅立轴;黄崇惺的侄子黄新宇藏有元代画家高克恭山水画。这样的收藏事例不胜枚举,一方面大量收购古代名迹尤其是对元代书画的收购给新安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文化遗产,(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载:“倪高士《幽涧寒松图》,详其风格,盖晚岁笔。此图收藏得地,纸质如新,笔墨精好,神采焕然,今在丰溪吴氏”[4](P114),徽商收藏的行为对古画起到了保护作用的同时也使得这些艺术品的价值得到挖掘和传播;另一方面,徽商收藏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文人画家身份的多样性。在商品经济未得到发展之前,只有达官显贵的仕人阶层具有收藏能力,能接触前代大师真迹的仅限于自家子弟,寒门文人不具备这样的学习条件,但自从徽商参与收藏后,普通文人也有机会向古代先贤学习绘画,“文人画家”这一职业不再是士族的专属职业,这使得徽州文人画家的数量远超前代,不同身份地位的文人从事绘画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文人画的内涵。
徽州人的桑梓之情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的同乡之谊,徽人的宗族观念与宋代大儒、理学大家朱熹为其乡人修定的《家礼》有着密切关系。这部《家礼》到明清之际被徽州人视为法律不能逾越,在它的影响下,徽州各个阶层的人都要以纲纪宗族为己任。因此,徽人从小受到宗族礼法的教诲要比其他地区严格。徽商在事业成功之后,为了宗族的兴盛,他们乐于助力同乡在文化艺术领域展露头角,其中新安画家便是徽商资助的重要对象。比如渐江,其家境贫寒又无功名,但得到溪南吴氏赏识与之交好。吴氏中的吴爔、吴熿、吴惊远都是夹笥丰盈的收藏家,渐江常到吴家赏阅并细致地研究元四家的作品,他对元四家研究的深入程度在其于顺治十三年(1656)所作的《山水三段图》中最能体现。作品分别用了倪瓒、黄公望、吴镇、王蒙四人的画法,这种近似炫技的创作方式,是研究渐江学习元代画家的重要证据。而在元四家中渐江用功最深的是倪瓒,他在《倡外诗》中有言“迂翁笔墨予家宝,岁岁焚香供作师”[4](P120)。其艺术上用笔清刚简逸,意境高洁俊雅的表现与徽商提供的藏品有着直接的关系。《清河书画舫》有云:“倪云林的《东岗草堂图》、《汀树遐岭》小幅、《吴淞山色》大轴皆是元镇极品,近归溪南吴氏,交谊最笃,里居相近,凡时贤未及睹者,皆得见之”[4](P115)。所以,徽商藏品对文化人采取开放态度的行为,首先是对本族的文人画家采取毫无保留的开放态度,在复古之风盛行的时代,新安画派独厚,尊享着徽商提供的古代大师的艺术盛宴。新安画家除了可以直接向元代画家学习之外,还热衷于向明代画家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等人学习,主因是这些书画家与元四家渊源颇深,通过他们直追元人是学艺之径。以沈周为例,他的祖父与王蒙是好友,沈周父辈对王蒙用功很深,沈周从小深受家庭熏陶对元四家均有用力,董其昌曾评价沈周学元四家“皆有出蓝之能”[5](P239)。所以,对于明末清初的画家而言,通过明代文人画家进而学习元四家是有益的,从新安画家学习的途径及经过来看,新安画家完整地继承了文人画的发展脉络。新安画派的画家们与徽商的宗族关系,使其具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可以领略前人的神采,直接登堂入室继承文人画的衣钵。从这一点分析黄宾虹所言“新安画派继承了文人画的正统”是中肯的评价,尤其是新安四家的作品呈现出疏简、不媚俗的特质,能领略到元人的精髓。诸画家们在商人的巨室豪宅内往来其间成为徽商家中常态,主人设具、列案、取卷、进册,古香经日不断,文人们更相辩论,龂龂不休。所以徽商为新安画派的发展提供了类似于现代图书馆和艺术沙龙的艺术环境,这种学艺环境对新安画派完整地继承文人画的衣钵起到了重要的文化支撑作用。
(二)徽商收藏与徽州画家声望之关系
徽商对书画收藏的世代积累使得部分徽商逐步成长为鉴藏家,詹景凤便是其中之一。他喜欢收藏文征明的短幅小长条,“购时时价平平……余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后有三年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酹悬黎矣”[6]。可见徽商对艺术品喜好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引导艺术品收藏方向的作用。所以徽商除了收藏元明书画外,他们也热衷收藏徽州画家的作品,像程嘉燧、程邃、渐江、查士标的画作是徽商的收藏热门。清初徽州书画收藏的专业程度非常之高,令其他地区的收藏家羡慕不已,也被其他地区的收藏家模仿。徽商经商外迁,促成了徽州与江南等地收藏家之间的交流,艺术的流通扩大了书画艺术的传播,使得徽州画家的影响随之扩大。许多依靠卖画为生的画家也随徽商居住,但族人优先始终是徽商对待徽州画家们的方式。比如徽州籍画家罗聘为扬州重宁寺绘制壁画时,徽商出资百金作为润格之资。当时清朝三品官员的一年俸禄银两也不过一百多两,而徽州画家常常可以通过一次画作换得这个收入,而非徽州籍画家则很难得到这样的待遇。例如石涛与徽商交往也很密切,石涛一生创作了大量的《黄山图》,多是为徽商定制而画。他写过这样的诗句“我生之友交大半,溪南潜口汪吴贯”[7](P589),道明了他与徽商的关系。虽然石涛受到众多徽商的热捧,但与徽州籍画家相比,还是有区别的。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可见端倪:大徽商江世栋与石涛是好友,一次江世栋在石涛处定制一幅屏风,屏风的构图和设色都是要求较难的通景屏风,石涛发现江家留下的银两与要求不相称,便写信给江世栋说明原因,婉约表明这样的屏风市价要普通屏风的两倍,从而推脱不能画。可见,徽商不是对所有的画家都出手大方,而是只对同族画家在学艺、声名和收入等方面采取格外的保护才使得新安画派在画坛得以迅速发展。
三、徽商参与画事活动对新安画家的影响
(一)徽商与画家的交游
明代初期,政府规定商人同其他编户齐民一样有科举入仕的资格,这一政策的实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士、农、工、商”社会排序的认知。商人社会地位得以提升,明代中后期的詹景凤、洪嘉植等人既是商人也是著名学者,亦儒亦商的形象使得徽商也被称为儒商。因此,徽商在才识与经济实力方面都吸引着文人画家与之交游。徽商时常主动把有名望的画家请入家中,供本族画家学习画技。大盐商汪廷璋为帮助同乡画家方士庶提高画技,散财千金请当时的画坛名手黄鼎到自家指点方士庶,使其画技大进;后又发现汪灏于山水创作颇有灵气,汪廷璋便请浙江画家张洽到家中与汪灏结为画友使其山水气韵得到提升;江世栋与石涛交情颇深,江家多名子弟拜石涛为师;扬州大盐商鲍志道、马曰兄弟经常把安徽籍画家罗聘、汪士慎、巴慰族、方辅、程晋涵等视为上宾宴于家中,类似事例在徽商之中极为普遍,徽商与众多文人画家交游为新安画派培养了大量的画家。当然徽商乐于与画家交好并非只是彰显文人雅好,宗族人才辈出,也有为徽商带来商业益处的因素。清代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是位爱古好事的官员,徽商用雅贿手段投其所好与他建立关系以方便徽商获利。此外,许多新安画家与官员交谊深厚,比较典型的像查士标、罗聘,他们是大徽商与政府官员的媒介,在满足官员的雅好同时也为徽商的商业活动带来许多便利。徽商与文人画家交好的行为渐渐使徽商区别于普通商人,使其更受人尊重且便于林下逍遥,陶冶性情,在完成商人雅俗转换的同时也提高了徽商的社会声望。
(二)徽商资助徽州画家游历
徽商除了在自家主持一些书画类的雅集外,还经常资助画家游历。游历对于画家而言既可以是山水之间的体悟,也可以是画友相访,欣赏画作、讨论画艺的过程。徽商资助画家的游资主要是通过购买画家的画作实现,阮元在评价查士标卖画的情况时说“家家画轴查二瞻”。查士标也自言,作画时常常墨迹未干就被人持去,得到的润格都无法计算;渐江在世时画的售价便与倪瓒相仿,受到人们的追捧。所以很多徽州知名画家的收入很可观,这为画家的出游带来了方便。另一种情况是徽商直接出财物供给画家出游,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好友之间。比如渐江一生喜游历,偏嗜攀险之境,他的游资多是吴氏家族中多位友人馈赠。程守在渐江的《晓江风便图》中有跋文曰“渐公留不炎家特久,有山水之资,兼伊蒲之供,宜其每况益上也”,从中可知吴不炎对渐江的资助之厚。这种馈赠式的资助不限于银两,也包括物件,渐江所藏倪瓒的《山水横卷》、黄公望的《山水挂轴》有可能是徽商的馈赠之物。
徽商资助画家游历促进了画家师法自然的热情,渐江就是新安画派中既师法古人又师法自然的表率,他一生游历过很多名山大川,黄山是家山水也是他流连忘返的钟爱之所,渐江在师法古人上受倪瓒的影响非常大,但因他与倪瓒所画的地貌区别较大,所以在艺术表现上他并没有泥拌于倪瓒的平远构图以及缓坡疏林的规范,而是根据黄山多石少土、山体形貌暴露于外的特点创造出独特的黄山图;在用笔上远山作草书笔意,近山主体作隶书用笔,形成了自己“笔如钢条,墨如烟海”的用笔特色;在构图上以几何型的叠加构成山峰的奇伟、冷峻的气势。黄宾虹评价渐江的黄山图时言“写崚嶒丘壑,不为平远而为深远高远,于元人之外,独创一格”[4](P120),这段话点明渐江的绘画图式是师法自然的结果,其所运用的艺术语言符合黄山真实的形象。渐江曾以诗言其作画心得时讲“敢言天地是吾师,万壑千岩独杖藜,梦想富春居士好,并无一段入藩篱”。现存渐江描绘黄山图60余幅,足见其写生数量之大,用心之专。后人评渐江的画有“减淡”之风,“减淡”的画风源于元代文人画家的精神追求,而渐江笔下的黄山图不仅继承了元代山水画的精神内核,还因其长期师法自然而别有韵味。黄山客观的自然环境为多石少土,不便多用皴法,因此“减笔”是符合事实的。所以渐江所画黄山写的是黄山实景,参的是元人的虚灵。董其昌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可作画”,这是画学之大旨,渐江恰是董其昌这段名言的有力践行者。渐江突破了摹古时风的束缚,常年与黄山为伴,因此才有大量的黄山美景在其笔下诞生,所绘黄山受到人们的膜拜,确立了自己独特的黄山艺术风格,其对新安画派艺术在中国文人画中地位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三)徽州画家在收入、艺术风格与徽商的关系
徽州交通闭塞,徽商大都迁往金陵、扬州、苏杭、武汉一带交通便利的地方做生意,因徽商的外迁导致许多徽州画家也跟随前往。扬州是当时徽商的主要聚集地,因此去扬州的徽州画家也最多,明代张丑《扬州画舫录》记载其时在扬州的画家半数来自徽州。所以在徽商周围形成了徽州籍画家聚集的艺术环境,徽商常常在自家庭院举办雅集,邀请文人名士、画家、官员共聚一堂品评名画。清代康乾时期,仅在扬州徽商修建私家园林用于供养文人的就有三百家之多,当时马曰琯兄弟的小玲珑馆最有名,金农、郑板桥、王士慎、高翔等都是坐上宾。徽商参与的画事行为给画家们的艺术交流提供了优雅的环境和良好的氛围,与西方的艺术沙龙相近。徽州画家的画作也在徽商的引导下顺利进入流通领域,艺术品进入流通领域后对于艺术家而言他们的绘画风格、题材自然需要取悦买主的喜好。所以徽州画家多选择徽州地区的景致入画以满足徽商常年在外的思乡之情。查士标一生的行踪都随徽商而居,所画内容又都是徽州山水,这充分体现出徽州画家与徽商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不仅体现在书画艺术的交易上,也体现在徽商对艺术审美的把控上,这也是新安画派一直以具有地域性特色的徽州景色作为绘画题材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明清之际,许多徽州籍画家随徽商外迁,这在客观上导致新安画派的画家成员处于分散状态。但新安画派于绘画题材上、对宋元笔墨精神的继承上、追求隐逸文人情怀上,皆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这些艺术表现是新安画派的共性。新安画派之所以能保持“共性”,一方面离不开徽商提供的大量藏品使新安画派形成遵崇宋元文人画的环境,优质的人文环境为画家在继承中国文人画传统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新安画派对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继承是全面的,尤其是对元代文人画笔墨技巧、意境的表达起到了承启作用,明清徽州画家学习传统的方式、方法是值得后世画家珍视的财富。当然,在复古思潮影响下新安画派,也未能逃离出大环境的影响,师法古人与师法自然相比较,复古是主流,画家们更醉心于临摹古画,导致新安画派大多数画家对师法自然仅是神往并不付诸行动,查士标作为新安画派的重要画家之一,也曾留下“我家黄山未识面”[8](P94)的遗憾。即便有些画家有机会游历黄山,也因不能长期体悟自然而导致所画作品难以描绘其神韵,清代画家汪家珍发出过“身见黄山而心不见黄山”[1](P96)的感慨。像渐江依靠徽商资助而实现既能专研古人绘画又能体悟自然之神韵,从而取得卓越成就的画家毕竟是少数,这也是新安画派到了清代中期开始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