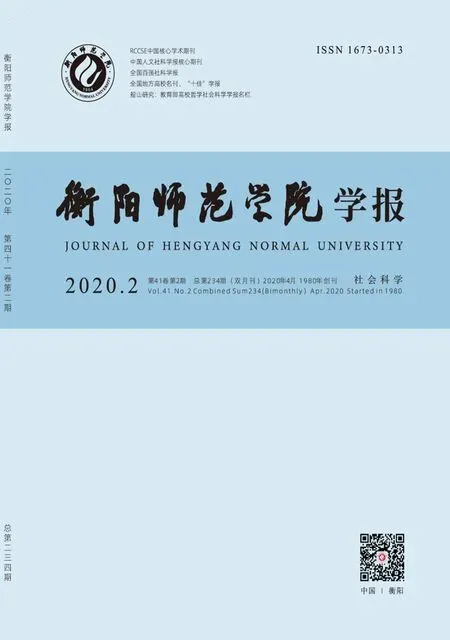康德的道德法则不可知吗
——从李泽厚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谈起
舒远招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曾区分现象与物自体(本体),认为自由、不朽和上帝这些“物自体”由于超出了感性直观的范围,不属于可知的现象界或经验世界,而属于不可知的本体界或理知的世界。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转换了角度,他不再从理论哲学而是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些“物自体”,由此提出纯粹理性在实践运用中作出一种在其思辨运用中根本不可能作出的扩展的“权利”,以及我们“如何能够设想纯粹理性在实践意图中的扩展而不同时扩展其思辨的认识”的问题。康德认为,虽然我们在理论的意义上不能认识自由、不朽和上帝,但我们可以在实践的意义上认识它们。康德还特别针对意志自由指出:虽然它超出了我们感性直观的范围,但我们可以通过道德法则而认识到它。在第二批判的序言中,康德一方面把自由说成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ratio essendi),另一方面把道德法则说成是自由的“认识理由(ratio cognoscendi)”[1]2。由于康德把道德法则当作我们意识(认识)到自己的意志自由的“条件”,而且康德的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一直在阐释和论证无条件的(定言的)道德法则,因而人们一般很少想到道德法则是不可知的。
但是,笔者在李泽厚先生刊载于《中国文化》2018年春季号的《关于“伦理学总览表”的说明》①中发现,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即康德所说的道德法则是否可知的问题。李泽厚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我曾译Kant那著名的‘墓志铭’,‘恒兹二者,畏敬日增: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我与Kant不同的是,在Kant那里,灿烂星空与道德律令都属于不可知的物自体、即本体世界,也就是一个超人类的理世界。我以为这仍然是‘两个世界’的文化心理结构。巫史传统的一个世界去追求超验,是失败过的(见《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文中‘宋明理学追求超验的失败’节)。我以为,灿烂星空的宇宙为何存在确不可知,但道德律令服务于人类总体的生存延续却是可知的。我更赞同Einstein的话:‘我不相信个体的不朽,我认为伦理学只是对人类的关怀,并无超人类的权威站在其后。’总体宇宙,人所难知,道德领域,人人参与。‘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所以在自由意志中,得归结于孟子了。”[2]
在这段话中,李先生首先谈到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结论”中的一个说法:对我头上星空和心中道德法则的惊赞(Bewunderung)和敬畏(Ehrfurcht)②。但接着,他把自己的思想与康德的思想进行区分。他说:“在Kant那里,灿烂星空与道德律令都属于不可知的物自体、即本体界,也就是一个超人类的理世界。”③而他自己则认为,“灿烂星空的宇宙为何存在确不可知,但道德律令服务于人类总体的生存延续却是可知的”。李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断言“道德法则是不可知的”,但从他所作的对比来看,他的确认为在康德哲学中道德法则是不可知的,因为物自体或本体界被限定为“不可知的”,而道德法则属于物自体或本体界。与之相反,他认为道德法则就“服务于人类总体的生存延续”而言是可知的。李先生还提出,虽然总体宇宙是人所难知的,但道德领域却可以人人参与。
康德真的把道德法则当作不可知的物自体吗?针对这个问题,本文试图依据康德的哲学文本作出进一步的探讨。李泽厚先生说康德的道德法则不可知时,并未指明是在理论的意义上不可知,还是在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上都不可知。本文试图表明:虽然康德的道德法则在理论意义上不可知,但在实践意义上是可知的,因而不宜在一般的意义上断言其不可知。
一、从《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得不出道德法则不可知的结论
李泽厚先生主要是依据《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康德在这个“结论”中的具体论述。康德在谈到对头上星空和心中法则的惊赞和敬畏之后,接着指出:“对这两者,我不可当作隐蔽在黑暗中或是夸大其词的东西到我的视野之外去寻求和猜测;我看到它们在我眼前,并把它们直接与我的实存的意识联结起来。”[1]220在这里,康德只是说头上星空和心中道德法则不可以在我之外的某个晦暗之处去寻求,而应该被当作如在我眼前的东西,并且把它们直接与我的实存的意识联结起来,这是在强调它们可以直接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但并没有肯定它们就是不可知的。
李泽厚先生之所以说康德认为头上星空是不可知的,或许是依据康德下面的论述:“前者从我的外部感官世界中所占据的位置开始,并把我身处其中的联结扩展到世界之上的世界、星系组成的星系这样的恢宏无涯,此外还扩展到它们的循环运动及其开始和延续的无穷时间。”[1]220虽然康德在此说的是从我所在的感性位置不断向外延伸,但李先生可能没有关注“外部感官世界中的位置”之类的提示,而是根据“世界之上的世界、星系组成的星系”的说法而想到了宇宙的浩瀚无际,并且从宇宙的浩瀚无际而想到了“世界本身”“宇宙本身”这个物自体,甚至想到了“灿烂星空的宇宙为何存在确实是不可知的”。
李泽厚先生说康德认为心中法则属于不可知的物自体或本体界,或许跟康德接下来的论述有关。康德说:“后者从我的不可见的自我、我的人格开始并把我呈现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具有真实的无限性,但只有对于知性才可以察觉到,并且我认识到我与这个世界(但由此同时也就与所有那些可见世界)不是像在前者那里处于只是偶然的联结中,而是处于普遍必然的联结中。”④在这段话中,“不可见的自我”“人格”都属于不可见的本体界,这个世界被说成“具有真实的无限性”,而且仅仅为知性所察觉。这个世界就是“理知世界”或“知性世界”,也就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一个超人类的理世界”。人们或许可以作如下推论:既然康德说道德法则是从这样一个“不可见的自我”开始的,并且把自我呈现在只有知性才可以察觉到的“一个超人类的理世界”中,那就可以把道德法则也当作属于不可知的理知世界的东西,并认定它是不可知的。这就是说,一旦我们把一切属于本体界的东西都当作不可知的物自体并认定道德法则也是属于本体界的物自体的话,自然也就可以得出道德法则不可知的结论了。
但是,尽管康德谈到了道德法则从我的不可见的自我、人格性开始并把我呈现在一个具有真实的无限性、但仅仅为知性所“察觉”的知性世界或理知世界,表明他把容纳道德法则的“我”视为一个不可见的“自我”或“人格性”,同时把道德法则当作不可见的本体界的法则,但我们并不能根据这些说法就认为康德宣称道德法则是不可知的。道德法则在不可见的“我”当中,也就是在我的“心”中。正是由于道德法则可以直接呈现在我的心中,可以被“我”所意识,所以它并不是什么不可知或不可以认识的东西。
二、在理论哲学中本体界的道德法则不可知
应该承认,如果按照《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提供的理论认识的标准,那么,所有属于本体的事物以及本体界都可以归入不可知的范围。在理论(思辨)哲学领域,康德给出的划分可知或不可知的标准,是某个对象是不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感性直观而被给予:所有逻辑上不自相矛盾但原则上不可以被直观到的对象,都是仅仅可以被思维和设想的东西,而不能说是可以认识的;而所有原则上可以被直观到的东西,都只能是经验对象或现象,而不可能是现象背后的物自体或本体。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的一个脚注中所说:“要认识一个对象,这要求我能够证明它的可能性……但我可以思维我想要思维的任何东西,只要我不自相矛盾……”[3]20。
按照这一标准,道德法则作为自由(自由属于本体界)的法则,也自然是不可知或不可认识的了。康德说:道德法则实际上是出于自由的原因性的一条法则,“因而是一个超感性自然的可能性的法则,如同在感官世界中那些事件的形而上学法则是感性自然的因果性法则一样,因而道德律规定的是思辨哲学曾不得不任其不加规定的东西,也就是其概念在思辨哲学中只具有消极性的那种原因性的法则”[3]63。说道德法则所规定的,是思辨哲学曾不得不任其不加规定的东西,这就表明在思辨哲学的范围内,道德法则本身还不可能得到确切的规定与认识。康德认为道德基本法则是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但该命题“不是建立在任何直观的基础上,无论是纯粹直观还是经验性的直观”[3]41。所以,按照是否可以直观的标准,道德法则当然应该归入不可知的范畴。
不仅如此,康德还多次指出,我们虽然可以通过道德法则而设想一个知性世界或理知世界,但该世界作为“本体界”并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因为我们不可能直观到它。例如,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下简称《奠基》)第三章第三节中论述与道德诸理念相联系的兴趣时,康德说到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属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属于知性世界。他写道:“甚至对于自己本身,即便根据人通过内部感受而对自己拥有的知识,他也不可以妄称认识他就自身而言是什么样子。因为既然他毕竟并没有仿佛是创造自己,不是先天地、而是经验性地获得他的概念,所以很自然,他也只能通过内感官,从而仅仅通过他的本性的显象以及他的意识被刺激的方式来获取关于他自己的信息,但他除了他自己的主体的这种纯由显象组成的性状之外,毕竟还必须以必然的方式假定某种别的作为基础的东西,亦即他的自我,如其就自身而言可能是的性状,因而就纯然的知觉和感觉的感受性而言把自己归入感官世界(zur Sinnenwelt),但就在它里面可能是纯粹活动的东西(根本不是通过刺激感官、而是直接达到意识的东西)而言把自己归入理智世界(zur intellektuellen Welt),但他对这个世界却没有进一步的认识。”[4]459在这里,康德把自我本身当作纯粹活动的东西,说它根本不是通过刺激感官而是直接达到意识的东西,这个自我本身属于知性世界或理智世界,但人对这个世界却没有进一步的认识。“没有进一步的认识”的原文是nicht weiter kennt,与第二批判“结论”中的表达一致,实际上意为“没有更进一步的切身了解”。
牙周手术前,两组患牙的TM均为Ⅱ度或Ⅲ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501,P>0.05)。与术前相比,术后6个月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有70.00%和66.66%的患牙TM得到改善(转为Ⅰ度)(Z=3.873,Z=3.464;P<0.05);而术后6个月两组间相比则无明显差异(Z=0.218,P>0.05)(表2)。
《奠基》第三章第三节论述“实践哲学的最后界限”时,康德还指出:“……如今,我虽然能够在还给我保留的理知世界中、在诸理智的世界中游荡,但是,尽管我对它有一个理由充足的理念,我却对它毕竟没有丝毫知识(Kenntnis),而且无论我的自然理性能力如何努力,我也绝不能达到这种知识。它仅仅意味着一个某物,当我只是为了限制出自感性领域的动因的原则,而把属于感官世界的一切都从我的意志的规定根据中排除掉之后,就剩下了这个某物;我这样做,乃是通过限定感性领域,并且指出:它并没有把一切都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在它之外还有其余的东西;但我对这个其余的东西却没有进一步的认识(kenne)。”[4]470如果我们可以确认这段话是在把感性领域与理知世界进行对比,则康德确乎认为,我们只知道理知世界是在感性领域之外的一个东西(某物),但关于这个某物,我们却并无更多的“认识”,也就是没有更切身的了解。
在这些段落中,康德像在第二批判的“结论”中一样,也把自我本身当作了物自体、本体,当作属于知性世界、理知世界或理智世界(康德使用了三个不同的说法)的东西,并且认为我们虽然可以直接意识到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但对于这个世界本身并没有更切身的认识或了解。
三、在实践哲学中本体界的道德法则是可知的
尽管道德法则以及与它相关的知性世界或理知世界不能进入理论认识的范围,但是,它作为一种实践认识却可以直接呈现在每个人以及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心中。对康德而言,我们虽然不能基于任何直观而从理论上认识到道德法则,但我们却可以直接意识到“理性作为纯粹理性是现实地实践的”[1]1,即意识到我们身上的理性能够独立于任何感性经验条件而给我们的意志颁布无条件的定言命令。这就是对道德法则的意识,这是纯粹理性的一个“事实”(Faktum),而且是唯一的事实,“纯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sic volo,sic jubeo)”⑤。康德还认为,我们对道德法则的这种实践意义上的认识,也可以说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自我意识”[1]37-38。
不基于直观的道德法则之所以在实践的意义上是可知的,是因为道德法则并不涉及以某种方式给予理性的诸对象的性状的认识,而仅仅涉及能成为某个对象之实存的根据的东西的认识,即涉及到纯粹实践理性。道德法则是纯粹实践理性给我们的意志所颁布的无条件的实践法则,它并不告诉我们对象是什么,或者是如何发生的,而是告诉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展开某种行动。所以,对道德法则的意识,就是对我们自己应该如何行动的意识。由于道德法则是撇开了一切经验条件的先天法则,因而对它的意识,也就同时是对我们意志自由的意识,这种意识使我们超出现象界而进入本体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德提出:道德法则为我们“提供出某种从感官世界的一切材料和我们理论理性运用的整个范围都绝对不可解释的事实,这个事实提供了对某个纯粹知性世界的指示,甚至对这个世界作出了积极的规定,并让我们认识到有关它的某种东西、即某种法则”[1]56-57。在这里,康德明确指出了道德法则是可以认识的。
对康德而言,他不可能仅仅在理论(思辨)哲学的范围内强调道德法则是不可知的物自体,否则,他就不可能在第二批判中从我们对道德法则的意识这个纯粹理性的“事实”出发,来说明我们具有对于意志自由的“意识”,也不可能把道德法则当作意志自由的“认识理由”,即从道德法则入手来认识意志自由了。一般而言,如果道德法则在实践的意义上也不可知,那么,康德的整个道德哲学(伦理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了。《实践理性批判》的第一卷“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论”的第一章论述的,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原理,其中重点就是纯粹形式的道德基本法则——“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1]39。从康德伦理的建构来看,我们很难设想康德把道德法则视为不可知的。理论(思辨)哲学中被说成是不可知的物自体,在实践哲学中必定会通过立场的变换,而被说成是可知的,尽管不是在直观、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还专门论述了“纯粹理性在实践运用中进行一种在思辨运用中它自身不可能的扩展的权利”[1]67,而这种“权利”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纯粹理性的“事实”即我们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或道德法则在我们心中的存在。
康德不仅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论证了道德法则在实践意义上的可知性,而且在《奠基》中也持相同的观点。康德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奠基》“无非是找出并且确立道德性的最高原则”[4]399。这里所说的“道德性的最高原则”,其实就是《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说的道德基本法则,它在《奠基》中表述为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4]428康德在该书第一章“从普通的道德理性认识到哲学的道德理性认识的过渡”中甚至提出:尽管普通的人类理性并不在一个普遍的形式中如此抽象地思考道德性的最高原则,“但毕竟在任何时候都现实地记得它,并把它当做自己判断的圭臬”[4]411。这表明,康德认为即使在普通的人类理性中也已经出现了对于道德法则的意识。
在《奠基》第二章论述意志自律原则时,康德指出,意志自律是意志的一种自我立法的状态,因为此时意志对于自身就是法则。该法则在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例如人)这里,表现为一个命令,一个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康德在此明确指出:“人们必须超越对客体的认识(Erkenntnis),达到对主体的批判,亦即对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因为这个无可置疑地颁布命令的综合命题必须能够被完全先天地认识。”⑥显然,他在此提出道德法则作为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必须能够完全先天地得到认识。在这里,对于客体的认识使用的是名词Erkenntnis,而对于定言命令的先天认识使用的是动词erkennen。这充分表明:康德不仅认为道德法则是可以认识的,而且必须从先天的意义上得到认识。
在《奠基》第三章中,康德还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属于知性世界的道德法则是可以认识的。说到底,这还是因为道德法则、定言命令仅仅是对意志的纯粹形式的规定。因而在康德看来,只要我们可以设想自己是知性世界的成员,即作为理智(Intelligenz)、作为理性存在者而存在,这个完全撇开了感性质料和内容的道德法则也就自动地跟着得出来了,我们也就可以设想我们作为单一知性世界成员会自动地按照形式命令而行动了。换言之,对道德法则或定言命令的形式主义理解,使得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设想它,也仅仅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能够认识它。康德说:“设想这个理想的纯粹理性,在去除一切质料亦即客体的知识(Erkenntnis⑧)之后,剩给我的无非是形式,亦即准则的普遍有效性的实践法则,以及依照这一法则,与一个纯粹的知性世界相关,把理性设想成为可能的作用因,亦即设想成为规定意志的原因。在这里,必须完全不存在动机;一个理知世界的这一理念本身就必须是动机,或者是理性原初感兴趣的东西。但是,使这一点可以理解,恰恰是我们不能解决的课题。”[4]470
可见,康德在《奠基》中不仅明确指出“先天综合地定言命令必须能够完全先天地得到认识”“我们认识到意志的自律”,而且进一步解释了这种认识是在什么意义上成立的。“设想”是一个关键词,我们一旦“设想”自己是知性世界的成员,或者“设想”我们的理性是属于知性世界的,就会认识到我们的意志需要服从纯粹形式的命令或要求。我们对道德法则的认识,是一种纯粹形式意义上的认识,不涉及任何感性内容或质料,因而自然不同于第一批判中所说的知性认识——这种知性认识依赖于感性直观所通过的经验内容。但是,在康德的几乎所有论述中,都始终在强调道德法则和意志自由具有层次上的不同,因此,在两者是否可以认识这个问题上的回答也是不同的。自由是无法说明和看透的,我们无法说明其原因,而只能将之交给理性的自发的能动性。但是,在意志自由这个“存在理由”业已给定的条件下,如果我们设想自己是知性世界的成员,我们就应该合理地设想对我们行动准则所提出的形式要求,即要求准则能够成为法则。一旦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纯粹理性的事实就出现了,我们对法则的意识也就出现了。
四、如何理解“对道德法则的意识不能作出进一步解释”的说法
虽然康德充分表明了在实践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直接意识到道德法则,并通过对道德法则的意识而认识到我们意志的自由,但是,他并没有忘记指出:我们并不能在理论的意义上最终解释或说明我们对道德法则的意识究竟是如何可能的。例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写道:“至于对道德律的这种意识,或者这样说也一样,对自由的意识,是如何可能的,这是不能进一步解释的(erklären)的,不过它们的可容许性倒是完全可以在理论的批判中得到辩护。”[1]61康德在此明确指出:对道德法则的意识和对自由的意识是一回事,而这种意识,我们不可能作出进一步的解释或说明。换言之,我们可以意识到理性作为纯粹理性现实地是实践的,我们身上具有理性的能力,能够为我们的意志颁布道德法则,但“这些能力的可能性是根本不能理解的”[1]62。
在《奠基》中,康德同样表达了这一层意思。也就是说,承认道德法则在实践的意义上是可以认识的,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说明意志自由,或者能够说明我们为什么具有纯粹理性的道德兴趣,说明我们的理性何以是实践的。对康德来说,实践哲学具有自己的“最后界限”:自由或法则在理论的意义上并不能给出最终的解释或说明。
《奠基》在论述了通过设想人是双重世界的成员而解决意志自由的可能性问题之后,康德进而断言:“实践理性根本没有因为设想(denkt⑨)自己进入一个知性世界而逾越自己的界限,但当它想直观 (hineinschauen)、感觉 (hineinempfinden)自己进入其中的时候,它就逾越了自己的界限。”[4]466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不误以为自己可以对此知性世界加以直观、感觉,我们设想自己进入一个知性世界就没有逾越实践理性的界限。“但如果实践理性还从知性世界索取一个意志的客体,亦即一个动因,那么,它就逾越了自己的界限,妄想认识(kennt)某种它自己一无所知的东西。”[4]466这里所说的知性世界中的意志的客体,不是指欲望或爱好的对象,而是理性本身的对象,康德并且把这个客体与动因相等同。康德认为这个客体不可知,我推测他是在说,道德法则的规定根据即自由,是不可能被确切认识的。康德在此肯定了什么东西是实践理性可以合理地加以设想的,进而否定了在这种合理设想之上继续探究其动因的可能性。他说:“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理性胆敢去说明纯粹理性如何能够是实践的,它就逾越了自己的所有界限,这与说明自由如何可能的任务完全是一回事。”[4]466这就明确指出了:“自由如何可能”和“纯粹理性如何能够是实践的”,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也是得不到说明(erklären)的问题。康德还把不可能说明意志自由,与不可能发现和解释人们何以对道德法则有兴趣相提并论[4]468。
在我看来,康德的这些说法并没有否定法则和自由可以在实践的意义上得到认识的观点,而仅仅是说,在理论的意义上,我们不能超越实践理性的界限,把自由和法则当作可以直观、感觉的东西来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和说明,但是在实践的意义上,哪怕它们是根本不可以被直观的,也是可以直接被我们意识到的。对法则和自由的意识,绝不同于理论的认识,因为这是一种行动意识,一旦我们意识到了法则,就意识到自己应该按照道德法则行动,或者至少不去做违背道德法则的事情。
总之,康德所说的道德法则作为我们意识到意志自由的一个“理性的事实”,虽然不是建立在任何直观的基础上的,因而不可能在理论的意义上得到认识,但毕竟可以在实践的意义上得到认识。因此,我们在理解道德法则和意志自由时,必须关注康德由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过渡,以及随着这一过渡而出现的理解视野的扩展。
注释:
①该文是在与刘悦笛先生的对话中展开的,因录音未成,李先生便亲自动笔写成。
②康德在这个“结论”的第一段话中使用了Bewunderung和Ehrfurcht两个德文词,在第二段开头作了改动,说的是Bewunderung和Achtung。邓晓芒老师的译本分别用“惊奇”和“赞叹”两个词翻译第一、第二段话中的Bewunderung,而把Ehrfurcht翻译为“敬畏”,Achtung翻译为“敬重”。
③李先生在此把“物自体的世界”与“本体的世界”视为含义相同的概念,并把两者归结为“一个超人类的理世界”。把物自体的世界等同于本体的世界,涉及“物自体”和“本体”是否等同的细节问题,在此不作深入探讨。把物自体的世界或本体的世界归结为“一个超人类的理世界”,这个“理世界”可能就是康德经常说到的“理知世界”或“知性世界”,在其中,人是作为理智(Intelligenz)或理性存在者,因而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者而存在的。
④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20.引文中“人格”的原文为Persönlichkeit,邓晓芒教授现在倾向于翻译为“人格性”,而用“人格”翻译Person这个词。
⑤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1.其中拉丁文意为“我行我素”,可直译为:如何想,就如何吩咐。
⑥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M]//康德著作全集: 第4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49.Erkenntnis原译文是“知识”。
⑦在这里,康德消除自由和法则的表面循环的思路,是引入具有自发性的、积极能动的理性。他实际上是把意志的自由与理性的自发的能动性联系起来,因此,他在后文中不仅认为自由是不可认识的,还认为理性的这种自发性同样也是不可认识。说到底,意志的自由就是意志中理性方面的自发的能动性,这是不可以再进行任何解释和说明的东西。
⑧Erkenntnis,是erkennen(认识)的名词形式。
⑨denkt,李秋零老师翻译为“设想”。对康德哲学的许多误解都是由于轻视了这个词。比如,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多次说到,我们可以把自己对道德法则的服从,设想为是对神的戒律的服从,其实道德法则不是神颁布的,而是人的理性颁布的。所以,不要因为康德设想了一个单纯知性世界的成员,或设想了一个完美的理性存在者或神圣的绝对善良意志,就担心他由此陷入了外在的宗教神学的“他律”。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导言中,康德在论述我们只能认识(erkennen)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时,曾特别作出保留,那就是我们尽管不认识自在之物,但至少可以设想(denken)自在之物。“……我们正是对于也是作为自在之物本身的这同一些对象,哪怕不能认识,至少还必须能够思维(denken)。”(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邓老师在此把denken翻译为“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