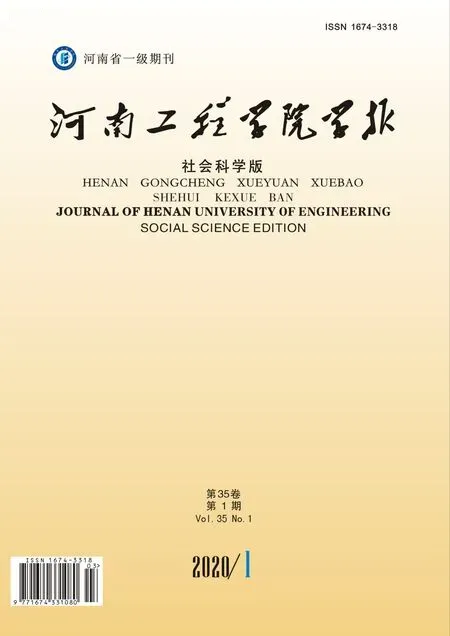越南科举制度停废百年的中国研究述评
许 露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361005)
2019年是越南科举制度停废一百周年。中国是世界上科举制度的发源地,越南是“世界上科举制度的终结地”[1]。分科举士从一种尝试到一种较为成熟的制度,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其目的在于选拔俊彦,促进社会公平和阶级流动;科举制度走出中国,直接辐射到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文教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越南是“最迟实行科举,也是最后废止科举的国家”[2]。越南科举制度对维护封建统治和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目前,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现实环境下研究越南科举制度停废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易于发现科举制度停废对越南社会的直接影响,而且利于丰富近代科举文化的内涵。
中国学者对越南科举制度的研究可以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有学者发现,越南废止科举的时间较为滞后。[3]其后,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内容逐渐深入,例如,厦门大学刘海峰在《科举学导论》一书中专设一节,题为“越南科举论”,详细论述越南科举制度的始终、特点及其社会影响[2];之后,刘海峰连续发表多篇论文(1)如《科举制——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科举学的起承转合——科举研究史的千年回顾》《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变》等。,从文化圈的视角考察科举制度在东亚、东南亚各地的传播,高度评价越南科举制度;姜振华研究了越南阮朝中后期科举[4];2015年,暨南大学陈文在《越南科举制度研究》中按历史脉络分析越南科举制度的起承转合[5]。
囿于语言障碍,本研究只能选择中国文献进行分析。除了上述研究成果,中国知网上关于越南科举制度停废的相关文献一共有28篇(2)其中,期刊论文有21篇,学位论文有7篇。。这些文献大多涉及越南科举制度停废的过程、原因和影响等方面。
一、关于越南科举制度停废过程的研究
就停废过程而言,中国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立刻停止论,另一种是渐进革废论。
越南科举制度立刻停止论是指越南科举制度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戛然而止。例如,萧源锦引用1919年越南《南风》杂志第24期载:“今科会试为我国最后之一科。殿试后,未中选者二十二人。”[6]从中可以看出越南科举制度停废的大致时间。持立刻停止论的学者往往对越南科举制度停废的过程并不关心,他们仅仅视越南科举制度停废为一项重大的事件或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一项重大事件的前后,越南社会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如:越南接受西方文化和思想[7],设置、调整、改造越南的各级、各类近代学校[8],发展本国语、本国文学和本国文化[9],重新调整对近代中国的认识[10]等。越南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又进一步强调科举制度停废的重要性。近代越南立停科举制度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和关键节点。
越南科举制度渐进革废论是指越南科举制度在一系列因素刺激和制约下,逐步实施改革,因无法完全实现预定目标而最终走向终结。根据《越南科举制度研究》一书记载,20世纪初越南科举考试内容和评卷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考试的科目发生了变化:取消传统经义和诗赋(从中国引入),分步推出“法语、国语(越南语)、时政、格物”[5]等新科目,新科目的推广不仅改变了地方乡试的面貌,亦改变了中央会试的面貌。另一方面,评卷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开始使用点数评分的方式:应试者各个科目所得到的点数十分重要,第一科所得的点数必须达到基本要求,才可以参加第二科考试;各个科目点数达到基本要求,并不意味着应试者可获得功名,只有各科都表现优异的人才,方能获得较高名次,具备进入更高一级科举考试的资格。然而,越南通过科举制度改革没有选拔出改变国家命运的领袖人才,没有在本国普及学校教育,也没有在国势衰微时力挽狂澜,这一改革的命运几乎与中国清末改革科举制度一样。
总之,任何社会改革都不会立竿见影,也不会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越南科举制度改革的每一个“小动作”几乎都曾引发社会争议。在或明或暗的对抗中,越南科举制度改革的效果不佳。科举制度改革不力逐渐成为阮朝朝野内外共同的焦虑,越来越多的人指责科举改革措施不合理,科举改革弊端明显,一些改革的支持者发生转变,反对更深层次、更多形式的改革。因科举制度改革产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科举制度改革彻底陷入僵局。最终,启定四年(1919年)越南皇帝决定停废科举制度。这一举措是越南改革不力的最终选择。
二、关于越南科举制度停废原因的研究
就停废原因而言,中国学者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内因是主导,一种认为外因是主导,还有一种认为内外因相结合,共同导致越南科举制度的停废。
(一)内因主导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科举制度停废是越南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在越南国民中,两类人对停废科举制度的贡献极大,一类是近代越南留学人士,一类是近代越南进步人士。这两类人存在一定的交集,但不完全相同。
近代越南留学人士对科举停废的作用极大。20世纪初,越南学子开始出国留学,有的远赴欧美,有的就近进入日本各类学堂——或是文科院校,或是军事院校,或是综合性的国立大学。留学期间,越南学子学到了较为系统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广泛接触到近代工业文明的各个方面,较全面地了解近代化内涵,较深刻地感受到越南与外界社会的差距。留学生回国之后要求停废科举制度,兴建新式学堂,选拔和培养各类人才,推动越南社会走向近代化。留学生“极大地震撼了越南的封建士大夫阶层”[11],引起了士大夫阶层分化,逐渐分为保守的一派和开明的一派,保守的一派始终坚持科举制度的传统性和合理性,开明的一派指责科举制度为“牢笼豪杰之闾里耳目”[5]。内部意见不统一是导致越南科举制度废除的直接原因。
近代越南进步人士对科举停废的贡献良多。近代越南的进步人士不仅包括越南留学人士,而且包括许多未留学的越南本土人士。越南留学人士回国后创办新式学校,发展新式教育,培养新式人才,这使一部分越南本土人士愈发开明,思想和观念趋于进步。1907年3月,“在梁文玕、阮权等进步士大夫的倡议下”[12],东京义塾成立。该校设在首都河内,为越南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由越南国人主导的新式学堂之一,该校的成立具有重要的意义。东京义塾聘请许多新式教师,他们接受过西方新思想的洗礼,传播新式思想;学校采用的教学形式多样,活动丰富,如课程讲授、文章讲评、读报竞赛和公开演说等;此外,该校还开设不少新式课程,大致分为语言类(3)如“法语”和“本国语”等科目。、数学类(4)如“算术”科目。、自然类(5)如“自然”和“地理”科目。和医药类(6)如“卫生”科目。等。在这些具有近代化思想的教师影响下,东京义塾“培养了近千名学员”[13],这些学员在越南各地广泛传播新思想、新理念,对停废科举制度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外因主导
外因在事物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越南科举制度停废是外国近代思想和实践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外因主导论又可细分为法国殖民说、日本经验说和中国教训说三种。
在绝大多数文章中,法国的殖民统治和教育改革实践为越南近代改革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法国殖民越南之后,“在文化教育和科举考试方面进行西化和去中国化的改革”[5],这使越南重新树立文化依赖的对象,逐渐地认同、恪守法国确立的政治统治秩序和工业文明。尤其是在不平等的《顺化条约》签订后,法国对越南控制程度不断加深,“实际上取代了越南帝王的统治”[2],并视越南为法国在东亚海外殖民的“试验田”,将法国的教育体制和工业文明移栽此处,“实行小学、中学、大学三级的近代普通教育制”[12];并配套相应的西式官僚体制,为越南部分阶层提供了职位上升的空间,“将受西式教育作为晋身的阶梯”[14]。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下,越南的中圻和北圻也受到一定影响,最终促使“科举考试寿终正寝”[15]。
日本经验说是指近代越南开明人士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并将这种成功经验嫁接到越南国内。凭借明治维新的改革,当时的日本从被动挨打逐步走向强大,并先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分别打败中国和沙皇俄国。战争滋长了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想,日本一跃而起,成为东方军事、文化强国,其成功的经验吸引了越南的注意力。同时,日本不是越南的殖民地宗主国,日越两国没有直接的冲突和利害关系。从革新走向富强,日本所依赖的是掌握西方先进科技的专门人才,而这些专门人才并不是由科举制度选拔和培养出来的。这一经验引起越南社会的注意。越南开明人士认为:应努力向日本学习,开设新学堂,学习新知识,培养新人才;用西方工业文明的知识和技术,服务于越南社会,“作为振民气、开民智的基础”[16],最终促进越南社会转型,摆脱被法国殖民的悲惨命运,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
中国教训说是指近代越南进步人士深刻反思近代中国科举改革失败的教训,这是当时越南不得不面对的现实。1905年9月,“作为中国传统高等教育重心的科举考试宣布终结”[17],这一事件对越南进步人士产生了一定刺激,他们不得不感叹:“中国废文章矣,停科举矣,我国人其鉴兹哉。”[5]既然连中国都立停了科举,越南又何必久久不能放下这一制度呢?不过,近代越南进步人士始终保持理性,因为他们发现,当时中国科举停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成功,这一激进的改革“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广泛社会后果”[18],尤其是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兴建学堂的举措“不断暴露出问题”[19]。中国科举停废的教训引起近代越南进步人士的警觉,他们有所犹豫,不敢贸然废除本国科举制度。越是观察中国废除科举制度的影响,近代越南进步人士越清楚,在没有周全的制度设计和保障下,尽量避免立即废除本国科举制度,防止社会动荡,尤其是20世纪初越南的封建统治已岌岌可危,内部起义和外部侵略交织,若是贸然废除科举制度,则很可能重蹈清王朝灭亡的命运。
法国殖民说、日本经验说和中国教训说等都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均是从某一个侧面审视越南科举制度废除的外部原因,不能偏颇,而应兼顾各种因素。
(三)内外因结合
还有人认为,越南科举制度停废是内外因相结合的产物。例如,厦门大学刘海峰认为,科举制度停废是越南人民对法国殖民统治秩序的最终选择,也受到近代中国科举制度停废的影响。[1]暨南大学陈文认为,越南科举制度的停废既与法国的殖民统治有很大关系,但也须反思科举制度的局限性;此外,陈文还从历史、地理方面指出,当时法国的殖民统治导致“越南南北交通受阻”[5],交通阻塞大大限制了越南各地考生参与会试、殿试。
我们应将内外因相结合,从两个方面共同考察越南科举制度停废的原因。中国科举制改革的教训、法国的殖民统治和日本的改革经验是不容忽视的外部因素,越南科举制度的弊端和越南人民的自主选择是不可否认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通过内部因素发生作用,最终导致越南科举制度停废。
三、关于越南科举制度停废影响的研究
“就废科举的影响而言,它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20]越南科举由形成到停废,持续时间长达八百年,科举制度已经渗透到越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的里里外外;科举制度的停废自然会影响越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方面面。就目前研究成果而言,科举制度停废被视为越南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直接影响越南的文官政治、学校发展和儒家文化[21]等方面。
越南科举制度选拔出不少社会精英,他们通过科举进入国家的文官体系,“崛起于破旧的诗书之中”[22],科举制度对越南的文化和社会阶层流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越南学者丁克顺认为,“科举制度已经给在越南乡村的人民创造了一个好学的精神”[23],这一好学的精神一直延续至今,对越南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有人认为,“越南传统文化的架构逐步倒塌”[12],涉及汉字、汉语、喃字和儒家学说等方面,汉文化的传播规模和影响程度大不如前。有人发现,科举制度停废后越南上层人士对中国儒家文化的认识不同,南圻普遍能接受“法语或拉丁语化‘国语’教育”,中圻和北圻对儒家经典念念不忘,儒家著作“仍奉若至宝”。[14]还有人考察科举制度停废前后越南大众的识字情况,发现社会上开始“倡导、推广和普及国语字(7)即越南如今使用的拼音文字。”[24],且“越南人的整体识字水平急剧下滑”[25],这对越南民族文化普及形成了障碍。
科举制度停废对越南教育亦有影响,越南新型高等教育兴起。1917年,《印度支那联邦公共教育法》正式颁布;同年,印度支那大学在总督阿尔伯特·沙罗的支持下得以重建,吸纳了印度支那医学院,设置多个应用技能学院,包括师范、兽医、农学、林学、市政工程和商学等不同学科;“越南高等教育正式步入正轨”[26],科举制度停废为越南新式学校提供了部分生源,学校体制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各级各类学校兴起,学校取代了科举制度的地位,“其(法国殖民者)文化渗透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地位”[8]。
四、结语
科举制度停废是越南近代史上一件举足轻重的事件。中国学者从不同侧面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其一,越南科举制度停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多方位的改革到最终走向停废;其二,越南科举制度停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既包括内部因素,也包括外部因素;其三,越南科举制度停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应从整体上予以把握。
然而,关于越南科举制度停废的研究仍存在不少空白,将来研究还有更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