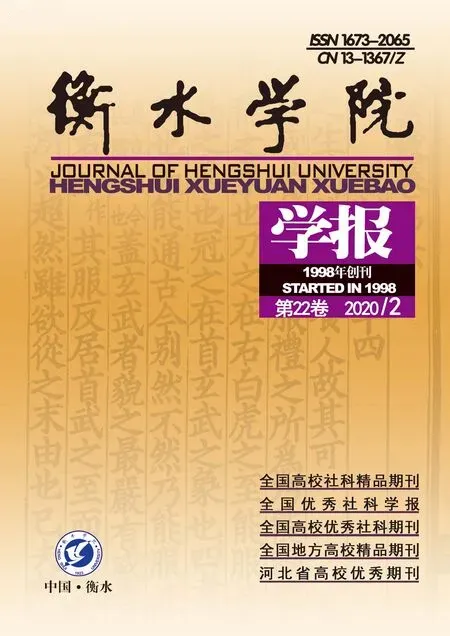张岱年先生早期中国哲学研究之范式意义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215006)
因为大家都明白的原因,张岱年先生在他学术生涯的中期,几乎不能公开署名发表或出版其中国哲学①中国哲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哲学,系指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系统理论;狭义的中国哲学,通常指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中国哲学史,本文中的“中国哲学”范畴,如未注明系取广义,一律特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论著,因而供我们后学研究的张先生的中国哲学论著,绝大多数属于其学术生涯早晚期论著。对张先生早晚期中国哲学研究论著之价值的评价,可能会有分歧,或认为其早期的中国哲学研究论著对我们后学进一步研究中国哲学的启迪、促进作用大;或以为其晚期的中国哲学研究论著对我们后学进一步研究中国哲学的启迪、促进作用大。这会因学养差异、为学旨趣差异而做出相异的判断。笔者为学一直限于中国哲学,而并不深厚的学养又主要限于儒家哲学,因此就笔者的眼光看,自然会认为张先生早期的中国哲学研究论著比晚期的作用更大(指促进中国哲学研究)。这就是本文为何将论域限定在“早期”的原因。要问如何划分张先生的学术生涯?笔者的回答是:张先生学术生涯的早期截止于1957年,而他的学术生涯的晚期开始于1979年。
一
张岱年先生的早期中国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学科创立之初期实践有密切关系,因而在叙述张先生早年如何研究中国哲学之前,有必要先简要说明中国哲学学科创立初期的基本情形。日本哲学家西周于1867年在其著《百一新论》中首先使用“哲学”一词。而“哲学”一词由日本输入中国,具体年代不详,但从王国维于1903年在《教育世界》发表了《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来断,大体可以将汉语“哲学”一词传入我国之时间具体限定在1901-1903年这三年内。至于“中国哲学”之称谓,还要晚至1906年才出现,证据是:那一年刘光汉(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哲学起源考》。刘师培坚持“以子通经”的学术取向,其眼中的“中国哲学”,主要指中国传统学术范畴中的子学与经学。刘氏的这一认识,大体上反映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学人对中国哲学的普遍认识。此文之后,大约又经历了十年,中国学人对于中国哲学的认识,仍然局限在传统学术范畴中的子学与经学那里,甚至难以彻底摆脱对传统史学内容的执着。这种情形,可以由北京大学所开“中国哲学”课程佐证。北京大学于1915、1916年有教授正式开讲的“中国哲学史”课程,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1]170。这样来讲中国哲学史,岂不等同于讲中国历史,消解了“中国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特性,使“中国哲学史”失去了存在意义。
有学友告知:1915、1916年在北大哲学门教授中国哲学的那位教授叫陈黻宸,据说他的“中国哲学”讲义尚存。笔者没看过陈先生的那部中国哲学讲义,对其学术价值,不敢妄加评论,这里想说的一点是:大约与陈先生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同时期,在我国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哲学专著,即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著191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此著分为三编,第一编为“上古哲学史”,第二编为“中古哲学史”,第三编为“近世哲学史”。其所谓“上古”,是指邃古至秦末;其所谓“中古”,是指“两汉至唐末”;其所谓“近世”,是指“宋元明清”四代。三编均分上下。第一编上限定在“古代及儒家”范围,共设三章,章名依次为“哲学之渊源”“六艺哲学”“儒家”。“哲学之渊源”章下分三节,节名依次为“邃古哲学之起源”“唐虞哲学”“夏商哲学”;“六艺哲学”章下亦分节,节名依次为“总论”“易教”“五教之学”;“儒家”章下分四节,节名依次为“孔子”“子思”“孟子”“荀子”。第一编下限定在“道墨诸家及秦代”范围,共设六章,章名依次为“道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秦灭古学”。这六章中,只有“道家”“法家”“名家”三章分节。“道家”章分五节,节名依次为“总论”“老子”“杨朱”“列子”“庄子”;“法家”章分四节,节名依次为“管仲”“申不害”“商鞅”“慎到”;“名家”章分四节,节名依次为“名家之渊源”“尹文”“惠施”“公孙龙”。
第二编上限定在“两汉”范围,共设十二章,各章下均不分节,章名依次为“汉代哲学总论”“陆贾”“董仲舒”“淮南子”“桓宽盐铁论”“刘向”“扬雄”“王充”“东汉经术今古学之分及其混合”“荀悦”“徐干”。第二编下限定在“魏晋六朝唐”,共设十章,各章亦不分节,章名依次为“魏晋及南北朝之儒学与经术总论”“晋世黄老刑名学之复兴”“六朝佛教之盛行”“三教调和论”“神不灭论与神灭论”“文中子”“唐代哲学总论”“唐代佛教略述”“韩愈”“李翱”。
第三编上限定在“宋元”范围,共设十九章,各章下均不分节,章名依次为“宋代哲学总论”“道学之渊源”“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二程同时之性情说”“程门诸子”“张南轩”“朱晦庵”“朱子门人”“陆象山”“象山门人”“浙东永嘉之学”“魏鹤山及真西山”“元之程朱学派”“元之朱陆调和派”“元之陆学派”。第三编下限定在“明清”范围,共设二十二章,各章下均不分节,章名依次为“明代哲学总论”“吴康斋”“薛敬轩”“曹月川”“胡敬斋”“陈白沙”“王阳明”“湛甘泉”“罗整庵”“王学诸子”“汤潜庵”“陆稼书”“颜习斋”“戴东原”“彭尺木”。
从以上烦琐罗列可以看出,作为第一部正式公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谢著虽然在中国哲学史之断代上突破了陈黻宸“从三皇五帝讲起”的局限,首次将中国哲学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大发展历程,但仍未将中国哲学从传统之经学、史学、子学中独立出来,因而够不上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加之其中国哲学史之断代,又被学者断为系承袭日本学者所著《支那哲学史》的分法,所以谢著虽为冠名《中国哲学史》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哲学专著,但一直未被中国哲学史界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第一部著作看待。
被中国哲学史界视为第一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此著先于1917年在北京大学印作讲义,正式出版在1919年。出版时,此著分为十二篇,篇下有的设章,有的则不设。不设章的为第一篇:导言;第三篇:老子;第五篇:孔门弟子;第七篇:杨朱。设章的有八篇,其中第二篇题曰“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下设两章,一曰“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二曰“那时代的思潮(诗人时代)”;第四篇题曰“孔子”,下设五章,一曰“孔子略传”,二曰“孔子的时代”,三曰“易”,四曰“正名主义”,五曰“一以贯之”;第六篇题曰“墨子”,下设四章,一曰“墨子略传”,二曰“墨子的哲学方法”,三曰“三表法”,四曰“墨子的宗教”;第八篇题曰“别墨”,下设六章,一曰“墨辩与别墨”,二曰“墨辩论知识”,三曰“论辩”,四曰“惠施”,五曰“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六曰“墨学结论”;第九篇题曰“庄子”,下设两章,一曰“庄子的生物进化论”,二曰“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第十篇题曰“荀子以前的儒家”,下设两章,一曰“大学与中庸”,二曰“孟子”;第十一篇题曰“荀子”,下设三章,一曰“荀子”,二曰“天与性”,三曰“心理学与名学”;第十二篇题曰“古代哲学的终局”,下设三章,一曰“西历前三世纪之思潮”,二曰“所谓法家”,三曰“古代哲学之中绝”。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甫问世,就受到陈黻宸的质疑,陈先生拿着《中国哲学大纲》讲义对哲学门三年级的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哲学的大纲了吗?”[1]171但是,该著出版后,却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然在一片赞扬之中,亦有学者不以为然,不点名予以批评。作为这一批评的代表之作,就是钟泰的《中国哲学史》。该著192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卷首列有著述“凡例”十条,其中有云:“中西学术,各有系统,强为比附,转失本真。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从这条著述原则可以看出,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应是不认同胡适中西哲学相比附的做法,特意与胡适唱反调的产物,尽管他在书中没有提及胡适的名以及胡适的书。
钟著全书分四编,并将四编分上下。卷上含第一编、第二编;卷下含第三编、第四编。第一编:上古哲学史,下设十三章,一曰“上古之思想”,二曰“王官六艺之学”,三曰“老子”(附管子、附《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解),四曰“孔子”,五曰“墨子”(附宋钘),六曰“杨子”,七曰“商君、尸子附见”(附论管商同异),八曰“庄子”(附列子),九曰孟子,(附曾子、子思,又告子附见),十曰“惠施、公孙龙”(附尹文子),十一曰“荀子”,十二曰“韩非、申子”(慎子附见),十三曰“秦灭古学”。
第二编:中古哲学史,下设二十三章,一曰“两汉儒学之盛”,二曰“贾生”,三曰“董仲舒”,四曰“淮南王安”(附刘向),五曰“扬雄”,六曰“王充”(附王符、仲长统),七曰“郑玄”,八曰“魏伯阳”,九曰“牟融”,十曰“荀悦”,十一曰“徐干”,十二曰“魏晋谈玄之风”,十三曰“刘劭”,十四曰“裴頠”,十五曰“傅玄”,十六曰“葛洪”(附鲍生),十七曰“陶渊明”,十八曰“南北朝儒释道三教之争”,十九曰“范缜”(附萧琛),二十曰“王通”,二十一曰“隋唐佛教之宗派”,二十二曰“韩愈、李翱”,二十三曰“柳宗元、刘禹锡”。
第三编:近古哲学史,下设三十一章,一曰“宋儒之道学”,二曰“周子”,三曰“邵子”(附司马温公),四曰“张子”,五曰“明道程子”,六曰“伊川程子”(附论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七曰“王荆公”(附苏东坡、苏颖滨),八曰“朱子”(李延平附见),九曰“张南轩”(胡五峰附见),十曰“吕东莱”(附陈龙川),十一曰“薛艮斋”(附陈止斋),十二曰“陆象山”(附论朱陆异同),十三曰“叶水心”(附唐说斋),十四曰“蔡西山、蔡九峰”(附蔡节斋),十五曰“杨慈湖”,十六曰“真西山、魏鹤山”,十七曰“元明诸儒之继起”,十八曰“吴草庐、郑师山”,十九曰“刘伯温”,二十曰“方正学”(附宋潜溪),二十一曰“曾月川、薛敬轩”,二十二曰“吴康斋、胡敬斋”,二十三曰“陈白沙”,二十四曰“王阳明”,二十五曰“罗整庵”,二十六曰“湛甘泉”,二十七曰“王龙溪、王心斋”(附钱绪山),二十八曰“胡庐山”(附罗念庵),二十九曰“吕心吾”,三十曰“顾泾阳、高景逸”,三十一曰“刘蕺山、黄石斋”。
第四编:近世哲学史,下设十五章,一曰“清儒之标榜汉学”,二曰“孙夏峰”(附汤潜庵),三曰“陆桴亭”(附陆稼书),四曰“黄梨洲”,五曰“顾亭林”(张蒿庵附见),六曰“张杨园”,七曰“李二曲”,八曰“王船山”,九曰“唐铸万”(附胡石庄),十曰“颜习斋、李恕谷”,十一曰“戴东原”,十二曰“彭允初、汪大绅、罗台山”,十三曰“洪北江”,十四曰“龚定庵”,十五曰“曾文正公”。
钟泰是以传统子学①包括儒学的广义子学。规范中国哲学,其著在断代上只是将谢无量、胡适分法中的“中古”时期又具体分为“中古”“近古”两个阶段;而在内容上虽然将中国哲学独立出经学②他认为中国哲学源于“六艺之学”,然并不等于“六艺之学”。,但未能将中国哲学与中国学术、思想清晰地区分开来,仍然属于泛化的中国哲学论著,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难以构成实质性的挑战。真正对胡著构成实质性挑战的论著是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该著上卷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上下两卷本一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则是在1934年;虽篇幅远超谢、胡、钟各著,但只分为两篇,第一篇:子学时代;第二篇:经学时代。第一篇“子学时代”,下设十六章,一曰“绪论”,二曰“泛论子学时代”,三曰“孔子以前及其同时之宗教的哲学的思想”,四曰“孔子及儒家之初起”,五曰“墨子及前期墨家”,六曰“孟子及儒家中之孟学”,七曰“战国时之‘百家之学’”,八曰“《老子》”及道家中“《老》学”,九曰“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十曰“庄子及道家中之庄学”,十一曰“《墨经》及后期墨家”,十二曰“荀子及儒家中之荀学”,十三曰“韩非及其他法家”,十四曰“秦汉之际之儒家”,十五曰“《易传》及《淮南鸿烈》中之宇宙论”,十六曰“儒家之六艺论及儒家之独尊”;第二篇“经学时代”,下设十六章,一曰“泛论经学时代”,二曰“董仲舒与今文经学”,三曰“两汉之际谶纬及象数之学”,四曰“古文经学与扬雄、王充”,五曰“南北朝之玄学(上)”,六曰“南北朝之玄学(下)”,七曰“南北朝之佛学及当时人对于佛学之争论”,八曰“隋唐之佛学(上)”,九曰“隋唐之佛学(下)”,十曰“道学之初兴及道学中‘二氏’之成分”,十一曰“周濂溪、邵康节”,十二曰“张横渠及二程”,十三曰“朱子”,十四曰“陆象山、王阳明及明代之心学”,十五曰“清代道学之继续”,十六曰“清代之今文经学”;附录五篇:一曰“原儒墨”,二曰“原儒墨补”,三曰“原名法阴阳道德”,四曰“原杂家(与张可为君合作)”,五曰“孟子浩然之气章解”。
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比,它不是有头无尾之作,而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之整体做系统阐述之作;同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钟泰的《中国哲学史》相比,它之优长,不仅体现在它在量上远远超过谢、钟氏二著的篇幅,而且体现在它突破了谢、钟二氏传统的叙述方式,属于运用现代哲学方法来阐述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之作。因此有学者高度评价它的价值,称之为“是用现代哲学方法编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通史著作,对中国哲学史形成一门独立学科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2]。但胡适似乎不这么看,因为他在回应冯著对其著的挑战时,特意强调冯著仍然属于传统学术范畴,不承认其现代学术性质。
冯著出版两年后,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于193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此著是范氏于1933年在武汉大学所编“中国哲学史”讲义修改而成,全书除“绪论”,分为六编。第一编:先秦时代的哲学(子学),下设六章,一曰“概说”,二曰“儒家”,三曰“道家”,四曰“墨家”,五曰“名家”,六曰“法家”;第二编:汉代的哲学(经学),下设五章,一曰“概说”,二曰“刘安”,三曰“董仲舒”,四曰“扬雄”,五曰“王充”;第三编:魏晋南北朝的哲学(玄学),下设五章,一曰“概说”,二曰“清谈——老庄哲学的勃兴”,三曰“道教组织的完成”,四曰“佛教思想的勃兴”,五曰“经学的衰落与分裂”;第四编:隋唐的哲学(佛学),下设三章,一曰“概说”,二曰“佛教各宗思想的概要”,三曰“儒学的统一及其反响”;第五编:宋明的哲学(经学),下设四章,一曰“概说”,二曰“宋明儒家思想的概要”,三曰“佛教教宗的衰落与禅宗的隆盛”,四曰“道教宗派的分裂与教理的革新”;第六编:清代的哲学(经学),下设五章,一曰“概说”,二曰“宋学派”,三曰“实行派”,四曰“汉学派”,五曰“公羊学派”。
范氏在此书“付印题记”中写道:“就内容言,疏漏错误,自知不免;即间有所得,亦多采自当代著作家之说,出诸自创者盖鲜。而余在是书之编撰上最受其补益者,厥推武内义雄、宇野哲人、境野黄洋、小柳司气太、河上肇及梁启超、周予同、胡适、冯友兰、雷海宗诸家。余固不敢掠人之美也。”从范氏这一申明可以看出,他的这部中国哲学史,是兼收中日当代著作家的学术成果的产物,而他所吸收的那些成果,在内容上固然多属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成果,但也当包括中国之经学史、儒学史、思想史方面的成果。而按照范氏自己在该书《序言》中的强调:本书“观点却与当时各家不同,主以唯物辩证法阐述我国历代各家之思想”[3],范著区别于谢、胡、钟、冯四著的根本特色在于第一次运用唯物辩证法评析中国哲学。
在范著出版前一年,张岱年先生开始写《中国哲学大纲》,在范著出版后一年,张先生完成《中国哲学大纲》的写作,然《中国哲学大纲》印作讲义,在1943年,距范著出版,却迟了七年多。就《中国哲学大纲》后于《中国哲学史通论》而论,后者对前者有可能产生影响,但迄今我们未发现两者有所交集的材料,所以笔者暂且不认为范著对张著有过影响。换言之,笔者认为: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之实践过程中,张的实践,实际上是跨过范著而直接上接冯先生的实践——张著是为了弥补冯著缺陷所著。为了认识这一点,准确把握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实践的“正—反—合”过程,有必要具体叙述张先生是如何实践的。因为无法再现其实践的详情,下面的叙述,只能根据其论著发表前后的历史顺序来把握其实践阶段及其特征。
二
上面的叙述表明,中国哲学史学科之初步创立,大约经历了20年。这20年内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成果与不足,就是张岱年先生早期中国哲学研究所要面对的现实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先生从他十七八岁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史,就清醒地面对当时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积极回答当时中国哲学研究所提出的问题。
据说,于1927年发表于《师大副刊》上的《评韩》,是张先生的第一篇中国哲学方面的文章,但已佚,无法评说。就我见到的史料来说,张先生公开发表的中国哲学方面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列子》,于1928年3月分四次发表在北平《晨报》副刊。此文考证列子其人其书,其考证以文献史料为据,决不凭空推断,且力戒孤证,所据以论辩的文献史料相当全面,几乎囊括古今学人论列子其人其书的重要文献史料。在不能利用电脑从网上或电子著作上查阅资料的90多年前,时年才19 岁的张先生能发表这样性质的学术论文,不仅说明他开始从事中国哲学研究时就注重以史料立证,而且信服乾嘉朴学之学术理念,信守“孤证不足凭”这一学术考证之方法论原则。
《关于列子》发表后三年,张先生又于1931年6、7月间在《大公报》上分三期发表了《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即便不细看此文,仅从“假定”这个词也不难认定此文亦属于考证性质的论文。与《关于列子》比较,此文对老子其人其书的考证,虽同样注重以史料立证,同样恪守“孤证不足凭”的方法论原则,但在考证的范式上较《关于列子》有新的突破,或者说确立了有别于乾嘉考据范式之新考证范式。问题是,它是什么范式?用张先生自己的用语说,它可以简称为“四个字”范式:“我觉得考证至少须符四个字,即‘周’‘衡’‘严’‘微’。各方面都要注意到,都平等地看待。不肯偏倚,更须替反方想理由。方法、步骤要严格,不要轻易得结论。不要滥找证据。小的地方,一毫的差异,都不要轻易忽过。假若你的证据全备,各个证据自会‘挤’出一个结论,正卡在那儿,上也不得,下也不得,只是在那儿才行。事实是不犹豫的。”[4]60尤其要重视的是,张先生提出这“四个字”范式,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发,而是针对当时学术论辩之弊端所发:“我觉得这个问题①指老子年代问题。讨论了六七年还不得解决,主要是因为辩论的各方考察的方法与态度,都不十分适当。他们不了解史事的性质,不知史事的错综复杂,他们总想求个直线的说统。他们常满足于单方面的证据,不知道综观各方的证据,更再也不会替反方面设想。对于每一证据之本身,又不分析鉴别其作证资格、作证力量。所以在旁观的人看来,觉得他们是在争胜,不是在共同求真实。”[4]59
作为“四个字”范式的首次实践,《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一文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先不要……先要”这一具体的操作范式:“先不要考老子这个人的时代,先要考《老子》这本书所表现的思想在什么时代才会产生;先不要考《老子》思想之年代,先要考《老子》这本书的性质。在考察前,我们要清清楚楚地把老子、《老子》书、《老子》思想,个个分开。我们毫不可假定这三项之间有任何关系,然后才能做客观的靠实的考较。”[4]60尽管张先生自己宣称,该文所运用的考证“方法仍嫌太不严密。距离科学的考证,还有两万八千里”[4]60。但笔者认为,这个操作范式即便在现今仍具有普遍的工具理性意义,给予我们这样的启迪:客观科学的考证,要避免主观意见的干扰,恪守“先不要……先要”操作范式,就十分必要。因为这个操作范式,以“先不要”力戒主观意见对客观考证的干扰,而以“先要”来保证客观考证的正确路径。
1932年9月发表于《大公报》第8 版《世界思潮》第2、3期上的《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之上》一文,是张先生公开发表之中国哲学论文的第三篇,它标示着张先生的早期中国哲学研究由重具体人物与著作的考证转向了重整体思想的分析。作为张先生第一篇分析中国辩证法整体思想的论文,该文的范式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了老子、《易传》《墨经》、庄子、荀子、《吕氏春秋》这一先秦辩证法思想衍变次序,更在于它以中西哲学比较的视角对中国古代辩证法做出了整体把握:
严格地讲来,说中国哲学里有辩证法,并不恰当,似乎只宜说中国哲学中有与辩证法类似的东西。不过,假若我们能说中国有philosophy,而不必说中国有与philosophy 类似的东西,那么,说中国有Dialectic,似亦未尝不可。中国的辩证法,与西洋的比起来,有显著的不同,然而在最主要的几点上,却是一致的,所以也可以接受“辩证法”这个名字。不过讲中国的辩证法,实切忌随便引用西洋辩证法的种种来附会。其与西洋辩证法的同与异,是须同等地重视的。
中国辩证法的元祖可以说是老子。在老子之后,发挥辩证法观念最丰富详密的,是《易传》。《易传》前后的别的哲籍如《墨经》《庄子》《荀子》《吕氏春秋》,也都有片段的类似辩证法的话。到汉代后,《淮南子》、董仲舒、扬雄,都有关于辩证现象的议论;魏之王弼,更比较有新的观察。宋代哲学家中,似乎只有张载、二程,注意到辩证法现象,而张载尤有贡献。元明以后,似乎不见什么发展了;清初的王夫之,曾偶然发表过些新的意见。[4]79
这一把握,由于史料的限制①未能阅读方以智的《东西均》《易余》以及未能阅全王夫之的哲学著作。,固然有不足②未提及方以智对中国辩证法的杰出贡献以及对王夫之贡献之评价高度不够。,但它对我们全面把握中国古代辩证法之范式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上文发表后三个月内,张先生发表的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有四,依次为:《评李季的〈我的生平〉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之下》《评冯著〈中国哲学史〉》《胡适的新著:〈淮南王书〉》。这四篇中,“辩证法下”一文勿用说系上面提及的“辩证法上”一文的续篇,它值得重视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对秦先后的辩证法理论贡献予以总体评价,强调秦以后辩证法较之秦以前辩证法“实在也有不少的进步”,但并“没有了不得的大进步”“在大体上则可说没有远离先秦的限际”[4]113,然而这一见解,显然是可以商榷的;二是他接受了谢无量、胡适用语,以“上古”与“中古”称谓中国辩证法的两大发展时代,但同时强调这“并不是可以拿某一年划作一个迥然相判的界限的,其间实有个过渡时代”[4]113。而这个过渡时代,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到董仲舒学说成立、盛行止。张先生明确交代,以董仲舒为中古哲学开端,“系从冯友兰先生说”[4]113。另外三篇,都是书评,从中可以看出张先生对享誉当时之冯(友兰)著、胡(适)著的评价。对李季评胡著的观点,张先生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以为它“在其‘反胡适’上,固无大的意义,但里面却有积极的贡献”[4]96;张先生强调:胡著的贡献,在当时虽“已是过去的”,但一味地批胡适,否认胡著的功劳,也不可取,因为“胡适确有过大贡献”,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已是固定的了”[4]96。对胡适的《淮南王书》,张先生评价极佳,说它“是一本道家哲学的最好的引导书”[4]146,但对胡适所谓“道家出于齐学”“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4]147说不认同,予以商榷。他更批评胡适的研究方法,明确指出:“胡适好用西洋的学说来比附、来解说中国的思想,有时便令人‘醒’,有时便‘不切”[4]147。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张先生的评价更好,说它“是现在比较最好的一部中国哲学史”[4]132,具有当时其他中国哲学史所不及的四大长处,即史料鉴别“谨严”、探幽寻微“深观”、叙述“条理系统”、评论“不偏”。尽管给予这么高的正面评价,但张先生也不讳言自己对冯著不足的看法,指出它有“两项重要的缺点,即第一对于当时学术的大势及学派源流交互影响,似乎缺少点充分的论述;第二,似乎缺少一个‘哲学史论’”[4]133。张先生这是在强调着中国哲学史,先要有个“哲学史论”,即“哲学史的哲学”①张先生语。以为方法论原则。今天我们讲着什么样的哲学史当先树立什么样的“哲学史观”已是常识,不足为奇,但在83年前,张先生提出写中国哲学史要贯彻“哲学史论”的主张,弥足珍贵。这就难怪连张先生自己对这一主张也信心不足,非要特意申明:“‘哲学史论’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未知当否。”[4]134
张先生于1933年发表的首篇中国哲学论文是《斯辟诺萨与庄子》。此文发表在《大公报》1月19日第8 版《世界思潮》第21期;后一个多月,又在该报之《世界思潮》第26期发表《颜李之学——李恕谷逝世二百年纪念》以及《“万物一体”》;再后一个多月,于《世界思潮》第31期发表《谭“理”》。此后于《世界思潮》再发二文:《中国哲学中之非本体派》(8月10日,第50期)、《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本根”概念之解析》(8月31日,第53期)。综合言之,这六篇论文较之以前的论文,显著的不同在于:它已将中西哲学比较方法运用于中西哲学家之个案分析;它不再局限于中国哲学具体内容与问题,而是触及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与一般特性。
1933年在张岱年先生早期中国哲学研究历程里可以说是一个划阶段的年份。此前的八年,是他早年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阶段,此后(1934-1943年)的十年,是该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内,张先生撰成或发表的论著,仅五种:《中国思想源流》(1934年1月)、《中国知论大要》(1934年4月)、《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与读法》(1935年4月)、《老子补笺》(1936年12月)、《中国哲学大纲》(1935年开始写、1937年2月完稿,1943年印作大学讲义),数量上并不多,但同以前论著比较的话,不难看出在这十三年内张先生对中国哲学研究更倾向于全面、系统、整体的综合归纳分析,而其中之杰出成果,就是《中国哲学大纲》(又称《中国哲学问题史》)。张先生在1937年的“自序”中就该著撰述动机与特点指出:“近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颇盛,且已有卓然的成绩。但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的书,似乎还没有。此书撰作之最初动机,即在弥补这项缺憾。此书内容,主要是将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选出,而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亦可以看作一本中国哲学问题史”[5]1。这可以具体理解为张著是为弥补胡著、冯著缺陷而著,其特点在于以中国哲学问题提出的历史顺序来叙述中国哲学发展的条理系统。
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除“序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宇宙论,下含三层,先为“引端:中国宇宙论之发生”,次为“第一篇:本根论”,后为“第二篇:大化论”。第一篇:本根论下设八章,一曰“中国本根论之基本倾向”,二曰“道论”,三曰“太极阴阳论(附五行说)”,四曰“气论一”,五曰“理气论”,六曰“唯心论”,七曰“气论二”,八曰“多元论”,此后另有“本根论综论”;第二篇:大化论下设六章,一曰“变易与常则”,二曰“反复”,三曰“两一”,四曰“大化性质”,五曰“始终、有无”,六曰“坚白、同异(附录:形神问题简述)”,此后另有“大化论综论”。
第二部分:人生论,下含四层,先为“引端:人生论在中国哲学中之位置”,次为第一篇:天人关系论,再次为第二篇:人性论,又次为第三篇:人生理想论,后为第四篇:人生问题论。第一篇:天人关系论下设二章,一曰“人在宇宙中之位置”,二曰“天人关系论”(补录:天人有分与天人相胜),此后另有“天人关系综论”;第二篇:人性论,下设五章,一曰“性善与性恶”,二曰“性无善恶与性超善恶”,三曰“性有善有恶与性三品”,四曰“性两元论与性一元论”,五曰“心之诸说”,此后另有“人性论综论”;第三篇:人生理想论,除列首之“简引:人道与人生理想”外,下设八章,一曰“仁”,二曰“兼爱”,三曰“无为”,四曰“有为”,五曰“诚及与天为一”,六曰“与理为一”,七曰“明心”,八曰“践形”,此后另有“人生理想论综论”;第四篇:人生问题论除列首之“简引:人生问题”外,下设九章,一曰“义与利”,二曰“命与非命”,三曰“兼与独”,四曰“自然与人为”,五曰“损与益”,六曰“动与静”,七曰“欲与理”,八曰“情与无情”,九曰“人生与不朽”(补录:志功问题简述),此后另有“人生问题论综论”。
第三部分:致知论,下含三层,先为“引端:中国哲学中之致知论”,次为“第一篇:知论”,后为“第二篇:方法论”。第一篇:知论,下设三章,一曰“知之性质与来源”,二曰“知之可能与限度”,三曰“真知”,此后另有“知论综论”;第二篇:方法论,下设二章,一曰“一般方法论”,二曰“名与辩”,此后另有“方法论综论”。
第三部分之后为全书之“结论: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结论”之后,又有“补遗”。
《中国哲学大纲》印作讲义后十四年,是张先生早期中国哲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他发表的中国哲学方面论文只有14篇:《孔学评议》(1946年5月)、《评〈十批判书〉》(1947年4月)、《墨子的阶级立场与中心思想》(1954年3月)、《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1954年10月)、《张横渠的哲学》(1955年)、《关于张横渠的唯物论与伦理政治哲学》(1955年)、《11世纪卓越的唯物主义者张横渠的哲学思想》(1956年6月)、《关于张横渠的唯物论思想——对〈张横渠是一个唯心论者〉一文的答复》(1956年)、《〈老子〉中唯物主义思想》(1957年)、《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1957年)、《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1957年)、《中国古典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1957年)、《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1957年)、《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1957年)。从这十四篇论文看,张先生在早期中国哲学研究的最后阶段,除了侧重研究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思想,尤其是张载的唯物论思想外,就总体上讲,并未创造出超越前两个阶段的更杰出的成果。
三
从张岱年先生1937年撰成《中国哲学大纲》迄今已八十二度春秋,按中国人通常以三十年为一代计,该著流传已接近三代。有一种观点以为,传统是指一种精神之不断裂的持续,如果一种精神持续三代不断裂,就成为传统。那么,就发扬传统来讲,我们今天究竟能从张岱年先生早期中国哲学研究中得到哪些范式意义的启迪?下面,就这个问题谈三点不成熟的看法,请大家指正。
首先,中国哲学研究要不要形成一脉相承的范式传统?从前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张先生早期的中国哲学研究,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张著是弥补胡著、冯著缺陷的产物,在中国早期的六部“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地位尤其重要。谢(无量)、胡(适)、钟(泰)、冯(友兰)、范(寿康)、张(岱年)六人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可否认客观上构成了内在联系,即互相解构的联系。解构意味着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则用“正反正(合)”辩证眼光看,那六部“中国哲学史”著作不妨分为三组,其中谢著、胡著为第一组,代表“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之实践的“正”过程;钟著、冯著为第二组,代表“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之实践的“反”过程;范著、张著为第三组,代表“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之实践的“正(合)”过程。就“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之实践的“正反正(合)”过程而论,六部书中以胡著、冯著、张著三书尤为重要;而胡著、冯著、张著三书中,就探讨“金岳霖之问”——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的启迪意义而言,当以张著更为重要。
张著对创建“中国的哲学”的重要启迪,在下面论述,这里先谈一个问题:张著既然是上述“合”过程的产物,意味着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实践的终结,那么照理说,后张著时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如果要创建“中国的哲学”,当承袭张著之书写①笔者从研究与著述一体意义上使用此名词。范式。张著的书写范式,用张先生自己的用语来表达,不妨称为“问题”范式,则承袭张著书写范式,具体讲就是以“问题”范式书写中国哲学。可是从民国后期一直到现今,虽先后产生了许多中国哲学书写范式,诸如“‘唯物、唯心’两条路线”范式、“‘儒家、法家’两个阵营”范式、“圆圈”范式、“‘范畴’衍演”范式、“究极本体论”范式、“基源问题”范式等,但没有哪一个范式是对张著书写范式(问题范式)的承袭和推进。这表明什么问题?它表明:已有百年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创建实践,呈多种书写范式并存、多种路径并进的局面,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书写范式,因而未能形成统一的精神传统。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之所以经历了百年发展历程,却只形成表面形式上联系,而内在精神上是断裂的,未能形成始终一贯的精神命脉,究其原因,当归咎于在张著后未能承袭与推进张著之“问题”书写范式。
有的学者质疑笔者的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确立一元的书写范式,势必导致中国哲学之书写的教条与僵化,而多元书写范式的并存,定会造成中国哲学之书写的生动与丰富。笔者正视这一质疑,但至今也未能想通放弃这一观点的道理。在笔者看来,主张以统一的书写范式书写中国哲学史,未必会损害中国哲学的丰富性,但若不以统一的书写范式书写中国哲学史,却一定会损害中国哲学精神承续上的一贯性。因为: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如始终不能按照一个共同书写范式“接着讲”,却每个时期的每个人各依各的范式、各按各的想法来讲,难以形成大家共同认同的中国哲学当有的书写传统也就不言而喻,不足为怪。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是否有必要继续维护这种各讲各的局面而拒绝各家都遵循一个共同的范式而“接着讲”。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只有各家都遵循一个共同的范式而“接着讲”,才能真正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否则,中国哲学的叙述,终究不能避免简单形式下的内容重复(例如按年代的先后依次叙述每一个思想家的哲学之各个层面)。那么,如何去构建这样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中国哲学的书写范式?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里只能就这个问题谈点肤浅看法。笔者认为要建立一个贴合中国哲学实际的中国哲学书写范式以便各家遵循,当兼取张(岱年)劳(思光)方(东美)萧(萧萐父、李锦全合著《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四家著述之长,即先从方东美,以“究极本体论”把握中国哲学性质;然后从劳思光,依“基源问题研究法”分析确立中国哲学的“基源问题”;再后从张岱年,以中国哲学“问题”所固有范畴反映与梳理中国哲学“基源问题”的内涵、形式与联系;最后从萧萐父、李锦全,以“圆圈”的方式揭示中国哲学思想范畴展开与推衍的逻辑。这是一个综合各家长处的范式。至于如何称谓之,待定。
其次,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要不要放弃考据功夫?张先生早期中国哲学研究成果,考证论文,如《关于列子》《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勿用说,即便是思想分析论文与专著,如《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本根”概念之解析》《中国知论大要》《中国哲学大纲》,也都大体采用第一手史料,且史料极其丰富,体现了张先生深厚的乾嘉朴学的考据功夫。张先生的考据功夫,给他创造了杰出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让我们现今研究张先生学说时不由得思考一个问题,即在当代研究中国哲学是否也要学张先生的考据功夫。当代是信息时代,研究中国哲学的大量第一手史料,通过网上搜索与电子书籍检索,都能轻易搜集到,因此像张先生当年所用的凭两眼与两手搜集史料的“死功夫”,在现今似乎失去了效用。但仔细思考的话,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现今固然不必全盘仿效张先生那般的“死功夫”,但就现今研究中国哲学仍需要遵循张先生在八十多年前所提倡的“四个字——‘周’‘衡’‘严’‘微’”范式来讲,考据功夫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效用价值,永远都不会过时。我们今天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不应是考据功夫是否过时这一问题,而是在信息时代如何不放弃考据功夫。较之乾嘉考据,我们在现今运用考据功夫,不妨叫作“新考据”。“新考据”如何发扬旧考据精神,坚守旧考据功夫,对这个问题笔者曾实有实验,那次实验所感,写入了《由读张岱年先生的信所引起的考证》一文。笔者将该文附于本文末尾,以说明笔者所谓“新考据”是如何具体操作的。
最后,张著(《中国哲学大纲》)有什么具体范式启示?张先生早期中国哲学研究的成就,无疑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大纲》,所以张先生早期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意义这个问题,也可以换言为张著《中国哲学大纲》对当代研究中国哲学有什么启迪意义。对这个问题,无疑见仁见智,而在笔者看来,其启迪有三:
其一,张著的重要性不在于内容的丰富超越他著(例如冯著在内容上远比张著丰富),也不在于方法上之创新比他著独特,而在于它的“问题意识”独到:以中国哲学的“问题”规整中国哲学的内容;以中国哲学固有的范畴贯串中国哲学的内容;以中国哲学的范畴之衍演与扩展反映中国哲学的发展。这样的问题意识,应该是对它之前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之实践自觉反思的产物,它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要避免书写成“哲学在中国”,真正书写成“中国的哲学”,就应该像张著那样以中国哲学的“问题”规整中国哲学的内容;以中国哲学固有的范畴贯串中国哲学的内容;以中国哲学的范畴之衍演与扩展反映中国哲学的发展。
其二,就内容而论,张著与其他五著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其他五著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经学与哲学、学术思想与哲学思想混而不分的现象,而张著则比较“纯哲学”,彻底舍弃了属于经学及学术思想、政治思想的许多内容。问题是,正如张先生自己所指出的,正因为坚持求“纯哲学”,使得张著不免在“取材和论述范围”方面存在明显的缺欠。张著所遭遇的这一矛盾,是否意味着创建“中国的哲学”就一定要遭遇两难问题:求中国哲学之纯粹性势必牺牲中国哲学之丰富性,反之亦然。
其三,如果说胡著、冯著对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的运用是自觉主动的,那么比较地说张著对西方哲学方法的运用却是非主动不得已的。所以不得已运用西方哲学方法,照张先生自己的解释,是因为谈中国哲学却“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5]1。“不得不然”云云,显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张先生主观上并不想以西方哲学方法来把握中国哲学,但客观上他把握中国哲学又只能以西方哲学为“表准”。换言之,张先生固然可以做到以中国哲学的固有问题、中国哲学固有范畴展开逻辑来叙述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但他在界定中国哲学问题的性质(例如属于宇宙论还是认识论)、把握中国哲学范畴的蕴涵、评价中国哲学思想的价值上,根本就做不到不以西方哲学为“表准”。张先生所难以化解的这一主客观矛盾,让我们警惕的应该是:将创立“中国的哲学”建立在彻底排除西方哲学方法之运用的前提下的任何构想与实践,对于成功创立“中国的哲学”来说,可能都是徒劳的。
附录:
由读张岱年先生的信所引起的考证
在《忆张岱年先生对我的教诲》博客文中,我说张先生生前至少给我写过五六封信,我只找到了四封,另几封不知是弄丢了还是收在什么文件袋里一时没找到。今晨三点半,失眠,便起床找写方以智论文的材料(都是我手抄的),却无意在一个大信封里发现了张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心中一阵高兴。读完了信,我就有了考证的兴趣,于是检索和查找材料,得出了初步看法,也就有了写这篇博客文的可能。
要考证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个考证又是由读张岱年先生的信所引起?看了张先生的信,这个问题就会不言而喻。这里如实转录张先生的信如下:
国保同志:
您好!来信收到,
“孔子不假盖于子夏”的出处,我亦不记得,可再查《礼记·檀弓》《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孔子集语》等书。但查起来很麻烦,不注明出处也可。
致堂系宋代学者胡寅的号,他著有《读史管见》,可查《宋史》列传及《宋元学案》。
匆匆,祝
近好
张岱年
97、3、13
从邮戳看,此信是第二天(3月14日)从海淀路邮局发出。从信中不难明白,张先生给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我写信向他请教两个问题:“孔子不假盖于子夏”一语的出处以及“致堂”是代指谁。我当时为什么为这两个问题打扰先生,现在仔细回忆,当是因为在注释申涵光《荆园小语》时遇到这两个问题而自己实在无能力解决。我之注释《荆园小语》,是应安徽人民出版社所约,但这个注释后来不但没有出版,而且交给出版社的稿子后来也被他们弄丢了,底稿在几次搬家后,也找不到了(今晨在发现张先生那封信之后,我又发现了一个草稿,翻翻,竟是为注释《荆园小语》而写,想是该书稿之前言),所以我是否根据张先生的指示,在那时就查出了“孔子不假盖于子夏”一语的出处,现在已记不清。但从我读这封信时对“孔子不假盖于子夏”一语毫无印象来推断,我当时很可能没有查出此语出处,只得以不注释完事。这倒激起我考据的好奇心:当年博学的张先生凭记忆没能解决的问题,今天靠现代的检索技术,能否解决?我于是通过《四库全书》电子版来检索此语。
我先以“孔子不假盖于子夏”一语来检索,结果只出现了一条,见于金·王若虚《滹南集》卷十一《史记辨惑·取舍不当辨》:
《史记》老子列传训诲孔子如门弟子,而孔子叹其犹龙者,盖出于庄周寓言,是何足信而遂以为实录乎?至于成王剪桐以封唐叔,周公吐握以待士,孔子不假盖于子夏,曾子以蒸梨而出妻,皆委巷之谈,战国诸子之所记,非圣贤之事而一切信之。子由为《古史》,迁之妄谬去之殆尽,而犹有此等,盖可恨也。
王氏在此明确指出诸如“孔子不假盖于子夏”语者皆出于“战国诸子之所记”。那么它(孔子不假盖于子夏)见于哪个子学著作呢?我又以“盖于子夏”来检索,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出现了十四条,除了上面的那一条之外,还有十三条,其中多如《晋书》列传卷四九《嵇康传》所载,为“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另苏辙《古史》卷三十二作“孔子行遇雨,弟子欲假盖于子夏氏”(王若虚因此批评苏辙)。但这些记载仍无法解决此语(孔子不假盖于子夏)是否出自战国诸子之口。不过,《太平御览》卷十的记载,“《孔子家语》曰:将行遇雨,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却明确指出此语出自《孔子家语》。问题是,上述两种检索,都没有显示《孔子家语》中记载有此语。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难道《太平御览》中的记载有误?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只能用死办法,从纸质的《孔子家语》中查找(我用的是《百子全书》本),结果在《致思》篇查到这样的记载:
孔子将行,雨而无盖(国保按:雨具),门人曰:“商(国保按:子夏姓卜名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甚吝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
一查到《孔子家语》中的这段记载,我立马明白:虽然“孔子不假盖于子夏”或者“仲尼不假盖于子夏”一语不见于《孔子家语》,但该语无疑是后人根据《孔子家语》那段论述概括出来的。今本《孔子家语》不是战国的作品,那么它的那段记载是否亦有所本呢?为此我又以“甚吝于财”检索,希望能找到战国作品中的记载。结果检索到十条,除了《孔子家语》那条记载,其余九条记载,全是照抄《孔子家语》。至此,可以断定:“孔子不假盖于子夏”或者“仲尼不假盖于子夏”,就发生学而言,源自《孔子家语》。
今本《孔子家语》,非《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孔子家语》,而是王肃伪造。王肃伪造这一说法是否亦有所本,现在已难考。我们现在只能考定:先是王肃(195-256年)在《孔子家语》中编造了那样的说法,后在房玄龄等编撰的《晋书》之《嵇康(223-262年)传》中被概括为“仲尼不假盖于子夏”,再后在南宋时期又转为“孔子不假盖于子夏”。
以上考证,因一时兴起而为,待考证结束后,我却意犹未尽,不禁想在此谈谈考证以外的体悟。它有三点:一是古今学术之别。过去靠勤读书、靠记忆强造成的学案性的、材料归类性的学问,因现代的电子技术,已变得毫无学术价值,那么今天做学问,还需不需要勤读勤记勤写?需要还是不需要,这确实已成为一个问题?二是过去凭记忆难以考据的问题,我们今天凭电子技术,一般都能考据清楚,那么以资料详实为长的考据学,就学风讲,在今天还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或者说我们今天做考据的学问,除了有解决具体疑问这一意义外,还有什么普遍性的学术价值?三是为了培养扎实的学术工夫,我们可不可以拒斥检索之类的电子技术?我不赞成为了显示自己的为学工夫就彻底拒斥检索之类的电子技术。但如何一方面利用检索之类的电子技术,另
一方面又不至于因此变得懒惰、彻底地放弃传统的“抄书”工夫,也的确成为今天做传统学术研究之学者认真思考的问题。不敢说对这些问题都有清晰的认识,只是提醒自己:在这个一切变得十分功利、十分便利的时代,不以学术为功利之利器,亦不以学术为乡愿之儿戏,有多大的能力做多大的学问,有多大的学问说多大的话,既不自卑学不如人,也不自傲学超众人。我学如我人,功过后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