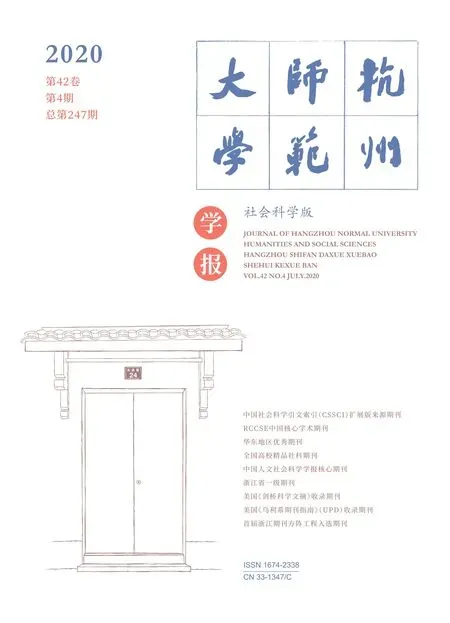叶公超的比较文学思想研究
凌淑珍
(1.清华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4 ;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外语系,陕西 咸阳 712100)
近年来,国内对叶公超的研究逐渐呈现递增态势,这些研究集中在他的教学思想、诗学和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等方面。然而少有的几篇介绍叶公超比较文学思想的论文尚未秉承叶公超对文本的细读宗旨,缺乏从作品出发去深度探究叶公超的比较文学思想。叶公超秉承以作品为中心的理念与他所接受的人文教育以及剑桥学术传统密不可分。1924-1926年叶公超求学于剑桥大学,并获得文艺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在剑桥期间,他深受当时学术多产的李维斯、瑞恰慈、燕卜逊、艾略特的影响,反对印象式批评,排斥空洞的概念和理论,主张作品的细读和批评的准确性等。受叶公超细读作品的启发,本文采用历史分期的思路,尝试细察叶公超的作品,分析他的比较文学思想。
一、比较文学意识的觉醒
自成立起,清华大学外文系就一直具有浓厚的比较文学氛围。1925年9月,清华大学增办大学部。1926年,西洋文学系成立,王文显任系主任,设有英文门、德文门和法文门。1926年吴宓代系主任,仿照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拟定了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办系方针和课程计划。在《外国语文学系学程一览》开篇的课程总则中,吴宓提出了清华外文系5个培养目标: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将能 (甲) 成为博雅之士; (乙) 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 (丙) 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 (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 (戊) 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1](P.315)。这个培养目标下的课程设置展现了“博雅”与“专精”两个原则。课程设置要求本系学生第一年起就研修法、德第二外国语,故本系学生法、德两种第二外国语必须研修4年(1935年开始规定第二年研修第二外国语)。另外,大一课程以中西文史为核心,兼顾数理化生,同时强调国文的学习,使学生熟悉西洋文学和中国文学,从而汇通中西。就此而言,清华大学外文系的课程设置可谓中西合璧、文理兼修、专精结合。这种办学理念和实践成为清华大学“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学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华大学这种博雅的学术传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比较意识,形成对中西语言文学的整体认识,从而最终促成中国比较文学在清华大学最早萌芽。在第一代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人中,出身于华侨家庭的王文显基于他的多种语言文化背景,用英语编写戏剧,向西方传播正面的中国形象和中国风情,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做出了贡献。王文显师从耶鲁大学戏剧大师乔治·皮亚斯·贝克(George Pierce Baker)教授。1927年,他用英语创作了《北京政变》。该剧在美国成功上演,获得贝克教授的盛赞:“自从西方接触中国以来,外人曾经努力表达各方面的中国生活,传教士、官员、游历者和小说家,在文学上和舞台上,出奇制胜,刻画中国,因为并不公正,结局大多数人对于中国人形成一种定型的看法:刺激、邪恶、古怪,但《北京政变》努力表现中国人民的生动的风俗人情,可能尽一份力克服西方人士的误解。”[2](P.172)1929年,王文显的英文三幕剧《委曲求全》(SheStoopstoCompromise)在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再次成功上演。除了文学创作,王文显给学生讲授莫里哀的《吝啬鬼》、易卜生的《傀儡家庭》等现代戏剧。与王文显不同,在哈佛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硕士的吴宓掌握多种语言,教授《柏拉图》《文学与人生》等古典文学课程和《中西诗之比较》《世界文学史》等比较文学以及中西方哲学比较课程。他反对某一国别研究,主张打通外语专业和中文学科界限,用比较方法审视中西方文化。他不仅比较了中西方有关音乐的诗歌,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的相似性,而且他采用比较的方法得出结论:《红楼梦》胜过任何一部西方小说。
清华大学外文系的比较研究氛围离不开清华大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经验。众所周知,清华大学的人文学科一直以比较传统和跨学科研究著称。陈寅恪和冯友兰等人在历史和哲学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比较研究。陈寅恪和吴宓虽然治学方向相异,但关系甚好。陈寅恪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发表在吴宓创办的 《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继而又刊登在吴宓主办的《学衡》杂志上。和老师吴宓一样,浦江清虽然大学期间主攻西方文学,但是由于毕业后他做了陈寅恪助手,也一样受到陈寅恪影响,极重中国旧学。此外,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在增加古典文学课程的同时,并没有减少比较文学课程。[3](P.193)
叶公超受益于清华大学人文学科的比较传统,比较成功地从前期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浅薄认知转变为一位比较文学学者。叶公超吸纳王文显和吴宓等清华大学外文系老一辈学者的比较意识,发挥他在欧美现代文学的优势,推动中国文学的新旧传承、中西方文学互鉴,有效解决新时期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比较文学的“清华学派”。叶公超9岁起就留学美国,除了中途短期回国之外,他先后在英美国家的中学、大学接受了10年西学教育。这样的学习经历不免使他和中国传统产生隔阂。1926年他从剑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在东南大学任教时,校长郑洪年曾称他为“外国名士派”。此话不虚。1929年,叶公超正式任职清华。据梁实秋回忆:“本来他(叶公超)不擅中文,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够深。闻一多先生常戏谑的呼他为‘二毛子’,意思是指他的精通洋文不懂国故。”[4](P.11)显然,叶公超受了刺激,开始恶补中国文学,通过一段时间的研习,不久他就成了“十足的中国文人”。同时,叶公超开始对比较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929年夏至1934年夏,他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开设一、二、三年级的英文课、英国散文、现代英美诗、18世纪文学、文学批评和翻译等课程之外,还开设中国新诗中的西洋背景等比较文学课程。
1929年任职清华大学之后,叶公超开始和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具有比较意识的学者朝夕相处,深受清华大学自由开放和充满人文主义的学术氛围的熏染。1931年自徐志摩逝世后,叶公超承担了《新月》最后6期的编辑工作,1934年又与闻一多等合作创办《学文》,推介清华大学师生的作品,刊登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钱钟书的《论不隔》(《谈艺录》的先声)等。他与《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沈从文、《文学杂志》主编朱光潜过从甚密,积极参加朱光潜等组织的读诗会。在清华大学,吴宓是公认的“中国比较文学之父”。自1926年回国,叶公超就与他相识。叶公超和吴宓在清华大学是同事,叶公超受到吴宓的比较文学意识的影响自不待言。据梁实秋记载:“(叶公超)住藤荷西馆,与吴雨僧(吴宓)为比邻。一浪漫,一古典,而颇为相得。”[4](P.11)据吴宓日记记载,叶公超和吴宓两人共同承担一些课程,而且经常串门,吴宓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在叶公超家搭伙吃饭。1929年之后,叶公超投入到比较文学研究上,同时倡导将外国文学人才的培养定位在为中国语言和文学服务。根据叶公超的学生常风回忆,有一次叶公超教导他说,咱们学外语的人总须另找个安身立命之处。只教外文,讲外国文学,不过是做介绍,传播外国文化的工作。这固然重要,可是应该利用从外国学来的知识在中国语言和文学方面多钻研。[5](P.58)这可以视为叶公超比较文学思想的自觉表现。
二、从比附西学到中西比较
任教清华大学之前,叶公超着力欧美文学评论,先后发表以下文章:1926年6月在《晨报副镌·戏刊》上发表《辛额》(JohnM.Singe)、1928年3月在《新月》上发表《写实小说的命运》、1928年9月在《新月》上发表《牛津字典的贡献》。在《写实小说的命运》中,他将福楼拜等法国小说和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等英美现代小说进行比较,从而辨识出这些现代小说呈现的冷静的客观主义和对全人类的普遍同情的特征。在这段时间,他局限于英、美、法等欧美文学之间的比较,这和常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讲授“比较文学”的温德教授类似。在《牛津字典的贡献》一文中,叶公超详细介绍了《牛津字典》的编撰过程和特点,同时指出《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辞源》等中国辞典在体制和细节等方面都远不及《牛津字典》。同样,《辛额》这篇评论再次展现了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浅薄以及对西方文学的盛赞。他详尽介绍了辛额这位爱尔兰作家的作品和性情,但在文章末尾,他只是用寥寥数语呼吁中国作家需要多“注意于方言和村民的各种信仰与传说,用同情的态度和他们一同度生活,方可以得着民族的自然精神”[6](P.110)。虽然此时,胡适已经在北京大学等地展开收集民谣等工作,但是叶公超对中国当时如火如荼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却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像胡适、朱自清等学人那样借鉴西方诗歌来发展中国文学。由于缺乏国学背景和比较文学意识,仅仅有西学背景的叶公超无力化解中西文学、新旧文学沟通互鉴的难题,而只能参照、比附西学。
1929年之后,叶公超的文学批评展现了他开始摒弃此前所怀有的比附西学心态。在《文学的雅俗观》一文中,他大量引证了古人品藻诗文的标准:姚惜抱与陈硕士、归震川与沈敬夫的书信,《论语》《周礼》《孟子》中的诸多论述以及刘海峰的《论文偶记》等。他指出这些文学体现了恰当的雅俗观。他揭示出诸多西方著名批评家所使用的文学批评名词并非我们想象的具体和切实。在文尾,他强调王尔德、萧伯纳和韦尔士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俗”在于“过分表露情感”。在1933年3月发表于《新月》第4卷第6期上的《论翻译与文字的改造——答梁实秋》中,叶公超认为翻译的问题不在于直译、曲译和硬译,而在于没有绝对正确的翻译。“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没有任何一种能单独的代表整个人类的思想的。任一种文字比之他种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这是很显明的。从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译到中文都可以使我们感觉中文的贫乏,同时从中文译到任何西洋文字又何尝不使译者感觉到西洋文字之不如中国文字呢?就是西洋文字彼此之间只怕也有同病相怜之感吧!”[6](PP.152-153)在叶公超看来,由于不同的文明发展有差异,所以文字并无优劣之分。
叶公超凭借他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造诣和掌握英法两种语言的优势,不仅醉心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英美新批评的研究,更是将中国文学作品与抽象的西方文学理论结合,将中西方文学比较,从而将西方理论本土化。在《谈读者的反应》中,他举证中国宣纸来解释莫泊桑所持的“不受任何成见的心灵”的观念。“当然,最理想的是我们的心灵(mind)在阅读的时候能像一张旧宣纸一般地灵敏。最好的旧宣纸必是矾棉生熟的成分最相称的,所以才能显出笔墨间种种细微的差别。它不只能吸收墨色,而且能忠实地透出各种运笔的方法(即董其昌所谓劣纸有墨无笔之意),使善书者全分的精力与技能都现身于纸面。” [6](P.39)从跨学科视野出发,在赞扬宣纸和国画的单纯的同时,叶公超采用比较方法,深入浅出地解释了文学作品会受到读者反应的影响,以及读者和作者的情感经验难于同一的现实复杂性。为了揭示源于西方的读者反应理论,他首先列举了读者对柳宗元《江雪》这首五言绝句可能会产生的三种直觉:人道、美观和训世;然后恳请读者纵观柳宗元的年谱和作者的生活情况,以此考证这首诗的整体意义和柳宗元对世态凄凉的感慨。总之,通过把西方理论放置在中国古诗的大语境中去审视,叶公超有效地传达了来自西方的读者反应理论的复杂之处。
叶公超不满足于使用中国文学来印证西方理论。他还从比较出发,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用我国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独特的见解和洞察力来丰富、补充、重估西方文学研究的成果。虽然他对瑞恰慈的理论极为推崇,但是在1934年7月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一文中,他指出:“英国批评家瑞恰慈在他的《科学与诗》里说文学是人对于外界一种情感的满足。这话说得未免太不着边际一点。”[6](P.33)叶公超并不满足于用瑞恰慈的西方观念来分析和解释中国文学。他认为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可以满足读者的情感诉求,而且可以满足他们的理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他的观点。首先,他指出,当我们阅读《水浒传》时,“我们读着只感觉自己深入了另一个世界,而这里的一切恰都合于我们的理智与情感条件” [6](P.34)。对叶公超而言,虽然施耐庵创作《水浒传》是主观的,但又是合乎作家的理智与情感条件的。他认为,一个有判断力和有情感的作家创作的一部分动机是由于他们想充分认识复杂的现实世界。当现实无法满足作家的理智和情感时,他们就会根据所接触的生活,通过创作来创造、翻造一个符合他们的理智与意愿的艺术世界来替代现实。同时,他指出艺术世界的真实性和生命力不仅是由于艺术家主观地创造一个符合他自身的理智与情感的艺术世界,而且艺术还要符合广大读者、一般人的理智与情感世界。他赞誉施耐庵的作品不仅创造了一个符合作家本人的主观世界,而且这些作品符合广大读者的理智和情感。他不仅关注艺术的自足性,而且主张艺术与时代、大众的生活体验、广大读者的情感以及理智密不可分。他辩证地看待艺术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关系。为此,他教导学生在创作时,一定要扩大生活经验,这样读者才能从理智和情感上去理解和感应。在他指导和修改季羡林书写的《年》这篇散文时,他建议作品要超出个人狭隘世界,要有“扩大意识”。要将作家个人观念和情感扩大到一般人的世界。他认为艺术作品影响到广大读者之后,艺术才会有真实性和生命力。
三、叶公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叶公超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文学,使他能够超越胡适和梁实秋等人对中国现代作家做出更为完整和公正的评价。在19世纪30年代吴宓和许多文人交恶之时,1931年吴宓创办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刊登了叶公超的《志摩的兴趣》。他认为徐志摩的诗也许不及他崇拜的雪莱,但是其幽默却远在雪莱之上。在叶公超看来,雪莱时时刻刻不忘是是非非的争斗,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不免缺乏相当的幽默。相反,徐志摩本性的纯真,对一切生活的热爱和毫无怨恨之性情,使他超越平凡、追求远大理想的同时,还能够领略人生的趣味。这种平行研究促使人们超越浪漫主义概念的束缚,从文本出发去深入了解徐志摩。叶公超不仅用比较的方法客观评价了他的好友徐志摩,而且也用比较思维公正评价了和他政治思想相异的鲁迅,他指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6](P.97)梁实秋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虽是叶公超的好友,但对叶公超的上述评价甚为不满。他们都从欧美留学回国,并均从事平行比较实践,他们却对鲁迅的评价殊异。他们对鲁迅评价的差异与他们的比较文学观的不同大体一致。在《文学改良刍议》(1917)、《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26)、《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35)等文章中,胡适呼吁国人承认中国物质文明不及西方的事实,并且虚心接受西方及它背后的精神文明,从而更新中华文明。胡适的《论新诗》(1919)更是多次援引西方例证来佐证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在此意义上,胡适主张采用比较的方法来吸取他者的长处,从而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无独有偶,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用西方文学批评标准的框架,反思中国新文学的浪漫和任性,批评其缺乏建构文学的标准。鲁迅和左翼作家对梁实秋有关文学与抗战以及文学与人性方面的见解曾发表过尖锐的批评。与胡适、梁实秋不同,叶公超用比较方法来研究中国新文学的问题,对于鲁迅的评价却更为公正和客观。他认为一方面,由于鲁迅的易怒性格容易使他摒弃初始的冷静讽刺,而走向谩骂境界,所以他不及斯威夫特显示的理智和冷静;另一方面,受制于18世纪英国礼貌风气的斯威夫特讲究礼貌,压制个性,缺乏鲁迅特有的抒情。“这种‘沉静下去了’的感伤情调是鲁迅的一种特色。斯伟(威)夫特则不但没有这种的表现,而且在《论优良礼貌与修养》里曾表示对于描写自己的悲哀的轻视。”[6](P.100)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叶公超弱化了鲁迅的反抗姿态,对鲁迅作品进行了误判,但是叶公超超越时空的平行研究,以外来资料来填充本土框架,增加了我们对鲁迅的了解。鲁迅与斯威夫特的比较研究展现了叶公超对比较对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认识,避免主观任意和似是而非之嫌。他深谙斯威夫特书写《一个小小的建议》(AModestProposal)时展现的冷静讽刺的原因在于,当时英国模仿法国要求在生活和写作中讲究礼貌。由于他搜集到充分的史料和证据,并且具有高超的推理判断能力和综合贯通的眼界,叶公超将看似没有接触和相互影响的不同时代和国家的人物进行比较,避免了一般平行比较和简单类比的牵强附会、隔靴挠痒之嫌,更使得他对鲁迅为代表的白话散文和徐志摩为代表的中国新诗等中国文学的评价丝毫不逊色于他早期对外国文学的评价。
叶公超利用学到的西方现代文学知识来补充和丰富中国新文学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艾略特和伍尔芙(Virginia Woolf)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受到排斥。《细察》(Scrutiny)杂志的评论家布雷德·布鲁克(M.C.Bradbrook)批评伍尔芙仅仅给予主要的情境一些反思性的、间接的呈现(reflected,indirect presentation)[7](P.344),但是此时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却意外地在中国受到欢迎。叶公超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向国人介绍艾略特等现代主义作家的学者。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叶公超曾得到过艾略特的赏识。作为艾略特的信徒,他不仅写过《艾略特的诗》《再论艾略特的诗》,还指导卞之琳翻译了艾略特重要的论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为赵萝蕤翻译的《荒原》作序。除此之外,他还书写《墙上一点痕迹译者识》介绍伍尔芙,发表《曼殊菲尔的信札》介绍曼斯菲尔德。“叶公超的文学批评,应当引起我们更多思考的, 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如何阐释和研究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与批评,并转换应用于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建构上。”[8](P.191)叶公超等学人在20世纪30年代借鉴欧美现代文学,尤其是艾略特的古今错综意识为中国文学的古今弥合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他借助艾略特的比较方法,推动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北伐运动后,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传统无法和新文学汇通。此时中国的外文系肩负时代使命,思考由中心走向边缘的中国该如何在新的世界文学和世界体系中求生存,他针砭中国新文学沉溺于抒发个人情绪的“西化”之滥觞,唤醒中国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知。
我们可以从新诗和白话散文两个方面来具体考察叶公超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在《论新诗》中,叶公超反对当时兴盛的“新诗是从旧诗的镣铐里解放出来的”之说,也质疑闻一多对严格格律的坚信。他指出“我们新诗的格律一方面要根据我们说话的节奏,一方面要切近我们的情绪的性质。西洋的格律决不是我们的‘传统的拍子’,我们自己的传统诗词又是建筑在另一种文字的节奏上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诗人都负着特别重要的责任:他们要为将来的诗人创设一种格律的传统,不要一味羡慕人家的新花样”[6](P.51)。叶公超主张中国新诗要借鉴中国古代诗歌的格律形式,认为格律是变化的起点和归宿,是组织我们情绪的根据和增加我们内在形式的力量。在新诗的形式方面,他不仅强调格律,而且注重诗歌的节奏和音步。
叶公超借助比较的方法,为中国新诗提出建设性的主张,强调中国古诗里有许多新诗可以借鉴的材料,中国现代诗人要扩大对传统文化的意识,要大胆地阅读古诗,觉悟“他本国的心灵”[6](P.63)。针对当时国人羡慕西方诗歌的流弊,叶公超强调西洋诗的所有技巧都可以在中国诗歌里找到。他察觉到,中国新诗多半受英国19世纪浪漫情绪影响,但是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运用文字的技巧而论,中国诗词至少是不低于任何西洋诗。”[6](P.53)他以杜甫的《月夜》为例,指出中国古诗里最有诗意的特殊隐喻在任何西洋文字和中国白话里都不易有同样的办法。他引用《文心雕龙》来说明中国古诗讲究字音彼此的合作。他揭示出追求音乐性的中国文字和西洋文字之间的差异,在《音节与意义》文中,叶公超认为丁尼生(Tennyson)诗歌中的音乐性太浓厚,破坏了意义的表达,赞扬徐志摩的《火车禽住轨》诗中节奏与火车奔驰呼应的情景,指出卞之琳及其何其芳常用的平淡、从容的节奏和所表达的思想极为和谐。在比较研究中,叶公超建议“诗人的情绪与经验上确应当多多的增加本色或土色的表现。我感觉,新诗人一方面应当设法移种外来的影响,不是采花而是移种,一方面应当多接触中国的东西,多认识中国的事情”[6](P.72)。叶公超辩证地指出,脱胎于西方的中国新诗需要借鉴西方资源的同时,还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优秀传统。
叶公超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还在于他对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白话散文的客观评价上。鲁迅去世后。叶公超发表《谈白话散文》(1939)一文,基于比较中文和西洋文字之间的殊异,他揭示出鲁迅散文的特色。他认为中国文字的力量在语词上,而西洋文字的特殊力量在句子或段落的结构上。他还特意指出鲁迅的文字特色正是在于语词的力量。叶公超和朱光潜属于当时少有的从中西方语言的比较出发去评析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的学者。虽然叶公超未曾提及鲁迅以及中国历来在句法上的造诣,但是“这在‘五四’以后受欧化影响而依赖日趋僵硬单一的语法构造的白话文世界,还是具有纠偏作用的,尤其是可以弥补片面追求句法效果而不知练字的不足”[9](P.50)。
叶公超从艾略特为代表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中吸取一种比较意识,并自觉地运用这种比较观念和外国知识来钻研中国文学,来重新审视唐宋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在《艾略特的诗》和《再论艾略特的诗》中,叶公超发现艾略特将英国17世纪玄理派与法国19世纪象征派进行比较,“就是用两种性质极端相反的东西或印象来对较,使它们相形之下益加明显……这种对较的功用是要产生一种惊奇的反应,打破我们习惯上的知觉,使我们从惊奇而转移到新的觉悟上”[6](P.122)。他探究到艾略特将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进行比较,从而使读者产生异样的联想。受艾略特的比较思想启发,叶公超遂将艾略特的用典技巧和宋代的夺胎换骨之说进行比较,使我们顿悟中国古代高超的智慧所在。在他看来,艾略特主张利用古代现成的典故来补充我们个人才能的不足,形成一种古今错综感和扩大的意识,而唐宋诗词借用古人句律却略去原句的意义,这些真正高明的中国古代诗人借用他人的东西“熔化于一种单独的感觉中”,创造一种与脱胎的原物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为赵萝蕤翻译的《荒原》作序中,他指出“艾略特可以说是主张文以载道者,他的‘道’就是他在《奇异神明的追求》里所提出的tradition和orthodoxy的两种观念。假使他是中国人的话,我想他必定是个正统的儒家思想者”[10](P.225)。叶公超将艾略特放置于中国文化语境中进行阐释,帮助读者形成对中国文化的觉悟。他主张中国新文学必须更多地借鉴中国古典语言、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才能使其有所发展和突破。他将民族文学的特色、特性的保留作为比较的基础。在他看来,有了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学这个媒介,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才能深入持久。概而言之,比较文学既彰显民族文学特色又存在跨界联络。
四、结语:比较文学走向人类共同命运
叶公超的比较文学思维聚焦于他对整个人类共同命运的体察。在叶公超看来,艾略特的价值和重要性不仅在于他的古今错综意识,而且在于艾略特对人类共同命运和整个人类文明前途的思量。在1934年发表的《艾略特的诗》一文中,叶公超批评马克格里非片面推崇艾略特的天主教信仰,抹杀了艾略特在诗歌技术上的创新,他主张将艾略特诗歌的技术和宗教信仰分而论之。他指出:“总之,艾略特的诗所以令人注意者,不在他的宗教信仰,而在他有进一步的深刻表现法,有扩大错综的意识,有为整个人类文明前途设想的情绪,其余的一切都得从别的立场上去讨论了。”[6](P.117)艾略特对于欧洲文明深有反思,忧心于人类发展的前途。一战后,诸多英法人士对德国予以责难并肆意瓜分德国利益,这成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休战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的重要原因。其实艾略特早已感叹道:“如果我们思考的只限于反对德国,那么我们不会走得比1918年更远。为了超越1918年,我们必须尽力对我们自己和德国持同样批评的态度。”[11](P.291)就此而言,鉴于对人类发展的关照,艾略特主张英法等欧洲国家要反思自身。虽然叶公超并没有具体甄别和详细考证艾略特作品中的世界主义元素,但是他体察到艾略特对于人类整体的忧虑和设想。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叶公超的这一评价是公正的,具有前瞻性的。就此而言,叶公超对比较文学持有浓厚的兴趣并非仅仅局限于西学中用,对于他来说,比较意识可以给学者提供一种借鉴,一种整体视野。这一见解在1934年发表的《从印象到评价》一文中有集中体现。他认为:“文学批评的范围自然就变成整个人类,或整个文明的批评了。因为惟有从整个文明的前途的眺望上,我们才可以了解生活中种种状况的意义。” [6](P.20)他主张文学批评涉及整个人类文明,坚信比较视野可以关注人类的整体。叶公超主张文学批评要超越个人的经验和意识,将文学批评的范围扩展到整个人类的批评,将文学批评定位在肩负整个人类文明的前途上。“批评家先要了解他自己的经验的意义,……当然,已往的经验是最主要的,不过已往的经验很容易给我们一种错觉,一种个人的色彩,或自身阶级的意识。这时候,文学批评的范围自然就变成整个人类,或整个文明的批评了。因为惟有从整个文明的前途的眺望上,我们才可以了解生活中种种状况的意义。所以历史上的大批评家大半都不免带着几分道德与训世的色彩。”[6](P.20)叶公超主张超越自我为中心,把“人类全体的文化”[12](P.90)看作一个整体,将本民族文化看作是人类全体文化中的一个元素而已。
叶公超对人类共同经验的注重还可以追溯到瑞恰慈、燕卜逊等剑桥学派。1924-1926年求学于剑桥的叶公超与他们的交往至深。1929-1930年瑞恰慈离开剑桥大学的教职,来到清华大学任教,与叶公超共事。在清华任教期间,瑞恰慈讲授《文学批评》课程,推动实用批评。他深感中国学生对西方文学的误读并非种族和智力所致,而是语言和传达的问题。这种见解超越了诸多西方人所持的东方主义偏见。正因为此,他自此花费毕生精力致力于建立和普及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以促进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叶公超准确把握瑞恰慈的思想。在为曹葆华翻译的《科学与诗》写就的序言中,叶公超指出:“ 瑞恰慈的目的,一方面是分析读者的反应,一方面是研究这些反应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他的抱负也是要用文学,尤其是诗,来保障人类的将来,因为他相信惟有好的艺术与文学作品才能给我们最丰富、最敏锐、最活泼、最美满的生活。我们的经验,不论是生活中的还是作品中所表现的,都应当受同样标准的评衡。”[6](P.147)在瑞恰慈的影响下,叶公超不仅在文学批评上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还在实践中积极推动跨文化的双向传播。叶公超非常赏识高徒卞之琳。诗人卞之琳的小说《红裤子》记载了山西八路军游击队抗击日寇的故事。叶公超将《红裤子》翻译成英文,转发给燕卜逊,发表在英国杂志《人生与文章》上。就此而言,叶公超向世界传达了勇敢顽强的中国形象。1937-1939年燕卜逊和叶公超一起在西南联大任教,叶公超曾无微不至照顾燕卜逊。在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期间,叶公超经燕卜逊引介,认识奥威尔。1943年9月20日应奥威尔邀请,给BBC录制了英语讲座“我希望的世界”(The World I hoped For)。
1929年叶公超任职清华大学,涵养于清华大学比较文学氛围。为此,他逐渐摒弃了早期对中国文化及文学的隔膜,从比较文学视角关照和反思中国新诗、小说等的发展,用比较文学的成果推动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叶公超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熟练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来丰富、补充、重估西方的英美文学研究成果。他以超越时空的平行研究,用外来资料来填充本土框架,增进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了解。他坚持中国架构,保留中国传统,同时极力在中西文学比较中保持公正态度。他将民族文学作为比较的基础,认为中国新诗和白话散文更多地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主张中国新文学除了借鉴西方文学技巧之外,更多地还需要借鉴中国古典文学。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学这个媒介,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才能更深入持久。比较文学是既保持民族文学特色又存在国际联络的文学批评。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